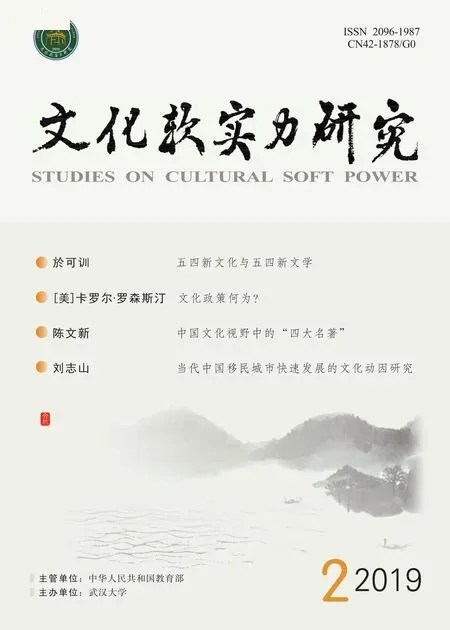中国文化视野中的“四大名著”
2019-12-26陈文新
陈文新
“四大名著”是《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的合称,其前身是“四大奇书”(《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与“四书”相对而言的“四大奇书”,具有鲜明的近世文化品格。
从历时态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经典以“五经”“四书”和“四大名著”最为重要,大体说来,“五经”经典地位的确立,标志着文化史上的中古时代正式开始。中国历史上的帝制时代始于秦始皇登基,帝制时代的前期常常被称为“中古时代”,其主体部分为秦汉至唐末。而就文化性质而言,汉武帝时期至盛唐才是典型的中古时代,其特征是,以“五经”为核心的儒学在帝国的政治秩序、文化秩序中居于主导地位。“四书”经典地位的确立,标志着文化史上的近世正式开始。帝制时代的后期常常被称为“近世”,其主体部分是宋元明清。而就文化性质而言,唐中叶至明中叶才是典型的近世,其特征是,以“四书”为核心的理学在帝国的政治秩序、文化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四大奇书”的崛起是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标志,而“四大名著”经典地位的确立则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化传统已渐趋成熟,这个新的文化传统是西学与中学相互冲突和融汇的产物。
从“五经”“四书”到“四大名著”,是一个经典更替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演进的过程。
一、从“五经”“四书”到“四大名著”
先秦时期已有“六经”之说,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由于《乐》经久已亡佚,汉武帝时期已习称“五经”。
“五经”经典地位的确立得益于官方的制度性支持,其中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是“五经”博士的设立和“太学”的兴办。如李泽厚《秦汉思想简议》所说:“进‘教化’,立官制,重文士,轻武夫;建构一个由‘孝悌’、读书出身和经由推荐、考核而构成的文官制度,作为专制皇权的行政支柱。这个有董仲舒参与、确立于汉代的政治—教育(‘士—官僚’)系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了解自秦汉以来中国历史的重大关键之一。”①《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在这个系统中,教育、举荐、考核人才的内容和标准,都以“五经”为主。
自西汉至盛唐,经典的数目有“七经”“九经”“十二经”等差异,但始终以“五经”为经典体系的核心。这一体系从中唐起才逐渐被以“四书”为主的经典体系所取代。这并不是说“五经”就不重要了,而是说“四书”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力更大。西汉大儒董仲舒教人以五经六艺为本,隋代大儒王通著《续六经》授徒讲学,唐太宗命孔颖达修《五经正义》,所看重的首先是“五经”。而中唐韩愈等人已注意到《孟子》《中庸》《大学》的重要性,开宋代理学之端,至宋代大儒如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等人,虽然学术主张不尽相同,但在论述为学次第时,都一致认可“四书”的优先地位。如朱熹所说:“《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2册》卷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8页。陆九渊提出为学首先应当“将《孟子·告子》一篇,及《论语》《中庸》《大学》中,切己分明易晓处,朝夕讽咏”③(宋)陆九渊著:《陆象山全集·卷四》,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37页。。张载在《经学理窟·义理》中也认为,研习经典有主有次,首先是《论语》《孟子》,其次才是《诗》《书》,最后才是《礼》,而《礼》经中应重视的是《中庸》和《大学》。④(宋)张载著,章锡琛点校:《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77页。吕思勉据此作了这样的概括:“唐中叶后新开之文化,固与宋当画为一期者也。”⑤吕思勉:《吕思勉史学论著·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6页。
“四书”取代“五经”,与应对外来思想的挑战有关。相较于儒学,盛行于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佛学,优长在于心性之学。对心性之学的深入拓展,使得佛学渐脱玄学苑囿,至隋唐而大张其道,士庶上下莫能逃其浸润。为了抗衡佛学异端,复兴儒家的文化传统,有必要对儒家经典重新加以诠释,即回溯儒学原典中的心性之说,深化儒学心性话语。韩愈重视《孟子》《中庸》,大力发挥孟子的“性善”学说,李翱标举《大学》《中庸》,在《复性书》中致力于分辨情性。中唐时期依托“四书”构建的儒学心性话语在宋代进一步完善,而在集大成者朱熹那里得到了完成。
宋代以后,“四书”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超过了“五经”。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恢复科举,规定第一场即从“四书”内出题,且只能依据朱熹的章句集注。明清时期,八股文成为最主要的考试文体。八股文别称“四书”文,就因为“四书”是八股文的核心题库。钱大昕注《日知录·科场》,有这样一句说明:“乡会试虽分三场,实止一场。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⑥(清)钱大昕著,陈文和、孙显军校点:《十驾斋养新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90页。
“四大奇书”是明代四部长篇章回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的合称。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这四部书就常被论小说者并列,在这个基础上,清初李渔明确提出了“四大奇书”的概念。他在为两衡堂刊本《三国志演义》所作的序中说:“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记》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为近是。”①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6页。
“四大奇书”这一术语,是比照“四书”而来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四大正书”,《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则是“四大奇书”,“正书”代表的是大传统,“奇书”代表的是小传统。
清代中叶,《红楼梦》问世,迅速取代了《金瓶梅》的地位。《金瓶梅》之所以为《红楼梦》所取代,原因有二:一是《金瓶梅》并不适合作为普及读物,尤其不适合青少年阅读。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四曾为《金瓶梅》一类作品划出了两个不同的流通范围,一是在士大夫文人如袁中郎、袁小修、马仲良等人中间流传,这些人阅读《金瓶梅》,属于名士风流,他们有足够的鉴赏水平,因而不会受到负面的影响;一是“悬之国门”,成为市井读物,其刻卖者“坏人心术”,应受到下地狱的惩罚②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0页。,因为普通读者不具备相应的鉴赏水平,有可能该领略的丝毫不能领略,却只关注那些意义不大却很有负面影响的地方。由此看来,《金瓶梅》这类小说的正当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流通范围的问题。严格限制其流通范围,则自有其不朽价值;倘若任其扩散,则确有可能败坏风俗,遗祸甚烈。而明清两代一再重复的事实是:一些出版商为了牟利,大量刻印这种作品,以至朝廷和社会舆论相当一致地赞成禁毁《金瓶梅》这类小说。二是《红楼梦》比《金瓶梅》的文化蕴含更为丰厚。《红楼梦》之前的人情小说,从审美品格来看,大体呈现为两种倾向,即以《金瓶梅》为代表的写实和才子佳人小说对诗意的追求。《金瓶梅》的写实拘泥于市井生活的呈现,只能容纳平凡粗俗、琐细卑微的人物,读来令人沉闷。而才子佳人小说的玫瑰色诗意却又靠牺牲写实得来,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说基本上是失败的记录。《红楼梦》的卓越之处在于:将《金瓶梅》的写实和才子佳人小说对诗意的追求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具有一种宇宙般的深邃感,从贾宝玉到薛蟠,从妙玉到多姑娘,从贾元春到刘姥姥,从林黛玉到王熙凤,既有中国古典诗词(如李商隐、李贺、姜夔的作品)、戏曲(如《牡丹亭》《桃花扇》)的感伤、凄丽,又包含了市井文艺(如《金瓶梅》《三言》《二拍》)的泼辣、直白。它是一部为现实而写、也为未来而写的伟大作品。
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鲁迅等意气风发的新文化人,致力于确立《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在主流文化中的经典地位。20世纪50年代,在整理出版传统文化经典的过程中,《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获得了“四大名著”这一并称,在国民教育中的重要性也日渐凸显。1996年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附有“课外阅读书目”,1999年新课程改革启动,其后颁布的语文新课程标准中有“建议性课外读物书目”,在这些书目中,“四大名著”的分量越来越大。其中,《三国志演义》是历史演义的代表作,《水浒传》是英雄传奇的代表作,《西游记》是神魔小说的代表作,《红楼梦》是人情小说(或世情小说)的代表作。
“四大名著”的经典地位获得了广泛认可。20世纪初至今,无论是在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新文化运动”的视野中,还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大陆地区文化界,甚至在当今深受西方学术传统浸润的欧美汉学家那里,都一致认可四大名著的经典地位。如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所说,“的确,从过去40年间学术界在这几本书上所下的惊人工夫来看,似乎就是它们构成了中国小说的传统。现在,不仅中国学者,就连西方的汉学家,对有关它们的作者以及版本方面的最细微的问题,也都以极为严肃的态度来探讨”①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四大名著”享誉中外,其传播日渐广泛。英文译本、法文译本、俄文译本、捷克文译本、罗马尼亚文译本、波兰文译本、越南文译本、朝鲜文译本、日文译本……遍布海外各地。以“四大名著”为研究对象的海外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学术专著以及期刊论文,更是不胜枚举。“四大名著”因为无数读者的阅读,而获得了永不衰竭的活力。
二、“四大名著”的近世文化品格
唐中叶以降的历史、文化发展历程中,有个事实极为重要,那就是门阀贵族势力的衰落和科举出身的平民士人的崛起。陈寅恪注意到,唐代出生于士族的政治人物,如李德裕,与出身于寒门、经由科举考试而登上历史舞台的政治人物,如牛僧孺,有一个显著区别,即李德裕尚“礼法”,而牛僧孺等则“尚才华而不尚礼法”。②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6页。这一区别延伸到宋元明清时期,形成了礼法相对松弛的局面。有意味的是,有一部作品,既与唐代有关,又与金元有关,还与清代有关,正好用作考察这一变迁的案例。这个作品就是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又称《会真记》)。在金元时期,它化身为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在清代,《西厢记》杂剧进入《红楼梦》中,成为宝黛共读的爱情启蒙读物。在这个不断分身的过程中,男女感情与礼教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折射出了不同的社会文化形态。
戏曲史上有这样一个现象:许多取材于唐人传奇或唐人诗文的元代杂剧其结局都变悲剧为团圆,比如,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元代白朴的《墙头马上》杂剧,源于唐代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井底引银瓶》,《莺莺传》和《井底引银瓶》都以悲剧结束,而《西厢记》和《墙头马上》则是大团圆的喜剧。在这种不谋而合的共同现象背后,深层的原因何在?
答案其实就在“文化的平民化转向”。元稹《莺莺传》从两个方面对崔莺莺作了重点刻画。其一,她在追求爱情时极为矜持。《莺莺传》赋予莺莺的是名门闺秀的身份:一个上流社会的少女。传奇由此出发,着力写她举止端庄、沉默寡言的闺秀风范,生怕有失名门闺秀的身份。其二,她没有勇气维护自己的婚姻权利。在预感张生有可能“始乱终弃”时,她不是想法阻止这一结局的到来,反倒说这一结局并不出人意外。她这样向张生倾诉:“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帻。”③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37、138页。这都是说,假如张生抛弃了她,也在情理之中。
元稹《莺莺传》这样描写崔莺莺,遵循的是唐代士族社会的婚姻法。按照这种婚姻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两个必备条件,一个私定终身的女子是没有资格成为妻子的。即白居易《井底引银瓶》所说:“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蘋蘩。”①(唐)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5页。白居易笔下的这位女子终于未能成为正式的妻子,而崔莺莺则是另择配偶。作为士族社会的一员,她们不可能越过婚姻法的障碍。
但士族社会的婚姻法在平民社会中并不一定需要遵守,即所谓“礼不下庶人”②(元)陈澔注,金晓东校点:《礼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所以,到了宋代,就有了一篇代表平民意志、针对元稹《莺莺传》而写的传奇小说《张浩》,它的男主角叫张浩,女主角叫李莺莺。李莺莺和崔莺莺的不同是:其一,她主动与张浩私定终身,没有丝毫扭捏;其二,她勇于维护自己的婚姻权利,不惜运用自杀、起诉等异常手段,最终与张浩喜结连理。这是平民社会的婚姻伦理。正是在这种平民文化兴盛的背景下,《西厢记》《墙头马上》等元代杂剧不约而同地改变了女主角追求爱情的行为方式或悲剧结局。《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迥异于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中的弱女子。她主动约少俊来家中的后花园私会,当他们的幽会被嬷嬷撞破时,一口承认是自己的主意,并非侍女引逗。她在作出私奔的决定时毫不犹豫。而《西厢记》最后一折的[清江引]曲,其“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③(元)王实甫著,(清)金圣叹评点,李保民点校:《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99页。一句,更是平民社会的宣言。
《红楼梦》的核心关目之一是宝玉和黛玉的爱情,而“共读《西厢》”则是他们进入爱情生活的标志。宝玉和黛玉等人是何时住进大观园的?是在第二十三回。而第二十三回,其主体内容即“《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西厢记》和《牡丹亭》,这是中国古代最为经典的爱情剧。《红楼梦》采用互文见义的方式,写宝、黛以阅读和聆听这两部爱情名剧开始他们在大观园中的生活,这样的情节安排,究竟有何深意?
这一情节安排告诉读者:宝玉和黛玉的爱情违反了士族社会的婚姻法,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作为他们婚姻的保障。许多读者对于黛玉的忧郁性格感到惊讶:年纪轻轻,又生活在如此优裕的环境中,何以常常有一种无处倾诉的强烈的忧郁和孤独感?比如,第二十六回,黛玉因晴雯的一句气话便又思忖起自己的身世处境来,“越想越觉伤感,便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不仅这心思,就连这哭声亦非常人所有,“那些附近的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一闻此声,具‘忒楞楞’飞起远避,不忍再听”。④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312、313页。这般情景在黛玉那里再寻常不过了,“埋香冢飞燕泣残红”“风雨夕闷制风雨词”,所传达的总是一种与孤独感相伴随的凄美和悲凉。如黛玉的《咏菊》诗所说:“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⑤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466页。
黛玉的这种忧郁性格其实是不难理解的。与宝玉的爱情几乎就是黛玉生活的全部,而她的爱情又是没有保障的。不仅没有保障,还有可能使她遭到周围人的鄙薄和厌弃,甚至连贾母也可能厌弃她。《孟子·滕文公下》有云:“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⑥(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48页。事实也正是如此。第九十七回,贾母针对黛玉和宝玉的私情说了这样两段话:“孩子们从小儿在一处儿玩,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该要分别些,才是做女孩儿的本分,我才心里疼他。若是他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你们说了,我倒有些不放心。”“我方才看他却还不至糊涂。这个理我就不明白了!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就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①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258页。贾母说的“这个病”,就是“私定终身”,就是违反了礼法。在贾府里面,黛玉最亲的长辈只有贾政和贾母。贾政是她母亲的同胞兄弟,贾母是她的亲外祖母。贾政是不管家里事情的,只有贾母还可以仰仗。而因为没有遵循礼法,连贾母也厌弃黛玉,其他人更可想而知了。
在《红楼梦》中,《西厢记》又被称为《会真记》,而《会真记》是元稹《莺莺传》的别名,并不是《西厢记》的别名。这里,《红楼梦》并不是疏忽所致,而是有意识地提醒读者留意《红楼梦》与《莺莺传》的关联。其关联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其一,《莺莺传》和《红楼梦》所写的两对情侣,张生和莺莺、宝玉和黛玉,都以悲剧结局,而原因是一样的,即男女当事人违背了礼法。其二,《莺莺传》和《红楼梦》,在相同之外却有一个巨大的差异:《莺莺传》是认同礼法的,至少表面上是认同礼法的;而《红楼梦》却并不认同礼法。这里试就两者的这一差异多说几句。
《莺莺传》的男主角张生在与莺莺热恋了一段时间后,决定断绝来往。他不仅没有羞愧之意,而且在说出这个决定时理直气壮。他的理由是:“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②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39页。这些话出自元稹的代言人——张生之口,与白居易新乐府《李夫人》所说“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③(唐)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3页。,《古冢狐》所说“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④(唐)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8页。,旨趣相同或相近。这样一种议论,虽然带有游戏意味,但从字面或表面看,《莺莺传》对于违背礼法的莺莺,确乎是鄙薄或不屑的。
《红楼梦》的态度与《莺莺传》形成鲜明对照,或者说,宝玉对于黛玉的态度,迥异于张生之于莺莺。宝玉对黛玉的爱情,一方面是对黛玉身上所体现的“美”的爱,另一方面也是寻求生存意义的努力,是他对抗现实世界的精神支点。由于他已悟出“人生情缘,各有分定”⑤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441页。,因而格外珍视会为他洒泪的林黛玉的那份深情。他对金玉良缘的抗拒从这个角度才能获得理解。毫无疑问,作为妻子,宝钗几乎是无可挑剔的。然而,尽管娶了这样一个贤妻,宝玉依然对人生充满了遗憾。《红楼梦曲》第二支《终身误》以宝玉的口气感叹道:“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⑥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61页。所谓“齐眉举案”,用的是汉代梁鸿与孟光夫妇相敬如宾的典故,在《红楼梦》里是指宝钗与宝玉相互敬重,夫妻关系和谐。所谓“美中不足”,并非说宝钗不值得尊重,而是说宝玉和宝钗的婚姻尽管美满,但失去了黛玉,毕竟是人生中无从弥补之憾。其中并不包含对宝钗的贬抑,只是表达了一种不能舍弃黛玉的铭心刻骨的伤感。何以如此?原因在于,黛玉与宝玉心心相印,亲密无间,是宝玉感情世界的知音。宝玉这个惊世骇俗的价值判断,体现了鲜明的平民文化品格。
这里可以提到清初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的一段话了:
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①(清)刘献廷著,汪北平、夏志和点校:《广阳杂记》,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06~107页。
刘献廷的议论透露出三个重要信息:一是主张要在小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经典,二是确认小说戏曲才能代表他所处的时代的文化,三是强调新的文化经典的确立要“原本人情”。“原本人情”是近世文化的重要内容,而《红楼梦》对宝黛爱情的认同,则是对“原本人情”的升华,是近世文化品格的一个重要表现。
三、“四大名著”的现代文化意义管窥
中国传统社会的五伦,父子、夫妻、兄弟直接与家庭有关,而君臣一伦是比照父子一伦而提出的,朋友一伦是比照兄弟一伦而提出的,所以,家庭伦理实为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之所以如此重视家庭,是因为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要考察“四大名著”的现代文化意义,从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切入,是一个较好的角度。
在“四大奇书”中,《三国志演义》由于关注的重心是庙堂和战场,对家庭着墨不多;《水浒传》写豪侠闯荡江湖,家庭是一个应该挣脱的羁绊;《西游记》写的是佛教高僧的取经生涯,也不会留意家庭;所以,这三部名著淡化家庭的做法,并不表明作品否定家庭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从《水浒传》到《金瓶梅》,家庭之于个人,明显占据了主导地位。
《金瓶梅》的开头几回借用了《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故事。《水浒传》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回集中描写了西门庆、潘金莲、武大郎、武松等人之间的纠葛,其题材虽属公案性质,但因其具有浓郁的市井生活气息,已与人情小说相通。容与堂本《水浒传》第二十四回回末评语曰:
李生曰:说淫妇便像个淫妇,说烈汉便像个烈汉,说呆子便像个呆子,说马泊六便像个马泊六,说小猴子便像个小猴子,但觉读一过,分明淫妇、烈汉、呆子、马泊六、小猴子光景在眼,淫妇、烈汉、呆子、马泊六、小猴子声音在耳,不知有所谓语言文字也。何物文人,有此肺肠,有此手眼!若令天地间无此等文字,天地亦寂寞了也。不知太史公堪作此衙官否?②(元)施耐庵,(明)罗贯中著;凌赓等校点:《容与堂本水浒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页。
容与堂评语所说的淫妇、马泊六之类,都是市井生活中的常见人物。其实《水浒传》与世态人情有关的描写尚不止这几回,第十七回何涛、何清之间的口角,第二十一回宋江与阎婆、阎婆惜之间的纠纷,都是绝好的市井常谈、闺中琐语。由这一类情形看来,《金瓶梅》与《水浒传》之间确有不容忽略的血缘关系。
不过,《水浒传》与《金瓶梅》毕竟不是同一类型的小说。前者站在豪侠的立场上写世态人情,后者站在常人的立场上写世态人情,眼光不同,对有关题材的处理显然有别。就本文的论题而言,尤为重要的是对武松社会关系的改变。《水浒传》倾向于让好汉们摆脱家庭束缚,鲁智深、石秀等在小说中几乎没有直系亲属;如果不是为了写武松的复仇壮举,可以断言不会有武大这个人物。但《金瓶梅》却倾向于让人物接受家庭生活的考验。在《水浒传》中,迎儿是武大家里的小婢,《金瓶梅》却让她成了武大的女儿(武大前妻所生),即武松的亲侄女。做这样的改动,目的是将武松置于家庭伦理的约束之下。迎儿的父亲是武大,武大去世之后,她的生活与前途理当由武松来照料。如果武松真的爱他的兄长,他就应该对兄长的女儿尽到责任。然而他没有,只顾杀人,在生剐了潘金莲之后,又割下王婆的头,还打算到隔壁王家去杀王婆的儿子王潮儿。那时已是初更时分,武松却把迎儿一个人倒扣在屋里(按:即凶杀现场)。迎儿道:“叔叔,我也害怕。”武松道:“孩儿,我顾不得你了。”①秦修容整理:《金瓶梅:会评会校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291页。武松没有找到王潮儿,遂席卷王婆的财物,奔向梁山。至于迎儿是否会成为街头的饿莩,或是流落青楼,武松是不在意的。《金瓶梅》借此表明,武松这种没有家庭责任感的好汉不值得钦佩。
较之《金瓶梅》,《红楼梦》中的家庭或家族,在面对个人时具有更大的权威性。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贾宝玉一生下来,他的人生道路就因为家族的需要而被确定了:他必须做官。他生下来口里就含着一块玉,大有“命中注定”的意味。身为荣国府的公子,他享受了这个家族给他的荣华富贵,也有责任为家族荣华富贵的延续尽责。第三十二回,湘云对宝玉说:“如今大了,你就不愿意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会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谈讲谈讲那些仕途经济,也好将来应酬事务,日后也有个正经朋友。让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的出些什么来?”②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387页。湘云说这些话,其不言自明的前提是:只有做官才是宝玉正当的人生选择。如果追问一句:宝玉何以必须做官?答案是:这是家族交给他的使命,一个不容拒绝的使命。
对于社会生活中的人来说,做官或者不做官,并无绝对的好坏之分。适合做官的就去做官,不适合做官的也不必强求。而就宝玉而言,他既没有兴趣做官,也没有能力做官,可以断言,做官对他并不合适。第三十回这样写道:“话说贾母自王夫人处回来,见宝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欢喜,因怕将来贾政又叫他,遂命人将贾政的亲随小厮头儿唤来,吩咐:‘以后倘有会人待客诸样的事,你老爷要叫宝玉,你不用上来传话,就回他说我说的:一则打重了,得着实将养几个月才走得;二则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见外人,过了八月,才许出二门。’那小厮头儿听了,领命而去。贾母又命李嬷嬷袭人等来将此话说与宝玉,使他放心。那宝玉素日本就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今日得了这句话,越发得意了,不但将亲戚朋友一概杜绝了,而且连家庭中晨昏定省,一发都随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园中游玩坐卧,不过每日一清早到贾母王夫人处走走就回来了。却每日甘心为诸丫头充役,倒也得十分闲消日月。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劝导,反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子,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意造言,原为引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了!’众人见他如此,也都不向他说正经话了。独有黛玉自幼儿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所以深敬黛玉。”①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431页。这样一个宝玉,却因为家族的意志而必须做官,确乎是一件难堪的事。
不适合做官的宝玉,在文学艺术方面却极有天分。第十七回,他所题的那些匾额、对联,他就这些匾额、对联所发的议论,都着实令他的父亲贾政感到得意。有这样一个天分卓异的儿子,贾政是真的开心。所以,当宝玉退下来时,刚到院外,就有跟贾政的小厮上来抱住,说道:“今日亏了老爷喜欢,方才老太太打发人出来问了几遍,我们回说喜欢;要不然,老太太叫你进去了,就不得展才了。人人都说你才那些诗比众人都强,今儿得了彩头,该赏我们了。”②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99页。宝玉在文学方面的天分有目共睹。
宝玉的学养也不同寻常。“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行人来到后来被命名为蘅芜苑的所在,看去“一树花木也无,只见许多异草:或有牵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岭,或穿石脚,甚至垂檐绕柱,萦砌盘阶,或如翠带飘飖,或如金绳蟠屈,或实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香气馥,非凡花之可比。贾政不禁道:‘有趣!只是不大认识。’有的说:‘是薜荔藤萝。’贾政道:‘薜荔藤萝那得如此异香?’宝玉道:‘果然不是。这众草之中也有藤萝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芜,那一种大约是茝兰,这一种大约是金葛,那一种是金䔲草,这一种是玉蕗藤,红的自然是紫芸,绿的定是青芷。想来《离骚》《文选》所有的那些异草:也有叫作什么霍纳姜汇的,也有叫作什么纶组紫绛的,还有什么石帆、清松、扶留等样的,见于左太冲《吴都赋》。又有叫作什么绿荑的,还有什么丹椒、蘼芜、风莲,见于《蜀都赋》。如今年深岁改,人不能识,故皆象形夺名,渐渐的唤差了,也是有的……’”③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95页。
梁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是一部选录集部作品的总集。其选录对象除诗之外,主要是辞藻华丽、声律和谐的楚辞、汉赋和六朝骈文。他在《文选序》中谈到选编原则时说:《文选》不选经书和子书,是因为经、子“以立意为宗”,旨在阐发作者的见解,而“不以能文为本”;不选史书,是因为“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史书经由对史实的记述表达作者的历史观和是非原则,仍以见识为骨。纯文学的特征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④(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页。,即注重辞采之美。隋唐以降的诗文作家,无不以精通《文选》为首务。而宝玉对于《文选》的精熟程度,假如要与杜甫、苏轼比较,怕也逊色不了多少。
宝玉还是一个出色的书法家。第二十六回,薛蟠的生日快到了,他问宝玉:“可是呢,你明儿来拜寿,打算送什么新鲜物儿?”宝玉道:“我没有什么送的。若论银钱吃穿等类的东西,究竟还不是我的;惟有写一张字,或画一张画,这才是我的。”⑤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309页。这是写宝玉的自信。第二十九回,张道士告诉贾母:“前日我在好几处看见哥儿写的字,做的诗,都好的了不得。怎么老爷还抱怨说哥儿不大喜欢念书呢?依小道看来,也就罢了。”①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348页。这是外界对宝玉书画的评价。而宝玉本人,也对书法绘画充满了兴趣。第二十三回写他“不说宝玉闲吟,且说这几首诗,当时有一等势利人,见是荣国府十二三岁的公子作的,抄录出来,各处称颂;再有一等轻薄子弟,爱上那风流妖艳之句,也写在扇头壁上,不时吟哦赏赞:因此竟有人来寻诗觅字,倩画求题,这宝玉一发得了意,每日家作这些外务”。②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68~269页。
这样看来,如果宝玉可以根据自己的擅长和兴趣选择人生道路,他绝不是一个平庸的人。可是他没有这个权利。宝玉的尴尬,验证了清中叶郑夑(板桥)《南朝》诗序中的一段话:“昔人谓陈后主、隋炀帝作翰林,自是当家本色;燮亦谓杜牧之、温飞卿为天子,亦足破国亡身。乃有幸而为才人,不幸而有天位者,其遇不遇,不在寻常眼孔中也。”③(清)郑板桥:《郑板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8页。或如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三第二五则所说:“宋太祖曰:‘李煜好个翰林学士,可惜无才作人主耳!’秀才郭麐《南唐杂咏》云:‘我思昧昧最神伤,予季归来更断肠。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④(清)袁枚著,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37页。
这里试以陈后主为参照作进一步的讨论。
陈后主在史家眼里是一个以不理朝政著称的帝王。身为帝王,却不理朝政,这种定案足以使陈后主成为被讽刺的对象,而他所作的《玉树后庭花》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亡国之曲,即杜牧《泊秦淮》诗所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⑤(唐)杜牧撰,吴在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56页。。但是史家的看法只是就某一层面、从某一角度立论,如果换一个层面、换一个角度,结论会显然不同。明末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其《陈后主集题辞》便更为公允,更见深度。他以为:
史称后主标德储宫,继业允望,遵故典,弘六艺,金马石渠,稽古云集,梯山航海,朝贡岁至,辞虽夸诩,审其平日,固与郁林、东昏殊趋矣。临春三阁,遍居丽人,奇树夭花,往来相望,学士狎客,主盟文坛,新诗方奏,千女学歌,辞采风流,官家未有。⑥(明)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60页。
所谓“史”,指《陈书·后主纪》。张溥据以认定,陈后主的不幸在于他是国君:
使后主生当太平,次为诸王,步竟陵之文藻,贱临川之黩货,开馆读书,不失令誉。即假列通侯世阀,鱼弘羊侃数辈,亦扫门不及。乃系以大宝,困之万几,岂所堪乎?鹤不能亡国,而国君不可好鹤,后主盖与卫懿公同类而悲矣。⑦(明)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60页。
陈后主这种角色上的错位,造成了其人生悲剧。而需要追问一句的是,这种角色上的错位是谁造成的?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不止涉及陈后主,也涉及《红楼梦》中的宝玉。贾宝玉,一个具有卓越的文学艺术天赋的人,一个可以在艺术的世界中陶然如醉的人,何以不能自主选择人生道路,而必须顺应家族的意志?《红楼梦》写出了贾宝玉的悲剧,因而具有了不同寻常的现代文化意义。它引导我们反思传统社会的体制,以及支撑这种体制的思想文化。
正如西方民族国家意识的萌生,伴随的是各国民族文学的兴起,意大利有但丁,英国有乔叟,中国也要在西学东渐时代建立民族的文学与文化。“四大名著”之所以成为现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就因为其中包含着与现代文化相契合的思想因子,承载着人类关于理想社会的追求。本文从家族与个人关系的角度对《红楼梦》所做的考察,旨在以小见大,对“四大名著”现代文化意义略作管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