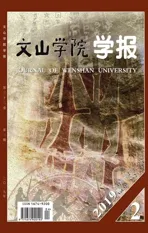浅析凌力历史小说《少年天子》的新历史主义特色
2019-12-26郑逸群
郑逸群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新历史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对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对文本的纯结构形式进行封闭式研究的反驳,主张恢复历史维度,重视文化研究。因此,不同于以往的史学观念,首先,新历史主义更加关注历史的客观性问题,即“历史不是传统历史主义所认为的完全的客观的历史,而是被叙述的过去的故事”[1];其次,注重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即强调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再次,注重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即主张在文本分析时倾向于“文化诗学”,要探讨“文学文本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文本中的社会存在”两大问题。
凌力的长篇历史小说《少年天子》是一部描写清朝入关后第一代皇帝顺治(爱新觉罗·福临)政治生涯与爱情生活的佳作,曾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全书主要围绕两条主线来展开故事情节,其一是顺治帝福临与其心爱的董鄂妃、孝庄太后、简亲王济度、安亲王岳乐、大学士傅以渐等贵族士大夫阶级的故事,分别描写了朝廷、宗室与后宫这三个方面;其二主要以唱戏的柳同春兄弟,佃户乔家母女同反清复明势力的种种纠缠,这条线索为我们展开了清代中下层百姓的生活图景。该书的作者凌力始终把人放于第一位,正如她自己认为:文学的本意乃是人学。因此在《少年天子》创作过程中,她主观上把人作为创作中心。本文将从三方面来分析这部小说的新历史主义特色。
一、历史轶闻主义下的碎片化处理
轶闻概念在历史学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它往往作为道听途说的野史、秘史、稗史,充当着正史的补充或反叛的配角,因此轶闻的方式一直被史学界所摒弃与诟病,但是新历史主义的兴趣点却在这些轶闻上。在此,日记、回忆录、传记成为了文本构建的重要来源。
纵观全书,作者在描写明清革鼎之际的历史态势时,其着眼点并非是许多气势恢宏的历史性事件,作者善于通过以小见大的手法来突出历史事件对普通百姓的影响并使读者加深对这一事件的理解。比如在处理清初圈地和逃人法这些著名的历史事件时,作者的笔触并未触及那些功勋卓著的王公贵族,而是用了一个贫苦低微的老汉的口吻来讲述圈地和逃人法对平民百姓的沉重压迫,并且文学中常用的巧合在此也发挥了功用。老汉不幸的遭遇,先是土地被当地都统圈走,接下来几个儿子由于严苛的逃人法而纷纷丧命,在他人生最低谷时,却有幸遇见两位贵人,一位是饱读诗书、一腔正义,日后荣升至翰林院的熊赐履,另一位居然是微服出巡的圣上。这样的巧合不仅使老汉的难题迎刃而解,而且也使年轻的顺治帝在为国家选贤举能这一大事上有了更深的理解,像熊赐履这样胸怀天下、惜老怜贫的文士方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凌力在处理简亲王济度因不满朝廷汉化、蓄意谋反这一事件上则用了双重“以小见大”的手法,这些导火索在正史记载中几乎难觅,但是用于一部历史小说则显得恰到好处。首先,济度便衣出府视察民情时偶遇两位前朝宰辅的后人,他们衣着简陋,为着琐碎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而烦忧。济度目睹了整件事情的经过,感触颇深,这件事更加深了他对“百无一用是书生”这种观念的看法。济度作为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的核心成员,其父郑亲王济尔哈朗是顺治帝忠心耿耿的叔王,在这样显赫的身份下,济度匡扶报国的想法便时刻萦绕心头,他无法眼见满廷汉化,汉官备受重用,他狭窄地认为一旦这样下去自己的子孙终有一日也会狼狈地流落街头;其次,简亲王府和佟家最大的靠山康妃无意触怒龙颜并惹来杀身之祸,这一点也使济度颇为不满,济度无法理解为何圣上冷落那些血统高贵的满族妃嫔,而对有一半汉族血统的董鄂妃情有独钟。这些导火索最终成为济度蓄意谋反的原因,作者这些“碎片化”的笔触使得历史情节活灵活现地展示在读者眼前。
除了借用“以小见大”的手法来建构碎片化的历史情境之外,参照历史名人的回忆录也是新历史主义鼓励采取的方法。在《少年天子》一书中有一位人物的出现不容忽视,即钦天鉴汤若望。汤若望并非中国人,他是一位受朝廷器重的西洋传教士,因为传播天主教教义有了声望,故留在朝中任职。他和顺治皇帝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每当年轻的帝王遇到什么难以释怀的事情时,总会向他倾吐衷肠。由于汤若望与顺治帝的密友关系,故而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对年轻帝王和董鄂妃之间的爱情佳话有诸多描绘。回忆录中不仅有关于董鄂妃曾经婚恋史的隐晦记载,还有关于她香消玉殒后,顺治帝哀痛不已的详细记录。
以上回忆录中的记载在这部小说里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这些碎片化的历史事实几乎很难一瞥于正史记载,在《清史稿选译》中《世祖本纪》一章中提到董鄂妃的地方仅有两句话,分别是“十二月已卯,册内大臣鄂硕女董鄂氏为皇贵妃,颁恩赦”和“八月……壬寅,皇贵妃董鄂氏薨,辍朝五日。甲辰,追封董鄂氏为皇后”。[2]当我们将正史记载与汤若望的回忆录结合起来审视这位17世纪的大清后妃时,不难发现虽然正史在极力回避这段帝王绝恋,但从祖制和时间上仍可以看出许多端倪。首先,颁布大赦令和辍朝是只有册封皇后和帝后去世后才能尊享的殊荣,后妃无权享用,顺治为董鄂氏开启的特权足以见一代帝王的痴情不渝;其次,董鄂妃卒于顺治十七年八月,仅仅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十八年正月顺治也于养心殿驾崩。在这半年的时光中,除却皇家那套声势浩荡的葬礼,所剩日子俨然不多,顺治再也无心治国理政,不久便因巨大的悲痛而撒手人寰。这些微小的历史碎片于正史无益,但却于文学有功,凌力细心地搜集起这些正史夹缝中的碎片并将它们重新拼贴、整合,于是一部饱含着深厚人文情怀的历史诗学文本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二、历史事件中小人物命运的发掘
在以往的正史记载中,我们的关注点总是集中在领袖、将军等各类领导人身上,那些平民百姓在正史中基本上处于失语的状态,他们不仅没有话语权,而且几乎不值一提。但是新历史主义借助“颠覆”与“抑制”的文艺功能来赋予他们话语权。所谓颠覆与抑制的文艺功能,在文学作品中常有三种具体的实现方式,即“实验”“记录”和“解释”。“实验”是指通过揭示边缘群体意识上的荒诞和虚妄,来暗示主流文化自身在信仰、意识等各个层面的相似性,这属于抑制中的颠覆;“记录”指文艺作品在记录主流意识形态并美化其存在时,也会记录下种种边缘和底层的声音,这些底层的对抗性话语意在促使观众接受当时的权力结构,这属于颠覆中的抑制;“解释”指当主导权力发现自身的局限性时,会通过解释来修复自身的权威,这属于抑制中的颠覆。笔者认为,在《少年天子》这部书中主要运用了该文艺功能中的前两者“实验”和“记录”。“实验”体现在作者将唱戏的柳同春与乔梦姑的爱情描写与顺治、董鄂妃的互相辉映上;“记录”则体现在民间朱三太子朱慈炤的冷酷残暴与顺治帝的勤政爱民方面。
柳同春兄弟以及乔家母女是凌力笔下塑造的非常成功的一类人物。柳同春和柳同秋早年拜于柳师傅门下学戏,后来由于清政府开始圈地,柳师傅失去了大片土地并陷入了贫困的状态,无奈之下他只好将两个徒弟抵押给戏园以此换取微薄的收入。数年之后,同春与同秋成为京师梨园的名角。同春自幼在马兰村长大,和同村的乔梦姑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原先打算通过唱戏攒下些钱后迎娶梦姑,谁料梦姑的母亲嫌弃同春的戏子身份,将女儿嫁给藏匿在道观中的朱三太子朱慈炤,乔氏的想法极其荒谬,她以为朱慈炤和白衣道人这些乌合之众能够匡扶明朝宗室,这样一来其女梦姑便可以成为王妃。梦姑的不幸远远不止是嫁给自己不爱的人,更严重的是朱慈炤色厉内荏、喜怒无常,她常常成为丈夫政治失意的出气筒,而乔氏和儿子乔柏年又沉浸在荣华富贵的幻梦中无法自拔,因此梦姑仿佛生活在无尽深渊之中。柳同春未能迎娶梦姑后,决心脱离梨园身份,做一个清白且自食其力的人,他来到科举监考官李振邺门下,成为一名随侍的书童。在李振邺府上,同春目睹到许多官场的黑暗现象和人世间丑陋的一面,譬如李振邺以权谋私,利用监考官的身份在顺天科举上大售“关节”(即考试作弊时考生和改卷人员事先约定好的记号);李振邺的门生张汉和其勾心斗角的种种丑事等等。后来一切东窗事发,朱慈炤和白衣道人难逃一死,乔家女眷则被发配为奴;顺天科场舞弊一事经人举报,李振邺等人自是难逃法网,不久斩首示众。可以说,作者通过她笔下的两个虚构人物柳同春和乔梦姑,将清初许多历史事件串联了起来,这其中包括圈地法、逃人法、朱三太子谋逆案以及顺天科场案等。
同春和梦姑这一对作者虚构的恋人不同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顺治和董鄂妃,他们虽为虚构,却是清初成千上万个青年汉族男女的缩影。首先,清世祖入关初期,天下虽基本稳定,人民在饱经战乱之后也渴望过安居乐业的太平日子,但四海之内总有些蠢蠢欲动的势力在此起彼伏,譬如偏安一隅的南明王朝、福建郑成功,还有散落在民间的一些草寇盗匪等,这使得百姓的境遇无法完全安定;其次,满清入主中原,这对于天下占绝大多数的汉民及文士来说虽难言屈辱,但也是江山易主的悲剧。风俗习惯的变迁、社会阶级的流动使汉民的心理产生了许多变化。同春和梦姑皆是在历史大环境下难以为自己命运做主的典型代表,同春虽自食其力但无奈身份低微,梦姑虽温柔善良却遇人不淑。尽管知道梦姑被发配为奴后,同春决心重操梨园行当,试图在各类府邸找到梦姑,救她脱离苦海,但结局两人虽近在咫尺,却再难重逢。相较之社会中下层的同春和梦姑,顺治帝和董鄂妃似乎是高高在上的,一个是君临天下的帝王,一个是才貌双全的宫妃,但是即便如此两人的命运也难以自我掌控。作为入关后的第一代君王,顺治帝深谙“既以马上得天下,万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他通读历代汉文化典籍、改内院为内阁、设立翰林院、重用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汉臣如傅以渐、王熙等、严厉处置科场舞弊案、暂缓实行逃人法等。但是顺治在政治上的“文德绥怀”与个人情感上所追求的“情投意合”,在一些愚昧无知的满族大臣眼中却成为了亲汉疏满、违背祖制的离经叛道行为。董鄂妃来到志趣相投的爱人身边,也并不意味着从此你侬我侬、高枕无忧,相反她获得爱情的幸福是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在“一入宫门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的后宫中,上有皇太后、太妃需要恭敬侍养,中有若干后妃需要团结和睦,下有宫女内监需要调教,董鄂妃的幸福几乎是建立在如履薄冰之上,即便她的父亲、弟弟和年幼的四皇子相继过世,她都不愿也不能流露出过多的悲戚。于后妃而言,她是不幸的;但是于妻子而言,她又是那么地幸运,那些琴棋书画使得她与丈夫顺治帝有说不完的话,有太多的默契与共鸣。
三、历史背景下的诗学意境
新历史主义之“新”主要在于它对历史有别于传统的理解。海登·怀特提出了“元历史”概念,蒙特洛斯提出了“历史的文本性”概念,目的都在于解构历史的实体性与客观性,力图恢复历史的虚构化和诗意化本质,甚至明确主张历史也是一种诗意文本。众所周知,在叙述客观的历史事件时,历史将不可避免地带有史学家对事件的主观阐释,或者为填平历史事件之间的鸿沟而加入的想象与虚构。就历史记载的叙述而言,读者也更倾向于那种富有文采、富有传奇性色彩的历史叙述方式,因此譬如司马迁的《史记》,人们不仅公认为是史学界的经典,更将它视作文学佳作,鲁迅更是盛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正是历史与文学完美融合的上乘之作。
在《少年天子》这部将近5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中,作者凌力运用她独特的女性视角与细腻温婉的女性情怀将历史中许多空白环节填补进诗意的篇章,她善于捕捉文学人物的心理动向、善于营造充满诗意气息的外部氛围、善于将一些趣闻轶事和历史典故合情合理地插入历史事件之中。除此以外,一些诗词曲赋的适当渲染也增添了历史小说的文采与可读性。小说第三章描写顺治帝在太后寿宴上初次邂逅董鄂氏时,便运用了大篇幅的心理描写来描绘顺治对董鄂氏从内到外的赞赏与爱慕。后来曲终人散,碍于宫规和层层束缚,顺治难以再见到本是他弟妹的董鄂氏,他回到养心殿不由身心惆怅,暗叹命运弄人。这里凌力借用周围景物和一支曲子将年轻帝王的情思呈现了出来:
黄昏时分,皇城的宫殿在暮霞的背景上渐渐变成深色的剪影,寂静的宫廷透露出一股无法言喻的忧郁和惆怅。初夏温馨的空气也不能减轻伤心人的痛苦。追随着宛转的歌声,从养心殿中送出阵阵悠扬的丝竹之音,那拖得长长的音调如泣如诉,更增加了暮夜的缠绵和哀怨:
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云,心似飞絮,气若游丝。空一缕余香在此,盼千金伊人何之?证候来时,正是何时?灯未昏时,月半明时。[3]152
据历史记载,董鄂氏入宫时年龄18,她与丈夫顺治帝整整在一起度过的时光只有4年,4年后她便香消玉殒。史书为我们留下的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的符号,文学却可以将这4年无限延长,注入许多瑰丽诗意的想象。书中有一段文字描写的就是当董鄂妃身体欠佳时,顺治对她的细心呵护:
福临则是每日必来,或是看着她吃药,或是陪着她用膳,有时候便坐在皇贵妃的床沿上,两人小声说笑着,谈天道地,一同消磨冬日的黄昏。如果董鄂妃已经睡着,福临就轻手轻脚地看着门前小火炉上为她熬的参汤和药剂,再到床前撩开帐子,看看她的被子是否掖紧,气色是否好转,随后便在床前轻轻坐下,静静地一坐就是半个时辰,有时竟闭着眼睛仿佛睡着了一般。只有从他嘴角不时闪过的笑意,能觉察出他不过是陷入甜蜜的回忆。承乾宫一位老太监,是明宫留下来的旧人,他惊叹不已地对同伴们说:‘真没见过这样的多情天子!要不说人家关外人生性淳厚朴实呢![3]286-287
在凌力笔下,顺治帝与董鄂妃是一对完美意义上的爱人,可以说,当顺治帝无法将“汉化”的理想在朝政上得以实现之时,董鄂妃的出现弥补了他精神上的遗憾,并化解了其精神上的困顿。他喜爱《诗经》《楚辞》之类的汉文化典籍,但偌大的紫禁城几乎无人重视这些精神食粮,更不要提和他就书籍进行探讨了。董鄂妃的母亲为江南才女,她自幼旅居苏杭很长一段时间,深受中原古典文化的熏染,因此顺治的志趣爱好和她不谋而合,两人常有相见恨晚之感。加之董鄂妃冰雪聪慧又善解人意,除了宠妃的身份,她更像是顺治的知己和朋友。
小说中除却顺治和董鄂妃的诗意叙述,还有顺治帝邀请朝中文士傅以渐、金之俊、王熙等人赴宫中的桐荫书堂品诗论画,召翰林院学士徐元文、熊赐履、叶方霭等年轻学子欣赏他的藏书,和玉林禅师论禅,在钦天鉴汤若望的指导下制作珍珠粉和琥珀油以及让18头驯象在教堂街赛跑等精彩描绘,这些生动形象的叙述无疑为原本沉闷的史实注入一丝别样的意趣。在这本书中,作者已感悟到写人不仅仅是展示人的行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不同的人的群体联系到社会,而是把自己深深地浸入到对象主体的情感世界中,在心与心、情与梦的化合中来提纯历史生活,从而呈现出一种超凡的人性魅力和诗化的人生哲学。
综上所述,本文从“历史轶闻主义下的碎片化处理”“历史事件中小人物命运的发掘”以及“历史背景下的诗学意境”三个层面分析了凌力长篇历史小说《少年天子》的新历史主义特色。作者对轶闻典故的精确把握,对小人物的文学虚构,在新历史主义所倡导的“颠覆”与“抑制”下对人物关系的处理,都体现出文学与历史的完美融合。在传统的历史小说中,人物心理描写与景物描写往往易被忽视,而凌力本着“文学即人学”的思想创作出一部以少年天子顺治为核心,多重人物向中心聚焦并具有人文情怀的新型历史小说,这对于新历史主义的文本研究具有很大的价值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