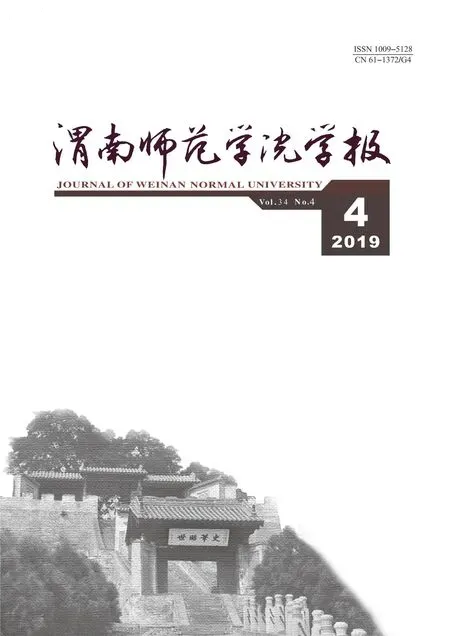由至微而体至尊:汉初后妃的人生轨迹管窥
——以《史记》为视角
2019-12-26黄腾
黄 腾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南宁 530006)
《史记·外戚世家》和《史记·吕太后本纪》为我们详细著录了许多宫廷女子的形象,其中薄太后、窦太后、王夫人、卫子夫是司马迁重点着墨的宫廷后妃,在这些典型的宫廷女子身上,我们不免发现:这些后妃们的出身诚如清人赵翼所言“汉初妃后多出微贱”[1]40。她们或凭借着皇帝的宠幸,或凭借儿子荣升帝位,不断掌握权力,位享尊荣,母仪天下。试问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普通人家嫁娶尚讲究门当户对,何况皇室宫廷中的帝王贵族们?本文试从上述几位出身寒微的后妃一步步登上尊位的传奇人生,探究《史记》中人物命运偶然性背后的决定因素。
一、后妃们传奇的人生经历
薄太后,汉文帝的母亲,出身微贱,为私生女。在诸侯反叛秦时,魏媪将女儿送入魏宫,让著名看相大师许负为薄姬看相,许负预言薄姬将来能生天子,魏王听后暗自欢喜,遂反叛汉王与楚王结盟,后被刘邦打败,全家被俘虏,薄姬被送进织室,后“汉王入织室,见薄姬有色,诏内后宫”[2]338,但是一直都未得刘邦的宠幸。年轻时薄姬曾与管夫人、赵子儿约定“先贵无相忘”[2]338。这两位夫人先后被刘邦宠幸,进而对薄姬极尽戏谑嘲笑,刘邦听后问其原委,后“汉王心惨然,怜薄姬,是日召而幸之”[2]338。这次宠幸之后薄姬便怀孕生下汉文帝,此后,她见高祖的机会微乎其微。在高祖逝世后,因备受高祖冷遇,吕后对其格外开恩,允许其跟随儿子前往代国。待到吕后病逝,诸吕被铲除,诸大臣看中刘恒的仁慈贤明,薄氏的仁善低调,刘恒遂被迎立为皇帝,薄太后改号为皇太后。薄太后这一生可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不争不抢却获得了吕后费尽心机捍卫的地位和权力。
窦太后,汉文帝皇后,名漪房,出身寒微,“窦太后父少遭秦乱,隐身渔钓,坠泉而死”[3]1973。其后一直生活贫困,吕后掌权后,“窦姬以良家子身份入宫侍太后”[2]338。恰逢吕后派遣一批宫女赏赐各诸侯王,窦姬也在其列,窦姬原是赵清河人,于是她拜托宦官“必置我籍赵之伍中,宦者忘,误置其籍代伍中”[2]338。闻讯窦姬哭泣埋怨宦官,不欲前往代国,强令她启程才不得不走,不料,至代国,独得汉文帝宠幸,生女刘嫖,生二子刘启、刘武,时汉文帝还没继位,其王后和四位王子却相继病死,后“公卿请立太子,窦姬长男最长,立为太子”[2]338。这就是后来的汉景帝刘启,小儿子则为后来的梁孝王。
王皇后,名娡,汉景帝第二个皇后,出身也不高。母臧儿为燕王臧荼孙女,父为槐里的平民王仲,王娡早年在母亲安排下嫁与金王孙为妻,生了个女儿,后其母请人为其女算命,知其“两女皆当贵。因欲奇两女,乃夺金氏”[2]339。金王孙不同意,于是其母动用各种关系将王娡送入太子宫。进宫后太子幸爱之,为太子生下三女一男。虽出身并非高贵,她深谙人心、善于经营,展现出了温良贤惠、识大体顾大局的形象,一步步取得窦太后、汉景帝的信任;同时她擅于抓住机遇、颇有手腕,先是通过联姻与长公主联手,长公主正面进谗栗姬,王娡暗中催促大臣请立栗姬皇后,里应外合,使刘彻成功当上太子,自己也顺理成章当上太后。
卫皇后,名子夫,汉武帝第二位皇后,私生女。子夫原是平阳公主家的一名歌女,汉武帝刚继位,几年没有儿子,在祭祀回来的家宴上,平阳公主为武帝挑选了十几名美人,“主见所奉美人,上弗乐。既饮,讴者进,上望见,独说卫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轩中,得幸”[2]340。后平阳公主便奏请将卫子夫送入宫中,然而“入宫岁余,竟然不复幸”[2]340。显然武帝已将卫子夫遗忘,在武帝将宫中无用女子遣返时,子夫趁机见到武帝哭泣自动请求回家,“上怜之,复幸,遂有身,尊宠日隆”[2]340。卫子夫后来为武帝生下三女一男,男名为据,即卫太子。卫子夫的人生经历可谓一波三折,终位尊皇后。
二、成功“上位”原因
纵观这几位皇后生活的时代,从公元前241年到公元前91年,这一时期正处在西汉王朝建立的初期。在这一时期,她们从出身卑微低贱的底层女子一步步走向叱咤朝野、受万人敬仰的尊位,这种跌宕起伏、富有传奇性的人生经历的背后,除却主观因素的争取,更多的是当时时势的造就,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既有命运中的偶然性,又有社会历史的必然性。
(一)主观上的争取
1.窦太后:深谋远虑,手段干练
窦太后作为一位叱咤朝野的后妃,深深地影响着景帝、武帝前期的朝政。在治国理政上,窦太后有其独特的政治远见,她偏爱黄老之术,景帝及窦氏子弟不得不读《老子》,尊黄老之术,黄老之术的核心是“无为而治”。在刚刚经历秦朝的严苛剥削、秦末的农民战争,此时人民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轻徭薄赋的执政纲领和重农抑商、发展农业经济的施政方针,窦太后深谙这一历史趋势,在她的提倡下,使黄老思想贯彻于汉初期社会的各个方面。除此,汉武帝初期,经过休养生息,国家各方面实力空前强大,已经逐渐具备与匈奴相抗衡的实力,汉武帝想发动对匈奴的战争,窦太后做出一个判断:如果此时开战,不但无法取得胜利,而且会让文景以来的基业化为乌有。接着窦太后分析到:其一,此时汉朝国力虽然强盛,但根基尚浅,容易被大规模的战争所动摇。其二,此前一直奉行着几十年的和亲政策,边境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导致当前军队训练懈怠,将领的选拔有所松弛,而且北击匈奴需要大量训练有素的骑兵,西汉的养马业甚为松弛;相比匈奴属于马背上的民族,战斗力非常强悍。其三,当时通往西域之路尚未开通,汉朝无法与西域各国取得联系,对匈奴内部的情报掌握也不稳定,一旦开战,孤军深入,极其危险。综合上述因素,此时窦太后断定仍不是与匈奴开战的最佳时机。直到张骞出使西域,充分掌握匈奴的内部情况,武帝这才一举发兵,将匈奴驱逐,完成万世基业,由此也证明窦太后的政治远见。
政治上如此的深谋远虑,那么其在后宫手段又如何?韩兆琦先生《史记·外戚世家》题解中提到:窦太后的一生可谓是福星高照,歪打正着,充满着传奇色彩。窦姬至代国后,独得汉文帝宠幸,接着,代皇后及其四个儿子相继病逝,窦姬及景帝相继上位,在“窦太后传奇人生经历,其中有没有人的因素,司马迁没说,我们也不好瞎猜。但司马迁所提供材料有不少显然是人为的,超出了‘偶然性’的范围”[4]3892。显然,韩兆琦先生认为窦太后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并非以一个“偶然性”所能解释得清楚;在《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记载着一件事:汉文帝晚年宠幸慎夫人,一次宴会上汉文帝命人把慎夫人的位置与窦皇后同席而列,后被袁盎撤下。袁盎后解释道;“陛下幸之,即厚赐之。陛下所以为慎夫人,适所以祸之。陛下独不见‘人彘’乎?”[2]89陛下难道没看见过“人彘”吗?这是袁盎对汉文帝的提醒,侧面向我们传递出窦太后后宫手段未必比吕后差。在蒋葵《〈史记〉中的偶然与必然》一文中直接指出:“观代皇后及四子相继早世,并非巧合其中可能另有蹊跷也不无可能。”[5]西汉流传着“女无美恶,入宫见妒”的格言,宫闱中夺嫡争宠的现象长期存在,西汉同样不例外,太史公在书中尚未提及窦太后在后宫中如何争宠夺利,上述事件中的窦太后,绝非一位深受命运垂怜的幸运儿,只是窦太后把一切做得太完美,使得世人无法察觉罢了。从种种事迹来看,窦太后无疑是一位智谋和权谋都堪称一流的女中豪杰。
2.王夫人:审时度势,奉上迎下
与吕后和窦太后的政治手腕相比,王夫人更善于对后宫的经营,一步步打造温柔贤淑、识大体顾大局的形象,深得景帝、窦太后和长公主的欢心。为保证刘彻顺利登上皇位,王娡可谓苦心经营,在《汉书》中记载:“男方在身时,王夫人梦日入其怀,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贵征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6]3946作为汉景帝的第九个儿子,也是其继位的第一个儿子,王娡紧紧捉住汉景帝喜欢祥瑞、迷信的这一心理特征,创造出“日入其怀”之说,把刘彻包装神化,比作天上太阳,无形之中使刘彻在景帝的心目中增加了不少的印象分。在与栗姬及刘荣的斗争中,王夫人步步为营,与长公主联姻,后用进谗、挑拨和陷害的方式彻底击垮栗姬,为刘彻登上天子之位铺平道路;争取窦太后的信任,她积极迎合窦太后,七国之乱后,国库空虚,汉景帝对匈奴用兵,在一次由窦太后组织的游戏上,名为游戏实际是为匈奴战争募集军饷钱财,王娡洞悉窦太后的用心,她慷慨解囊主动献出自己平时积累的珠宝首饰,用实际行动迎合窦太后的心愿,也充分显示她支持景帝的决心。通过一系列的举措不断树立起一个识大体顾大局、善解人意的形象,深得皇帝和太后的信任,进而缔造自己精彩的人生。
3.薄太后、卫子夫:恭谨谦和,把握时机
相对于前面几位后妃精明能干,薄姬和卫子夫却显得善良贤淑、谨慎低调,但关键时刻也绝不含糊,懂得紧紧抓住机会,改变人生的轨迹。薄姬作为战俘被关于织室,因颇具姿色而被纳入后宫,之后一直被刘邦所遗忘,阴差阳错之下得到刘邦怜悯,进而得到召见,于是她紧紧地把握这次机会,见刘邦之后,她说:“昨暮夜妾梦苍龙据吾复。”[2]338刘邦心想这不是变相在说自己便是真龙天子吗,听后大喜说:“这是好的预兆,我今晚就成全你吧。”这次宠幸也成为其人生的转折点,仅仅这次宠幸便生下了汉文帝刘恒,也因此改变了薄姬后来的命运;卫子夫,在汉武帝时期整整做了38年的皇后,在位期间她处事低调、谨小慎微,其人生经历也是一波三折,在平阳公主家的更衣间被武帝宠幸后,之后也是备受打压,后宫中长年独守孤灯,在一次汉武帝遣返一批宫女回家,见到武帝之时,卫子夫果断出手,跪下哭泣并请求武帝放她出宫,哭声凄凉悲恻,武帝回想起当年相遇的美好时光,心中不忍,于是重新宠幸了卫子夫,在为武帝诞下皇长子刘据后,于是被立为皇后,其后卫氏家族更有五人封侯的荣耀,在《乐府诗集·杂歌谣辞》歌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7]1181足见卫子夫尊宠日隆。
上述后妃虽出身卑微,凭借着自己的政治手段和能力,或凭借着对机会敏锐把握,这是西汉初出身寒微低贱的后妃们成功“上位”的前提。
(二)社会历史的必然性
在西汉初期特定社会历史时期里,一方面,受春秋战国余风的影响,旧的经济制度的瓦解,旧的宗法等级制度和思想离散;另一方面,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制度、思想观念、统治秩序尚未形成。社会在不断转型,恰恰给这一时期的女性提供了较充足的空间,处于这个时期的女性享有较高的地位,在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呈现出较大的自主性和选择性。
1.社会经济基础
在小农经济的体制下,进一步激发社会各阶层的活力,为女性提供了大量的机会。相对于封建社会其他时期,此时女性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着无可取代的作用,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半边天”,所以这一时期的女性地位享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她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参与其他社会事务,甚至是国家政治建设,推动她们一步步迈向富贵和权势。
(1)小农经济激发社会活力。马克思指出:“社会革命是从土地所有制开始的。”[8]66西周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天子再将天下土地分封各诸侯,诸侯有“国”,领主强迫庶民在井田上集体耕种;土地禁止转让买卖,这就是“井田制”,这时土地处于静止的状态。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各诸侯国不断强大,相互之间不断进行兼并战争,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逐渐把土地化为己有,在井田外开垦的私田也逐渐增多,土地变得可以自由买卖,井田制不断瓦解,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就应运而生。由血缘关系凝聚而成的宗法制社会不断瓦解,分散的个体劳动逐渐取代了井田上集体劳动,个体小农家庭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生产的主体,小农经济不断发展壮大。西汉王朝正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正因如此,个体经济制度为底层人民提供了更多成为皇侯贵戚的机会。一方面,个体小农经济制度极大地激发人民的积极性。这一时期土地自由买卖制度化,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由静止状态进入流通状态,这就把封建小农经济卷入一种竞争状态,这极大激发人民的积极性,使得社会充满着活力,底层人民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有机会实现由贱至贵的转变;另一发面,个体小农经济制度成为西汉政权的基础,小农生产方式是当时最主要的生产方式,他们是当时西汉财政收入的来源,是西汉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汉初统治者极为重视发展小农经济,从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措施促进其发展;同时对于小农阶层较为宽容,把等级门第观念看得很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些出身寒贱的女子凭借出众的色艺,“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游媚贵富”,入后宫,入主掖庭,“由至寒微而体至尊”。[9]114
(2)丰富社会实践为女性提供机会。女性地位的提高归根到底是由女性在社会物质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所从事的主要社会实践决定的。在母系氏族中,由于女性从事植物食品的采集,经营原始农业,在提供生活资料的可靠性、重要性上要比男子大得多。西汉初期女性之所以能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女性并未完全束缚在家中,能够广泛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活跃于西汉初期各个行业之中。在文献史料中常记载有秦汉时女性从事各种生产劳动: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高祖为亭长,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褥。有一老父请饮,吕后因哺之。”[2]71初为人妇的吕后带着儿女干农活。在《氾胜之书》载:“区麦种……大男大女治十亩。”[10]49《后汉书·逸民传》也曾记载:“(庞公)因释耕于垄上,而妻子耕于前。”[11]2776这些都较详细记载描写汉时女性普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汉时女性不仅仅是简单地从事劳动生产,并且对劳动生产做出突出贡献,据宁可《汉代农业生产漫谈》一文指出,秦汉时人口总数保持在五千万左右,其中农业人口约有四千万,以每户五口计,当时约有八百万户,每户两名劳动力(一男一女),共有八百万女性农业劳动者。若每人年产粮2000斤,则汉时女性年产粮160亿斤[12];另据吴慧在《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的估算,每人年产粮是3578斤,则秦汉女性年产粮286亿斤;前一组数字可提供约2000万食用一年,这一组数字可供约3400万人食用一年。[13]127-129可见女性劳动者对汉农业所做出的贡献。
同样,汉代女性在商业活动中也十分活跃,有从事开酒店的,在《史记·高祖本纪》就有记载:刘邦在参加农民起义以前“常从王媪、武负赊酒,醉卧,武负、王姐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2]71。《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2]672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后以开酒店卖酒为生。有从事漂洗业的,如“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2]547。有从事纺织业的,《汉书·食货志》载:“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6]1128妇女纺织除了家用之外,还要外出卖织品换钱,其中远近闻名的“丝绸之路”无可置疑地证明汉时期的女性是生产劳动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2.开放包容的人文社会环境
经历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礼乐崩坏,秦时专任法治,思想不断流变,到西汉初期,社会正处于大变革时期,旧的思想、旧的等级制度被破坏,新的封建等级制度和礼制正在酝酿,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尚未确立。正处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转换期,出现了一种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女性获得相对的人身自由,这为出身寒微的女子实现由微贱至尊贵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
(1)儒家封建伦理纲常尚未完善。宽松的社会环境得益于儒家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尚未形成,因此为汉初女性留下活动的间隙。汉初,天下初定,诸子并用,儒家的封建伦理思想正处于探索的形成期,西汉前期,贾谊就曾提倡家庭和谐,恢复儒家伦理观念,实行礼治,其中重要的观点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在《新书·礼》提出:“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至也……夫和则义,妻柔则正,姑慈则从,妇听则婉,礼之质也。”[14]215主张夫妻、婆媳都得按照礼制去做,这样才能保证家庭美满和谐。这是西汉时最早提出儒家伦理纲常,他也是点到为止,并未展开论证,也未对人们产生真正的约束力;接着,进入汉武帝时期,封建伦理纲常进一步发展,这时董仲舒创立“三纲五常”道德观,使夫妇人伦关系被“政治化”,妇女的地位进一步降低;他在《春秋繁露》中提到:“君臣父子夫妻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15]161把夫妻、男女关系与天道结合论证“男尊女卑”的永恒性,夫对妻有支配、统治的权利,妻对夫只有侍奉和听从的义务,夫妻关系变成专制与被专制的关系,女性彻底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儒家封建礼教发展至这里,已经逐步成型,但是理论的提出与实践效果尚有差距,理论想要完全渗透社会的方方面面,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儒家伦理纲常尚未对汉初女性形成实质性的约束作用。取而代之,西汉初期真正占据主导地位的则是“黄老思想”,治国上主张“无为而治”,思想层面上主张“兼容并包”,在这样的氛围影响下,汉初人们呈现出比较积极开放的心态。由于儒家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尚未给女性日常行为套上礼教的枷锁,真正占据统治地位的“黄老思想”提倡相互包容,所以在这宽容和开明的环境中,女性获得较大的自由。
(2)统治阶级的开明与包容。汉朝的建国皇帝及功臣多是出身寒微,他们等级门第观念淡薄。西汉的建立者刘邦,起义之前就是小小泗水亭长,仍需与其妻吕雉“居田中”参加生产劳动,外出喝酒时常常欠店家酒钱无力赔付,使人不得不“折卷弃费”,可见刘邦当时处境如此贫困窘迫;同样那些跟随刘邦起事的功臣们也多出身寒微,萧何曾为“主吏掾”,曹参为“狱掾”,樊哙曾以屠狗为生,韩信因贫穷竟靠一漂母施舍才能饱食,彭越在湖泽打鱼,还伙同他人做起了强盗。这些来自社会下层的百姓,无权无势,渴望富贵,渴望改变自己目前悲惨的处境,希望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他们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时代最强音,这也深深激励当时的社会女性,她们坚信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总有一天同样能出人头地。同时,在跟随刘邦夺得天下后,这帮出身寒微的功臣最终都被封侯列爵,成为新兴的地主阶级。参政后,因为出身于社会的底层,他们对民间疾苦深有体会,也只有他们才能切身体会到出身寒微到富贵的艰辛,因此他们思想比较解放,对一切保持着较强的宽容精神。在婚姻上,由于相同的出身,他们对于门第、等级没有严于苛责;由于相同的人生经历,他们情感上更同情这些出身寒微的女子。所以自皇帝到臣子,对自己配偶的选择上,不论门第出身,不论贵贱,不论贞操,使得许多出身寒微的女子有成为妃子的机会。
(3)选才标准:尚功尊贤,不唯血缘。汉初,统治集团主要是没有权势的家臣构成,他们出身庶族,因同高祖出生入死,一步步建立军功,而位居高位,因此以军功大小来论功行赏已经成为汉初选拔官吏的标准之一,改变家族政治以血缘亲疏作为选拔的唯一依据;而“尚功尊贤”这一标准在汉武帝时期得以最鲜明的体现,当时卫青、霍去病就因抗击匈奴立下卓越军功,卫青官至大司马、封长平侯,封邑万户;霍去病被封为冠军侯、官至骠骑将军、大司马。除却军功制度,平民百姓只要具备一技之长均可被授予相对应的职位,所以汉武时期各种人才相继涌现,《汉书》记载:“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6]2634正是由于这些各具才能的大臣共同辅佐,奠定了汉王朝强盛的局面,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汉初开放社会,能够为各种各样的人提供了一个广阔舞台,使得各类身怀绝技的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许多人凭借着才能和谋略终能位极人臣。“任贤而序位,量能以授官”[6]2623的选人标准同样反映在后宫选妃制度上,因此西汉的皇帝对于后妃的选择上,更看重实际,更注重于女子色艺和胆识,所以即使出身低贱的女子,凭借着出众的相貌和技艺同样能走上“后位”,尊享荣华。
此外,不唯血缘的选才标准,意味着家族政治被新的封建官僚所取代,导致家族政治瓦解,权力的分散;尚功尊贤的标准,意味着不管出身如何,只要有军功或有才能均能为官,这就决定着许多官员来自底层人民。家族政治的逐渐被取代、辅佐大臣出身寒微只能唯皇帝命是从,这就使得皇帝把皇权牢牢地握在手里,伴随着皇权的巩固,家族之间政治化婚姻则显得无关紧要,所以帝王们并不需要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在纳妃上完全可以凭着自己的喜好来决定,后妃只需尽心博取皇帝的欢心就有机会登上“后位”。
(三)吕后的教训
在蒋波、冯艳秋《论吕后与吕家的关系及其影响》一文中认为:“吕后母子能赢得太子之位,并带领汉朝平稳地由刘邦时代过渡到惠帝时代都离不开吕家的支持; 吕后能大封吕氏外戚、独掌大权也与吕家的政治势力密不可分。”[16]的确,从孝惠帝登基至吕后临朝改制十五年期间,吕后大力扶持吕氏家族的势力,封王封侯的数量之多,涉及领域之广、程度之深,吕氏外戚已经全面把持朝政的各个方面,外戚势力直接动摇了刘氏王朝的统治根基,这就给后世的皇帝和大臣敲响了警钟。
1.从根源上杜绝外戚干政
吕后教训背后,实质上是中央皇权与外戚权力之间的矛盾。成功诛伐吕氏后,在遴选继承人的问题上,大臣们“疾外家吕氏强暴,皆称薄氏仁善,故迎立代王为皇帝”[6]3941,除却刘恒为“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2]89,更为重要的是群臣忌惮刘襄和刘安的母家势力,《史记·外戚世家》中提到:“齐王母家驷,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2]89“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2]89齐王和淮南王外戚势力过于强大,一旦他们当政,难保不会出现第二个吕后,相反“太后家薄氏谨良”[2]89,薄太后不仅恭谨谦卑,最为重要的是其出身微贱,背后的外戚势力薄弱,不会对中央皇权造成威胁。
因此,想要从根源上杜绝外戚篡权的萌芽,行之有效的方法则是在于皇帝的选妃制度,皇帝在纳妃时更倾向那些出身寒微的“良家女”,她们出身社会底层,背后没有雄厚家族势力作为支柱,在朝廷内既无根基,也无社会经济背景,外戚纵想擅权也成不了气候,把外戚干政扼杀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加强了中央皇权。
2.重视外戚的道德教化
此外,为了限制外戚势力,群臣十分重视对外戚进行道德教化,进一步削弱外戚干政的根基。窦太后在寻回弟弟窦长君后,群臣十分重视窦广国和窦长君的安置问题,绛侯、灌将军等商议:“吾属不死,命乃且县此两人。两人所出微,不可不为择师傅宾客,又复效吕氏大事也。”“于是乃选长者士之有节行者与居。窦长君、少君由此为退让君子,不敢以尊贵骄人。”[2]339名为挑选有德之人对其进行辅佐,实则先入为主,从意识观念深处使其建立起对皇权绝对服从的理念。由此观之,大臣为防止外戚干政可谓是用心良苦。
三、结语
依上所述,西汉初期出身微贱的后妃能够成功“上位”,并非作为偶然现象存在,除却主观上积极争取,更多的是在西汉初期所处的特殊社会背景下,是当时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后妃的传奇经历对当代寒门青年的奋斗极富启发意义,不管出身如何,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相结合,紧紧把握时代赋予我们的机遇,在奋斗中实现个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