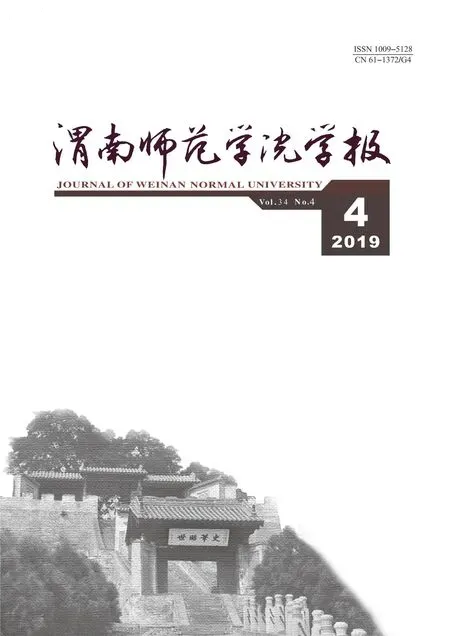从历史文学角度论《史记》的“曲笔”
2019-12-26胡静
胡 静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一、历史文学与《史记》之“曲笔”
文史兼备、形质兼美,是绝大多数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典籍的共同特性和优良传统。无论是《诗经》的史料存留还是《左传》的散文价值,中国文学与史学有着不可割裂的血脉渊源。先秦《孟子》一书最早提出“义”“事”“文”史学三要素的观点,重视“文”在史学中的地位。《孟子·离娄章句下》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1]300“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史之为务,必藉于文”[2]114-152,文和史交织渗透,既彼此独立又相互借鉴,共同熔铸成博大而精深的中华文化。而历史文学,正是文史交融所绘就的华章。白寿彝在对中国史学遗产进行发掘爬梳、整理研究时,较早系统地提出史学四大组成部分的论断,将历史文学与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并列并重,又在其《史学概论》中做了进一步阐释:“历史文学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指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另一个意思是指真实的历史记载所具有的艺术性的文字表述。”[3]189而将《史记》划入历史文学的范畴,正是从史学的视角,探究其作为历史著作在文字表述上的艺术特性和审美诉求。
《史记》作为“史家之绝唱”和二十四史之首,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和第一部有组织、有系统、有规模的大型专门性史书。唐代韩愈对司马迁极为推崇,在《答刘正夫书》中称“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4]207,明代金圣叹将《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这些,都恰是对其文学性特色的赞誉。
而探究《史记》中的“曲笔”,也正是站在历史文学的范畴,偏重叙事上的间接呈现本题而非平叙其事,抒情上的不写自己情感而借他人抒胸臆,而非传统史学意义上与直书相对的阿谀谄媚之曲笔。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运用“曲笔”,让文学性充分彰显的同时,含蓄地传承史实,委婉地抒发褒贬,寄予了无尽的慨叹。正如程余庆在《史记集说序》中的阐述:“《史记》一书,有言所及而意已及者,有言所不及而意已及者,有正言之而意实反者,有反言之而意实正者,又有言在此而意则起于彼,言已尽而意仍缠绵而无穷者。错综迷离之中而神理寓焉,是非求诸语言文字之外,而欲寻章摘句以得之,难矣!”[5]34
站在历史文学的角度,在文学方面,《史记》中星罗棋布的“曲笔”为《史记》平添了一抹绚烂的色彩;在史学方面,也正因为这些“曲笔”实录的存在,客观全面地展现历史原貌而不重避讳、不隐真相,让不少捍卫儒家礼义道德的政治家、史学家等斥判《史记》乃“谤书”。《后汉书·蔡邕列传》中王允为杀蔡邕,首次提出“谤书”之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6]2006此后“谤书”之声延绵不绝,直至清代李晚芳《读史摘微》中尚有此论。兼顾文史,“曲笔”是非,正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二、《史记》之“曲笔”与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源于鲁国旧史《春秋》一书,是中国历史常用叙述方法和语言艺术。经学家认为,《春秋》为孔子所撰并含垂教后世之大义,每用一字、必寓褒贬,微言大义。《左传》总结:“《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7]317在史书撰述中,大部分史学家的观点与经学家泾渭分明,他们认为史书应重视春秋大义——明辨是非、邪正、善恶、褒贬,经世致用;却并不赞同对“每用一字、必寓褒贬”这一笔法的过度强调,欧阳修《新五代史》即因对微言大义形式的过度追求、埋没史实而受到批判。
清代章学诚在史学理论著作《文史通义》的《申郑》篇中写道:“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8]249文化史上,无论是站在文献视野还是历史文学、历史编纂学角度,将司马迁《史记》与《春秋》并论,都有着深刻的渊源。家学沿袭上,司马氏世为史官,这种传统在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处仍绵延不绝。《隋书·经籍志》载:“谈乃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9]956司马谈因天子封禅泰山不得从行一事抱憾而亡,嘱其子司马迁承其志;司马迁将司马谈的遗志进一步承继发展而著《史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10]760(《太史公自序》),可见其家学上对《春秋》的重视和汲取。师承关系上,司马迁曾向董仲舒学习《春秋》,董仲舒作为公羊学大师,在《春秋繁露》中归纳出许多属于《公羊传》的春秋大义,《公羊传》更是坚持孔子“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7]537,司马迁正是以“后圣”作为自己的目标。著史动机上,他认为《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然而孔子之后大道不传,故秉承圣人遗志,发愤著书,他在《太史公自序》写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10]760在自身定位上,司马迁著《史记》常自比于孔子作《春秋》。孔子周游列国,厄于陈蔡,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际遇的相似赋予司马迁以戚戚之感;《春秋》绝笔于鲁哀公获麟之年,《史记》叙事亦“麟止”于汉武帝元狩元年,司马迁续继《春秋》之统的心迹可见一斑。
《史记》中对春秋大义和春秋笔法是极为推崇的。对于春秋大义,他在《太史公自序》中称赞道:“《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并反观现实,认为《春秋》对现实社会有指向性、规范性的重要作用:“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面对壶遂的质疑,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解释:“《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10]761注重《春秋》的积极意义。甚至在卷目后的论赞中直接阐述对《春秋》的理解和承继,如在《匈奴列传》指出:“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10]646而对于春秋笔法,他更是大为欣赏:在《儒林列传》指出:“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以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10]700《太史公自序》亦言:“《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10]760
2)滤波。将作为3.1节所述滤波算法的输入,对所有模型Mj并行进行自适应交互双模算法计算,更新xj,k+1|k+1和Pj,k+1|k+1。
春秋笔法中是包含了史学意义上的曲笔的:作为鲁史的《春秋》一书,在撰写过程中本就因著史者主观原则态度因素,推重鲁国而存在与直书相对的曲笔回护,导致史实记录上的不客观;后人阐释讲求的春秋学和春秋笔法,在儒家礼文化的束缚下,赋予一些固定用法以特定礼教意义,更加突出为尊者、亲者、贤者讳等忌讳之曲笔。春秋笔法凸现着中国史学从源头上对史义的重视和以史为鉴、彰善瘅恶的价值选择,《史记》深受这种史义观的影响并与之一脉传承;但需要强调的是,春秋笔法中的曲笔属于传统史学意义上曲笔的形式之一,它与历史文学角度《史记》中的“曲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同中有异,批判继承。《史记》存在“曲笔”,但主要体现在历史文学表达的措辞上,重在继承春秋笔法中史学上的不隐真相、直面褒贬和文学上的委婉含蓄、文笔婉转相统一这一特点,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事涉君亲、曲笔回护、一字褒贬。因此,在《史记》这部鸿篇巨制的创作过程中,司马迁不仅仅继承春秋大义、将春秋笔法点染其间,更重要的是他超越了春秋笔法写史的局限,站在更为广阔的视角、运用更为丰满的手法,通过“曲笔”,将价值判断寓于平实的叙述之中,将历史史实寓于客观的论断之中,将微文刺讥隐于布局谋篇,将笔削彰瘅隐于文辞选定,用文学化的“曲笔”实现着直书的终极意义。
白寿彝指出:“《史记》之继《春秋》,主要目的是‘渐’,表现的方法是‘微’。”[11]70其中,“渐”即未然,防微杜渐;“微”即表达上委曲婉转而展现真实,反映其所察觉的社会危机。在这种“渐”“微”的背后,实质是深思之、再思之、三思之的定论。《史记》中的“曲笔”,是历史文学上的艺术高峰,传达的更是一位史官对历史的高度尊重和良苦用心;“曲笔”的运用,愈加为《史记》这幅恢宏壮阔的历史文化长卷增添了隐晦、朦胧之美。
三、《史记》中“曲笔”的呈现形式
从全书整体篇章构建来说,《史记》的“曲笔”主要展现在三点:各篇互见,展人事全貌;叙中寓论,浇心中块垒;篇末论赞,隐史迁褒贬。需要注意的是,所谓“曲笔”,是把纯文学性质的夸张和作者认知的局限排除在外的。
其一,各篇互见,展人事全貌。这是一种结构上的“曲笔”。《史记》错综离合而又彼此关联,各篇独立成章而又共成一体,故不应将某一篇章孤立看待,要立足全局、综合考量,于零枝碎叶中窥“曲笔”大观,并在对比中探析司马迁的真实意图。
“曲笔”互见法有三方面的作用:第一,它与纪传体这种历史编纂方法有关,同一事件可能涉及诸多人物,为避免重复而各篇互见。如《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10]41同时《吕不韦列传》有曰:“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10]511两文对照,“曲笔”之间秦王政之身份无须重复而自现。第二,它可以集中史事,使叙事完整,条理分明,重点突出,在某一篇章中着重并凸现人物特定性格,从而利于人物形象塑造和唤起读者的关注。宋代苏洵指出:“迁之传廉颇也,议救阏与之失不载焉,见之《赵奢传》;传郦食其也,谋挠楚权之缪不载焉,见之《留侯传》。……夫颇、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过一者也。……是故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则其与善也,不亦隐而章乎?”[12]233正是对这一作用的详尽阐释。第三,也是较为重要的方面,是政治环境桎梏下通过文学性手法实现实录。整体上,如项羽入本纪,陈涉入世家;细节上,正如清代高嵣指出:“此书有讽意,无贬词,将武帝当日希冀神仙长生,一种迷惑不解情事,倾写殆尽。故前人谓之谤书,然其用意深矣!此事并《平准》《酷吏》《大宛》数篇,合成《孝武》一篇本纪。”[13]面对潜在的政治压力,司马迁并没有放弃秉笔直书,而是转而使用“曲笔”来艺术化传承史实、重现历史。综合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互见法并不是局限于传统研究上为本朝帝王而作的“曲笔”,对孔子、廉颇以至韩信等不同性质的人事,司马迁心中自有审美和褒贬上的权衡,故多有“曲笔”互见。
其二,叙中寓论,浇心中块垒。这是通篇文字表述上的“曲笔”。顾炎武《日知录》指出:“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14]1432《史记》运用“曲笔”,寓论断于叙事之中,不仅仅是顾炎武所言的篇末他人论断;实际上,它包含了不同层面的内容。
一曰他口明志:文中或文末忽然加进某件事或某人言语,却又不做置评,看似突兀的一笔,其中况味与深意却是无尽的。《淮阴侯列传》中用四分之一篇幅记叙武涉和蒯通游说韩信背汉自立,自当是借之抒韩信之冤痛的。《平准书》中写到卖爵敛财的桑弘羊,正文文末以“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焉”收束,其后却又加一段:“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10]188如此一笔,寓客于主,用卜式之口抒太史公之心,司马迁对桑弘羊的贬斥在“曲笔”间已经昭然纸上。二曰直叙明志:无须通过他人品评,也不必作者直发议论,而在平实的描写记述中将彰瘅褒贬表现得淋漓尽致。以《李将军列传》为例,司马迁没有华丽的辞藻和慷慨的陈词,将自己的万千思绪、千言万语凝注浓缩在淡然的史实描写中,他写匈奴闻广居北平,“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他写广一生家无余财,而“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他写李广自刎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10]633。无一字议论而字字倾慕、字字血泪,将个人际遇与李广的身世悲歌合二为一,达到历史文学创作的顶峰。隐去著者身份,反之直接用客观视角来讲述史实和描摹人物,不加评判,而评判的主动权实现从著者到读者的转移。读者仔细品味文字,则可以窥见文字背后所隐藏的司马迁对人物、对历史的态度。这种“曲笔”,已经成为记述和反映史实的重要部分,云谲波诡中自有义法,正是《史记》的特色之一。
其三,篇末论赞,隐史迁褒贬。这是单独列出篇末“太史公曰”中的“曲笔”。司马迁继承《左传》“君子曰”的表述,在《史记》中独具特色的引入了“太史公曰”的写法。据学者统计,《史记》中文末有“太史公曰”者共计106篇。如果说《史记》中司马迁通过互见法和寓论断于叙事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是间接的,那么如此浩繁的论赞则是在真实反映历史之外,最能直接展现司马迁个人对史事褒贬的原始材料。
对于与汉朝无重大关联的人事,自然可以妍媸毕现地直抒胸臆,也可以用“曲笔”更为生动地剖明心志;而有些相关人事的评论,则选择含蓄委婉,言此意彼,绵里藏针,“曲笔”隐现史实。称萧何“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灿眼”,论陈平“及吕后时,事多故也,然乎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对于在刘邦、吕后一朝得以善终的名臣,一段段看似褒扬的论赞,结合韩信等名臣的落寞结局,细究之中自有深意,既实现了真实史料的留存,而“曲笔”之间的无限韵味,又让人不觉莞尔。“太史公曰”中除却用隐含的深意“曲笔”表达褒贬外,与各篇传记排列次序亦有关联,这在历史文学史上是开创之举。《匈奴列传》曰:“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10]646汉武帝好大喜功,伐匈奴数次却建功不深,其间反讽是很明显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此篇“太史公曰”,清代何焯指出:“下即继以卫、霍、公孙弘,而全录主父偃谏伐匈奴书,太史公之言深矣。”[15]一篇论赞,看似平平,实则从语言、次序两个方面见“曲笔”之意,表达对汉武帝好大喜功和诸将相建功不深的讽刺,亦为“太史公曰”中较为特殊的“曲笔”。
除却整体篇章构建的“曲笔”,在其他细节描摹上,《史记》也多有“曲笔”。如言约意丰的炼词、丰富多姿的修辞、盛赞之下的反讽……《史记》中的“曲笔”并不局限于列出的典型表现形式。这些“曲笔”,在史学平淡的记叙中给读者以跳跃的灵动,且更好地实现实录的目标,在历史文学史上熠熠夺目。
四、《史记》中“曲笔”的原因探析
《史记》中形式多样的“曲笔”星罗棋布,首先是史学创作中语言表达的需要,是文笔与史笔并重的结果。《论语·雍也》曰:“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83《文史通义·史德》曰:“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8]265史学著作最重要的诚然是坚持信史、直言录实,但其语言表达上依然需要一定的技巧雕琢,才能成为久传不衰的经典。文似看山不喜平,奇势迭出、波澜涌动,都是历史文学作品应该注重的。司马迁的《史记》正是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点,文笔与史笔交融,在文学和史学两个层面达到高峰,成就历史文学的辉煌。“曲笔”正是文笔和史笔结合的一种形式。文笔贵曲,史笔贵直,“曲笔”形曲实直。相较于史笔的直,《史记》的“曲笔”富于意蕴,富于暗示,更能揭露真相,反映事实。概而言之,《史记》中的“曲笔”,是司马迁文笔与史笔相辅相成、交融统一的展现,文笔是“曲笔”的表现形式,而史笔是“曲笔”的目的归宿,文笔和史笔在“曲笔”的交合点上相映成辉,终使《史记》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史记》中的“曲笔”,也与社会环境相关。西汉王朝的性质决定了司马迁在记述部分事件时不得不使用“曲笔”来实现直书的目的。西汉是继秦之后的第二个统一的封建王朝,政治不断完善、经济持续发展、文化趋向繁荣的同时,尊卑秩序、人伦纲常也被提升到重要的高度。《刘敬叔孙通列传》对汉七年诸侯群臣长乐宫朝见的记述是这一现象的一个侧影:“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10]585自此,西汉走上了等级森严的新起点。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司马迁著史时自然需要谨慎。史家著史就像带着镣铐舞蹈,心中的良知和笔底的责任告诉他们要秉笔直书,而现实条件的桎梏又会警醒他们必须学会在罅隙中生存,用“曲笔”的形式实现直书。故此,在对本朝帝王及与帝王相关人物的记载和评价也是“曲笔”集中凸现之处。《三国志·钟繇华歆王朗传》载曹魏王肃言:“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16]418刘歆《西京杂记·书太史公事》载:“作《孝景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17]44皇帝希望自己及祖先被放大、神化,而司马迁则剥下其神圣外衣,不因忌惮权贵而抛弃信史,旨在将千秋功过昭之后世,于是帝王本纪中“曲笔”丛生就有了合理解释。也正因为这样,让《史记》置于传统儒家道德捍卫者的旋涡。东汉班固《典引序》引汉明帝诏书曰:“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明末王夫之在《读通鉴论·武帝》中亦称司马迁之言为“背公死党之言”而不足取信,皆是明证。
司马迁写《史记》时,西汉王朝历经六位不同形式的统治者:名实兼备的汉高祖刘邦、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和汉武帝刘彻,有名无实的汉惠帝刘盈和有实无名的高后吕雉。因孝惠帝政治无所作为且早逝,《史记》并未为其单列本纪;吕雉,功过参半、名实一致;刘恒,励精图治、德孝兼备。故对帝王记述的“曲笔”主要集中在《高祖本纪》《孝景本纪》和《孝武本纪》三篇帝王传记中。
先看刘邦,《高祖本纪》中的汉高祖是一个母“梦与神遇”、父“见蛟龙于其上”、吕公相而嫁女、吕后望其云气的天命所归的形象,是“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韦宁,改制易俗”的圣贤君主的形象,然而,我们继续翻动书页,便可以从其他人物的传记中还原一个栩栩如生的真实的刘邦,一篇立之而多篇破之,各篇互见成为对刘邦的描摹中“曲笔”的主要表现形式。《项羽本纪》载,刘邦获胜入彭城而“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兵败外逃而“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10]66,抛弃儿女等典型事件将刘邦性情里的阴暗面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季布栾布列传》记载他得天下后以怨报德杀害曾放走他的项羽部将丁公,《魏豹彭越列传》点明他因性格多疑逼反杀害追随自己一生、为汉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诸王功臣。至于为项羽立本纪、为陈涉立世家、为韩信赞功这些举动本身,虽然不容置疑地有为了证明西汉王朝政权合法性的一方面,但更在“曲笔”中呈现了司马迁对刘邦评价的客观性。
再看刘启,《孝景本纪》中说他“至孝景,不复忧异姓”[10]100,与文帝共同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局面,然而这一篇较之其他篇章的血肉丰满,几乎是单纯的大事记,庄严肃穆的突兀文风和似正实讽的著述语气里,亦可观司马迁的好恶。《孝景本纪》中仅客观记述历年大事,而在晁错、周亚夫和张释之的传记中则较为详细地呈现了事情始末,其他篇章轻描淡写地详尽“曲笔”里,刘启性格里的阴晦被含蓄地铺展在阳光下。
最后看刘彻,对于这位与自己在纵横两个节点上都恰好处在交织位置的帝王,在涉及刘彻的“曲笔”问题上,综合了各种“曲笔”方式,在此仅列一例,不再详述:《平准书》中评论秦朝“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10]189,借古讽今,对比还原,正是对刘彻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的影射。后世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指出:“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18]872朱熹等也持相同意见。而后人的观点综合借鉴诸多史书史料,侧面说明司马迁即使处于政治高压中,对武帝的记述依然相对全面地展现了史实。
《史记》中“曲笔”的另一原因是司马迁的个人际遇。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宫刑之痛,“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报任安书》),他忍辱负重而著《史记》,将历史的是非曲直和自己的阴晴圆缺以“曲笔”的形式灌注到书中去,蔚为大观。
五、实录精神:《史记》中“曲笔”的本质
实录精神是史学家的道德准则,也是史书的核心品质。刘知几《史通·直书》曰:“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2]179史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记录史实,更在于劝诫后人。唯有坚持实录,史书才能彰显价值、发挥作用,史学文化才能不断发展。故此,先秦时代,孔子就提出了“笔法不隐”的原则,晋杜预提倡“尽而不污,直书其事”的方式,唐代刘知几认为史学家必须兼备史学、史才、史识“三长”,史识,是历史见解,其核心在于秉笔直书,忠于史实。重视史德是我国历史学界一脉相承的优秀传统;对于败坏这一精神的人,后人是持唾弃态度的,甚至称为“秽史”,如南北朝史学家魏收即因著史不实而受到质疑。
然而,坚持实录是有风险的,“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著史者“身膏斧钺,取笑当时”而史书“书填坑窖,无闻后代”数见不鲜。面对这一现实,以刘知几为代表的大多数史学家依然认为当坚持实录,在《史通·直书》说:“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2]180他们强烈斥拒非历史文学角度的曲笔,在《史通·曲笔》中说:“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185
按照刘知几《史通》的观点,史学上的曲笔有三等,都与实录精神相悖。一等,最鄙劣的曲笔是史家追求利禄、谄媚权贵:“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若王沈《魏录》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贪图功名的他们完全按当权者的意愿去写,极尽歌功颂德的谄媚之姿,这自然也为世人所不齿,这类人应受到最严厉的道德批判。二等,历史观不严肃,著史随心所欲:“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这类史家更多的是因个人习惯等造就不能实录,但身为史家却不能坚守基本的史家修为,也是为历史所鞭挞的。三等,因父子君臣的亲疏差别而曲笔回护:“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对于这类史家,需站在其所处的具体环境考虑其认知的局限性,其曲笔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实录,不值得提倡。
汉代扬雄在《法言》一书中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太史迁,曰:实录。”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对《史记》评价道:“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史记》能够作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其实录精神是分不开的。其文直,直词述史,客观真实。《史记》的语言通俗而不粗鄙。如将《尚书·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对比,我们便能清晰地感受到司马迁驾驭语言时炉火纯青的功力。其事核,凭据撰史,掷地有声。对陈胜吴广起义的记述,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俱全,生动地塑造了以陈涉为代表的起义军的形象,完整地展现了秦末农民起义的壮阔画卷。不虚美,《游侠列传》里的热情歌颂;不隐恶,《酷吏列传》中的无情鞭挞,都体现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应该看到,实录精神和司马迁《史记》中历史文学层面上的“曲笔”并不存在水火不相容的情况。《史记》中的“曲笔”不仅不妨碍实录,而且是为了更好地展现实录而存在的。《史记》中直言直书的实录遍布全文,但这并不能否认委婉实录——亦即“曲笔”的价值。司马迁的“曲笔”是在文学和史学间寻求的平衡点,书中在保留原始史实的基础上,对一部分艺术化处理、创造、升华,注重文学审美的同时更好地展现史实。在这里,“曲笔”不等同于臆说妄说,不等同于谤言谀言。没有绝对的“曲”,也没有绝对的直。直中有“曲”,才能明晰而深刻;“曲”中有直,才能含蓄又严谨。这类“曲笔”所反映的价值取向,本质上正是实录精神,“曲笔”只是其追求实录道路上或欣然而为之(文学层面)或必要而为之(史学层面)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对实录精神的发展和深化。《史记》中的“曲笔”同直书一样,其归宿都是寻求历史的真实,而“曲笔”把这种真实艺术化呈现出来,增添了无穷魅力。二者殊途同归、相得益彰,共同演绎着实录精神的笔底壮阔。而这,正是司马迁《史记》的珍贵所在,并使《史记》达到历史文学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