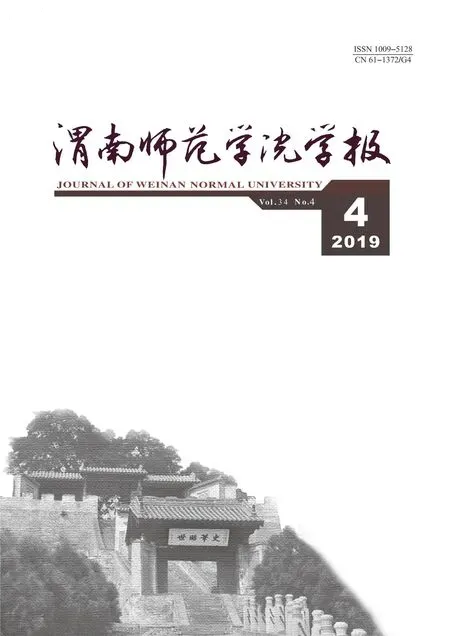论李广利的历史形象及其与司马迁宫刑之关系
2019-12-26田瑞文
田 瑞 文
(平顶山学院 文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0)
李广利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在武帝后期征宛伐匈的战争中一直身处主帅之位。然而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却说武帝拜其为贰师将军,是“欲侯宠姬李氏”[1]3853,后来司马迁又在《报任安书》中说:“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2]2730以至于遭受宫刑。自是而后,人们多是在裙带关系的视域中看待李广利,认为他“凭恃皇亲国戚专宠,纯粹是一个庸将”[3]47,武帝派他为统帅,完全是为了让其封侯,以博李夫人欢心。[4]20即使在肯定武帝征伐西域是为了“图制匈奴”的前提下,也仍然认为武帝“意在使其立功绝域以封侯”[5]。这些关于李广利的传统看法,实则与史多有不合。
一、李广利因军功而封侯
李广利生于倡家,因其妹李夫人得入宫中。《汉书·佞幸传》载:“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2]3725李家最先接近汉武帝的是李延年,《史记·外戚世家》记载:“李延年以音幸,号协律。协律者,故倡也。”[1]2401因李延年《佳人歌》,李夫人得幸于武帝,故《汉书·外戚传》说:“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2]3951李广利因是李夫人兄长,而为武帝所知晓,并被拜为贰师将军。李广利虽以李夫人之兄的身份进入武帝的视野,但其被拜为贰师将军,并不能完全看作是武帝因爱李夫人而恩及李广利的表现,伐宛归来,他是因功封侯,与已经去世三年左右的李夫人并无关系。
第一,作为武帝“欲侯宠姬李氏”之前提,武帝与李夫人的感情并非如史书所言生死相恋,情深义重。首先,武帝与李夫人的爱情神话——招魂故事是虚构的事件,不能用以说明两人深厚感情在李夫人死后还一直延续不已。《汉书·外戚传》载:“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2]3952鲁西奇认为“少翁招致李夫人亡魂的故事,无论如何,都不会发生”[6]45。原因是《史记·封禅书》所记少翁招魂的对象是王夫人,在桓谭《新论》中,虽然方士换成了李少君,但招魂的对象还是王夫人;又,少翁于元狩四年(前119)被杀,李夫人则是太初元年(前104)左右才离世[7]183,故此不存在少翁招魂李夫人之事。也就是说,作为武帝与李夫人深爱之明证的招魂事件是虚构的,那么武帝与李夫人之深爱也就不再那么令人深信不疑,而以之为基础的武帝因李夫人而偏袒李广利的说法也自然失去了令人信服的基础。其次,武帝对征伐大宛的李广利并无体恤之意。太初二年(前103),李广利征伐大宛不利,请求回到玉门关内,武帝的反应是:“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1]3854可见武帝并未因李夫人而特别恩宠李广利。再次,太初三年夷族李氏也可见出武帝对李夫人之爱随着李夫人的去世很快就消失了。《汉书·佞幸传》载:“延年弟季与中人乱,出入骄恣。及李夫人卒后,其爱弛,上遂诛延年兄弟宗族。”[2]3726《史记·外戚世家》载:“是时其长兄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不及诛。”[1]2401李氏被夷族应在太初三年,因为太初二年,李广利还在谋求回到玉门关内,显然此时李氏应未被夷族;而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2]202,“天子为万里而伐宛,不录过,封广利为海西侯”[1]3857,因此,李氏被夷族也不可能是在太初四年,所以李氏被夷族应该是在太初三年。此距太初元年(前104)李夫人之卒仅三年左右,此时李广利尚在征伐大宛的途中,武帝若念李夫人之旧情,若察李广利为其征战之辛苦,也不会因李季乱于中宫,而罪及李氏一门。此事足可说明,最迟至太初三年,武帝于李氏已恩断义绝。在武帝与李广利此后的关系中,再也没有了因李夫人而恩及李氏的可能了。所以《史记·大宛列传》言武帝“欲侯宠姬李氏”、踵其说的《汉书·外戚传》(李夫人传):“上以夫人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封海西侯”[2]3952,以及本此两说,认为武帝因李夫人而偏袒李广利的说法,都是不合具体史实的。
第二,从时人不愿西行的态度,也可看到李广利被拜为贰师将军并不是武帝“欲侯宠姬李氏”的体现。关于西取宛马一事,《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较《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更为详细:“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2]2694《史记》中也有“其后益习而衰少”一语,三家注没有注释此语,《汉书》师古注曰:“以其串习,故不多发人。”颜师古的意思是使者对西域越来越熟悉了,所以天子不再派遣更多的人去。这个理解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其后益习而衰少焉”的意思应是对西域进一步了解后,主动去的人越来越少了,其原因是西行之苦,“非人所乐”,“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2]2689就是一个例证。张骞卒于元鼎三年(前114),十年后,即西行使者“益习而衰少”的时期,李广利被拜为贰师将军。后人多从武帝与李夫人之裙带关系来看待这一事件,却忽略了时人对西域之行的态度,在西域之行百余一二的凶险面前,只有那些被武帝“激怒令赎复求使”者及一些“妄言无行之徒”才愿意亡命西去,而李广利所率的主体正是“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此体察李广利之心情,很难说李广利会认为至贰师城取马是一份美差。在这种背景下,司马迁说武帝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是“欲侯宠姬李氏”应是与史不合的。
第三,与卫青北击匈奴的情况对比来看,李广利第一次征伐大宛几乎没有实现目标的可能,以之说武帝欲使其立功绝域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首先,从对敌情熟悉程度看,汉、匈自高祖刘邦时就有交兵,故汉对匈奴较为熟悉,而对大宛则不然,直到张骞元鼎三年(前114)卒后年余,“西北国始通于汉”[2]2693,在李广利征伐大宛前,唯有张骞及郡国恶少年带来的一些并不完整的关于大宛的信息,甚至可以说是一些错误的消息,比如:“诸尝使宛姚定汉等言:‘宛兵弱,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强弩射之,即破宛矣。’”[2]2698姚定汉的话只要和张骞以及从西域侥幸返回的汉使言行做一对比,就可知其言之虚。因此可以说此时汉对大宛的情况知之甚少,而此正是兵家之忌。其次,从兵力上说,元光六年(前129)卫青拜车骑将军击匈奴,与之同时“击胡关市下”的还有公孙贺、公孙敖、李广,各万骑,此役唯卫青“斩首虏数百”,其他三人的结果分别是无功、失军、为虏所得。元朔元年(前128),“青复将三万骑出雁门”“斩首虏数千”。元朔五年(前124),“令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得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2]2474-2475,使者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而李广利远征并不熟悉的西域,却只有六千骑以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1]3853,而这数万的“郡国恶少年”实质上是“常常以各种方式进行抵制”[8]的“谪民”[2]200。这样看来,与卫青动辄数万的骑兵相较而言,贰师将军伐宛的兵力是非常弱的。最后,从结果上看,李广利伐宛第二年,“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1]3854,单看这条信息,自然会让人觉得李广利带兵无能,但尚有三点需要考虑:一是与军各万的公孙贺、公孙敖、李广的无功、失军或为虏所得的结果相比,李广利“士不过一二”的结局并不是最糟糕的,至少不能据此说李广利是个庸将;二是与张骞相比,李广利“士不过什一二”并没有比张骞“百余一二”的结果更坏;三是西域环境恶劣,大不利于行军。宛人的分析是:“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1]3852这虽是敌方的分析,但也大体符合实际情况。从李广利伐宛二岁“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1]3854的情况看,汉室的辎重补给也应是远远不足行军所需的,这与宛人的说法正相印证。基于以上几点因素考虑,则李广利第一次伐宛几无胜算,与战情相比,这次伐宛之败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李广利个人领兵才能的问题。
第四,李广利是因伐宛获胜被封为海西侯的,与李夫人之裙带荫恩无关。在李氏被夷族的第二年,李广利伐宛旋归,“天子为万里而伐宛,不录过,封广利为海西侯。又封身斩郁成王者骑士赵弟为新畤侯,军正赵始成为光禄大夫,上官桀为少府,李哆为上党太守。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余人,千石以下千余人”[1]3857。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封赏的范围自将军遍及士卒,赏赐的官爵或财物也多过其望。其中尤需注意的是,赵弟也因斩郁成王而封侯,也就是说这场伐宛之战,并不只是李广利一人封侯,此其一。其二,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余人,等等,可见受封赏者范围之广。这两点足以说明,伐宛之战,并非是武帝为封侯李广利而专门设计的,更谈不上是因为宠爱四年前已经离开人世的李夫人而封侯李广利。
综上来看,在编年体的叙事线索中,李广利拜将封侯事件的叙事顺序依次是:太初元年(前104)李夫人卒、西行大宛非人所乐、李广利被拜为贰师将军;太初二年(前103),李广利伐宛无果,欲回玉门关内,武帝怒止;太初三年(前102),武帝夷族李氏;太初四年(前101),李广利伐宛胜利归来,被封为海西侯。在编年体的叙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武帝与李广利的关系中,李夫人的作用仅仅是让武帝知晓了李广利,而此后两者的关系中,则完全没有了李夫人的因素。据此来看,《史》《汉》以武帝“欲侯宠姬李氏”为逻辑起点的纪传体叙事是不合史实的。
二、李广利为武帝朝三大将之一
李广利因李夫人进的事实,很容易令人想起卫青、霍去病,清代赵翼就认为:“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赵氏说:“李广利之进也,其女弟本倡,后得幸于帝,为李夫人。帝用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得其王母寡头以归,封海西侯。三大将……徒以嬖宠进,后皆成大功为名将,此理之不可解者也。”赵氏无奈地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间气所钟,固有不择地者哉”[9]51。这个解释显然是不恰当的,赵氏本人已经说了李广利的功绩是“得其王母寡头以归”,但他囿于李广利起身“嬖宠”,不愿正视其功绩,故未能理性地看待李广利虽以外戚进,而因军功兴的事实。赵氏的这种偏见,实则远绍司马迁、班固对李广利历史形象的塑造。
李广利在历史上的庸将形象,是《史》《汉》选择性叙事的结果,与史实并不相合。一是《史记》《汉书》“李广利传”的内容集中讲述的是李广利征伐大宛之事,伐宛的艰辛易于反衬出李广利的无能。而李广利自太初四年(前101)被封为海西侯至征和三年(前90)投降匈奴的十余年间,则一直是对匈奴作战的主帅,建功颇多(详见后述),对此,《史》《汉》“李广利传”均未展开叙事,而是将之分散在“匈奴传”中。这无疑就在叙事效果上,突出了李广利的无能,淡化了他的历史功绩,易于给读者留下“李广利是一个庸将”的印象。显然由叙事建构的庸将形象与李广利为武帝三大将之一的形象相去甚远。二是《史》《汉》“李广利传”是按照武帝“欲侯宠姬李氏”逻辑展开叙事的。《史》《汉》“李广利传”为了证成武帝“欲侯宠姬李氏”而回避了太初三年李氏被夷族一事。这一事件分别被记录在《史记·外戚世家》和《汉书·佞幸传》中。李氏夷族事件固然是因为李季乱于后宫而引起的,记录在《外戚世家》或《佞幸传》中更为符合因类相从的史例,但显然,如果它出现在“李广利传”中,那么“欲侯宠姬李氏”的逻辑是无法成立的。在“李广利传”的叙事中对此事的回避客观上造成了武帝是因李夫人而封侯李广利的假象,也造成了两年后的李陵事件中,武帝因偏袒李广利而罪责李陵、司马迁的假象,沿着这一逻辑,后之学者进而推导出了司马迁的悲情人生与《史记》悲剧意识生成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建构的前提显然也是经不起推敲的。然而《史》《汉》的巨大影响使后人几乎不加怀疑地接受了李广利的庸将形象,并自然认同了《史》《汉》建构的叙事逻辑。这与李广利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
李广利虽以外戚进,却以军功兴。从伐宛起的十余年间,李广利一直是对宛、匈作战的主帅,当得起武帝朝三大将之称。太初年间(前104—前101)李广利是伐宛主帅、天汉二年(前99)、天汉四年(前97)、征和三年(前90)等对匈作战中,李广利都是主帅。比如天汉四年,贰师将六万骑、步兵七万,老将路博德将万余人与贰师会、韩说将步兵三万人出五原、公孙敖将万骑,步兵三万出雁门[2]3777,从领军数量上可以看出,贰师是绝对主力。其中路博德、韩说、公孙敖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武帝在四人中,独以贰师为帅,显然也是对贰师领军作战能力的肯定,若李广利真是庸将,以武帝的精明和专制也不可能一直重用他。从匈奴的迎战态度看,也是将李广利作为最厉害的对手来看待的。天汉二年迎战贰师的是匈奴主帅“右贤王”、天汉四年匈奴“悉远其累重于余吾水北,而单于以十万待水南,与贰师接战”、征和三年匈奴迎战的主力分别是右大都尉、左贤王左大将、单于。后来,贰师降匈奴后,胡巫杀之时的说辞是:“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2]3781从胡巫的言辞中也可以看出匈奴是把贰师作为汉军主帅来看待的,这足以说明,武帝后期的十余年间贰师将兵对匈奴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从战绩上看,李广利也成绩不俗。伐宛前期的失败主要是战情复杂与兵力极弱的合力所致,后期武帝调整了对宛作战策略,大增兵力,“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以万数……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適,及载糒给贰师”[1]3854,结果是大胜归来,李广利也因之被封为海西侯;天汉二年(前99),征伐匈奴,“得首虏万余级而还”,虽然三万骑死伤“什六七”,但考虑到他迎战的是匈奴主帅“右贤王”,同时,与此役中老将公孙敖、路博德“亡所得”、李陵降敌[2]3777的结果对比来看,李广利的战绩并不算差;天汉四年对匈作战,贰师与军十万的单于连斗十余日,也表明了贰师较强的作战能力。征和三年(前90),贰师再征匈奴,“汉军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敌”[2]3779。这些战绩与卫、霍相比,虽稍有逊色,但客观来说,也是战功卓著。
戾太子事后,李广利因欲谋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刘髆为太子,事发,李氏再次被夷族,李广利最终投降匈奴,为卫律所害,死于匈奴。征和三年(前90)李广利出击匈奴,他的儿女亲家、丞相刘屈氂为之祖道,李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2]2883事发,刘、李皆被夷族。如果了解到征和三年武帝对立太子事的态度,就会知道李广利谋立昌邑王其实是自寻死路。首先,戾太子事后不久,武帝即已深悔不已。在对戾太子无尽的悯怀中,突然听闻丞相与李广利密谋新立太子,武帝自然会把一腔恨意发泄到二人身上;其次,两年后的后元元年(前88),上欲立六七岁的刘弗陵而杀其母钩戈夫人,理由是“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10]755。依此来看,颇有军功的李广利欲谋立其外甥昌邑王,恰恰触犯了武帝忌外戚壮大之讳,即便是武帝欲立刘髆,比照钩戈夫人的下场,李广利也不会有好的结果。从李广利的人生结局来看,在波谲云诡的武帝朝政局中,他的生与死、功与名似乎都是他自己所无法左右的,他只有通过不断的征伐去获得战绩,希望通过触摸自己的功勋能寻找到一些人生踏实的感觉,正是这样的一种心理成就了他不俗的战绩,也因之被后人目为武帝三大将之一。然而,因为司马迁的一句“沮贰师”,李广利以及与之相关的这段历史真相却一直被司马迁和李陵的悲情所遮蔽。
三、李广利与司马迁受宫刑无关
自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之后,人们多认为司马迁的宫刑之因是“沮贰师”,即武帝因深爱李夫人所以偏袒李广利,从而罪责李陵并下狱为陵说情的司马迁。然而征之于史,“沮贰师”说是不符合史实的,李广利与宫刑事件并无直接关系。吴汝煜说:“所谓‘沮贰师’,就是打击贰师将军李广利。其实,当时李广利出征并未遭到失败,比起出征大宛来,人马损失也比较少,加上李陵当时不隶属于李广利部下,所以不存在‘沮贰师’的问题。”[11]吴氏对此仅点到为止,未进一步讨论李广利与李陵之间的复杂关系及李陵之祸的真正原因,也未深究司马迁何以将宫刑之因归于“沮贰师”。
李陵兵败降敌并非李广利的责任。天汉二年(前99)的对匈作战中,李广利向西进军,李陵向北进军,两者不在同一条战线上,也不具有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因此,李广利没有驰援李陵的义务,他对李陵之降也不应负有责任。在李陵事件的研究中,学者们较少讨论武帝安排李陵为贰师将辎重的前情,对这一细节的讨论,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李陵事件的性质。实际上,武帝对匈作战的想法早在太初四年(前101)伐宛获胜后就已产生,“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1]3523,对武帝来说,让刚刚伐宛胜利归来的李广利为征匈主帅显然是无须多加考虑的事,那为什么武帝的布局中要让李陵为之将辎重呢?原因有二:一是李陵对北胡比较熟悉,早在李陵被拜为骑都尉时,他就“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2]2451;二是贰师伐宛军还时,负责接应的就是李陵,“汉遣贰师将军伐大宛,使陵将五校兵随后。行至塞,会贰师还。上赐陵书,陵留吏士,与轻骑五百出敦煌,至盐水,迎贰师还。”[2]2451由此看来,李陵与李广利早在伐宛后期就已经有所接触,比较熟悉。以上两点正是武帝欲使李陵为贰师将辎重的原因。武帝的这一安排意在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击之,胜算较大。然而将门之后的李陵立功心切,愿自领一军,这就在客观上分散了兵力,打乱了武帝的安排,也大大降低了此战的胜率。“天汉二年,贰师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召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陵召见武台,叩头自请曰:‘臣……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上曰:‘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予女。’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2]2451从实际的战情看,一方面,缺少了李陵的补给,“匈奴大围贰师,几不得脱”[2]3777;另一方面,李陵兵少而败,被迫投降。这两方面的结果,都可说明兵力的分散是导致此次征伐匈奴失败的原因之一,而兵力分散的主要原因是李陵“恶相属”于贰师,从这一层面看,是李陵负了贰师,而非相反。又,贰师出酒泉西行击右贤王,而李陵北行过居延千余里,两者之间距离过远,李陵虽曰:“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实际上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贰师被困,几不得脱,正是这一实际情况的反映;同时,贰师西行被困,自顾尚且不暇,更别提千里驰援李陵;再者来说,此次征伐,贰师与李陵各领一军,相互不具有领属关系,贰师也没有驰援李陵的责任。所以,后人将李陵的失败归于贰师,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李陵获罪及司马迁下狱非关李广利,而是与当时人们对降北者的处罚惯例有关。李陵其实是可以不降的,《汉书·匈奴传》载:“单于围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脱归汉者四百人。”[2]3777李陵的五千步卒最后尚有四百人归汉,以李陵的勇武完全可以脱归还汉,可为什么李陵选择降敌呢?实际上李陵欲降敌而后归的做法是有先例可循的。上一年为虏所得的浞野侯赵破奴刚刚“亡还,天子客遇之”[2]2454。更早的降归不问其罪的例子是李陵的祖父李广,元光六年(前129),李广出雁门击匈奴,为匈奴生得,亡归,当斩,赎为庶人。在这种降归的传统下,李陵之降并不奇怪,司马迁说他有降后伺机而归的想法,当属实情。李广当时降归的处置,给我们分析李陵之降提供了一种思路,即从应该“当斩”和实际“赎为庶人”两个层面来讨论。从降敌理应当斩的层面看,朝堂之上“众皆媒孽其短”是正常的,无甚不妥。从“赎为庶人”的实际处置层面看,只要李陵降而后归,也应是被接受的,司马迁说李陵“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正是从实际处置的层面上看待李陵之降的。司马迁的这一说法得到了武帝的认可,“久之,上悔陵无救……乃遣使劳赐陵余军得脱者”。一年后,武帝又令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公孙敖无功而返,随口应付差事说李陵正在为匈奴练兵,“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2]2457。公孙敖的谎言改变了李陵投降的性质,从可能的假投降变成了真投降,假投降是可以接受的,武帝等了一年即为明证,但真投降则无法接受,李陵必须按照当时对降北者夷族的处罚惯例接受相应的惩罚。司马贞《索隐》注“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曰:“降敌者诛其身,没其家。”[1]2711《尉缭子·重刑令》载:“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众,命曰‘国贼’。身戮家残,去其籍,发其坟墓,暴其骨于市,男女公于官。”[12]52近些年出土的汉代文献中,也不乏类似的记载。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载:“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13]3银雀山汉简《敦煌汉简》(983):“亡入匈奴,外蛮夷……皆要斩,妻子耐为司寇作如。”[14]256-257这些对降北者的处罚,表明了当时社会人们对降敌的普遍认识。武帝夷族陵家,符合当时社会对降北者的处罚惯例。这一处罚还进一步牵连到与李陵“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的司马迁,司马迁虽然不是李氏家族的一员,但在众皆“媒孽其短”[2]2729中,司马迁独为李陵说情,也自然是被看作李氏之党的,所以司马迁也同样要被问以死罪,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遂下于理”的实际情况。
但司马迁并没有理性地认识到李陵之祸的真正原因所在,而是错误地认为是武帝偏袒李广利所致。司马迁的逻辑起点是武帝所言的“将恶相属也”。所谓“恶相属”就是说李陵不愿为贰师的属官,武帝对李陵不愿为贰师将辎重原因的推测是合乎情理的,从后来武帝令路博德为李陵之应,路博德“亦羞为陵后距”[2]2451一事上也可见李陵“恶相属”之心理,即不愿为师“后距”,而意在立功于前锋。武帝“恶相属”推测之语,实则建构了李陵与贰师在建立功名问题上的矛盾关系,司马迁正是沿着这一逻辑,把李陵惟五千步卒与贰师的三万骑对比,将李陵的失败与贰师“生恨”未予驰援关联起来,把李陵五千步卒杀敌万余与贰师三万铁骑“几不得脱”对照起来,从而认为自己对李陵的肯定,在武帝看来是“沮贰师”,即对贰师的“毁坏”(颜师古语)[2]2732,故下己于理。司马迁之所以会有此联想,直接诱因固然是武帝所言“恶相属”一语,但深层原因则是他对贰师的偏见所致,即贰师封侯是武帝“欲侯宠姬李氏”,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一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司马迁对外戚贰师的偏见,不仅影响了他对李陵事件的叙事,也更深刻地影响到《史记》的相关书写,钟书林说:“将《李将军列传》与《卫将军骠骑列传》相对读,不少人都发现了司马迁褒李广,而贬卫、霍的情感倾向。”[15]钟氏的观点有助于人们更客观地认识到司马迁在将门、外戚的历史叙事中,情感好恶因素对叙事效果的深远影响。然而后人往往容易把当事人的唯一叙事,当成无情感影响的史笔资料来看待,忽略了对当事人情感倾向的分析,也就容易忽略对相关史实的检讨。这种接受的误解从班固既已开始。班固《汉书·李广传》附的《李陵传》在司马迁所谓“欲侯宠姬李氏”的逻辑基础上,进一步点明了李陵与贰师在军功上的对照关系,并以之证说此为“沮贰师”之成因:“上遣贰师大军出,财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功少。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2]2456班固的这一说法也就坐实了“沮贰师”是司马迁遭受“腐刑”的原因,从而使“沮贰师”说由司马迁的假设推理变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也成了后世《史记》接受史的一个重要逻辑起点,影响深远。这一观点固然有其形成的内在逻辑,但却是与史不合。
司马迁之所以在《报任安书》中认为是“沮贰师”致其宫刑,也和他于征和二年作是书时朝中的一些人事变化有关。征和二年(前91),身为中书令的司马迁是“游宴后庭”的武帝身边的近臣,与甚得武帝信任的霍光,多有交集,他们不仅同为武帝晚年身边的近臣,也有更进一步的私人关系,比如司马迁的女婿杨敞“给事大将军莫府,为军司马,霍光厚爱之”[2]2888。而霍光“素与陵善”,昭帝时,霍光辅政,“遣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2]2458。这至少说明,从天汉二年李陵被俘到昭帝时,霍光对好友李陵是持同情态度的,这种态度可以看作是对司马迁的支持,所以在事情已经过去八年的征和二年,司马迁仍然在《报任安书》中坚持自己当初做法的正确性,即认为李陵有“国士之风”,其行为值得肯定。另一方面,自太初三年李氏被夷族后,李广利一直积极重建朝中的政治利益集团,他与丞相刘屈氂结成了儿女亲家。从征和三年(前90)刘屈氂、李广利被夷族一事看,刘、李集团与武、霍集团是利益的矛盾双方,站在武帝集团的政治立场来看,以对立派系中的李广利为怨恨对象也是合乎司马迁心理发展轨迹的。“沮贰师”说的形成过程,据此可见一斑。
通过以上史实的考论,可知李广利作为武帝朝三大将之一,是当之无愧的。然而由于《史》《汉》的选择性叙事,使李广利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依靠裙带关系而兴的“庸将”形象,这与李广利真实的历史形象相去甚远。同时,《史》《汉》塑造的受武帝偏袒的李广利的“庸将”形象,也使人们轻易地相信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言的“沮贰师”的观点,从而将两个实际上并无关系的事件联系起来,构成了后来司马迁阐释史建构的逻辑基础,形成了痛恨李广利、同情司马迁的阐释框架,《史记》的悲剧性等问题就是在这一框架中展开论述的。然其逻辑前提既然与史不合,那么本此而来的相关论述也需要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