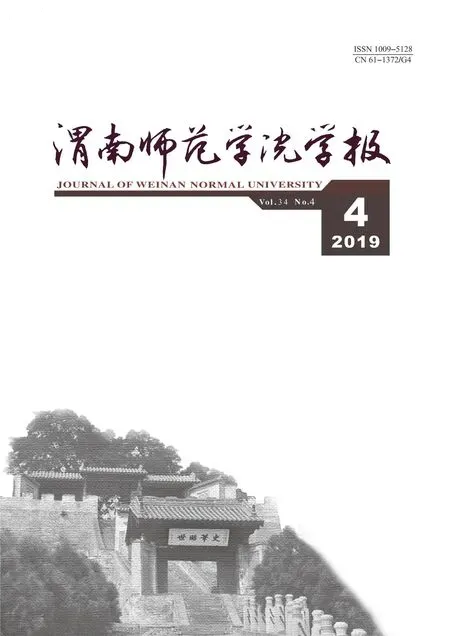司马迁的布衣情结
2019-12-26李领弟
李 领 弟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经笔者考察,在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中,“布衣”共出现43次,“黎民”11次,“庶民”17次,更在67卷中提到“百姓”出现高达178次。还有与此相近的元元、黎庶等词也多次出现。司马迁从近三千年的历史中披沙拣金,挑选出最能体现中国历史发展变化的人,为他们树碑立传,“布衣”形象也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司马迁不因他们位卑而不予以记载,而是使用大量篇幅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平民布衣形象。这充分说明了司马迁重视底层人民的力量,赞赏他们的精神品质,他的这种庶民布衣情结最能打动我们的心弦。司马迁的布衣情结主要表现为在《史记》中多次强调“布衣”一词,并蕴含丰富的内涵,塑造了一大批有操守的布衣之士,歌颂了他们的历史功绩,并在《史记》中处处体现出布衣地位的提升!本文旨在揭示“布衣”一词在《史记》中的多重内涵,确定《史记》中布衣阶层比较明确的范围,以他笔下典型的布衣形象为例,分析探讨司马迁形成布衣情结的缘由以及这种布衣情结所带来的影响。
一、“布衣”在《史记》中的多重内涵
“布衣”一词在《史记》中共出现43次,其内涵并不是单一的。“布衣”顾名思义就是麻布衣服,但它作为一个沿用至今的历史名词,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的代称,还包含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一)布衣的物质内涵——粗布麻衣
《说文解字·巾部》载:“布,枲织也。”[1]160“枲”泛指麻,古代的“布”就是指麻葛之类的织物,因此“布衣”就是指平民百姓的最普通的廉价粗布衣服。
《史记·平准书》:“初,式不愿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为郎,布衣屩而牧羊。”[2]1719此处的“布衣”即指麻布衣服。司马迁讲述了平民出身、靠牧羊致富的卜式,当官之后依旧穿着布衣草鞋牧羊,赞扬了卜式输财助边,济国家之困却不求官、不慕名、不爱财的爱国行为。又如《史记·鲁周公世家》:“三十一年,晋欲内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因六卿谢罪。”[2]1856这里的“布衣”亦指麻布衣服。
(二)布衣的政治内涵——平民百姓
《荀子·大略》载:“古之贤人,贱为布衣,贫为匹夫。”[3]513汉代桓宽《盐铁论·散不足》亦载:“古者庶人耋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4]350在古代,普通人只能穿麻布做的粗衣,要至八九十岁才可穿丝制衣服,所以就把老百姓称为“布衣”。这是把“布衣”指代为平民百姓最早的定义。于春媚于《论布衣及布衣精神的内涵》一文指出:“在我国古代,服饰是‘礼’的一种表现,是身份的象征。布衣因其粗劣而多为庶民所服,于是成为庶民的代名词。由此,布衣开始借指平民百姓。”[5]
《史记》中出现的“布衣”,多指平民百姓的身份。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2]293-294司马迁笔下的尉缭,虽为一介布衣,却能审时度势。尉缭在被秦王嬴政赏识之初曾认定嬴政的面相刚烈,欠缺礼遇天下百姓的仁德之心,于是多次尝试逃离秦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2]2102范蠡对勾践为人以及封建社会中的君臣利害关系看得非常清楚,所以经商大获成功之后便再一次急流勇退,辞官散财,逍遥而去。司马迁赞扬了范蠡忍辱负重,发奋图强的精神,批判了勾践滥杀功臣的恶劣行径。又如《史记·萧相国世家》:“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2]2435-2436司马迁寥寥数语便刻画了东陵侯召平的形象。召平在秦亡之后沦为平民,以种瓜为生,韬影晦迹,鄙视功名,多为历代文人称颂。《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2]3076“黔首”秦时亦指百姓,司马迁将布衣、黔首相连而说,强调其平民布衣的身份。除此之外,还有《史记·淮阴侯列传》载:“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2]3147司马迁旨在记述韩信以布衣起家,为人不拘小节,为佐汉破楚立下汗马功劳,同时也对韩信的悲惨结局充满了同情惋惜。《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2]2512绛侯周勃做平民的时候,粗陋平庸,曾为平定七国之乱,维护国家统一做出贡献,功勋卓著,晚年却被诬告谋反而被捕入狱,司马迁对此愤慨不已。
此类例子在《史记》中还有很多,此不赘述。司马迁旨在强调布衣作为平民百姓的身份,这是布衣内涵由单纯的服饰含义到具有一定阶层意味的身份含义的一次转变。
(三)布衣的精神内涵——平民知识分子或平民侠义之士
从指代平民百姓的身份到蕴含某种人格品质的精神含义,是《史记》中“布衣”内涵的又一次转变,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司马迁将布衣与“士”“侠”等联系起来,开始使用“布衣之士”“布衣之侠”的称呼。“士”代表中国古代的一个社会阶层,具有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内涵也十分丰富。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的引言中用西方“知识分子”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的“士”,他说:“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的私利之上的。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不难看出:西方学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6]2詹福瑞也在《布衣及其文化精神》一文中指出:“布衣虽然在一般意义上是指平民与寒士,但大多数场合不是泛指一般的平民百姓,尤其对于那些口不离布衣的士人来说更是如此。在他们的心中,布衣绝不是普普通通的百姓,而是胸怀王霸之术、屈指可取公卿的人。”[7]
由此可见,布衣之士虽为一介平民,却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形成了我国社会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布衣精神。孔子便是这种文化传统的典型代表。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孔子来自中国文化的独特传统,代表‘士的原型’。”[7]6《史记·孔子世家》赞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2]2344孔子以布衣兴学,开创儒家学派,学说传世十几代。上至天子,下至百姓都将他的话作为评判道德的标准,可以说他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司马迁因其“布衣”而宗之,因其人格修养和文学艺术修养而仰之,将其放入“世家”体例中,足见他对孔子的尊崇仰慕之意。
又如《史记·苏秦列传》载:“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贤君之行义,皆愿奉教陈忠于前之日久矣。”[2]2713司马迁把布衣称之为“士”就完全有别于一般的平民了。布衣之士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热情丝毫不亚于卿相大臣,这里将“卿相人臣”和“布衣之士”相对,旨在强调他们对国家的忠心程度是相同的,只是贫富悬殊而已。《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载邹阳上书梁孝王的一段话:“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贱,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逢、比干之意,欲尽忠当世之君,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思,欲开忠信,辅人主之治,则人主必有按剑相眄之迹,是使布衣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2]2987邹阳希望梁孝王可以给那些身在贫贱,却怀有济世之志的布衣穷居之士多一些施展抱负的机会。司马迁认为此段文字比物连类、言辞恳切,并对邹阳的坦率耿直、不屈不挠大为赞赏,亦表现出他对布衣之士的才能和品格精神的肯定。
除此之外,《史记·游侠列传》中还出现了诸如“布衣之侠”“布衣之徒”的称呼。如“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2]3839,又如“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2]3839该传中记载了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五位游侠的事迹。司马迁认为他们的行为符合道义,重诺守信,轻生取义,廉洁而有退让的精神,能以一介布衣而名满天下,有值得称赞的地方,同时还对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对统治者诛杀这些“布衣之侠”表示愤慨。如《史记·游侠列传》中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2]3845司马迁讽刺了以公孙弘为代表的儒生们皆以猎取功名为目标,以阿谀人主、粉饰酷法为能事,从而成为第一个为布衣之侠正名并加以歌颂的人。司马迁这种包含着民本思想和侠义精神的先进意识正是源于其深藏于心的布衣庶民情结。
总而言之,布衣精神就是古代平民知识分子或布衣侠士所坚守的一种信念,他们不畏强势,心怀天下,自由而旷达。于春媚说:“(他们)身为平民却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及独立自由的人格精神。这种精神不因身份境遇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它产生于封建专制时代,是对专制压迫的反抗,是历史的进步力量,是祖国优秀的精神文化遗产。”[5]
二、司马迁布衣情结的成因
司马迁在《史记》中讴歌布衣的人格品质,弘扬平等博爱的精神。赖明德认为司马迁的这种思想是“一种推崇平民精神,关心民间生活,探讨社会真相、肯定市井人物,旨在弘扬平等、自由、博爱的民本思想”[8]547。一般来说,人的思想的形成不外乎三方面原因:对个人以往生活经历的感悟和总结;所处的时代环境背景的影响;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和升华。司马迁于《史记》中表现出的布衣情结就与这三方面的原因不可分割。
(一)个人的生平经历
关于司马迁的生平经历,研究者众多,成果也颇丰,分析研读,可知他布衣情结的成因主要有三方面:耕读、游历、受刑。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2]3970-3971
根据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的自述,我们可知其早年在龙门有过耕读放牧的经历,年仅十岁便已习诵古文;随后相继游历了江淮、汶泗、齐鲁、鄱薛、梁楚等广大地区;出仕为郎中后又游历了很多地方,还曾奉命出使到巴蜀以南的邛笮、昆明等地考察。早年的耕读生活使他深切体验了下层平民布衣的生活状况,感受到了人民最真切的呼声,游历的途中不仅可以让他饱览山河、寻访文化遗迹、收集历史资料,还可以让他真正深入到民间社会,向布衣百姓进行深入的调查和学习。因此,无论是智慧深藏的隐者,还是行侠仗义的侠士,抑或是心怀天下、积极进取的士人,都在《史记》中留下了身影,使我国的传记文学内容更加丰富。
他本以为可以一直在游历创作中度过,但“自古天意高难问”。四十岁的时候,一场意外的灾难降临到司马迁的身上,成为李陵事件中的受害者,被囚于监狱处以宫刑。韩兆琦曾说:“受宫刑一事给司马迁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耻辱,但也使他的思想获得了净化和升华。从此他的眼光更敏锐、更有洞察力,他的立场感情也更加向下,更加接近劳动人民了。这对于贯穿《史记》的批判精神与民主性的加强,显然有着重要的意义。”[9]2受刑之后,司马迁内心无比自卑,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低贱,不过倡优、蝼蚁一般。《报任安书》说:“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9]1811因此他发愤著书,希望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建功立业,名垂青史。明朝有些人认为,司马迁之所以在《史记》中塑造了很多惩恶扬善,重信重义的布衣侠士,主要是因为他在遭受责罚之时,竟无一人为他辩白。《报任安书》:“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9]1811统治者专横凶残的本质,官场的利欲熏心,让他更深切地体会到侠义精神的可贵。
《史记》是在司马迁身负屈辱,忍受酷刑的境况下完成的。他立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遵循实录原则,力求保持人物的本来面貌。司马迁几乎注意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对平民布衣的关注,也成为司马迁独特的视角。他突破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从自身的生存状况出发,站在底层平民的立场来判断是非,表现出对布衣命运及布衣所生存的环境的关注,体现出那种“礼不卑庶民,刑不尊大夫”的观念,显示出史学家的开明与智慧。
(二)时代环境的影响
司马迁的这种布衣情结不仅和他个人的生平经历有关,与他所处的封建社会初期人民地位上升的时代性质和政治环境也不无关系。西汉的开国英雄大部分起自布衣,不仅为布衣出身的人开辟了道路,也极大地提高了布衣阶层的社会地位。马彪在其导读及译注的《史记》序言中说:“时代的巨变必然反映于历史记述之中,《史记》中就处处体现着‘布衣’(穿麻布衣服的庶民)地位的提升,刘邦从‘布衣’成为皇帝,以韩信、萧何为首者成为‘布衣将相’。”[10]23刘邦造就了一个布衣皇帝的新时代。他称帝后按功授爵封官,追随他打天下的诸臣,绝大多数起自布衣,从而开创“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学界对此研究颇丰,例如张胡玲《试谈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张健强《两汉布衣入仕研究》、唐赞功《汉初“布衣将相”浅论》等。
于春媚说:“秦汉之间布衣集团的胜利,不仅带来布衣政治地位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对布衣的人格塑造起到了推动作用。布衣当政打破了天命王权的神话,为战国以来的天命怀疑论思想提供了凿凿佐证。”[5]这一点在《史记》中也有明确体现,刘邦是历史上第一个布衣皇帝,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其多以布衣称之。《史记·高祖本纪》:“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2]2187《史记·萧相国世家》:“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2]2431《史记·留侯世家》:“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2]2467《史记·张耳陈馀列传》:“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2]3104《史记·韩信卢绾列传》:“高祖为布衣时,有吏事辟匿,卢绾常随出入上下。”[2]3179司马迁赞扬刘邦以一介布衣崛起于乱世,诛秦抗敌,平定天下,成为叱咤风云的历史英雄。
不仅如此,刘邦还在较大程度上摆脱了因为出身问题而对人才使用的限制,把选官对象的范围向布衣阶层开放,一大批的“布衣将相”作为一个新的政治群体,积极活跃于政治舞台,将布衣的地位推到了一定的高度。例如《史记》中还记述了以韩信、萧何为首的布衣将相的地位的提升,他们以建功立业为手段,积极活跃于政坛之上,颠覆了承侯世卿的传统格局。这是历史的进步,值得历史的肯定。孙家洲在《汉代的“布衣”意识》一文中说:“在以服饰显示等级身份的古代社会,布衣是与贵族相对立的平民百姓的统称。但在汉代,‘布衣’一词还带有明显的褒义,享有一份特殊的尊荣。譬如,得士人死心追随的田横,不愿向刘邦俯首称臣,慨然自杀。刘邦为之流涕感叹:‘嗟乎,有以!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非贤哉!’并以王者之礼安葬田横。”[11]180刘邦出身布衣,具有平民化的精神,能体察民情,虚心纳谏,任贤举能。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布衣之士也都充满着强烈的进取精神,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渴望投身于官场,实现理想抱负。
(三)对前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升华
追本溯源,司马迁的布衣情结主要是对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升华。我国民本思想的发展源远流长,商代以前仅限于神话传说中,或者说处于朦胧状态,殷商西周时期便进入萌芽阶段。《尚书·五子之歌》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2]52和《春秋穀梁传》“民者,君之本也”[13]364是“民本”一词的最初来源。司马迁在《史记》中就直接继承了这一思想,《史记·殷本纪》载“王嗣敬民”以及“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都在强调重视民众,为百姓谋福!
因此,司马迁特别支持布衣平民依靠个人的努力去建立事业,积累财富。《太史公自序》:“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2]3998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塑造了一批正面的、积极的、有生气的商人形象,如白圭、乌氏倮、寡妇清等,赞扬了他们于国家和社会有益的商业行为。正是出于对平民布衣的重视,司马迁才会讴歌他们经商创业的商业活动,一反重农抑商的社会观念,将商人的社会地位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的经济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民本思想的形成确立时期,关于民本思想的论述就更加丰富了。例如《孟子·万章章句上》记载的关于对布衣之士伊尹的任用:“伊尹耕于有萃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14]167由此可见统治者任用布衣之士早有传统。司马迁也在《史记·殷本纪》中记述了汤得民心,推翻了夏桀的暴政,礼贤下士,在政治上启用平民阶层的伊尹。“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2]122-123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对司马迁的影响之大。
正是这种民本思想使得司马迁在著史的时候,将自己置身于平民生活之中,用一种平民布衣的心态和角度去塑造人物。无论是布衣、商人、地主还是社会的游浪之群,如日者、游侠、滑稽等都用自身独有的技艺渲染了《史记》的浓重气氛,让千百年来的读者看到了平民布衣的力量,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灵魂,更为《史记》增添了民本思想的特色。
三、司马迁布衣情结的影响
(一)铸造了《史记》在史传文学中的独特品格
司马迁这种包含着民本思想和侠义精神的布衣意识,使得《史记》多了一份平民气息,同时也是《史记》成为千百年来人们喜爱的历史读物的原因。正如梁启超说的那样:“《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15]19司马迁这种“以人为本”的平民意识,不仅让《史记》充满了人情味,也使得《史记》成为中国的“正史”之首!
中国的“二十四史”以及《国语》《左传》等史书,虽然也蕴含了一定的民本思想, 但只限于某个历史问题或历史事件。它们大多为奉旨修编,主要以记录政事和王孙贵族为主,极少涉及下层布衣。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一部私人撰述的历史著作,显示出有别于传统官修史书的魅力,其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不惜笔墨,为布衣平民树碑立传,不因他们位卑而不予以记载。他曾在《史记·伯夷列传》中感慨:“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2]2574司马迁为那些没有承侯袭爵相续,仅凭布衣之身立有功德,却无人为之立传,事迹无法流传于后世的布衣之士感到惋惜。所以他以为那些布衣之士树碑立传为己任,充分肯定布衣平民所做的历史贡献,重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因此,从平民意识的角度来考察“二十四史”以及《国语》《左传》等史书,无论是其广度还是深度,都不能与《史记》相提并论,也铸就了《史记》在史传文学中的独特品格。李长之说:“从来的史书没有像它这样具有作者个人的色彩的。其中有他自己的生活经验,生活背景,有他自己的情感作用,有他自己的肺腑和心肠。所以这不但是一部包括古今上下的史书,而且是司马迁自己的一部绝好传记。”[16]223《史记》以布衣精神表现出来的思想优势,也超越了历代史书,成为中国史传文学公认的经典。
司马迁站在宽仁爱民的立场上,在《史记》中记录了不同类型的布衣之士和平民侠客,真实地反映了布衣阶层的精神风貌。他们所体现出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品质为中国史传文学增添了一批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底层人物群像,成为中国传记文学的里程碑。《史记》不仅超越了它的时代,而且对后代史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它所蕴涵的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起了一面光辉的旗帜,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关注布衣平民,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几千年过去了,《史记》仍然拥有大批读者,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知识分子还在这些传记故事中寻找着灵魂的慰藉和精神的支柱。所以,不管历史如何变迁,文学创作贴近下层社会,贴近人民群众,永远都是时代的主流。
(二)对后世布衣之士的借鉴意义
司马迁笔下的布衣之士,不畏权势,胸怀济世之志,自任当世之责,自由旷达,倾其一生践行着布衣精神。他们虽身处贫贱,却通经籍、明道义,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处世,等待时机一展抱负,他们的精神激励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布衣之士。
我国著名的贤臣名相诸葛亮,出山前也不过一介布衣,却能以才智名满天下。我们从《三国志》《出师表》等著作中可知他对天文地理等无所不通,而且在他后来的一些论述中,也可见《史记》《左传》等著述对他的影响。他曾于《出师表》云:“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17]130他隐居山野,安贫乐道,淡泊名利,不求富贵,却在社会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克己奉公,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践行着自己的忠心,是布衣精神的典型体现。
唐代的李白虽为一介布衣,却傲骨天然,不卑不亢,追寻心中侠义。在《与韩荆州书》中,自称“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17]147,自有一种布衣之士的潇洒从容,隐约其间。李白才华横溢,却在官场上屡屡碰壁。他欣赏战国时期鲁仲连的品行和人生态度,为其写了不少诗句,且大多用以自比,表达自己不贪图虚名的高尚情怀。他希望自己能够像鲁仲连那样,建立一番功业,然后飘然远去。瞿蜕园、朱金城于《李白集校注》言:“以鲁连功成不受赏自比,为李诗中常用之调。例如《在水军宴幕府诸侍御》:‘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留别王司马》:‘愿一佐明主,功成返旧林。’《五月东鲁行》‘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皆是。”[18]112司马迁于《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云:“鲁连其指意虽不合大义,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2]2989司马迁十分欣赏鲁仲连,认为他虽为布衣,却能放浪形骸,不屈服于诸侯,不为功名利禄所羁,荡然肆志,得以自主。可见司马迁笔下的鲁仲连对后代布衣之士人格形成的影响之大,他不仅对李白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杜甫也是一个典型,他虽为一介布衣,却时刻忧患天下,希望辅佐朝廷,成就圣贤事业。《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记录自身处境“床头屋漏无干处”“布衾多年冷似铁”,但他牵念的却是全天下的布衣穷处之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种心怀天下的胸怀和责任感,也使得他的诗歌思想内涵更加深刻。不仅如此,杜诗中还有许多赞美司马迁批判精神和实录精神的诗句,例如“美名光史臣,长策何壮观”(《舟中苦热遣怀奉呈阳中丞通简台省诸公》),他将司马迁的这种精神完全继承下来,创作了许多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也是其“诗史”意义的具体表现。
这样的典型形象在我国文学史上不胜枚举,在此不一一列举。我们由此可见,无论是司马迁本人还是《史记》中所塑造的这些布衣之士,他们用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成为后世知识分子学习的楷模,也是我国宝贵精神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现当代文坛上一大批作家,诸如老舍、路遥等,他们多以平民视角反映了大众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揭示了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流露出浓厚的平民情结。他们的这种平民意识为现当代文坛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文学价值。
我们研究司马迁布衣情结的文化意义就在于,虽然历史和时代在不断变迁,但是布衣之士的精神信念是历经千载而不灭的,不仅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布衣之士,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也极具启示意义。布衣文化也因此成为我国优秀传统思想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布衣之士的社会价值和人格价值对现在的知识分子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对和谐社会的建设越来越重要,民本思想自然而然被提上日程。作为一名当代的知识分子,我们更应该秉承司马迁留下来的人文主义思想,坚持以人为本,不断解决好人民的问题,增加人民的幸福感;继承布衣之士的精神内涵,不负重托,投身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