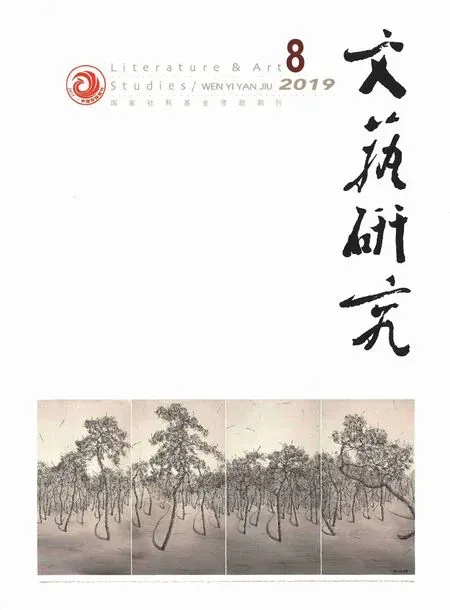作为文学叙事的明清鼎革
——以《桃花扇》的写作、接受和重写为中心
2019-12-21卢燕娟
卢燕娟
明清鼎革,从中国历史发展角度看,是最后一次王朝更替,也是继蒙古灭宋建元之后的又一次非汉族政权入主中原;从世界历史视野看,欧洲进入现代、重构世界秩序的17世纪,是中国从天下中心走向世界边缘、即将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夜。如何理解和讲述这场鼎革巨变,是从明清之际一直延续到现代的思想文化史中极为困难也极为重要的问题。
明清之际的士人要处理的不仅是旧主新恩、夷夏之辨这些传统问题,亲历崇祯误国、弘光亡国之痛,又置身以崇孔尊儒、吊民伐罪建构自己统治合法性的新朝,他们一度深信不疑的君国一体、夷夏之辨等原则不断受到挑战乃至颠覆。在天崩地裂、国破家亡的兴亡之感中,他们更需考虑如何从天下、民族、文化、信仰的大崩坏中重建一种新的历史文化表述,以解决从宏大理论到切身经验所遭遇的困境。他们的持续反思虽然没有引发西方那样翻天覆地的思想革命,却也使得儒家思想从内部开始裂变:道德至上原则与君国一体、夷夏之辨等思想观念本来共生于儒家理论内部,前者却在这一时期呈现出覆盖后者、成为判断政治文化合法性更有效标准的趋势。二百余年后,晚清覆灭,中国被卷入现代世界,屡历外侮而内患频仍。对此间从传统进入现代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颠沛流离、四顾茫然之苍凉,与明清鼎革之际的山河飘摇、江山残照之感大相共鸣;而政权之新旧更替、华夏文明与异质文明的交锋乃至在他族侵略压迫中被催生的民族认同与诉求,也不断与明清之际士人们所追问和反思的理论问题相接应、碰撞。因此,他们不断激活、回应、征用与重构明清鼎革的情感经验和理论问题,并以之与自己所置身的时代情感相共鸣、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相呼应。这就使得明清鼎革从二百多年前的天下兴亡问题进入现代中国认同与建构的问题框架中,不断释放出巨大的情感能量,生产出新的理论维度。
孔尚任完成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的传奇剧本《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①,以文学形式再现了当时的思想冲突和文化裂变。因此,虽然中国现代主流文学日益从西方现代文学而非中国传统文学中汲取资源,致使《牡丹亭》《西厢记》等经典传奇一度沉寂,即使后来重上舞台,也往往是单纯再现,而鲜有再创作,但以明清鼎革为主题的《桃花扇》却始终活跃在近现代历史中:其情感经验、经典意象被反复征用②,其核心故事则被重写为小说、戏剧及影视剧等多种形态③。
当下对《桃花扇》写作、接受和重写的研究,或着眼于传奇与晚明史实的关系及其对兴亡教训的思考④,或着力于现代话剧、小说、电影对原有故事主题的转移和情节的更改,从影射时事、服务抗战角度归因,从艺术表现、情节逻辑角度评价⑤,鲜有研究将贯穿三百余年间《桃花扇》的写作、接受和重写,置入思想文化史上的明清鼎革问题视野中阐释,从而注意到:文学叙事的建构与沿革,始终呼应、呈现着从天下兴亡到现代国家认同与建构的历史意识变迁。孔尚任的写作本身呈现出明清之际儒学理论内部发生的冲突、裂变。当晚清知识分子借明清鼎革之痛召唤汉族的华夏认同,以排满与反帝相并提时,梁启超对《桃花扇》的评论与批注就在现代民族主义的视野中开始思考“何为中国”“中国何以现代”等问题。而在抗日战争期间,文化界从以对晚明、满清、李自成农民军等诸多政治势力的阐释、反思来回应不同政治力量的抗日主张时,欧阳予倩、周贻白等人的“重写”则开启了对“由谁、怎样从危机中创造现代中国”的思考。
一、以道德原则突破君国一体、夷夏之防观念——孔尚任写作所呈现的思想文化裂变
明清鼎革之后,对明清两朝的价值判断与情感立场成为当时所有试图讲述这一事件的士人不可回避的问题。这里有两重问题:其一,作为明朝旧臣或旧臣的门生后人,他们要在君臣大义上有其立场和解释;其二,作为汉族儒生,他们要就夷夏之防做出判断和选择。然而,有明一代,屡经党祸、权宦,至崇祯朝,君臣离心已积重难返。孙奇逢云,建文之难,“一时靖节之臣,死者死,遁者遁,不下数百人”;而到崇祯时,“死社稷者仅二十余人,以视建文时又何如哉”⑥?明清之际的士人在崇祯误国、弘光祸国的痛切经验中打开了以臣子批评君主的可能空间。张岱说:“自古亡国之君,无过吾弘光者,汉献之孱弱,刘禅之痴呆,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王毓蓍曰:‘只要败国亡家,亦不消下此全力也。’”⑦甚至对死国之君崇祯,邵廷采也批评他“刚愎自用,莫肯虑下,屡用诏狱、廷杖以待言者,任人理财,每与《大学》平天下之道相反”⑧。这些批评不仅挑战了传统儒家君臣秩序,更蕴含着两层极具挑战性的逻辑:其一,君主是可以被批评的个体,不再凭借血统就能代表国家;其二,臣子批评君主的合法性在于:国家社稷关乎天下存亡,其意义大于君主,所以对不能存社稷的君主,臣子可以批评甚至否定。
同时,清朝前期统治者,既以尊孔崇儒标榜自己的文化合法性,又以吊民伐罪建构自己的政治正统性。康熙帝曾发布面谕,称清政权并非取自前明,乃是在李自成破北京后“臣民相率来迎”,是吊民伐罪;从现实看,自己做到了“敬天法祖”,“宽严相济,经权互用”,因此“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⑨。这一叙事以道德原则遮蔽夷夏之辨,其动机不言自明,但在人心虽对前朝仍存眷眷却对弘光君臣普遍失望之时,提出统治合法性不得自出身、民族而得自道德,这一说法却令当时士人难以全然否定。由此,上有统治者有意建构,下有几代士人反思推进,君国一体、夷夏之防的观念渐渐让位于道德至上的观念。至唐甄提出“亡国破家”要问为君之罪⑩、顾炎武提出“亡国”与“亡天下”之分⑪,则成为当时反思明清鼎革的最具革命性的声音。《桃花扇》正是用文学方式呈现了这些思想冲突与文化裂变。
首先,呼应着当时士人对君主的批评,《桃花扇》不再重视由君国一体观念决定的君主血统正当性,而以其道德表现作为君主合法性的判断标准,将错立德不配位之帝作为南明败亡的根本原因。剧作首先借史可法之口,肯定“昭穆伦次,立福王亦无大差”⑫,即虽然马士英等拥立福王是出自私心,但在崇祯殉国、太子失踪的情况下,福王朱由崧作为神宗亲子,是从血统上最有资格继位的皇帝人选,弘光之立就“昭穆伦次”而言是合法的。但随即,剧作借侯方域之口历数福王不可为帝的“三大罪”,否定了这一合法性。这三项罪名,除第一项指向其母外,第二项骄奢与第三项父死弃尸而逃、乘乱纳民妻女⑬,都指向其“君德全亏尽丧”⑭。剧作固然也将文臣争门户、武将闹意气纳入对南明败亡的反思中,但争门户的东林党人也在为国事奔走,闹意气的武将也在尽力撑持江山。国破之时,这些各有缺陷的文臣武将中更不乏慷慨殉难者。反而是弘光帝,作为君主毫无社稷之念,前明之亡反成他窃取名器、骄奢享乐的机由,南明覆灭之际,他也只全力逃生。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与情感立场中,孔尚任开始将君与国区分开来:国家不是君主一家之私传,所以君主也不再单纯依靠血统而获得合法性。对明朝江山社稷,他固有无限同情、凭吊行诸笔端,但对其最后一个君主弘光帝,却唯恐批判、暴露不力。
其次,为呼应清初统治者“吊民伐罪”的叙事,《桃花扇》回避了明亡清兴、以夷代夏的尖锐矛盾,在挽明的同时,也从道德角度赋予满清合法性。剧作建构了明亡于流寇而非满清、满清入关乃灭贼而非覆明的叙事逻辑。为此,孔尚任将对明朝社稷的哀思寄托于崇祯而非弘光。忠臣、遗民们为崇祯痛哭之时,已经说出崇祯之死不是在王朝延续过程中的皇帝大行,而是国祚已终、“亡家破鼎”之事,是“独殉了社稷苍生”⑮。在这一情感逻辑中,南明很难成为明王朝统绪的合法有效传递者。由此,亡明之恨,就不再指向覆灭南明、擒获弘光的满清,而是指向攻破北京、逼死崇祯的李自成农民军。进而,满清入关,也就不是取明朝天下,而是“大兵进关,杀退流贼,安了百姓,替明朝报了大仇”⑯。这段话从为崇祯皇帝收殓遗骸、守灵哭丧的前明锦衣卫张薇口中说出,从而有效地赋予满清政权“吊民伐罪”的道德合法性。
从道德至上的标准中产生出批评甚至否定君主的合法性,超越传统夷夏之防接受满清政权合法性,是孔尚任在《桃花扇》书写中对其时代思想转型的呈现与应和。而这些发生在儒家文化内部的裂变,虽然较之传统历史叙事体现出了极大的异质性和挑战性,但是并没有越出儒学基本的思想方法和理论立场,而只是其思想体系内部的冲突、裂变。这些冲突、裂变进入《桃花扇》的书写,构成隐匿在文学叙事中的逻辑困境和情感张力。
从叙事逻辑来说,孔尚任将明朝败亡归因于君主道德崩溃而非朝政失误,对弘光的批评完全指向其私德不修:选歌征舞、沉迷酒色是不仁,弃绝元配是不义,幽囚崇祯太子是不忠,父死不葬是不孝,而弃国奔逃更是无耻。这种将道德作为历史变革动力的方法,在此陷入了另一重叙事困境:弘光私德不修,固然使正士离心、邪佞幸进,但是剧中堪称道德楷模的史可法手握重兵,为何也守不住南明半壁江山?当兵临城下时,竟至三军离叛、军令不行。史可法一腔忠义,却只能痛哭至浑身血泪⑰。这一情节固然塑造了史可法完美、悲壮的忠臣形象,但也呈现出道德在这场鼎革巨变中其实百无一用、不堪一击。这种强调道德却又深感道德无力的困境,体现出儒学理论在此时虽迫于新的现实问题不断调整、裂变,但仍宰制着士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和阐释。
从情感立场来说,孔尚任既批评弘光帝德不配位、肯定清王朝“吊民伐罪”,又书写这样一个“桃花扇底送南朝”的故事,本身就浸润着对最后一个华夏政权覆灭的遗憾与怅惘。孔尚任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东林士子、爱国武将乃至风尘侠客悲壮、英勇的抗清斗争,并赋予崇高的道德意义。抵抗满清的道德意义与满清入关的道德意义在剧作中并存,造成剧作情感立场的分裂——这或也是作为汉族儒生的孔尚任与感念康熙尊孔礼遇的孔尚任在情感立场上的矛盾。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或能理解:晚明四公子中,陈贞慧、方以智、冒辟疆入清后或投身抵抗,或隐居不仕,而孔尚任却选择了唯一一个入清应试且中了副榜的侯方域作为自己故事的主人公,且是正面主人公。这一选择,隐隐对应孔尚任对康熙简拔礼遇之恩“犬马图报,期诸没齿”⑱的由衷感念及基于这份感念对汉族儒生“仕清”的理解和评判。然而,在传奇中,孔尚任隐去侯方域入清后的真实经历,以其与李香君双双入道为这段离合兴亡的故事作结,这样的处理体现出孔尚任及其同时代士人在明清鼎革中努力重构一套历史表述时所遭遇的理论难题和情感困境。
二、现代民族主义视野下的“何为中国”“中国何以现代”问题——梁启超《桃花扇》评论与批注中的现代思想意义
如上所述,在孔尚任及其同代人对明清鼎革的阐释中,道德原则和国家社稷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暧昧状态:道德似是天下兴亡的最终动力,但在鼎革巨变中却又百无一用。要解决这种根源于儒学思想方法中的暧昧性,需要引入新的观念体系。晚清以降,西方民族国家和国民观念慢慢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将明清鼎革所内蕴的情感经验与理论问题转化为带有现代民族主义色彩的叙事,由此提出“何为中国”“中国何以现代”等理论命题。梁启超身处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刻,其思想中既有现代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观念最初进入中国的痕迹,又有最后一代士人传统的天下认同。他对《桃花扇》的仿写、评论和批注,颇具代表性地体现了这种观念转型的复杂、难明,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首先,梁启超对《桃花扇》的解读,体现出现代民族主义观念进入他的知识结构,部分重置了他对中国历史的判断。他认为:“《桃花扇》于种族之戚不敢十分明言,盖生于专制政体下,不得不尔也。然书中固往往不能自制,每一读之,使人生故国感……读此而不油然生民族主义之思想者,必无心人也。”⑲这里发生了两重概念置换。其一,剧作确有故国之思,但如上文所分析,其中兴亡之感深而夷夏意识淡,挽明并不导向排满。其二,即使剧作确实隐匿着孔尚任在夷夏问题上的某种情感张力,但当时的夷夏问题也不同于晚清的民族问题。前者是传统中华文化帝国内部的民族矛盾,后者则是现代主权国家之间的对立冲突。就前者而言,虽然儒学理论强调夷夏之辨,但从整体视野来说二者共属同一个文化政治结构中,可以有机融合,罗志田特别强调,“夷夏之辨本以开放为主流,许多时候夷可变夏(反之亦然)”⑳。但对后者来说,这是从国家利益到文化政治的全面冲突,其极端形式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殖民乃至灭亡。所以,读《桃花扇》而生民族主义思想,是梁启超从新的理论视野和知识结构出发,又有感于中国在此间世界中的处境,对《桃花扇》题旨的后设解读。而将原作意涵与自己解读之间从概念到情感的明显差异解释为孔尚任在“专制”政体下不敢明言,对于精通史料、详熟孔尚任生平自述的梁启超而言,主要是他自己身处新旧交替时刻,对新的国家观念与传统天下朝代之间的本质差别缺乏辨析所致。
因此,这一误读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它呈现出梁启超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在排满与反帝并存、传统夷夏之辨与西方民族国家互文的知识结构中思考“何为中国”的问题,正如罗志田所言:“晚清的民族主义兼排满与反帝两面。”㉑将“满”与“帝”指称为夷狄,固然来自传统夷夏观念,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排满的目的不是产生新的汉家王朝,而是要建立新的民权国家;反帝也并非传统儒家文化圈内的民族矛盾,而是在国家主权不断被侵略、窃取的现实中生发出现代民族主体意识。正是从这样具有现代民族主义色彩的视野出发,梁启超才会力赞《哭主》《沉江》这两出戏,说自己小时候为之“不知淌了几多眼泪”㉒。前者是故国之思,后者是抗清之烈,俱是《桃花扇》中最易转化出民族主义情绪的笔墨,而梁启超也确实从中生发出了具有革命性的现代民族思想:“对于满清的革命思想也有一部分受这类文学的影响。”㉓他仿《桃花扇》所创作的三部传奇《新罗马》《劫灰梦》《侠情记》,不仅仅是在形式上征用《桃花扇》的宾白唱词,更是在剧作主旨上将其从《桃花扇》中获得的情感经验投射到现代民族求独立、求解放的革命叙事中,开启了对《桃花扇》主旨虽不明确却包含着现代意识的阐释和重写。
其次,此时的知识分子开始从带有现代民族主义色彩的国族意识中思考“中国何以现代(自新)”的问题。梁启超提出“新民”说,将现代国民的出现作为中国自新的必要条件㉔。这一说法是在孔尚任的知识视野之外回应了孔尚任的困境:个人行为的意义不再从抽象的道德原则中被给定,而是要在其与国家的能动关系中获得。
梁启超对《桃花扇》的批注,与他的新民理论分享着同一问题视野,通过看似中立的材料考据、辨析,阐发出对国家与国民关系的现代理解。其所补充的史料,基本都集中于剧中人物是忠于故国还是投降新朝这个核心问题。表面上看,这与孔尚任的道德叙事颇多重合,但仔细辨析会发现,如上所述,梁启超在将明朝理解为一个颇具现代政治意义的民族国家之后,对是否忠于故国的关注,其重心就不仅仅是忠孝节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增加了个体应该如何担当对国家的责任这一问题。
比较梁启超在剧作中杨龙友问题上的两次异议表达,可清晰见出其关注视角的转移。他考证出剧作中的杨龙友事迹与史料记载在两个事件上不符:其一是杨龙友为阮大铖拉拢侯方域,其二是南明败亡时杨龙友弃国而逃。对前者,梁启超仅节录侯方域书信,指出“然则为阮奔走者实一不知名之王将军,而与龙友无与”㉕的事实即作罢。对后者,梁启超不仅详述了杨龙友在南明溃败后的真实经历:“仍赴苏松巡抚任,与清兵相持,败后走苏州。清使黄家鼐往苏招降,文骢杀之,走处州。唐王立,拜兵部右侍郎,提督军务,图复南京。明年(丙戌)七月,援衢州,败,被禽,不屈死。”㉖更直接发表了对剧作中这一情节设置的不满:“乃不录其死节事,而诬以弃官潜逃,不可解。”㉗同一历史人物,同是与史实有出入,而梁启超的反应却大相径庭。考其原因,应在于梁启超评价人物的标准从抽象的道德原则转移到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因为如果从道德标准说,孔尚任创造的这两个情节,都是对历史人物杨龙友的抹黑。但相较之下,前者似更有损杨龙友的道德形象。毕竟,敌军破城,生死一线,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仓皇出逃,虽不光彩,却也难以苛责(毕竟不是投降,更未卖国),而主动依附权奸、败坏友人名节,这显然是更严重的个人道德问题。但如果从个体与国家的关系而言,则是否坚守自己对国家的责任与担当,显然才是更重要的评价依据。因此,梁启超对前者不甚在意,却对后者责之以“诬”。由此我们或能透过梁启超为剧作中不甚重要的陈定生、吴次尾等人耗费大量笔墨,详述他们入清后坚持抵抗或归隐不仕的批注,窥见梁启超对传统“私德”与“公德”的区分中,也渗透着从现代民族主义视野出发对个人与国族关系的思考。
进而言之,梁启超对这一关系的思考,已经越出了道德范畴,开始关注个体行为对国家的能动影响。他虽然从个体对国家的主观态度出发,关注剧中人物对待明朝的态度,但较之是否忠于明朝,他更关注的是其行为对明朝存亡发生了怎样的实际作用。当主观态度忠于明朝与客观行为贻误社稷并存时,梁启超会毫不犹豫地打破孔尚任的道德叙事,对人物作出截然相反的评价,这集中体现于他对左良玉的评价中。如果说有关杨龙友的故事还存在着剧作与历史史实的分歧,那么左良玉无论在剧作内还是历史中,都确实是以抗清明臣的身份死于国事,但梁启超却对孔尚任将其塑造为正面形象极其不满。梁启超并不关注左良玉在道德上是否是忠臣,而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其行为对南明社稷的危害。他历数左良玉在国家危难之际纵兵为匪祸乱国家、统兵无方几至哗变、擅自移防破坏抗清部署等行为,并加以批判㉘。这些行为,既与《桃花扇》所述几无出入,亦很难说是左良玉私德败坏的体现,只有从个体对国家的能动影响角度审视,左良玉才难辞其咎。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从传统步入现代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梁启超对《桃花扇》的评论与批注,仍体现出文史不分的传统思维特征,也没有对自己思想中现代民族认同与传统夷夏之辨相混杂的状态做辨析,故其对国家与个体关系这样极具现代问题意识的思考,仍包裹在儒家忠孝仁义的话语体系中。后人如不仔细分析其情感倾向与价值判断背后的观念转型,则难以发现其隐匿在“批注”这一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体例中的现代思想价值。
三、危机中对现代国家主体的辨析和指认——抗日战争中重写《桃花扇》所打开的问题空间
抗战时期,中国思想界兴起南明史学研究热潮,核心问题意识是从中总结历史教训以为借鉴。这种借古鉴今的阐释,使得明清鼎革问题从传统兴亡叙事真正转型为对现代国家问题的讨论,成为现代思想文化观念形塑与知识生产的有机部分。
日本侵华造成民族与文化将偕亡的深刻危机。如何应对危机、抵抗侵略,进而言之,如何从危机中建构新的现代国家?围绕这一问题,当时中国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共识与分歧皆坦露出来。这一现实投影于南明史研究,促使其关注重心不仅离开了孔尚任时代的兴亡叙事、道德反思,也越出了梁启超时代缺乏辨析、大而化之的民族主义意识,进入到对南明政局中各种政治力量的辨析评价,以此为现实中各种政治力量及其主张鼓呼。国共两党作为当时最重要的两股政治力量,在这一讨论中争论最烈也影响最大。陶希圣写作而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就认为:“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骑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消灭了。”㉙以此为其“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张目。翦伯赞、郭沫若等则与之针锋相对,从马克思的阶级观念出发分析南明各阶层,从中得出不同于此前任何一种南明史研究的阐释:南明社会既有满清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也有上层统治者和下层人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在这双重矛盾中,李自成农民起义既有反抗压迫的阶级解放意义,又有抵抗侵略的民族斗争意义。在这一阐释逻辑中,明清鼎革就不是发生在崇祯、弘光、顺治几个皇帝之间的江山易主,而是受压迫的汉族人民与侵略者、压迫者的斗争;农民军不是败亡江山的流寇,而是推动历史解放与进步的人民;中国也不再是一个存在于抽象文化意义上的、可以由明王朝代表的天下,而是可以从内部区分为不同力量阵营并在这些力量阵营的斗争、消长中不断发展的现代政治场域。从这一阐释出发,“现代中国”就不仅仅是一个中西思想文化交融、碰撞中的概念辨析问题,而是要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在血淋淋的现实斗争中,指认出属于历史进步力量的国家主体,动员、教育、组织以使他们担当抗日救亡、创造现代国家的历史使命,也要辨析出那些在历史中发挥反动作用的力量,斗争、消灭并抛弃之㉚。
呼应着这些探讨,此时文艺界出现了很多《桃花扇》的改编之作,这些作品将梁启超等提出的“何为中国”“中国何以现代”等问题,推进到“由谁、怎样从危机中创造现代中国”这一更具体的层面。其中,欧阳予倩的改写最为著名也最具问题意义。他于1937年将《桃花扇》改编为京剧,1939年将京剧改编成桂剧,1946年又着手创作其最具影响力的话剧《桃花扇》,于1947年定稿出版㉛。在最早的京剧改编本序言中,欧阳予倩就已经明确表述了自己的创作意图:“我突出地赞扬了秦淮歌女、乐工、李香君、柳敬亭辈的崇尚气节;对那些两面三刀卖国求荣的家伙,便狠狠地给了几棍子。当时有不少那样的知识分子,看着局势大变,便左右摇摆,大发挥其两不得罪的处世哲学。”㉜这一表述带出的问题不仅仅是借古鉴今、动员抗战这一在当时比较普遍的主观创作意图,更是剧作家历史观念的更新。
欧阳予倩对孔尚任《桃花扇》最重要也最具问题意识的改写,是拆解了夫妇一体、家国同构观念,将男女主人公视为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根据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行为划分其历史阵营:是站在进步的一方坚持抵抗,还是站在落后甚至反动的一方变节投降?并使这历史阵营的选择超越夫妻情爱获得更重要的意义。在传奇本中,侯李二人屡经悲欢离合,相互间却始终为一体,不存在人生道路选择的分歧。李香君虽在“却奁”事件中批评侯方域,却是以侯生妻妾的立场维护丈夫声誉,体现的是夫妇一体的伦理认同。最终重逢而不团圆,亦非缘于彼此认同有变,而是在家国同构的意识结构中,国家君父皆亡,则夫妇之伦失去依托无处存身。在欧阳予倩的改写中,“却奁”却成为二人道路分歧的伏笔,暗示着这对年轻人在人生观上有着严重分歧。最终侯方域出仕清朝,李香君不能妥协而悲愤义死。这就不再是家国同构、国破则家亡的故事,而是现代国家社会中不同阵营力量抗衡、斗争的故事。
在这一改写中,李香君从传统贞烈美人,变成居于底层而有民族气节的现代女性。传奇中,李香君并没有体现出鲜明的国家民族意识,她的道德价值主要体现为虽沦落风尘却能洁身自好,经历威逼利诱却不失节——这里的“节”,更多指向传统女性的“节烈”。话剧中,李香君之“节”不再是为夫守节,而是转向抵抗侵略的民族气节。传奇中,李香君“却奁”是因为关切夫君名声,提醒他“也提防旁人短长”㉝;话剧中,李香君“却奁”是作为一个有独立身份的个体表白自己的立场:“尽管你们把我看成下贱的女子,可是我心还没有死……就把我凌迟剐碎我也不会随便接待一个奸贼的走狗。”㉞她还以平等身份批评侯方域:“大丈夫,有话说话,有错认错。”㉟传奇中李香君与侯方域分离后哀怨自伤,而话剧中李香君却在分别之际鼓励侯方域:“你到了江北,一定有更多报国的机会。你不要顾我,你只要为国家保重自己。”㊱传奇中李香君始终恪守“既嫁侯郎,怎肯改嫁”的贞烈观念,国破时也无甚兴亡之感,只是执著于“铁鞋踏破三千界”也要“寻着侯郎”㊲。到话剧中,欧阳予倩特别增加了李香君在与侯方域结合前,读岳飞事迹而痛哭的情节,使李香君体现出明确的国家政治关切。她与侯生的结合,也包含着将其当作有志报国的知识分子的期许。最后,传奇里在山河巨变中心心念念只想寻夫的李香君,变成能果断与投降敌国的爱人生死决裂的现代女性,这是欧阳予倩询唤出的新的历史主体。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话剧中陈定生说出了这样的台词:“贪官污吏,到处横行;苛捐杂税,重重剥削;百姓们求生不得,又怎么不成流寇!”㊳随后,将“骂筵”情节发挥为对流离失所的百姓痛苦生活的呈现与对压迫百姓的统治者的揭露和鞭挞。这样的情节和台词,使得欧阳予倩的文学创作与同一时期翦伯赞、郭沫若等的历史研究桴鼓相应:欧阳予倩创造了在民族内部区分不同阵营的叙事逻辑,这无疑呼应着翦伯赞、郭沫若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分析历史中社会阶层的思想探索;而选择李香君、秦淮乐工等这样一些出身下层的人物来担当历史新主体角色,并将底层人民受到压迫、欺凌援引为农民军起义的合法性解释,将出身较高的侯方域塑造为软弱变节的反面形象,则是与翦伯赞、郭沫若等一起,将克服危机、重构家国的希望,放置在那些受压迫最深也反抗最坚决的底层人民身上。
因此,与欧阳予倩同时代及其后对《桃花扇》的改编,基本保留了从欧阳予倩开创的这一叙事结构:李香君作为下层人民的代表,日益成为叙事的中心形象,而侯方域在诸多改编本中,也以投降变节为结局——即使没有投降、保持正面形象设置,但也不再是生旦传奇中的主人公,而变为李香君的陪衬㊴。同时代谷斯范的长篇小说《新桃花扇》,特意让柳敬亭说了一段“恶县令逼反李岩”的新书,以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视野中,李自成农民军不再是流寇,而是在压迫与侵略中奋起反抗的人民㊵。这种让受压迫的“老百姓大家起来”㊶的呼吁,也成为此时的左翼知识分子对“由谁、怎样从危机中创造现代中国”问题的最直接回答。
从传统天下兴亡到现代国族救亡,从救亡中产生出“何为现代中国”“谁之现代中国”“中国何以现代”的问题。《桃花扇》从康熙年间的写作到晚清乃至近现代的接受与改写,既是其作为艺术经典的余音绕梁,亦是从天下兴亡到现代国家建构的观念变迁与问题延伸。正如许纪霖所言:“在今天这个时代,‘什么是现代中国’是一个知识性的问题,不仅与认知有关,而且需要解读和想象,是主观和客观相互交错在一起的知识,是各种各样竞争性的话语,或者知识类型。”㊷从这样的思想方法出发,则历史文本就不是已完成的叙述,而是一个不断与现实对话的动态场域。由此,或能打开思想史与现实问题的交界。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百年文艺中的‘家国’关系变迁——以‘五四’至今的文艺为对象”(批准号:16BA014)、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杰出学者支持计划资助项目成果。
① 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页。对《桃花扇》的离合之情、兴亡之感主旨,孔尚任自己已经指出,“离合之情”是借以承载“兴亡之情”的依托,所以主旨是“兴亡”而非两者并重。对这一点,沈墨、沈成垣父子曾经指出:“《桃花扇》乃先痛恨于山河迁变,而借波折于侯、李,读者不可错会。”这一说法颇得后世认同(陈仕国:《〈桃花扇〉接受史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
② 如梁启超不仅批注过《桃花扇》,而且其所著《新罗马》《劫灰梦》《侠情记》三种传奇,对《桃花扇》亦有大量仿写。韩文举在《扪虱谈虎客批注》中云:《新罗马》传奇的“楔子”“全从《桃花扇》脱胎”,“曲白文词和结构关目方面……对《桃花扇》多有袭用和借鉴”(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一九,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9755页)。再如欧阳予倩电影剧本《新桃花扇》(载《文学丛报》1936年第2期),讲述北伐战争时期进步知识分子与戏曲演员之间的悲欢离合,以“桃花扇”为名,既指在剧本中使用了《桃花扇》的片段,更是借用《桃花扇》在大时代动荡中写离合悲欢的立意,将两个年轻人的爱情、人生与时代社会的命运相结合。
③ 近现代文艺史上,对《桃花扇》的改编之作极多。自从汪笑侬在1904年前后将《桃花扇》改编为京剧并亲自粉墨登场演出,重启“勾栏争唱”序幕后,《桃花扇》重新进入现代文艺视野,被改编成多种体裁,较为著名的有谷斯范的长篇小说《新桃花扇》,周贻白的话剧《李香君》,欧阳予倩的新京剧、话剧、电影剧本和桂剧《桃花扇》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诸多地方戏曲、影视剧作品(参见陈仕国《〈桃花扇〉接受史研究》,第128—167页)。
④ 从文学叙事与历史真实关系的角度研究《桃花扇》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视角。明清之际士人多有为前朝存信史的情结,孔尚任也自言:“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孔尚任:《桃花扇》,第11页)梁启超的批注也多从其与史实是否契合的角度落笔。直至当下,仍有学者如章培恒作《〈桃花扇〉与史实的巨大差别》(载《复旦学报》2010年第1期),继续从这一视角研究《桃花扇》。
⑤ 如王亚楠《论周贻白话剧〈李香君〉的剧本与演出》,载《成都大学学报》2016年第8期;单永军《“桃花扇”故事的电影传播》,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王永恩《论欧阳予倩抗战时期的戏曲改编成就》,载《戏剧》2017年第4期;宋灿灿《从结局看石小梅传统版〈桃花扇〉的改编》,载《大学语文建设》2018年第14期;朱梦颖《从〈1699·桃花扇〉的导演风格看田沁鑫的舞台表达》,载《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⑥ 孙奇逢:《畿辅人物考序》,《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页。
⑦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三二,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第143页。
⑧ 邵廷采:《史论·列传》,《思复堂文集》卷八,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60页。
⑨ 朱轼等纂修《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辛未”,《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94—697页。
⑩ 唐甄:“川流溃决,必问为防之人;比户延烧,必罪失火之主。至于破家亡国,流毒无穷……非君其谁乎!”(唐甄:《潜书·远谏》,古籍出版社1955年版,第127页。)
⑪ 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三“正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56—757页。)
⑫⑬⑭⑮⑯⑰㉝㊲ 孔尚任:《桃花扇》,第97页,第97页,第97页,第92页,第135页,第228—231页,第55页,第236页。
⑱ 孔尚任:《出山异数记》,《孔尚任诗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38页。
⑲ 梁启超:《小说丛话》,载《新小说》1903年第7期。
⑳㉑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5页,第204页。
㉒㉓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一九,第3586页,第3587页。
㉔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四,第5213—5461页。
㉕㉖㉗ 《梁启超批注本桃花扇》,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第175页,第175页。
㉘ 梁启超对左良玉的批判,几乎见于其《桃花扇》批注本中凡涉及左良玉事迹处,较为集中的则在第九出《抚兵》,梁氏开篇即评论道:“《桃花扇》于左良玉袒护过甚。”随后以较长篇幅历数左良玉养寇自重、拥兵不救、结纳贼匪等劣迹。在这段文字中,梁启超明确将左良玉作为亡明罪臣加以评述,体现出和孔尚任截然不同的情感态度(《梁启超批注本桃花扇》,第47—53页)。
㉙ 蒋中正:《中国之命运》,中正书局1943年版,第13页。
㉚ 这些论述见于翦伯赞写于20世纪40年代前后的《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等论文。这些论文在当时多被国民政府禁止发表,后收入《翦伯赞全集》第3卷《中国史论集》第一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在序言中,翦伯赞对此情况有所说明。而最集中也最经典的论述,是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此文最早连载于1944年3月19—22日重庆《新华日报》,本文所据为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单行本。
㉛ 陈仕国:《〈桃花扇〉接受史研究》,第261页。
㉜ 欧阳予倩:《桃花扇·京剧》“序言”,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页。
㉞㉟㊱㊳㊶ 欧阳予倩:《桃花扇》,中国现代文学馆编、葛聪敏编选《欧阳予倩代表作》,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页,第151页,第157页,第133页,第136页。
㊴ 与欧阳予倩同时代的周贻白以《桃花扇》为基础改编的话剧,就因为明确将叙事重心放置在李香君身上而命名为《李香君》(国民书店1940年版)。该剧延用了侯生变节的情节,在当时《桃花扇》改编本中亦较为著名。20世纪40年代以后对侯李结局的诸多改编详情,参见陈仕国《〈桃花扇〉接受史研究》第四章“从清以来的改编看〈桃花扇〉之接受”,第219—308页。
㊵ 谷斯范:《新桃花扇》,上海文化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㊷ 许纪霖:《何谓现代,谁之中国?》,许纪霖、刘擎主编《何谓现代,谁之中国?——现代中国的再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