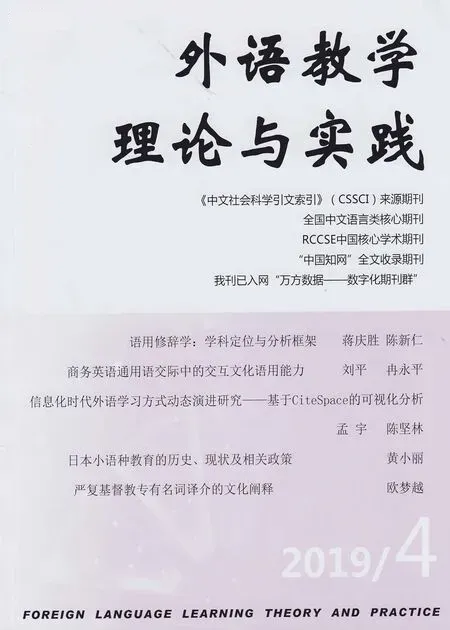严复基督教专有名词译介的文化阐释
2019-12-21复旦大学欧梦越
复旦大学 欧梦越
一、引言
严复基督教专有名词译介,是指严复论及基督教的所有著述(包括译著和论著)中的专有名词译介,包括人名、地名、著作名(书名、篇名、章节名)、流派名、重要概念等。目前学界关于严复基督教译介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李安泽、李炽昌与李天纲、李炽昌与涂智进、任东升等学者的文章,主要聚焦于严复如何认识基督教,属于一般的翻译研究和宗教思想史研究。至于深入到词语层面进行具体而微的细化分析,国内外学术界尚无专文研究。业师邹振环先生《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多处论及基督教专有名词译介,笔者深受启发。严复所译基督教专有名词中,不少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笔下的基督教专有名词译法不同,如“毕协”“波罗忒斯坦”“票利丹”,往往使读者颇感费解。其实,“毕协”即通译“主教”,“波罗忒斯坦”即通译“新教徒”,“票利丹”即通译“清教徒”。而一些专业辞典极少给出这方面的解释,无法满足读者需求。本文以“溯源”式的考释方法,从上下文具体语境中找出严复翻译的英文原词,在初步系统梳理考辨的基础上,进一步予以文化阐释,同时纠正学界错误的解释,旨在为阅读和研究严复著译扫除阅读障碍,同时提升严复译词研究的文化意味,这对拓展和深化、细化严复研究、基督教译介史研究以及近现代语言史、翻译史研究领域,具有不言而喻的价值和意义。
二、遵循基督教汉译传统与“别出心裁”
严复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和英国经验主义、保守主义思想的双重影响,十分尊重传统,对传统充满敬畏之心,尊重前人的成果,重视知识的积累性。因此,他的基督教专有名词译介,许多地方仍遵循基督教汉译传统。光绪三十四年(1908),严复时在上海,受“大英圣书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即“英国及海外圣经会”总经理文显理的委托,用文言翻译《圣经·新约·马可所传福音》(仅完成前四章)。他基本上遵循教会的《圣经》汉译传统,即当时的通行译法。上帝、基督、耶稣、福音、以赛亚、约翰、犹太、耶路撒冷、约旦、加利利、拿撒勒、西门、安得烈等,皆为当时通译名。又如,严复将God译为“上帝”,Gospel译为“福音”,Holy Spirit译为“圣灵”,等等。公元7世纪,景教传入中国,“耶稣”音译为“移鼠”“翳数”,同时期明教(摩尼教)将“耶稣”译为“夷数”,自明末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Jesus的音译多达“热所”“耶书”“耶逊”“耶稣”数种,后改译为“耶稣”,通用至今。上帝,通译“耶和华”,汉语音译分别有“耶和华”“雅威”“耶威”“亚卫”等。耶稣会士将Sacerdos(Priest)译作“撒责尔铎德”,简称“铎”“铎德”或“司铎”,“神父”“神甫”是日常对“司铎”的尊称。相比其他不常见或已被淘汰的译法,严复采用耶稣、耶和华、神父、神甫等通行名词。严复受托译《圣经》,不只限于提升《圣经》翻译的品位,化浅俗为文雅,目的更是在于普及与接受,以期减少基督教传播在士大夫文人阶层中的阻力,故采取“吾从众”的策略。
严复常将基督教(Christianity)译为“景教”。光绪十八年(1892),他翻译《支那教案论·教事篇》,曰:“景教西来,始于明季;定约容纳,保护于本朝道咸间”(汪征鲁等,2014:卷五,520)。光绪三十二年(1906),《论南昌教案》曰:“考基督教之来中国,最早莫如景教”(汪征鲁等,2014:卷七,197)。《法意》案语说:“夫欧洲景教之祸,中古最烈:固迷信也”(汪征鲁等,2014:卷四,572)。“景教”原名“Nestorianism”,于唐太宗贞观九年(635)由波斯人阿罗本传来中国,取名“景教”。“景”,光明之意,喻耶稣给人间带来光明。古有景净《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吴相湘,1965:62)。实际上,唐代传入中国的景教只是基督教的一支(聂斯脱利派),用来指称全体基督教,严格说来并不准确。
戴维·莱特认为严复用“景教”一词来翻译Christianity,是他倾向于有意选用古代汉语体系中的语词将西方新词直译或者实现其本土通俗化的一个例证,因为“景教”实际上是出现在唐朝的一个名词(Wright,2001:235-249)。严复在《原富》中介绍景教之国时,对自己的译词选择做如下解释:“考唐之《景教碑》,所谓景教者,实非基督教宗,乃教外别传。今借用为教宗统名,以偏概全。古之命名,固有此法也”(汪征鲁等,2014:卷二,125)。严复认为“以偏概全”是古已有之的译词“命名”方法,流行已久,故沿袭使用。可见,严复尊重译词的“约定俗成”,与此同时,他十分清楚“景教”作为译词的不准确性,为此还特意考辨一番,体现出科学而严谨的学术态度。实际上,“以偏概全”,即以部分代全体,本是古代汉语修辞格中的“借代”,是古人习惯的一种语言表达。从这一角度看,“景教”译词也无可厚非。戴维·莱特并未具体明确指出严复之所以袭用传统译法,是因为尊重古人“借代”修辞手法,他只是大而化之地用“本土通俗化”来解释,说明他对严复译词选择所蕴含的传统文化信息的认识还不够明晰。严复并非无知,而是尊重传统积累的经验,是退而求其次的有意为之。
严复一方面尊重传统,另一方面又敢于并善于创新。在进行基督教名词译介时,他时而沿袭通译,时而有意“别出心裁”创制译词。对于译事,他内心有自己的标准与主张,他的译名也往往有别于通译名。
严复《论南昌教案》曰:
西班牙人,名罗曜拉,本为军人,以伤出伍。至一千五百二十八年,学于巴黎大校。目击旧教中衰,结合同志于一千五百三十四年创立新派,号耶稣军,以劝转信心,抵制新宗为要旨。教皇保罗第三嘉奖所为,于一千五百四十一年降敕,以罗为耶稣军上将。(汪征鲁等,2014:卷七,197—198)
伊格纳修·罗耀拉(1491—1556),又名伊纳爵·罗耀拉,严复译为“罗若拉”或“罗曜拉”。1534年,西班牙贵族罗耀拉在巴黎大学创立耶稣会,仿军队建制,纪律森严,要求对宗座绝对忠诚。严复领会原词的本质内涵,将通译的“耶稣会”译为“耶稣军”,突出其半军事组织的特征,十分合理。
Lutheran Sects,通译“路德教派”,信服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教义之教徒,严复译为“路得宗”。《原富》曰:“所谓异宗者有二:一曰路得宗,一曰葛罗云宗”(汪征鲁等,2014:卷二,545)。John Calvin(法语Jean Calvin,德语Johannes Calvin,1509—1564),通译“约翰·加尔文”,又译“嘉尔文”“喀尔文”“克尔文”“卡尔文”等,严复音译为“葛罗云”。卡尔文派(Calvinists,Calvinistic sects),通译“嘉尔文主义”“加尔文宗”,亦称“长老宗”“归正宗”,严复译为“葛罗云宗”。《原富》曰:“葛罗云宗之用于苏格兰者,其制小有损益,而为伯理斯白特宗”(汪征鲁等,2014:卷二,546—547)。严复译“摩蒙宗”(Mormonism),通译“摩门教”。“宗”,指宗门、宗派、派别,佛教名宗有禅宗等;“派”,派别,宗教或团体内因不同主张而形成的各种分支或门派。“宗派”连用,也可分用,宗即派,派即宗,并无本质区别。严复习惯以“宗”代替“派”,而“派”成为至今通行的译名。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严复译《群学肄言》曰:“吾英三百年以往,固已有持其说者,呼刻尔《宗教群法》第一编,尝举此义,非所谓瞩遐鉴洞者耶?当其世所谓科学,与一切科学之思想,闇汶无足言者,而呼刻尔氏独具先觉如此,斯足异矣”(汪征鲁等,2014:卷三,200)。呼刻尔,是严复对Richard Hooker(约1554—1600)的音译,通译“理查德·胡克”或“理查德·胡克尔”,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圣公会神学家,因与清教徒特拉维斯(Walter Travers)于1586年圣殿教会(Temple Church)辩论而名震一时。台湾林载爵主编《严复合集·群学肄言》注释说:
呼刻尔,Joseph Dalton Hooker(1817—1911),严复又译福克尔,英国植物学家,曾到南极、印度、纽西兰、北非、北美等地,发现许多新品种,认为植物变种与生长环境有密切关系,并在植物上证明“进化论”的存在,与达尔文是密友,著有《植物的属》,书中收集植物7 569属,约97 000种。(林载爵主编,1998:350)
按:《群学肄言》译自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于1873年所著《社会学研究》(TheStudyofSociology)一书。斯宾塞于1873年明确说“吾英三百年以往,固已有持其说者”的呼刻尔(胡克),显然绝对不可能是自己同时代的约瑟夫·道尔顿·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此Hooker非彼Hooker也。《严复合集》编者的注释显然是错误的。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界无人发现这一错误,一直以讹传讹。
三、“同名异译”的得与失
近代中国处于接受新事物、新知识、新概念的草创期,许多译词的通行译名尚未确定,不同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创制不同译名,同一术语在不同译本中的意义差距很大,甚至同一个译者,不同作品、同一作品中也存在译名的不统一现象。(1)同一名词,往往存在多种译法,即“同名异译”,又称“一词多译”。如society同时有社会学、群学、世态学等汉译名;science对应汉译有格致学、物理学、科学;philosophy有哲学、智学、爱智学、理学、性理学等汉译并存;economy有计学、经济学、生计学、理财学、财政学、平准学等汉译并存;logic一词的中文译词有名学、辩学、论理学、理则学,等等。名词的繁芜是近代译本的显著特征,正如《瀛寰志略》中所总结的:“十人译之而十异,一人译之而前后或异”(徐继畲,1866:3)。严复笔下,“同名异译”现象尤为突出,基督教专有名词译介也是如此,或有别于他人译名,或是自己对同一词有不同译名,因此有必要专门论述。
严复常常音译、意译并用,造成译名的多样化。The Society of Jesus,通译“耶稣会”“天主教修会”,严复袭用,《政治讲义·第七会》曰:“诸公倘以吾言为疑,则请观二百年来泰西之历史,虽有极放任政府,其于耶稣会Jesuitism一宗,其驱逐无不至严。无他,恶其权盛而已”(汪征鲁等,2014:卷六,59-60)。同时,严复又将Jesuitism音译为“叶舒伊会”,《群学肄言》曰:“如西班牙之罗若拉,创为叶舒伊会,本以保教,后乃树党擅利,权倾国家,而终于屏逐”(汪征鲁等,2014:卷三,21)。Protestantism,通译“新教”,严复意译为“修教”。《原富》曰:“苏格兰之布里必斯持,与瑞士之葛罗云大同小异,乃修教之一大宗,与罗马公教异门者也,斯密氏特举之”(汪征鲁等,2014:卷二,第126)。《群学肄言·教辟》“教之为辟”一段眉批曰:“以下言欧洲通行基督教派之辟。加多力即公教,即罗马天主,其旧者也。波罗脱斯坦即修教,即耶稣,即誓反,其新者也。二宗之外尚有特宗,特宗者不纯主国教而树义自立者也”(汪征鲁等,2014:卷三,181)。“加多力”即公教的音译,“波罗脱斯坦”即“修教”的音译,严复还将“修教”音译为“波罗忒斯坦”,《群学肄言》曰:“乃至加多力宗之谓波罗忒斯坦宗也,其不平亦然”(汪征鲁等,2014:卷三,182)。
音译法是近代中国人译介西方新概念常用的方法和策略,严复也不例外,在其基督教专有名词中,音译词所占居多。譬如严复译词“加多力”(Catholic,Catholic Church),通译“天主教”;“托直斯特麦”(Methodists),通译“卫理公会派教徒”;“摩尔底斯”(martyrs),通译“烈士”“殉难者”;“亚达那献”(Athanasian),通译“信奉亚大纳西教义之人”;“旁狄非加特”(pontificate),通译“教皇职位”;“票利丹”(puritans),通译“清教徒”。(2)光绪四年二月九日(1878年3月12日),严复与郭嵩焘论及张力臣《瀛海论》,张力臣提出十字架和天主教流传自东方,严复批驳道:“不识所流传者其字乎?其音乎?其字Roman Catholic,其音则罗孟克苏力也,何处觅‘天主’二字之谐声、会意乎?”(郭嵩焘,1984:497)。可见严复对该词也主张音译。至于何时用音译,何时用意译,合理的解释是,在从事《圣经》译介活动时,严复考虑到原著传播教义的宗旨,故多采用“约定俗成”的译法。而在翻译学术性著作时,严复把读者对象预设为饱读诗书的士大夫文人,他便自如地根据所需采取不同的译法。新词的创制无非音译、意译和释译三种。音译简单直接,直观感强烈,便于读者诵读,然而,音译容易造成语义理解与记忆的困难,这一弊端也导致了严复音译的绝大多数词语后来被淘汰(参见黄克武,2012:97)。近代西学译事活动中,关于音译与意译的讨论也从未停止。(3)狄考文认为翻译中过多使用西方文学中常有的描述性语言,不符合汉语的特点,相比冗长的表达或是词不达意,音译胜于意译(Mateer,1904:1-2)。傅兰雅则认为汉语不能够适应西方的思想文化,单纯的音译或直译也不利于记诵和理解,不应提倡。译名应该采取意译,或者必要时采取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式创制新词(Fryer,1890:534-538)。严复翻译并未拘泥于某一种形式,而是音译与意译并用,并融入文化阐释,旨在会通中西。
严复的“同名异译”有得亦有失,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即使同一个名词,他也创制多个音译。abbot,通译“男修道院院长”,他音译为“亚博”和“阿勃”;Presbyterian Church,通译“长老会”,他音译为“伯理斯白特”“伯理斯白特宗”;pope,通译“教皇”,他音译为“朴柏”“朴伯”。Moses,通译“摩西”,严译“麦西”;Mecca,通译“麦加”,严译“墨加”;Monsieur Jourdan,通译“约旦”,严译“约但”。以上译名并无本质差异,同为音译,严复择取相似读音的不同汉字,繁衍出不同译名,看不出有何深意,倒是徒增了译名的繁芜。此外,严复将missions译为“居留所”,明显不如通译“布道所”准确。
尽管严复许多译名最终未能走进现代汉语体系,但不少译名本身仍具有学理性价值,甚至比通行译词更为合理,如以“毕协”译bishop(通译“主教”),音译兼意译,不失为一个好译名。严复译词“华理”(Whalley),克服了通译词“华里”作为长度单位可能引起的歧义。再如“牛德阶”(Newdegate)一词充分体现了人名翻译的“中国化”特色,比起通译“纽德盖特”,以中国人的姓氏“牛”对应“new”,凸显本土文化的同时,也符合英文发音的规律。语言的通行与否,固然取决于其本身有无科学性,但仍有不少是遵从“约定俗成”的规律,掺杂着不少“非学理”性因素。通行的未必是最合理的,被淘汰的也未必皆不合理,今天对严复的基督教专有名词译介,甚至严复创制、使用的所有译词也应作如是观。
四、“本土化”理论自觉
唐代,儒、释、道三教鼎立,景教传入中国后,为了适应和生存,传教士译介时主动与儒、释、道融合,探寻在华传教策略,做了不少“本土化”的努力。(4)异质文化要想走进一种新的语言,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得到重生,必须做出一定的“本土化”努力。明末清初的来华耶稣会士们制定“适应性”策略,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译介西方概念,促进了中西文化沟通与融合。(张国刚,2003:357—365)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载,景教传入中国时,《圣经》译述往往附会道家之言,如“天尊”本出道教,《序听迷诗所经》以道家的“天尊”称基督教的上帝(天主)(参见朱谦之,1993:117)。不仅如此,景教士也借用善缘、妙有、慈航、世尊、大德、法王、慈恩、功德、大施主等佛教概念术语,且“僧”字常用于景教中人物的汉译,如“僧景净”“僧业利”“僧行通”“僧灵宝”,等等(参见俞强,2008:70)。
严复基督教专有名词译介有明确的“本土化”理论自觉。他“以儒解耶”,即译名采用传统儒家概念。如disciples,严复译为“弟子”,弟子,即学生,《史记》有《仲尼弟子列传》。严复以“文士”翻译scribe(犹太法学者,宗教导师),“文士”,指读书人,知书能文之士。汉语中,“文士”并没有宗教含义,但严复的“文士”译名显然让正统儒生们满意,虽然严格说来并不准确,但确实拉近了坚守传统的儒生们与《圣经》的心理距离,也正符合严复对目标读者的期待,即“多读中国古书之人”(汪征鲁等,2014:卷八,121)。
更多时候,严复选择“以佛解耶”,即用佛教概念翻译诠释基督教概念。汉明帝时,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用白马驼经来到中国,初止于鸿胪寺,遂取“寺”名创立白马寺,后世“寺”遂指佛教场所,浮屠所居皆曰“寺”。故严复特以“(教)寺”翻译西方的教堂,如以“圣波罗寺”译“圣保罗教堂”(St.Paul),以“峨特教寺”译“哥特式教堂”(Gothic Church)。严复又以“长老”来翻译主教,如Archbishop Sumner,通译“萨姆纳大主教”,严复译为“山蒙纳长老”。“长老”,本指老年人,德高望重的年长者,佛教中尊称释迦上首弟子,如长老舍利弗、长老须菩提,或尊称住持僧和僧人。
佛教名词罪业,指身、口、意三业所造之孽,也泛指应受恶报的罪孽。严复借用佛教有关“罪”的概念,如以“罪业”和“罪过”对译基督教的“罪”(hamartia),将罪人译为“造孽者”。其实汉语本身没有对译的词汇,严复做了“处境化”处理,这是一种“格义”(李安泽,2012)。严复将禁食译为“斋而禁食”。在撒种的比喻中,他以佛教概念“善地”译“好土地”,以“福报”译“好庄稼”。这些译法未尽准确,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西宗教文化差异。“格义”之法古已有之,更是近代中国学人最常用的意译解读西学的方法,即以中国传统为坐标系,用比较、类比的方式解释跨文化背景下的西学概念。这种带有比附性的“格义”,严复著译中多有存在。
严复常借助中国传统作为参照物,即将汉语文化体系作为“中间人”,引介西方新知识、新概念,旨在会通中西文化。“基督”,意为“受膏者”,是一种名衔,而“耶稣”是名字。严复所译《圣经·新约·马可所传福音》第一章中,将“耶稣基督”顺序颠倒为“基督耶稣”,称“上帝子基督耶稣,福音之始”,将个人名字置于后,符合中国传统的人名表述习惯。与此同时,严复也能够清晰地辨别出中西文化语境下同一名词内涵的本质差异,他指出,西方的“教”“师”不同于中国,“中国君师之权出于一,而西国君师之权出于二”(汪征鲁等,2014:卷二,550),“又其所谓师者,非止于授业解惑,与夫以善教人已也。必求其似,则犹古者之巫祝……其所业皆介于天人之际,通夫幽明之邮”(汪征鲁等,2014:卷二,550)。西方的“教”是宗教,“师”是传教士;中国的“教”本义是教育,上所施下所效,传授文化知识,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师”是教师,皆与宗教无关。
严复对基督教的认识,带有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传统观念作为“前理解”在其基督教专有名词译介中发挥前导性作用。(5)李安泽(2012:42)认为传统文化是作为解释基督教过程中的“前见”。严复采取“归化”策略,创制新名词,翻新古典语义,丰富扩大了近代汉语词汇体系,尽管有些译词不尽完善,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勒弗维尔认为,翻译就是文化“改写”(rewrite),“改写”就是一种“操纵”(manipulation)(Lefevere,1992:9)。改写往往出于不同意识形态的需要,如果不同文化背景的意识形态之间发生冲突,译者自然有必要进行一些“改写”,让原文和原作者更加走近读者,满足目的语群体的期待。“改写”是一种文化“再创造”,它赋予原文以新的内涵和意义,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一方面,严复身为译者,即翻译活动的主体,他是一名“操纵者”,巴斯奈特认为,在文化功能等值的过程中,译者有较大的主动权,可以灵活改写,甚至打破原文的文学形式(Bassnett.&Lefevere,1990:10)。但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的“操纵”下,严复又是一名“被操纵者”,囿于权力话语,难以幸免。他的基督教专有名词译介的优劣皆由此造成。
严复强调指出:“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汪征鲁等,2014:卷八,121)。他深受“桐城派”古文理论影响,对译词有明确的典雅化追求,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讲究“雅洁”“雅驯”,以“雅言”来“达旨”,“雅”与“俗”相对,又有“古”“正”含义。严复以“桐城派”所推崇的汉以前单行散体古文来译介西学名著,反对使用“近世利俗文字”(汪征鲁等,2014:卷一,79)。古雅、简洁的语言,是为了培养文化精英,即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而不是“市井乡僻”之浅学者。中西语言相互沟通,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严复译词尤具古典美,如以传统术语,将“司”译为“太祝”,将“圣殿”译为“神宫”。再如严复译词“神甫德黎”和“神甫竺萨稣”,分别对译通译的“神父特雷”(Abbe Terray)和“杜塞尔梭神父”(Father Ducerceau)。甫,古代男子名字下所加美称,多用于表字之后,又作男性长辈的通称,亦通“父”。严复所译“神甫”比通译“神父”更加雅驯。虽然英语文化中对神父的尊称的确是父亲的“父”(father),但严复选择古汉语“甫”,更加符合传统文人的审美文化心理,也符合他的传统儒者的文化身份。
书名是一类特殊的专有名词,严复的书名翻译也十分讲究雅驯。严复译呼刻尔(胡克)《宗教群法》(EcclesiasticalPolicy),即《教会组织法》或《教会政制法规》(OftheLawsofEcclesiasticalPolity)。“群”是严复独创的概念,群学,即社会学。严复译《迦南录》,即《迦南乐土》。“录”,古代记载言行或事物的书册,如唐李翱《来南录》、宋文天祥《指南录》,还有《景德传灯录》《碧岩录》等禅宗语录。BookofJob,严复译为《乔布之记》,即《乔布书》。“记”,记载事物的书册或文字,如《史记》《夷俗记》《列国变通兴盛记》。严复译词承继古人书籍命名之特点,极富传统文化意蕴。
严复有强烈的承旧统、开新域的文化使命感,他选择先秦典雅文言翻译英文著作,实际上即是表明了自己的主体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他的基督教专有名词译介也不例外。严复对基督教专有名词做中国化的“处境化”处理,即是主体文化融入和渗透的有力佐证。语言代表一种文化积淀,“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海德格尔,2015:217)。严复选择“雅驯”文言,而不使用白话文翻译英文,让英文与古汉语对话,强调传统文言的现代价值,强化对传统文化的崇敬和承继,不使母语“破碎”,极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欧梦越,2015)。
五、结论
严复基督教专有名词译介,首先遵循基督教汉译传统,采取“吾从众”的策略,尊重译词的“约定俗成”,如沿用“景教”译词,但对其不准确性有清楚的认识。同时又“别出心裁”,独创译词且多用音译,带有时代色彩。严复将Richard Hooker音译为“呼刻尔”,通译“理查德·胡克”,林载爵主编《严复合集·群学肄言》将理查德·胡克注释为约瑟夫·道尔顿·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显然是错误的。严复基督教译名中,“同名异译”现象突出,有得有失。其中不少虽在近现代译名史上逐渐被淘汰,但有些译名本身仍具有学理性价值,不可轻视。近代基督教专有名词汉译,因缺乏统一规范,译者多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翻译。严复译词虽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不少专有名词译介具有明确的“本土化”理论自觉,如“以儒解耶”,特别是“以佛解耶”,儒、佛、耶三者会通,且译词追求典雅化,旨在不使母语“破碎”,极具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