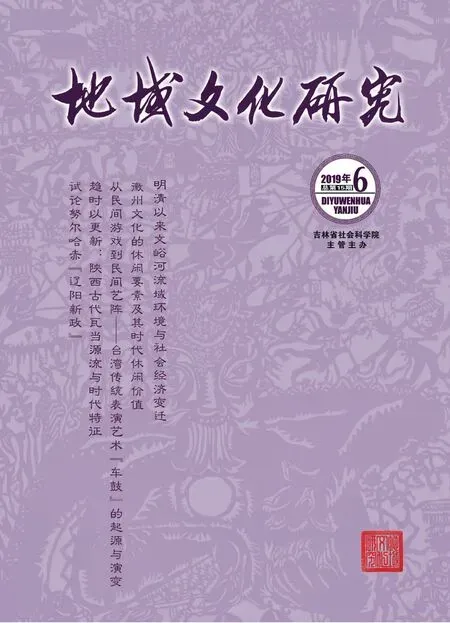回顾与省思:2018年中华龙文化研究述评
2019-12-14宋永林
宋永林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新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贯彻为当代社会服务的现实目标,革新研究理念与方法,努力开拓研究领域和方向,取得了瞩目的研究成果。早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兴起,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持续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当今,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增强民族凝聚力、认同感与自豪感的重要途径,也是走向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龙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它发源于远古时期中国先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深深植根于中国独特的社会土壤,是中华民族最为显著的文化符号。数千年来,伴随着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龙文化的内涵与外化表征日趋完善,在与异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包容、多元、开放的文化价值体系,彰显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2018年,学界对中华龙文化的研究继续保持着强劲的势头,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本文对2018年出现的有关中华龙文化研究的代表性论著进行总结和反思,以期有助于今后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全面开展。
一、龙纹的发展演变及其内涵
纹饰是一种或繁或简的图案,但在某些时候则是一种文化的外像标识,可以使我们清晰地了解文化的意蕴和内涵。中国的龙纹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期,而后随着社会生产力和手工业技术的进步,于商周时期开始以不同的形式被镌刻在青铜器表面。朱敏的《西周青铜器龙纹浅识》一文对西周青铜器上的龙纹进行了分析,并根据不同的标准把龙纹分为不同的类型,主要有团龙纹、两头龙纹、盘龙纹、爬行龙纹、双体龙纹、交体龙纹等。西周时期的龙纹在承袭商代纹饰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具有对称性、连续性、注重美感、雕刻技法高超等特征。文中指出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艺术表达、精神寄托、维护统治三个方面散发着鲜明的时代文化内涵。龙纹是西周时期青铜器纹饰的主要样式之一,不仅是当时人们对“自然精神崇拜的产物”,而且是“王权的象征,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是‘别尊卑,明贵贱’的标志”。①朱敏:《西周青铜器龙纹浅识》,《理论观察》2018年第2期。中国古代的龙纹图案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丰富,形成了不同的主题风格、规格形状、内涵寓意。1978年河南省南乐县发现的一座东汉大墓中出土了一件盘龙石砚,其雕刻主题是“驾六龙而御天”②刘素阁:《东汉盘龙砚的龙文化主题与雕刻艺术》,《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雕纹细致入微,飞龙栩栩如生,十分精美。
到了明清时期,龙的图案已十分圆润、唯美,而且皇家对龙纹使用的管控更加严格,官民不得擅自生产、使用或穿着印有龙纹的器具、服饰。张科撰文考述了明代五爪龙纹瓷的使用及相关问题,从使用人群的身份入手,将明代五爪龙纹瓷的使用情况分为皇帝所用、品官和平民所用、亲王和郡王所用、大乘法王所用四种,在此基础上又对身份等级配享和来源途径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文章着重指出嘉靖之前五爪龙纹瓷的使用符合礼仪规制,但嘉靖以后出现了逾越级别的特赏,这种违背禁限的现象尤以私自定烧最为突出,且非一般僭越行为可比,“应是晚明时期‘僭礼坏乐’社会风气的产物”。③张科:《明代五爪龙纹瓷的使用及相关问题》,《东南文化》2018年第4期。龙纹是皇家器物、建筑上的独享图案,其中龙纹琉璃瓦就是瓦当和龙纹相结合的经典之作。杨柳认为在观察清东陵的龙纹琉璃瓦时,可以把整个清代的琉璃瓦龙纹演变过程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从而有助于深入认识清东陵建筑的艺术价值、景观构成及文化内涵。④杨柳:《清东陵龙纹琉璃瓦当的魅力》,《中国文物报》2018年8月17日。
除了青铜器、瓷器、陶器外,玉器也是龙纹图案的一个重要载体。玉器研究专家杨伯达认为中国玉文化经历了“巫玉——王玉——民玉”三大历史阶段,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厘清了玉器龙纹造型的发展脉络。薛玉涵、于敏洁以此为基础撰文分析了龙纹造型在玉器上的演变,亦将玉器龙纹造型发展划分为巫玉时期(新石器晚期至夏朝时期)、王玉时期(夏朝至唐朝末年)、民玉时期(宋代至今)三个时期,“巫术盛行、王权至上、百姓喜爱,这都是各个时期的特点”,充分体现了龙纹玉器的权力象征的转移与削弱,并逐渐向普通民众开放、解禁的主趋势。在此一过程中,权力因素、经济因素、礼仪因素都对玉器龙纹造型产生了影响。⑤薛玉涵、于敏洁:《龙纹造型在玉饰上的历史演变》,《工业设计》2018年第11期。但中国国土广阔,地域文化差别较大,不同地区的龙纹玉器也有着不同的风格。范杰所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红山文化龙纹玉器研究》,将红山文化中龙纹玉器的类型分为“C”字形玉龙、玦形玉龙和其他龙纹玉器(双首龙纹玉器、直体龙纹玉器、蚕形玉器),并对龙纹玉器造型的原型、年代界定及分区进行了研究。⑥范杰:《红山文化龙纹玉器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龙纹在我国古代的应用十分广泛,龙纹与其他纹饰相互融合,形成了众多新的独立纹样,“鱼龙纹”便是其中之一。鱼龙纹是中国传统鱼纹和龙纹的结合体,王小燕的《中国传统鱼龙纹的源流及内涵》一文,从表现形式、历史渊源两个方面缕析了鱼龙纹的发展演化,认为鱼龙纹自出现后便被赋予了富贵、威严、勇猛、平步青云的吉祥寓意,而且以实干、自由、平等为核心的鱼龙精神亦可在当代社会中发挥自身的价值。①王小燕:《中国传统鱼龙纹的源流及内涵》,《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龙纹是中国古代人民群众的优秀文化创造,如何在当今社会主义时代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亦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在现代标志设计中,有学者认为将龙纹图案应用于现代设计时应遵循“在形式上进行创新,在意境上进行延伸”的原则,善于将传统的龙纹图案和创新理念结合起来,积极进行龙纹图案设计思想的革新,以避免设计中雷同现象的出现。②雒岩:《龙纹图案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再生探讨》,《中国民族博览》2018年第6期。在现代纺织品设计中,有研究者则认为要将龙纹设计氛围、龙纹的“意”、龙纹的具体造型、龙纹织物的传统工艺与现代纺织品充分融合,从中华民族传统纹样的继承与我国纺织品行业发展角度出发,“不断扩大龙纹的适用性,追求龙纹在现代纺织品中的再创新”。③陆裕:《元明清时期龙纹造型在现代纺织品设计中的创新应用研究》,武汉纺织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二、中外龙文化比较研究
龙文化从文明起源到初步成型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早期中国”④“早期中国”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于1975年创办《早期中国》(Early China)刊物时提出,时间范围从史前直到汉代,其所谓“中国”更多的是一个地理概念。此外,有中国学者亦提及“早期中国”的概念,韩建业则从文化意义上理解“早期中国”,认为“早期中国”指秦汉以前中国大部分地区因文化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相对的文化共同体,也可称为“早期中国文化圈”。和秦汉帝国以后历史上的中国相比,韩建业认为“早期中国”有着鲜明的特征:处于“前帝国”时期,还未出现真正的中央集权;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虽已登上历史舞台,但因实力有限尚未对中原等地的农业民族造成太大压力。(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页。)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龙”符号在“早期中国”经历了复杂多样的变化、聚合、革新,逐渐成形。“龙”符号从“早期中国”阶段初步酝酿、成长,到帝制时代大致被作为政治合法性的符号,再到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中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是“龙”符号源流大致经历的三个阶段。⑤李竞恒:《早期中国的龙凤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文化符号,中国人往往自称为“龙的传人”,常用“龙”来建构自己的族群形象。由于文化背景和社会风俗的差异,中外之间的龙形象与内涵也截然不同。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分别是东亚文化与南亚文化的核心内容,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也影响了中国的龙王形象。李程的硕士学位论文《印度那伽形象与中国龙王形象关系研究》,以印度那伽形象在中国的传播为切入点,详细探讨了印度那伽形象与中国龙王形象的关系。李程在分析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南北两条路线的基础上,认为图像作品中的龙王形象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而且受到佛教龙王信仰的影响,中国本土龙从唐代开始逐步向人格化神转变,形成了多元化的龙王形象。至于佛教龙王和中国本土龙相互渗透后之所以形成了统一化的图式——帝王的象征,作者认为其主要缘于“翻译问题、都与水有关、都是恩惠于人民的象征、都是财富的象征”等方面。①李程:《印度那伽形象与中国龙王形象关系研究》,鲁迅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近年来,随着中非之间的交流日益加深,文化成了增进不同国家人民之间友谊的一条重要纽带。津巴布韦籍的来华留学生马俊贤(Mandiringana James Tinashe)的硕士学位论文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探讨了津巴布韦与中国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龙”的含义、形象及历史变迁。作者指出中国“龙”是传说,是整个国家的象征,是图腾文化却没有法律基础;而津巴布韦的“龙”是一条真实存在的大蟒,仅是一个部落的图腾,并不是所有津巴布韦人的图腾,但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基础。在基督教和西方文化入侵后,津巴布韦“龙”的邪恶身份色彩更加浓厚,而中国的“龙”一直是瑞兽,两者不同的寓意也透视了社会地位不同。该文还深刻论析了当代世界文化传播与交流问题,通过分析中津两国龙文化的异同,为中津两国人民加深对彼此文化的了解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②马俊贤:《论津巴布韦与中国文化背景中“龙”的形象及文化意义差异》,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文字是文明的载体,诠释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成就和发展历程。中西之间文化迥异,而中国“龙”与西方“dragon”两个词汇亦存不同之处。闫增丽、范晓琪的《中国“龙”与西方“dragon”的文化内涵差异及其误译》一文,指出由于在翻译实践中通常将“龙”与“dragon”等值互译,易造成对中西文化内涵的误解和歧义。文章从形象、文化内涵两个方面对比了中国“龙”与西方“dragon”之间不同的文化内涵,进而分析了“龙”与“dragon”误译的原因和影响,最后提出了一个解决“龙”与“dragon”互译问题的重要方法,即将两者区别对待,“分成两个概念,各自使用正确的翻译”。③闫增丽、范晓琪:《中国“龙”与西方“dragon”的文化内涵差异及其误译》,《通化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对于英语中“龙”(“dragon”,读作“扎根”)的读音,徐江伟在《简论英语“龙”的读音来自古藏语》一文中,认为其来自于东方的古羌藏语,并随着史前羌藏类游牧民族的西迁传播到西方文化中。文中指出藏语“扎根”的本义是“眼睛猪”(具体而言则是“长有猴王眼睛的公野猪”),而“眼睛猪”正是“龙”的起源,与原始苯教的固有信仰密切相关。④徐江伟:《简论英语“龙”的读音来自古藏语》,《杭州学刊》2018年第4期。徐江伟从英语“dragon”读音入手,缕析起源、发展与演变轨迹,展现了古代中西方之间的民族融合与文化碰撞,以及人文、地缘环境因素孕育下的不同的“龙”文化内涵。
三、龙神信仰与崇拜研究
龙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象征,“龙”不仅是中国古代帝王皇权的独断标识,而且与广大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龙”是包括汉族在内的众多民族的共同信仰。早在原始社会时期的红山文化中,“龙”是该文化的主要内容,红山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也占有格外突出的地位。迄今在辽西地区发现了许多“龙”形遗存,以玉器为最多,因此有学者将该地视为“中华崇龙文化的发源地”。⑤腾海键:《红山文化与崇龙》,《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玉龙的出现是红山文化发展成熟的体现,但其绝不是龙文化的唯一发源地。中华文明呈现出“多元融合”的格局,除红山文化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等文明发展中都出现了龙崇拜现象,这说明龙文化的最终形成是中国早期各类型文明相互交融的结果,而红山文化在其中起到了“奠基性作用”。中华文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华各民族不断聚合、互动的过程。沙勇在《明清时期洮州地区龙神信仰的文化内涵》一文中,通过分析洮州地区多元宗教文化共存的社会空间特征,缕析该地区的龙神信仰体系,深刻指出了洮州地区龙神信仰的文化内涵,这既是“汉族移民对原生地文化的追忆”,又反映了“汉族与当地藏、回等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的真实社会场景”。在历史与社会的变迁中,在超族群、跨地域的民间信仰仪式与祭祀活动中,各民族的族群意识逐渐淡化,“却凸显了各民族共同的国家认同意识”。①沙勇:《明清时期洮州地区龙神信仰的文化内涵》,《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龙”的符号与认同,亦深深镌刻在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历程中。殷鹰在《简论彝族民间信仰中的龙崇拜》一文中,论述了“龙”神崇拜与彝族起源发展的关系,指出龙不仅是彝族普遍崇拜的图腾祖先,而且被尊为“创世之神、祥瑞之神、司水之神”。其中汉文化对彝族文化产生了多重的影响,“彝汉文化交流过程中,在涵化作用下,彝族文化中龙崇拜的边界日渐扩大,龙的属性逐渐泛化”,至今仍存在着隆重的祭祀龙神仪式。②殷鹰:《简论彝族民间信仰中的龙崇拜》,《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在关于“龙”的众多崇拜中,“司水之神”则是彝族最早的信仰。杨杨、杨甫旺的《洁净与异化:彝族自然崇拜中的水与龙》一文以云南昙华山彝族龙崇拜为个案,指出由于当地彝族民众对水的生存依赖及其对风调雨顺、无水旱涝灾之虞的期望,引发了对掌管水的种种神秘力量的崇拜,加之明清以后汉族龙崇拜思想对彝族的渗透,使水崇拜与龙崇拜相结合,孕育出了在农业生产和祭祀活动中占有崇高地位的龙神信仰体系。③杨杨、杨甫旺:《洁净与异化:彝族自然崇拜中的水与龙——以云南昙华山彝族龙崇拜为个案》,《攀枝花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在古代中国,漕运一直在国家交通运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京杭大运河内帆船接踵往来,岸上楼宇鳞次栉比,十分兴盛。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岸地区普遍存在着水神信仰,而金龙四大王则是最具代表性的水神之一。胡梦飞在《明代漕运视野下的金龙四大王信仰》一文中探讨了金龙四大王信仰这一特殊区域文化现象,指出漕粮运输中的艰难险阻,使得明代开始出现了专门的漕运保护神——金龙四大王,而金龙四大王庙宇的分布与地区漕运、河患的现实情况密切相关。随着金龙四大王信仰对明代漕运及其治理的影响日益凸显,对水神的敕封、建庙、祭祀逐步转化为一种“国家仪式”,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④胡梦飞:《明代漕运视野下的金龙四大王信仰》,《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以“龙”作为司水之神古来有之,但在金龙四大王信仰体系中,借用“龙”之威名,将“龙”神归附于现实中的治水忠义之士,且经过文人对金龙四大王形象的改造,金龙四大王信仰呈现出人格化特征。区域社会的复杂性造就了水神信仰文化的差异性,胡梦飞另撰文考察水神信仰盛行的江南地区,指出在其信仰体系中既有全国性水神(金龙四大王、晏公、龙神等),又有区域性水神(潮神、湖神、地方祈雨神、妈祖等),认为江南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该地各种水神信仰盛行的重要原因,而崇祀水神在应对水旱灾害、促进官民互动、强化地域认同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⑤胡梦飞:《明清时期江南运河区域水神信仰文化述略》,《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在漫长的农耕文明进程中,龙神信仰一直充盈了中国历代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内容,是他们“生活的办法”①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第8页。,亦是民众理解、把握自身命运的一种观念和文化创造,“是解决自己现有知识和能力边界之外的日常生活问题的一种方式”②李俊领:《天变与日常: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华北泰山信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69页。。以龙舟竞渡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中国龙舟文化,最早起源于祈雨除厄的祭祀仪式。而后伴随着民族之间的融合、南北经济的交流等,龙舟文化逐渐传播到中国各地甚至国外。台湾地区学者黄丽云的专著《龙、船、水与端午竞渡:龙神信仰的文化符号》,以台湾地区的龙舟文化为对象,展现了几经中国改朝换代而不断上演的各种民营、官营龙舟竞渡。这一现象在清代一度达到鼎盛,黄丽云指出清朝海航贸易与物物交换的发达,使得台湾地区这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作为龙神信仰之路、守护海上贸易及通商达成之地而备受重视。作者认为祭龙竞渡的演变与龙神信仰的发展密切相关,龙舟竞渡不独农耕祈雨仪式的宗教性、祷祝行为的竞技性之崇拜,更是历史进程中政权的象征符号与经济指标,产生了相当大的经济效应和社会功能。③黄丽云:《龙、船、水与端午竞渡:龙神信仰的文化符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四、龙文化的当代价值与开发
毋庸置疑的是,“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更是千百年来中国的国家象征,在当代社会发展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刘东的《中国龙文化历史嬗变的哲学解读及其当代价值的实现》一文,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革,民众对龙文化的认知从抽象符号向精神内核转变,受众群体则从特权阶层向普通民众下移。指出“解读龙文化中的崇拜文化、节庆文化和教育文化”,“领会龙文化的艺术内涵、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依托龙文化的内涵、当代发展和广泛传播”是实现龙文化当代价值的现实路径。④刘东:《中国龙文化历史嬗变的哲学解读及其当代价值的实现》,《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由龙文化而形塑的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实践。中国人一直以“龙的传人”作为自己的身份标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仍需要以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认同感凝聚民族力量,在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开发中汲取营养,获得新的意蕴。
“龙”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信仰,亦是众多社会活动与民俗风尚中的文化符号。舞龙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民俗运动,不同的仪式透视着厚重的文化意义。刘鲲的博士学位论文《舞龙仪式的文化考察》以崇义沈埠畲族七节龙和关田镇三节龙为个案,综合运用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细致描述并分析舞龙仪式的形式与内容、演进历程及原因、历史记忆、时间与空间结构、物品与行为的象征意义等,揭示出舞龙仪式背后的“国家、社会、民间、宗族的互动”及“经济、政治、文化、信仰背景”,并试图对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启示。舞龙不单是一种仪式,更是“一种认同、一种纽带、一种敬畏”,不应只活跃在竞赛、舞台之中,更要在日常生活中,让民众感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秩序、仪式感和凝聚力”。⑤刘鲲:《舞龙仪式的文化考察》,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伴随着复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热潮的涌动,舞龙运动从民俗运动发展成一项竞技运动、文化教育活动。傅学祥、毕玉祥在《“舞龙”对促进大学生民族文化认同的作用研究》一文中,分析了高校开展舞龙运动的现状与挑战,认为在高校开展舞龙运动承载着传承和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使命,且在“构建民族文化传播和促进文化认同”、“增强民族的文化自觉性”、“培养大学生对文化的理性选择思维”、“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①傅学祥、毕玉祥:《“舞龙”对促进大学生民族文化认同的作用研究》,《武术研究》2018年第8期。
正如龙文化的区域性差异,南北舞龙运动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王海彬的《皖南民俗体育发展研究》一文,以皖南池州舞龙习俗为研究对象,展现江南地区“以文为主,突出龙的灵活敏捷、变化自如”的风格。当今舞龙民俗文化的保护面临着宣传力度弱、民众意识淡薄、人才不足、政府投入少等问题,而大力发展舞龙文化产业、加强舞龙文化的传承、广泛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重视学校的文化教育功能等则是解决以上问题的方法。②王海彬:《皖南民俗体育发展研究——以池州区域舞龙习俗为研究对象》,《淮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年第3期。舞龙民俗运动在当代社会中遭遇的发展瓶颈,是众多中国传统民族文化遗产面临的共同挑战,继承传统、发扬经典,仍是我们需要重树的理念思维。
五、材料、方法与视野:关于“龙文化史”研究的片段思考
近年来,学界尝试从跨学科、多维度对龙文化进行研究。中华龙文化传承数千年而历久弥新,作为一种蕴含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文化类型,除了从文化学角度进行阐释外,尤要注重社会变革和时代蜕变中龙文化的发展演变历史,这需要具有更多的历史学研究思维和关怀。所谓“龙文化史”,亦即龙文化发展的历史,具体而言则是龙文化逐渐大众化的历史。开展“龙文化史”研究,应秉持“眼光下移”的原则,回溯龙文化影响下的历代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展现文化与社会的有机联系和互动关系。这不仅是研究领域的深化,更是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新拓展。
首先,进一步发掘和整理相关资料。傅斯年曾说,“史学便是史料学”,“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的话也从侧面反映了基本资料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若要使某一方面的学术研究富含生命力和创新力。并不是简简单单地移植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更重要的在于对资料的发掘与思考。开展“龙文化史”研究,目光向下,聚焦于民间社会,族谱家乘、神话小说、方志碑刻、文集笔记、日记回忆、戏本歌谣等是主体史料。当然,龙文化的发展与中华文明的演进相生相长,诸多历史文化遗存亦是我们“重塑”原始场景的重要参考方面。数千年来,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带来了精神生活的更革,龙文化的内涵亦不断丰富,而这种变化则主要以民众的物质资料为载体。故而开展“龙文化史”研究,应将实物资料与文本资料相结合,“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证,如此更能清晰地反映龙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
其次,汲取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和理念。20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学经历了数次转向,从兰克史学到年鉴学派,从传统政治史到经济社会史、心态史,对文化的考量不断强化。20 世纪80年代,西方历史学的“文化转向”(或“语言学转向”)带来了“新文化史”的兴盛,原先被边缘化的大众文化和小人物开始得到关注,同时更加注重历史事件背后的文化因素,着力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对“龙文化史”研究而言,则需从文化视野中进行历史的考察,借鉴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分析符号、仪式、信仰、节日等的文化象征意义,“深描”普通民众对龙文化的理解、情感和态度,还原一个“自下而上的历史”。关注龙文化影响下的历代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亦不能仅仅停留在“描述史实”浅显层面,“一定要从‘生活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既要研究社会生活,也要研究背后隐藏的社会观念”。①左玉河:《突出成绩与发展瓶颈:20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载郭莹、唐仕春主编《社会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1页。
再者,树立全球史视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近年来,西方史学界在继“文化转向”之后,又发生了“全球转向”,“全球史”浪潮正在冲击着历史学科各个领域的研究。所谓“全球史”或“全球史研究”,简言之则是“大范围的互动研究”,其核心理念是全球之间的“互动”,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接触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领域实现互动。②刘新成:《文明互动:从文明史到全球史》,《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龙”的崇拜广泛存在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中,开展“龙文化史”研究,需要突破以往狭隘的思维框架,以更宏观的视角来检视跨国与跨文化交流、碰撞下的诸多问题。但仍需注意的是,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日益激烈,“龙的传人”依然坚定捍卫中国传统文化。“龙”的符号象征与民族认同在近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亦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历程中宝贵的文化资源。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中,我们的研究归根结底要植根于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土壤之中。全球史的研究应当是多样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当我们在把握全球史的跨文化研究标签的同时,不该忽略本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研究者应找好平衡点,将宏观的全球史与微观的全球史相结合,既要与世界相对接又要讲好“中国故事”,理性地游走在民族国家与人类世界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