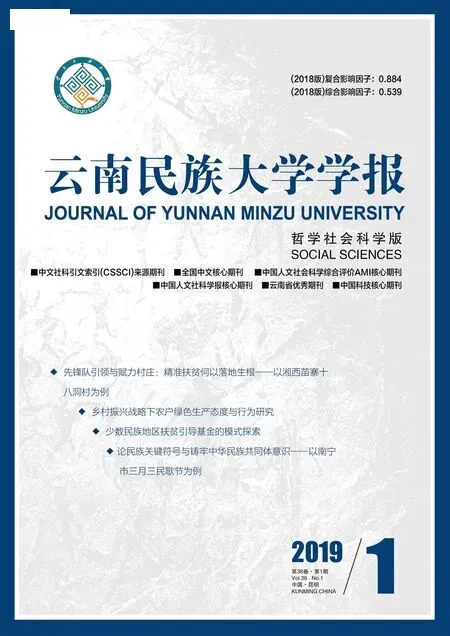“非遗”后艺术民族志书写及其社会想象
2019-12-09杨秋月
周 园,杨秋月
(1.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都与艺术行为表现形式紧密联系。这些在人类行为习惯下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形式,不仅是艺术的外在存在形式的展现和技艺存在方式的体现,更是叙事化和结构化的历史语境书写,甚至成为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根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 2、表演艺术 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 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5、传统手工艺。的界定可以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存在,它具有流变性、独特性、传承性、民族性、多样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往往又是通过艺术民族志而被更多的人所认识。艺术民族志通常是以兼具研究者对于艺术本体以及艺术参与者的体验而形成的文本。在书写艺术民族志时,原本是借助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把艺术作为包含艺术本体以及艺术参与者两方面情况的一个整体进行书写,但是当非物质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作为兼具文化与艺术双重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被重新发现,致使其因独特的价值而在特定时空中成为社会想象对象,进而改变了艺术民族志的书写范式和书写目的。尽管这种书写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艺术本体和艺术参与者创造艺术本身的意义、本质和目的的真实再现,但是却又赋予其新的社会价值蕴含,同时也验证了既有的学术观点:不同的艺术民族志书写范式虽各有侧重,但其旨趣均在于寻求某种艺术文化脉络中的客观真实,研究文化事项过去、现在、未来的状态,试图发现暗含在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价值和意义,从而了解社会,理解人类本身。*张絮:《艺术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大众文艺》2016年第1期。
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成为社会多方密切关注的话题。特别是2006年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后,在我国首次以政府决策的形式组织开展了对乡民艺术进行“保护”。在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促进下,组织开展了诸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员认定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工作及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众教育等多方面的保护工作。同时,在民间层面也相应产生了众多围绕“非遗”的应对策略,比如文化重构、历史溯源、复兴再造等等。正是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推动下,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当代非遗建构过程。
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化建构,对于其传播与保护也有着积极的作用。“文本化”意味着关注与艺术互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强调艺术活动的过程性、语境性和可读性,实现了审美与民俗活态之间的良好平衡。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化之后
“非遗”术语含名词与动词词性。作为名词,意指先辈创造遗留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动词,则含有根据一定的目的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特定的社会意义的行为和结果,使其蕴含着权力、社会、认同等,而且使得“非遗”之后书写艺术民族志时显然地观照了从多角度阐释艺术的存在、价值、发展以及对其历史、现实、未来和相关权利关系这两种维度。所以,“非遗之后”也被称为“申遗之后”,目的就是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以及被赋予的社会意义这两重属性。从现实的角度看,“非遗之后”的环境是在国家、社会、乡民等在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被多方关照后,对于这些民间文化艺术的解释和认同方式随之转变的社会时空,自“非遗”概念产生后的多方观念、行为、价值的存在于成为这一时空中的“非遗”生存场域之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创作者总是在特定的时空内创造出“通过生产对艺术家创造能力的信仰,来生产作为偶像的艺术品价值。”*[法]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 276 页。传统艺术研究视艺术为无关功利的精神领地,而布迪厄的艺术场域理论则更加务实,说明艺术的小领域和社会大世界之间有着难分难舍的关系和逻辑。“非遗”在多重权力的主导下,有意无意的穿梭于各种社会场域中,使得这一时空中的乡民艺术已不同于原生环境中的艺术存在。这种“非遗”之后的“艺术”存在模式受到政府、社会、乡民等多方关照,也受到经济、意识、权利的干预,这些多方因素都成为了乡民艺术在“非遗”之后的生存状态和延展趋势。因此,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以历史叙事的方式,通过一个具体的实物在连续的长时间段考量该种文化现象的传承及变迁,这种结构主义式的考察不仅使研究者关注该种艺术形态当前的表现形式,更让考察者去进一步探寻这种表现形式过去的历史形态,以及背后的文化因素、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宗教因素等诸多历史背景内容,以试图对当前艺术形态的保护和复原延续着某个特定文化群体的记忆传承。
乡民文化艺术在这样的联系中发生着变迁。“非遗”前后,乡民艺术经历了从自然变迁到人为变迁的变化:“非遗”之前的艺术变迁主要存在于乡民自我生活发展的一个自然变迁和自然选择,“非遗”之后的艺术变迁则受多方的影响且朝着多维向度发展。在非遗之后,乡民艺术作为多种角色在诠释地方民族文化,因而许多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不同角色获得了不同的解释表征和社会关系网。这样的多重语境,成为了“非遗”之后乡民艺术存在的现实境遇。在多重语境的“非遗”乡民艺术,存在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变迁的动态过程,无论是生态环境还是文化环境都在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都是“非遗”之后现代艺术变迁的多重因素。
任何文化的产生都和人类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非遗”之后的乡民艺术的生态环境、文化环境、政治环境、权力环境、发生环境都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而形成多种存在的社会结构形态。显然,“非遗”之后艺术活动的发生环境、艺术主体、呈现方式、社会功能等都发生了变化,逐渐成为了政府、学者、乡民互为主体下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等,各方均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和处理非遗的当下社会存在。这诸多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存在的艺术民族志的书写。
二、非遗之后的艺术人类学研究
伴随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深入,艺术人类学越来越受到人类学和艺术学界的关注,“非遗”也成为了当下艺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艺术人类学秉持着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关照来讨论当下“非遗”的昨天、今天、明天。
在研究者层面,他们力图通过田野调查并采用当代社会学科学的统计方法,以科学客观的手段,在学理上做出阐释和说明,不断反思艺术民族志的使命,力求使之成为文化当事人和政府之间的粘合剂。而文化当事人也在‘非遗’之后的场域中发挥着主体性作用,与学者、政府、市场和文化自身发生着深深的互动。当某项传统乡民艺术事项被发现和再造并完成了“非遗化”过程之后,这些原生态的民间艺术事项在当代大众文化的通俗审美之下,以其独特的民族志书写形式和特有的文化张力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出新的审美形式潮流。
“非遗”之后的乡民艺术由此具有了现实的依托乃至多重的身份,是文化、是话语、是遗产、是资源,这些不同的身份为其当下的存在奠定了基础。这些身份是由政府、学者、社会、乡民多方赋予的,也受多方凝视和“操控”。艺术人类学的当下任务,应该是从民族志的书写中发现并以文本的形式清楚地阐释这些不同的传统乡民艺术形式在“非遗”受多方凝视所产生的多种环境,并用人类学的视角阐释乡民艺术的历史、文化、价值、评价、未来等,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She thinks she is a whale(鲸).But she is a shark(鲨鱼).She is very elegant(优雅的).
“非遗”之后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在整体观的基础上,注重对文化多样性的把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非遗’保护工作从根本上是在保护文化的多样性。”*种隽迪,熊玉媛,李亚,朱腾蛟:《“非遗之后”田野论坛综述》,《大音》2016年第2期。这里所指的多样性不仅仅是指外在表现形式的多样,更是指深深蕴含于多样性群体内心的宇宙观、世界观。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活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本身就是一种乡土艺术,艺术人类学对传统乡民艺术的田野考察、记录和研究的终极目标就是力图触及其深刻的内涵。“非遗”之后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特别关注文化创造者和持有者的主题性地位和表现,尤其是对那些因为“非遗”之后环境变化而导致的文化参与者原有主体性丧失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照。在“非遗”活动中,政府及相关组织操办一系列活动,为“非遗”扩大了社会知名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文化群体或文化持有者文化自信的增加,“然而……‘非遗’的问题也凸显出来。……作为文化持有者的当地百姓反而逐渐失去了对自己文化的话语权,被作为“他者”的政府、社会组织或学者所牵着鼻子走。”*纳日碧力戈,胡展耀:《“非遗”中的互为主体与人类学的社会担当》,《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比如,在白族传统石宝山歌会或壮族歌会中,人们对唱的空间是分散的,或者说是无中心的。在分散的空间中,该文化现象的主体通过艺术的展现形式来彰显其存在性。但是当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在成为一种范式化的表演之后,在空旷区域就形成了一个话语中心的舞台。当舞台中心与话语权之间发生不匹配时,艺术主体就失去了其话语权。基于此,“非遗”之后如何保护文化当事人的主体性往往被当作是人类学的担当。
人类学的担当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去追寻一切文化事项的本质和意义,因此,针对围绕着乡民艺术事项非遗化前后的种种现实变化,人类学者、艺术人类学者宜给予其更多的关注,把握好发现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价值、当下价值,尽可能妥当地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最大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对文化自身造成的伤害,增强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与发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不同文化群体和谐关系建设之间的关系的科学性。
三、非遗之后的艺术民族志书写
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文本本质上是艺术民族志的书写,是“非遗”之后艺术人类学必须关注的重要领域。有学者认为,人类学是“做”出来的,“做”,首先就要落实到民族志上。*高丙中,李立:《用民族志方法书写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作为知识生产的场所的村落关于写文化的对话》,《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同样,要做好艺术人类学就必须要建立在做好艺术民族志书写的基础上,艺术民族志的书写水平也是体现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艺术民族志的书写既是书写“非遗”在当下语境中的存在形式、意义和价值,也是“非遗”之后写文化的重要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适应社会、传承生活所留下的人类财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志的书写是文化诗学的阐释。
纵观有关“非遗”艺术民族志研究成果,“非遗”之后的艺术民族志书写不完全是对田野工作的简单记录,而是把“非遗”之后的具体文化事项作为艺术发生体在空间场域内实际发生的意义进行书写,也就是站在阐释意义的视角进行艺术民族志的书写,书写范式与之前完全忠实于客观真实再现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了保证再现艺术民族志时避免完全的失真,应该牢牢记住“民族志写作的关键特征就像失窃的信一样,它就在眼皮底下,反而逃脱了人们的注意”*[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方静文,黄剑波译,褚潇白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的警示。因此,艺术民族志的书写一定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艺术民族志的书写应该是“艺术田野”后对于整个艺术文化体系的“深描”。“艺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学术取向便是改变艺术研究中的‘标本化’或‘博物馆化’状况 ,”*何明:《直观与理陛的交融:艺术民族志书写初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对研究对象采取“正在进行时”的观察。
“非遗”之后艺术民族志的书写应该置身于当下“非遗”环境现实和不断变化的艺术场域,在“动态”的艺术场域中对“非遗”进行观察、体验、描述和分析,以“他者”“自我”的双重身份在现实社会关系网中进行深入剖析。“非遗”之后的乡民传统艺术成为了多方关照下的社会文化、历史遗产、发展资源,对于这一时空中的艺术“深描”需要权衡多方利益,以不同的视角解释艺术的社会性。随着艺术人类学理论的不断更新与发展,对于“非遗”的研究已不再是“见树(艺术)不见林(文化)”的本体研究,而是从艺术本体的研究转向对于艺术发生、传播、传承、发展的多方研究,在“非遗”热潮的驱动下,开始从读书转向读社会,“非遗”之后的艺术已从原本的乡民文化转变成了社会资源供多方凝视。
其次,“非遗”之后的艺术民族志书写应该是多角度地考虑当下“非遗”的社会角色及其所建构的当代“非遗”保护场域,应该从历史溯源、社会评价、建构再造、共同体形成等维度进行艺术的把握和阐释。多维视角中“非遗”的社会阐释与社会构想成为了当下艺术民族志书写的社会集体视角即社会想象,这种多维度的社会思考与把握也为解决我国非遗保护问题提供了文化视角与学术参考,艺术民族志的书写经过社会多角度的想象和阐释,最后通过文本化策略得以实现。
“非遗”之后的艺术民族志书写要以社会评价为参考进行多角度的考量,通过不同的群体、阶层、场景的反映来记录非遗的现实社会评价。“遗产资源论”是“非遗”之后人们普遍认同的一个观念,乡民艺术通过“非遗”化后已成为了当下人们的文化资源。对于这一现象的书写,应该从遗产的现实社会价值出发。遗产到资源的转变是“非遗”后乡民艺术主体地位转变的重要标志,“遗产通过神话、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当地自豪感、浪漫思想或仅仅是市场营销,被加工成商品的历史。”*Schouten,F.J..Heritage as Historical Reality [M]//D.T.Herbert,eds..Heritage, Tourism and Society.London:Pinter,1995.
“非遗”作为动词正在完成这一过程,过程中的社会评价将是这一乡民艺术发展动向的有力参考,在艺术民族志书写中要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乡民艺术从“遗产到资源”的社会反应和社会因素。“非遗”之后的乡民艺术正在作为资源被多方重新建构,建构的过程和方式则根据资源持有者的价值判断进行。从“乡民艺术”到“非遗”再到“资源开发”,过程中的“资源开发”是“非遗”之后政府、学者、资源持有者当下急待解决的一个难题。传统的乡民艺术无论是本体还是文化系统,已不再适合当下大众生活与审美。怎样建构这些文化遗产来适应当下生活,也是“非遗”之后艺术民族志书写中要多方阐释的。从方法、结构、意义、体系等角度解释遗产资源也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建构过程。
再次,“非遗”之后的艺术民族志书写,要从历史的维度理顺艺术作为文化的“前生今生”。历史维度中的原本乡民艺术的发生、存在、价值,是当下“非遗”之后书写的基础。从历史中可以深层次的理解原本艺术的“那时”意义。书写历史的“文化自觉”的基础,历史是一切文化发展与创新的基石。费孝通先生就提出 “‘文化自觉’的意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 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方李莉:《中国陶瓷艺术审美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新艺术史观》,《民族艺术研究》2012年第6期。通过书写历史在认识作为“非遗”的乡民艺术及其存在的社会,并在此基础上更好的讨论“非遗”作为遗产、资源的现实价值问题,艺术民族志书写中历史视角是为了现在和将来更好的运用遗产资源。
此外,“非遗”之后的艺术民族志书写也要考虑“非遗”化后乡民艺术的相互认同和新共同体的形成。“非遗”本是原生环境中乡民族群认同、文化认同的重要参照,“非遗”后的乡民艺术无论发生环境、传播媒介、发展空间都不同于传统的场域。展演成为了“非遗”之后乡民艺术最主要的存在方式,政府、学者已经成为其共同体的形成的主导因素,作为主导因素的政府、学者和具有主体性的文化参与者脱离了原生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体系的存在,成为一个新的“非遗”之后的场域中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主要任务更多成为对外的,宣传展示性的,而不像以往主要是对内的。乡民自我认同的艺术共同体正在被削弱和简化,在进行艺术民族志书写中应该从不同的历史角度解释“非遗”之后乡民艺术新共同体的建构,并分析原共同体弱化的原因。
四、结语
多维视角阐释是当下“非遗”书写的重要途径,乡民艺术从民间文化通过“非遗”后,成为多重语境中多方凝视的资源。政府、学者、社会、乡民等多方,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作为艺术的“非遗”进行共享。艺术人类学方法植入“非遗”的研究将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对非遗进行剖析,从“他者”“自我”“社会”的角度出发书写非遗的当代境遇及发展趋势。
在对“非遗”的保护和建构中,艺术民族志的书写给官方和民间都拉响了警笛,不仅要关注作为静态展示的“物”,同时也要关注作为活态传承的“人”。官方和民间应该共同致力于发挥文化持有者在“非遗”保护中的主体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从研究“物品”转向研究当前的“非遗”实践有着重要意义:关注非遗保护的主体不能仅仅局限于关注当前特定民族文化的“非遗”状态,更应该厘清物和人在不同文化框架以及特定历史阶段中的脉络联系。只有这样,才能依据“地方知识”制定有效措施,将“非遗”中的文化持有人的主体性发挥出来,并且让“非遗”实践成为一场真正自觉的有益的行动,而非流于形式的表演。
人类学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文化深描的过程就是由田野考察走入非遗的地方性知识所编织的意义知网的过程,他们通过对非遗中作为主体人的符号性的能指与所指进行的阐释,充分展现了书写“身临其境”的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范式,突破了“非遗”发展与社会发展脱节的瓶颈,以社会能动、实践、发展的视角进行“非遗”的研究,使得艺术人类学解释“非遗”具有了时代属性。以艺术民族志的书写方式记录并解释乡民艺术在“非遗”之后的生存与发展,以文本解释社会想象中的“非遗”及我国“非遗”之后的问题,为理解我国“非遗”之后的真实境况提供了一种文化视角和学术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