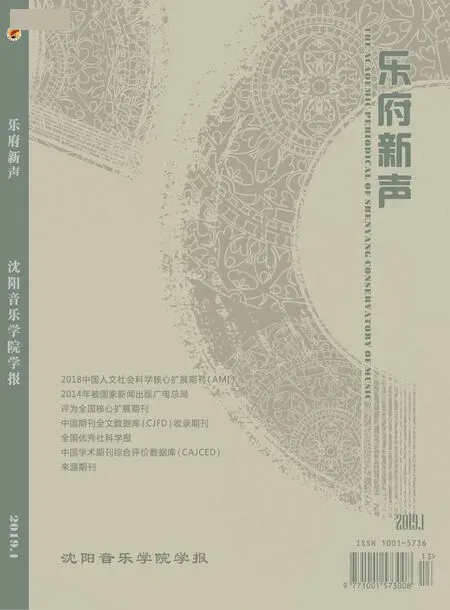高屋建瓴:学术大家的“未竟之作”
——评保罗·亨利·朗文集《音乐学与音乐表演》
2019-12-08周俊宏
周俊宏
[内容提要]文章将以著名音乐学家保罗·亨利·朗的遗作《音乐学与音乐表演》为评述对象,着力考察作者以不同身份,站在不同角度对音乐理论、音乐史、音乐表演实践的论述,及其凭借全面修养和敏感眼光对音乐事件的探讨。本书在将各个学科领域有机结合的同时,也深入剖析了音乐现象中易被忽视的细节。从学科理论到史学研究,再升华至表演实践,不仅反映了朗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发展轨迹,也彰显出一位理论家为实现音乐的最终目的而作出的巨大贡献。
美籍匈牙利音乐学家、音乐批评家保罗·亨利·朗(Paul Henry Lang,1901-1991)的这部《音乐学与音乐表演》文集[2]保罗·亨利·朗.音乐学与音乐表演[M].马艳艳,译.孙国忠、孙红杰,校.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是在朗辞世后,由美国音乐学家乔治·比洛[3]乔治·比洛(George J. Buelow,1929-2009),美国音乐学家。印第安纳大学荣休教授,曾任美国巴赫协会主席。代表著作有<巴洛克音乐史>、<晚期巴洛克歌剧>等.(George J. Buelow,1929-2009)与美籍德裔音乐学家阿尔弗雷德·曼[4]阿尔弗雷德·曼(Alfred Mann,1917-2006),美籍德裔音乐学家,音乐理论家,学者型指挥家。二战后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师从保罗·亨利·朗).(Alfred Mann,1917-2006)编辑出版的朗的遗作。其中收录了他1950-1980年代的29篇文章,“很好地反映了朗的‘学术生命’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轨迹,这对于我们从整体上观照朗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5]引自孙红杰“保罗·亨利·朗<音乐学与音乐表演>中译本序”.“西方学界一致公认:保罗·亨利·朗是最具宏观视野和最博学的音乐学者之一。其扛鼎之作《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是音乐文化史的代表性论著,其汉译本在中国的音乐界和文化界已产生广泛而健康的影响。《音乐学与音乐表演》则从另一侧面展现了这位饱学之士为人称道的广阔视野、敏感眼光和华美文风——其中不仅涉及专门的学理和史学课题,也对诸多当代和眼前的音乐话题发表了深刻而锐利的评议。这是不可多得的学问之书,也是开阔眼界的赏乐之书。”[1]引自杨燕迪对<音乐学与音乐表演>的评论.
保罗·亨利·朗出生于布达佩斯,曾就学于布达佩斯音乐学院,后赴海德堡大学和索邦大学攻读哲学、法语文学和音乐史。1928年获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而移居美国,先后在瓦萨尔、威尔斯、卫斯理三所学院任教,后在康奈尔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34年起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享有“美国第一位音乐学专席教授”之殊荣。其扛鼎之作《西方文明中的音乐》[2]保罗·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顾连理、张洪岛、杨燕迪、汤亚汀,译.杨燕迪,校.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被誉为“学养”与“文风”上的双重典范。朗是美国音乐学会的奠基人,曾担任国际音乐学会主席,他被公认为20世纪美国音乐学界的领军人物。
朗的文集《音乐学与音乐表演》是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目前正陆续推出的俄耳甫斯音乐译丛中的“重头戏”(2017年9月第1版),该译本由马艳艳[3]马艳艳(1983~),女,博士,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英语教师。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分别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和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法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音乐文献翻译工作,曾参与上海音乐学院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并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翻译,孙国忠、孙红杰校,这是上海高校高峰学科“上海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团队”的建设项目,是汉语文献中继《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之后被翻译引进的第二部保罗·亨利·朗的著作,也是他漫长学术生涯的“谢幕曲”[4]引自孙红杰“保罗·亨利·朗<音乐学与音乐表演>中译本序”.。
《音乐学与音乐表演》一书,在宏观架构上以“论音乐学”开篇,以“论表演实践”结尾,中间为“古乐新思”至“二十世纪文明中的西方音乐”的历史叙述,共四部分。全书虽然是四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但仍然可见清晰的历史脉络,以及从理论走向表演实践的升华。在此,文集的框架就已反映出作者对各个不同著述领域的涉及,从音乐学理论到相关表演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从远古的文艺复兴时期到二十世纪音乐。这部规模不算宏大的文集(中译本约30万字)不仅涵盖了16世纪中叶至20世纪末期的主要历史人物及其创作历程和风格特征,以及对当下事件的述评,还包含对音乐学学科概念、学者素养、学术研究方法的基本认识,并最终体现出音乐学理论研究对音乐表演实践的指导意义。同时,在微观叙述上,凭借其丰厚学养与华美文风,无论是理论性的论述,还是表演性的指导,作者都能游刃有余地作出权威性的解释。无论是对历史人物及其风格本质的探究,还是对当下的音乐事件的批评,作者总是能一针见血地道出真谛。
一、作为音乐理论家:执深厚的理论捍卫学术原则
“音乐学”(Musicology)是二十世纪初期才创造出来的词汇[5]约瑟夫·科尔曼.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M].朱丹丹、汤亚汀,译.汤亚汀,校.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那时的人们对这一术语感到迷茫甚至怀疑。在保罗·亨利·朗于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音乐学”是备受关注的焦点,直到以90岁高龄辞世的那一年,朗始终是它的捍卫者。[6]参见保罗·亨利·朗<音乐学与音乐表演>编者按.
由此,文集开篇的第一部分《论音乐学》是学科导论式的文字,朗运用其深厚的理论功底以及跨学科的广泛学识,从音乐学理论的角度论述学术规范与原则,为学者、学生们提出良好的建议。例如,在关于音乐学研究的问题上,朗认为,音乐学家不应只专注于自己的研究而不屑对其研究的内容进行解释,应承担起专业普及的任务,专业学者的贡献不仅仅是增长知识,还包括整合研究成果并形成一种叙述,达到有效传播的目的。朗希望学者的研究既充分适用于研究论题,也充分适用于研究目的。[1]保罗·亨利·朗.音乐学与音乐表演[M].马艳艳,译.孙国忠、孙红杰,校.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3-14.又如,在关于跨学科的问题上,朗毫不掩饰地坦言道:“音乐学家的首要资质便是意识到:钻研其他学科是情势所必须,而不是个人的趣味和期望使然。”[2]同上,第15-16页.朗仍然强调音乐学不仅需要人文学科的帮助,也需要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帮助,因此,对于音乐学来说,跨学科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再如,关于音乐与历史的问题,朗通过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例子,说明他们的一些作品明显脱离了所处时代的音乐潮流,证实许多音乐鉴赏书籍存在误评的情况,因此希望音乐史专业的学生们能辨别历史判断,扼制歪曲性言论的不断扩散。[3]同上,第36-37页.
朗总是能自如地运用各个学科的知识,全面透彻地剖析音乐中已存的现象。例如,朗为了论证“研究一种艺术发展的首要前提是必须深入探查其内部的动力、张力、事件节奏,以及存在于价值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他选取了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古典时期进行论述,令人赞叹的是,朗不仅通晓音乐学学科理论和音乐史,还涉及哲学、文学、美学、历史学、心理学、宗教史、社会史、自然科学等学科领域。[4]同上,第一部分第三篇文章“音乐与历史”的论述.使得朗看待音乐文化现象时极具全面性和关联性,他总是能将它们有机地联系起来,并给予读者全方位的知识养分和研究建议。
二、作为音乐史学家:以活力的洞见阐述艺术人物
朗对历史艺术人物的评述在这部文集中彰显出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见解,他并不是像以往一样按照生平、背景、体裁、风格的模式撰写,而是从整体上把握作曲家及其作品的特点,结合史实与美学价值,剖析音乐的本质。既有历时性视角承接的连贯性,又有共时性视角通过其他文明要素论述该艺术人物的精神层面。朗以非同寻常的切入点、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和极具活力的洞见更加丰富地展现出以往容易被我们所忽视的方面。
例如,在谈及将巴赫的独特伟大性、历史地位归因于他的真诚,他笃信的宗教信仰的问题时,朗认为这种教科书中“官方化”的赞美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他的生活,也忽略了他的人生价值。朗更注重于巴赫的心灵,认为巴赫是一位具有灵性的诗人,他的前奏曲充满诗意。巴赫的大多数作品不仅表现了宽广而多彩的诗意范围,还往往具有严格而清晰的逻辑结构。朗认为这才是将巴赫称为艺术家的真正原因。[5]同上,第二部分第三篇文章“巴赫:艺术家与诗人”论述.朗对于亨德尔的深入研究发现,虽然这位宗教音乐的模范人物与巴赫齐名,但他的作品缺乏伟大的巴赫音乐中所具有的深刻奥秘,而且他没有谋求高瞻远瞩,而是沉醉于当下;他的音乐虽然具有强大的道德力量,但同时也颂扬肉体的吸引力并诉诸感官上的美妙。[6]同上,第110页.
又如,对于莫扎特的描述,朗认为莫扎特的伟大性超越了我们的分析和讨论,莫扎特的音乐是纯净、完好、圆满而善终的,没有可以讨论的切入点。因此,朗并没有提及莫扎特具体的某一部音乐作品,而是从整体上对其音乐语言、音乐意义、音乐灵魂进行述说,更多的是结合史实,从感触上描绘莫扎特的音乐本质。显然,朗这样的写作方式更具震撼力。在他的评述中,莫扎特的音乐早已上升到触及灵魂的高度,是不卷入喧嚣的世俗,独立自处,梦想着在更纯净、更高尚的地方游走,他的音乐是天使们的音乐诗歌。[1]见保罗·亨利·朗.音乐学与音乐表演[M].马艳艳,译.孙国忠、孙红杰,校.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二部分的第七篇文章“莫扎特”的论述.
再如,当论及瓦格纳时,朗从《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进入,非同寻常地谈及了瓦格纳的男女关系问题,虽然朗说:他放荡、毫无节制,在这方面他完全没有道德原则。[2]同上,第151页.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创作境遇似乎与这些放荡情事的特点并不符合,而是他与魏森冬克的炽烈爱情的灵感结晶。在瓦格纳的作品中,对狂喜和死亡的赞歌虽然浓烈,却经不起沉思,因为它没有明确的指向和目标,也没有融入戏剧的综合体。[3]同上,第153页.
三、作为音乐批评家:持犀利的文笔批评当下事件
朗不仅关注“过去”,也关注“现在”。他不仅为读者带来了针对历史上最伟大艺术人物的新意迭出的论述,还乐于评论当前发生的事件。虽然它的论述对象是当时发生的事情,但他的写作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局限于时代的。朗用犀利的笔锋、幽默的语调和坦率的建言对当下他所认为不良的音乐现象发出警告。
如谈及十二音体系时,不可否认,勋伯格的音乐具有高超的作曲技术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他的艺术具有不可阻挡的影响力。但朗直言不讳地指出:勋伯格错误的音乐美学观却创造了一个可怕的世界,为那些回避清晰感和单纯意义的作曲家提供一个骇人的庇护所。他认为,音符的罗列和排序并不意味着任何“音乐性”,因为它并不出于审美构造的范围之内。[4]同上,第166-168页.
在“二十世纪中叶的奉神音乐”一文中,朗先是用幽默风趣且带有讽刺意味的言语描述着圣诞节的宗教音乐:“教堂唱诗班翻出封存已久、布满灰尘并带着折角的《弥赛亚》……管风琴师们将乐意为不合适的音乐提供一个合适的改编版,并确保他们的伴奏甜蜜而拖曳,据说这样就能营造出所谓的宗教气氛。”[5]同上,第219页.紧接着,朗直言批评:“报纸上将预告圣诞期间会被演出的音乐作品目录,我再也想象不出比这些节目更枯竭、更悲哀、更无味的三流‘宗教艺术’了。”[6]同上,第220页.随后便讲述了巴赫时代圣诞节礼仪活动的传统,朗赞叹过去写作教堂音乐的是每个时代最伟大的作曲家,但他对如今大师创作宗教音乐成了非常稀奇的事情这个现象深表遗憾。于是,他又批评道:“我们那低俗的音乐文化修养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低劣的教堂音乐。”[7]同[6].朗在文末再次告诫宗教音乐作曲家:应承担起培养他们的主管领导和宗教会众在音乐上的品位,不应违背天职去用甜美的音乐来娱乐大众。
当电影《莫扎特传》获得许多荣誉后疯狂席卷时,朗毫不客气地提出了警告:《莫扎特传》这部电影,无论它是否为了娱乐观众,都对莫扎特和萨里埃利造成了不公的冒犯,它使广大观众对这两位作曲家长期怀抱着扭曲的看法。它那擅长把真相神秘化的作者,所提供的是武断的心理解读,而非真正的灵魂评估。[8]同上,第246页.朗不仅是在批评这部电影的作者,还讽刺了电影界的评奖准则。
在对于白宫的仪式音乐问题上,朗列举了当时的一些质疑性报道,并坦率建言,认为不应该在重要的国事晚宴上展示类似百老汇小曲这样粗糙的文化表演,应邀请一位音乐大师来策划仪式音乐,避免出现尴尬。[1]保罗·亨利·朗.音乐学与音乐表演[M].马艳艳,译.孙国忠、孙红杰,校.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252.
四、作为音乐表演艺术家:从学术的角度指导音乐表演
音乐表演是兼有“技术”、“艺术”、“学术”这三重属性的实践活动,因此也相应召唤着三重素养。[2]引自孙红杰“‘音乐表演学读本’释注”.“不仅音乐学是密切联系实践的学科,好的音乐表演也必须具备“学术”尊严的实践。”[3]引自赵晓生“保罗·亨利·朗<音乐学与音乐表演>中译本序一”.现在,研究表演实践已成为音乐学家的伟大责任。《论表演实践》是全书最为精彩的部分。作为一位音乐学家、音乐批评家,朗的文笔和思维深度无可争议,令人吃惊的是朗对音乐表演技巧与原理的论述和评价,处处彰显出他在音乐表演领域的专业性以及他在艺术领域的全面性。
朗原本是想写一部论述音乐表演实践的专著,但由于他的离世,这便成为了一部“未竟之作”,也是他六十年辉煌学术生涯的“谢幕曲”。[4]参见孙红杰“保罗·亨利·朗<音乐学与音乐表演>中译本序二”.朗在晚年转变了写作风格,文人身份和评论家身份开始发生融合,凭借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渊博学识和职业表演家(朗谦虚地自称为“演奏者”[5]同上,第264页.)的丰富经验,探讨有关表演的学术研究与现代艺术家用自己的方式重塑经典时对音乐学术的动态吸收过程之间的相互影响。
朗常常对当下的表演实践提出一种批评性、沉思性的问题,并提供指导性建议。他对音乐表演的发展线条有着极为清晰的思路。朗认为,每一时期的艺术都是唯一的,它们不可能被复制或完整再现。[6]同上,第261页.由此,引申出对“本真性”言辞激烈的论述。朗断言:伴随本真性成为了古乐复兴的战斗口号,我们仍然处于篡改历史的危险之中。当下的一些古乐复兴者,只是在作表面工作,而没有真正复活音乐的内心精神。[7]同上,第267页.其次,由于早期作曲家并不是必然地把他的作品看作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也不会在乐谱上写下每一个细节,所以演奏者在表演时,通常也有参与创作的自由。更何况早期音乐时常出现即兴华彩,这原本就应该是由表演者即兴发挥,而当下的复兴者却依赖档案证据来进行表演,这就禁锢了即兴表演,因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兴。[8]同上,第四部分第五篇文章“论装饰音与即兴演奏”的论述.再次,那些复兴者还提倡复兴古乐器。朗认为,虽然对古乐器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其中包含了对乐器制造者、作曲家、表演者以及听众的考虑。早期乐器制造者的能力有限,制作出的乐器原本就存在缺陷;但作曲家的创作带有预见性,作品是为他们心中更理想的乐器而作;当下的表演者也并不适应使用古乐器演奏;现在观众敏锐的耳朵也并不能接受有缺陷甚至走音的乐器。可以想象,这样组合而成的复兴古乐表演是多么的别扭。[9]同上,第四部分第四篇文章“论古乐器”的论述.所以,朗认为,关于表演实践仍没有足够充分的事实可以保证绝对的本真性。他最终建议:不要使用这个大言不惭的词藻,而是要尽量地避开他。[10]同上,第280页.朗的论述虽然有理有据,但颇为遗憾的是,在我们该如何复兴古乐的问题上,朗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法,同时他还对现存的复兴者持批评意见,那么会使读者产生一些困惑,例如,我们该如何复兴才能做到既恪守学术上的要求,也响应艺术实践的需求?
朗的评述不仅建立在学术理论之上,还根据他的亲身经历谈其感悟。例如,在论及阉人歌手时,朗认为,除了极个别出色的阉人歌手外,其余的大多只是善于卖弄“喉咙”,并没有达到“歌手”的含义,他们就像是不会犯错的歌唱机器。朗以1912年观看两位阉人歌手表演的亲身经历证实这一论点:不再处于鼎盛时期的阉人歌手的嗓音冷酷平静、缺乏色彩。[1]保罗·亨利·朗.音乐学与音乐表演[M].马艳艳,译.孙国忠、孙红杰,校.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299-302.再者,朗之所以想写一部论述音乐表演实践的专著,也起因于他所观看的一场海顿早期四重奏表演。该表演的节目单详尽到附录了四重奏中每件乐器完整的发展史,但其表演因使用了所谓的古乐器而导致音乐过于拘束,声音单薄晦涩,由此,朗希望能寻求一种权宜之计——既恪守学术上的要求,也响应艺术实践的需求。[2]同上,第259-261页.
结 语
保罗·亨利·朗的这部“不愿掺杂别人意念”的“未竟之作”不仅反映出作者各不相同的著述领域,还很好地反映了他学术生涯的研究轨迹。在音乐学的学科理论方面,朗运用其深厚的理论功底以及跨学科的广泛学识,在捍卫学术原则的同时,也为学者、学生们提出了诸多宝贵的建议;在音乐历史学方面,朗有机地将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以非同寻常的切入点、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和极具活力的洞见,更加敏锐细致地为我们阐述了艺术家及其作品的本质;在音乐批评方面,朗用犀利的笔锋、幽默的语调和坦率的建言对当下他所认为不良的音乐现象发出警告;在音乐表演方面,朗根据其毕生的经历与经验,在全方位的理论知识构架之上,对“当下的”表演实践提出了批评性、沉思性与预见性的问题。从学科理论到史学研究,再升华至表演实践,彰显出一位理论家为实现音乐的最终目的而作出的巨大贡献。无论是音乐学学科理论与跨学科知识的结合,还是音乐史学与音乐表演的结合,作者总是能游刃有余,操控自如,从而达到“掌控全局”的高度。
从写作方式来看,作者并没有将文字写得“高深莫测”而难以理解,相反,他更偏向于“普通读者”,在运用各学科知识进行论述的同时,也不失简洁易懂、幽默风趣的语调。该文集不仅适合音乐学理论专业的学生仔细研读,还适用于音乐学表演家,甚至可作为音乐爱好者的进阶读物。可见,这部翻译引进的《音乐学与音乐表演》对我国当下的音乐学和音乐表演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
本文集中,保罗·亨利·朗以其音乐学家、音乐批评家的身份,站在囊括哲学、文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领域的角度,对音乐学、音乐史、音乐表演的深度文字表达,为我们展示了一位学术大家才思敏捷、修养全面,且能掌控全局的风范,值得我们深入学习,细细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