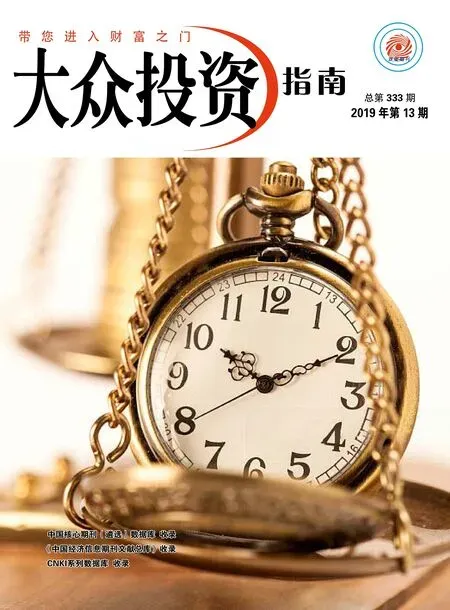我国北方民宿产业集群化的经济效应研究
——以北京市延庆区民宿集群为例
2019-11-29孙艳芳
孙艳芳
(北京市海淀区职工大学,北京 100083)
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我国出现了大量的民宿业态。伴随着我国旅游业的业态升级,我国游客消费水平的提高与消费需求的多样性,民宿行业受到游客的广泛青睐。民宿,作为一种新兴的非标准住宿产品,主要是指结合当地旅游发展的市场需求与地域文化特点进行自建、租赁改造或新开发的小规模旅游住宿功能产品,可以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体验住宿服务。旅游行业是民宿行业发展的基石,依托当今旅游业的飞速发展,我国民宿行业开始迈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从单体民宿到民宿的品牌化、连锁化以及当前的集群化,我国民宿产业一直在摸索中升级转型,民宿集群已成为民宿发展的趋势。
一、民宿集群化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根据国外相关文献,有关民宿产业集群研究成果,主要是针对美国的46个州和 403家B&B (bed and breakfaster) 民宿的经营状况与经济效益的研究,普遍得出结论,较大规模民宿比小规模民宿更容易获得较大的市场份额和较高的经济效益,所谓的“较大规模”主要是通过合作或者连锁加以运作[1]。这表明,民宿产业存在规模经济,如果单体民宿在一定空间上相对集中或通过合作、连锁方式进行跨区域整合,可以实现更高投资效益[2]。在国外产业集群的理论研究成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马歇尔(Marshall)的外部经济理论、韦伯(Weber)的工业区位经济理论、佩鲁(Perrour)的增长极理论、谬尔达尔的循环因果积累论、胡佛的产业聚集最佳规模论、巴顿的城市聚集经济论等。此后,产业集群理论逐步发展成为基于集群竞争优势与技术创新的新产业区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是斯科特(Socott)的新产业空间学派、巴格那斯科(Bagnasco)的新产业区理论和波特(Porter)的新竞争经济理论等。研究认为集群内的中小企业间更容易发展高效的协作与竞争关系,具有极强的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而形成专业化、柔性的生产协作网络,保持了地方、区域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一)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
最早研究产业集群现象的是英国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解释了专门工业集中于特定地方这一现象,即生产性质相类似的中小企业集中生产的“产业区”现象。他不仅发现了产业集群这一重要经济现象,而且研究了集群企业之间的客观协作行为、聚集经济表现形式,提出外部经济的概念,为集群研究奠定经济理论基础。其中,外部经济归类为三个方面:第一,企业聚集有利于形成知识信息的溢出和创新的环境;第二,企业聚集有利于非贸易投入品和服务行业的发展,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聚集可以为生产中间投入品的企业提供规模效应;第三,企业聚集有利于形成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市场,节约雇主与劳动力之间的搜寻成本。
(二)韦伯的工业区位经济理论
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提出了工业区位经济理论。韦伯在《工业区位论》(1909)一书中,把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影响工业分布的“区域性因素”,另一类是引起工业再分布的“集聚因素”。其中集聚作用可分为两个阶段:初级集聚阶段,即企业经营规模本身的扩大;高级集聚阶段,即多种企业在空间上集中的阶段,互相带来更多的收益或节省更多的成本,也就是所谓的产业集群。韦伯认为,集聚因素是一种“优势”,在一定集中化程度下,成本因工业的集中而大大降低,并具体分析了集聚的优势。韦伯的工业区位经济理论对以后的区位理论、经济地理理论、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巴格那斯科的新产业区理论
80年代初,意大利学者巴格那斯科(Bagnasco)等在意大利东北部发现了类似于马歇尔式工业区的新兴工业区。后来,巴卡提尼( Bacattini)、皮埃尔(Piore)、赛伯(Sable)等人进一步研究认为,“新产业区是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社会地域生产综合体”,其经济特点是:第一,生产体制与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集群“弹性专精”的生产方式使中小企业发挥其优势;第二,强调专业化分工和本地合作的作用、本地网络对本地社会制度文化的根植性;第三,集群具有特殊的创新和技术学习的方式。[3]
(四)Carbonara的集群学习机制理论
Carbonara(2004)在《技术创新》杂志上发表题为 “集群的创新过程:一个认知的角度”的文章中讨论了三种不同类型集群的学习机制:小企业聚集的学习机制是“干中学”和“当地化学习”;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类集群还有“用中学”“专业化学习”“集体学习”三种机制;轴心企业、集群协会与高度专业化类集群除了以上两种类型的学习机制外,还有“以研发为基础的学习”和“互动学习”两种机制。三类集群的认知特征虽有区别,但知识易于分享和信息传递快速是共同的特征。一般认为,集群企业人员的非正式交往是知识信息传播的途径,知识溢出在集群创新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五)迈克尔.波特的新竞争经济理论
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是目前最有影响的产业集群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集群的成长需要四大因素之间的密切配合,这四大因素是需求条件、关联与支持性产业、因子条件及企业竞争与战略。地理上的集中使这四种相互分离的因素相互作用,这四个因素会由于地理的相近而相互增强,地理集中促进技术的创新与升级,邻近的竞争者会促进模仿行为,靠近竞争企业群的大学更可能与企业相互支持,供应商会因靠近研究与开发活动而创新,附近有经验的购买者最可能交换信息,及时反映对新产品和新技术的需求,尤其是对特别服务和产品特殊功能的需求。迈克尔·波特指出:“它作为某个地方、特定领域内获得不同寻常的竞争胜利的重要集合,其因素支配着当今的世界经济地图,而且事实上它已成为每个国家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州内经济,甚至都市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尤其如此”。[4]
基于中国知网的数据库,国内对“民宿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宿产业群的实证研究(如深圳大鹏新区、浙江民宿产业集群)、民宿集群的空间发展、供应链视角下民宿集群的品牌塑造研究、发展趋势研究、发展模式研究等。朱明芬在产业集群理论的基础上,以浙江省 4 个民宿集群为例深入分析民宿集群产生的集群效益。并得出结论,区位优势决定民宿集群的规模与档次,资源禀赋是民宿集群的核心要素,人文特色决定民宿集群吸引力,政策引领优化民宿发展环境。赵雅萍从空间区位的角度出发,以浙江省湖州市为研究案例地,探究其民宿的空间集聚现象及影响因素分析。汪婵娟从民宿集群发展前提、产业模式、管理模式三个方面阐述了适合安徽黟县古村落民宿发展的模式。熊国铭在供应链视角下研究民宿集群的发展状况,并进一步分析民宿集群内部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合理有效的解决措施。陈佳洁,陈静,林佳玲探究浙江省乡村旅游目的地影响品牌构建的因素以及民宿集群对于构建品牌的作用与影响。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非常重视民宿产业集群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国外学者更注重产业集群的深层理论研究,我国学者借鉴国外产业集群理论并试图对我国民宿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竞争优势、发展实践,从动态演化的角度进行实证分析。但是,仍存在一定局限,例如研究领域中较少研究我国北方民宿的单体特征、区域特征与民宿集群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北方民宿集群的集群理论适用性与经济效用。
二、北京市延庆区概况
根据交通、气候、生态环境和自然与人文景观等因素,结合目前中国民宿客栈发展的实际状况 ,大致可以划分为十大区域民宿发展集群:京津冀民宿区、珠三角民宿区、长三角江沪浙民宿区、浙南闽北山地民宿区、滇西北民宿区、浙闽粤海岸民宿区、湘黔桂民宿区、川藏线民宿区、徽文化民宿区、客家文化民宿区,从区域分布来看,除了西部的川藏线民宿区和北部的京津冀民宿区两个集群外,其他八个均位于长江以南的南方地区。其中,我国北部的京津冀民宿区以北京市延庆区民宿产业为发展核心。
延庆位于北京市西北部,属于北京市郊区。东邻北京市怀柔区,西与河北省怀来县接壤,南接北京昌平区,北邻河北省赤城县。气候冬暖夏凉,素有北京“夏都”之称,延庆地域总面积1993.75平方公里,其中,山区面积占72.8%,平原面积占26.2%,水域面积占1%。辖11镇4乡,常住人口28.6万。延庆是首都北京的绿色屏障和后花园,湿地面积近100平方公里,对外开放的景区景点多达30余处,其中A级以上景区16家,包括八达岭古长城、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百里山水画廊、松山国家森林公园、龙庆峡、水关长城、康西草原、玉渡山等景区景点。
三、北京市延庆区民宿产业集群化的效应分析
(一)产业集群化的集聚效应
集群从本质上说是各种网络关系在空间上的集聚(Saxenian, 1991;Camagni 和 Capello ,1998;Porter,1998;盖文启 ,2002)。集群之所以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竞争力 ,其根源在于集群所引致的规模经济(集聚经济)和制度化要素的空间密集性。通过“集群化”或“网络化”成长[5]。产业集群化是产业呈现区域集聚发展的态势,是指在一个适当大的区域范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若干个同类企业、为这些企业配套的上下游企业以及相关的服务业,高密度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产业集群[6]。
根据传统的区位理论研究,主要是针对可见的物质生产资料的区位理论,而在民宿产业区域结构分析中有更重要的集聚效应特殊性,首先,民宿业的生产具有不可转移性(Unchangeability of Tourism Production),民宿业以当地的旅游资源为依托,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文旅游资源通常都是不可移动的,顾客只能到旅游资源所在地进行消费,因此,区位是体现民宿特色与服务不可分离的部分,影响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其次,民宿的需求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例如不同的顾客对于相同的旅游资源和相同的民宿产品很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吸引力与消费效用,由于顾客的生活背景、文化背景、职业因素、兴趣爱好、性格特征、审美观、价值观等主观因素不同,顾客周围的行业文化、朋友圈、经济状况、流行时尚等客观因素也会影响民宿的效用及顾客的选择。因此,不同层次、不同特色民宿的集聚更有助于增强集聚区域的顾客需求,产品的异质性在降低彼此之间竞争激烈程度的同时带来了市场总体需求的增加。
Marshall 指出集群可以通过降低顾客的搜寻成本 ,增加市场需求为集群内的企业创造利益。对于住宿业的非标准化产品民宿业来说,尤为明显。因为顾客在追求个性化特色文化的同时就要付出搜寻成本,而地理位置的邻近可以使顾客有更多可以选择的竞争性同类服务,可以更加容易方便即时地评估大量同类产品,而这一点也能激励集聚的民宿群增加产品的异质性,错位竞争以满足与提升顾客的需求。
北京市延庆区根据乡村旅游观光、度假、生活并存的多元化市场需求,设计了精品民宿、中端客栈、基础农家乐三个层次的供给结构,形成了层次鲜明的错位竞争产品与规模经济,既增加了区域的顾客需求,也拓宽了聚集区域的整体市场需求边界。延庆区的精品民宿提供高端化、特色化服务,乡村客栈提供标准化、规范化服务,农家乐提供乡村农宿当地的住民生活体验。同时,延庆精品民宿根据要素禀赋的不同,整合知名民宿品牌,开发了“长城文化”民宿集群、“缤纷世园”民宿集群、“激情冰雪”民宿集群、“山水休闲”民宿集群等4个特色精品民宿集聚区,这些不同特色的民宿集群,既增加了产品的高度异质性,也提高了区域民宿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北京市延庆区民宿集群无论从供给结构体系,还是从精品民宿的差异化产品特性上,顾客在北京市延庆区区域内都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不同的民宿产品,大大降低顾客的产品搜寻成本。民宿集群内的产品实现了多样化与互补,从而可以进行错位竞争,互相补充客源,扩大市场范围。
(二)获取资源的外部性效应
1、共享区位公共服务优势,获取公共资源的外部经济
当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经济主体的福利产生影响,而从货币关系上或市场交易中并没有把这种影响反映出来,即一项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大于私人效益时,就存在外部经济性。民宿集群内的企业可以获得集群内区位的公共服务与公共资源的外部经济,这是集群外企业所不能获得的资源,也就是公共资源的获取优势。
例如北京市延庆区改善下湾村、大石窑村等13个星级民俗村的旅游服务配套设施,建设改造13座旅游公厕、9个旅游咨询站,建设统一规划旅游标识体系,实施建设百里画廊滨水步道,推出井庄镇、旧县镇等8个特色小镇,以及北菜园、妫州牡丹园等13个现代园艺产业集聚区。北京市延庆区充分改善民宿集群的旅游基础服务配套设施,提升旅游的综合公共服务保障能力,集群内的民宿企业充分共享了区位的公共服务优势,获得了公共资源的外部经济,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的民宿企业选择在延庆区创建。
2、营造制度化要素的空间密集性
作为组织形态,企业集群处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制度环境可以分为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包括合约、产权、标准、组织文化等,宏观层面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等。企业集群的形成可以统一市场、规范行业标准、推动专业分工技术、互相协作,建立网络信任关系、共同的诚信合作的组织文化,减少签订合约与履行交易的成本费用。另外,政府可以重视并制订特定的企业集群的产业政策、有利的集群产业制度来促进集群、区域的整体发展,营造制度化要素的空间密集性。
延庆区民宿集群企业与政府共同合作营造了制度化要素的空间密集性。2018年北京市延庆区组建了包含旅游委、农委、公安等23个部门的民宿联席会议制度,制订并整合民宿集群相关的政策与制度,形成区域空间协同管理、民宿集群产业体制机制统一的重要制度要素禀赋比较优势。
3、获取重要产业要素的供给优势、区位服务优势、专项资源优势
民宿集群内企业通过组织联盟的关系、政府扶持可以获取重要产业要素的供给、区位服务、 专项服务资源或者专项关系资源方面的优势。Baum &Oliver(1992)指出这些类型的关系不仅仅会使集群内企业受益 ,同样会使整个集群所从事的行业的所有企业受益 。
延庆区民宿集群内的企业通过民宿联盟与延庆区共同充分利用当地农民的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资源,农民可以通过租赁房屋的形式盘活资产获取租金,通过民宿管家、运营维护等形式获取劳动力工资,通过众筹装修的形式获取入股红利,等等。集群内企业能够直接接触到延庆区当地的重要供给资源,具有产业要素供给优势。
同时,延庆区民宿集群还具有区位服务优势。延庆区当地政府进行农村闲置资产调查,建立了全区闲置农宅数据库,为集群企业对接区内资源提供重要数据服务。延庆区还在北京市率先出台精品民宿专项奖励政策,对民宿集群形成良好的竞争激励服务,也进一步使区内民宿集群与当地的本地化经济深度融合。
延庆区为民宿集群企业提供金融专项资源,使集群内企业具有专项资源优势。延庆区与北京市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和北京银行合作,为延庆区乡村民宿搭建融资担保平台,为农家乐的升级改造以及精品民宿投融资提供了资金支持。
(三)柔性专精与分工深化效应
集群的产品优势还体现在柔性专精与分工深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效应 。具体到民宿业而言,就是产业集群内不同企业通过分享公共资源与专业技术劳动力资源 , 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 ,促进了民宿之间的异质性分工和产品灵活性,不同类型的民宿可以提供不同类型的产品和服务 ,充分地满足不同顾客的需求 。
民宿业具有综合性强和强关联性,所以在区位布局时不仅要考虑民宿业本身的行业特征,还要从当地区域整体的布局与发展角度全面考虑,民宿产品的具体内容除了传统的旅游内容“食、住、行、游、购、娱”外,还需要考虑当地区域的景点、交通、环境、园林、体育、科技、文化等相关部门的整体促进与融合。
首先,延庆区民宿集群可以集聚在一起深化分工,延展民宿产业链并互相深入合作产生化学反应,例如衍生出后向的民宿地产开发、休闲创意农业,以及前向延展的康养民宿、文旅民宿、养老民宿、度假民宿、会议民宿、长租短租式民宿,集群内不同类型的民宿提供不同类型的差异性产品与服务,增加产业链价值,从而提高延庆区的区位核心竞争力。
其次,民宿集群的各企业产品可以做到柔性专精,既可以有各自的特色产品,也可以互相学习、互通有无,进行柔性化的迅速市场反应,及时增加或改变企业的特色产品与服务。根据客房定位的不同,各民宿小院的特色餐饮不同、住宿建筑风格不同,体验性消费项目不同。
而且,延庆区民宿集群深化分工,整体提升智能化水平。延庆民宿联盟和腾讯公司就平台共建、网络用户触达、智慧住宿体验升级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使民宿集群内企业共享智能化产品优势。房东通过APP就可以远程开启空调和空气净化器,通过人脸识别功能的使用,使房客实现刷脸入住联网登记、刷脸就餐、刷脸消费、危机预警等等。
(四)学习和创新的内在机制效应
在民宿集群内部, 民宿通过自身各种网络关系中, 实现缄默知识的低成本转移(Harrison, 1991 ;Cooke et al .,1997);通过建立网络间信任(Lundvall , 1992;Maillat et al ., 1993)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通过面对面交流(Dicken et al .,1994;Saxenian,1994)来获取外部信息,为企业创新和提高市场竞争力创造必要的条件。民宿集群在柔性专精、深化分工中竞争合作,容易形成持续的学习和创新内在机制,共享区域发展的经济效应,共担区域竞争的风险。
延庆民宿集群内的企业以地缘关系、民宿联盟组织关系集聚在一起,可以通过近距离观察、人才流动、定期面对面交流、合作伙伴、各村落亲人朋友交流建立信任关系,实现作为缄默知识的低成本转移交流渠道,获取信息,激励创新,提高区位竞争力。
延庆区成立的北方民宿学院为民宿集群搭建正式面对面学习知识、行业交流、传播区位民宿品牌、统一规范的学习创新核心平台,民宿学院的课程既有民宿选址、建设规划、装修设计、市场定位、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技术指导课程,也有民宿管家制、民宿与乡村产业转型、民宿服务等实战的特色课程。聘请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的建筑、旅游等专业教授和来自民宿、乡创的全国领军企业经营管理者传授课程。同时,北方民宿学院还不定期召开主题论坛、问题交流、学术研讨等。为延庆区民宿群的产业发展,以及北方区域、全国范围的乡村民宿人才累积与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创新核心基地。
(五)区位品牌效应
首先, 民宿集群有利于形成区域品牌。一方面, 大量相互关联的民宿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协作而结成本地化网络, 克服了单体民宿参与市场交易的分散性和不确定性风险。延庆区民宿集群通过精品民宿、中端客栈、基础农家乐三个层次专业化分工合作,为不同的客户层提供不同的专业化服务,建立延庆区民宿联盟和乡村客栈联盟,克服了民宿“单打独斗”的客户不确定性与经营分散性风险,加强行业自律、提高标准化、规范化经营程度。
其次,民宿集群可以培养民宿企业对集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增加对新加入民宿的吸引力。民宿集群是一种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 ,产业地域空间的集中性就使得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即使是各个民宿企业互相独立地进入市场, 但是顾客对这一地域民宿的产品和服务都会有一个整体性的特定的地域性认识, 这种独一无二的地域特性会增加对新进入民宿的吸引力 。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会相伴形成区域品牌 ,区域品牌的形成是集群发展的一种结果。反过来 ,区域品牌形成之后 ,对集群的可持续发展会产生一种互动效应。集群的发展除了所在区域本身的区位条件 、自然条件等因素外, 区位的服务品牌是形成区位整体吸引力的要素之一[7]。
(六)区域协同效应
集群的区域协同发展的重点是对“协同”的理解,协,字义上是“和”“合”“帮助”“和谐”“协调”的意思。同,则有“同步”“会同”的意思,而非“相同”。通常,区域协同包含两层含义——协作与同步。因此,区域协同问题大体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一个或多个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为追求更多利益而需要与辖区之外的其他地区进行协作的问题;二是一个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与辖区之外的其他地区保持同步、和谐和局面,并非完全相同,而是不能发生矛盾和冲突[8]。
城市间很容易展开资源的恶性竞争,尤其是相邻的城市,导致产业结构的趋同与资源的浪费,这就需要各城市或地区间进行产业协同、分工合作,在产业政策上互相进行衔接合作,从而提高整体区域的产业竞争力。只有共同制定公平公正、透明具体、共同遵守的市场规则,才能界定和约束各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选择,才能保证良好的市场竞争运行环境。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权威的区域协同机构出台共同准则来指导和约束各地方政府的地方行为标准和准则[8]。
由延庆民宿联盟和客栈联盟倡议联合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山区等6区,以及天津市津南区,河北省张家口市、承德市、秦皇岛市以及内蒙古兴和县等市区县旅游行业协会以及企业代表,共44家民宿品牌地方协会共同发起成立“北方民宿联盟”,实现京津冀内蒙资源共享、机遇共赢、分工合作、协同发展。在联盟内实行“资源共享、机遇共赢、协同发展”,致力于实现京津冀内蒙区域民宿行业产业链的分工协作与一体化建设,以“国际化”的高标准打造北方民宿的共同行业标准,同时在市场客源、旅游资源推广、行业大数据、民宿管家培训、民宿品牌塑造、经营管理、平台资源共享等方面进行协同合作,提高北方区域民宿产业的整体实力,共同建设跨地方的区域协同的公平公正的良好市场运行环境。
四、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北京市延庆区民宿集群作为我国北方民宿的典型代表,通过错位竞争提升顾客需求,扩大了市场总需求边界,实现了产业集群化的集聚效应;通过共享区位公共服务优势、重要产业要素的供给优势、专项资源优势,营造制度化要素的空间密集性实现了集群的外部经济效应;同时该集群还实现了柔性专精与分工深化效应、学习和创新的内在机制效应、集群式的运营管理效应、区位品牌效应、区域协同效应,因此,北京市延庆区民宿集群通过旅游升级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农村资源,增加了当地农民、低收入农户的收入,提升了延庆区的旅游综合服务能力,同时拉动了京津冀内蒙区域的乡村新型服务业协同发展,成功打造了北方民宿的品牌特色与行业标准。
我国的民宿业经历了从模仿者到创新者,再到目前探索中国式地方特色创新的过程,迎来了全面开启自主品牌发展的新时期,民宿集群不但需要建立品牌文化、民族文化,还需要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加强民宿业的研发设计、标准规范、营销网络等各个方面,不断提升民宿业产业链上产品和服务的增加值和产业融合,同时推动我国民宿业向国际分工的更高价值链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