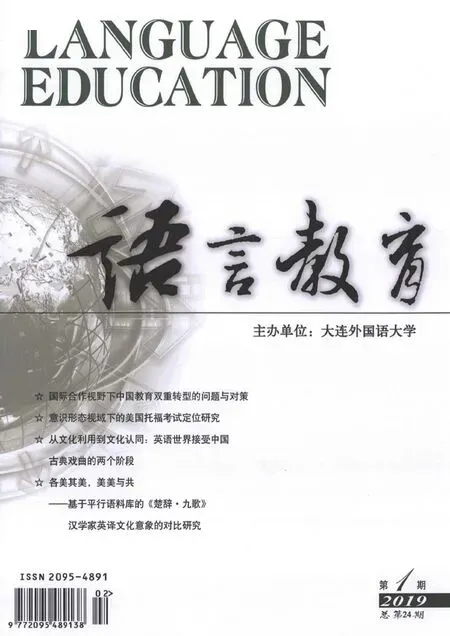卡莱尔的社会批评思想对《荒凉山庄》的影响
——卡莱尔和狄更斯结构批评研究
2019-11-27王威
王 威
(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大连)
1. 引言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之中,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和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构成极为典型的师徒关系。在他们于1840年首次相见之际(Christian,1947a:28),卡莱尔已颇赋名望,向“切尔西的圣贤”(Tennyson,1984:xiii)稳步靠近,而狄更斯已经开始他的文学生涯,因《匹克威克外传》[《匹》](Pickwick,1837)、《雾都孤儿》[《雾》](Oliver Twist,1838)和《尼古拉斯·尼克贝》[《尼》](Nicholas Nickleby,1839)等作品而声名鹊起。狄更斯“对卡莱尔的敬佩与年俱增”,“在人生的后半期最钦佩、最瞩目他”(Forster,1876: I,236),希望他成为《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1943)的首位读者(Forster,1876:II,137)。《艰难时世》[艰](Hard Times,1854),这部“最具‘卡莱尔特色的’小说”(Storey,1987:11),被题献给他。“我想在首页写下,本书题献给托马斯·卡莱尔”(Dickens,2012:278-279)。虽然这一行为有“职业发展”的考虑,但是“强烈的个人感激之情”鲜明可见(Kaplan,1988:91)。在“爱德华·爱(Edward Eyre)事件”的争论中,他拥护卡莱尔的立场,并成为“辩护委员会”的一员(Kaplan,1988:481)。卡莱尔在初次见面时即对这位后辈怀有好感(Kaplan,1983:260-261)。虽然他对虚构类文学作品持怀疑和批评立场,但是《双城记》[《双》](A Tale of Two Cities,1859)仍被认为是一部“杰作”(Carlyle, 1904:II,205)。对于狄更斯的去世(9th Jun. 1870),他表示深切的哀悼,认为意味着“所有民族快乐”的“消失”(Shepherd,1881:II,292)。
在社会观点方面,狄更斯受卡莱尔的影响最为深刻。卡莱尔可谓“狄更斯最大的思想影响”(Storey,1987:2)。这一影响开始于30年代,在40年代变得明显(Oddie,1972:5)。在社会改革问题上,狄更斯仅接受过边沁(Jeremy Bentham)和卡莱尔二人的观点(Engel,1959:172)。他初期相信“功利主义的普遍原则”,认为“社会改革可通过制度改革实现”(Goldberg,1972:62),后接受卡莱尔的批判态度,将功利主义看作“算计的、决定论的、机械论的”(Storey,1987:2),无法实现社会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功利主义“将所有的关系归结为个人利益”、“自由主义”作为唯一的经济运营模式以及将“工资体系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之上并仅由市场控制”等做法,甚为诟病(ibid)。放弃功利主义原则,堪称狄更斯思想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此后,他在议会改革、权力重组、教育、卫生和移民等方面全面接受卡莱尔的相关主张(Goldberg,1972:64-69)。
在狄更斯以社会批评为主题的小说之中,卡莱尔的影响清晰可见。“狄更斯对卡莱尔社会理论的依赖”甚至贯穿“从《雾》到《德鲁德疑案》(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1870)”(Tarr,1971:275)的全部写作过程。《匹》、《雾》和《尼》等早期作品虽然创作于他们相见之前,但是卡莱尔在《伏尔泰》(Voltaire,1829)、《时代的标记》(Signs of the Times,1829)、《特征》(Characteristics,1831)、《旧衣新裁》(Sartor Resartus,1833-1834,1838)和《法国大革命史》[《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1837)等作品中的社会理念在其中有明显的体现(Christian,1947b:11)。《艰》虽然在“结构”上未见“卡莱尔的影响”,不过对理性主义的批判这一主题来源于“这位时代最重要的反理性主义者”(Oddie,1972:42,41)。《双》与《革命》在主题上极为相似。“在制度与人文目的不相符合的时代对个人能力社会化方式的探寻”(Marcus,1976:56),贯穿两部风格迥异的作品。包括《荒凉山庄》[《荒》](Bleak House,1853)和《小杜丽》(Little Dorrit,1857)在内,卡莱尔社会观点的影响体现在所有这些晚期小说作品之中(Christian,1947b:17)。与卡莱尔一样,“社会批评”同样构成狄更斯晚期作品最为主要的主题之一(Johnson,1977:342)。
《荒》是狄更斯晚期作品中最为重要的一部。相关创作构想产生于1851年(Forster,1876:II,118)。同年的通信中(to Mary Boyle,21stFeb.)提到,“一个全新故事的某些影子已经以诡异的方式萦绕于我周围”(Dickens,2012:227)。此后,狄更斯在致友人信件中多次提到创作过程(Dickens,1977:885-889;2012:248,259)。《荒》于1852年3月至1853年9月连载(Dickens,1977:885-886),1853年以书的形式出版。虽然狄更斯本人持保守态度,认为与《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1850)相比,《荒》在人物塑造上远远不及(Forster,1876:II,127-128),而且时论亦多贬低、诟病和指责之词(Collins,1986:275,281,283-284,287-289,297-298,298-299),但是无论在主题设计还是在谋篇布局,无论在人物塑造还是在叙事多样化等方面,《荒》均具有极强的解释潜力,甚至堪称狄更斯最为优秀的小说作品(Storey,1987:17)。
在主题上,《荒》明显地体现了卡莱尔的影响。创作期间,狄更斯反复阅读《革命》,甚至“无论走到哪里都怀揣一册”(Froude,1884:I,80)。“这部神奇的作品”,他“再次阅读一遍,这已经是第500次了”(Forster,1876:II,72)。虽然这样的说法有夸张之嫌,但是他对《革命》的推崇毋庸置疑。《革命》强烈地影响了《荒》的主题。与《革命》一样,《荒》“描述了社会制度从旧向新”这一“社会和经济权利结构的转变”(Arac,1977:59)。此外,对“海外人道主义计划无情的讽刺”(Christian,1947b:17),是《荒》中另外一个明显的卡莱尔式的主题。其程度堪与“卡莱尔在《黑人问题》(“The Nigger Question”,1949)中对约翰·罗素勋爵援助西印度群岛黑人计划的抗议”媲美(Christian,1947b:18)。《荒》中“对杰利比夫人(Mrs.Jellyby)和帕迪戈尔夫人(Mrs. Pardiggle)的具有讽刺性的描写”,是“最鲜明影响”的体现(Tarr,1971:276)。最后,对“无为主义”(dilettantism)的批评,是另外一个借鉴主题(Christian,1947b:18)。狄更斯对戴德洛克爵士和夫人(Sir& Mrs. Dedlock)的批评(ibid.),与卡莱尔对“贵族沦落为享乐派”所持的观点极为相似(Goldberg,1972:65)。总体而言,《荒》是狄更斯紧承卡莱尔“控诉英格兰今夕现状的苦难”这一主题,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具有启示性的回应”(Mackenzie,1979:248)。
在《荒》中,卡莱尔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批评主题上,更表现在批评结构之上。卡莱尔的社会批评除主题批评(thematic criticism)之外,还有结构批评(structural criticism)这一层次。结构批评建立在卡莱尔的社会结构构想之上。社会在结构上被分为本质(essence)和表现(appearance)两方面内容。社会本质决定社会表象,而社会表象对社会本质进行表现。社会表象对社会本质的表现程度,决定一个社会的运行状况。社会批评主要以社会表象与社会本质之间出现的裂隙与分歧为对象,以实现两者的弥合和对接为目的。总体而言,结构批评是主题批评的基础和前提,主题批评是结构批评在某一方面的具体体现。卡莱尔式的结构批评被狄更斯借鉴,表现在《荒》的社会批评之中。
本文以卡莱尔和狄更斯的结构批评为研究对象,分两部分。其一研究卡莱尔式的结构批评,其一研究《荒》中的结构批评。
2. 卡莱尔的结构批评
卡莱尔式的结构批评,以他的社会结构构想为基础。他对社会结构的理解,具有极强的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特征。社会被类比为人的身体,是一个机体性的(organic)结构。如果“政府”构成“外在的皮肤”,“工艺协会”以及“联盟”等机构是“肌肉和骨骼组织”,那么“宗教”则是“最内在的心包和神经组织”(Carlyle,1937:216)。在此,社会被分为内外两方面。与人的身体一样,社会的内外构成具有不同的作用。“若没有[心包和神经组织]”,“(工业的)骨骼和肌肉就无法活动,只有通过电流的刺激才表现出生气;皮肤就会变成枯萎的皮毛,或是快速腐烂的生皮”(ibid.)。可见,社会的内在构成起主导作用,外在构成仅起辅助作用。
社会内外构成作用的不同,决定两者地位的不同。具有主导作用的内在构成,被认为是社会的本质。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宗教对于社会的生成(generation)所具有的作用之上。“只有通过宗教,社会才变得可能”(Carlyle,1937:215)。“只有通过仰望天堂,……我们所谓的……社会等才可以实现”(Carlyle,1937:214)。非常明显,宗教是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的根源所在。在决定社会的生成这一意义上,社会内在构成是社会的本质。与此相对,社会外在构成因不具有主导作用,故不对社会的生成产生影响。包括所有社会机构在内的外在构成,作为社会的表象而存在。
社会的外在表象和内在本质处于表现和被表现的关系之中。这一表现与被表现关系在《特征》中有详细的论述。在社会“无意识状态”(Unconsciousness)的论说中,卡莱尔指出:
任何社会、任何政体都有一个精神原则;是一个理念具有尝试性的,或者多少完备的表现:其所有的行动取向、风俗特征、法律、政治以及程序……均由这一理念决定,从中自然发展而来,就像运动从动力源产生出来一样。(Carlyle,1899b:13-14)
社会在外表现为“行动取向、风俗特征、法律、政治以及程序”等,在内则表现为“精神原则”。前者是后者的“表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类比为“运动”和“动力源”之间的关系。非常明显,这是社会的外在表象和内在本质之间的表现和被表现关系。
社会的外在表象和内在本质之间表现和被表现的关系,对于理解卡莱尔的结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这种关系决定了现实(actual)社会的理想状态。当外在表象完全表现内在本质时,即当外在表象与内在本质一致时,现实社会处于理想状态。对于社会理想状态的界定,卡莱尔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如上所述,宗教被看作社会的内在本质。现实社会的理想状态是与宗教相一致。在此意义上,“任何可以想象的社会……可以看作一座教堂”(Carlyle,1937:215)。至演说集《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1841)出版,宗教被理解为“英雄崇拜”。“信仰是对某个有灵感的导师,对某个高尚的英雄表示的忠诚”(Carlyle,1966:12)。据此,现实社会的理想状态是与英雄崇拜相一致。“任何地方的社会都是英雄崇拜……有等级的表现”(Carlyle,1966:14)。这一认识上的变化并无前后矛盾。宗教和英雄崇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英雄崇拜]是宗教的基础,不仅异教如此,而且……一切宗教,都是如此”(Carlyle,1966:11)。可见,英雄崇拜是宗教的深化。总体而言,现实社会的理想状态是与宗教相一致,作为宗教的完全表现而存在。
另外,这种关系决定了现实社会可能状态的范围。如果理想状态是现实社会可能状态的上限,那么下限则是外在表象与内在本质完全不一致的状态。若以“危机状态”称之,则现实社会的可能状态处于从理想状态到危机状态的范围之间,即
现实社会=[理想状态, 危机状态]
然而,卡莱尔并不认为现实社会可以处于理想状态。“不完美的人类社会”只能是“完美的某些接近”而已(Carlyle,1965:26)。相对于理想状态,现实社会只能接近(approximation),而无法实现(realization)。这样,理想状态对于现实社会而言永远是封闭的。理想状态不在现实社会可能状态的范围之内,即
现实社会=(理想状态, 危机状态]
现实社会永远不能与宗教或者英雄崇拜相一致,而只能处于无限接近两者的过程之中。这是一个现实社会无限接近理想状态的张力性社会发展模式。
现实社会对于理想状态的接近程度(degree of approximation),是卡莱尔社会批评的对象。现实社会对于理想状态的接近,有程度上的区别。概而言之,接近可分为两类:其一为“可忍受”(supportable),其一为“不可忍受”(ibid.)。接近程度与可容忍程度成正比,即
接近程度∝可容忍程度
接近程度高,则可容忍程度高。反之亦然。社会的存亡取决于可容忍的程度。“人面对可忍受的接近可以保持耐心”,但是如若发展到“不可忍受的阶段”,则“国家本身在走向自杀性的死亡”(ibid.)。在可容忍的范围内,社会可以保全。超越可忍受而进入不可忍受的范围,则社会瓦解。在不可忍受的范围内,大规模的社会危机爆发。“曼切斯特起义、法国大革命以及成千上万的大小现象,急声宣告有必要提升[外在表象的接近程度]”(Carlyle,1965:27)。可见,在卡莱尔对社会危机现象观察和批评的背后,存在着他对社会理想状况的企望。
卡莱尔结构批评的主要内容在以上分析中表现出来。总体而言,结构批评以社会的理想状况为依据(i),对现实社会的实际状况进行考察(ii),主要对现实社会接近程度低于可忍受范围的危机情况进行批评和否定(iii),以实现接近程度的不断提升为最终目的(iv)。非常明显,与通常的平面式的社会批评模式相比,卡莱尔的结构批评不仅对社会的现实情况进行考察(ii)以及对危机状况进行否定和批评(iii),其中还有社会理想状态的探讨(i)和社会发展终极目的的实现(iv)等维度的存在。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以理想(ideality)为依据、对现实(actuality)进行考察的张力性批评结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性(tensionality),是卡莱尔结构批评的主要特征。
卡莱尔的结构批评并非仅仅停留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性结构之上,而是进一步以实在性(reality)对两者进行理解。理想被认为是实在的(real),而现实则是非实在的(unreal)。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他对英国社会结构的认识之上。在结构上,英国社会可分为“事实(fact)的内在范围”和“外表(semblance)的外在范围”两部分(Carlyle,1965:18)。所谓的事实是“英雄崇拜”,而所谓的“外表”是“自由主义”、“供求关系”和“金钱关系”等(Carlyle,1965:38)。非常明显,所谓的“事实”对应于“理想”,而所谓的“外表”对应于“现实”。两者在实在性上的表现颇为不同。只有事实才是实在的,只有以事实为依据所谓的“正义”(justice)才可以实现(Carlyle,1965:19)。最终,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性结构被转化为实在(reality)和非实在(unreality)之间的结构。卡莱尔的结构批评是以理想的和实在的(the ideal-real)为依据,对现实的和非实在的(the actual-unreal)进行否定和批评。
理想-实在与现实-非实在之间的张力性批评结构,表现在卡莱尔社会批评的所有方面。在对时代特征的整体判断中,“机械时代”被置于与“英雄的、虔诚的、哲学的或者道德的时代”之间的对比之中(Carlyle,1899a:59)。对“机械时代”的批评最终发展为对“一个崭新的、更加明亮的精神性时代”到来的预言(Carlyle,1899a:81)。同样,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盈亏哲学”与“信仰”构成对比(Carlyle,1937:159)。对功利主义作为社会规范方式的否定,是对“一个可以洞见事物内在的真正英雄”的呼唤(Welch,2006:385)。在对机械论(mechanism)的批评中,“[卡莱尔]社会批评的主要魅力之一便是他看到‘机械’的内在和外在意义、理解科技变化和情感效果”(Sussman,1968:35)。可见,结构批评普遍存在于卡莱尔的社会批评之中。
3.《荒》中的结构批评
《荒》中的社会批评主要针对大法官庭制度(Chancery)所造成的弊病(Ford,1955:104)。作品开宗明义,以伦敦一场漫无边际的大雾象征诉讼制度的腐朽和黑暗。“腐败的大法官庭本身和它的陈旧而繁琐的条文与程序”(狄更斯,1998:序,1),在批判中暴露无遗。特别是“运用象征、比喻手法对生活进行宏观的把握”的写作方式,“显示了狄更斯的小说艺术又有了重要的发展”(薛鸿时,1996:167)。除大法官庭制度外,人道主义的滥用以及贵族制度的没落等同样构成比较重要的批评对象。
如果以上内容是《荒》结构批评中的现实维度,那么理想维度则表现在女主人公埃丝特(Esther Summerson)对现实社会的观察、感受和体验之上。埃丝特怀有的仁爱(sympathy)思想,是理想维度的主要内容。所谓的仁爱,是与他人怀有相同的(sym-)情感(-pathy)之意。同感的实现是家庭建立的基本条件。初次见面之时,埃丝特便与同样是孤儿的婀达(Ada Clare)和理查德(Richard Carstone)建立起兄妹之情(Dickens,1977:30)。同感进一步将贾迪思先生(John Jarndyce)纳入他们的情感世界。他好像“慈父”一般(Dickens,1977:60),与本来应该在法庭上相见的对手组建起一个与家庭非常相似的情感共同体。同感对于社会关系同样具有维系作用。埃丝特通过同感成为凯蒂(Caroline Jellyby)的知己(Dickens,1977:43-44)。贫民窟之中的女子“由于遭受这种悲惨命运而相爱相怜”,“相依为命”(Dickens,1977:101)。相反,若无同感,即使是家庭也只能有名无实。戴德洛克夫人终日一副冷面,对所有的一切都毫无情趣,“厌烦得要死了”(Dickens,1977:11)。可见,《荒》结构批评中的理想是一个以同感为基础、与家庭结构类似的社会共同体。
同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情感效果,而是具有一个明显的发展和深化过程。移情(empathy)是前提。移情即进入(em-)他人情感(-pathy)世界之意。从自我情感范围超越出来并进入异己的情感世界的愿望,是幼年时期埃丝特的本能。这个“非常胆怯”,“不大敢跟人说话,也从来不敢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的“小姑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情感天地,“喜欢默默地观察眼前的事物,希望更深刻地了解这些事物”(Dickens,1977:17)。这种了解非我对象的愿望,便是移情的主要表现。埃丝特对移情始终怀有强烈的需求。她自以为“没有经验,对于那些生活在不同环境里的人,[她]不善于设身处地地去想他们所想的事情,也不善于从适当的观点出发去和他们交谈”(Dickens,1977:96)。然而,正是这种类似于苏格拉底式的无知之知的意识,让她始终可以实现移情。
移情是同感的前提条件。移情的缺失,可以导致同感的失效。杰利比夫人因缺乏移情的愿望,甚至在家庭生活完全失序的情况下依然热衷于非洲的慈善事业。“非洲的规划占了[她]的全部时间”,“需要[她]全力以赴”(Dickens,1977:38)。正是这种盲目的仁爱,致使家庭成员生活困苦。杰利比先生性格犹豫自闭(41),女儿终日“抄抄写写”(Dickens,1977:44)。凯蒂“希望非洲毁掉”的心声(Dickens,1977:43),可谓对这种“望远镜里的慈善事业”的巨大嘲讽。帕迪戈尔夫人同样缺乏移情的愿望。即使面对烧砖工人赤裸裸的贫困,她依然固执己见,口若悬河,进行毫无意义的道德说教(Dickens,1977:98)。这种以“大大扬名”为目的的“贪得无厌的慈善事业”( Dickens,1977:93),根本无法治愈工业社会的顽疾。
与以上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埃丝特可以高效地实现移情。移情主要表现在她的感受力和体验力之上。相见之初,移情让她发现“[婀达]的举止落落大方,富有魅力”,发现“[理查德的]态度坦诚,笑起来非常动人”(Dickens,1977:30)。这种入微的体验实现了兄妹之情的建立。在杰利比府上,移情使她在第一时间注意到杰利比一家的缺失。一个母亲应负的责任,一时间由她承担。受伤的啤啤(Peepy)被她安慰(Dickens,1977:36),杰利比小姐对失责母亲的控诉由她倾听(Dickens,1977:43-44)。在帕迪戈尔夫人虚伪的慈善事业面前,她可以深入烧砖工人一家的情感。她可以直接地“意识到,在我们和这些人之间,隔着一堵铜墙铁壁,而[帕迪戈尔夫人]是不可能把它拆掉的”(Dickens,1977:99)。同样,在首次与生母相见之时,她可以透视戴德洛克夫人冷漠的外表,直接感受到迟到的母爱。“[戴德洛克夫人]脸上有一种表情,是[她]小时候就梦见的,是[她]在别人脸上从未见过的,也是[她]在[戴德洛克夫人]脸上从未见过的”(Dickens,1977:448)。
移情来源于爱人的意志(the will to philanthropy)。如埃丝特所言,“当[她]热爱一个人的时候,[她]似乎就心明眼亮起来”(Dickens,1977:17),可以进入他人的情感世界。爱人的意志是移情的前提。她的这种意志曾经受到过压抑。幼年的她生活在具有浓郁清教(puritan)色彩的家庭氛围里。她的出生被认为是罪过的开端,生命的目的在于赎罪(Dickens,1977:19)。作为唯一的家庭成员,教母与她毫无情感交流,她也“始终没有爱过[教母]”(Dickens,1977:18)。即使经历这样的压抑,她的爱人的意志依然没有被消灭。她虽然“始终不能象[她]所希望的那样爱[教母]”(Dickens,1977:18),但是依然怀有强烈的爱人意志。教母去世后,爱人的意志可以自由地满足,移情成为她始终如一的行为准则。
以上便是《荒》结构批评中理想维度的全貌。这一理想维度在宏观上是一个以同感为基础、与家庭结构类似的社会共同体,在微观上则是建立在爱人欲望基础之上的移情诉求。以同感为基础的社会理想与现实社会构成鲜明对比。这一对比集中体现在对大法官庭制度的讽刺和批评之上。大法官以及相关法律从业者毫无同感之念,根本未能体会争讼双方的情感诉求。他们有意拖延诉讼周期,专营私利。身在其中“那就象在一个慢慢转动的磨子里被碾成齑粉;就象在用文火烤炙;就象被一只只的蜜蜂螫咬;就象被一滴滴的水淹没;就象长年累月一点一滴地发疯”(Dickens,1977:52)。在微观层面上,这一理想维度以爱人意志为基础,因而融入有直观的体验和感受,具有强烈的实在性。与此相比,全部法律争讼过程则表现得虚幻荒诞。“贾迪思控告贾迪思”案件的结局,竟然是遗产全部耗尽。这样具有强烈讽刺性的结局与深入他人情感相比,毫无实在性可言。
4. 结语
综上可见,卡莱尔和狄更斯的社会批评并非对社会弊病简单的暴露和揭发。社会现实否定和批评的背后,明显隐藏着他们所怀有的社会理想。社会理想构成他们社会批评的基础和依据,是社会批评的起点。社会批评是社会理想的应用和践行,最终目在于社会理想的实现。这种现实与理想交织在一起所构成的张力性的批评结构,便是本文所谓的结构批评。结构批评是一个二维的批评结构。在结构批评中,现实的批评往往伴随着理想的弘扬,而理想的诉说往往意味着现实的否定。结构批评对于理解卡莱尔和狄更斯的社会批评,对于理解他们之间的思想借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除卡莱尔和狄更斯之外,结构批评对于理解现实主义(realism)文学同样具有一定的价值。在一部分现实主义文学之中,对现实(或实际)的描述、展示和体现伴随着理想的辩护、投射和伸张。在此意义上,现实主义文学并非理想主义(idealism)的对立。相反,现实主义是理想主义的扬弃。在宏观上,对现实的再现贯穿现实主义文学;在微观上,对理想的弘扬潜在于现实主义文学之中。现实主义文学放弃了对理想的直接描绘和陈述,但是没有失去对理想的隐匿编织和追求。这种现实和理想交织在一起所构成的张力性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重要表现,对于理解现实主义文学的全貌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