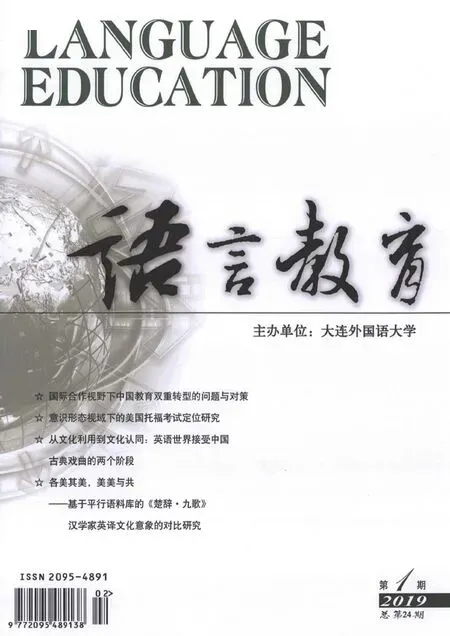“经文辨读”视角下先秦儒家的“天人合一”与理雅各《论语》译本中“天”的英译
2019-11-27冯华
冯 华
(东北财经大学,辽宁大连)
引言
我国著名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基于对中国古代哲学著作的系统研究指出: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天”分为物质之天、主宰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与义理之天,而《论语》中孔子所论及的天,都是主宰之天(单纯,2003:112)。在《论语》中,汉字“天”总共出现了49次,但并不总是单独出现,其中“天道”出现1次,“天命”出现3次,“天禄”1次,“天子”2次,“天下”23次。“天”字单独出现和与其它字组成词语出现,意义是有所变化的。“天”单独出现时,大多是“主宰之天”。比如“知我者,其天乎。”“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里的“天”都是人格化了的至高无上的主宰。而“天下”“天道”等词中的“天”则另有内涵,在《八侑》篇中“天下之无道也久矣”中“天下”是自然之天,意指四海之内,是与地相对应的自然的概念,而随后的“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中的“天”仍然是主宰之意。在《泰伯》篇中也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这里的“天下”也是自然界的天。而“天道”做义理之天的例子在《公治长》篇中:“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在中国传统义理系统中,“天”是最重要的概念。“天”是至高无上的,这种理念在夏商时期就已经被广泛接受。《尚书》甘誓中有“今予推恭行天之罚”,成汤在讨伐夏桀之前,特别做了“汤誓”,《尚书》中也有记载,成汤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群雄在逐鹿中原,争霸天下的过程中,会把自己说成是“天命”所归,所作所为就会有一种合理、合法性,有了“天命”的加持百姓也会追随,这样的传统,在整个中国古代史的朝代更替中贯穿始终,说明“天”作为至上神的观念深入人心。在殷商时期,人们对“天”更多地称为“帝”和“上帝”,但是到了周朝,人们就用“天”代替了“帝”,直接以“天”作为最高信仰,认为“天命靡常”,天意并不总是与帝王的意志相符,而更多地取决于民众的意志。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加强的当代,在《论语》的众多诠释译本中,儒家传统的“天”是否仍能保持其原有的含义?在诠释学的“经文辨读”视角中,儒家的“天人合一”如何实现?在两种异质文化的相互碰撞中,除了互为他者的排斥和抵触,会不会有相互促进和相互改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在对经典文本的阅读中找到答案。
1. 儒家传统的“天”
在《论语·公治长》篇中,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关于文章学问方面的言论,学生们可以听到,可是关于天性、人性和天道的观点,学生们是听不到的。这里所谓人性主要是指人的自然属性,因为关于人的社会属性,孔子的言论是很多的,但是关于人天生的本性,孔子只在《阳货》篇中说过一句评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关于“天道”,孔子更是没有提及,杨伯峻把子贡说的“天道”释为“自然和人类社会吉凶祸福的关系”(杨伯峻,2015: 52),认为孔子之所以不和学生讲天道,可能是受了和他同时期的子产和晏婴的影响,《左传》中记载郑国子产说:“天道远,人道逊,非所及也。”认为天道和人道各有轨迹,是不相关联的。而晏婴说:“天道不谄。”认为人类的言行意愿是不能改变天的规则的。孔子对这两位年纪较长的思想家很是推崇,因此不讲自然运行法则和人类社会的关系,可能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朱熹《论语集注》中对这一段的解释是“言夫子之文章,日见乎外,固学者所共闻;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这里朱熹认为,子贡是初次聆听了孔子很少言及的关于人性与天道的思想,所以不禁发出感叹。孔子很少言天道,但是也有言的时候,只是少数弟子才有机会听到。
朱熹这样的诠释是有其根据的:1993年在湖北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中出土了804枚竹简,上面有一万三千多个楚国文字,其中除了道家学派著作以外,其余多为儒家学说著作,这些儒家文献多是孔子的七十弟子和他们的学生的作品。“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圣人知天道也”,“察天道以化民气”(李零,2007:101,102, 208) 在《郭店楚简》中有大量探讨天道、人道和圣人关系的语句,如果孔子从来不言天道,很难想象他的弟子们会把天道的思想这样发扬光大。也许孔子有关天道的言论,只是没有被更多的弟子听到,因而没有很多记载。
由此,孔子的不讲“天道”,并不能证明儒家没有超越的概念,儒家的超越界是“天”,作为一个“一以贯之”的哲学体系,儒家思想一定对宇宙自然的终极真理有所思考和论述。儒家的“天”从来不是自然界的天空,而是有着哲学和宗教的超越意义的概念,正如道家的“道”,老子说“道生一”,说明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而“道”也从来不是一个自然的概念,虽然老子也说“道法自然”,但是这里的“自然”是指事物原本的样子。儒家的“天”和道家的“道”,就像基督教的上帝一样,是宇宙万物运行的主宰和法则。
基督教有“道成肉身”,然而在原始儒家看来,孔子的“天”是不容易和人合而为一的,《周易》中说“推天道以明人事”,虽然“天人合一”是目标,但是却要经过一生毫不懈怠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论语》讨论的核心是“仁”,可以说“仁”就是对“推天道明人事”的实践。《论语·为政》篇,孔子对自己的人生轨迹进行了概括,说道:“五十而知天命。”那么“知天命”的方法是什么呢?在《论语·宪问》篇中,与子贡讨论至此的时候,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下学礼乐而上知天命,儒家的“礼”可以是个人对待世间万物的方法和态度,而“道”是世间万物的运行法则,通过后天的学习和不断地践行仁义,由下学而上达天道,这就是知天命的方法,要完成从“人道”到“天道”的转化和超越,就需要以“仁”为行事准则。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表达的也是这样的内涵。人通过观察天道,从天的表象而推知内在,以天道为依托,养身修身,以达到至圣通天的“天人合一”。
《论语·泰伯》篇中,孔子认为尧是伟大的国君,因为他懂得并能够效仿天而广施德行,并认为人人都应该学习像尧这样尽心尽力效法天道,履行自己在人世间的职责。孔子这种“则天”的思想,由孟子进一步推进发展,使天的概念内在化,成为“心性之天”。孟子认为人“尽心”即可“知性”,由此可以“知天”(宁新昌,2004: 14)。这就是说,由人性可知天命,修身是人类事天立命的途径。“养性事天”和“修身立命”成为儒家之“天”的重要内涵。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此言圣人与天地同体”,由此,儒家的“天人合一”与基督教的“道成肉身”颇有异曲同工之理。
然而,从超越的角度来分析,儒家的“天人合一”与基督教的“道成肉身”又正是相反的运行轨迹。《圣经》中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1: 14)。耶稣以人的形象在世间行走,和人一样有各种情感,还要饮食休息照顾好肉身,道成肉身,才能给人类提供完美可信的榜样和老师,最终也通过牺牲肉身的方式,教人类学会实现“天人合一”的方法。基督教的“神人合一”与儒家的“天人合一”最本质的区别更在于,“神人合一”只能在天国实现,不在现世也不在人间。而孔子的“天”是人生哲学中的“天道”,《论语·卫灵公》篇中,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强调的是现世中人的主动性,在实现人道与天道的过程中,儒家的“天人合一”是世人安身立命的唯一正途。
2.“经文辨读”的命意与内涵
“经文辨读”(Scriptural Reasoning)作为神学和哲学领域的一个研究流派,出现于20世纪末的美国大学,是通过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学者之间的对话展开跨宗教的经文阅读与讨论的一种研究方式。“经文辨读”以小组活动和对话实践为核心,考查不同宗教经文,比如《塔木德》、《圣经》和《古兰经》的语言、句法和语义,分析历史上的阅读与诠释,并试图对各宗教经文进行新的阐释。
“经文辨读”的东方之行开始于2008年(张华,2014: 261-273),杨慧林教授应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恩·威廉斯之邀参加了在兰柏宫举办的学术对话,其间杨慧林教授与大卫·福特教授的对话使他开始关注“经文辨读”,随后杨慧林教授将“经文辨读”介绍到中国学术界,并将其作为比较文学领域内的一个跨学科研究理论话题来推广研究。
将儒家经典纳入“经文辩读”体系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作为对神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扩展,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可以使神学诠释学以“经文辨读”的方式从神学研究的领域进入公共学科研究的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使既具有神圣性又具有文学性的儒家经典融入“经文辩读”的视野中,则会为神学研究进入公共领域提供新的途径和视野,而“经文辨读”作为理雅各《论语》英译本的内涵和特质,将会引领我们在新的时代重回儒家经典。
理雅各的《论语》英译本以“经文辨读”的方式向西方世界、也向我们展示了阅读自身经典的新的可能和视角。从他者的眼中,我们也许可以看到更加清晰的自己。
3. 理雅各的“经文辨读”视角和“天”的英译
中国儒家经典是否可以作为“经文辨读”活动中的研究对象进入西方概念系统?在持续了五百年的“西学东渐”浪潮之后,“中学西传”是否能够实现?在全球化的去中心过程中,东方哲学是否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提供助力?
对于这些问题,理论上的分析与论证也许可以给出答案,但是在实践上,从1861年以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的身份出版《中国经典》英译本到1873年以汉学家的身份回国,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用长期的翻译工作证实了对儒家经典进行“经文辩读”的可能性,“经文辨读”尝试的实例在理雅各《论语》英译本中处处可见,这也是造成他的《论语》译本与其它《论语》英译本不同的主要原因。
在整部《论语》中,理雅各并没有将孔子的天翻译成“God”,而是翻译为首字母大写的“Heaven”。在《牛津简明词典》、《柯林斯英语词典》和《英汉大词典》等词典中,“Heaven”首字母大写可以表示超越界的天,也可以表示基督教等宗教中的上帝,或神所居住的天国,同时也可以指自然界的天空。如果全部字母小写,前面常需要加“a”或者“the”,有时后面还可以加“s”,在诗歌或文学作品中表示自然意义的天空。因此,理雅各将《论语》中的“天”译为“Heaven”的可能解释有两种:其一,首字母大写的“Heaven”既可以指“义理之天”、“自然之天”,也可以指“主宰之天”,含义广泛,更能代表中国传统中“天”的含义。其二,如果用“God”来译“天”,恐怕一些笃信基督教的人会认为是对上帝的冒犯和不敬,毕竟儒家也好,儒教也好,对基督教会来说仍然是异教徒世界的哲学传统。
尽管如此,“Heaven”这个词的含义和首字母大写的拼写方式还是会体现出基督教的渊源。安乐哲(2009)就指出,把“天”译成首字母大写的“Heaven”,则“无论你愿不愿意,在西方头脑里出现的是超越现世的造物主形象,以及灵魂、罪孽、来世等概念”(金学勤,2009: 172)。会让“对此毫无戒备之心的读者不假思索地倾向于将其解读为God”(安乐哲,2009: 345)。
在理雅各所处的时代,来华传教士们曾经在《中国丛报》和《教务杂志》上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译名之争”。争论的中心是如何将《圣经》中的“God”译成相对应的中文语词,争论中分出了三大阵营:第一阵营认为应该用“帝”或者“上帝”来译“God”;第二阵营主张用“神”;第三阵营主张用罗马天主教的“天主”。虽然三大阵营在辩论中各持己见,无法分出胜负,但是将近两百年的时光过去,由谁胜出不言自明,“上帝”的译法已经深入人心。而另一方面,这一语词在中文语境中也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用法和含义,虽然“上帝”一词在《诗经》中出现了38次,但是当今的中国人在提到“上帝”的时候又会有多少人想到的是中国古代典籍呢?
对于理雅各而言,除了如何将《圣经》中的“God”翻译成中文,另一个需要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在翻译中将《论语》中的“天”与《诗经》中的“帝”和“上帝”区分开来。由此,在词汇的选择和对比中“经文辨读”的思维时时影响着理雅各翻译的进程。他把《诗经》中的“帝”和“上帝”译成“God”,而把《论语》中“天”译为首字母大写的“Heaven”,既体现了两者的不同,也论证了自己在“译名之争”的观点。
在对“天”的翻译中,与理雅各思虑周翔却收效甚微的“Heaven”译法相比,辜鸿铭直接将“天”译为“God”,似乎更加洒脱但欠缺严谨,而辜鸿铭也曾特别注释说其《论语》译本中的“God”所指并不是西方宗教中的人格神,而是指“宇宙秩序”,是指固有的、最高的、普遍的、根本的“宇宙真理”(辜鸿铭,2013: 234)。因此将“天”译成“God”的归化译法,只是为了使更多的西方读者愿意阅读《论语》并了解古老的中华智慧,这是由辜鸿铭所身处的时代特点决定的。张政和胡文潇在研究中提出,应该把《论语》的“天”翻译成“Tian”,这样既能够保留“天”的多重含义,达到意义的准确,也能使“天”的概念拥有哲学上的差异性,同时因为这种译名唯一性的特点,在交流的过程中也更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比如道德经中的“道”被译成“Tao”,“阴阳”被译成“Yin and Yang”,以及“气”被译成“Qi”,“风水”译成“Feng Shui”等,都是这种异化翻译的成功范例(张政 胡文潇,2015)。
然而,这种译法虽然有诸多优点,但是读者接受起来恐怕会有各种困难,首先,对于完全以汉语拼音出现的“Tian”,母语非汉语的读者和看惯了威妥玛拼音的读者会有发音上的困难,因而会产生心理上的隔阂,其次,如果“天”翻译成“Tian”,那么“天道”和“天命”应该怎样翻译呢?
《论语·为政》篇中有:“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说法,因为这个句子是《论语》流传最广泛的箴言之一,所以“天命”在中国传统里成为了非常重要的文化概念,它既表示冥冥中主宰一切,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的天的意志,也表示社会中的规则和人性准则、人的自然天赋和遵守这些准则的能力(张立文 周桂钿,2004: 30)。辜鸿铭把“天命”译为“truth in religion”,用了“religion”一词,“天命”是“宗教中的真理”。对此,辜鸿铭在随后的长篇注释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天命”是宇宙的终极神圣秩序,是宇宙中最高的道德标准,认为儒家的“天命”就是道家的“道”,也是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所说的“宇宙的神圣理念”(辜鸿铭,2014:26)。但是与哲学家们不同,没有足够的智慧和性格力量帮助,普通人是不能够时刻遵守这些标准和理念的,马修·阿诺德说:“道德准则,最先是一种理念存在,然后才被当作法律被严格遵守,它只是为圣人准备的”(辜鸿铭,2014:27)。因此想要民众时刻遵守“天命”,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就需要宗教的加持,宗教的信仰能使普罗大众产生一种安全感和永恒感。正如歌德描述的:“虔诚……仅仅是一种方法,通过它给人的精神和性情赋予完全而完美的平静”(辜鸿铭,2014: 27)。因此,辜鸿铭把“天命”译成“宗教的真理”,也是他从儒家的角度对基督教经文的一次“经文辨读”。经过一番具有辩读性质的比较之后,他认为能够使人发自内心的真正遵守“天命”的唯一权威是道德感,是人心中的君子之道。并引用孔子的“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和耶稣的“上帝就在你心中。”来证明这种自觉遵守道德准则的必要性。
理雅各选择将“天命”译为“decrees of Heaven”,刘殿爵也采取相同的译法;阿瑟·韦利将其译为“biddings of Heaven”;另外有林戊荪的译文“mandate of Heaven”,从词义上来说,“命令”和“指令”都稍显生硬,而理雅各选择的decrees“旨意”更能表现出冥冥中无所不在的终极真理,但是这种译法也有过于强调命运而减轻了万物运行之道的意蕴。
与此“天命”的翻译不同,理雅各、韦利和刘殿爵都将子贡所说的“天道”翻译成“Way of Heaven”,天理运行的道路,宇宙运转的方式,这样的选词可能比辜鸿铭将“天道”翻译成“subject of theology”更加贴近原意,因为《论语》中毕竟是没有讨论过神学的,而是用普通百姓都能明白的词语在宣扬自己的教义。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对于“天命”和“天道”,辜鸿铭都采用了同化翻译策略,其实也是一种经文之前相互辨读的有效尝试,以西方宗教学的词汇来解释中国的传统经典,对于西方读者来说,确实更加容易接受,尽管这种接受可能是以歪曲甚至牺牲了原来文本词义为代价的。
4. 结语
不论作为文学文本、宗教传统的文本还是哲学传统的文本,《论语》参与到“经文辨读”中都是有益的,它可以影响甚至激发“经文辨读”原本涉及的宗教传统的改变,正如学者们在研究中指出,对儒家经典的“经文辨读”是神学研究进入公共领域的直接入口。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在文章《圣经诠释学》中写道:“把圣经文本揭示的经验与人类经验整合成为一个整体,这是神学的任务”(范胡泽,2012: 295)。福音书使希望和自由成为可能,它使人类通过想象和诠释改变了对自我的理解。而在“经文辨读”的视角下,这种作用在其它可以被列为“经典”的文本中也可以找到。在《论语》英译本的各种诠释中,无论依据何种注疏,无论理解的历史性和视域融合如何影响对文本的解读,先秦儒家的真正意图和孔子本人的确切声音,就在这些诠释中,经典的意义就在不断的诠释中得到体现,我们正是在这众多的诠释中找到改变对自身理解的可能性。
我国近代穆斯林学者马德新在伊斯兰教和儒家思想的对比研究中,认为儒家敬天和尊天的宗教情怀与穆斯林对真主安拉唯一信仰是一致的。与穆斯林学者的观点相同,理雅各对儒家经典刮目相看的重要原因之一,也许正是孔子的“天”具有至高无上和唯一性的特点。与其它的翻译版本相比,理雅各对于“天”的英译,相较于“God”、“Providence”和“Nature”更加易于被西方读者所接受,随后的韦利、刘殿爵和林茂孙等译者也多沿用这一用法。
从“经文辨读”的角度来看,理雅各的选词也体现了一种经文之间的替代,用非人称的“Heaven”来替代有人称的“God”。而究其实,“god”一词在英语中起初也不是作为基督教“上帝”的意义出现的,根据《牛津英语大辞典》,“god”原指由于具有超越自然和人类命运的力量而受到崇拜的超人(Coleridge,1989:639)。
在将儒家经典中的“天”译为“Heaven”的同时,理雅各也深知,儒家的“天”常常可以与“帝”互换,就好像在《新约》中“Heaven”与“God”也是如此。但是“Heaven”的译法更贴近儒家传统中对于天的非人称的理解,也使人们对基督教中的“God”产生了一种非人称理解的可能性。《约翰福音》的“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约1:1) 在传教士的合作译本中被翻译成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种词汇的选择和对“God”非人称意义的理解正体现了两种异质文化碰撞时的相互促进和相互改变。
一百年前,理雅各从汉学发展的角度指出,中国之所以值得研究,正是因为它不能像任何其它传统那样被研究,正是因为它的独立性和“固执的疏离状态” (Girardot, 2002:131)。 汉语语言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传统的独立性。语言表达思维也限制和定义思维,在哲学、诠释学和神学中间,有一个交汇的边界,如果说语言是走入这一边界的工具,而“经文辨读”是走入这一边界的方式,那么充满着诗学语言的理雅各(2015)《论语》英译本是对“经文辨读”的有益补充也是他先于自己的时代走入这一边界的尝试。从“经文辨读”的角度,对理雅各译本与其它《论语》英译本中“天”的翻译进行诠释学的比较研究,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审视和思考自身文明的全新视角,从而理解经典文本为我们所提供的人类的普遍性,以及能够展现时代精神的“经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