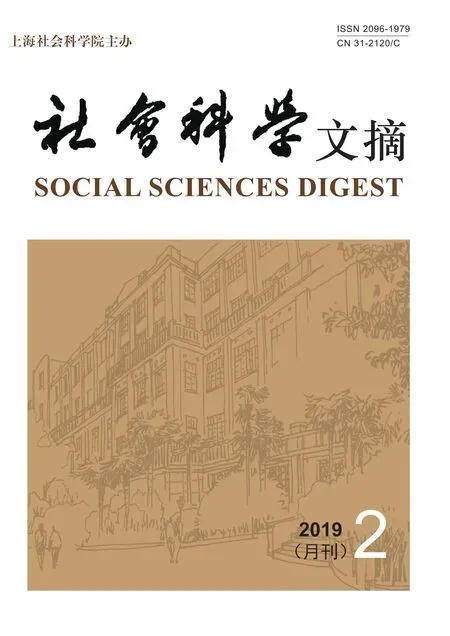记录见闻:中国文言小说写作的原则与方法
2019-11-17
中国文言小说写作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方法是记录见闻。记录,是强调小说的成书是记录(record,report),而不是虚构(invent)或创作(create);见闻,是强调小说作品中的记载有来源和根据,是眼见和听闻而来,而不是想象(imagine)和杜撰(fabricate)的。记录见闻是文言小说不同于古代白话小说以及来自西方的现代意义的小说的重要特质。现代学者对此认识不足,导致古代小说研究中长期存在着许多误区,包括作品解读不当、小说史脉络错误等。
从古代目录学看小说记录见闻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叙是中国最早对小说进行全面论述的文献,作为文类的小说由此诞生,其中已经蕴含着小说记录见闻的思想。如说“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造”并不是创造、编造的意思,而是达到的意思。又说这些小说“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是说闾巷中的下层士人将这些言说记录下来,使之不被遗忘。“缀”字的本意是缀联,这里指将零散的言说进行组织和记录。实际上鲁迅早就指出:“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值得指出的是,“缀”字暗示小说在体式上的一个特征,即一部小说作品应由多则条文组成,这就是桓谭所说的“小说家合丛残小语”,缀者,合也。反映在小说书名中,有“丛”“林”“苑”等字眼,如《桂苑丛谈》《语林》《异苑》等,表明多条文丛集是小说形式上的一个重要特征。
《隋书·经籍志》进一步将小说与乐府采风诗的传统联系起来(小说的合法性由此而来),小说家叙说“道听涂说,靡不毕纪”,“纪”取代了此前意义较为含混的“缀”字,更明确道出小说是记录而非创作的实质。《旧唐书·经籍志》称小说家“纪刍辞舆诵”,“纪”(记)而非“作”,是小说不同于诗歌的一个本质性的特征。《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没有小说家叙,但在一些小说的解题之中常常可以看到说某作品是记录见闻而成。小说以记录见闻而成书,可以说是宋人的共识。
在古代目录学集大成之作的《四库全书总目》中,“见闻”也是小说论述的关键词。其子部总序云:“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愈于博弈,故次以小说家。”小说作者记录了见闻,小说读者才有广见闻的可能和结果。四库分小说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三类,“叙述”在这里是记叙和陈述(故事)的意思,“缀辑”表明搜集之意。在小说作品的提要中,记录见闻也是经常出现的字眼,而对书中见闻不实和记录可疑者,则予以批评。四库的小说观,石昌渝总结得比较清楚:“其内涵是叙事散文,文言,篇幅短小,据见闻实录;其外延包括唐前的古小说,唐以后的笔记小说。按这个标准,背离实录原则的传奇小说基本上不叫‘小说’,白话的话本小说和长篇章回小说更不叫‘小说’了。”石昌渝将此小说概念称为“传统目录学的‘小说’概念”。其实这不只是传统目录学的小说概念,而是整个古代的(文言)小说概念,小说记见闻是古人的普遍认识。
从书名和成书过程看小说记录见闻
书名是了解古代书籍编撰方式和书籍性质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很多小说作品的名称清楚地反映了其书记录见闻的性质。
汉隋之间的小说书名,常有“记”“录”之类表示记录之意的字眼,也有“林”“苑”“薮”等表示多条丛集之意的字眼。书名出现“见”或“闻”最早的是牛肃《纪闻》和封演《闻见记》,此后“见”“闻”便成为古代小说书名中最常见的用字,而且其书自序所述的成书经过也常提到这一点。如《洛阳搢绅旧闻记》《邵氏闻见录》《中吴纪闻》等。与见闻相关的字眼“耳”和“听”,也常常见于小说书名,如《惊听录》《耳目记》《贵耳集》《耳谈》《耳邮》《道听途说》等。
小说可记自己的亲见亲闻,也可记他人的见闻。实际上将他人见闻或者所说的话记录下来,是小说中常见的一个类型,这样的小说常以“谈”“话”“说”加上“记”“录”等字作为书名标示,有时还标出所听闻的来源。这种小说以唐代韦绚之作为最早——韦绚在夔州刺史刘禹锡门下问学,记其“日夕所话”而成《刘公嘉话录》;在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幕下,记其谈“古今异事”而成《戎幕闲谈》。不专记一人之谈,而广采众人之谈,记各种所听所闻,则是更多小说成书的常态,表现于书名中仍是以“谈”“话”标示。如《谭宾录》《宾朋宴语》《茅亭客话》《延宾佳话》《国老谈苑》《翰苑名谈》《师友谈记》《步里客谈》《香饮楼宾谈》《茶余客话》等。
大部分小说并不是因(专门)记录他人谈话而作,而主要是个人闻见的记录,包含有名人轶事、朝野趣闻、历史掌故、学问知识、异闻怪谈、风土人情、里巷传闻,以及个人的议论说理和感想情志,等等。这些小说作品的名称,仍然喜欢用谈、话、语等为主要标识。如《镫下闲谈》《玉堂闲话》《野人闲话》《道山清话》《石林燕语》《晁氏客语》《齐东野语》等。小说书名中还喜欢用笔录、笔谈、笔记,因为它们都直接表示了用笔记录的意思。
桓谭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小说的体式特征之一是多条文的汇集,这也是它区别于单篇文章和传记的重要标志。六朝已有以“林”“苑”为名的《语林》《笑林》《异苑》《笑苑》等小说,唐代开始又有以“丛”命名者。丛,聚也。如《桂苑丛谈》《铁围山丛谈》《后山谈丛》《西溪丛语》《四友斋丛说》《浪迹丛谈》《听雨丛谈》等。胡应麟分小说为六家,其中便有“丛谈”一类,“丛谈”二字很好地揭示了宋人小说丛脞和记谈(见闻)的特点。
从古代小说序跋看小说记录见闻
志怪小说,今人常以虚构、幻想视之,将其看成是作者有意识的创作,进而探求作者的立意、匠心之类。其实小说的作者反复申明——书中故事是记录,并不是创作。志怪小说的早期代表《搜神记》便是如此,干宝自序说到“闻见之难”,还谈到其书内容的两个来源,抄录古书和采访前辈先贤,二者都可以说是见闻。唐宋以后志怪小说的序跋和评论更是常常提到见闻。如《夷坚志》支志庚序说“每闻客语,登辄纪录,或在酒间不暇,则以翼旦追书之,仍亟示其人,必使始末无差戾乃止。既所闻不失亡,而信可传”,足见洪迈记录之勤奋与认真。清代《聊斋志异》,今人尤喜讨论其虚构和命意,其实蒲松龄自序就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他强调书中所记都是搜集而来的。蒲松龄的朋友唐梦赉所作序也说:“凡所见闻,辄为笔记。”蒲松龄为搜集故事以烟茗招待路人的著名传说,也正说明他的写作不是现代意义的小说创作,而是传统意义的记见闻。
轶事小说记见闻,这一点学界较为熟悉和认同,不再多论。可以说,自宋代起人们已经确立了小说记录见闻的基本观念,正如叶梦得说:“士大夫作小说,杂记所闻见。”一些小说还强调征实。如李德裕《次柳氏旧闻》中的故事辗转来自高力士,讲述人的线索是:高力士→柳芳→柳冕→李吉甫→李德裕。尽管书中也涉及神怪故事,自序还是强调“非出传闻,信而有征,可为实录”。今人见到小说记神怪故事,常以为是古人虚构,其实古人(尤其是宋代以前)在一般情况下多是信其实有的。如鲁迅所说:“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又如清代《三冈识略》书前凡例,有“事虽细微,各有依据,不敢妄为称述”“凡系风闻、未经目见者,必书某人说”二则。小说中常见称某事据某人说,不能认为是作者“故弄狡狯”。但也要注意,记录见闻,来源有据,并不保证所记事件便真实可信。如沈括所说:“盖小说所记,各得于一时见闻,本末不相知,率多舛误。”
民国时期,现代小说写作已经成为主流,但传统文言小说仍未断绝,且不说《花随人圣庵摭忆》《一士类稿》《新语林》等轶事小说,志怪作品仍然沿袭传统的记见闻的写法。如《养和轩笔记》,“见有遗闻轶事,辄取片纸书之……益以身世所经、见闻所及,与夫名家记载、报纸流传”;《葂丽园随笔》,“爰将亲所见闻及本身所历之因果事实、善恶报应,据实以书”;《柘园野语》,“睹诸目,闻诸耳,写诸楮,不斧斤经营,不烟云渲染,不海市蜃楼”;《客窗消闲录》,“或采之笔录,或得诸耳闻”;《古春草堂笔记》,“举囊昔见闻所及,盘错所经,援笔而为之记”;《惜荫轩随笔》,“将素所闻见及世所传述者随时拉杂记之”。时至今日,网络上流传的《世说》体的《学林广记》等,可算文言小说之后裔。
余论
记录见闻是文言小说基本的写作原则和写作方法,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受到西方和现代小说观念的影响,要么是对文言小说记录见闻这一特质注意不够,要么是在“传奇小说”的视野下将记录见闻作为笔记小说的一般性特点,并给以较低的评价,并产生出错误的小说史。
中国古代小说按语体可分为文言和白话两类,各有其渊源和流变,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是主流和正宗。这可以四个方面来说明。(一)从时间上来说,文言小说从汉代至清代有大量写作,民国始衰落。白话小说起于唐宋说话及其记录文本,流行于晚明和清代,民国后则与现代小说合流。文言小说的起源早于白话小说,流行时间长于白话小说。(二)从数量上来说,文言小说多于白话小说。据《中国古代小说总目》,1912年以前的文言小说2904种,白话小说1251种,据《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文言2192种,白话1389种。而且大部分白话小说产生于晚清最后20年。(三)从地位上来说,白话小说一直低于文言小说,受到歧视和贬低。历代公私目录一般不收录白话小说,文人偶然写作,常不署其真名。文言小说则相反。(四)从古人小说观上来看,在晚清(光绪)以前人们说到小说,主要指文言小说。大约在1895年以后,白话小说地位陡然提升,乃以白话小说为小说之主流和正宗。
晚清民国以来,注重人物、故事、虚构等要素的西方小说及其观念进入中国,由于白话小说与西方小说更为接近,加上当时政治和历史的原因,如提倡白话文学和通俗文学、希望借小说来救国存亡和改造民族等,白话小说地位迅速提升。在进化论思想和西方文学史的影响下,白话小说被看成小说史的逻辑终点和近世文学史的明星,于是,六朝志怪→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这样一个中国小说史,也随之建立起来。由于将文言小说看作是和白话小说、现代小说相类似的事物,研究者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人物、故事、虚构等要素去看待和要求文言小说。很多学者在分析论述作品时,不考虑小说记见闻这一性质,不注意其书中的内容来源原本很复杂,或所记之事已经过多次转述和变异,或是从前代书籍抄写,或凭记忆概述,而简单地将全书视为作者一人之创作,进而探求其写作主旨、艺术特征云云。这是大有问题的。
学界对于文言小说记录见闻的特性也有所认识,尤其是在谈笔记小说时,如苗壮谈笔记小说的特点有“基于耳闻目睹的现实性”,谭帆、王庆华认为“‘笔记体小说’多表现为‘据见闻实录’的记述姿态和写作原则”。不过,将记录见闻限定在笔记小说上不够准确,它实际上是几乎所有古代文言小说的基本写作原则,更进一步来说,古代文言小说的主体本来就是今人所谓的笔记小说。笔记小说这一概念是20世纪兴起的,后来使用它主要是为了与传奇小说相区别。而所谓“传奇”或“传奇小说”,实际上是一个现代以来在西方小说观念影响下建构起来的概念和文类。那些名为传和记的单篇作品,本来是一些带有传奇性的传记,在古人看来最多勉强算作广义的小说。小说与传记在古代是两个不同的目录门类和文类。小说是多条文的丛集,故内容驳杂;传记记录一人或一事,内容单一。小说记事多是片段的,传记一般是首尾完整的。小说是记见闻的,传记因为要保持完整性和一定的篇幅,故而在传奇性传记中逐渐允许想象和夸饰。现代学者把传奇看得很重,其实是将数量不多的传奇性传记,和另外一些原本属于不同文体、文类的作品(如普通传记、诗序、传体文等),再加上小说中的一些篇段,合在一起算作“传奇”,“建构”了这一文类。
根据篇幅的长短、叙事的精妙、虚构的有无等标准,将文言小说划分为“笔记小说”和“传奇小说”两大类,然后抬高和重视传奇,贬低和忽视笔记小说,是小说史学界长期以来的做法。这样的结果之一就是,小说记录见闻的特性被忽视,笔记小说的身份变得尴尬,以至于唐宋以来大量记见闻的小说成为小说史上的配角,尤其是轶事小说因为比志怪更“不像小说”,除《世说新语》外差不多都被小说史所遗忘。更进一步,小说史学界干脆就放弃了对这些小说的研究,甚至“剥夺”了它们的小说的身份和称呼,使很多作品只好以“笔记”的身份存在于中文和历史两个学科的边缘。今人把小说这个概念拱手交给较具虚构和想象的白话小说和传奇,“剥夺”传统的文言小说(尤其是轶事小说)的小说名分,而以“笔记”来称呼它们。古人对《世说新语》和《酉阳杂俎》称誉很高,但今人看重的则是传奇和白话小说。不得不说,古今的小说观念发生了严重错位。当下学界在古代小说研究中忽视文言小说,在文言小说研究中忽视轶事小说,正是小说概念和观念变化造成的。
浦江清1944年曾对小说概念和观念的变迁做过很好的论述,他说:“中国人的性格是核实的,从前的文人对于历史和掌故的兴味超出于虚幻故事的嗜好。所以据宋人的看法,小说的最高标准也许是《梦溪笔谈》和《容斋随笔》。……若照老的标准,认为小说不单指虚幻文学,那么宋人的笔记还是在向上进展的路上,笔记小书到了宋代方始体制完备,盛极一时。……即如宋人笔记,多数是可爱的小书,惟其作者漫不经意,随笔闲谈,即使不成立为小说,也往往有小品散文的意味,实在比他们文集里面的制诰、书奏、策论、碑志等类的大文章更富于文艺性。我们觉得假如小说史里不能容纳,总的文学史里应该列有专章讨论,以弥补这缺憾。如有人把笔记文学撰为专史,而观其会通,那末倒是一部中国本位的小说史,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按此设想,在现有的小说史框架之外,尊重古人的小说观念,突出记录见闻的文言小说在小说史上的主体性,揭示它独特的魅力,探讨它在古代文人写作和精神世界中的地位,再建一个“中国本位的小说史”,是一件值得尝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