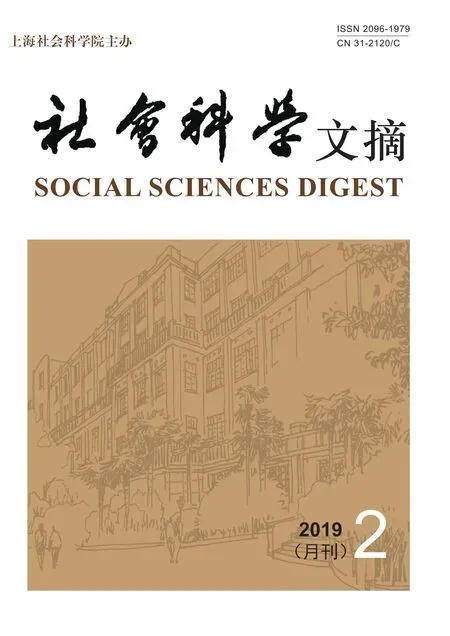自拍:一种纠结的“自我技术”
2019-11-17
自拍这一新媒体时代的行为,是如何折射着人们的自我?自拍这一看似可以自由控制的技术,是否真的能实现自我的自主建构?这些问题,将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
从书写到自拍:“自我技术”的演进
福柯认为,技术有四种:生产技术、符号系统技术、权力技术和自我技术。其中,自我技术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自身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
但福柯研究的自我技术主要是古希腊时期的,更多地是看重“自我技术”的伦理目的。福柯设想个体通过“自我技术”构成为主体,也就是说“自我”能够是“自我构成”而不仅是“被构成”的,因而“自我技术”对个体的自我创造就十分重要。
新媒体技术作为新的“自我技术”,给了人们新的自我关注与自我创造可能,也在重新定义与自我的关系。然而,今天的自我技术,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古典时期的自我技术,因此,我们对“自我技术”的研究,也不应囿于福柯的思路。新媒体时代的自我技术不仅推动了个体的“自我关注”意识,更重要的是,将这种自我关注置于前所未有的互动环境中,研究这样一种互动环境是如何影响个体的存在感、自我评价、自我建构及自我认同的,是研究包括自拍在内的新的自我技术的重要角度。
自拍与“在场”:“我拍故我在”?
(一)在场或缺席?
在一定意义上,自拍的确是个体自我意识增强的体现,人们开始试图挣脱外在的摆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存在方式,同时,以昭示在某种现实空间中自己的身体“在场”,来彰显其存在感。
新媒体不仅给予每个人麦克风,也给了每个人独自表演的舞台,而自拍是最简单直接的表演方式,也没有任何门槛。各种社交平台的“自媒体”,让人们这种存在有了“告知”的渠道。尽管新媒体给了人们“虚拟在场”的可能性,使人们可以实现“无所不在”,但自拍这样的证实自己身体在场的方式仍然必要,甚至变得更为重要。因为,身体在场的背后,暗含着某种可以炫耀的能力或资本。自拍的另一种用处,是不在现场也能制造出在场的效果。在场的那些心理满足,同样可以通过假装在场的方式获得。
自拍看上去强调了“我的在场”感,但另一方面,它可能将自拍者的注意力从真实的现场转移开。因自拍而失去对环境观察导致的悲剧事件,如失足身亡,也时有发生。因此,所谓的在场只是影像化的、数字化的,人们呈现自己的在场,更多地是为了在社交平台中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在真正的现场,反而可能呈现一种“缺席”状态。为证明身体在场,却造就了某种意义上的“缺席”。这是移动时代的一种空间悖论。
在社交圈发自拍照,也是强调自己在社交圈中的“在场”。对某些人来说,这甚至变成了一种仪式,有些人会每天都履行这一仪式。但是当他人对这种仪式熟视无睹时,这种仪式也就退化为一种纯粹的个人的行为艺术。强调自己在社交圈的“在场”,最终在他人眼里成为一种可以自动无视、屏蔽的背景,在场也随之消失,这是另一种悖论。
用自拍来宣告自己的在场,看上去是自主的,但一旦放在社交平台上,它就会受到社会互动环境的影响。自拍中真正“在场”的,不仅有个体的身体与“自我意识”,还有个体从他者角度进行的自我审查与评价,尽管这种审查与评价未必是准确的,但它会时时会起到干扰作用。因此,自拍中表现出来的“在场”方式,常常也是被环境与他人建构的。
(二)作为政治手段的在场
个体的在场,有时也会变成一种政治手段。对普通个体来说,自拍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是个人态度与“姿态”的显现,可以成为表达,甚至抗争的手段,特别是在一些社会行动中。通过公共行动中的自拍照及其分享,个体可以更充分地呈现自己在公共空间的在场及其态度。
从政治表达的角度来看,身体在场往往成为一种必须。这种身体在场所需要付出的不仅仅是时间,有时还伴随着风险,甚至是危险,也正是这种身体在场的风险凸显了抗争的意志。
对于普通个体来说,自拍要成为一种抗争手段,往往需要与他人的行动汇聚在一起,形成一定的规模,因为集体性的在场比个体在场更有力量。当然,个体自拍的政治力量并不一定要通过社会抗争行动来体现,事实上,随时随地发生的自拍行为以及社交媒体上无所不在的自拍照,便挑战着传统媒体中只充斥着政治人物或其他公众人物照片的旧有传播模式,这本身就具有政治性意味。而在一些重大事件中普通个体表现自己在场的自拍照,或许会使这些重大事件在公众面前呈现的图景变得更丰富,突破传统媒体报道的局限,一些普通个体也有可能留存于公共历史的记忆中。
对政治人物来说,自拍也正在成为一种新的个人形象塑造策略。政治家们自拍的一个常见的策略是,通过与平民的自拍,来显示自己在平民社会的“在场”,以拉近与平民的心理距离。
自拍与自我建构:“三重自我”的调和与冲突
自拍强调的“在场感”,不仅仅是为了“存在感”,也是为了社会互动环境中自我形象的建构,也如戈夫曼所说的社会性表演。
(一)社会性表演与三重“自我建构”
网络中的表演手段很多,让自己的形象成为表演手段,有时更为直接、有效,也吻合了这个“颜值即正义”时代人们“看脸”的需求。通过自拍完成社会性表演或印象管理,往往会考虑以下几种要素的选择:自身形象、合拍对象、时间、环境、其他道具等。
作为表演或印象管理的一种方式,自拍既在传达自拍者对自我形象塑造的意愿,也在通过别人对自拍照的评价,在与他人的关系(包括群体的关系)中,来评估自我及其社会关系。自拍反映的是个体的自我建构过程,这种过程并非封闭的,而是在社交平台上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实现。
自我建构的概念最早由黑泽尔·罗斯·马库斯和北山忍于1991年提出,指的是个体在认识自我时,会将自我放在何种参照体系中进行认知的一种倾向。玛莉琳·布鲁尔等认为,每个个体的自我建构都包含三个组成部分:从自身独特性定义自我、从自己与亲密他人的关系中定义自我、从自己和所从属团体的关系中定义自我。他们将这三种建构倾向分别命名为个体自我、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也称为自我的三重建构。对每个个体来说,这三重自我建构都存在,只是对于不同个体而言,三种建构倾向的相对强度存在差异。自拍及晒自拍照的行为,是三重自我相互关照、相互博弈的过程。人们首先通过自拍来塑造“个体自我”,然后在社交平台中,通过晒自拍照来进行“关系自我”或“集体自我”的构建,寻求获得对“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的积极回馈。但是,社交平台中亲密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反馈,未必总是对个体塑造的自我的肯定,反而可能是负面的评价。这时个体往往需要通过一定的调整,例如删除自拍照或调整自拍策略等,来改善“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的形象。在这个“展示—获得反馈—自我调节”的过程中,个体在不断地试图调和三重自我的关系。
自拍及晒自拍照,也为个体对自己社交对象的关系属性或亲密程度进行判断提供了一种中介,其依据往往是他人对自拍照的反应和评价。
(二)自我建构的偏差与冲突
1.“我所理解的理想自我”与“他人眼中的自我”间的偏差。个体的自拍往往是为了塑造理想的自我,但有时“我所理解的理想自我”与“他人眼中的自我”会存在偏差。在现实中,可能导致偏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是情境抽离导致的理解偏差;其二是社会角色期待与自拍形象间的错位;其三是情绪的错位。
2.自我放大后对他人形成的压迫感。自拍的目的常常是试图构建一个自认为理想的个体自我,并以此对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的建构形成积极作用。但在实际中,对后两种自我来说,自拍未必一定会起到正面的作用,有时反而会成为一种障碍。
自拍行动本身未必一定带有利己主义的趋向,但自拍的确容易让他人产生“自恋”“自我中心”的联想,因此可能导致他人的反感。自拍也容易带来“自我放大”,频繁的晒自拍,可能会在社交圈子中对他人形成一定的压迫感,自我的炫耀容易使他人产生心理上的失衡,这些都会影响到个体与他人及集体的关系。
(三)建构或解构?
尽管多数时候人们的自拍都是为了理想的自我形象的建构,但某些时候,自拍也可能成为自我形象的一种解构,例如,自拍丑照。这既可能是表达个性、个人态度的一种方式,也可能蕴含着某些政治或艺术性的目的。
在摄影艺术领域,对自拍的探索早已超越了自恋的范畴,例如日本摄影师森村泰昌在自拍摄影中的一系列实验。在专业摄影领域里自拍的演化,特别是后期的实验性自拍,逐渐将自拍变成对社会文化和权力的原有框架的解构,从而完成对社会现象的诠释、批判与抗争。这种趋向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在普通个体的自拍中出现,虽然这不会是自拍的主流。
另一种自我解构,是对自己以往在他人心目中固定印象的解构,从自拍者角度看,这是为了塑造和展现自我的多面性,而非真正的解构,但如果拿捏不当,或许会使自己以往好不容易积累的“人设”在他人眼中崩塌。
(四)个性,还是去个性?
自拍是“自我”的一种建构,自拍中也存在着个体差异,但它未必一定带来个性的张扬。
自拍行为仍然折射着既有的一些文化传统或框架,这些旧有文化(特别是性别文化)仍然在对个体形成抑制。对于很多女性来说,自拍并不是其个体意识觉醒的表现,反而成为迎合性别文化老套路的一种新方式。从审美角度看,自拍也会带来个性的抑制或削弱,自拍越来越变成趋同的面具下的表演。社交和群体归属需要,也会强化自拍的某些趋同性,如果自拍是加入某种群体或流动的共同体的需要,那么,迎合、趋同而非个性,会成为自拍的基调。
自拍与自我认同:基于身体的表演
自我认同是指在个体的生活实践过程中,通过与他人及社会进行能动互动,以及通过内在参照系统形成自我反思,使行为与思想逐渐形成并自觉发展成一致的状况。自我认同概念起源于埃里克森,虽然心理学领域的自我认同研究,更多关注的是青少年社会化阶段中自我认同的形成,但自我认同过程其实会一直伴随着个体。
自我认同研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安东尼·吉登斯更关注的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关系,他尤其注意到了“身体”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身体并非一个简单的“实体”,而是被体验为一种应对外部情景和事件的实践模式……对身体保持规训,是优秀的社会能动者固有的一种能力……对身体的惯常性控制,既是能动的一种内在本质,也被他人接受(信任)为个体的一种能力。在他看来,身体成为了自我反思与社会互动的一个中介,为自我认同提供了一种实践模式。
自拍提供了新的身体表演方式,也给“身体”带来了新的应对外部情景和事件的“实践模式”。即使人们的身体实体不能随时调节,但通过自拍的设计与美化,它们也可以更好地配合或回应外部的情景。
吉登斯还指出,大规模对形体外表进行自我陶醉式保养的运动,所想表达的是深埋于内心的、欲主动对身体进行建构和控制的一种忧虑。
在现代社会,对身体的保养和控制已经成为社会性表演的一种重要形式,特别是公众人物以及中产阶层等社会阶层,对于身体的控制某种意义上成为他们彰显自己的生活优越感、自我意志力和成就感的方式。但对于多数人来说,身体的控制需要很高的成本和自我控制能力。而自拍加上美图,将这样一种身体的控制和表演虚拟化了,控制成本因此变小。
自拍可能会创造出一个与现实自我发生越来越大分离的、依托于美化后的身体形象之中的如吉登斯所说的“虚假自我”,且在个体生活中不断弥散。虚假自我与现实情境的冲突可能会逐步加深,他人也会日渐对其“虚假自我”的表演感到厌倦、排斥。
自拍:权力的规训还是自我的规训?
福柯的研究中,将“权力技术”视作“自我技术”的对立面,权力技术的目标是对个体进行规训,而自我技术则试图使个体能够“自我构成”,而不仅是“被构成”。但今天,包括自拍技术在内的各种自我技术,让我们看到了权力技术与自我技术间界限的模糊。
福柯的圆形监狱的寓义,在今天有了新的解释。社会化媒体成为了一种新的圆形监狱,它有一道无形的墙,那就是他人的评价。人们的自我意识及其表达,总会碰到这堵墙上并反弹回来。通过“圆形监狱”对个体进行监视的,不仅有权力,还有“自我”。自我在不断地进行表演的同时,时时从社会或他人的眼光对自己进行审查,并不断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进行自我调整,社会化媒体的普及应用,使得这种自我表现——从他者角度进行自我审查(既来自真实的他人,也来自想象中的他人)——自我调整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常态与频繁。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一系列的纠结与矛盾:虽然自拍强化了个体的“在场感”,但这种“在场”往往是为了给别人看的;自拍传达了个体的自我建构愿望,但这种建构会更多受到他人与环境的影响,“关系自我”“集体自我”这两者对“个体自我”的作用会加深;自拍是一种自我认同实践,但同样,这种主要基于身体表演的自我认同过程,也时时会受到外部力量的规训。
自拍的确是一种新形式的自我技术,它也能在身体、行为、存在方式层面实现如福柯所说的能达成自我转变的一系列操控,但这种操控更多地不依赖人们的伦理原则、意志和控制力,也难以使人们成为欲望与快感的主人,反而可能在某种程度通过这些简单、无需意志力的个人技术,使人们进一步被物化的世界和他人的评价所“构成”。看上去自由的“自我构成”与“自我的转变”,更多时候还是为了迎合物质化世界和外部力量的规训。自我的技术,在变成另一种自我的“支配的技术”,也带来了多重的自我纠结。今天社会化媒体的种种个人表演手段,也与自拍都有异曲同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