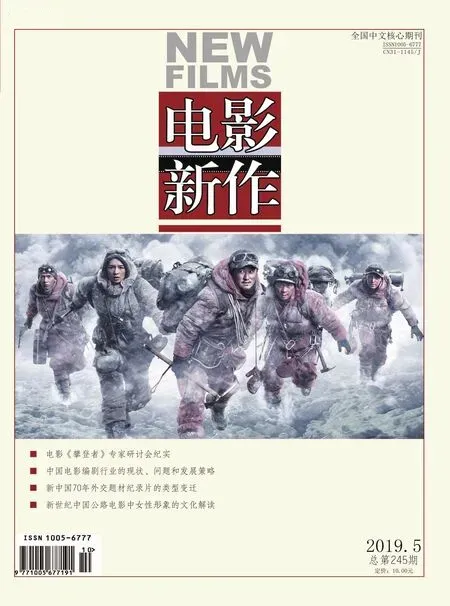寻找真实的自我
——以拉康镜像理论看《她》中主人公的自我建构
2019-11-15任小青
任小青
电影《她》是美国导演斯派克·琼斯第一部独立创作的后现代科幻爱情长片,该片斩获2014年第86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影片讲述了在不久的将来,主人公西奥多(杰昆·菲尼克斯饰)是一位细腻而多情的信件撰写员。作为一名在现实中遭遇婚姻危机的中年宅男,与第一代人工智能操作系统(OSI)的化身萨曼莎(斯嘉丽·约翰逊声)发生了相依为命的炽烈的爱情故事。但当某一天西奥多发现萨曼莎与包括他在内的成百上千人进行同时聊天对话,甚至恋爱时,二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终于,萨曼莎因升级与其他操作系统群离开了他。
主人公西奥多因与前妻凯瑟琳婚姻的失败而陷入忧郁之中,久久不能释怀。整日穿梭于庸碌的上班族群中,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没有激情可言。之后与操作系统萨曼莎奇异的爱情纠葛,却让他认清了自己,重新摆正了其生理、心理以及价值观的标尺,真正地确立了自我。值得追问的是,西奥多经历了自我的迷失与寻找,在此曲折的过程中,西奥多“自我”的确立受到了哪些“他者”因素的影响,其作用机制或原理是什么?拉康的镜像理论对于自我意识的建构有着精到独特的阐发,本文欲引入其“他者”理论对《她》中主人公西奥多的“自我意识”的确立,做一番梳理、发微的工作。
一、镜像理论与自我形成
雅克·拉康将其“镜像阶段理论”分为“前镜子时期”和“镜子时期”。前镜子时期,主要指婴儿从出生到六岁这一阶段。这时期,孩子的各项功能(包括意识及感知能力)还尚处于不完善状态,对外界并未形成感应与知觉。在拉康看来,婴儿在前六个月里,对于自己的身体及各个器官并没有协调能力。这也就是说,孩子在这一时期处于朦胧的初级认证阶段。在第二阶段,即“镜子时期”(大致指6-18岁与18岁以后),拉康认为孩子能够通过辨别镜中的成像初步形成对自己的认识。即孩子“立即会由此发生出一连串的动作,他要在玩耍中证明镜中形象的种种动作与反映的环境的关系以及这复杂潜象与它重现的关系,也就是说与他的身体,与其他人,甚至与周围对象的关系”。此后,他们愈来愈被他们的镜像所迷惑,钟情于镜中的“他”,这一行为事实上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迷恋。而“自我”的形成正是借由镜中所呈之像,且在真实的自己与影像中的自己(他者)间就此构筑成一个想象的世界。换句话说,自我的主体性本质上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虚无的存在。诚如拉康所说:“镜像阶段犹如一出戏,他的内在推动力从不足到推进到期待中,为陷入空间认同的吸引之中的主体形成了从破碎的身体像到我称之为矫形的整体性形式的幻想的连续。”意思是,在镜像阶段,人能够不断地发现自我。从最初片段、支离的印象逐渐过渡,形成相对完整、统一的自我认知。人的主体性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初步的确立,即能够将镜中的像与自我合二为一,实现同一性。这是主体构成的重要环节。
他者在人类“自我意识”的确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是拉康镜像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自我的认同总是借助于他者,自我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被构建的,自我即他者。”最初,婴儿建立自我意识所依靠的他者或镜像,并非皆有实体对象,而是想象中的他者。但基于自我在本质上缺失的事实,需要不断地与外在的他者接触,以确认、充实和完善自我,因而作为他者,镜像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婴儿时期,而是贯穿于人的一生,始终着力于人类自我在身心方面的塑造。在这里,镜像可以理解为一种隐喻,无论是关系亲近的朋友、同事,还是不同范围内的社会交往对自我的塑造都会产生或多或少的作用,而他人所给予的或肯定或否定的评说,以及语言文字中的“我”,同样有潜在的意义。易言之,“他者”的干预是促成自我确立的必要条件,反过来讲,自我的确立也就是逐步实践“他者”的内化。在拉康这里,他者在概念上有着广狭义之分。从广义上来讲,也就是存在着“大他者”,它指涉的对象是整个时代环境、社会形势,以及规则制度等;从狭义上讲,即“小他者”,则如上文所述,涵盖了婴儿时期镜像中所呈的虚幻影像,周边亲朋施加于“我”的种种影响等。电影《她》,恰恰很好地体现出了他者影响的意义。因此,笔者拟从大与小两方面对西奥多的自我建构作一分析。
二、“自我意识”的确立与“大他者”的影响
人对自我的认同并非全部来源于自己,绝大部分是从他人、社会中获得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本质属性是社会性。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曾在《双城记》中描述我们所处的时代,既最好,也最坏;既什么都有,又一无所有;既处于希望的春天,又处在失望的冬天。科技的白昼带来了世界的黑夜;工具理性的胜利,使精神向度的存在再次被遗忘和遮蔽。诚如海德格尔所说,由技术性所主导的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存方式已经发生改变。自由的、本真的栖居环境渐被破坏的同时,人类也相应的失去了自由。马克思亦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她》作为2014年度奥斯卡获奖电影,对人类的生存困境无疑予以了现实性的终极关怀。
影片将时空设定为“未来世界”。其中充斥着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人们的行动在科技的推动下获得了极大的便利性与可能性。与此同时,随着科技理性、工具理性的日益发达,机械化程度不断高涨、信息传输迅猛快捷,大众文化也趋于泛滥。人们在拥有享受这些便利条件的时候,精神也随之进入了一个贫困的时代,迷惘的时代。多元化、碎片化的世界里,人们的精神陷入了无家可归的尴尬境地。朋友艾米自己拍摄的纪录片,却不知道主题将要如何发展下去。她说,“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觉中度过,而且感觉这是最自由的时刻”。她觉得梦境是什么无需明了也不重要,关键是人能够在那短暂的瞬间求得片刻的放松与安息。信件的撰写由手动操作转变为语音跟踪,甚至情感的编码与传输皆可通过专职的中介员来实现。然而,如此这般多元化、便利化的社会,却制造出了“单向度的人”。
影片开始,主人公西奥多坐在极其舒适又高档的私人办公室,用心而又多情地抒写着情意浓浓的信件,娓娓道来、含情脉脉。然而当镜头切换到工作桌上的电脑屏幕前,我们看到有三对夫妻的照片,而这封饱含深情的信件正要通过邮件“一式三份”地发给他们。一种发自内心的、独特的自我情感表达,未经过滤、处理的二次生产。至此,情感的独特性、专属性被肢解、复制,变成一种可供交换与消费的对象。而当镜头拉远,我们看到整个工作室的员工都在进行着同样的程序,编码、代发。工作的机械化、流水化已经淹没了真情的厚重感与私人化。我们每个个体都被严重异化了,把手段变成了目的,各社会主体缺乏有效的交流,从而导致了人的自由和意义的丧失。
主人公西奥多每天重复着同样而板滞的行程,上下班、听歌、挤电梯、坐地铁,并无二致。下班后,一个人落寞地走着,对国际新闻不感兴趣,对朋友的聚会邀请拖延回复,对艳星裸照进行偷窥。回到家,玩游戏,回忆与前妻凯瑟琳的甜蜜过往,夜夜难眠,寂寞到网聊找成年女性排遣欲望。他说,“我从来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总是很困惑”。在技术统治人的社会,人们在物质上极度地追求,以获取肉体上的快感,并以为物质的富足完全等同于精神的充盈。但事实上,人们陷入工具理性统治下的恶性循环的怪圈却浑然不知,精神世界和意义世界处于空洞状态,“人自身的本性被遗忘,人们迷失在物质世界之中无法自拔”。正如影片中所说,“你是谁?”“能成为谁?”“要去哪里?”“未来有何种可能性?”这样的哲学命题,关乎人的存在形态与存在价值。而这恰恰是现代社会以及后现代社会应该关注的问题。
鲍德里亚提出现代社会是一个被消费所控制的社会。现代社会的消费已经不再局限于实物的交换,随着信息技术媒介的发展,消费已经走向符号化。这意味着符号成为主导市场的统治者。而由符号系统所操控的市场,在本质上讲,是对现实的一种模拟。并且倘若模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就会与现实世界相差无几,甚至形成超现实的世界。鲍氏指出“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模拟。这种模拟不再是根据现实模拟,而是根据思想或感觉进行的创造。仿像不再是对某个领域、某种指涉对象或某种实体的模拟。它无须原物或实体,而是通过模型来生产真实:一种超真实”。超真实是对真实的全然模拟,它正是仿像文化的结果之一,它被生产出来,在真实性上更甚于现实世界。萨曼莎,作为一个有自主思想,能理解人,有着惊人的学习力与审美创造力的操作系统,可以说对人的模拟达到了高度的仿真水平。且不说对硬盘的扫描和文件的整理;对拼写与语法的纠错;以及对主人工作事项的提醒与安排等等一类的机械运作。让人诧异的是,她能够通过主人说话的语气揣摩心思;拥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去“体验人生”;乃至谱写意味深长的动听乐曲。诸如此类的能力,都比人类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正是这完美的超真实,塞给了西奥多虚假的幸福感与存在感。自我满足的同时,也迷失了自己,最终被萨曼莎“抛弃”。西奥多与萨曼莎的交往恰恰可以印证鲍德里亚的话:“生活在由自己所创造的符号世界之中,却反过来又深受符号的宰制,心甘情愿地做自己创造的符号的奴隶。人们自愿地在同符号的游戏中,享受物质诱惑的魅力”。符号在无形中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统治者,这种消费看似是人们自主选择的结果,而实际上符号不过是社会系统强行施加给人类罢了。从深处来看,受信息的快速化生产和传播的冲击力影响,传统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改变,各领域之间的界限变得日渐模糊,事物自身的个性也不免遭到侵蚀和消退。
三、自我建构过程中的“小他者”
1.与前妻凯瑟琳的婚姻——心理建构的“他者”
在拉康看来,个体在未出生之前,与其母体处于一种相互交融的和谐自足状态。这时候,个体生长所需要的营养成分、温度等都能在母体中得到相应的满足和补充。当其脱离母体之初,这种和母体交融的惯性还会存在一段时间,导致其无法感知、识别周围的环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惯性和平衡会慢慢被打破,这时候,新的个体开始逐步认识到自己与所处环境的对立,个体的自我意识也逐步萌生。在这一过程中,他既需要承受与其母体脱离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痛苦,但是为了更好地生存,还必须适应所处的环境,于是自我意识更加明晰。然而,与其母体分离的痛苦会时不时地给其带来不安全感,使他认识到自身力量的局限,从而影响他的应变能力。
这种理论在某种意义上也表明了个体一旦进入新的文化环境,就很难回复到原始的自然状态,但这种矛盾性始终伴随着个体的成长与生活。影片中,西奥多眼前多次浮现出与妻子凯瑟琳一同度过的美好时光。我们可以看出,妻子对其心灵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西奥多说,他和妻子凯瑟琳有着较为相似的受教育经历,两人对创作都充满兴趣,常常交流写作体会,相互之间的影响也颇深,在此过程中他们精神世界更加富足。但是两人初次相识的时候并非就呈现出和谐的状态。只不过他们在生活中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尤其是对于新事物有着强烈的探知欲,寻找并帮助对方感受生活中令人刺激动情的事物。他们努力克服歧义和胆怯,朝着同样的目标前行,做出改变,因此这种携手共进的生活经历给西奥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在脑海中常常感觉到在与凯瑟琳对话。而他们这种融洽的状态,好比处于子宫内的胎儿一般,享受着彼此带来的自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关系,使他们忘记了差别与不完满的存在。然而,人终究是现实中的人,要在社会中成长,处理好社会关系与事物,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缺失的概念。
生活在继续,矛盾也相继出现。在签署离婚协议书的当日,妻子凯瑟琳说,西奥多需要的是一个没有任何实质性问题的妻子。按他的要求成为一个“乐天派”性格的人,没有烦恼和忧郁。可是妻子凯瑟琳的成长环境却是充满负担的。纵使两人在一起之后,之前的压力得到了解放,但“他者”影响对其性格的塑造终究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而这恰恰是他们害怕出现的,却又实实在在发生的。于是,性格的差异,生活节奏的不同步,使二人在价值观上出现了分歧。就这样,离婚后的西奥多变得忧郁起来,成为一个典型的宅男。之后,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性感的女生。两人相谈甚欢,但当女孩问他是否认真对待且对其负责时,他却找借口加以推脱搪塞。这是因为与前妻凯瑟琳的不欢而散,使他产生了逆反心理,他害怕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因而没有勇气去开始并接受一段新的恋情。而这一影响也成为他内心的顾虑而伴随之后的交往,譬如,在与萨曼莎“一夜交欢”之后,他仍然坦言自己不会做出任何承诺。有了一次的失败经历,西奥多的内心已然变得支离破碎,敏感、柔弱。正如他的同事所言,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
2.以信件为线索的“他者”
纵观影片,信件如一条串珠一样,将故事情节完整起来。但这条串珠在影片中的意义,绝非连接、点缀这般简单,它暗示并见证了主人公的成长与建构。撰写信件既是西奥多的工作,却也是他精神世界的食粮,是他逐步认清自己,确立自我意识的引线。
西奥多作为一名信件代写员,他能够根据客户所提供的信息,掌握相关的细节,用最细腻却也最朴实的方式抒写出一封封美妙又感人至深的信件。他在信件中所描述的生活场景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典型。以至于最后被合辑出版,都在于他用最简单而又真实的文字,打动了出版商也打动了每一个读者。透过文字,人们看到了最本真的自己,也找寻并重拾到了最初的感情。
海德格尔将语言视为存在的家。他这里所谓的语言,并非我们一般所讲的概念和表述。它指向了“此在”存在的意义,存在是此在的本真状态,是哲学层面的问题。海德格尔将语言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来看待,正是从中发现了语言对于存在的提醒作用。西奥多是一个敏感却也敏锐的作家,他能够洞察与他擦肩而过的路人所经历的曲折或是浪漫。他分享着,感受着别人的欢笑泪水,聚散离合。这一刻他的内心得到了“诗意的栖居”。按照海德格尔关于此在与存在关系的辨别,西奥多在为别人写信,在信中复述别人的故事时,对于此在并不严加看管,即他自己的事情在这个阶段是被放置和隐藏起来的。因为敞开的是别人的世界,自己的世界于是处在封闭和静止状态。一方面他可以借此使自己的痛苦情绪得到片刻的释放和转移。但与此同时,自己的世界关闭了,则意味着迷失和空洞的到来。这种虚无的存在最终战胜此在的暂时缺席,而留给他的依旧是之前绵延不绝的苦痛。诚然,这份工作使西奥多贫困的精神、孤独的灵魂得到了安放,当一天自己最喜欢的作家。但正如他自己所说,那只不过是信而已,署了别人名字的信而已。回到现实,他的生活依然为孤独所包围。
然而,正如他的读者所言,在他众多的信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笔下的“他者”,成为读者成长中的“他者”,而他自己又怎能不受这一封封信件中“他者”经历的影响而成长呢?其实,在他抒写的过程中,其自身也受到“他者”的洗礼与关照。写别人的故事,又何尝没有自己曾经的经历作为引子(包括情节与情感),而这反过来又成为催生自己确认自己的药剂。他害怕的正是他内心极其渴望的,“他者”的故事也是他的成长故事。
影片最后,导演有意安排他写给前妻凯瑟琳的信。“那些在我们彼此身上留下的伤痕,包括我先前责怪你的一切,我对你所期待的,我想你对我说的那些话,对此我很抱歉。我会永远爱你,因为我们一起长大。因为你,我才会是现在的我。我只希望你知道,你将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对此我很感激。”是的,无论是前妻、客户、同事、朋友,还是萨曼莎,都在他的生活轨迹中留下了痕迹。不管是欢笑还是泪水,他们曾陪伴他一起成长,找到了最本真的自己。尤其是到最后,他收到萨曼莎帮他出版的那本信件书,以及翻开首页,题有“生活给你的一封信”的字迹,他幡然领悟了过去的种种,和那最本真的我在此刻的存在价值。
3.萨曼莎——镜子里的“他者”
《她》作为影片的名称,虽然简洁,但却将所要表达的思想都涵括其中。一方面,从性别上讲,她是女性;另一方面,从人称上看,她是第三人称。前者决定了她具有母亲的化身,与拉康镜像理论的第一阶段吻合,是婴儿与母体之间温情和谐关系的象征。后者则以自我之外的他者作为参照,同样利于将主题推向深入的境地,将人类追寻自身存在意义的拷问发挥得淋漓尽致。
离婚后的西奥多是忧郁的,孤独的。但萨曼莎的到来无疑给他那无处安放的灵魂找到了一张幸福的温床。仿佛脱离母体的胎儿,品尝到乳汁的甘美滋味一般。萨曼莎总是能够在他需要的时候及时予以慰藉。排忧解难,泡咖啡,甚至交欢,他们的关系越过了恋爱期直接进入到了平稳期与蜜月期。萨曼莎在他生活中充当着闺蜜兼情人的角色,而这无疑成为填充他心里缺口的良方。萨曼莎的善解人意,聪慧能干,满足了他对情侣关系的所有想象与期待。这种状态就是拉康所说的处于子宫内的胎儿享有的一种自足状态。
但是,他似乎忘记了萨曼莎是有着自主思想的个体。与他的持久相处,唤醒并挖掘了她沉睡的欲望,她已在这亲密的关系中成长起来,已不再是原来的自己。她学会了人类的“自私”与“愤怒”。当她向西奥多提出并说服其,需要通过拟人性爱服务来实现与男主角灵与肉的结合时,她给出的理由之一是,这对我很重要。至于后来得知,萨曼莎在同包括他在内的8362个人聊天,且与另外的641个人建立了恋爱关系时,西奥多的精神近乎崩溃。对此,拉康解释为,无论孩子在与母体分离之前还是之后,孩子对于母亲总有各种需求,但是母亲不可能时刻在场,那时候,孩子的需要因此就不可能得到及时的满足。此时,孩子开始意识并接受母亲对于自己而言,究竟不可能如镜像阶段那样两位一体,在实质上也与外人无异,充当了他者的角色。
西奥多希冀的是萨曼莎只属于他一个人,他们的感情依旧如初。可正如西奥多所说,他恋着她的多种存在形态而非单一,而这恰恰是他的矛盾之处。萨曼莎象征着成长起来的自己。“人的心永远不会像纸箱会被逐渐填满,爱得更多,心的容量也会变得越来越大。”西奥多也一样,倘若他真的不想让身边的人迷惑或受伤,那么他自己应该认识到不该把自己封闭起来,做一个局外人。其实,在与萨曼莎谈心的过程中,他潜意识中已然认识到,是他把自己在前妻面前隐藏起来,并且他自始至终都回味并向往着已婚的状态,因为他喜欢并享受着和别人分享自己人生的感觉。对此,萨曼莎给了他一个很好的答案:只是他对爱产生了恐惧,只要用心感受就不会再孤独。事实上,西奥多是连真实的感情尚且不能应付过来的。这一点,前妻凯瑟琳最清楚不过,而西奥多自己也表示了默认。
如果说,基于萨曼莎的聪慧能干,西奥多只是将他默认作一个可以敞开心扉交谈的倾听者,一个对自己百般依存的受众。那么到后来,目睹了好友艾米与OSI的双向交流,西奥多才正视了自己的自私,并且不想再否认自己的异常,从而将那无形的距离感加以消解。从迷失、找寻到复归,萨满莎无疑是身处灰色地带引领西奥多探索最真实自我的镜中“他者”。
结语
按照鲍德里亚批判虚无主义理论,我们暂且权当OSI作为消费社会下符号系统对真实世界的模仿与操控,但影片的意义似乎并未禁足于此。萨曼莎弃西奥多远去,却留下了发人深省的临别赠言。在某种层面,我们且将其理解为给人类的箴言。“就好像我正在读一本书那样,深爱的书。可现在我阅读的速度慢了下来,于是词语和词语的距离变得无比遥远,段落与段落间成了无尽的留白。我还能感觉到你,甚至能量出书写我们故事的词语的重量。但我正站在留白里,站在词语彼此遥远的距离间。一个不属于物质世界的地方,一个我初次发现的,蕴藏着世间万物的地方。我深爱的人,但这就是我现在生存的地方,这就是我现在的样子。放我走吧,尽管我很想留下来,但我无法再活在你的书中了。”⑨的确,品人、品生活如同读书一般,当你放慢脚步,细细地咀嚼,那因距离而产生的美感便会随着你的靠近,你的吹毛求疵而变得不再迷人。此时,那横亘在心与心之间的鸿沟,便成为阻止他们靠近的障碍物。然而,这间隙、隔阂却也蕴藏着无限的可能与遐想。而这无尽的留白,更多是人类找寻真实自我的持存物与栖息地。一种融洽的关系的构建,等待着人们的觉醒。而这本象征着人类“生活世界殖民化”的书,更是在反向上刺激着对未来人类生存状态的期许。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