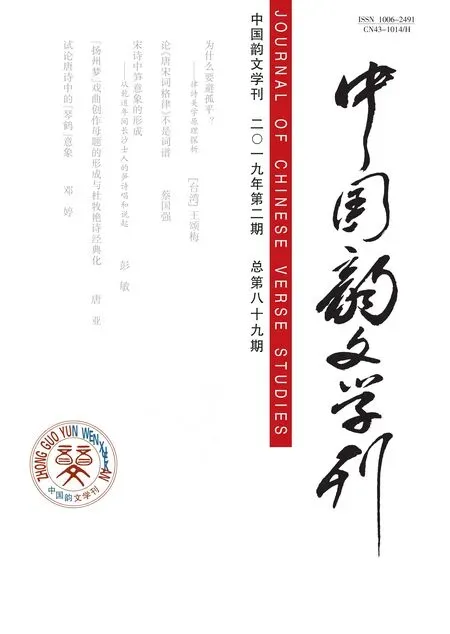“诗余”谫论
2019-11-13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北碚 400715)
“诗余”一词自宋代出现以来,就与词学的发展产生了紧密联系,明清时期的评论家对其内涵作了多方面的阐发,今人对此已有相当充分的梳理与分析。但在这一论题中,似乎仍有几处模糊的认识还有待于强调或澄清,笔者不揣谫陋,试作讨论。
一 宋人对“诗余”的体认
随着词体创作的兴盛,各类论词之语也频频见诸载籍。唐末五代至北宋,世人称“词”为曲子、乐府、长短句、小词等,“诗余”一词尚未见使用;时人对这一新兴文体(艺术形式)以及其与前代诗歌的异同,也还没有自觉的体认,这是一种新文体在起步成长阶段的正常遭遇。尽管如此,苏轼、黄庭坚等人都发表过一些词为诗人余技、诗歌绪余的言论,这通常被视作是“诗余”的渊源。到了南宋时期,《草堂诗余》和《樵隐诗余》的出现,可说是“宋人用‘诗余’这个名词的年代最早者”,施蛰存先生的这一说法基本代表了学界的共识。
《草堂诗余》是南宋书坊编的一部词选。传世文献中,王楙的《野客丛书》最早记录了该选,依据《野客丛书》的成书时间及现存《草堂诗余》的入选篇目,今人推定该选为“南宋孝宗、光宗年间(1188—1202)坊间无名氏所编,何士信在理宗淳祐九年(1249)之后增修编订”。这一结论大体可信。而《樵隐诗余》之名见于乾道二年(1166)王木叔的《题樵隐词》,由此看来,宋人用“诗余”的最早例证应为《樵隐诗余》;但又有学者举邓肃《西江月》“流莺夜转诗余”句与仲并《浪淘沙令》“草圣与诗余”句为证,认为“‘诗余’最早作为单独的词语出现,应在南宋初绍兴二年或之前。这比现时所知最早以‘诗余’作书名的情况(《樵隐诗余》[1166]),约早三十多年”。对于这种看法,有必要加以辨析。
先看邓肃《西江月》的下片:“玉笋轻笼乐句,流莺夜转诗余。酒酣风劲露凝珠。我欲骖鸾归去。”词写一次听曲的经历,“玉笋”二句对仗,“乐句”指歌伎所用的拍板,“诗余”意谓歌曲、小词,可以视为一个“单独的词语”,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语典,源出苏轼的“微词宛转,盖诗之裔”(《祭张子野文》)、“张子野诗笔老妙,歌词乃其余技耳”(《题张子野诗集后》)和黄庭坚的“嬉弄于乐府之余,而寓以诗人句法”(《小山词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诗余”,更像是“诗之余”的简写,它虽然是“词语”,却没有实际而稳固的内涵,它只是一个临时组合,而非专指某种文学体裁。
再看仲并《浪淘沙令》上片:“草圣与诗余。清韵谁如。生绡团扇倩谁书。月湛素华天似水,深院凉初。”详味词意,“草圣”与“诗余”对举,“草圣”即草书,“诗余”则是指绘画,故云“生绡团扇倩谁书”;释祖可《书秦处度所作松石》中“怜君作诗自无敌,游戏诗余画成癖”句可为旁证。“诗余”即“诗之余事”,绘画则是诸多余事之一,也就是苏轼《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所说的“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仲并词中的“诗余”与词体无关,反而说明了其自身内涵的不确定性。
“诗余”从一种泛称,到成为词体之别名,这一过程持续至宋元之际,前辈学者对此已有敏锐的观察,施蛰存曾“怀疑南宋时人并不以‘诗余’为文学形式的名词”,王炎《松窗丑镜序》就证实了这种怀疑:
三山郑中卿来宰婺源,……中卿始出平日所著示某,其别有六:一梅隐、二哦松、三南游、四北辕、五经论、六诗余,而总目为《松窗丑镜》。……至我朝有宋,文有欧、苏,古律诗有黄豫章,四六有王金陵,长短句有晏、贺、秦、晁,于是宋之文掩迹乎汉唐之文。……予得《丑镜》阅之,议论以意胜,诗以格胜,词以韵胜。
这段话交待了《松窗丑镜》的编排分类,“梅隐”“哦松”“南游”“北辕”“经论”皆无关乎体裁,“诗余”放在最末,没有明显的体裁标识意味。分类时以“诗余”为目,下文却说“长短句有晏、贺、秦、晁”“词以韵胜”;在王炎的观念中,“诗余”与长短句、词应该仍有不同,所以他才会自觉地进行区分,不会混淆使用。与此可作对照的是王炎的另一篇《绿净文集序》:“《绿净文集》,族伯父万载丞所著也。古律诗四十、诗颂三、偈一、表笺十有七、书二、序二、述一、墓表一、乐语一、长短句一,厘为上中下三卷。”《绿净文集》是按体裁分类的,长短句与古律诗、书、墓表等并列,因为它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体裁的稳定的名称。
在另外的一些例子中,我们也可看出,时人似乎对“诗余”与词体的其他名称(长短句、乐府、词)的使用场合有意识地进行了区分,即使在所谓的“词集名称”中已经含有“诗余”,也不例外。王木叔《题樵隐词》:“樵隐诗余一卷,……或病其诗文视乐府颇不逮。”楼钥《求定斋诗余序》:“平日游戏为长短句甚多,深得唐人风韵,其得意处,虽杂之《花间》《香奁》集中未易辨也。……(吾兄)读书博而能精,属文丽而有体,长短句特诗之余,又尚多遗者,此何足以见兄之所存耶。”在二序正文的表述中,都没有使用“诗余”。又如魏庆之的诗话类编《诗人玉屑》,其末卷标目为“诗余”,与“禅林、方外、闺秀、灵异”并列,但在《诗人玉屑》全书中,“诗余”一词从未出现。这些应该能说明,“诗余”南宋前中期只有分类标识的功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体裁名词。就此而言,说“诗余”是乾道、淳熙年间“流行的一个新名词”,“‘诗余’一词,以词集名称出现,大概流行于南宋孝宗乾道初至理宗淳祐末(约1166-1249)之间”,皆容易让人误解,仿佛那时的“诗余”,作为词体之别名,已是一个广受认可的新概念。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于所选词人名下多有点评,其中提及词别集、总集共11种,用“诗余”者仅《履斋诗余》一例,词人小传中频繁称词、乐府、乐章等,未见“诗余”。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词曲类”著录词别集、总集共123种,以“诗余”名集者仅5种。可以想见,在更早的孝宗、光宗年间,词集命名用“诗余”者必然极为罕见。因此,我们不难推知,“草堂诗余”的出现应该是一个相当特别的个案,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草堂诗余》得名之因——自然会再次引起我们的兴趣。
二 《草堂诗余》之得名
关于《草堂诗余》得名之因,目前已知的共有三种说法。第一种也是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见于杨慎《词品序》,其他两种皆由当代学者提出。先来检讨一下杨慎的说法,其《词品序》云:
昔宋人选填词曰《草堂诗余》。其曰“草堂”者,太白诗名《草堂集》,见郑樵《书目》。太白本蜀人,而草堂在蜀,怀故国之意也。曰“诗余”者,《忆秦娥》《菩萨蛮》二首为诗之余,而百代词曲之祖也。今士林多传其书,而昧其名,故于余所著《词品》首著之云。
杨慎的说法很快得到了周复俊更详细的解释:“唐人长短句,宋人谓之填词,实诗之余也。今所行《草堂诗余》是也。或问:诗余何以系于草堂也?曰:按梁简文帝草堂传云,汝南周颙昔经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怀,乃于钟山雷次宗学馆立寺,因名草堂,亦号山茨,谓草为茨,亦述蜀语地名,别有蚕茨,是其旁证也。李太白客游于外,有怀故乡,故以草堂名其诗集。诗余之系于草堂,指太白也。太白作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则今之填词,非草堂之诗余而何。放此选蜀志之词,以太白二阕为首云。”杨慎论诗崇尚六朝,论词则强调“风华情致”的本色,他把《草堂诗余》与李白联系起来,就能建立起一个“六朝诗歌——李白诗(草堂集)——李白诗之余(《忆秦娥》《菩萨蛮》;词曲之祖、草堂诗之余)——《草堂诗余》(宋词)”的词史统序。《草堂诗余》是“宋人选填词”,在决定明人的词学认知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杨慎的话实有溯源与正体的双重作用。但这种说法能否成立,关键在于宋人对“草堂”以及李白词史地位的认识;从这两个层面观察,杨慎之说很值得怀疑。
首先,李白诗集确曾名《草堂集》,李阳冰《草堂集序》可以为证,可惜这篇序文没有交代“草堂”的涵义。李阳冰编辑的这个《草堂集》在北宋可能仍有流传,但不显于世,而宋人在整理李白著作时,都没有沿用“草堂”这一名词,宋人著述中也未见以“草堂”代指李白者,这说明李白与“草堂”的关系在宋代渐趋疏远。杨慎是蜀人,褒扬李白甚勤,在他那里理所当然的思路,放在宋人的语境中可能就不合时宜了。
其次,《忆秦娥》《菩萨蛮》为“百代词曲之祖”的说法首见于黄昇的《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是词史上对李白二词地位的首次认定,有着特殊的背景。宋人在描述词史进程时,常常认为词体继中晚唐诗而兴:
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至唐末,遂因其声之长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变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
陆游《长短句序》:雅正之乐微,乃有郑卫之音。……千余年后,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
王炎《双溪诗余自序》:今之长短句,盖乐府曲之苗裔也。古律诗至晚唐衰矣,而长短句尤为清脆,如幺弦孤韵,使人属耳不厌也。
赵以夫《虚斋乐府序》:唐以诗鸣者千余家,词自《花间集》外不多见,而慢词尤不多。
杨冠卿《群公乐府序》:乐府之作盛于唐,自温庭筠而下,或者置而不论。
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可见当时很少有人会把盛唐诗与词体之兴关联,他们也不关心李白二词的重要性,特别是李之仪,虽然他有一首《忆秦娥》“用李白韵”,但在回顾词史时完全忽略了李白的位置;而即便宋人谈到李白,说的也是他的其它作品。如朱翌《猗觉竂杂记》卷上:“古无长短句,但歌诗耳,今毛诗是也。唐此风犹在,明皇时,李太白进木芍药《清平调》亦是七言四句诗。”沈括《梦溪笔谈》卷五:“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此格虽云自王涯始,然贞元、元和之间,为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阳沽酒宝钗空’之句,云是李白所制,然李白集中有《清平乐》词四首,独欠是诗。”张镃《梅溪词序》:“自变体以来,司花傍辇之嘲,沉香亭北之咏,至与人主相友善。”等等。
我们知道,《忆秦娥》首见于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菩萨蛮》首见于文莹《湘山野录》,二作在被发现时,其作者就有疑问,李白的著作权为宋人认可尚需时日。《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之前的各选本,选及唐人者,要么编定的时间太早,李白二词未现人世,如《花间集》;要么是分类编排,体现不出词史观念,如《草堂诗余》,所以二词的词史地位也没有机会表彰。而《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以人为序,黄昇安排李白居首,并说二词是“百代词曲之祖”,显然有为词史溯源的意图,同时也是在纠正时人普遍以词体接续中晚唐诗的做法,将词体之兴与盛唐大诗人关联,确有独到眼光。至于《草堂诗余》,其前集分春景、夏景、秋景、冬景四类,后集分节序、天文、地理、人物、人事、饮馔器用、花禽七类。《忆秦娥》是“秋景”类第二首,位列赵元稹《满江红》之后,《菩萨蛮》位于“人事”类第四首,前有韦庄、李后主、周美成词各一首。从这种编排体例来看,《草堂诗余》的编者根本不可能有明确的词史源流意识,命名词集时更不会有《忆秦娥》《菩萨蛮》是“百代词曲之祖”的觉悟。杨慎的解释诚然高明,但也只能是后来者的一厢情愿而已。
关于《草堂诗余》得名之因的第二种说法,是认为草堂“泛指隐逸山林者的茅屋庐舍”,“《草堂诗余》一选既以南宋江湖词坛为背景,为主要选源之一,并客观地折射出江湖词人的审美观念,那么,以‘草堂’名集,实际上就是山林隐逸的意思,就是江湖的意思,《草堂诗余》就是《江湖诗余》,就是《隐逸诗余》,是陈起之前数十年词坛上的另一部《江湖集》”。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其实也存在疑问。今日所见元明刊本《草堂诗余》俱非其初刊时的原貌,后人对该选之篇目不但有“新增”“新添”,还有删削,如王楙《野客丛书》提到的《满江红》,还有史铸《百菊集谱》提到的《鹧鸪天》,都不见于今传本,因而,根据入选篇目来推测该选的审美观念,有简单化的嫌疑。另外,“草堂”一词确实较为常见,在宋人的诗文著述中,多数是“泛指隐逸山林者的茅屋庐舍”,有时也用来指修建过草堂的诗人如杜甫。但和“诗余”连用,则应该取后一种情况,也即“草堂”是一种确指。因为“诗余”在宋人词集名中的出现遵从了一种“通例”——“个人的词集虽题曰‘诗余’,其前面必有一个代表作者的别号或斋名。词选集有《草堂诗余》《群公诗余》,‘草堂’指李白,‘群公’则指许多作者,也都是有主名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笔者翻检了大量的南宋词学文献,确实未见反证。在这种情况下,“某某诗余”,往往就是“某某诗之余”,诗、余二字在涵义上可以不连属,“诗∕余”前的主名也必然是有具体内涵的作者名。而上面引述的第二种说法,实际上是基于“草堂∕诗余”而解释的,“草堂”也不是作者,而是对某一类“诗余”抽象特点的说明;衡之以宋人对“诗余”的认识以及当时词集命名的习惯,是很难成立的。
关于《草堂诗余》得名之因的第三种说法,是认为《草堂诗余》出现于南宋,词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尊体的意识也进一步加强,此时杜甫的地位如日中天,“如果把‘草堂’二字和杜甫挂上钩,以见出词乃诗坛正宗之余,当然也就没有轻视的必要,因而也能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判断”。相对来说,这最后一种说法,具有更多的合理性。
如前所述,在宋人的词集命名习惯中,“草堂”应该是某作者的代称,相比于李白,这个作者更可能是杜甫。《草堂诗余》出现的南宋前期,“草堂”与李白早已渐行渐远,而当时正是杜甫地位尊隆之时,“草堂”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杜甫的代称,“草堂诗”也就是杜甫诗。略引几则例证如下:
刘应时《读放翁剑南集》:少陵先生赴奉天,乌帽麻鞋见天子。……蜀人至今亦好事,翠珉盛刻草堂诗。
王质《和袁丞海棠》:海棠不入草堂手,(自注:见韩子苍诗。)雪堂乃与同春风。(自注:见苏子瞻诗。)
王迈《读诚斋新酒歌仍效其体》:古来作酒称杜康,作诗只说杜草堂。
高斯得《次韵戴石屏见寄》:投老安蓬户,平生似草堂。(自注:戴诗颇近子美。)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学林新编》:元祐中胡资政知成都,作《草堂先生碑序》曰:“蜀乱,先生下荆渚,泝沅湘,上衡山,卒于耒阳。”
李昴英《吴荜门杜诗九发序》:草堂诗,名辈商评尽矣,反复备论为一书者盖鲜。
“草堂先生”已经成了杜甫的专属,故《锦绣万花谷》卷三十一在罗列“古人称号”时云:“青莲居士(李白)、骑鲸仙人(同白)、锦袍仙(同上,又谪仙);浣花翁、草堂先生、杜陵老翁(并杜)。”由此可知,南宋人但凡说到“草堂”,首先想到的应是杜甫,而非李白;“草堂诗”如非泛指,即是杜甫诗。能够对此补充说明的是,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四所录皆为论杜资料,而这一卷标目是“草堂”,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十四征引过一部《杜草堂事实》,赵子栎编有《杜工部草堂诗年谱》,影响更大的则有蔡梦弼编著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和《杜工部草堂诗话》。
结合《草堂诗余》编订的时代背景,说它在命名时有意要攀附杜甫,恐非无的放矢之言,但笔者以为这种攀附也许不是出于“尊体”的考虑,而只是一种书商吸引读者的营销策略。当然,杜甫没有词作传世,但这与“诗之余”的观念不算是完全矛盾,而书商们也不会为这类困扰今天的我们的疑点而较真。值得注意的是,《草堂诗余》之名与当时已编刊的《谪仙集》隐然对应,这或更可说明,该词选应是书商跟风运作的产物。吴昌绶说《草堂诗余》“出坊肆人手,故命名不伦”,这种不是解释的解释,虽然有点令人失望,但却可能更接近事实。
三 “宋无诗”说与明人对“诗余”的阐释
如果说“诗余”在宋代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体概念,那这种情况到了明代已得到根本改观,“诗余”作为词体别称,已被广泛接纳。“‘诗余’作为独立的词之别名而畅行于词坛大概是明代张綖《诗余图谱》出现以后的事。张綖此书可看作一个转机。但其根本原因恐怕得归于《草堂诗余》一书的风行。”鉴于《草堂诗余》在明代词学中无可撼动的地位,考察“诗余”一词的接受,自然会对它另眼相看,事实上,在“草堂”系列选本的序跋评论中,关于“诗余”内涵的阐发相对来说也更集中。然而,除此之外,明人对“诗余”的接受是否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呢?当我们将视线放宽到诗学领域时,对这个问题也许会看得更全面。
明代诗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整体上有一股强烈的崇唐贬宋思潮,其中的“宋无诗”说看似偏激,却又有着相当多的支持者。早在明初,刘崧就认为,诗歌“列而为大历,降而为晚唐,愈变而愈下,迨夫宋则不足征矣”,此后的诗坛名家,从李东阳,到李梦阳、何景明,都极度贬低宋诗。同时,这股思潮又与元明两代流行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论息息相关。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论的雏形是“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虞集云:“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乐府。”此类言论在元、明时期已相当普遍。既然唐诗是“绝艺”,是高峰,那唐以后之诗自然就盛极而衰,不足道哉了。胡应麟说:“诗至于唐而格备,至于绝而体穷。故宋人不得不变而为词,元人不得不变而为曲。词胜而诗亡矣,曲胜而词亦亡矣。”这种文体递降的论调在当时颇为流行,许当世《白雪斋选订乐府吴骚合编》云:“吾阅宋之今律,非无律也,不及唐也。唐无选,非无选也,选不及晋魏也。汉无骚,非无骚也,骚不及屈宋也……唐之续选与骚,又何必不在律也?则选与律,一骚也。词者,律与选之余也,曲者,词之变也。以盛国之曲踵宋之词,世推宋词元曲,良非虚语。”也就是在这种思路中,词体继唐诗而兴,其优缺点就无法切断与唐诗的联系,于是“诗余”就成了“唐诗之余”,只不过,对“余”的理解会有不同。
胡应麟有着浓厚的“诗本位”观念,卑视词体的他,从诗词递降的角度否定了这种文学史的演化;但浏览明人的论词资料,我们发现,还有另一条与胡氏相对的肯定的线索。前文曾述及,宋人追溯词体之兴时,通常以词继晚唐诗,这种看法被明人接了过来。陈耀文《花草粹编叙》:“诗盛于唐,而衰于晚叶,至夫词调独妙绝无伦。”李谨《新刊草堂诗余引》:“(诗)衰颓至于唐季,而诗余之变渐盛,至宋则又极焉。”在这种背景下,诗余逐渐成为唐诗在没落后的转世替身,尽管其长短句的形体与齐言体有些差别;并以此处处与宋诗相对照,反衬出后者“非诗”。范文英《诗余醉序》云:“诗余者,余焉耳。余者,天地之尽气也。……唐人出,回以大雅之首,情无不剖,体无不备。于初盛为极,至中晚而靡,故其世衰。《香奁》虽艳,尚未离本调也。至宋则理多情寡,论多调寡,诗之一道无复存者。而人心中精华要渺之所存,遂旁溢于词。”因而,时人对宋诗缺点的抨击,就在客观上激发出“诗余”的阐释潜能。李梦阳《缶音序》:
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絃。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者也。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流动情思,故其气柔厚,其声悠扬,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也。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
这段话指出了唐诗优于宋诗的两个特点。一是唐调可歌咏,可被管弦;二是唐诗多比兴,不避风云月露。幸运的是,虽然宋诗不可歌,多理语,但作为唐诗之余的词,却能很好地继承唐诗的优点。
关于前者,与李梦阳大约同时的另一诗坛复古派谢榛有更清晰的表达:“唐人歌诗,如唱曲子,可以协丝簧,谐音节。晚唐格卑,声调犹在。及宋柳耆卿、周美成辈出,能为一代新声,诗与词为二物,是以宋诗不入弦歌也。”有的学者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从合乐的角度,将唐诗、宋词、元曲贯穿起来,这既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说提供了学理根据,又为晚出的词、曲二体正名,可谓一举两得。王肯堂云:“夫诗,乐章也,歌之而比于八音以成节奏者也。三百篇之歌失而后有汉魏,汉魏之歌失而后有《选》,《选》之歌失而后有唐,唐之歌失而后有小词,则宋之小词,宋之真诗也。小词之歌失而后有曲,则元之曲,元之真诗也。若夫宋元之诗,吾不谓之诗矣。非为其不唐也,为其不可歌也。”王象晋在其《重刻诗余图谱序》中,也强调诗歌“被之管弦”“可讽可咏”的本质,正是因为“元声本之天地,至情发之人心,音韵合之宫商,格调协之风会,风会一流,音响随易”,所以“宋之填词即宋之诗”,“诗亡而后有乐府,乐府亡而后有诗余。诗余者,乐府之派别而后世歌曲之开先也”。诗、词、曲三者,本质上具有相通性。俞彦《爰园词话》对“诗余”的解释也正是从此着眼:“词何以名‘诗余’?诗亡然后词作,故曰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也。词亡然后南北曲作,非词亡,所以歌咏词者亡也。谓诗余兴而乐府亡,南北曲兴而诗余亡者,否也。”
关于后者,即批判宋诗多理语,是与明代诗坛流行的主情论相表里的。在明人的二元对立思维中,情、理于诗中难以并存,而要想完美地抒发性情,则不免要借助于对风云月露的比兴式创作。唐诗以此风神蕴藉,垂范后世,而诗余亦擅言情,完全可以胜任唐诗的衣钵传人,沈际飞《诗余四集序》就道破了这一点:“词吸三唐以前之液,孕胜国以后之胎。……诗余之传,非传诗也,传情也。”而在“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制”观念的支配下,钱允治感叹诗、词、曲之递降,曰:“词者,诗之余也,词兴而诗亡,诗非亡也,事理填塞、情景两伤者也;曲者,词之余也,曲盛而词泯,词非泯也,雕琢太过,旨趣反蚀者也。”周永年的《艳雪集原序》更把“情”与比兴结合:“夫情则上溯风雅,下沿词曲,莫不缘以为准。若绮靡两字以为诗法,则其病必至巧,累于理,僭以为诗余法,则其妙更在。情生于文,故诗余之为物,本缘情之旨,而极绮靡之变者也。从来诗与诗余亦时离时合。……大都唐之词,则诗之裔,而宋之词,则曲之祖。唐诗主情兴,故词与诗合,宋诗主事理,故词与诗离。士不深于比兴之义,音律之用,而但长短其诗句以命之曰词,徒见其不知变耳。”从抒发性情的角度而言,诗、词、曲也可以贯通起来,冯梦祯曰:“词曲本诗余,诗余本唐人之诗,唐人之诗本汉魏古选,汉魏古选本三百篇,虽曰愈趋愈下,其为宣达性情、古今雅俗,一也。”周珽曰:“由三百而骚、而古、而近绝、而诗余,世递变而脉递长,总之发乎性情,止乎礼义,不外一诗旨也。故唐之诗余,即乐府之变,实为宋元开山。”这类表述也许用意各有侧重,但不约而同地,它们都无视了宋诗的存在。从诗到诗余,再到词余,在这个大韵文的谱系中,“余”的存在,在使“真诗”一脉相传的同时,也遮蔽了唐后之诗,宋后之词。
最后来看明末云间词派领袖陈子龙的两段词序:
《三子诗余序》:诗余始于唐末,而婉畅秾逸,极于北宋。然斯时也,并律诗亦亡。是则诗余者,匪独庄士之所当疾,抑亦风人之所宜戒也。然亦有不可废者。夫风骚之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托于闺襜之际。
《王介人诗余序》: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免于有情也,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可及。
陈子龙的文学思想也属复古一系,对李梦阳也比较推崇,但和李梦阳相比,他的词体创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并且对词学有着自觉反思。上引两段序文中,他抹倒宋诗以突出诗余言情的特点,其“言情之作,必托于闺襜之际”正好对应了李梦阳所说的“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其“言理而不言情”正好对应了李梦阳所说的“宋人主理,作理语”。如此看来,他对诗余特性的阐释其实就是“宋无诗”说在词学领域内的自然延伸。
四 结语
“诗余”一直被当作词体的别称,也是词学界在探讨诗词关系时给予重点关注的一个概念,但如果我们回到宋代的语境,就会发现,从“诗之余”到“诗余”的过程是相当漫长的。在南宋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在当时绝大多数提及“诗余”的文献里,它还只具有文集分类标识的作用;认清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理解《草堂诗余》的得名至关重要。“草堂诗余”不是简单地“草堂+诗余”,它的命名必须符合宋人使用“诗余”的通例。在“草堂”与杜甫关系密切的时代,“草堂诗余”这一名称的出现更可能是书商攀附名人的营销策略使然;它与李白无关,与词选的实际内容也无关。到了明代,具有文体意义的“诗余”已被广泛接受,其流行之时,正值诗坛极端复古论甚嚣尘上。在“宋无诗”说的刺激下,明人将“诗余”理解成“唐诗之余”,以词体接续唐诗。此举一方面验证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判断,客观上提高了词体地位;另一方面则发掘了词体合乐、言情的正面价值,都具有独特的词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