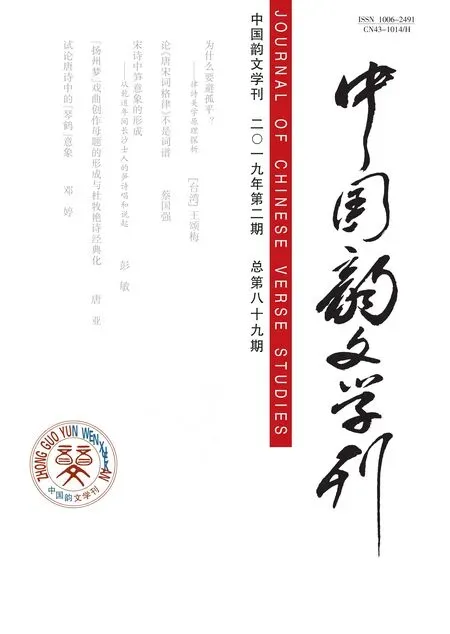“扬州梦”戏曲创作母题的形成与杜牧艳诗经典化
2019-11-13
(贵州民族大学 图书馆,贵州 贵阳 550025)
“扬州梦”一词源出杜牧《遣怀》诗,诗云“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占得青楼薄幸名。”晚唐五代笔记中出现了不少杜牧的冶游轶事,这些轶事被看作是如《遣怀》等艳诗的“本事”而广为流传,后世对这些本事或辗转相抄,或模拟化用,或渲染附会,“扬州梦”逐渐形成文学史上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典故,附着于“扬州梦”故事的杜牧艳诗也随之被经典化。“扬州梦”是一个在诗文词曲中通用的典故,但由于其产生之初就与故事相生相伴,所以戏曲中对“扬州梦”的反复演绎最具典型性。“扬州梦”主题由于其相关本事的传奇性、广泛的知名度和心理情感之于古代文人的普适性使其成为了传统戏曲中特有的创作母题,具有艺术原型的意义。杜牧本人也由于戏曲的反复演绎使其风流才子甚至轻薄文人的文学形象深入人心,在其艳诗得以经典化的同时也对其真实历史形象造成了遮蔽,使得杜牧本人及其部分诗歌遭受了长久的误解。这可能是杜牧诗歌经典化过程中有得也有失的一面。
一 “扬州梦”本事来源:晚唐五代出现的杜牧冶游轶事
后世“扬州梦”主题戏曲中的基本创作单位主要来自于三则杜牧冶游轶事,这类戏曲的剧情都是由这些轶事加工、改编、扩容、串联而来。追根溯源,杜牧这三则冶游轶事在晚唐五代笔记中就已经出现了。一则是杜牧在扬州牛僧孺幕中供职时颇好宴游的故事(后文简称“扬州轶事”),源出《太平广记》卷第六第二百七十三引高彦休《唐阙史》:
唐中书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笔成咏。弱冠擢进士第,复捷制科。牧少隽,性疏野放荡。虽为检刻,而不能自禁。会丞相牛僧孺出镇扬州,辟节度掌书记。牧供职之外,唯以宴游为事。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没驰逐其间,无虚夕。复有卒三十人,易服随后,潜护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谓得计,人不知之。所至成欢,无不会意。如是且数年。及征拜侍御史,僧孺于中堂饯,因戒之曰:“以侍御史气概远驭,固当自极夷涂,然常虑风情不节,或至尊体乖和。”牧因谬曰:“某幸常自检守,不至贻尊忧耳。”僧孺笑而不答。即命侍儿,取一小书簏,对牧发之,乃街卒之密报也。凡数十百,悉曰:“某夕杜书记过某家,无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对之大惭,因泣拜致谢,而终身感焉。故僧孺之薨,牧为之志,而极言其美,报所知也。
一则是杜牧在洛阳李司徒筵席上索要歌妓紫云的故事(后文简称“紫云事”),源出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
杜为御史,分务洛阳时,李司徒罢镇闲居,声伎豪华,为当时第一。洛中名士,咸谒见之。李乃大开筵席,当时朝客高流,无不臻赴。以杜持宪,不敢邀置。杜遣座客达意,愿与斯会。李不得已,驰书。方对花独酌,亦已酣畅,闻命遽来。时会中已饮酒,女奴百余人,皆绝艺殊色。杜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亦皆回首破颜。杜又自饮三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逸,旁若无人。杜登科后,狎游饮酒,为诗曰:“落拓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情。三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后又题诗曰:“觥船一棹百分空,十载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
这则轶事中出现了杜牧的三首诗,“华堂今日绮筵开”一首题作《兵部尚书席上作》,收在《樊川别集》;“落拓江湖载酒行”一首题作《遣怀》,收在《樊川外集》,两诗最初都见于上引《本事诗》的记载。“觥船一棹百分空”一首为《题禅院》,收在《樊川文集》卷三。
另一则是杜牧与湖州女子有十年嫁娶之约的故事(后文简称“湖州轶事”),源出高彦休《唐阙史》卷上《杜舍人牧湖州》:
杜舍人再捷之后,时誉益清,物议人情,待以仙格。紫微恃才名,亦颇纵声色,尝自言有鉴裁之能。闻吴兴郡有长眉纤腰,有类神仙者,罢宛陵从事,专往观焉。使君籍甚其名,迎待颇厚。至郡旬日,继以洪饮,睨观官妓,曰:“善则善矣,未称所传也。”览私选,曰:“美则美矣,未惬所望也。”将离去,使君敬请所欲,曰:“愿泛彩舟,许人纵视,得以寓目,愚无恨焉。”使君甚悦,择日大具戏舟讴棹较捷之乐,以鲜华夸尚,得人纵观,两岸如堵。紫微则循泛肆目,竟迷所得。及暮将散,俄于曲岸见里妇携幼女,年邻小稔。紫微曰:“此奇色也。”遽命接致彩舟,欲与之语。母幼惶惧,如不自安。紫微曰:“今未必去,第存晚期耳。”遂赠罗缬一箧为质。妇人辞曰:“他人无状,恐为所累。”紫微曰:“不然。余今西航祈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来而后嫁。”遂笔于纸,盟而后别。紫微到京,常意霅上。厥后十四载,出刺湖州。之郡三日,即命搜访,女适人已三载,有子二人矣。紫微召母及嫁者诘之。其夫虑为所掠,携子而往。紫微谓曰:“且纳我贿,何食前言?”母即出留翰以示之,复曰:“待十年不至而后嫁之,三载有子二人。”紫微熟视旧札,俛首逾刻,曰:“其词也直。”因赠诗以导其志,诗曰:“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树成阴子满枝。”翌日,遍闻于好事者。
这则轶事最后出现的这首赠诗题作《叹花》,收在《樊川外集》,《全唐诗》卷五二七亦题作《怅诗》。《全唐诗》卷五二四所录《叹花》诗前三句与《唐阙史》不同,全诗为“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阴子满枝。”
上述三则文献是后世流传的杜牧扬州轶事、紫云事、湖州轶事的最初版本,后世记载都是从这里或辗转相抄,或增删改动,或添枝加叶而来。《兵部尚书席上作》和《叹花》两诗本就是在笔记小说中最先出现,后来也就一直和本事捆绑在一起流传,《遣怀》则和《赠别二首》等诗一起作为杜牧扬州轶事的注脚出现。尽管如《叹花》一诗作者或别有所托,但由于杜牧湖州轶事的广为人知,后世几乎一直将其作为《叹花》之本事来理解。这些故事其实大多有附会成分,如胡可先认为扬州轶事中提到的杜牧由牛僧孺幕吏“征拜侍御史”与杜牧生平不符,缪钺认为湖州轶事“与杜牧行迹及史事颇有舛午,且于情理亦不合也”。然而由于杜牧冶游轶事具有很大的传奇性和喜剧性,其本事的牵强附会之处并未妨碍它们的广泛传播,人们出于猎奇心理也并不十分关心轶事的真伪,反而对其津津乐道,所以“扬州梦”主题戏曲的创作自元至清历久不衰。
晚唐于邺的笔记小说《扬州梦记》记录了上述全部三则轶事,其文全同《太平广记》卷第六“杜牧”条,然《太平广记》注出高彦休《唐阙史》。由于文献资料缺乏,目前尚无法证明于邺的记载是否出现得更早,但从“扬州梦”主题戏曲的创作源流上考虑,《扬州梦记》更具关键意义。不管杜牧上述三则冶游轶事是否最先出现在《扬州梦记》中,至少于邺是第一个用“扬州梦”这个主题去统合杜牧冶游轶事的作者,尽管其中两则轶事的发生地并不在扬州。后世戏曲作家对于邺的这种处理一脉相承,“扬州梦”作为创作母题的内涵在《扬州梦记》中已初具雏形。
二 “扬州梦”戏曲的发展嬗变:创作母题的演绎和影响力
晚唐五代杜牧的冶游轶事出现后,两宋时期的诸多笔记诗话对这些轶事辗转相抄,但基本沿袭原文,记录者自己发挥的部分相当有限。从元代开始,以杜牧冶游轶事为蓝本创作的戏曲开始出现,其中以“扬州梦”为主题的戏曲主要有元代乔吉的杂剧《杜牧之诗酒扬州梦》、明代卜世臣的传奇《乞麾记》、清代嵇永仁的传奇《扬州梦》、清代黄之隽的杂剧《梦扬州》、清代陈栋的杂剧《维扬梦》等。
乔吉的杂剧《杜牧之诗酒扬州梦》共4折1楔子,演绎的是杜牧和张好好的故事。主要讲述杜牧与张好好在豫章太守张纺处相识,在扬州牛僧孺处重逢却又错过,在长安由白谦做媒终成眷属的故事。本剧虽然部分剧情发生在扬州,杜牧那场与好好席间相逢饮酒的梦也的确是在扬州所做,但此剧没有利用任何一则杜牧冶游轶事,连它牵合的《张好好诗》也并不属于杜牧艳诗。《杜牧之诗酒扬州梦》只是在抽象意义上使用了“扬州梦”这个戏曲母题,它塑造的杜牧是一个“酒病诗魔”的形象,甚至因“贪花恋酒”差点受到了朝廷的谪罚。把张好好同“扬州梦”联系到一起,是乔吉对于邺《扬州梦记》的发展,后代的“扬州梦”戏曲将同样无关于艳情的杜秋娘也放进这个主题,当是受到了乔吉这种创作思路的影响。
明代卜世臣的传奇《乞麾记》今无传本,据吕天成《曲品》著录得知此剧与杜牧艳情有关,利用了杜牧的湖州轶事和紫云事来进行创作,“发挥小杜之狂,恣情酒色,令人顿作冶游想。……小杜风流处处,其钟情髽女,注目紫云,固豪士本色。每读‘两行红粉’及‘绿叶成荫’之句,辄柔肠欲绝。今记中乃两全之,良是快事。”剧名“乞麾记”取自杜牧诗句“拟把一麾江海去”(《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应该指的是湖州轶事中杜牧为“髽女”乞守湖州的情节。本剧中“恣情酒色”的杜牧应是延续了乔吉剧中“酒病诗魔”的杜牧形象,它运用了杜牧的冶游轶事进行创作,与“扬州梦”主题的内涵之一“逸游”有所关联。但由于传本已佚,无法进一步得知其具体内容,故在此仅作介绍,下文不再讨论。
清代嵇永仁的传奇《扬州梦》共32出,是敷衍杜牧冶游轶事的戏曲中规模最大、篇幅最长、体系最完整、情节最复杂的一部作品。它不仅将于邺《扬州梦记》中的三则轶事串联编织成一个前后关联、逻辑自洽的故事,创作增添了如韩歌娘、齐小二、阴万鹗等全新人物,还将杜牧的历史形象也融入剧中,在“风流”之外着意表现了杜牧的军事才华。对杜牧这三则冶游轶事作者都做了充分的想象和展开,《水嬉》《聘鬟》《判绿》写的是湖州轶事,作者甚至将湖州轶事的主人公“幼女”直接以《叹花》中的词句命名为“绿叶”,《惊座》写的是紫云事,《筵目》《青楼》写的是扬州轶事,作者将《遣怀》一诗巧妙安排于其中,变成了“缉事人”抄录下来向牛僧孺报告杜牧流连青楼的证据。嵇氏笔下的“扬州梦”不仅仅局限于“风月情浓”,杜牧也不再只是个倚红偎翠的浪荡公子,他表现得胸襟飘逸,富有智慧和韬略,充满济世救民的政治抱负,虽然有时候也表现出陈腐的道学气息。《乞守》一出主要讲述杜牧为与紫云相会乞守湖州,然而作者却浓墨重彩地叙述了“三策”之论。“三策”之论的观点来自于杜牧的著名军事论文《罪言》,而《罪言》恰恰写于杜牧“浪游”扬州那几年,显然嵇永仁看到了“扬州梦”香艳背后的失意感。嵇永仁正是借杜牧之酒浇胸中块垒,正如周亮工在《扬州梦传奇引》中所说:“余与留山交二十年,知留山以古今文字驰骋当世,而尤留心经世有用之学,乃郁不得志。至止酒罢剑,降笔为此等,以宣泄其无端之悲夫!”“扬州梦”的核心主旨从表现风流文士的吟风弄月转移到了才人沦落的感叹,尽管嵇剧最终仍以杜牧功成名就、妻妾受封结局,然而这不过是他对自己和现实中的杜牧本人怀才不遇的心理补偿而已。嵇剧虽然对杜牧与紫云、绿叶的情事也极尽描摹,但醉翁之意不在酒。据嵇永仁《自题》:“牛僧孺相业史所不满,余独爱其待杜一段。杜参军淮南时,牛廉知狭邪事情,条满巨簏。于杜入朝,畀簏赠之,其成就人如此,杜宁不心感乎!虞仲翔云:得一人知己,可以无恨。若牛可谓知杜矣。”嵇永仁有感于牛僧孺对杜牧的知遇之恩,他在《荐友》一出特意设计了杜牧被牛僧孺破格提拔的情节,这正显示出嵇氏沉浸于和杜牧“扬州梦”相同的失意之感中对知己的渴望。“扬州梦”作为戏曲创作母题在嵇永仁手里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和丰富,此剧由于揭示出“扬州梦”背后普遍的文人心理而具有相当影响力,据载京剧中有《扬州梦》一剧,荀慧生曾演,其故事正是根据嵇剧改编。
清代黄之隽的杂剧《梦扬州》共4折,糅合了杜牧的扬州轶事和紫云事,虚构了一位名叫红雨的歌妓作为扬州轶事的女主角,基本上延续了嵇永仁之前“扬州梦”戏曲“风月情浓”的主题,没有多少新开拓。清代陈栋的杂剧《维扬梦》则以杜牧扬州轶事为基础,将杜牧的其他轶事和有关无关的人物都牵合到扬州的大背景下加以表现,虚构了人物之间的关系。比如张好好是杜牧在扬州来往甚密的“曲中第一知名女郎”,杜秋娘是好好的好姐妹,紫云是秋娘的外甥女,后来成为了牛僧孺的歌妓。杜牧在秋娘处与紫云订下三月之约,后来在牛僧孺的宴席上见到紫云便向牛索女。这显然是把杜牧湖州轶事“十年之约”的情节改造后放入了紫云事中。陈栋还将以前戏曲中没有出现过的杜牧扬州诗如《扬州三首》《赠别二首》用到了杜牧寻花问柳的情节中。此剧最值得注意的是《投笔》一出,杜牧在被幕主牛僧孺嘲讽之后做了一场噩梦,梦中家庭贫困,孩子不学无术,被冤魂索命,最后因心高气傲被赶出幕府,将“幕途恶况,一一皆尝”。本来“在牛僧孺幕府,因感知遇之情,全不以功名为念”,经此神明示意终于省悟,决定参加科考博取功名。此前《春醉》一出中杜牧友人全畅、邢怀就有做幕僚“处不士不宦之间,功名未遂,既不能学行商坐贾、仆仆马牛,惟此游幕一途,尚不失读书人本来面目。上可以交卿相,下可以肥室家”的论调,而杜牧不以为然,认为“做幕客的人”“要想白日骄人,势不得不去胁肩谄笑。除却束修正数,那一件免得鼠窃狗偷。此外种种情形,更有令人不忍出诸口者”,陈栋借杜牧之口和梦境,将做幕之辛酸一一道尽。杜牧参加科考后历官清要,与全、邢二人脱馆失势后投奔杜牧的狼狈之态形成鲜明对比,《维扬梦》剧中的“扬州梦”更带有特定时代和作者本人的色彩,剧中杜牧对往事前尘的悔恨更多是对过去安于幕僚生活的否定。
随着“扬州梦”戏曲的发展嬗变,剧情越来越枝蔓离奇,“扬州梦”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拓展,但总体看来“扬州梦”母题的核心精神变化不大,那就是浪漫风流的诗人风采、香艳氤氲的脂粉气息和委婉微妙的忏悔之情。杜牧本人“扬州梦”的关键在于“一觉”,“扬州梦”戏曲的“梦”之内容尽管各不相同,却不约而同都把重点放在了“梦醒”上。乔吉《杜牧之诗酒扬州梦》中的杜牧在罪行被赦免、好好归嫁后决定“毕罢了雪月风花,医可了游荡疏狂病”,“从今日早罢了酒病诗魔,把一觉十年间扬州梦醒,才显得翰林院台阁文章,终不负麒麟上书名画影”;嵇永仁《扬州梦》中的杜牧在因军功升官、妻妾俱封后感叹道“畅好是扬州梦醒鸳鸯福,较当初落魄江湖差免哭。更忆那惊座狂言,皆辏成了好骨肉”;陈栋《维扬梦》中的杜牧在脱离宾幕、平步青云后也感慨“并不羡威凛凛乌纱帽笼顶,也不羡韵悠悠红袖妇鸣筝。则是功勒贞珉名汗青,茶幄香浓,绣窗人静。那一件与幕途相厮称。可惜下场头再没个有意思的神灵,把千万梦人齐唤醒”。“扬州梦”戏曲中的“梦醒”导向的其实是“梦圆”,对往昔风流的否定和忏悔才造就了功名美人双收的美满结局。作者借此为杜牧圆梦,更为自己圆梦,剧中的圆满正是对现实失意的寄托和补偿。
随着“扬州梦”戏曲的演变,虽然创作母题的核心精神变化不大,但曲家敷衍出的故事距历史上的真实杜牧是越来越远,戏曲中的杜牧已然成为了文学形象意义上的杜牧。由于戏曲具备强大的传播效应,无疑使杜牧风流才子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附会在轶事上的艳诗也随之声名远播,历久不衰。艳诗随着杜牧文学形象的生成而经典化,杜牧的历史形象却随之被混淆,这是“扬州梦”戏曲的历代演绎所带来的两个截然相反的效应。
三 杜牧艳诗:本事“二度创作”造就的文学经典
唐诗经典通过发现人而被大众接受,而发现人对唐诗经典的筛选主要通过选本、诗话、笔记和论诗杂著等四种途径来完成。笔记多记载诗坛掌故、诗歌本事和诗人轶闻等,这些内容由于缺乏理论价值一般不受重视,却是唐诗经典形成的重要途径之一。杜牧艳诗的主要经典化途径就是诗歌本事。杜牧艳诗的本事具有传奇性和趣味性,本身对读者就有巨大吸引力,加之历代“扬州梦”戏曲的反复演绎和夸大渲染,使其不论在普通大众还是精英读者中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被本事所附着的艳诗也随之声名大震,成为了文人自命风流的典型话语:
珠帘十里城南道,肯作当年小杜看。
(陈师道《席上劝客酒》)
风雨唤人归去好,免教街吏报平安。
(陈师道《城南夜归寄赵大夫》)
紫云有语君知否,莫唤分司御史来。
(苏轼《闻李公择饮傅国博家大醉二首》)
紫云莫厌频来客,未抵当年御史狂。
(韩元吉《秋雨新霁过赵慎中留饮》)
歌短旧情长,重来惊鬓霜。怅绿阴,青子成双。
(尹涣《唐多令·苕溪有牧之之感》)
今日临邛负弩迎,可还杜牧寻春否?
(袁枚《送裘叔度同年归觐》)
将艳诗置于杜牧经典诗作中看,艳诗本身的经典品质不算突出,如果没有后来诗歌本事的出现,杜牧艳诗或许就淹没于杜牧众多诗歌中而不会被经典化,甚至不能引人注目。正是因为诗歌本事给了杜牧艳诗特定的诠释角度,这种角度得到的理解正好暗合了封建文人普遍的心理诉求,在共鸣心理之驱使下杜牧艳诗和本事被不断演绎,最终形成了以“扬州梦”为代表的表达文人风流潇洒又宦途失意的经典艺术母题。“扬州梦”能够得到封建文人的普遍心理认同是必然的:这里面既包含着才子们对诗酒风流的向往,又有文士们普遍遭遇的怀才不遇的慨叹和功名无成的悔恨,更有人类永恒的人生如梦、往事如烟的感受。从经典化途径的角度看,杜牧艳诗得以经典化或许是偶然的,但从艺术情感的角度看,艳诗连同本事形成“扬州梦”母题进而被经典化又带有某种必然性。
尽管艳诗本身的经典品质放在杜牧经典诗作中不算突出,但如果将其置于晚唐艳诗创作的大背景下,杜牧艳诗就体现出不同流俗的独创性。不同于元白艳诗的浅切淫靡,也不同于李商隐艳诗的缠绵悱恻,杜牧艳诗无意于表现男欢女爱本身,而是更多地带有高门贵公子的风流自赏、男儿的豪侠纵情而别有怀抱。不同于元白艳诗对齐梁宫体的继承而着眼于女子眉眼服饰的描写,杜牧艳诗带有强烈的雅化色彩,他往往着眼于女性风姿情韵的展现,用绝妙的比喻和新颖的构思从虚处传神,给人无穷美感而无半点轻薄之意。比如“豆蔻梢头二月初”(《赠别二首(其一)》),用比喻将少女之美描绘得清丽脱俗;再比如“绿叶成阴子满枝”(《叹花》),用开花结果暗示心仪女子已结婚生子,显得文雅而含蓄。杜牧艳诗的核心精神在于对“名士风流”的向往和展现,正如学者刘青海所说:“读他的冶游七绝,关于某一次情感际遇唯有一些零星的印象,而杜牧本身风流不羁的形象却极为鲜明。这少年是如此自信,盼顾之际,风流自赏之态可掬。”杜牧艳诗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更多地是借写浪迹青楼寄托自己不遇的感慨和对世俗礼法的蔑视,正如葛晓音先生对《遣怀》和《念昔游三首》的评价:“可见在这十年里,杜牧心头翻腾的是暴雨般为国立功的热情,这就是他那‘青楼薄幸之句’中的风骨,也是他的风情诗高出于元、白之处。”另外,杜牧艳诗的强烈抒情性和七绝歌调性质又给它奠定了易于传诵的基础。由此可见,杜牧艳诗的经典化虽是靠着本事的推波助澜,但它本身的优秀品质更是不容忽视。本事起到的是将艳诗从茫茫诗海中挑选出来的作用,而杜牧艳诗最终能得到广泛认可,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雅俗共赏的品质。
冶游轶事在将杜牧艳诗经典化的同时也对杜牧真实的历史形象产生了遮蔽。由于风流韵事和“扬州梦”戏曲的广泛流播,杜牧风流才子甚至是轻薄文人的形象在后人心中牢不可破,这种印象甚至影响到了人们对杜牧诗歌创作的认知。“杜牧之诗只知有绮罗脂粉”、“作诗多言闺帏之事”的评价代不绝书,虽然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杜牧诗主体的艳情之作在《樊川文集》中其实是凤毛麟角,且多出现在外、别集中。宋人田昼也曾写诗讥讽杜牧“弟病兄孤失所依,当时画语最堪悲。岂面乞得南州牧,却恨寻春去较迟”,蔡正孙点评“此诗正以讥牧之放肆之过也”。清人姚莹就对这种普遍存在的误解颇为不满,他说:“十里扬州落魄时,春风豆蔻写相思。谁从绛蜡银筝底,别识谈兵杜牧之!”他感叹大家都只看到风流浪荡的杜牧,谁又了解那个热衷于谈兵论政、忧国忧民、满怀经邦济世理想的杜牧呢?尽管有不少古人像明代何良俊那样通过廓清误解认识了真实的杜牧,也有不少古人对杜牧所谓的风流韵事嗤之以鼻,但艳诗盛名对杜牧诗歌创作的实际成就和杜牧本人真实形象的遮蔽之大是显而易见的。冶游轶事的流传和“二度创作”使杜牧艳诗声名大噪,杜牧的确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讨论,但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这或许是杜牧诗歌经典化历程中有得也有失的那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