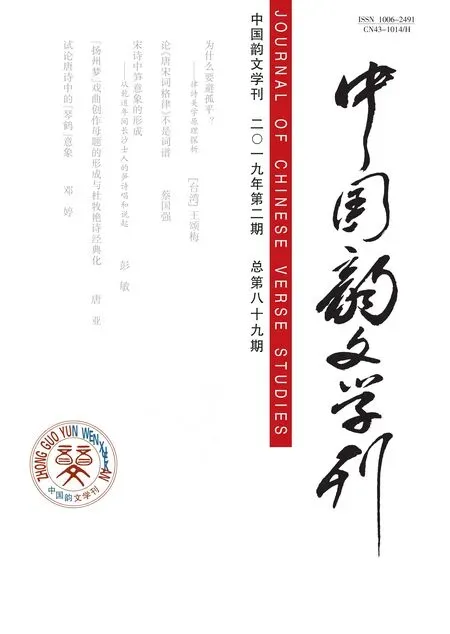民国报刊所涉辛弃疾接受之新变及意义
2019-11-13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辛弃疾以其传奇人生、杰出才干和旷世佳作千百年来赢得了一代代读者的喜爱。1874年,郑瑞清发表《摸鱼儿·饯春用稼轩春晚韵》,辛弃疾的名字第一次登上报刊,拉开了报刊上接受辛弃疾的序幕。进入民国,有关辛弃疾的专著、论文层出不穷,报刊作为新媒介在其研究和接受方面厥功甚伟。此期由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人对辛弃疾的鼓吹声势过大,导致当今学界对这些名家的成果关注度高、利用率大。相对而言,报刊上颇具价值的文献资料反被忽视,诸多看点和亮点隐而不彰,辛弃疾的整体研究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本文重点观照民国报刊上的辛弃疾研究,同时兼顾普及性文章在辛弃疾接受方面的贡献,以期揭橥此期辛弃疾研究的热点、新变及学术意义。
一 民国报刊所涉辛弃疾接受的“热点”
民国时期的报刊种类繁多、风起云涌。值报刊这种新媒介鸿运当头之时,传教士、政治家、企业家纷纷染指,文人、学者亦不甘寂寞,相继撰文立说、传播文化。据初步统计,与辛弃疾有关的文章约有200多篇。涉及作家的年谱传记、生平思想、作品分析等研究内容,墓志铭、词集版本、序跋、书评、图书介绍等宣传文章。其热点主要集中在辛弃疾的相关考证、生平研究和作品品鉴等方面。
第一,辛弃疾的相关考证。民国报刊上有关作家的考证主要是交游考。邓广铭的《辛稼轩交游考》从辛弃疾词集、辛启泰的辑词、辛弃疾诗集、文抄、宋史稼轩传、其他书传等六大方面入手,考证出与辛弃疾交游者共195人,第一次充分而全面地呈现了辛弃疾的“朋友圈”。他的《稼轩词笺证(感皇恩)》一文,考证两首《感皇恩》皆为寿范邦彦而作,词题中的范倅同为一人,修正了《稼轩交游考》中的相关论述。
辛词的考证,主要以词作互见考、系年考和辑佚为主。首先,是词作互见考。唐圭璋“宋词互见考”中有7篇涉及辛词。其中,辛弃疾与朱敦儒互见的《鹧鸪天(天上人间酒最尊)》《鹧鸪天(有个仙人捧玉卮)》、与刘过互见的《西江月(堂上谋臣帷幄)》、与张孝祥互见的《菩萨蛮(东风约略欠罗幕)》四首皆非辛词;与陆游互见的《恋绣衾(长夜偏冷添被儿)》《恋绣衾(病来自是于春懒)》、与姚进道互见的《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三首当属辛词。其次,是词作系年。关于辛词《念奴娇·书东流村壁》的创作时间,梁启超《稼轩先生年谱》定于“四十八岁以前”;梁启勋《稼轩词疏证》定于“二十三岁以前”;梁品如驳斥了二人观点,认为前者“失之含混”、后者“失之过早”,应为“三十七岁所作”,较为合理。最后,是辛词的补辑。周泳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辛弃疾词《好事近·西湖》一篇,为学界普遍接受。
此外还有版本考。此期版本研究,收获有二:一是发现了毛抄四卷本。光绪末年,张元济从涵芬楼中见到汲古阁毛晋精抄本“稼轩词”甲乙丙三集,疑有丁集存世。民国年间,经赵万里指示,得以重金购得。随后,夏敬观、潘景郑、顾廷龙等人索览、展开研究。张元济《毛抄稼轩词甲乙丙丁集跋(一)》和夏敬观《毛抄稼轩词甲乙丙丁集跋(二)》二文力证四卷本优于十二卷本,今人多从其说。二是对四卷本与长沙本关系,有不同意见。梁启超《跋四卷本稼轩词》认为《稼轩词》在宋有三刻,除四卷本及十二卷本外,另有长沙一卷本。赵万里《馆藏善本书提要:辛稼轩词四卷(宋辛弃疾撰抄本)》持同样看法。邓广铭先生《书诸家跋四卷本〈稼轩词〉后》予以驳正,认为此四卷本即长沙本,现存各本虽优劣互殊,究其本源均不出四卷本及十二卷本。
第二,辛弃疾的生平研究。辛弃疾是伟大的爱国志士,又是杰出的思想家、军事家、词人,他丰富的经历、传奇的人生,令后世无限仰慕,也让学者们产生了极大的研究兴趣。民国报刊所涉辛弃疾生平研究集中在年谱、传记、人格研究三项。
民国时期掀起了编撰辛弃疾年谱的热潮。自清嘉庆年间辛启泰为辛弃疾首撰年谱后,民国学者为辛弃疾编撰的年谱达6本之多,作者依次是熊光周、梁启超、龙榆生、陈思、郑骞、邓广铭。其中,载于报刊上的就有熊光周、陈思二种。虽然刘咸炘评价熊著“凡轶事足以见其人者皆录入,于朝野杂记得其年月,于本传南归年十三逆推得其生年,居然首尾完具,较之况夔笙所编《白石年谱》生卒无考者,详备多矣”,但除了邓广铭集大成者,其他皆“勇于臆测,疏于寻证”。邓著年谱出版之后,又陆续补充修订,其《辛稼轩晚年的降官和叙复》一文,就开禧元年(1205)三月稼轩“坐谬举降朝散大夫”一事发覆,探明稼轩晚年又叙复了朝议大夫,前后几道制命皆出蔡幼学的手笔。
民国学者还热衷于为辛弃疾作传。这些传记在内容上颇多重复,都津津乐道如下事件:追杀义端、手擒张安国、建“飞虎军”、江西赈济、死后削爵、追赠“忠愍”等,而充满爱国色彩和政治热情则是其共同特点。尤其是1930年以后,辛传完全成为了时代的传声筒。诸作中,标明为传记而影响较大者有三种,分别是:吴世昌的《辛弃疾(传记)》、陈福熙的《辛弃疾评传》和徐嘉瑞的《辛稼轩评传》。吴世昌的《辛弃疾(传记)》,共分十七个标题,从“楔子”开始止于“酒醉的笑话”,以若干故事连缀起词人一生的经历。文章先从天安门前的石狮子写起,写它见证着这个民族被“统治着,压迫着,欺骗着,宰割着”,辛弃疾就是这样的石狮子。吴传有一些其他传记没有的亮点,如辛弃疾的恋爱故事、辛弃疾与朱熹之间微妙的人际交往等。陈福熙的《辛弃疾评传》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叙述辛弃疾生平、第二、三部分串讲辛词、第四部分同情词人并介绍辛词版本。文章以“在今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积极侵略之下,国势之危,当不亚于南宋,幸抗战以还,举国上下,莫不抱着‘抗战到底’的决心,作前仆后继的准备;然而,做汉奸的依然很多,如果我们再不来揭发他们丑恶罪状,足以危害抗战前途,一朝人心皆死,国家不亡而亡”煞尾。该文发表在《战时中学生》,有明确的针对性。徐嘉瑞的《辛稼轩评传》将辛弃疾的生平分为三个阶段,认为“辛稼轩的生活,实在是一幕悲剧”。徐传偏于辛弃疾政治思想的解读,特别是主战思想的介绍,对词人作品几乎不予涉及。徐传1946年又在文通书局出版,《图书季刊》当年刊发的书评曰:“不但不见有何新意,即前人研究心得,徐君似亦忽略之;对研究辛氏最要之资料——辛氏本人之词集,徐君似亦无深刻之认识也。”三种传记中,吴传文字优美、可读性强、水平最高;陈传采用一般文学史的写法,传递知识时重在爱国教育;徐传最为拉杂,可读性差,不类传记,更像政论文。总之,三篇传记皆以古鉴今,呼应着时代的需求。
关于辛弃疾的人格,民国学者也颇多发挥。民国学者虽然高呼辛弃疾的爱国精神,但也极力烘托他人性化的一面。于是,关于辛弃疾,他兼有了北方人和南方人的双重气质,刘咸炘《稼轩词说》说他“秉北人之刚质,染南人之柔风。所作长短句,慷慨豪宕,幽约怨断,兼擅其长”。他还拥有四种品质,却是一个悲剧人物。祝世德《爱国词人辛弃疾》说:“以一个性格勇敢,负责,廉洁而豪爽的人,却生在一个外则强寇压境内则因循苟安讲和误国的时代中,这痛苦不言可想——那便是弃疾一生的悲剧了。”针对清人沈谦评价《祝英台近·晚春》“昵狎温柔,魂销意尽。才人伎俩,真不可测”,胡云翼反驳道:“这有什么不可测?唯大英雄乃大情痴。”除了“情痴”,伴雪说他是一位多愁善感富于热情的文人,一位浪漫不羁的风流文人。郑枢俊说他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怪杰”,但又是“爱好自然的雅士”。总之,辛弃疾人格、思想、情感的多样性,民国学者心领神会。
第三,辛弃疾的作品品鉴。辛弃疾诗、文、词兼有,可惜此期的研究热点只在词上。诗文的研究相对较少。有人把施仲言《南宋民族诗人陆放翁辛幼安之诗歌分析》一文看成是辛诗研究的发轫之作,那是受了题目的误导。其实,该文采用了广义的诗的概念,比较陆、辛差别时以陆诗比辛词,重点还在词上。赵璧《南宋爱国词人辛稼轩》一文顺带提到诗歌:“他也写过许多的诗,但是传下来的不多,诗中也有着和他词中一样的豪迈之气。”邓广铭《辛稼轩集中误收秦桧诗》一文,辩证《御赐阁额》二首乃秦桧之诗非辛弃疾之诗,系辛启泰从《永乐大典》中辑佚所致。辛弃疾文的研究,以王易《读稼轩文感书》最早,是一篇辛文的选登。王易说辛弃疾具有“御侮,整军,救灾,平政”诸伟绩,而今日的中国“东省具坏,瓯缺于先;淞沪近畿,鱼烂于后”,遂摘录《美芹十论》《九议》《淳熙乙亥论盗贼札子》《淳熙乙未登对札子》中的17则“俾当世览者藉为殷鉴,亦尚友之道而观物之方也”。该文的贡献在于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章中发掘出这四篇文章的价值,尤其是政治、军事价值,并给予初步介绍和高度评价。邓广铭《关于辛稼轩的〈美芹十论〉》用五条证据证明《美芹十论》的著作权属于辛弃疾,而非南宋黄兑,对辛文研究大有裨益。
较之诗文研究的死水微澜,辛词的研究可谓风生水起。其时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辛词的内容、风格、艺术等,大致有三种情况。其一,个别学者对辛词的特质予以抉发。如田非《词人辛弃疾》认为“他的生活是兼有伟大和兴味二者的特点,所以在他的作品里就包含有构成波澜重叠的生活之一切要素”。缪钺《论辛稼轩词》认为:辛词恒给人双重印象,于豪壮之中又有沉吟、蕴藉、空灵、缠绵调剂,故能跻于浑融深美之境,而这与作家的才学和修养有关。其二,有些学者针对部分辛词进行专业鉴赏。龙榆生整理沈曾植的遗稿《稼轩长短句小笺》,标志着对辛词单篇笺释的开始。俞陛云发表“宋词选释”,对31首辛词进行了鉴赏。唐圭璋的《辛稼轩词释》,依次鉴赏了《贺新郎(绿树听鹈鴂)》《念奴娇(野棠花落)》《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永遇乐(千古江山)》《祝英台近(宝钗分)》《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汉宫春(春已归来)》8首辛词,除最后一首外,前7首收入后来出版的《唐宋词简释》一书,成为经典。唐先生的鉴赏能抓住词旨要害、点明篇章结构、揭示艺术精髓,文字虽简,却能以少胜多。其三,大量学者将辛弃疾与其他高尚文人进行比较,各抒己见。如张少孙《陆游和辛弃疾》一文,认为南宋诗以陆游为代表、南宋词以辛弃疾为代表,一直到他们的产生,中国才有真正的民族文学作品、真正的民族文学家。履泽《辛稼轩和瞿稼轩》一文,从辛弃疾和瞿式耜同号“稼轩”入手,漫谈他们有四点相似之处:乱世的英雄、前进的思想、志勇杀敌的战士和照耀文坛的明星。辛弃疾追慕陶渊明,郑骞《辛稼轩与陶渊明》说:“辛之于陶,遥遥相契,莫逆于心。他已从性情生活中,深切体会到陶诗的风味。”周幼农说陶渊明是辛弃疾理想上最高的人物,惟二人心境有广狭之异、个性有刚柔之差,辛弃疾虽极力想做陶渊明,而仍不似陶渊明。
新文学运动以来,白话文渐成主流,但旧体诗词并未消歇,民国报刊上登载的大量古诗文及仿效之作就是明证。辛词也概莫能外,普及之作俯拾皆是,其类型有三。一是登载辛词。政治色彩浓厚的报刊尤喜登载辛词,如《前途》1934年刊发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黑白》1935年刊发的《清平乐·贺韩侂冑》、《挺进(长沙)》1936年刊发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诗以寄之(词)》等等。当然,也有不迎合时局而迎合刊物者,如《佛学月刊》1941年就刊发了辛词中反映佛教思想的一首《浪淘沙(山寺夜半闻钟)》,说明辛词在当时的普及并不局限于某一类型,而具开放性。二是步韵辛词。辛词数量居两宋词人词作之冠,民国人写词常步韵辛词。如陈配德《金缕曲·用稼轩同甫唱和韵送龙教授榆生赴粤》步《贺新郎(把酒长亭说)》之韵。辛词原为送别:陈同甫拜访辛弃疾,同游鹅湖,分别之后,辛弃疾又追至鹭鹚林,不遇,遂写词以寄。后来,陈同甫唱和,辛弃疾再和,同甫三和,如此往复。陈配德此次送词学专家龙榆生赴粤,俨然把自己比作同姓的陈同甫,把龙教授比作了词坛上的辛弃疾,故以辛词为范本,次韵以寄,追步古人,诚为佳话。此外,詹安泰的《水龙吟(感旧用稼轩登建康赏心亭韵)》、杨彦的《念奴娇(潘叔玑先生命赋金陵怀古用稼轩野塘花落韵)》等,都是此制。步韵之作是民国旧体文学的组成部分,为传播辛词做出了贡献。三是集句辛词。民国人喜欢集辛词创造出新形式的作品,如黄濬贺胡适四十岁生日时集的对联:“刘伶元自有贤妻,乍可停杯强吃饭;郑贾正应求腐鼠,看来持献可无言。”其中“腐鼠”二字原为“死鼠”,“看来”二字原为“肯来”,集句时都做了改动。登载、步韵、集句,这些不同种类的转换之作,皆赋予了辛词新的生命,使其继续传播,造福当代。
二 民国报刊所涉辛弃疾接受的新变
民国时期的大动荡、大变局与此期发达、便利的报刊事业相交织,在辛弃疾的研究和接受方面鼓荡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别样的文化景观。接受者不再局限在传统官员、文人与儒生之间,而一变为大学教授、文学爱好者、学生和普通民众。接受形式也不限于词体一项,而开始向其他文体渗透。受西方文化影响,辛词开始被翻译成英文,而传统的热门话题“苏辛比较”开始了现代转型。国人救国情绪的高涨又为辛弃疾平添了多重身份,“爱国词人”“民族词人”“英雄词人”“国防词人”等头衔频扑纸上。这些皆是辛弃疾“民国化”的产物,是此期辛弃疾接受的新变。
首先,辛弃疾接受主体普及化,接受文体多样化。就接受主体而言,批评家、作家、读者皆是此期辛弃疾的接受者。其中,大学教授是一个引人瞩目的群体。其时执教于燕京大学的顾随、郑骞,杭州大学的储皖峰,之江大学的夏承焘,重庆中央大学的唐圭璋,暨南大学的龙榆生,北京大学的赵万里、邓广铭,国立武昌大学的胡云翼等人,既是辛词的爱好者,又是辛词的研究者。这一时期,青年学生作为新的接受群体也登上了历史舞台,针对他们的刊物如《青年界》《小学与社会》《苏中月刊》《新苗(北平)》《战时中学生》《金科中学年刊》《中国青年(重庆)》等,皆刊发过涉及辛弃疾的文章。其中《青年界》发文最多,学术价值最高;《中国青年(重庆)》规格最高,登载过蒋介石、陈诚等人的文章,政治性强。《新苗(北平)》是大学校刊,《金科中学年刊》是中学校刊。《苏中月刊》和《战时中学生》是中学生刊物,《小学与社会》是小学教育刊物。可以说,这一时期涉及辛弃疾的文章覆盖了从小学到大学,从少年到青年的各种刊物。就接受形式而言,除了以诗词的形式学习、追和辛词以表达仰慕之情,如白毫子《鼓枻词:霜天晓角·和辛稼轩》、倪瑞江《读稼轩词有感》等等,还以通俗小说、书画、翻译等形式进行再创造,扩大辛弃疾的传播与影响。如连载于《玄黄朔望刊》上的通俗小说《南烬窃愤录:徽钦二帝蒙尘被虐日记》,署名为“宋辛弃疾著,华亭孙世英铨次编校”,实为孙世英改编《南烬纪实》而来,并依照原书托名为辛弃疾。獭啼猿馆主《江上涕洟录》第一回《江山信美千秋沉痛稼轩词,日月重光万里归来丁令鹤》以辛词《永遇乐》开场,虽非杰出的小说,也使辛弃疾从古典走向了现代。熊秉三根据辛词《太常引(一轮秋影转金波)》创作了国画,并题词画上,使辛弃疾的生命力不仅留在了词中,还活在了画里。在外来文化影响下,这时出现了辛词的翻译之作,最早被翻译成英文的是《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标志着辛词开始走向“国际化”。
其次,“苏辛比较”开始了现代转型。“苏辛比较”是传统辛弃疾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受西方学术影响,此期的“苏辛比较”在形式上实现了印象式评点向规范化学术研究的转型,内容则更深入新颖。突破之处大致有三。其一,肯定苏辛同为杰出词人,但认为辛弃疾的爱国精神和人生经历使其超越了苏轼。介西说“他的生活,比东坡还要丰富。所以,他的艺术的创造性,无疑的,也要比东坡充实”,庄桥说“苏轼只能及得弃疾的豪放的气概,还没有他那种洋溢于字里行间的热情万斛的爱国心”。其二,客观分析苏辛艺术上的差异,不分轩轾高低。张鹤群《论苏辛词之异同》认为:风格上,东坡豪旷凌放,复有清逸潇洒韶秀叙舒,稼轩则雄壮悲凉沉着痛快;艺术上,东坡写物取神,稼轩写物托意,东坡常就景以叙情,稼轩则即事以叙景,东坡赋情不能作悲壮哀艳之言,稼轩亦不能作清丽婉雅之辞,东坡词往往不协词律,稼轩喜多用事。其三,力证词史上存在一个苏辛词派,并抉发该派的文学特征。龙榆生《苏辛词派之渊源流变(上)》认为苏辛词派,在情境上“以歌词抒写热情怀抱,慷慨淋漓”,在修辞上“但求气骨之高骞,不斤斤于雕琢字面,且不为一般所谓精艳字面所囿”,在声律上“渐与音乐脱离”,正因“有此三种特征,乃得建立宗派”。苏辛比较,始于南宋,清代周济、谢章铤、陈廷焯、况周颐等人皆有评说。此期学人对苏辛比较再三致意,既跟进了清代学术,又吸纳了新方法、新思路。从浮光掠影式的片言点评,到注重理论的长篇大论,辛词的比较研究实现了现代转型。
最后,肯定辛弃疾是一位“爱国词人”“民族词人”“英雄词人”“国防词人”。辛弃疾当弱宋末造,以气节自许、以功业自负,一腔忠愤,不可尽展,遂付之于词,而其词又特能振起人心,故民国学者皆以辛弃疾为时代偶像和宣传对象,大肆宣扬他的爱国精神。白桦《南宋爱国词人》说:“南宋第一个时期最伟大的爱国词人,不,中国全部的词史上最伟大的爱国词人是侠骨豪情才华盖世的辛弃疾。”董启俊《辛弃疾及其民族文学》说稼轩之前,词坛上那些“依红偎翠”之作因缺乏生命力而不能代表整个民族的灵魂,豪放词只有到了稼轩才集大成者,“他的壮词,足以惊动二三千年来死气沉沉中华民族的灵魂。他的词正好比午夜的警笛,黎明的晨钟,他的一字一句,犹如一枝一枝的吗啡针,使人由此得到兴奋,觉悟,鼓舞,而去找求民族奋斗之路”。赵东原《民族词人辛弃疾诞生八百年纪念》认为:“辛弃疾不只是一个气象雄伟、才华盖世的大词家,而更是一个为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而贡献其毕生心力来从事斗争的伟大的战士。”“自由和解放”是当时的流行语,作者用在辛弃疾身上,恰恰说明辛弃疾在当时具有唤起民族斗争精神的意义。罗先高《英雄词人辛弃疾》阐发了“英雄词人”的内涵:“他不仅是一位大词人,而且是一位大英雄,唯因其有丰富的战场生活,天天经历在出生入死的斗争中,自然所写出的词是非常豪迈壮烈……所以以他生活的经历,情怀的豪放,国事的衰乱,更加以郁郁的不得志,因之他的作品是‘词中有英雄,英雄来写词’呢!”四种称呼中,“国防词人”比较特别,只出现了1次,后来也鲜有人用,在当时却应运而生。凌沅祥《国防词人辛弃疾》说辛弃疾是一个敢作敢为、极不平凡的国防词人,文末呼吁:“现在国事日非,不减当年的南宋,愿我知识分子,急起效法前人,提倡伟大的‘国防文学’!”辛弃疾四种身份的出现是民国化的必然产物,反映了民国人眼中的辛弃疾,开拓了辛弃疾研究的新视野。
三 民国报刊所涉辛弃疾接受的意义
民国时期的辛弃疾研究相对于传统研究具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成果大多发表在报刊上,从而与报刊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报刊参与并引导了辛词的大众普及,学者对报刊的诉求又促成了学术专刊的诞生。凭借着《词学季刊》等一大批报刊,此期的辛词研究取得了质和量的双重繁荣,且打下鲜明的民国印记。对这些论文进行梳理和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正是本文选择民国报刊文章作为观照对象的原因所在。
首先,透过民国报刊所涉辛弃疾接受情况,可了解民国语境下的辛弃疾研究。纵观这一时期的辛词研究,突出的特点是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高扬。尤其是1930年以后,随着抗战的爆发,国人救国情绪高涨,纷纷以辛弃疾精神救世。也是从此时开始,辛弃疾被冠以“爱国词人”等诸多头衔,实现了与时代的接轨。像“国防词人”这种称呼,此前闻所未闻,深深地打上了民国文化的烙印,是辛弃疾“民国化”的一种外在表现。而辛弃疾的“民国化”又折射出当时人的文艺思想、审美追求和心灵世界。梁品如《稼轩词研究》写道:“吾于稼轩词作有系统之研究,自‘九一八’始,以此后国势,酷似南宋之局,旷世相感,益觉稼轩之亲切也,吾述稼轩词之作风,技术,品藻,源流,纪事,辩证,版本,竟而国难愈深国势愈弱,吾百感交集,百忧填膺,吾欲无言,然又乌能无一言?”可谓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呐喊!民国学者与辛弃疾的隔空对话、心灵交流,根本上还是在与时代对话、与自己交流。就此而言,此期的辛弃疾研究更是民国学者“心灵史”的一部分,是民国学者心灵的外化。从研究报刊上的辛弃疾开始,到探索辛弃疾与时代的关系,再到揭示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辛弃疾的“民国化”意义深远、值得重视!
其次,梳理民国报刊所涉辛弃疾研究论文,可填补辛弃疾接受史研究的不足。辛词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慷慨纵横之外,兼有清丽妩媚,又能自铸新语、檃括前人作品,故南宋以来,始终是词家研究的一大热门,相继推出的学术论著颇为可观。目前,关于辛弃疾的资料汇编和总结性论述已有若干成果,如辛更儒的《辛弃疾研究资料汇编》、张毅的《宋代文学研究》、程继红的《辛弃疾接受史研究》、朱丽霞的《清代辛稼轩接受史》《20世纪辛弃疾研究的回顾与思索》等,都对不同时期辛弃疾接受的资料进了整理和介绍,具有导夫先路的作用。但这些研究成果或不收民国、或妄顾报刊,致使这部分内容成为研究中的短板。不可否认,这部分内容中,普及之作占很大比重,学术价值不高、内容重复者也不在少数,因其反映了民国时期辛弃疾接受的客观现象,对今天的研究也不无启发,故对待这些文献,不可视而不见、束之高阁,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最后,解读民国报刊所涉辛弃疾研究特点,可为同期其他文人研究提供借鉴。朱丽霞女士曾言:“辛稼轩已经具有了超越时空的经典意义。他总是拥有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研究者,引起他们连绵不断的文化怀念,形成了一部以审美陶冶、理性阐释和创作滋养为内容的稼轩接受史,并一直延伸到今天。”事实上,涉及审美陶冶、理性阐释和创作滋养的文学接受又岂止辛弃疾一人,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其他作家。辛弃疾作为个案研究中的一个点,处在整个民国文学史的版图之上,与他同为爱国作家的还有岳飞、陆游、姜夔、文天祥等人,与他同为豪放作家的还有苏东坡、张孝祥、张元干、刘过等人,他们皆进入了民国学者的视域。只有将点连成线、将线合为面,才能对整个民国文学的全貌一览无余,才能对此期的文学接受做出更准确、更客观的判断。处在词学研究的腹心地带和爱国词人与豪放词人的交汇点上,辛弃疾的典范价值对其他词人研究具有辐射作用。通过梳理辛弃疾相关文献,可为古代其他作家的接受史研究提供方法论上的启示。
综观民国报刊上所涉辛弃疾接受文章,无论是研究观念、方法或成果,皆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时编订的词人年谱、笺释的词集文本、采用的研究方法,皆奠定了此后的研究格局。这些文章继承了传统治学经验,又开现代学术研究之先河,其历史功绩永垂不朽!曹辛华先生说:“全面整理与研究民国诗词学文献无论从学术意义、文化意义还是社会意义来讲都是不可小觑的。”此中矢之论。民国作为中国学术史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承前启后,意义深远。希望本文能引起学界对此期文学的重视,刷新对辛弃疾及其作品研究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