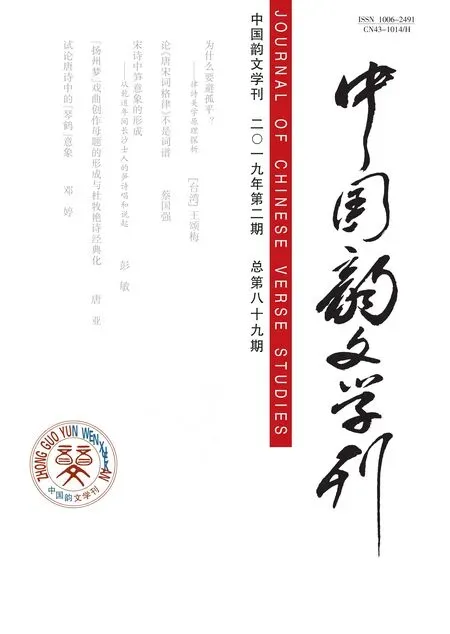意象思维的时间性:在有序和跳跃中回忆、直面和想象
——以六朝咏物诗为例
2019-11-13
(南昌师范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2)
引言
意象是构成中国诗歌的核心要素。对诗歌意象及意象思维的研究是中国诗学的重要内容。在文学自觉的汉魏六朝时期,咏物诗的兴起,无疑孕育了大量的对中国古典诗歌具有重要诗史意义的诗歌意象。六朝诗人在咏物诗的创作中,也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意象结构方法和模式。先秦以来以“比兴”为主体的意象思维和观念至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诗人在喧妍物态中解放了个体诗思,也解放了自然万物。他们以诗心巨眼观照自然风物时,不再单向度地强调其物我合一的道德人格特性,而是要在主客心物宛转、情思往还的过程中获得超越的审美体验和生命趣味。意象既是达成由语词组合到意境营造之审美境界的纽带与桥梁,又是诗人交融人情和物态的个体化生命趣味的载体。目前学界六朝咏物诗的“意象”研究仍以探究个别意象的诗史流变和文化内涵为中心,而非从诗学的角度研究意象和意象思维本身。本文以六朝咏物诗为例,通过细致分析文本,结合诗人创作的语境及心态,剖析六朝咏物诗意象思维的时间性,澄释咏物诗意象思维和结构的方法与特征,庶几对中国古代诗学的意象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一 比体咏物诗意象思维的时间性
意象思维的时间性问题是六朝诗人创作中营造意象时间模式的思维特征,此问题关系咏物诗创作思想的意象构思、营造、思维展开等诸多方面。六朝咏物诗意象思维的时间性问题在比体和赋体咏物诗中表现得尤有特色。六朝比体咏物诗是指六朝时借“物”之特征或品质来比喻人的特质,表现手法上多用比兴的咏物作品。其重心不在物象当下情态的描摹,更多的是一种与中心意象相关联的情感。这种意象思维的时间性,不仅体现于六朝前期的作品,也体现于梁陈时期的众多比体咏物诗中。
比体咏物诗的中心意象包含了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要素;在全面完整描绘物象线性时间中的情态时,突出对过去或未来中心物象情态的追忆或期盼。如梁吴均的《咏雪诗》:
雪逐春风来,过集巫山野。
澜漫虽可爱,悠扬讵堪把。
问君何所思,昔日同心者。
坐须风雪霁,相期洛城下。
全诗虽用过半的篇幅描述正逐着春风而来的飞雪,但诗人所思念的乃是昔日同心者,期盼的是未来能与其相会于洛城。诗中的“坐须”有徐俟、静待之意,指向的是即将要、行将的未形情态。因此,诗中突出的是飞雪意象晴霁的将来形态,而与故人相会的美好期盼紧密地联系起来。
诗人对中心意象当下情态的描写,突出了当下与过去、未来的情态对比,在对比中表现一种情感的矛盾,从而营造出无限的诗意氛围。如:
早知半路应相失,不如从来本独飞。
(梁·萧纲《夜望单飞雁诗》)
忆啼流膝上,烛焰落花中。
(梁·萧纲《和湘东王古意咏烛》)
人怀前岁忆,花发故年枝。
(梁·萧绎《咏梅诗》)
何时如此叶,结实复含花。
(梁·萧绎《宜男草诗》)
前三句是追忆过去中心意象所关联的故人情感,后一句是期盼中心意象——宜男草将来能“结实复含花”。无论它们在诗中的比重大小,都是诗人所要突出表达的关注点。这也是由比体咏物诗自身的比兴手法创作特点所决定的。这些诗歌都突出了当下时间“物”状态的描写,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完整的意象。但诗人情思的着力点并不在当下,而是顺着物理时间的推移,超拔当下生活的缺失,寄情于将来,并在未来的物理时间中,虚构一个情意完满的意象和境界。当下的生命矛盾,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移或变化,也可以在追忆中获得心灵的抚慰。情事与物象宛转绸缪过程隐含的是完整的线性物理时间。
六朝比体咏物诗意象思维的时间性特征表现为:第一,作品中物理空间的线性时间模式之书写方法是通过中心意象的今昔对比,突出所咏之“物”的变化,这种描写上的变化可归结为咏物诗人创作上由当下的一种失落展开对未来的图景或心中的期盼。其根本上是诗人在心中对生命历程和人类时空的不断追索和往复轮回,其指向的是生命当下的缺憾,从而在意象构造上以当下中心物象的存在形态来衬托所咏之物可能的理想状态或美好存在。第二,比体咏物诗以线性时间模式展开的是一个生命历程,这与六朝时期“感物”与 “物感”的诗学思想是相吻合的。诗人营造意象遵循自然物象的变化—诗人心理的触动—情感的波动—吟咏性情的创作过程。第三,比体咏物诗中“比”的意义,具有意象的象征性、隐喻性,从而以物的生命情态与人之生命情态形成全息式的象征隐喻系统,为意象形成稳定、系统的文化内涵奠定了基础。
二 赋体咏物诗意象思维的时间性
据笔者统计,从宋到陈,七百余首咏物诗中,对中心意象的时间描绘忽略过去与现在,而强调现在的占93.7%,这之中大部分是赋体咏物诗。赋体咏物诗是指以铺陈、描摹中心物象具体形貌为创作主旨的咏物之作。如果说比体咏物诗是要在物理时间展开生命历程,以象征和书写不同时间中的心理情态和生命节奏,其本质是音乐性的诗思呈现;那么赋体咏物诗的意象时间性则忽略过去与将来,将中心物象的时间坐标集中于“现在”的状态,以此当下状态为中心做细致和全面的描摹。因此其本质是以当下时间在空间中延展情态,是时间向空间的诗意展开。
首先,中心物象各个部分的描摹,都只为强调其当下的美好,无关于过去也无求于未来。例如:
翻阶没细草,集水间疏萍。
芳春照流雪,深夕映繁星。
(齐·王融《咏池上梨花诗》)
白水满春塘,旅雁每回翔。
唼流牵弱藻,敛翮带余霜。
群浮动轻浪,单泛逐孤光。
悬飞竟不下,乱起未成行。
刷羽同摇漾,一举还故乡。
(齐·沈约《咏湖中雁诗》)
双燕有雄雌,照日两差池。
衔花落北户,逐蝶上南枝。
桂栋本曾宿,虹梁早自窥。
愿得长如此,无令双燕离。
(梁·萧纲《双燕离》)
王融《咏池上梨花诗》用了四个不同的比喻来形容池上梨花当下的美丽,全诗不见过去的追忆,也没有诗人对未来的期盼。沈约《咏湖中雁诗》全诗十句都着力塑造了一群大雁在湖中嬉戏的情态。而萧纲《双燕离》则细致描绘了双燕的相亲相爱。如诗中提到的:“双燕有雄雌,照日两差池。”这几首赋体咏物诗虽没有明显的时间提示,但隐含了所突出的时间是现在。如萧纲《双燕离》最后一句“愿得长如此,无令双燕离”即表明所突出的不是未来而是现在——诗人表达了希望能凝固此时此刻的恩爱,而不愿时间前进。
不同于比体咏物诗纠结于过去和将来,赋体咏物诗甚至扩大了“现在”这一时间概念所占的篇幅,全诗都在描绘自然物此时此刻的美好形象。上引诗歌描绘的自然物的一切美好都是发生在当下。萧纲《双燕离》中“愿得长如此,无令双燕离”,正道出了赋物诗人的创作心理:捕捉自然物现在的美好形象,并详细描摹。
其次,赋体咏物诗这种艺术特征与诗人创作动机的不同有关。从建安到陈代,诗人群体创作咏物诗的动机,由抒发自身情志变为享受诗歌形式追求带来的欢娱和快乐。既然及时行乐弥漫了齐梁以来的诗坛,那么无论是对过去的怀念,还是对未来的期望都不再占据诗人的脑海。因而活在当下,把握所有哪怕是短暂或微小的快乐,以及触动这些快乐的举动——比如描绘眼前的美景或分享所描摹之物带给自己的愉悦的心境。在一个追求先据要路津、讲究早慧的时代,吟咏物色当下的美好形象,才是诗人最值得着墨之处。如刘孝绰《咏素蝶诗》:“随蜂绕绿蕙,避雀隐青微。映日忽争起,因风乍共归。出没花中见,参差叶际飞。芳华幸勿谢,嘉谢欲相依。”素蝶一会儿和蜂雀追逐嬉戏,一会儿在阳光下随风起舞。无论是在花中还是叶际穿插,都只不过是不同角度、不同情境下素蝶当下的美好形态。赋体咏物诗中过去、未来的时间性描述则隐没不闻。又如萧纲《赋得蔷薇诗》:“石榴珊瑚蕊,木槿悬星葩。岂如兹草丽,逢春始发花。回风舒紫萼,照日吐新芽。”诗人着力描绘“蔷薇”风和日丽下的妖娆之美时,不忘强调关键词——“逢春始发花”。花无四季红,诗人一个“始”字捕捉住了蔷薇最美好的时刻,也让我们触碰到了赋体咏物诗意象创造的时间性。
再次,除去这种注重捕捉并描绘意象的即刻美外,从诗人构思中心意象的时间所体现的思维特性来看,也存在一种由滴水不漏按顺序叙述转变为思维跳跃式、画面剪辑合成中心意象的方式。我们来看魏晋咏物诗,诗人将过去、现在、未来贯穿成一线,一般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叙述描绘,使读者能随着时间的流逝来体验中心意象的演变。如行云流水一般,诗人和读者都能按习惯和节奏表达和欣赏,不会出现六朝后期咏物诗人那种跳跃式的表达和思维特点。
如曹植《吁嗟篇》有:“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因为时间的长度本身是抽象而无形的,可穿越空间的。 这或许与他们去汉未远,并不似齐梁诗人那么求新求异的离经叛道,而是多少仍将汉赋描绘中那种需要按物象的东西南北、早晚朝夕、古往今来等等都囊括殆尽方能体现赋家之心一般。即便其中一些并非以抒情言志为创作动机的赋体咏物诗,也有这样的表现。如应瑒的《斗鸡诗》:
戚戚怀不乐,无以释劳勤。
兄弟游戏场,命驾迎众宾。
二部分曹伍,群鸡焕以陈。
双距解长绁,飞踊超敌伦。
芥羽张金距,连战何缤纷。
从朝至日夕,胜负尚未分。
专场驱众敌,刚捷逸等群。
四坐同休赞,宾主怀悦欣。
博弈非不乐,此戏世所珍。
诗人将斗鸡的缘由、经过、结果按时间顺序和事件的发展先后一线性地交待清楚。再从中心意象“鸡”来看,从斗鸡的出场照面、它们的战斗场景、鏖战难解、荣誉战胜等形态也是连贯性地展示动态美。而由于创作思想的变化,发展到齐梁咏物诗时,诗人群体在赋体咏物诗中更多地展示意象的即时状态,而且通过破坏中心意象那种行云流水的线性结构,采用一种看似无序其实更加符合形式美追求的描摹物象的写作方式。
人们观察自然“物”时总会不断地改变空间角度和距离,不仅是描摹物的静态,也观察它的动态特征和运动规律,并从中引发联想、联系,获得审美体验。诗人按上述过程积累了足够的创作体验后,逐步认识和总结前人的创作经验,并作出了适当的调整和改造。而跳跃式的剪辑和呈现,就是咏物诗人对中心意象的时间性改造的具体表现。六朝后期的咏物诗人往往围绕着中心意象,把一些看似没什么联系却表现特定情感、内容的画面,按一定的节奏、逻辑组合在一起,使其产生新的整体画面和带给他人以新的感受。比如萧绎《咏细雨诗》:“风轻不动叶,雨细未沾衣。入楼如雾上,拂马似尘飞。”这四个画面在时间上并无先后,诗人的观察视角也是随机而无规律可循。诗的中心意象——细雨,在四个并列的画面中分别扮演了轻风、细雨、薄雾与飞尘。四个表面不相关的画面的唯一联系,就是它们都在形容“雨”和它的特征“细”。又如王融《咏池上梨花》的意象构思与萧绎《咏细雨诗》相同,而大部分南朝后期的赋体咏物诗都是如此。他们不像王粲、曹植、应瑒、繁钦、张华、陆机等魏晋咏物诗人那样,在描摹自然物时似乎还附带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或物的运动轨迹叙述一个事件。而刘宋因处于咏物诗前后变化的过渡时期,所以诗人进行咏物诗创作时,虽主旨不离“中心意象”,却仍有按时间顺序叙述故事的创作风气。此类咏物作品,如鲍照的《山行见孤桐》等。六朝后期虽仍有少量寄物抒发身世之感的比体咏物诗,如沈炯《咏老马诗》等,但总体上看,诗人时间思维由线性转为跳跃性,空间视角由远及近、由宏观聚焦到局部的时候,时间的维度也从对中心物象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面描写,转变为对中心物象即时状态的集中描摹。
六朝后期咏物诗人描摹中心意象时,逐步在诗歌中淡化时间因素和顺序的叙述性,与他们对创作规律的认识后的创作思想有关。第一,当下即永恒的意象审美心理和审美观照,其思想渊源于佛教自然观的“超时空”特征。在佛教自然观超时空的世界之中,客观自然的时空规定性已被彻底打破,眼前的意象经禅心重新组合,主体心灵得以从时空的束缚中解脱,于刹那间见永恒。第二,齐梁以后的咏物诗在意象的动静、构图诸方面营造与当时重形似工美的审美风尚相关。诗人创作中存在一种按顺序叙述转变为诗思跳跃,剪辑画面合成中心意象的模式。其通过破坏中心意象营造线性模式,采用更加符合形式美追求的描摹物象的写作方式。第三,体现出一种文学创作的建筑之美。这种对物象仰观俯察的方式展现的是时间的空间延展,是以赋体铺衍的建筑韵律凝成意象逻辑时间的恒定。而其本质正是诗人借助生命空间的扩大,审美体验的空间扩张而把握道——本体与永恒的诗兴智慧。
三 六朝咏物诗意象思维的时间性与求全、求美的诗学思想
六朝咏物诗意象思维时间性特征的变化表明诗人文学思想经历了一个由求全到求美的转变过程。古人根据日月运行、日影推移等自然现象来计量时间。所以,咏物诗意象中的时间性有很多是透过空间为参照而加以表现。梁人刘孝威《咏素蝶诗》曰:“映日忽争起,因风乍共归。出没花中见,参差叶际飞。”素蝶争起那活泼、热闹的美好瞬间,是在“日头”的映衬之下。而其忽隐忽现、忽高忽低的动态之美离不开“花中”“叶际”等空间方位的衬托。需注意的是,从“忽”“乍”等字眼看,齐梁咏物诗人在以空间衬托时间过程中,有一种力求描述意象最美瞬间的创作观念。而较早期的咏物诗虽然也是通过空间作为表现时间的参照物,但显然体现了另一种创作思想——求全。如曹植《吁嗟篇》详述了“转蓬”漂泊无依、茕茕孑立之貌。从其离开本根、昼夜漂泊、遇飘风而上、忽下沉渊、终流转无恒处等整个过程。此过程可视为贯穿一个完整的时间概念——永久,即转蓬从离开本根开始就一直漂泊不定。曹植如何用空间等方位词来衬托出这一时间概念呢?如诗句有“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飘飖周八泽,连翩历五山”等。如此一个完整的的昼夜无停漂泊无依的转蓬形象,便跃然纸上。从东西到南北,由八泽至五山,诗人力图不落下任何一个场景和时刻。
通过刘孝威和曹植咏物诗对比,可以发现魏晋和南朝诗人在营造意象时,所突出的时间思维确实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咏物诗人认为意象需要通过全面、各方位地描述来表现转变为捕捉、攫取其最美的一瞬。现再例举六朝前后咏物诗句以证:
双鹤俱遨游,相失东海傍。
雄飞窜北朔,雌惊赴南湘。
(魏·曹植《诗》)
惊雷奋兮震万里,
威陵宇宙兮动四海。
六合不维兮谁能理。
(晋·傅玄《惊雷歌》)
厥初月离毕,积日遂滂沱。
(晋·傅玄《雨诗》)
缘阶已漠漠,泛水复绵绵。
微根如欲断,轻丝似更联。
长风隐细草,深堂没绮钱。
萦郁无人赠,葳蕤徒可怜。
(南齐·沈约《咏青苔诗》)
浮华齐水丽,垂彩郑都奇。
白英纷靡靡,紫实标离离。
风摇羊角树,日映鸡心枝。
谷城逾石蜜,蓬岳表仙仪。
已闻安邑美,永茂玉门垂。
(梁·萧纲《赋咏枣诗》)
风轻不动叶,雨细未沾衣。
入楼如雾上,拂马似尘飞。
(梁·萧绎《咏细雨诗》)
前三首为魏晋时期的咏物诗,如上文所述它们的时间性即因空间等参照而出,诗人以空间的全面、无遗映衬出意象时间性的完整、连贯。如傅玄《惊雷歌》用万里、四海、六合刻画了一个无处不达又时刻心怀天下的“惊雷”形象。后三首意象的时间性则更为隐蔽。如萧绎《咏细雨诗》并没有出现任何与时间相关的词汇,但这并不代中心意象没有时间性。其实,诗中以四个不同的比喻,来突显诗人只是想要表达出此刻眼前细雨带给他的审美。类似的作品还有王融《咏池上梨花》和何迅《咏春风诗》及阴铿《咏石诗》,都是利用比喻、短谜或典故多方位、多角度的表达“此刻”这个时间概念下中心意象的审美。
咏物诗意象思维时间性的变化及诗人“求全到求美”的文学思想的发展都有着深刻的背景。汉末以来,学术思想的表达由繁琐的注经解字到玄学思想影响下以少总多的清谈妙语。而文艺创作也由务求形似发展到追求神似。咏物诗作为重要的诗类之一,其创作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六朝前期构造意象似汉大赋般追求全面和完备到六朝后期追求“画龙点睛”——择取现下最美一面。可以说,从求全到求美的创作思想的变化与学术思想的演进、文学自身的发展密不可分。笔者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政治大一统局面的崩塌,影响到文人思想中从任何事物只追求“大一统”演变成“大小相通”。如晋人王弼《老子指略》曰:“然则四象不形,则大象无以畅,五音不声,则大音无以至。四象形而物无所主焉,则大象畅矣;五音声而心无所适焉,则大音至矣。”由此,包括咏物诗在内的文学创作也由汉赋那种好大求全、淋漓恢宏的唯一追求开始逐渐接受描述“小”也是不逊色于追求“大”的一种审美。那么,到了六朝后期,咏物诗意象那种覆盖整个时间长河的时间性就逐渐为尽力呈现出意象最美一刻的创作思维所替代。文人意识到“万重岭”再多,也只有“一丘”是真正的自我的空间。空间缩小了,则需融入更丰富的时间概念。陆机《文赋》提出:“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即可视为这种“由大及小、从有限透视无限”创作思想的理论表达。
第二,汉魏六朝的乱世,使得许多文人发现生命易逝。因此,没有足够的时间给他们去观察和追求那种恢宏、全面且完整的意象。朝不保夕的生存状态使得这种迁逝感在六朝咏物诗中逐渐显现,如:
俯仰岁将暮,荣曜难久恃。
(魏·曹植《杂诗》其四)
且以乐今日,其后非所知。
(魏·何晏《言志诗》其二)
兹晨自为美,当避艳阳天。
(宋·鲍照《学刘公干体诗》其一)
根叶从风浪,常恐不永植。
(南齐·谢朓《蒲生行》)
愿君早流眄,无令春草生。
(南齐·徐孝嗣《白雪歌》)
六朝时期,咏物诗意象时间性体现出的迁逝感越来越密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建安诗人仅在曹植咏物诗中发现3首出现这种时间的迁逝感。到了齐梁时期,这种比例大增。王融、谢朓、萧纲、萧绎等几乎所有咏物诗人的作品中具有这种透过意象表达对时间易逝的感受。时局复杂,诗人朝不保夕。浓郁的悲剧气氛占据了绝大多数诗人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因此,美好的时刻更显得来之不易,即便人们已经发现对美好事物的长久拥有只是奢望。《陈书·孙玚传》记载,陈后主为孙玚所题铭有云:“今时日月,宿昔绮罗。天长路远,地久云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既然天长与地久只是传说,那么诗人也渐渐发觉咏物“求全”的不切实际。因此,创作上与其耗费精力、小心谨慎的去追求毫发无遗,不如捕捉并呈现所咏之物所呈现出的最美一刻。
第三,个体意识的觉醒促发了咏物诗创作由求全到求美思想的转变。大一统政治局面和“独尊儒术”思想体系的崩塌,造成一个重要的结果——个体意识的觉醒。这种被称为“人的自觉”的思想解放,其强调和标举的是一种对抗儒法思想的任真、自然的个性及个体自由。嵇康《赠秀才入军》之十八云:“身贵名贱,荣辱何在?贵得肆志,纵心无悔。”而陶渊明《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也说:“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而在咏物诗中这种对个性解放和个体自由的呼唤更比比皆是。如:
天姿既否戾,受性又不闲。
(魏·王粲《诗》)
云间有玄鹤,抗志扬哀声。
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
岂与鹑鷃游,连翩戏中庭。
(魏·阮籍《咏怀诗》之二十一)
安得游云上,与尔同羽翼。
(南齐·谢脁《蒲生行》)
儒家、法家等思想强调的是人类社会的群体性,个人要服从集体。因此,只有国家等群体的意志和思想才有价值。这种思维特点导致在绘画和文学创作上都更加重视整体而忽视个体和闪光点。这些从现存的文艺作品都可以得到证明。那么,源于道家思想的玄学思潮影响下,诗人则普遍接受了个体的自由及个性张扬的观念。这种观念对咏物诗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意象时空的大幅收缩,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变得更加注重个体的物而非诸多物象组成的景色(山水诗创作热潮自然会过渡到咏物诗);其二,不再追求中心物象在不同时空及所有特性的全面形象,而是注重一首诗只表达一个最显著的特性或诸多姿态中最富个性的一面。
综上所述,六朝咏物诗意象时间性表达的趋势可概括为从追求时空的无限表达到自觉接受从有限中表达无限。文学创作的主流思想也从“求全”转变为“求美”。而这种思想的转型具有“大小相通”或“长短相同”“迁逝感”“个性觉醒”三个特征。
需注意的是,这个变化趋势并非是递进、直线式地向前发展。这个变化过程其实曲折而反复。笔者略述如下:
就咏物诗而言,刘宋以来追求“形似”的创作思想似乎比东晋玄学思潮影响下的作品反而更接近“求全”的文学思想。《文心雕龙·物色》曰:
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也。
文中“近代”应指刘宋以来。考之刘宋的文学创作,“描摹”景物确是当世诗歌创作的主题,也就是上文所述的“形似”“体物”“密附”等创作观念。钟嵘《诗品》亦多次出现“形似”或“巧似”等词以赞赏擅长描摹景物特别成功的诗人。当世著名的谢灵运的诗歌即可为证,其山水诗如《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等多为描述寓目所见的景物。有学者将这种寓目辄记的写法归纳为两种模式。第一联山景,第二联水景或第一联上句山景,下句水景,第二联上句山景,下句水景。这种受赋影响的诗歌创作观念似并非谢灵运个人喜好。孙宜康《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说:“结果诗赋联合成了当时诗学的一个主要特点。将它们捏合在一起的还有那个时期特殊的感觉品味——对自然界的深刻描写、精心设色、直接观照。”况且,谢灵运诗在当世被誉为“初发芙蓉,自然可爱”。谢诗如此,与其同负元嘉诗坛盛名的颜延之则为“错彩镂金,雕缋满眼”,亦是作诗求形似者。现举例证明元嘉咏物诗这种雕缋满眼的求全创作思想。
霰先集兮雪乃零,散辉素兮被檐庭。
曲室寒兮朔风厉,州陆涸兮群籁鸣。
(宋·王韶之《咏雪离合诗》)
连阴积浇灌。滂沱下霖乱。
沈云日夕昏。骤雨望朝旦。
蹊泞走兽稀。林寒鸟飞晏。
密雾冥下溪。聚云屯高岸。
野雀无所依。群鸡聚空馆。
川梁日已广。怀人邈渺漫。
徒酌相思酒。空急促明弹。
(宋·鲍照《苦雨诗》)
桐生丛石里。根孤地寒阴。
上倚崩岸势。下带洞阿深。
奔泉冬激射。雾雨夏霖浮。
未霜叶已肃。不风条自吟。
昏明积苦思。昼夜叫哀禽。
弃妾望掩泪。逐臣对抚心。
虽以慰单危。悲凉不可任。
幸愿见雕斫。为君堂上琴。
(宋·鲍照《山行见孤桐诗》)
与谢灵运同为刘宋诗坛代表的颜延之,其现存咏物诗《归鸿诗》一首和残句《白雪诗》一篇都是以全面描摹物象为主。如《归鸿诗》:“昧旦濡和风。沾露践朝晖。万有皆同春。鸿雁独辞归。相鸣去涧汜。长江发江畿。皦洁登云侣。连绵千里飞。长怀河朔路。缅与湘汉违。”
另外,何承天《君马篇》《芳树篇》《石流篇》,谢庄的《七夕夜咏牛女应制诗》、《和元日雪花应诏诗》、《瑞雪咏》(大明元年诏敕作)等诸多诗人及作品都体现出这种不避繁琐、描摹务求形似的观念。
相较而言,东晋的咏物诗反而更加简约、含蓄:
遥望山上松。隆冬不能凋。
愿想游不憩。瞻彼万仞条。
腾跃未能升。顿足俟王乔。
时哉不我与。大运所飘遥。
(晋·谢道韫《拟嵇中散咏松诗》)
灵菊植幽崖。擢颖陵寒飙。
春露不染色。秋霜不改条。
(晋·袁山松《菊诗》)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
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
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
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
(晋·陶渊明《饮酒》其八)
求全到求美创作思想的发展似乎有迹可循,却又并非固定不变。从这种创作思想嬗变的轨迹出发,我们更易理解咏物诗创作的实际。从意图经纬时空,到捕捉物象转瞬即逝的美,展示了咏物诗人意象时间观的成熟。
无论是六朝前期咏物诗中在全面描述中心意象过去、现在、未来的形态后,重点突出其某个时段的美好形态,还是六朝后期咏物诗详细地表现中心意象的“当下”状态,都“是从混整的悠久而流动的人生世相中摄取来的一刹那”,而“本是一刹那,艺术灌注了生命给它,它便成为终古,诗人在一刹那中所心领神会的,便获得一种超时间性的生命,使天下后世人能不断地去心领神会”。朱光潜上述之言阐明了咏物诗中意象时间性由全方位描绘演变为集中描写“物”的即时状况,也让我们明白时间轨迹的展示由有序转化为跳跃的原因。其实,诗人群体改变意象时间性特征的叙述模式与诗人创作思想由全面描摹中追求美变为对刹那美的重视有深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