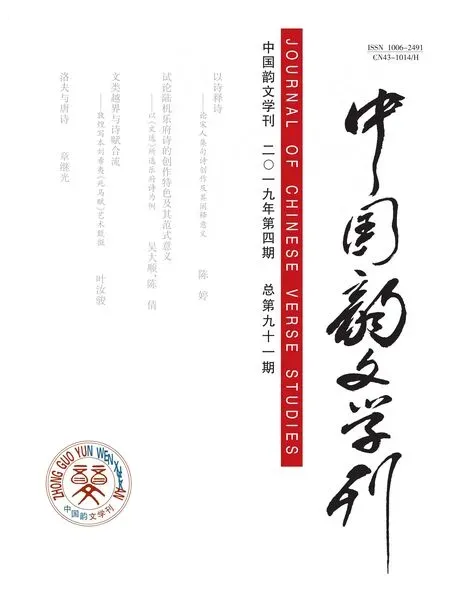文类越界与诗赋合流
——敦煌写本刘希夷《死马赋》艺术甄微
2019-11-12叶汝骏
叶汝骏
(台湾政治大学 中国文学系,台湾 台北 11605)
一 前言
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不少唐人赋作,其中许多作品不见于传世唐人别集和各类总集所载,因而具有极高的辑佚价值;其他已见载于传世别集、总集者,因敦煌残卷写本年代颇早,故而也具备了很高的校勘价值。
特别是其中一些唐代重要文士的作品由此得以辑佚或补阙,对于相关研究的推进颇有助益。譬如高适《双六头赋送李参军》各本皆失载,惟幸敦煌遗书之《高适诗集》存其篇什;又如《酒赋》不见于刘长卿别集所载,然敦煌遗书中就有多达六种唐人写本;再如本文所要研讨的刘希夷,其脍炙人口的名篇《代悲白头翁》在敦煌遗书中就有四种完整程度不一的写本,今人据以重新校订全文。至于刘希夷的《死马赋》,《文苑英华》《全唐文》《全唐诗》等传世总集俱不见载,可知此篇佚失已久,而敦煌写本的发现,对于散佚严重而今仅有三十余首作品传世的刘希夷而言,绝对是一个颇具意义的发现。
《死马赋》写本见于法人保罗·伯希和所编号之敦煌遗书3619(简称“伯3619”或“P.3619”)的卷号中,按写本原貌并辅以文意及用韵来看,首尾完整无缺。最早对《死马赋》进行整理的是著名敦煌学者王重民,其于1963年发表《补全唐诗》一文,将此篇作品校正整理并补入了《全唐诗》。随后不少学者对王重民所整理的《死马赋》进行了补正或重校,目前最新的整理成果为2011年由台湾逢甲大学唐代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编校、简宗梧与李时铭共同主编的《全唐赋》所收版本,其中《死马赋》由林聪明先生考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并进行校正。本文所用《死马赋》即采《全唐赋》订校之版本,兹录如下:
连山四望何高高。良马本代君子劳。
燕地冰坚伤冻骨,胡天霜缩落寒毛。
愿君回来乡山道。道傍青青饶美草。
鞭策寻途未敢迷,希君少留养疲老。
君其去去途未穷。悲鸣羸卧此山中。
桃花零落三春月,桂枝摧折九秋风。
昔日浮光疑曳练。常时蹑景如流电。
长楸尘暗形影遥,上兰日明踪迹遍。
汉女弹弦怨离别,楚王兴歌苦征战。
赤血霑君君不知,白骨辞君君不见。
少年驰射出幽并。高秋摇落重横行。
云中想见游龙影,月下思闻飞鹊声。
千里相思浩如失。一代英雄从此毕。
盐车垂耳不知年,妆楼画眉宁记日。
高门待封杳无期。仙桥题柱即长辞。
八骏驰名终已矣,千金买骨复何时?
关于《死马赋》的著作权问题,虽稍有疑虑,但基本可以判定归于刘希夷。敦煌残卷P.3619此篇题为“死马赋 刘希移”,学界多以“移”为“夷”之误。理由主要包括该卷接抄《死马赋》的《白头翁》与清编《全唐诗》所载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文苑英华》及宋本《乐府诗集》所载刘希夷的《白头吟》内文完全相同;又该卷所抄未题作者之《北邙篇》的内文,亦与《文苑英华》《全唐诗》所载刘希夷的《洛川怀古》相同;更显见的证据是该卷所抄之《捣衣篇》,不仅直接题署“刘希夷”,且内文与《全唐诗》载刘希夷同名篇什相同;再从韵部来看,“移”“夷”虽分属“支”“脂”二韵,然唐人此二韵通用。可知《死马赋》为刘希夷之佚作当无疑问。
由于《死马赋》长期散佚,故不为古代学者所关注。直到敦煌遗书的发现,此篇赋作才开始走入近人的视野,然如上所述,今人对《死马赋》的相关研究,基本仍处于文本整理与校订之阶段。但不可否认的是,有赖于前贤细致谨严、沾溉后学的基本文献整理工作,吾人才有立足之根基进而做出更为深入的研究。检视当前学界对《死马赋》单篇的进阶研究,似仅有台湾学者胡幼峰的《敦煌残卷刘希夷佚诗“死马赋”的写作特色》一文而已,该文从取材、章法、对比技巧、寓意这四个方面探讨了《死马赋》的写作特色。再扩大至整个刘希夷的相关研究来看,目前学界仍以《代悲白头翁》等传统名篇的研究为主,多数成果并未将散佚已久的《死马赋》纳入研究的视野,或仅在论述中轻描而过,遑论与之进行整合研究,此为当前研究现状中的主要问题之一。
问题之二则在于,《死马赋》虽明确题为“赋”,然自王重民先生将《死马赋》补入《全唐诗》后,此篇作品通常被归入了“诗”的文类,而常被视为刘希夷的佚诗而非佚赋来看待。由张锡厚先生编校的《敦煌赋汇》与《全敦煌诗》,更分别将《死马赋》视作了“赋”和“诗”,同时收入两书。事实上,《死马赋》是在敦煌遗书的“唐人选唐诗”残卷中发现的,可见也有部分唐人将其作为诗歌来看待。《死马赋》在文类界划上的这种游离、摆荡或分歧,事实上关涉到了此篇赋作的艺术特质问题。故笔者认为此一议题值得深入探讨与抉发。
二 亦赋亦诗:《死马赋》的高度诗化特质
在敦煌遗书所载的18篇不见于别集、总集的唐人赋作中,刘希夷的《死马赋》与高适的《双六头赋》与其他赋作面目不同,前贤将此二者称为“诗体赋”,又以其余为“俗赋”。这一界划虽基本不错,惟“诗体赋”和“俗赋”之对举,非基于同一逻辑层次,前者为文类概念而后者则为风格概念。但亦不得不承认,这一界划事实上十分精准地拈出了这两类赋作的不同艺术特质,刘希夷的《死马赋》与高适的《双六头赋》,正是以其独特的诗化特质,而与存留在敦煌遗书中的其他赋作鲜明地区隔开来。王重民、张锡厚等前贤之所以将《死马赋》划入“诗”的界内,亦是基于《死马赋》在艺术上与“诗”存在着难舍难分的关联。
(一)形式的诗化:通篇以整饬均齐的七言句式结撰
《死马赋》在形式上的最主要特征,在于舍辞赋之基本句式而通篇纯以诗的七言句式来结撰。通观历代辞赋,以四言和六言为其最常用的句式,此外三言句式的使用频率亦较高,此三者可称为辞赋的三种基本句式。三种句式的源头各不相同,此一点可结合辞赋的起源来考察。辞赋的起源众说纷纭,大体上与诗、骚、诸子皆有关联。《文心雕龙·诠赋》云:“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从句式的角度来看,诗、骚分别以四言和六言为基本的句式,辞赋中最常见的四言和六言句式亦分别导源于《诗》《骚》。四言和六言在辞赋中虽有不少单用之情形(如邹阳《几赋》、刘安《屏风赋》、扬雄《逐贫赋》等通篇用四言写就,王延寿《王孙赋》全篇64句中仅有一句为非六言句式),但更多的情形是互相配合来使用。刘勰《文心雕龙·章句》谓“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四言细密整饬,六言舒缓雍容,非常契合于辞赋铺陈、描述的体式特征,这种从汉赋中发展起来的四六句组配结构后来直接影响了骈文的句式结构,“四六”更成为骈文的代称(简宗梧先生称骈文是“赋体化的散文”)。但全篇若纯以四言和六言运行,则稍显单调,故而辞赋家往往引入三言、五言、七言、八言等其他句式来调节全篇语势,以造成灵动多变的审美效果,其中三言是比较多见的(尤其在早期辞赋中)。三言句式的主要来源于诸子散文,由于节奏短促紧凑,审美效果与四、六言句的舒缓曼妙不同,且三言句式往往是采用排比罗列的方式,这在汉大赋中出现频率很高,后世一些描写宏大华美题材的赋作也好用三言句式,如杜牧《阿房宫赋》以“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的三言排比句式起首,节奏峭拔,突出了阿房宫的凌厉气势。
以四、六、三言为基本的句式,再杂以五、七、八言等其他句式,这是辞赋一般的句式组配模式。而《死马赋》全篇共32句,纯以属非辞赋基本句式的七言句式来结撰,且不杂以其他任何句式,显示出其在形式上的高度诗化的现象。在以往的辞赋作品中,纯以单一句式结撰者本属少数(又以纯四言体赋为主),而纯以五、七言的诗的句式结撰者更是罕见。这里需进一步说明的是,为何七言是属于诗的句式?前文已言,辞赋以四、六言为最基本的句式,三言次之;而诗的基本句式则从先秦两汉的以四言为主转为了后世的以五、七言为主。四、五、六、七言句式之所以与某种文类产生直接的关联,这是由各种句式的美学特质所决定的。根据冯胜利的汉语韵律诗体学的相关研究,诗的基本韵律机制的两节行律,如四言为2+2、五言为2+3、七言为4+3;而六言的标准韵律结构是2+2+2,其内部结构多变,有悖于诗的两节行律,所以六言是文的句式。四言和六言是辞赋最常用的句式,四、六言的组合正是诗的句式和文的句式的组配,这也正透露出辞赋的介于诗与文之间的文类特性。其中四言既是早期诗歌的基本句式,亦可视作构成后世七言诗句的一个拍节单位,此一点也从侧面印证了古人以赋出于诗的观点,如班固《两都赋序》云:“赋者,古诗之流也。”而执行两节行律的五、七言并不是文的句式而是诗的句式;且由于《死马赋》通篇皆采用了单一的诗的七言句式,这同时又将承自六朝骈赋的句式骈俪、对仗整饬的特点也进一步强化了。
总上所言,《死马赋》的高度诗化特质,很大程度是透过诗化的形式来呈现的。《死马赋》通篇纯以整饬均齐的七言句式结撰,将原本辞赋之中那些源自诗的质性突出化、极端化了。而这种诗化特质的根源,具体则是从属于诗的七言句式之美学特质中生发出来的。此一点,也正是那一类大量运用五、七言句式的辞赋被称作“诗体赋”的主要原因。
(二)表现方式的诗化:比兴寄托的运用与抒情因素的强化
陆机《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对陆机的此一论断,学界虽有互文见义、合论诗赋的歧解,但古今主流的观点仍是以之为分论诗、赋各自的特点。“缘情”和“体物”固非某一文类的专属,然陆机将其大别为诗、赋各自之主要特点,亦是具眼之论。虽然诗之大宗“咏物诗”或能与“体物而浏亮”的特征合辙,且辞赋一体从源头来看,本亦就有“辞”偏于抒情而“赋”偏于体物的差别。然这些局部牴牾之处并不占主要的地位,就总体的情形而言:与诗相较,“体物”固为赋之突出特点;与赋相较,抒情自是诗之擅场。
“体物”既是赋之所长,刘希夷的《死马赋》从题名来看,更是极适宜用辞赋一体来呈现,此篇赋作也常被视作咏物赋。按照以往咏物赋的写作理路,对于“马”之描写应为全篇之主要部分,赋之直陈铺叙的特点也应在这一部分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而刘希夷在全赋的34句中,关于“马”的直接描写则大概只有“燕地冰坚伤冻骨,胡天霜缩落寒毛”,“昔日浮光疑曳练,常时蹑景如流电”,“悲鸣羸卧此山中”这几句而已,其他间接描写者亦殊少。作者对“马”的描写如此惜墨如金,作风与以往的咏物赋不同。由是可察,刘希夷意不在对“马”的铺陈描述,而在借由“马”前后遭遇的转变以抒发作者内心复杂的情感。这复杂的情感主要涵括以下几个层面:其一,表层的情感,是对这匹“马”前后遭遇转变的感怀,其从一匹意气风发、驰骋幽并、追日逐云的“良马”,最后竟变成了一匹壮心未已而羸卧山中、久事贱役的“死马”,透露出对“马”前后遭遇的同情;其二,中层的情感,是透过以马喻人,抒发英雄末路、报国无门、受封无期的无奈与不满,特别是“一代英雄从此毕”之句,以犀利锋芒的语气道出了士不遇的苦闷与悲凉;其三,深层的情感,则是由马及人、进而再由人及于整个社会现实,此赋末言“八骏驰名终已矣,千金买骨复何时”,意在表达从“良马”到“死马”的凄惨变化终究还是了结了,然而作者对这种扭曲不公的社会现实的改变却极不乐观,为其加上了一个无尽的期限,这便将作者内心的愤懑郁结之情推至了极点,令人悲慨不已。可见《死马赋》并非单纯的咏物赋,而是一篇寄寓复杂情感的言志抒怀之作。
刘希夷在《死马赋》中推进以上三个层面复杂情感的方式,主要的还不在于直陈铺叙的赋法,更多的是透过比兴寄托的表现方式。赋中所描绘的“马”只是一个符号,它的遭遇,其实也是赋中所描绘的“君子”的遭遇;而这位“君子”事实上或也仅是一个符号,其毋宁说是作者心迹的一种改装和表露。伏俊连曾考证《死马赋》所咏之事为战国时期魏国田子方事,事见于《韩诗外传》卷八:“昔者田子方出,见老马于道,喟然有志焉,以问于御者曰:此何马也?御曰:故公家畜也。罢而不为用,故出放之也。田子方曰:少尽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为也。束帛而赎之。穷士闻之,知所归心矣。”此一本事之引起刘希夷的共鸣,或与其身世遭际相关。关于刘希夷的生平与死因记载很少,刘肃《大唐新语·文章》等笔记所载其“为奸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云云,不尽可信,惟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七所述“不为时所重”一句,似透露出了一些隐微的消息。刘希夷在其时或怀才不遇、久不得志,《死马赋》中的“死马”和待封无期的“君子”之不幸遭际,或许是比野史小说更可信的对作者身世遭际的注脚。刘希夷在《死马赋》中所抒发的情感,非由赋法铺陈而出,而是透过比兴之法,将这些隐微的寄托层层烘托出来。《死马赋》这种表现方式是对汉大赋为代表的咏物模式的一种反叛,而直接于楚辞的抒情传统。前文已言,辞和赋有偏于抒情和体物之别,而楚辞的比兴又承继《诗经》而来,王逸《离骚经序》即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比兴作为一种诗歌的优良传统为唐人所重,比兴寄托的运用使诗意由直抒变为曲叙,契合于诗之追求含蓄委婉的特质,故而在诗中常见而在赋中不占主流。
由上可见,《死马赋》高度诗化特质的另一大来源,显然是从比兴寄托的表现方式而来。《死马赋》摒弃了传统咏物赋铺陈体物的特质,大幅减少了赋中直陈铺叙的成分;全篇缘情而作,改接源自《诗经》和早期辞赋中的抒情传统,以比兴寄托的表现方式运行全篇,故能形塑出一篇沉郁凄楚、意味深长而极具抒情效果的“诗体赋”。
(三)用典、语言与声韵的诗化——沈约“三易说”在《死马赋》中的表现
南朝沈约曾提出著名的“文从三易说”,此说见载于《颜氏家训·文章》:“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从当时的文笔观念来看,这里的“文章”是指有韵之文,自然是将诗和赋涵括在内的。“三易说”主要从用典、语言与声韵方面对诗赋等韵文做出规范:“易见事”即主张用典既要力避生涩穿凿,同时也要避免用典过多而导致文意堵塞;“易识字”是指要用字要浅显平易而避免使用冷僻的“玮字”;“易读诵”则是指声调要流利上口,适于吟诵。沈约在当时又提出更具影响的永明声律说,这主要是针对五言诗而论,然所谓的“三易说”实际上也是永明声律说相互表里、配合行进的,它们共同显著影响了六朝以至唐前期诗歌的创作。此一阶段的诗歌,少用或不用典故而多采白描手法,语言浅显平易少用僻字,调谐四声平仄而声调整严,这不仅突出体现在新体诗及后来的律诗上,在古体诗中亦成一时风尚。
《死马赋》在体制上形同七古,其高度诗化的特征除了表现在形式、表现方式等层面,在用典、语言及声韵上也显现出向当时诗歌趋近的态势。用典方面,《死马赋》完全没有诸如大赋那般典故堆积壅塞且不易索解的弊病,全赋明显的用典之处为“汉女弹弦怨离别,楚王兴歌苦征战”“盐车垂耳不知年,妆楼画眉宁记日”“仙桥题柱即长辞”“八骏驰名终已矣,千金买骨复何时”这几处,且所用多为寻常熟识之典。语言方面,《死马赋》以平易浅近为特征,而无汉赋好用的冷僻难训的“玮字”,由平易浅近的语言来表达深远婉曲的情感,实是作者才情的展现,亦是其时诗歌的一致追求。平易浅近之外,《死马赋》的语言又有通俗化的趋向,如起首的六句,明白如话。事实上通俗化也是刘希夷诗歌的总体特征,如顾璘评其脍炙人口的《代悲白头翁》云:“意态亦好,惜多俗句。”蒋一葵亦评曰:“半俗半雅,正好。”声韵方面,《死马赋》声调流利,韵部平仄通押,转韵方式上也同于七古的四句或八句一转的规制,全篇32句均齐地分叶七部韵,前三部与末三部皆是四句一转,惟正中间的第四部是八句一转,且除第四部后半外每一部四句中皆是第三句不用韵。具而言之,第一部叶平声豪韵(高、劳、毛),第二部叶上声皓韵(道、草、老), 第三部叶平声东韵(穷、中、风),第四部八句一转,叶去声霰韵(练、电、遍、战、见),第五部叶平声庚韵(并、行、声), 第六部叶入声质韵(失、毕、日) ,最后一部叶平声支韵(期、辞、时)。从叶韵规则来看也趋近于当时的七言歌行。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卷六云:“希夷虽则天时人,然格律已有天宝以后之风矣。”此即就刘希夷作品追求声律流畅之特点而论。
除以上几个方面,《死马赋》在对仗方面呈现出精工巧妙的特点,此是受南朝至初唐诗歌好用对仗风气之影响。再者,刘熙载《艺概·诗概》云:“伏应转接,夹叙夹议,开阖尽变,古诗之法。”《死马赋》在章法结构上开阖变化,转接有序,显然是借用了古诗的技法。前引胡幼峰之文已对此两点作了细致分析,可资参看,本文不再赘述。
综上所论,刘希夷的佚作《死马赋》呈现出了高度诗化的特征。许结、郭维森在《中国辞赋发展史》中概括辞赋五大创作特征为直陈法、铺叙法、用韵法、构篇法(问答体)、藻采法。然而,除用韵法以外,《死马赋》在创作上对赋的其他几项特征都有不同程度的消解甚至摒弃。那么,如此异于赋之创作特征的《死马赋》,是否还能将其视为赋呢?笔者主张仍将其留在赋的界内。理由一是从敦煌遗书中《死马赋》的写本原貌来看,作者毕竟将这篇作品题为“赋”,为尊重作者意图与作品原貌,应视其为“赋”。二是这种诗化的赋毕竟在辞赋的创作史上不是孤例,所谓的“诗体赋”在六朝以至唐代赋的一个特殊的门类,若细致寻绎仍能发现其与传统赋体的关联。三是诸如形式上的高度诗化等特征,也并不能完全消解赋的特质,因为赋并不像律诗那般存在几乎无法撼动的形式规范,即如限制最为严苛的律赋,也未曾限定不能使用五、七言的诗体句式。故《死马赋》虽呈现出高度诗化的特征,但它的文体属性仍是赋。
三 诗化与赋化:刘希夷诗赋的越界书写
《文心雕龙·通变》云:“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中国古典文论中“体”内蕴纷繁,刘勰所言之“体”自然也包涵了文类(体裁)、风格(体貌)、语体等多元层面的问题。若从文类(体裁)角度而言,诗之文类特征鲜明,而赋则是介于诗文之间的一种“亚文类”,从整体来看,赋虽脱胎于诗而最终趋近于文,赋的文类特征也在这种历史进程中不断消解、重构并趋明确,故而诗赋各有其“常体”。刘勰所谓的“变文之数无方”,从文类(体裁)角度而言,借鉴其他文类的特征以变其“常体”的做法,也是古人惯常的“变文之方”。刘希夷在各体文学的书写中,正是特为青睐于这种文类越界的书写方式。不仅其赋作呈现出高度诗化的特征,已如上述;且他的诗作也好用文类越界的书写方式,采用“以赋为诗”的做法,使其诗歌呈现出鲜明的赋化特征。
(一)铺陈刻画,体物入微
清人刘熙载《艺概·赋概》云:“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叠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此论精要地道出了赋的文类特长,诗以凝练含蓄为旨归,而赋则以铺陈刻画、体物入微见胜。刘希夷以赋为诗,这种铺陈体物的赋化特征在其诗歌中屡屡可见。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他的这首七言歌行《捣衣篇》:
秋天瑟瑟夜漫漫,夜白风清玉露漙。
燕山游子衣裳薄,秦地佳人闺阁寒。
欲向楼中萦楚练,还来机上裂齐纨。
揽红袖兮愁徙倚,盼青砧兮怅盘桓。
盘桓徙倚夜已久,萤火双飞入帘牖。
西北风来吹细腰,东南月上浮纤手。
此时秋月可怜明,此时秋风别有情。
君看月下参差影,为听莎间断续声。
绛河转兮青云晓,飞鸟鸣兮行人少。
攒眉缉缕思纷纷,对影穿针魂悄悄。
闻道还家未有期,谁怜登陇不胜悲。
梦见形容亦旧日,为许裁缝改昔时。
缄书远寄交河曲,须及明年春草绿。
莫言衣上有斑斑,只为思君泪相续。
此诗从描写对象和文意来看,显然是化自汉代班婕妤的《捣素赋》而来,这一层渊源关系实际上也奠定了《捣衣篇》的赋化特征。《捣素赋》叙写捣衣思妇思念远方游子之情,而《捣衣篇》则踵事增华,又在捣衣细节、缝补过程、环境景物等方面尽情铺陈刻画,将这种凄凉孤寂的情境与深刻绵长的思念加倍渲染出来。该诗的赋化特征随处可寻,如首二句“秋天瑟瑟夜漫漫,夜白风清玉露漙”,第一句两组叠词的运用,以及第二句“夜”“风”“露”这三个物象的排列,事实上都是赋体的常见手法;又“燕山游子衣裳薄,秦地佳人闺阁寒”两句,将“燕山”“秦地”两处遥远的时空勾连起来,这种时空的巨大转换与跳跃,也正是源自赋体的写作特性。故清吴乔《围炉诗话》直言道:“刘庭芝《捣衣篇》通篇是赋。”
铺陈直叙的赋法不仅体现在刘希夷的歌行中,其在律诗中亦好为此法。如五律《晚春》:
佳人眠洞房,回首见垂杨。
寒尽鸳鸯被,春生玳瑁床。
庭阴幕青霭,帘影散红芳。
寄语同心伴,迎春且薄妆。
此诗透过“佳人”的视角及其感受从而与“晚春”产生联结,通篇都是从首句“佳人眠洞房”一路说开去。《唐律消夏录》载谭友夏(元春)云:“下七句都从‘眠洞房’生来。自‘垂杨’至‘散红芳’,俱床上望外景事,所以有‘且薄妆’之语。盖急欲迎春,眠起不暇浓妆耳,此解是矣。但‘寒尽’二句,如何亦是望外景事?口气有怪得夜来暄暖,原来春色已如许了也。此一层意,便粗看过去。”黄生《唐诗矩》更直言此诗“全篇直叙格”。是以可见,“以赋为诗”是刘希夷的古、近体诗的一大重要表现技巧。
(二)倾怀叙情,不肯留余
诗歌追求情感的节制,以形成含蓄悠远的审美效果。赋则“吐无不畅,畅无或竭”,追求将情物表现得具体、彻底、入微。与赋的此一艺术特性直接相关,刘希夷在诗作中常常不能有效地节制情感,而任其延展泛滥,非要将胸中所感倾泻而出。试看其《代悲白头翁》: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
洛阳女儿惜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
古人无复洛城东,新人还对落花风。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寄语全盛红颜子,须怜半死白头翁。
此翁白头甚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
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
光禄池台文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
一朝卧病无人识,千朝游历在谁边。
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白发乱如丝。
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悲。
此诗通过花与人的连类、今与昔的对比、“红颜美少年”与“半死白头翁”的对照等,将青春易逝、盛年难再、世事无常之情感透彻地抒发出来。《代悲白头翁》所长不在体物,而在于叙情,按王闿运的说法,可以将此类诗作目为一种“叙情长篇”。此篇作品的主旨清晰显见,并无隐微难解之处,原因就在于刘希夷将情感和盘托出,而无甚保留。此诗全篇结构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前四句以落花起兴,写洛阳女儿对花叹息,后面的诗句皆是铺写其“长叹息”的内容,故而清王夫之《唐诗评选》评此诗曰:“唯‘长叹息’三字顺出一篇。”这种铺叙的技法正是借鉴赋体的写法而来,但也因此落下了“太尽”的微词。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云:“刘庭芝藻思快笔,诚一时俊才,但多倾怀而语,不肯留余。如《采桑》一篇,真寻味无尽。《春女行》前半亦婉约可思,读至‘忆昔楚王宫’以下,不觉兴阑人倦矣。钟氏盛称之,独贬其《代悲白头翁》。此诗悲歌历落,昔人之赏自不谬。特亦微嫌太尽。”此一“尽”字,正道着了《代悲白头翁》的抒情特点乃是受赋的影响而成。“物尽其态”是赋体的特征,宋人李仲蒙云:“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古人对《代悲白头翁》的微词,正是以其叙情“太尽”而稍离诗歌含蓄委曲之美学特质。
(三)篇幅加长,转韵灵活
今存刘希夷三十余首诗以歌行为主,且大多为中长篇幅,如上引《捣衣篇》28句、《代悲白头翁》26句。另如《嵩岳闻笙》全篇18句,《蜀城怀古》《秋日题汝阳潭壁》《采桑》《将军行》皆20句,《谒诸葛祠》24句,《公子行》《春女行》28句,《孤松篇》与《谒汉世祖庙》皆为32句、五排《初度岭过韶州灵鹫广果二寺其寺院相接故同诗一首》则多达32句,《洛川怀古》(敦煌写本题作《北邙篇》)更是长达38句。这种篇幅的加长,正是援赋入诗的直接结果,从前文分析的两篇诗作即可了解。而因应篇幅的加长,势必要对诗歌进行押韵以求节次分明、文意承递。由于赋是一种适于诵读的文类,故而较早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押韵程序以适应诵读的节奏。其程序大体上是四句或八句一转韵,且四声或平仄交替。这一点明显又影响了六朝以至唐代的歌行。如前文分析的《死马赋》的用韵方式,正是赋的这种影响的写照。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刘希夷不仅辞赋中存在着高度诗化的现象,其诗歌(无论古、近)亦多采“以赋为诗”之法,呈现出明显的赋化现象。这种不同文类间越界书写现象,在刘希夷的作品中鲜明、集中地表现出来。
四 代结语:诗赋合流现象与刘希夷的标本意义
在以往关于刘希夷的研究中,主要围绕其传世名篇《代悲白头翁》而展开,着重关怀的是刘希夷的情感世界及其在唐诗风貌塑成方面的意义。此一研究进路大抵是受闻一多的影响,其在《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言刘希夷是“卢、骆的狂风暴雨后宁静爽朗的黄昏”,又指出他的《代悲白头翁》等作品“从蜣螂转丸式的宫体诗一跃而到庄严的宇宙意识”。事实上,敦煌遗书中刘希夷佚作《死马赋》的发现,其意义不仅在于赋作本身价值(包括文献、思想与艺术)的抉发,也直接助益于刘希夷整体研究的拓疆、丰满以及完形。《死马赋》恰可视作刘希夷研究的一个新的突破口,此篇“诗体赋”的思想艺术水准实堪与《代悲白头翁》颉颃,甚至对其形成了超越,这对刘希夷的整体研究无疑是颇具价值的,也有助于后人完善甚至重构对刘希夷的相关认知。闻一多从《代悲白头翁》中感知到的“庄严的宇宙意识”,实际上在《死马赋》中亦复如是,此赋所呈现的世事无常、好景难留以及个体无法对抗世界的无奈与悲哀,与《代悲白头翁》的主旨亦相合辙。但《死马赋》的意义,显然不止于为刘希夷的情志多做一个注脚,其在艺术上的意义(即极端的诗化特征)亦不容忽视。再者,从高度诗化的《死马赋》反视刘希夷的诗歌,同样可以发现其诗歌中也存在着鲜明的赋化现象。诗歌与辞赋这两种文类在刘希夷作品中频繁地越界,两者呈现出互相纠缠、高度融合、难分彼此的样态。这种“赋的诗化”“诗的赋化”以至两者合流为一体的现象,成为刘希夷创作的典型特征。然而更重要的是,若将刘希夷的诗赋作品置于整个“诗赋合流”的历史脉络进行观照,可以发现其更具备一种作为标本的意义。
关于诗、赋之复杂关系,前贤已反复爬梳。究其大要,大抵表现为二端:一是从“体源”来看,赋出于诗;二是从“体制”来看,诗、赋分疆以后两种文类间存在着“互参”的现象。可见诗与赋无论在先天、后天都存在着一种相互纠缠的关系,而极盛于南朝至初唐时期“诗赋合流”的创作现象,则是诗、赋这种纠缠关系的最鲜明的体现。“诗赋合流”表现为“赋的诗化”和“诗的赋化”两个面向。所谓的“诗化”“赋化”,虽兼涉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两方面,但又以艺术形式方面的互参最为显著。然从整体发展脉络来看,“诗的赋化”助益于诗歌走向律化进程以及表现技巧的丰富,且不损及诗歌的核心特质;而“赋的诗化”则情形不同,其虽亦有艺术方面的助益,但长远看来无节制的“诗化”存在着消解赋体特征的隐患,后来“诗体赋”的逐渐消亡正说明了此种变体的局限性。若就此一点出发,相比“诗的赋化”呈现出积极的意义,而“赋的诗化”可以说更多的是负面的导引,清王芑孙《读赋卮言·审体》所谓“七言五言,最坏赋体”之论,可视为古人对“赋的诗化”的主流认知。古人言“诗可坏赋”而不言“赋可坏诗”,其原因就在于诗、赋在互参之中存在不对等的关系,徐公持先生对此曾有精辟论断:“‘赋的诗化’与‘诗的赋化’相比较,前者在内涵上更深入、更丰富,原因是,赋与诗的交流,不是等量交换,在这场交流中,赋是入超者,诗是出超者。”再就本文的研究对象刘希夷来看,尽管其作品皆呈现出鲜明的“赋的诗化”“诗的赋化”特征(已如前述),但两者相较,又以“赋的诗化”表现得最为极端,此一点可以亦可以从“赋的诗化”的历史脉络中得以印证。
从整体发展态势而言,尽管赋胎于诗而最终向文趋近,但这种演变始终伴随着“诗化”与“文化”两股力量的相互拉扯,其实质则是赋这种文类本身特质的消解或独立。所谓的“诗体赋”,正是赋在后天“诗化”过程中而形成的一种产物。赋的“诗化”过程,从汉末即已开始显现,在早期主要体现为赋末系诗、赋中穿插诗作等方式,可视为楚辞的残留,像张衡《思玄赋》、马融《长笛赋》赋末均有一首七言系辞,赵壹《刺世嫉邪赋》在赋中掺杂了“秦客”“鲁生”的歌诗,但诗与赋在这两例中仍是貌合神离的,并未真正融合在一起。班固的《竹扇赋》虽通篇11句皆采用诗的七言句式,但如此成熟的七言作品是否出自汉人之手,实大有可疑之处。随后的晋赋中亦有不少参用诗体句式的现象,如左思、夏侯湛、湛方生等人的赋作,然这种“赋的诗化”现象的真正开显实始于南朝齐梁年间。清黎经诰云:“梁简文帝集中有《晚春赋》,元帝集有《春赋》,赋中多有类七言诗者。”另如简文帝萧纲的《对烛赋》28句中五、七言句多达18句,梁元帝萧绎的《对烛赋》17句中亦有11句为五、七言句式,又其《鸳鸯赋》一半的句子采用了五、七言的句式。此际诗化得更为极端的例子是沈约的《愍衰草赋》,除起首一句为三言,中间有四句六言外,主体的部分(共25句)皆用五言句式来结撰,另沈约的《天渊水鸟应诏赋》亦主要用五言句式写就。后来庾信、徐陵、江总、萧悫等人的赋亦皆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诗化现象,如庾信《春赋》以七言诗起又以七言诗结,中间亦掺杂七言诗句。又如同题的北齐萧悫的《春赋》体制更为独特,该赋完全舍弃以四、六、三言为主的辞赋基本句式,而通篇皆采用五、七言的诗歌的句式,较庾信更加诗化。唐初赋作多有受其影响者,如王绩《元正赋》全篇73句有超过一半采用了五、七言句式,更突出的例子是四杰。清许梿曰:“六朝小赋,每以五、七言相杂成文,其品致疏越,自然远俗。初唐四子颇效此法。”又李调元《赋话》云:“初唐四子词赋多间以七字句。”如王勃的《春思赋》和骆宾王的《荡子从军赋》,五、七言句式比例竟高达八成以上,稍不同的是王赋以五言句式为主,骆赋则以七言句式为主。这些“诗体赋”局部截出或稍加改装便可成为一首诗,如《全唐诗》所载王绩的《北山》诗,实为其《游北山赋》的节录;又如明代李梦阳曾将骆宾王的《荡子从军赋》稍加修改变成《荡子从军行》;再如王世贞言王勃诗赋界限之不明:“子安诸赋, 皆歌行也,为歌行则佳,为赋则丑。”事实上四杰的诗歌也存在着鲜明的赋化特征,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和骆宾王的《帝京篇》等长篇歌行,也可说是亦诗亦赋了。初唐歌行与辞赋关系之密切由是可见。
不过,这种“赋的诗化”现象最极端的例子,当属刘希移这篇全盘皆用七言句式来写作的《死马赋》。如果说沈约的《愍衰草赋》《天渊水鸟应诏赋》等真正开创了以五言为主体句式的“诗体赋”,而萧悫通篇皆采用五、七言句式结撰的《春赋》又标志着这种“诗体赋”演进到了与诗歌融合无迹,甚至全盘诗化的境地。那么,若考量到《竹扇赋》的可信度(时代与作者存疑,《竹扇赋》以后长期未现其他类似赋作)及完整度(《古文苑》卷五所载为残篇),刘希移的这篇《死马赋》可以说是目前文献可见的首篇全部采用七言诗体句式来写作,且完整可信的“诗体赋”。这又将萧悫《春赋》中已然呈现的高度诗化的特征更推进了一步:将句式彻底单一化、均齐化。《春赋》中残存的一点由五、七言句式差异所产生的参差感也因此完全消除。故可以说,刘希移的《死马赋》实标志着由汉末开显而盛于南北朝至初唐的“赋的诗化”现象,至此进至了一个最极端的层面,赋在形式上的特性也几乎消解在了这种高度诗化的艺术形象之中,以至于王重民等学者将其判入了诗的界内,而我们亦未觉有不妥之处。因此,强辩《死马赋》终极的文类归其属实意义不大,其特点正是透过这种两栖于诗、赋的文类属性而体现出来的。
综上所言,与此前的赋作面目不同,刘希移的《死马赋》呈现出了高度诗化的特征,其为“赋的诗化”现象中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标本。同时,结合刘希夷诗歌中鲜明的赋化现象来看,可知“赋的诗化”与“诗的赋化”这两条脉络在刘希夷的创作中互相纠缠、高度融合,故其当为六朝以来特为盛行的“诗赋合流”现象中一个不可多得的标本。若从此一点出发,再行检视刘希夷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可知其作品不止于如闻一多先生所拈出的“一跃而到庄严的宇宙意识”而已。吴相洲先生曾重估刘希夷的历史地位,推尊其为当时唯一兼具“骨力遒劲、兴象玲珑、神采飘逸、平易自然”四种风格的“初唐诗发展的总结者”。事实上,若从盛行于六朝至初唐的“诗赋合流”的历史脉络来考察,刘希夷堪当这种“诗赋合流”现象的一位“总结者”,其作品亦有一种堪为标本的特殊意义。而刘希夷历史地位的重估以及其作品标本意义的抉发与完形,实有赖于敦煌遗书中《死马赋》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