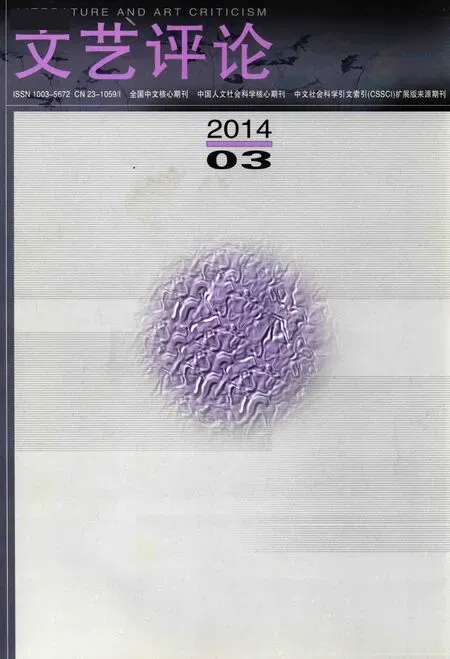当代文学中文类焦虑与纾解研究
2014-09-29○伊云
○伊 云
“文类”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文学分类系统,二是指系统下的类别。文类的产生是以实用为目的,它的功效就是将文学划分为若干的板块,可以使创作者得以寻阶登门,读者得以按图索骥,研究者得以提纲揭目。据此,可以将文类作为归纳、整理文学作品,而文学的重要性理当是在文类之上。然而诡异的是,在统合了大量优秀作品的特色之后,文类的地位竟然由“工具”突变成“准则”。这种主从关系的易位,堪称是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久而久之,文类甚至内化为一种先验真理潜在于文化结构之中。当代文学界所运用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类四分法,从文学教育到文学竞赛,这种系统可说是无处不在,仿佛通过这个系统就能将文学作品统摄于内,并使之按部就班,各就其位。
一、文类焦虑现象产生的缘由
文类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由前代优秀的作品归纳而得的。虽然,源头或许可以追溯至一位或一群作家,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文类一旦产生,就成为了一种语言结构范本,经历后继者不断模仿、传播而得以发展,文类也藉由这种学习过程产生了权威。作家们从小通过对大量作品的阅读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使他们熟悉一种文学类型的文类特征。这种观点一旦建立起来,便很难消除。文类参与了作家的培养,再也无法从作家的意识中抽离。这就有了“文类意识”。
对于进入文学世界的作者来说,常会以文类来指认创作者的身份,比如“诗人”、“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仿佛文类已化为创作者生命的一部分。只要创作活动仍然持续,文类便永远如影随形。的确,每一位作家都是从当代通行的文类起步,才逐渐建立起个人风格。不靠文类而能独创新体,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对艺术创作最讲究“自由”来说,文类却又处处充满了限制。保持文类的稳定对文学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许多时候文类不但是游戏规则,更是价值的判断。创作时严守当行本色,短期内固可获得一些利益或安全感。不过若作者真有心于艺境的提升,文类规范便往往成为困扰。在对规范的依违之际,焦虑感也就随之而起。
所谓的“文类焦虑”,就是一种因过度在乎“文类意识”而引起的不适感,并且作者常常因超拔不成而产生更巨大的痛苦。仔细分析起来,文类焦虑有两个层次,第一是如何提升单一文类(诗、散文、小说、戏剧)艺术境界的焦虑;第二是如何不受文类限制的焦虑。这两种焦虑常融合在一起,不是很容易区别的,况且两者之间还存有某种微妙的循环关系。文类焦虑其实并不是什么太新奇的论点,只是以前很少被提及,而总是跟整个文学界的思辨潮流合在一起讨论。
由于文类是创作的重要依据,无论题材、形式、技巧皆自此而出。于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文类是作者立身之所就一点也不为过了。当作家感受到文类开始僵化,对文类不再完全信任,却又逃脱不了已内化的文类意识时,焦虑感便油然而生。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家,心理焦虑研究权威的罗洛·梅解释说:“焦虑是因为某种价值受到威胁时所引发的不安,而这个价值则被个人视为是他存在的根本。”而且“焦虑是一种处于扩散状态的不安……是非特定的‘模糊的’和‘无对象的’。”①这也就是说个体根本弄不清使他产生不安的原因来自何处。文类焦虑,正是这样难以形容的情绪。虽然大部分的作者都无法觉察,但还是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作者在依循文类意识引导时可能遭遇的“威胁”,以凸显反文类动力的发生机制:
首先,焦虑来自于前人的崇高成就。每一位作家在创作生涯开始时,心中一定都抱着“首创”、“独创”的自我期许,去除这个“立言”的诱因,确实会使态度较积极的作家失去动力。然而,除了为数不多的强者外,能成心愿者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多数人在把自己的作品跟过去的丰富遗产进行比较后,便立刻落入了“自信迷失”的深渊。法国新小说派健将罗伯-格里耶在面对先驱者的作品时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作家本人,尽管想独立,却还是置身在某种精神文明与文学之中,即已写成的、过去的文学之中。他无法一下子摆脱一个他本身就是某产物的传统。”②这番话诚实地道出了当代作家不得不受前代影响的矛盾,无论独创的部分有多少,他的作品里总是可以找到前辈的身影。每一位作家都受惠于前人,但又不希望永远走不出“庇荫”。换句话说,就算作者自己承认很难创作出“名留青史”的作品,但潜意识里毕竟还是对自己的存在价值有所期望的。在这两种情绪来回晃荡间,焦虑感也就逐渐加深。完全顺服前人,按着前人的规范进行创作,易有“负债”的焦虑,而尝试挑战则得承受可能失败的后果。
在文学史上可以看到,发展得越成熟,法式规范越精密的文类,其影响力就越强,后人的焦虑感也就越严重。比如唐诗的光芒,就掩盖了唐代以后所有诗人的成就。宋代虽高才辈出,也改变不了“后到”的劣势。面对唐诗,宋人总是十分谦卑,但有时也不免会有些嫉妒。王安石就曾云:“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③这里,虽是对唐人的称美,然言下之意是对自己晚生似不无嗟叹之意,创作上所受的焦虑可见一斑。
而在传播工具发达的当代,影响发生的速度较过去快上许多,而且几乎没有时空的限制。在世纪之交开始创作活动的青年作家们,必须面对的强者上至新文学运动时期的名家,下至屡屡获奖的高手,甚至包括国外的优秀作家,只要他曾在这些人的作品中得到启发,或有欣慕赞赏之情,影响就必然存在。
其次,焦虑来自文类自身发展的局限。如果将文类当作有生命的客体,也是有萌芽、昌盛、衰亡等生命阶段。倘如一个作者正好身处文类的变化之中,恐怕就没办法冷静客观。因为文类关乎作者思考与说话的方式,少了文类,作者就会手足无措。当觉察到文类这一工具已经不再合用时,作者的不安也就特别明显。王国维《人间词话》中云:“盖文体同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循而作他体以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④这段话说明了文体(当今称文类)与作者相互密切的关系。文类的生命其实并非生物性的自生自灭,它的兴衰是由作者与读者决定,而作者又为文学作品的根本。文类可供作者驰骋的空间越大,表示他越年轻;反之当它的形式内容都被探索殆尽,作者无法从中获得创作的欢悦时,文类便已步入衰败。作者的“遁而作他体”,未必是纯然的逃避,而是包含着改进旧的文类,使其转生新的面貌的意思。
这种文类的焦虑是重在对当今文类的不满。这些不满有些是针对“工具性”,比如被文类成规限制住的语言、结构;有些则是针对“艺术性”,比如一种一成不变的风格等等。顾炎武曾云:“诗文之所以代变,又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模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⑤这段话就是站在作者的立场上,陈述了文类的局限。文类本是历史的产物,虽然有种种翻腾变化之姿让后继者瞠目,但这些庞大的遗产还是不足以帮助作者应付创作的需求,作者就会感到焦虑。也就是说,去除历时观点后,作者在乎的,只是文类好不好运用,能不能藉文类完美地表现自己而已。作家莫言在1999年4月的《新民晚报》上就坦言,自己就是把散文当小说来写的。他认为,任何一个作家,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巧遇巧合。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新生代散文”,核心就是对散文的“真实性”传统进行突破,强调具有虚构和想象的散文观念,从而叛逆了传统散文观。另一方面,小说家们在创作时,往往会采用“散文笔法”,例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汪曾祺的小说,其独具特色,就因为它开了新时期小说散文化的先河。汪曾祺历来主张小说应有散文的成分,他的小说,渗透着明显的散文化特征。并且,随着当代“新写实小说”的出现,由于“其创作方法以写实为主要特征,特别注意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⑥
第三,焦虑来自文类与社会环境的距离。文类的产生与发展跟社会的实际需求联系在一起。诗歌的音律形式,基本上就是口传时代的产物,戏剧与史诗,则是从表演中诞生。中国古典章回小说,起源于市民娱乐的说唱艺术。西方长篇小说在18世纪后逐渐昌盛,是与印刷出版业的进步,以及中产阶级的休闲生活有关。相反的,许多固有文类的消失,则由于环境的变迁,故无法再获得读者的青睐。比如西方史诗在18世纪后完全消亡,一方面是因为功能已被历史著作与小说分别取代,光从故事娱乐效果来看,小说又远比史诗来得完备;另一方面也是因大众对英雄已不像过去那么感兴趣。简而言之就是时代气息变了,读者的口味也跟着改变。文化研究者本雅明早在上世纪40年代欧洲城市进入成熟阶段时,便宣称长篇小说的时代已经过去,短篇小说则正在兴起。无论是读还是写长篇都有赖“手工艺”年代的氛围,而如今长篇小说的阅读氛围已不复存在。本雅明引梵乐希的话说:“所有这些不惜心血的持久劳作才能做出的产品都逐渐消失了。时间不足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代人不再干不可缩略的事情了。”⑦现今文坛犹在继续创作长篇小说的作者也许感同身受吧。
二、“跨文类”是纾解文类焦虑的首要途径
适当的焦虑对于作者来说是件好事。被誉为存在主义之父的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曾就焦虑与创造力、原创性和智识的辩证关系加以探讨。他认为应将焦虑视为“良师”,因为它能激发人的创造力活动,使个人得以走出“有限”的压制,具有体验与实现可能的机会。⑧心理学家罗洛·梅则进一步补充,指出越具创造力的人越容易面临焦虑情境,二者关系成正比。焦虑虽可能引发不良反应,但若将其转换为具有创意的活动,焦虑便可以获得纾解,他的结论是“焦虑是知识的阴影,也是产生创意的环境”。⑨虽然从心理学的焦虑理论还不能与文类焦虑完全合拍,但文类因焦虑而生“变”的创作心理机制是一直存在的。文类困境可能致使作者完全放弃,这时藉由逃避来纾解焦虑的方法。但谋求文类的新变,才是真正富有创造力而又能治本的纾解之道。
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曾在《文学论——文学研究方法》中强调,文类仅是一种制度,即便它有如国家、教会般森严稳固,但毕竟还是由人所制定,而且绝对是可被改造的。谢弗提醒所有的创作者,文学类型并非生物类型,文学的演化并不需要基因突变那么漫长的时间,同类型的作品更没有强制的血缘关系。“文本传统的逻辑总是一种间断性的逻辑,在两种文本之间,除了隐喻的意义之外,并不存在任何‘种属’的纽带”。⑩真正有文学创造力的作家正好冲决、扩大这一裂隙,以打破现存文类的垄断,甚至再创一个新的场域供自己攸游,在那里不受到文类传统的干扰。
由此可知,不管是作者的心理动机还是文类系统本身的缺失来说,文类改变都具备足够的理由。但是首先应注意的是文类可以“变”到何种程度。从理论上讲,文类的变化有无限的可能,正如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中所云:“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但现实是已有的四大文类仿佛将一切形式技巧通通概括,这些文类之所以经得起挑战,是因为很难找到一篇完全不具任何文类主导要素的文本,通常有争议的也只是要素比例问题而已。可想而知,文类意识还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大众的意识中,所以文类很难在一个人手中完全翻新,还得经几代人才能看到成果。英国学者福勒对文类的创新抱着否定的态度,认为:“未来的类型批评虽然应该十分关注新类型的鉴别……但是这些新类型大概会是通过人们熟悉的发展程序而产生出来的。就这个意义而言,至少在类型的太阳下是没有新东西的。”⑪必须承认正如俄国形式主义学者迪尼亚诺夫所指出的,文类的变化总先从挪用隔邻文类的要素开始。⑫因此,所谓的文变之法首先就是“跨文类”,这也是纾解文类焦虑的首要途径,正如小说家汪曾祺所说:“宁可一个短篇小说像诗、像散文、像戏,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愿意它太像小说。”⑬
当代文学作家中跨文类创作的不在少数。淡化文类界限的散文家董桥说:“你可以写一篇像小说的散文,也可以写一篇像散文的小说,或者像小说的评论,都行。”⑭诗人北岛也说:“试图把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引入自己的诗中,造成意象的撞击和迅速转换。”⑮种种表述及实践证明,文类互渗的跨文类创作已成当代文学作家一种“共识”和艺术趋势。至于先锋小说的叙事、语言革命说穿了就是文类革命。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中为了突出许三观一次次卖血这种循环往复又直击骨髓的审美效果,自觉地将浙江越剧和巴赫的《马太受难曲》等音乐的内在节奏直接结合进作品的叙述过程。散文的诗歌、小说化和戏剧的诗化等探索同样屡见不鲜。余秋雨、贾平凹、苏童的散文里明显有小说的叙述成分。孙犁、王小妮、于坚的散文则有诗歌的影响。
以上纾解文类焦虑的方式其实并未解除作者身上文类意识的枷锁,只是在各文类间不断“循逃”而已。积极的做法则是自行扩大文类的定义,进而破坏文类,并在其中获得冲破牢笼的快感。以文学发展而言,有时破坏反倒是好事。《文心雕龙·通变》中云:“变则堪久。”正是这个道理。前人的“破体”、“出位”也是说的“变”字。钱钟书曾说过:“名家名篇,往往破体为文,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⑯周振甫进一步解释道:“破体就是破坏旧的文体,创立新的文体,或借用旧名,创立一种新的表达法,或打破旧的表达法,另立新名。”⑰如果沿用旧名,表示该文类已经转变出全新的风貌;如果旧名都不保,则表示该文类已遭到淘汰。中国文学中自《诗经》的四言变为骚体,骚体诗变为汉赋,汉赋又变为魏晋六朝的抒情徘赋,乃至于唐宋的律赋与散赋,都是破体又创新。诗由四言而五言、七言,自古诗变为律、绝,而后又变为词、曲,更是破立相生的明显轨迹。破体是文类僵化时的转机,也是创作者解决文类焦虑的必然出路。钱钟书引孙缄“能废前法者乃为雄”之说,合并文类焦虑理论观之,实可视为文学演变的枢纽。所有改变文类现有体制的尝试,皆称为破体。如此这样,那么指称的范围便很大。而“向邻室借光”,即运用其他文类特色来打破自体的成规就称为“出位”了。
“出位”一词原为宋人语,本与文艺无关,后来钱钟书引之作为德国美学用语的对译,即指“一种媒体欲超越其本身的表现性能而进入另一种媒体的表现状态的美学概念”,主要用以讨论“诗画一律”、“艺术换位”等问题。虽然文学的文类严格说来属于同类媒体,是否贴合出位的本意尚有争议,因此就有学者认为纯粹表述文类格式的超越,使用“破体”就足够了,“出位”当另指内涵上的突破。但如果让其与原意脱钩,而将其当成一个文类学的特有名词,用来专指作者在创作A文类作品时加入了相当比例的B文类要素,而使作品在属性上朝B文类靠拢的现象。
“破位”与“出位”虽然看来相似,不过前者是所有打破文类成规行为的总称,后者则限定在文类交涉的范畴;前者的涵盖面较广,后者则缩小在较具体的方法学上。不过“破位”和“出位”虽可有效突破单一文类的僵局,纾解不少因重重限制而引起的焦虑感,但由于未能彻底摆脱主导要素的选择,所以瓦解文类体系的力道毕竟有限。换句话说,不管文类怎样“跨”,作家还是得选择一个文类基底,然后方以其他文类的要素加以改造。因此严格说来,以破位的方法并不能真正解除文类焦虑,只有当各文类要素平均地分布在作品中,连主导地位的轻重都无从比较时,就无法以固有的文类成规来看作品的优劣,这就达到“元类”,或者称为“去文类”,以彻底消解文类的焦虑。
三、“元类”与“元类散文”将为纾解文类焦虑根本出路
“元类”一词起源于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意即一种文学不须分类也无法分类的圆满状态。“元类”本身包含了各文类的性质,却又不属于任何文类。虽然这个词汇在语意上似乎有些矛盾,既然文类的划分功能已被消解,又将总体以类称之不免多余。但也正因为如此,才能更加看清其诉求的焦点。浪漫主义者崇尚整体及统一的理念,这种形而上理念与超越精神,使他们对于传统定义下的文类成规,以及文类背后的意识形态感到莫大的不满。故而他们反对文类的束缚,转而追求具有普遍意义的“元类”。
撇开“元类”一词的欧洲文学背景,这个理想所散发的魅力,其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类永远是把双刃剑,既有指引分判之功,同时也带来因循守旧等弊病。“元类”一说直接把文类观打破,将文学作品带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完足境界,种种因文类衍生的麻烦,自然也就消失无踪了。对此,无论是18世纪的德国还是当代中国,凡是受过文类意识钳制的文学创作者,必定都心向往之。
不过也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朝散文的回归。在前面说到在追求具有普遍意义的“元类”时所关照的是作品“因特征太多而无法辨识”,但是否有另一种情况,即“毫无特征可供辨识”,虽然这两者的出发点不同,但表现出来的结果却是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元类与散文可以相提并论的理由了。
在《辞海》中对散文的定义是这样叙述的:“中国古代为区别于韵文、骈文,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文章包括经史传书在内,盖称散文。随着文学概念的演变,文学体裁的发展,在某些历史时期又将小说及其他抒情、记事的文学作品统称为散文,以区别于讲究韵律的诗歌。现代散文是指与诗歌、小说、戏剧并称的一种文学体裁。其特点是:通过对某些生活片段的描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并揭示出一定的社会意义;篇幅一般不长,形式自由,不一定具有完整的故事;语言不受韵律的拘束;可以抒情、可以记事,也可以发表议论,甚或三者兼有。”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对散文的界定基本上是运用的一种非常特殊的排除法。叶圣陶也曾说:“除去小说、诗歌、戏剧之外,都是散文。”可见散文是一种缺乏自己独立特色的文类。单凭“对某些生活片段的描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并揭示出一定的社会意义”这种宽泛的要素,散文绝对难以跟成规具足的诗歌、小说、戏剧相比。但是没有特征也正是散文的主要特征。
由以上可知,散文与元类都是不具有明确的主导要素,那么这两者的意义就相当接近了。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元类”隐含的是文类大同的理想,而散文看来比较无争无求。这样不妨将以排除法归类的散文称为“元类散文”。
“元类散文”的存在,对“去文类”理论的意义十分重大。诗、小说和戏剧都是规则繁多,“竞争”也特别激烈的文类。诗人或小说、戏剧作者欲打破文类牢笼,除了想方设法“跨文类”之外,也可以考虑逆向操作,直接冲淡、稀释自身的主导要素,让作品“失去特征”,退回自由舒缓的散文领域当中。当然,这种方法不应称为“出位”,因为散文并无明确要素可供挪借,它其实是一种从外到内不断剥落、减损、去除文类层层限制的过程。在卸尽文类的神圣装扮后,最淳朴的写作动机就会显露出来。
“元类散文”不是严肃的庙堂,而是气氛轻松的休息园地。正如南帆所云:“文类向散文的过渡犹如一种反璞归真。规则的松弛使散文成为一片缓冲地带。散文成为诸文类退出竞技舞台之后的安居之地。”散文所谓“文类之母” 的特质,在此也表露无余。⑱
其实,在当代文坛上一直都有着回归散文,纾解文类焦虑的实践尝试,大量的作家创作的诸如诗化散文、散文化小说、散文化戏剧都是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进行着文类的悄悄变革。第三代诗的代表作家,如韩东、于坚,创作的《我所不认识的女人》、《罗家生》等,从形态上看具有叙事文学的要素,人物、情节、地点乃至性格仿佛诗的特征已淡化,但本质上它只是合理吸收了散文的笔法在情节构架里注意了情绪、情趣对事件的强力渗透,因此叙事也是情绪化叙事与诗性叙事。同样,擅长小说散文化的韩少功小说《马桥词典》,突破了以人物、情节、时间为中心的叙事结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重视小说的“感觉”营造。作者用词典的形式来编撰一个个故事,并在叙述过程中夹杂民族、文化人类学考察和思考。小说摆脱一贯的严肃叙事语言,融进情感和哲理,显现散文性因素。在借助语词,穿插人物形象,若即若离地呈现相关事件,显示出一种“松散随意”的写作特色。而他的另一部小说《暗示》已不是一个完整的叙事整体,而是围绕日常生活的具象,阐述语言背后的深层问题,一个个具象问题组成独立的片断,看似零散、独立,但又没有相互脱离。人物或事件作为线索,贯穿于各个独立的片断,最后都统一到一个中心上。
1987年《八方》第五辑上发表了汪曾祺的《小说的散文化》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汪曾祺向世人宣告一种新文体的出现,小说散文化也正式作为一个概念提了出来,其创作也获得了重视,以后小说散文化研究逐渐获得认同。如郝爱萍的《汪曾祺小说创作的散文化技巧》一文,研究了“汪曾祺小说从叙事语调的平静自然,视角的简约平实,及精炼、含蓄和抒情意象的语言,生动展示出市井百态”。⑲再如邵艳荣的《论贾平凹小说的散文化》对贾平凹中短篇小说进行分析,探索其小说中透露的散文化倾向,并从小说的情节、人物形象、细节表现等方面,分析贾平凹小说结构散文化具有明显写意的特点,形散而神不散,将生活中似断似续的人物、细节串联起来,法乎自然,不求严谨,贴近生活,近似于散文。小说散文化创作突破小说连缀式的线性写作模式,弱化事件的因果关系和事件冲突的戏剧性,情节淡化,人物形象写意化等。另外,小说散文化还注重日常生活事件的记录,内心情感的表达,形成一种独特的小说创作。小说非严谨的情节构造,细微的事件、平凡的人物蕴涵散文式的情致,朦胧的人物、事件背后,表达着创作主体独特的感情基调。小说的散文化以这种独特魅力,成为当代作家一种自觉的审美追求,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喜爱。
戏剧借助、汲收散文审美手段来建造戏剧艺术世界,也是当代话剧创作和演出中逐渐显现的现象。像《婆婆妈妈》、《街上流行红裙子》便是较为典型的剧目。在荣获中国剧协评选的优秀剧本奖的话剧新作中,也有相当数量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这一艺术特点。这些作品在总体艺术构思上运用散文式的结构和表现手段,有的如《宋指导员的日记》、《高山下的花环》、《双人浪漫曲》,在局部布局和舞台形象、舞台情景的创造上,汲收散文因素,采用非戏剧性的叙述方式来联结、组合戏剧场面和动作体系。它们借助散文自由的形式和长于叙事、抒情、议论的艺术功能,求得舞台时空变换的灵活,自然流畅,将具有认识价值和审美意义的生活片断和日常琐事综合成一个艺术整体,展现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揭示不同生活侧面的内在联系,赋以剧作和舞台动作以多义的主题和广阔的社会背景,开拓出独特的艺术境界,使剧作更具有真实性和生活化。
当代文学在进入新世纪后,文类归元现象势必越来越受瞩目,若再结合后现代思想,其文学意义将更突出。美国文学理论家查尔斯·纽曼直言:“后现代的写作模式是一种无体裁的写作。”⑳在这里,无体裁的意思就是无文类。但必须强调,去文类现象在文学发展历程中一直都存在的,并非直接肇因于后现代理论,只是由于后现代文学理论的反中心、反结构、反秩序的特质,恰恰符合了后现代语境。“元类”与“元类散文”的不拘一格,不但呼应了“随心所欲”的口号,也让这些作家在后现代“市场”中抢得了先机。长期以来,已有的四种文类能否与时代契合,一直是文类焦虑的来源之一。而散发着后现代气息的去文类观念,对守困在传统文类迷思中的作家而言正是一剂对症的良药。虽然目前还无法评估撤除文类这个参照坐标,全面回归文本后,对文学长远发展会造成哪些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作者的努力下,“跨文类”与“去文类”的精彩表现,一点都不会比过去逊色,光凭这一点就应该对未来抱着无比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