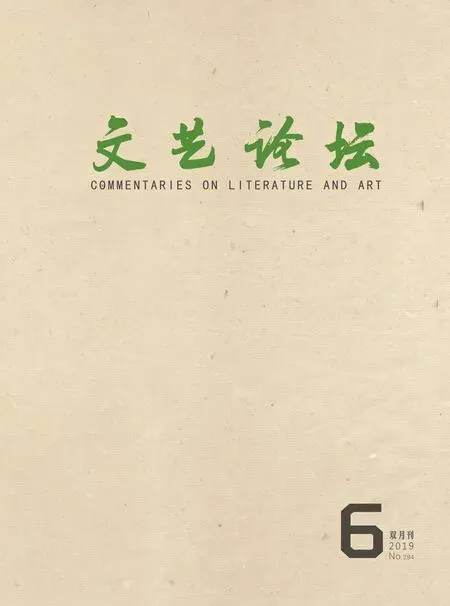“游于艺”:一种文学态度和生存方式
——京派作家与母语写作之二
2019-11-12杨经建
◎ 杨经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京派文学”是一个独特而重要的文学现象。诚然,对京派同人(包括作家和理论家) 的考辩中,的确存在着一个难以完全廓清的问题:京派同人究竟包括哪些人?不过,有一点却可以确认:京派同人都曾居留北平,不仅拥有相近的文学风范和艺术理念,而且展示出“京都”文化所濡染和熏陶出来的气质和风度。相对而言,我基本认同于吴福辉先生在《京派小说选·前言》中划定的京派同人的范围:“即便持一种狭义的观点,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周围聚集起来的作家为主来加以认定,也便有小说家:沈从文、凌叔华、废名、芦焚、林徽因、萧乾、汪曾祺;散文家:沈从文、废名、何其芳、李广田、芦焚、萧乾;诗人:冯至、卞之琳、林庚、何其芳、林徽因、孙毓棠、梁宗岱;戏剧家:李健吾;理论批评家:刘西渭(李健吾)、梁宗岱、李长之、朱光潜等。”其中,除了汪曾祺成名于1980年代,因而严格地说不宜归于经典时期(1930年代) 的京派作家外,吴福辉先生对京派同人的指认是合理而准确的。
一、新文统的构建与文学态度的抉择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在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中,存在着一种世纪性的文学现象——“新古典主义文学”,京派文学便是新古典主义文学的典型表征。因游离于主流文学之外,新古典主义处于边缘状态,却又不失为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演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文学史资源。就新古典主义这一话语概念本身而言,所谓“古典”,指的是一种艺术精神和文学观念,它追求清明而典雅、整饬而规范的风格,讲究精致化和稳定性,强调在均衡和节制的美感中,维持和谐的情致、雅驯的格调。当京派文学以这种“古典”风范面世时,曾被一些研究者贬为不思“进化”而安于“保守”,就此而言,京派文学被赐予“文化保守主义”之类称谓,又似乎在所难免。所谓“新”,是说新古典主义在其本质上,是由20 世纪中国“现代性”语境中生成的一种文化机制和审美话语:既有“背靠历史、融合中西”的立场,又有执着于独立、自由的文学理想的态度,同时它更表露出以“反现代性”面目出现的审美现代性品质(既批判现代性又推动现代性原则)。也因为这种“新”,京派文学又被称为“自由主义”文学类别。
在此,我无意对京派文学的新古典主义倾向进一步追究,只是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发挥、引申。新古典主义文学的“古典”传统,在文学理念和艺术规范层面,很大程度上与汉语言母语文学传统有着互文性指涉和内在逻辑关联,并借此阐发:“京派作家在对古今中外文学采取宽容通融的基础上,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和东方美学精神,与自身的生存方式和所感悟到的人生意义结合,……在母语写作被长期遮蔽的情况下不为‘时势’所迫地贯通母语文学的血脉,并将其提升到新的高度。”在此有必要申明,“母语文学”这个话语概念涵盖甚广,本文所论及的仅仅是,京派作家在母语化写作中所彰显的一种自由而独立的——“游于艺”的文学态度和精神风范,至于在这种文学态度和精神风范下产生出来的文学文本,那是我另外要完成的任务。
京派同人属于一个颇为独特又极富创造力、兼有艺术追求和个性才情的文学群体。在执守文化自律原则和人道主义文学前提下,他们既注重传统诗学的感兴式思维,又关注西方唯美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艺术,并努力以母语文学精神激活传统的和西方的话语资源,在创作、批评实践中创新和通变,形成了具有现代品格的、自足性的文学创作、批评体系;完全可以说,这样的文学创作、批评体系,当属母语文学精神的一种“新传统化”。或者说,京派同人秉持的是冯友兰式“接着说”,而不是照着说的文化态度。西方学者列文森曾有这么一个说法,他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大体是在理智方面选择了西方的价值,而在情感方面却丢不开中国的旧传统。由此看来,在京派同人那里,他们不仅是感情上而且理智上亦创造性的传承、赓续了母语文学精神。
我以为,所谓“创新”和“守旧”的说法令人怀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创新”和“创旧”。不是“守旧”而是“创旧”实际上意味着,人们之所以要对“传统”回望,是因为具备了某种“现代”的立场和视角,所以任何历史都是现在时的,任何“传统”事实上都不可能恢复而只能再生。问题还在于,在意识到传统存在之前,人们就已被置于传统之中——无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否愿意承认传统,传统已经先天性存在并成为他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诚然,传统不可能一成不变地为后代所接受,传统只能存活于人的理解中。是以,“接着说”的传统总是在人的理解中接受改造,乃至于一个“我注六经”的过程。故此,传统的意义不在于它自身,而在于由后代人对它的创造和丰富而发展下去。当传统的意义被不断阐发和解释出来,一个“新”的传统便创化而出。京派同人对母语文学新传统的创化亦可如是观。
在京派同人那里,“新传统”的实质不在“西化”,而是本土性再生、现代性重造,从而使“己丧失的传统价值得以回归到实际来”,创化“新传统”的本身就是“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以至于,母语文化/文学精神成为京派文学最为本质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一些研究者察觉到京派同人身上特有的那种贵族性和精英化,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指他们创作中透溢出的新古典主义式的纯正和雅致。而他们对汉语言母语文学近似天赐的本能,潜在的支配着他们的写作。比如萧乾,拥有辅仁、燕京的求学经历和知识背景,曾一度留学欧洲受到西方文化的浸润。他对汉语言母语文化充满着本能的依恋,不时会对外国人轻视母语文学而“愤愤不平”。诗人气质的梁宗岱将对母语文学的品读,作为灵魂净化方式和精神栖居途径:“可是每次回到中国诗来,总是无异于回到明媚的故乡,岂止,简直如发现一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源,一般地新鲜,一般地使你惊喜,使你销魂。”京派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星空中熠熠生辉的星座,正是缘于其对母语文学新传统的执念。
二、“艺之乐”和游戏精神
京派作家深受中西传统文化薰陶,士大夫文人的精英意识与五四文化启蒙的西方个性主义精神深深浸入他们的骨髓。他们秉持的是一种“自由”但不“主义”的文化姿态。相对而言,绝大多数京派作家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书宅、大学校园以及文人雅集的沙龙是京派同人的心灵栖居之所。从他们的自传性文字材料来看,他们属于那些在天性上最接近新古典主义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沈从文因而慨叹:“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的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情诗。”这一具有“光辉的意义”的“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指代的是京派同人孜孜以求的母语文学创作。
与当时的其他文学创作现象如海派文学、左翼文学相比,京派作家追求的是文学的内在质量,而不去追求所谓时尚性乃至“先锋性”。在创作语言的选择上他们倾向于汉语言母语雅致、诗性的一面。故而,母语写作成为他们必然的展示方式。这种文学选择的态度也得到京派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证实和认同。在京派作家的心目中,文学的世界是自足的世界。李健吾说道:“一件艺术品——真正的艺术品——本身便该做成一种自足的存在。”由于对文学自足性的张扬,他们强调艺术表现和意境营造,追求抒情性审美传统,在母语写作这一体现人生价值的行为中去追逐存在的意义。
在生活方式上,他们也讲究在艺术乐趣和审美情趣中表达自己的意趣。沈从文在《阿丽思中国游记后序》中说:“我除了存心走我一条从幻想中达到人与美与爱的接触的路,能使我到这世界有气力寂寞的活下来,真没有别的可作了。……只从自己的头脑中建筑一种世界,委托文字来保留,期待那另一个时代的心与心的相通。”何其芳则感喟:“我惊讶,玩味,而且沉迷于文字的彩色,图案,典故的组织,含义的幽深与丰富。”“我倾听着一些飘忽心灵的语言。我捕捉着一些在刹那间闪出金光的意象。我最大的快乐或酸辛在于一个崭新的文字建筑的完成或失败。”朱光潜断言:“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上述人生方式和写作方式,我将其称之为“游于艺”(《论语·述而》) 而京派作家的“游于艺”在某种程度上与宗白华的“美学散步”相通。周作人将其比拟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
严格地说,传统意义上的“游于艺”与“成于乐”相关联。在孔子那里,“游于艺”指的是熟稔地把握“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技能的自由感。由于儒家的礼乐制度注入了“仁”的精神——“仁”成为礼的精神、乐的精神本身,当人生向“仁”的境界提升为时,“游于艺”之“游”不仅在“艺”中,更是在“仁”的人生境界中随心所欲且又不逾规矩。“游”于是升华为一种审美化的人生境界,“艺”之“乐”实际上成为“仁乐”——“孔颜之乐”。与儒家不同,庄子讲究的是“逍遥游”。庄子认定人的精神或心灵能够修炼到自由而超越的境界,而“游”便是人的精神或心灵的一种特殊活动;至于“逍遥游”纯属一种无所待之“游”,从而规定了“游”与自然同一。与孔子的“仁乐”之“游”相比,“逍遥游”是一种之于“道”中的“天乐”之“游”。“庖丁解牛”之所以游刃有余,并非其技能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从而获得一种驾轻就熟、应付自如的自由感;而是缘于自然、顺乎自然,由此感受“天乐”。现实之中的人之所以不自由,是由于其“心”被压抑、被奴役;只有冲破世俗、时空和礼教的束缚,做到无己、无功、无名,方可让精神安闲自适,自由自在地逍遥而游。显然,这样的逍遥无待之“游”只能是精神上一种虚幻之境。
如果说孔子之“游”在于“仁乐”,庄子之“游”在于“天乐”,那么,京派作家之“游”在于“艺乐”。它相应的是康德、席勒对“游”或“游戏”的解说。康德认为,只要是具有强制性与功利性目的人类行为(活动),皆与真正的艺术行为(活动) 无关;艺术必须如游戏那样,既自由亦愉快。而在席勒那里,动物和人的本质区别在于,游戏的属人性与自由性,即,游戏原本就是人的天性。不仅如此,人的本质属性、游戏的本质属性、艺术的本质属性,都根基于自由。由是,人理应与艺术美共同游戏:“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人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可见,人的自由指向人的独立、圆满、自足,或,一种超验的我,一种原在的我。故此,美及其所有人类精神范畴的创造物,如艺术、文学……等等无一不是朝着人的自由展开。
通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切语言都是人的自由本性的展开,因为正是语言使人从对象世界、感性世界、目的性世界中超脱出来。而又是物和词的分离状态,促使人类的思维摆脱感性直接性而获得自由特质。在人的语言共同体特别是文学语言的世界中,人类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只属于自己的“自由宪章”。如果说,现实世界中的自由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对挣脱束缚的向往,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是超验视域中的绝对自由,一种自由的终极性和无限度,一种本体论的自由化;那么,文学(语言) 的自由与人的自由恰恰是在上述逻辑前提下,被接收和被界定的。这实际上意味着,文学语言的自由所呈现的就是人的生命自由和文学创造的自由。
问题在于,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的表音性语言,由于在词性、句式、语法,以及人称、时态、语态等方面设有严格限制,其逻辑性和抽象性限定了人的思维和表达。恰恰相反,以表意为旨归的汉语言母语天然地具备了简洁、练达、含蓄、隽永的诗性特征。“汉字不仅是汉语的书写符号世界,更是汉语文化的诗性本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汉字的诗意命名奥秘隐含着东方文化的多元神秘性和历史象征性。”而追求精神自由和文学(语言) 自由的中国作家要挣脱种种限定性,抵达无限自由的境界,势必求助于文学母语并发掘、领悟其诗性功能。京派作家所坚守的母语写作的价值意义就在乎此,它能克服五四以来文学语言由于欧化而导致的过分抽象化和逻辑化的特点,发扬并创化汉语言母语感性、具象、鲜活和灵动的诗性传统。
在这个意义上,语言的自由所呈现的是个体性创作所展露的自由本质,这样形成的世界是自足的世界。也因此,“游于艺”的“艺”之“乐”是与宇宙同一、与生命同在的境地。生命的热情因此被转换为诗意的抒写。
三、“自由”而不“主义”与回归母语言说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文学语言的革命作为价值取向,集中体现在以白话取代文言以及实施语言的欧化,祈望借助这种变革来适应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需要。语言的改变不但引起生活、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变化,语言的革新更会导致思想和思维的重组。于是,白话文的兴起不单是以口语取代文言,它还被要求通过改变话语言说方式去整合和改造社会——实现思想文化启蒙的历史使命。由此,文学语言的伦理价值意义被极端地强调。究其本质,这种被改变了的语言可以说是一种典范的权力话语:占主流地位的语言模式具有潜在的权势性。因为它带有不容置否的力量,遮蔽了文学语言的独立性和自我意识,并使话语接受者产生误读,导致误解。
如前所述,由虚构和想象构成的文学世界摆脱了束缚人类天性的诸般框范,使得人据有自由的世界而无限地趋近本体自由和超越性存在。现实情况却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创作却总是身处不自由的语言处境之中,有研究者甚至感慨为“母语的陷落”。亦如此言,“文学语言的权势性大大逾越了它的文学性和自由性,由此造成了整个文学的倾斜状态。从‘五四’的思想式写作,三十年代的革命式写作,以及四五十年代到建国十七年文学的马克思主义式写作和政治式写作,整个中国文坛一直是价值语言系统的权势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并逐渐形成一种经过严密编码的语言系统、思维模式、写作模式以及能指所指间极其固定的直接联系。”
京派文学通常被指称为自由主义文学,我以为,其“自由主义”实际上属于消极自由主义之类。所谓“消极”,是指它淡化西方式“现代性”诸如社会进步、文明进化的历史取向,具体说,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现代中国的社会解放和民族救亡的实践内容,因而曾被认为属于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所谓“自由主义”,则表明它同时又汲取了“现代性”的个性自由、人格独立的本质涵义,彰显出一种卓尔不群的文学姿态。对问题的进一步探求可以发现,京派作家的母语写作体现出一种解构意识,解构五四白话文学建构的运动式文学话语运作机制,建立起理想的个体书写方式以及个性话语,并以对“文艺复兴”(周作人语) 的吁求来重构母语写作的新传统。
在京派作家那里,母语文学是其自由个性的展开——他们可以从应然世界、目的性世界和对象世界中超脱出来,自由驰骋于文学的世界。朱光潜就认为,“美术不但可以使人超脱现实,还可以使人在现实界领悟天然之美,消受自在之乐。”即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实,在讲述小说《边城》的创作意图时沈从文曾说,“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并在自己的“湘西世界”中创设了一座供奉人性和神性的“希腊小庙”,通过对“希腊小庙”的凝神关注获得生命存在的诗化形态,从“边城”走向了“世界”。质言之,沈从文以“湘西世界”的独特创作,实践“游于艺”的理想追求。“他以超然尘俗世之外的审美心境,于边地的山石溪流之间,寻觅着自然人生的诗的种子。”应该说,沈从文的创作宗旨、态度作风、情趣风度都是京派同人自由自在的文学理想的典范。
与此同时,京派同人又与五四时期林纾们维护封建道统的文学观念不同,他们既注重文学传统的承传,更努力以母语文学精神创制新文统,转化西方文学资源。也可以说,京派同人是文学上的虔诚信徒和社会政治的高蹈者,语言成为海德格尔所说的生命存在的家园。朱光潜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即可如此理解:以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这一“入世的事业”,介入并超越现实生存——“出世的精神”。京派作家也常常被认为是借清疏的乡野和充满牧歌的田园来寻求灵魂的归宿。我却以为,京派同人是一些心智高深的族群,他们其实深知乡野田园的回归无望,即便如沈从文也每每表示出对其笔下“湘西”回归的虚幻,然而仍然执迷不悟地寻觅和追求。也许,他们真正能寻求能皈依的当属母语文化/文学的精神家园,这才是所谓诗意的栖居。惟其如此,“游于艺”方可像王国维说的“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四、艺术化人生和“诗意地栖居”



完全可以说,京派文学所关注的不是客观的对象化世界,而是主观的意趣所在;京派作家所向往的并非人的行为事功,而是人的心灵思绪。京派同人擅长于以虚静胸怀和澄澈目光,去探视世间的时迁物移、人情事理;他们力图排解浮世的营扰,信守于语言艺术中去开辟自由清明的文学境界,寻览自由自在的精神安顿——海德格尔式“诗意地栖居”。情况往往是,人一旦置身于自由清明的文学世界,摆脱了框范、束缚人类天性的诸般机构,便会因为这种拥有而无限地趋近本体自由和超越性存在。为此,京派同人有关“乡土”的叙事,就是在有所思中获取了极大的心境自由,且转化为自足的审美思维方式,和自适的创作行为范式。这就是我所说的“游于艺”。


无疑,这是“自由”而“节制”的文学意识和生命态度。它包含:自然高洁的人格理想,艺术澄观下的人生境界,静观沉思的生命体验,精致优美的艺术追求。当然,所有这些都被“节制”在母语文化精神中。京派同人祈望从人生中创造艺术,以艺术融化人生,以“游于艺”而诉求于生命的艺术化——在“游于艺”中去实践他们理想的生命存在方式。问题的关键是,语言的自由是文学创作终极性的创作趋向。如果说,文学是源于人类心灵的呼声,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呼唤;那么,作家只要趋于对生命存在和人类心灵的聆听,就会自觉地皈依文学。同理,作家对文学的皈依就自然会追寻语言——走向存在的家园。如此,人、文学、语言在本体性自由中,既相互见证又融为一体。可见,语言自由是文学自由的本体,而语言自由与文学自由最终归结到人的自由。即,从人生出发,通过对文学这一语言艺术的现代性型塑,实现对生命形式的美化,母语写作便成为实现生命形式美化的不二之选。这种“一念之本初”既是母语文化精神的彰显,也是京派同人“人生艺术化”的价值诉求。
必须指出,京派同人相对闲适的社会地位,较为优裕的生活条件,也都间接地成全了他们“游于艺”的心态和气度。实际上,完满、自足、清雅的环境,与偏安于“艺”之一隅之间,无形中存在着一种必然联系。况且,偏安于“艺”之一隅,何尝不是另一种执着。能做到无所着染却又入世有为,所谓“应物而不累于物”,未必不是更深的人文关怀。
注释:
①②杨经建:《新古典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艺研究》2006年第4期。
③杨经建等:《解构与重构: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母语化进程》,《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④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⑥⑰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0 卷):花城出版社 1984年版,第266页、第279页。
⑦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一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⑧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后序》,《沈从文文集》(第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⑨何其芳:《梦中道路》,《何其芳文集》(第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5页。
⑪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岳麓书社 1987年版,第6页。
⑫[德]席勒著,徐恒醇译:《美育书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4年版,第90页。
⑬王岳川:《汉字文化与汉语思想——兼论“字思维”理论》,《诗探索》1997年第2 辑。
⑭郜元宝:《母语的陷落》,《书屋》2002年第4期。
⑮王中:《文学语言的自由和人的自由——兼论20 世纪中国文学语言的流变》,《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⑯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8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3页。

⑲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 卷),安微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⑳滕咸惠校注:《人间词话新注》,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