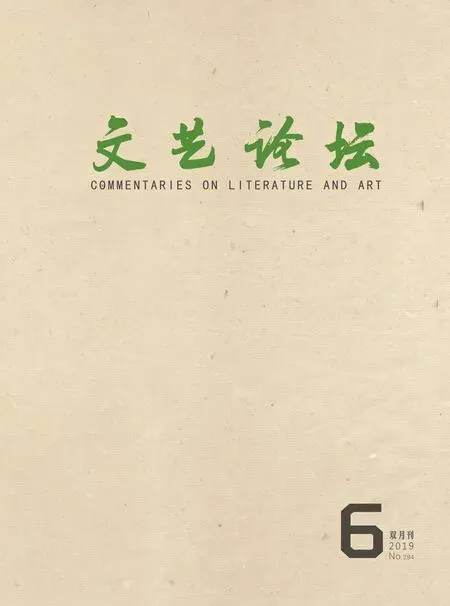巫道文化与当代湘西文学的自然精神
2019-11-12彭继媛
◎ 彭继媛
湘西是一个保留着浓厚巫文化色彩的有着明显地域性特征的地方,沈从文、黄永玉、孙健忠、蔡测海、彭学明等作家出生于湘西,有学者以为“历史上道家文化与巫文化互相渗透,使得湘西文化既保留了特有的文化特质,也染上了道家色彩,这种道家色彩以一种集体无意识方式积淀在沈从文的内心中,使沈从文的创作表现出了道家文化意蕴。”而我以为,追随着前辈湘西作家沈从文的写作传统,黄永玉、孙健忠、蔡测海等当代湘西作家创作不同程度不同角度地表现出了道家文化意蕴。或者也可说具有突出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湘西文化从另一角度也强化了沈从文等湘西作家对道家文化的认同,成为沈从文等湘西作家自觉或不自觉接受道家文化的接受场。在湘西,巫是原始宗教的遗风,来自自然,贴近自然,道家则提倡道法自然,以自然精神为法则。道和巫在这方面的相似性构成了当代湘西作家在自然观上的独特性。鉴于沈从文开启了当代湘西文学的传统,本文将沈从文作品同样纳入了研究视野,并拟从书写静幽澄澈的自然山水、呈现湘西人自然本真的人性,保持与世无争的生命方式三个方面分析巫道文化所蕴含的自然精神在湘西当代文学中的体现。
一、书写静幽澄澈的自然山水
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崇尚自然、笃信鬼神,相信一切有形或无形的自然现象、自然物都有“魂”或“灵”,相信自然本身充满着无限生命力和神秘力量。而这些神灵具有超凡脱俗的能力,影响甚至主宰着人的命运。巫楚文化对山水精灵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而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士子不满于现实或在现实中失意时,往往不仅在行动上回归自然,而且还用文学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回归自然后的美妙,或者直接在文学作品中勾勒心中的理想社会,寻找真正的精神家园。远在先秦老子心中有“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庄子有“至德之世”,随之而来有陶渊明、王维、韩愈、王安石、苏轼等的桃花源,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蒲松龄的花妖狐魅世界等等。深受巫道家自然精神浸润的当代湘西作家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条件,他们无需在内心中构建一方山水,而纷纷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已化为自身肌理的的湘西自然,在诗意宁静、充满灵性的山水间寄托自己悠远深邃的情怀。
沈从文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清灵俊秀、宁静怡然的湘西自然世界。《三三》中的夹溪山田,《黑夜》中的水苇泥泽,《阿黑小史》澄净、祥和的境界等等。此后当代湘西第二、三代作家秉承沈从文对湘西优美宁静山水的书写,寄托着他们对家乡无限的深情。黄永玉《蜜泪》中苍翠之极的峡谷,有白鹤灰鹤做窝的柏树,岸边的铁铺……叙写着凤凰城内百姓宁静祥和的日常,颜家文《清明茶香》中白雾缠绕的小镇, 《小溪哗哗》 中豆绿的溪水,《牧歌与归途》中的故乡的梯田、密林、小路,火塘等无不在述说着湘西自然山水宁静温暖的点点滴滴。蔡测海《母船》中陡峭的山,半间屋大的树,自然天成像怪兽的巉岩,窄而险的山路等等,构成了白河流域两岸神奇独特的自然风光。侯自佳《沅水放排》沅水两岸秀丽的风光,吴国恩《无雨季节》“依山而筑,寨子里竹篁幽深”的故乡苗寨,彭学明《在故乡的肩头》苍劲又滋润的家乡保靖,《白河》中空明澄澈,纯净与爽朗的河水,张心平《黄昏,静悄悄》中夜幕降临前祥和宁静又充满着生气的村寨,向启军《生命之泊》中静幽的老家长田河,田特平《悬崖上的野菊花》中蘑菇崖下水清如镜、碧绿如玉的蘑菇溪,《老人与树》中清澈明亮、汩汩潺潺的玉泉河,龙顺成《酉水》中沿着河崖一致挺着的黑瓦木楼,彭世贵《凤凰》中如画的凤凰小城,类似之处,不胜枚举。
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中,人们相信万物皆有灵。此后湘西作家同样如此,田瑛作品中的自然景物是非常有灵性的,他曾说“老家自古巫风盛行,除了赶尸,还有轮回转世一说。”黄青松《名堂经》中那棵长在寨子中央的遮天蔽日的“神树”,成为花桥人顶礼膜拜的神圣。而湘西作家对大自然的深情礼赞,并不意味着他们要做故土风景的忠实记录者,向启军曾说“永不停歇的风霜雨雪中的奔波劳顿,游子们已是身心疲惫,可望不可及的遥远的故乡便日渐幻化,最终变成了一片绿洲和黑夜里的最后一支烛光。因此游子们梦中的故乡,已无比完美,距离现实中的某个村庄已经很远了。游子们不回去,故乡就装在他们心里。心中的故乡温暖着他们,支撑着他们最后的信仰和希望。”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生于斯、长于斯的当代湘西作家纷纷把纯净而恬淡的目光深情地投向有着湘西田园世界里安静的大地、蓬勃的草木和简朴的村庄,向人们提供一个可供皈依的诗性的湘西世界。
二、呈现自然本真的人性
巫文化是一种有原始宗教意味的区域性文化,正因为它“在含魅的浑浊中保留人与自身神性的沟通和桥梁”。“所以人能在地处边缘、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的‘边城’中,固守自然的本性,在与大自然的亲密相处和灵性往来中,展现出最无机心的原始人性和人性中的神性。”而老庄道家反对异化人生异化人性,维护人的自然性情,追求一种自然和谐的生活。从自然之道出发,庄子与老子一样,主张人性之自然,强调人“不失其性命之情”,“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性命之情”即自然人性,庄子多次强调“真”“天真”“纯”“朴”“本”“性”“情”等,都是指自然人性。老庄道家视域中的“自然”是一种对天地万物本然状态、通常状态与理想状态的一种肯定,是一种对“真”生命的守护,也是对本真人性的讴歌。
深受巫道文化影响的当代湘西作家不遗余力地讴歌自然本真的人性。沈从文在他的湘西世界中最为典型地讴歌了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例如《柏子》《阿黑小史》《雨后》所表现出来的湘西世界中的强壮与健全的人格与城市中缺乏生命活力的“阉寺性人格”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充分体现了生命的本真。湘西边地的民间风俗也是沈从文着力用来表现的自然人性的一种方式。此后湘西第二、三代当代作家同样在他们的作品中以自己的方式同样讴歌自然本真的人性。彭学明《边边场》中对男女情爱奇异风俗、《赶秋节》中对秋千上歌男歌女以对山歌决定情爱方式、《踏花花》中对年轻生命放肆的爱情流光溢彩的书写仍是强调湘西人张扬自由的个性,追求自然本真生命的表现。而以下作品中湘西女性对爱情的选择无不显示着她们不受外界世俗干扰的本真人性。田特平《青草长在小河边》中纯净的姑娘菁菁不为卡奎丰裕的财产所动,表明自己爱的是像泥土一般踏实的人。向阳花《雪》中二翠除了那个聪明、标致而又勤劳、能干的后生仔,就算哪家是金子做屋檐、银子砌阶沿也不嫁。黄青松《打样》中的竹叶儿虽被迫嫁给了富裕人家的儿子,可她内心钟情的却是自己一眼就看上的打样的穷小子。值得一提的是黄永玉总喜欢用儿童的视角感受故乡,“我走在五十年前(半个世纪,天哪!) 上学的石板路上,沿途嗅闻着我曾经怀念过的气息,听些温暖的声音。我来到文昌阁小学,我走进了二年级的课堂,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黄永玉,六乘以六等于几?’我慢慢站了起来。课堂空无一人。”故乡早已物是人非,但这种温馨的记忆却依然如故。而这未尝不可视为是黄永玉对充满着本真人性和素朴单纯生命形式的无限怀念,其《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中得胜营的二舅是一个本真的人,虽谈诗论道头头是道,但儿时生病烧坏了脑筋,心智如孩童。田特平《哑大》中哑大也有这样的本真人性,听不到声音就没有一般尘世人的烦恼,七十多岁了还像个孩子,脸上随时挂着微笑,喜欢吃完晚饭就在小巷口的城垛上放风筝。这种孩童的思维和智慧可以使之从规则礼俗之中解脱出来,使他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他生长其中的传统文化体系,给他带来相当程度的自由。而巫文化对神性人格的追寻以及道家文化构筑理想人格的出发点就是消除一切外物对个体的奴役,“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物物而不物于物”,达到个体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因而湘西人貌似傻子的超越、自由与巫文化对人性中对最无机心的原始人性和神性人格、庄子所说的超越世俗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追求内在心灵上的自由。
黄永玉曾说“朱雀城建立在云贵高原的末端、山径回环、丛草蔓生之地,没想过带轮子的文明哪年哪月会滚到这里来。”即使随着现代文明不断地浸入,这里明丽山水的温暖怀抱哺育的边地山民仍然保持着质朴善良的人性。从以上当代湘西作家对自然人的刻画可以看出,诸多当代湘西作家对具有自然人性的人物的追寻承续了沈从文建立起来的价值取向,而这都源于他们把自己的立场深深地植入了巫道文化对自然人性的推崇。在这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年长还是年幼,他们都遵循自然的法则,不掩饰不做作,不受外界文明的干扰,当代湘西文学有了他们的存在显出至纯至美。
三、保持与世无争的生命方式
巫文化“万物有灵”“人神合一”的观念孕育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美好乐园。而“‘万物有灵’并非对自然的臣服和对自我命运的放弃,它是人类渴望与自然沟通以知道和掌握自己的命运的积极行动,是人类向大自然表达尊重和感谢的心理诉求,它有效地抑制了人的狂妄、贪婪、残忍等,张扬了人要用超自然力量控制外界的自信、人与自然平等相处的和谐、人释放焦虑和满足自身需求的祈愿。这种原始的思维方式造就了特殊的生命形式,即人性率真自然,达到与自然的神意合一的生命状态。人们在有神的时代,都能保持一颗单纯的心灵,享受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按自己的本性自在地生活。”跨越生死,超越苦难,实现精神的澄静与超脱,达到了人与神的合一,这是巫文化给予现代人的生命启示。而道家自然精神认为只要顺应和保持自然人性,人生价值就会自然生成,人生意义就会自然显现,人所做的就是退避自守,保持自然而然和无为超脱的人生态度,这是实现道家自然精神价值理想的原则。以此来观照当代湘西散文,作家文笔或清新,或闲适,或谈天说地、或品评风物,其胸次之悠然,其笔调之淡泊,与其说是他们的个性使然,不如说是他们深受巫道家自然精神的影响向往安适生命之道的内心流露。另外沈从文、黄永玉、蔡测海、向启军、田特平等也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来表现他们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
沈从文在《湘西·题记》中认为湘西之所以处处显得落后,是因为湘西人始终自负地保持着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沈从文的这一看法在湘西作家中较有代表性。向启军冲淡平和的心境,超然世外、达观潇洒的人格姿态在散文《吃茶》《阳戏》《界上》《小街驶过乌篷船》等中跃然纸上,例如《吃茶》:“守牛回来,或刨园子回来,已是夕阳悠悠坠落西山的黄昏。……一人独自吃茶,是悠闲,是得意”其《界上》男人女人春耕夏牧的情景更如世外桃源。龙顺成《流情湘西》中一生中年复一年默默打草鞋挂草鞋、任人随意来取草鞋的小脚婆婆在隐忍恬淡中修炼成了达观超脱的心性以及任性随物的人格品性。而柳丛梦在《散文三题》中更是直接指出:“以为得一份散淡是人生的超越。散淡是漫不经心而心境淡泊。……散淡构成的是一种内涵及其丰富的世界。散淡是气质,是天赋,是没有私欲的自在人生。无论做人还是做文柳丛梦推崇的是自得其乐、平心静气、随遇而安的那份闲澹与洒脱。
此外当代湘西作家也在小说中刻画人物来表达他们随遇而安、闲散淡泊的人生态度。沈从文建构的湘西边地世界,讴歌了和谐自由的原始自然方式,《边城》中的翠翠静静地等待傩送回来,“这个人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回来”,既有难以名状的忧伤,也有一种超然、轻灵的神韵。《菜园》中的老太太和儿子在闹市中保持一种超脱、淡然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老太太在儿子儿媳去世后仍隐忍淡泊地活着,更是显现了一种超然的生命形态。向启军《红斑草》中曾为参谋长的乔雨麦经历了人世沧桑变化之后最终拿起了犁耙锄头,躬耕于垄亩之上。乔雨麦身上有着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随性适分、旷达超脱的处世态度。田耳《界镇》中的“我”主动选择去一个与世隔绝的荒蛮之地工作,因为迷恋于乡村淳朴的乡情和简单平静的生活,“我”的选择是理智的也是从容的。田特平《透和尚》中透和尚不是和尚,是一般的俗人。他的妻子跟人跑了,透和尚不去找,别人询问他,他也是淡淡一笑,表现出不急不躁的态度。一切顺其自然。这正如他在《顺其自然》中所说:“不刻意,不乞求,不自卑,不轻狂,不烦恼,不忧愁,不妄想,不失落,一切一切,都顺其自然,这样的人生不亦悦乎?顺其自然是人生的大境界。”田特平《花儿与少年》中名噪一时的“满花匠”坦荡、知足地生活,自然地看待生死的轮回,他对死亡的超然态度和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都与道家的思想不谋而合。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中称“朱雀城海拔一千零二十市尺高。春天树上长芽开花;……一季三个月,一年十二个月完全规规矩矩按黄历行事。”足以见证朱雀城里的人过着随遇而安、简单、自然的生活。而其中得胜营的二舅娘就过着这样与世无争的生活,二舅娘是个温柔贤淑的女子,相貌一般,大字不识一个,她沉醉在琐碎的生活中,对她而言,“二舅早起来魏晋唐宋地吟哦,较之公鸡报晓更失意义。生活一切中规中矩成为习惯,无欲求,无企盼,无认命意义。”
从古迄今,湘西世界巫楚文化、道家自然精神无所不在,深受巫道文化影响的当代湘西作家通过书写澄澈静幽的自然山水、追求一种自然人性来最终表现其遵循自然法则随性而为的淡然的生命追求。当代湘西作家作品因注入了巫楚文化、道家文化自然而然的生命意蕴而获得了别样的清新、隽永、豁达、智慧、纯美之气。

注释:
①李健康:《论沈从文“新道家思想”》,《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版)》2010年第3期。
②田瑛:《未来的祖先》,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③⑭向启军:《向启军小说散文选》,民族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5页、第241-242页。
④雷鸣:《巫楚文化的诗意镜像——韩少功创作片论》,《山东文学》2007年第2期。
⑤⑬易瑛:《巫风浸润下的诗意想象——巫文化与中国现当代小说》,湖南师大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页、第119页。
⑥《庄子·骈拇》,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5页。
⑦《庄子·在宥》,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1页。
⑧参见郁建兴:《中国思想中的自然主义》,《杭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⑨⑮柳丛梦、张心平主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州40年优秀文学作品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第209-210页。
⑩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页。
⑪⑯⑰田特平:《寻觅双命鸟》,作家出版社 2008年版,第83-84页、第98页、第253页。
⑫⑱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中)》,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年版,第474页、第532页。
⑲江碧波、陶继锋:《浅谈巫文化的美学内涵及其艺术创作》,《新西部》2009年第2期。
⑳祁洞之:《佐思录(卷二)逻辑哲学讲演录》,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