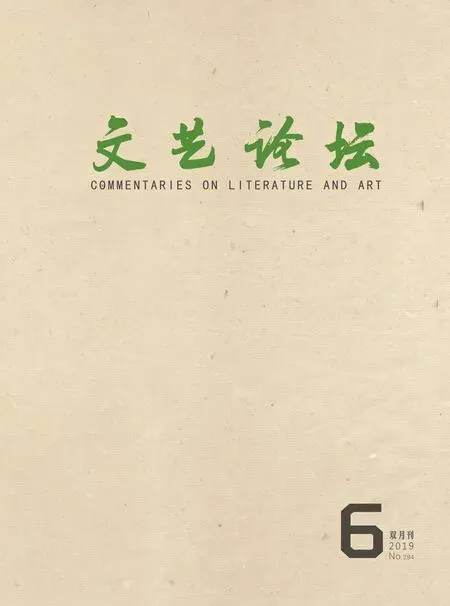电影生产的工业化组织管理与“电影工业美学”研讨纪要
2019-11-12李天铎陈旭光宇等
◎ 李天铎 陈旭光 向 勇 陈 宇等
陈旭光: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台湾昆山科技大学创意媒体学院讲座教授,文化产业研究资深专家——李天铎教授。这几年电影工业化、电影“工业美学”等话题成为热点。天铎老师从电影研究,转向大文化产业的研究,可见这两者之间有很多共通的东西。今天除了李天铎老师主讲之外,还特意约请了几位嘉宾:有创作经验的陈宇教授、导演;文产专家向勇教授。还有肖怀德,我的第一个毕业博士。他的博士论文是《中美制片人中心制比较》,那是2012年,在当时是颇为前沿的一个话题。
今天我们两岸三地电影人、文产专家汇聚一起,相信会有一个充满智慧的碰撞。
李天铎:大家好!近年来我把亚洲电影做了一些资料的整理,做一些比较和汇总。亚洲电影说穿了,印度是泰斗,真的很旺盛,但其实第一是中国、第二是韩国、第三是日本,就这三个。这三个是真正有产业实力、有产业结构的。今天的香港、台湾,通常只有片量但没有产业结构、没有规模、没有系统、没有制度。
中国我访问了万达总经理,访问了阿里、光线、华谊,还有于冬。香港我去见了庄澄、施南生,还有陈可辛导演。
电影这个行业,是一种影音商品,取决于千万消费者的口味,消费者非常固定,又会有反复无常,难以琢磨。电影、动画、漫画,都是所谓的叫做“体验性产品”。它们的生产没有办法用效率、精确计算、可预测性、严密控管去推进。管理学和MBA 专门就用这四个来最精准地控制和讲究产品的效果。但是我今天想讲的就是因为这个产业没有办法做到这四点,造成了电影产业可以像美国那样非常自主化。
第一,电影产业的结构,是企划到制作,到发行,到运营,到后来一系列的通路通下去。在这个结构体系里面,最咽喉的是发行。当年香港嘉禾电影公司董事长邹文怀就说发行是咽喉,是因为有发行,前面这些都得以成型,后面的窗口都可以实现;因为发行的承担保障,投资人有保障了,因此这个片子就会有很多的通路,所以说发行是咽喉。
中国大陆电影界有一个错误的观念。用“宣发”去替代很多东西,这不对,太窄化了。发行工作、检查票务,甚至还有公司请水军,这个是宣传,这个跟distribution(分配,分发) 有差别,这是中国目前可能最大的问题。我听到的包括学界都是在“做宣发”,尤其我最近看到的资料,这个“宣发”被谁取代了?这两个字被票务平台如猫眼,还有淘票票取代了。整个结构都变了。
我问了阿里和光线,问他能不能告诉我一部片子全部结账时,如果你收了100 块钱,大概有多少比例的钱是从影院来的?万达说90%,阿里估算是85%左右,平均大概是在85%—90%之间,而美国是27%是从影院过来的,这个差距太大了。如果是100 元,美国只有27 元是从影院来的,77%是从后面(家庭影音、网络视频、付费频道、广播电视、其它授权) 出来的。
好莱坞从企划开发走到发行,走完这么一圈(从企划开发到上述五个分支) 是7年,7年把它走完一圈,然后7年结账。
中国就变成直接到影院这里,这样很危险。陈旭光老师说的“电影工业美学”的各种结构化分层问题,这个结构化基本上就是以基础为结构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你上面再压重工业下来,还有高工业投资(你投资越大,你的回收应该越多,才越保险,回收窗口越多,钱就回来的越多),结果全部拿来堵这个票房,85%在票房上面。这个结构不正常吧。
在美国,再小的片子,再小的规模,它都要走完完整整的一个经营模式,这个叫做产业管理模式。《Green Book(绿皮书)》的预算是2300 万,全球(票房) 是3 亿多。美国的市场,第一个窗口(映演影院) 只占了27%。其他的都是别的地方来的钱。这个产业就是这样,票房赔了没有关系,别的地方可以补,补到7年以后大概能够过去,这样才健康。尤其是前面的制作是这么风险高的,那么不确定的。你面对那么不可控制,那么反复无常的,后面又有步伐,这个步伐是美国针对这个要控制的稳稳的,不能出问题,这个都叫创意管理,各个行业的创意管理,电影有电影的,电视有电视的,电视有控股的。
网络视频Amazon,它已经有一系列电影了,有些都没有被注意到,当然有些也许是不成功的。对Amazon 来说在不在乎(票房不成功)。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在这个平台上渐渐有知名的好片,他们一直这样做。所以这个就是我问阿里的,我说阿里自己也有平台,Amazon也是一个电商、零售商,Amazon 的概念是这样:你要买书到我这边来,你要买杂货和生活用品到我这边来买,可是你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别的方面,影音娱乐为什么不可以到我这里来买?它就开始做这件事,它的目的就在这儿。到我们这边来买,它就开始提供很多影片和剧,他们开始要出剧了。
我们来谈一下迪士尼。中国大陆总是在提我们有大电影,我们是电影大国,我们的电影将来是超越美国超越全球的。你想超越它,它是怎么做的?迪斯尼把发行、映演、制作三个环节都掐在它自己手上,任何的一个题材经过这个流程后都可以做成产品。比如一个小的故事进来可以变成一个主题公园叫海盗游乐园,二三十年来也没有改,他们就说这个海盗游乐园我们把它改一改,干脆就来弄一部电影叫做《加勒比海盗》,然后《加勒比海盗》再回头又可以去改那个主题乐园。我们在中国听到的是之前万达说我们要把迪斯尼赶出中国,我们要弄40 个游乐园。然而今天呢?因为你没有它的theme park 那个theme。迪斯尼是一个大的蜘蛛网体系,它有自己的拍片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戏剧展演公司、舞台剧展演公司,它自己有media,有电视台,有电视网,然后有互动媒体。现在大概还要把Hulu 收进来,有一个迪斯尼plus,就是它准备做Netflix,由迪斯尼plus 这个品牌做出来。
这是美国票房。诸位可以看到第7 个《战狼2》,是8 亿7000 多万的收入,它被挤到第7 名。这个domestic 是在美国的一个观点,它没有在美国本土卖,它还有国际的,它只有0.3%。Overseas 当然就是指中国了,占了99.7%,所以中国电影是属于一种内向性的。在中国如果现在强调重工业、大工业什么的,你那个投资高下去,你还只靠一个电影窗口回收吗?以前10 块钱拍的电影靠一个窗口,你现在要追求大工业、重工业等等投资100 块下去,你还是这个窗口吗?对比的话,说我们要超越它,口口声声说要超英赶美,变成世界一流的大国,你要超越它,你要超越它什么?我们学界应该去研究一下。
回到中国,一个电影形成健康生态最大的三个影响因素:第一,行政的规管;第二,“营销”两个字坏掉了所有的事情;第三,金融。
我问过他们片商,我问你愿意去票补哪一类的片子?他说当然要比较有市场性的各方面的片子,可以让消费者花二十几块就来看,他愿意做这个片补。那我就假设,我说今天来了一个《百鸟朝凤》,人家哭哭啼啼的,没有地方放了,这种片子如果上映了,你愿不愿意?照理说你应该去救助的,去贴补,让大家去看。结果最后消费者,我今天要看一个电影,我要看一个《百鸟朝凤》,我要花全价,大概要50 块还是60 块。可是我今天看一个大片,乱七八糟的大片,只要29、39,你说我看哪个片子?这个会扭曲市场的价值。
还有地产,我问过广电总局的研究员,他说银幕数又增加了,可能到了9000 多块,可是上座率持续下滑,就表明没有那么多人看,就算是看的人不够多,它还是会拼命建,因为那是地产,是商城。商城里面一定要有影院,商城里面要有百货公司,商城里面还要有吃的、喝的、玩的。电影院影院要拼命地盖,拼命地扩建,就变成这样了。
这是当年美国的音乐产业,也一样,艺人、唱片公司、音乐集团,出版的CD 到消费者,主导的(就是主要的发行品) 是那个video。这个是record label,一样的,艺人、唱片公司、唱片集团,然后出来了很多的平台、娱乐公司、live concert、online platform 都出来了,整个都建构出来了,每一个区块每一个区块都建构起来了。看中国大陆现在的问题出现了,中国大陆有没有音乐集团?没有音乐公司,有音乐艺人。艺人自行组一个音乐团体,就是这样的,然后完全靠什么?就靠艺人的music major 和online platform,主要靠这个。
台湾更糟糕。年轻人要拍片就找政府补贴一点,弄个几百万,然后再到台中市政府拍,台中市给一点补贴,然后再拉到高雄去拍,高雄再给一点。然后自己把房地产押一下,凑了钱就拍了。这个就是台湾主要的生产结构、生产的模式。
香港就更没了,香港现在全都要靠大陆,等于说补贴、制作、集资全都要移到大陆来,贴着大陆的身体。我看它的力道也差不多了,一天到晚就是《反贪风暴》或是《寒战》的。
日本的经济实力是真的停滞了,但还是富裕大国。日本每年有30%的人口递减。日本又是非常封闭的,它不喜欢外来的移民,人口就一直萎缩。人出生率少,年轻人就越来越少,人口就萎缩。年轻人萎缩了,电影人口是最主要的人口。这是东映的总裁跟我讲,他们就想办法在这个市场萎缩里面开始找出一个新的模式。
我用《死亡笔记》 举例,他们最近在重拍。《死亡笔记》谁的版权?出版社或者原著都可以。然后电影谁来拍?东映。然后电影原声带谁来做?找头绪吧。这个电影要发行找东映的院线,这个DVD 要租售,那就找DVD 的影音商进来。然后电视这个很重要。如果是《死亡笔记》,我举个例子,朝日,这个日本电视台,然后再来是WOWOW 卫星播映,再来是网络视频AMAZON,再来是电通,然后衍生电商玩具进来。看结构,通常电商玩具会占到日本一部电影总收入的60%到70%,这么高。为什么现在日本电影的走势拼命走向动漫二次元。很多的题材都是从那边过来的,很多的题材都不是原创的,都是从漫画这些东西过来的,这个就变成说经济的结构影响到它产品的产出。因为我一定要动漫,我有动漫,我后面才有衍生玩具的生意。我一定要动漫才会有DVD 的市场,后面才会强。很多原创的东西就很难去操作了。
日本电影的发行体系是非常健全的,日本的电影如果是三大电影制片厂,它们有它们的发行体系,有他们直属的院线。如果日本电影是有独立制作公司的,那么独立公司拍,它有独立的发行系统,到独立院线去。所以到涩谷到新宿,有的时候走到一个巷子,旁边居然就是一个影院,专门放映它独立的小片,这种小片大概进去看是六七十人的位置。一部片子放一放,涩谷这边放五六个小厅,新宿那边有三五个,然后拉到福冈那边又一两个,拉到大阪又三五个,这样走过全日本也有好几百小厅在放,那个钱一点一点的回收,也收得回来。它还有一个体制就是美商进口片,当然片子直接从美国就过来了,美国自己在那边有发行的系统,非常强。还有一些进口影片,像戛纳的最佳影片,这些艺术片什么的,它自己也有专属的院线去放,这是整个体系。
在这样的一个体系,消费者要看各种影片,你都知道该去哪个地方选择合适的商品,然后发行的人也应该知道这样的影片在什么样的通路去发行,绝对不会出现《地球最后的夜晚》 的事情。《地球最后的夜晚》应该是属于独立型的制片,不应该跑到那个体系上去。那样的做法是没有商业伦理的,那个做法是透支文艺片未来的发展资本,透支创意生产。毕赣的第三部片子谁会来看?都先防着会不会再被骗,这是透支。
这是日本,这个是他们的电影创作团队,这个是委员会组织起来的,各种的人才来了,把它委托给制作公司做,或者是导演的制作公司也可以,或者是什么特别的制作公司,都可以。然后它就去做,这些委员会就开始定有什么权利,大家的权利,他们各自的权利,在音像的、DVD 的或者是衍生商品玩具、游戏的、出版的授权,然后它有第一次收入,然后有后续收入。
这是韩国。我去访问了CJ,韩国电影的制作,在2002年左右,政府跟投资方跟制片方三边做了一个协商,如果要拍一部电影,有什么程序?有开发、制作、行销到发行,有这个程序。每一个程序上面要做一些什么事?这个都有信息的,他们有个表。制作的时候有什么事,要花什么钱,有什么支出项目,都列出来。列出来最大的精髓、最大的意义在这边,大家都列出来了,三方都看到了,以后你拍片的人就不要乱忽悠了,就照着这个预算做,投资方一看就照着这个预算看,没有骗你,你放心。他放心就把这个钱进来了。主要是说这个资金相互之间就成一个信任了,然后这个信任要进一步的保护,怎么保护?这是规定的,你们回去可以查韩国的这个规定。这样的话,拍片的人规规矩矩地做,投资方就很放心,这个钱就愿意进来,就通了,这个钱就不会像现在中国大陆这样还有投资参股这些问题,现在都说不清楚的,韩国现在就规范成这样。CJ 跟我讲说他们现在这个体系真的是让整个制片的供需双方非常的有信任感,这个就是一般管理学讲的建立市场秩序。引到这边来,我觉得中国大陆即将会变成世界第一的大市场,市场秩序的建立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议题?不要一天到晚忽悠忽悠的。
我觉得中国一定是世界电影大国,票房现在600 多亿。照理说它应该有1000 多亿,现在问题是往1000 多亿的媒体上走,我们在学界应该清楚在这个路上还缺什么,都要把这个给找出来,这是我们学界的价值所在。
陈旭光:感谢李天铎老师精彩的演讲。他以开阔的国际视野和亚洲视野,以他多年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的经验,会诊了中国电影产业,他对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的概括,对症结的揭示非常清晰,一针见血,现在真的很难听到这样赤诚的,“恨铁不成钢”式的见解。他的判断都是立足于资料、材料以及比较,这样的学术研究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
李老师主要是对于中国电影产业存在的很多乱象,最主要的比如说产业结构不合理、营收渠道狭窄单一,非合理化的均衡的布局这些问题有很多很深入的阐释。中国电影的确乱象太多,但是有时候我又觉得很奇怪,其实有很多时候这些乱象也不能说他们不知道,对于多条腿走路,多产品的开发,多渠道的多样化,甚至我们也叫了很长时间的制片人中心制等,他们也不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实行不了呢?“分级制”也是如此。我与浙大范志忠教授做的《中国电影蓝皮书》,遴选出10 部年度最具影响力的电影进行深度分析,叙事的、美学的,但是最重要的一块是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我也要求作者偏重制片宣发和营销,但是做起来非常难,因为它乱象很多,很多制片公司是浑水摸鱼,或者是脚踩西瓜皮走到哪里是哪里,以乱对乱,所以他不给你说实话,这里面有很多暗箱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怎么去破解,怎么进一步像李老师刚才引进域外的视野,那样一种工业形成的规范化,各种架构的合理化,我们如何去推进它,改进它?如何破这些局?循着这些话题,我们继续给中国电影产业进行会诊。请陈宇教授。
陈宇:天铎老师作为台湾学者对大陆的电影产业和结构能够这么深入的认知,非常难得。他已经摸到我们这个产业的很多很深入的东西。我们也在研究中国电影产业,但是我们所能获取的资料,像旭光老师说的,人家对你不讲实话,去电影公司摸的材料、预算,包括片子发行多少钱,谁收多少,我收多少,全部是假的。李天铎老师的分析站在比较高的亚洲视野的角度,包括也面向好莱坞,同时对我们亚洲的三国的透视,抓到了问题的本质。
今天天铎老师讲到对中国电影产业的会诊,我特别赞同他那一句话:中国电影产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被两个东西搞坏了,一个是金融化,一个是营销。这两个东西实际上是我们目前为什么后面搞不好很大一个原因。但是这两个原因,不是它的产生,而它是一个结果,出现这种状况本身是一个结果。
第一部分是观念的问题,刚才我讲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实我觉得这三个环节里面,目前国内的销售环节,他们已经是花招百出,他们卖电影的已经是各出奇招,虽然有的是乱象,但是他也想尽办法来做这件事情。其次是销售环节的问题,票务的问题控制以后,问题还不是特别大。我觉得更主要的问题其实还是在前面两个重要的环节。第一个是研发,可以说目前的电影公司是不管研发的,现在所有的研发是导演团队或者是编剧团队或者是创作核心在研发,他没有任何的电影公司会在研发的阶段去花钱。大家都知道前面的研发工作是非常花钱的,剧本从策划一个故事,到最终剧本成型,再由一个剧本内容变成一个项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但是这一部分我们国内是没有的。
第二部分到制片制作的阶段。我以前认为我们在这一块已经搞了很多年,如何控制剧组预算、如何生产等等,这一部分已经差不多了。但是实际上在真实的工作空间、生活空间还是问题非常多,因为我以前老是觉得自己参与的项目可能不够高端,但我发现到了这种最顶级的制作的层面,管理仍然是极其粗放的。为什么这么花钱?这个预算为什么要这样?没有这个讨论,直接就拍了,拍完以后就交过来。基本上,我们换句话说,在这种最顶级的中间仍然相对是比较粗放的,就是它的科学性和精确性没有达到那么高的程度。也就是说这是我开始说的,我们在真正比如说在研发的生产环节中间的工业化,我认为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所以说我们要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要走的路,我认为还很长,是需要我们学者、从业者,都还要再花很大的精力去建设的一个部分。
向勇:谢谢陈旭光老师搭建这个沙龙的平台。他从2017年就提出的“电影工业美学”理论,是一个新的,是观照现在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些问题提出的良方,试图去解决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
今天李天铎老师从各种角度来看电影生产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范式。我想围绕这个主题:电影工业生产,还是电影工业美学,还是文学创新管理的主题来谈一谈我对旭光老师这几年围绕电影工业美学的探讨,以及这么多年对李天铎在创意制片共同去提的概念,创意制片管理,这里面我们到底怎么去认知,我从五个方面谈一下自己的观点。
第一,旭光老师电影工业美学的重大命题,开始我没有那么重视,没有认真地去读。后来慢慢学习很多,果然确实跟我以前理解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以前我认为他可能在现在的阶段对电影发展一种语言的修辞,让这些不太重视工业化的、标准化的,没有职业分工的这些电影行业的人士一个提醒,但后来发现不是,它是整个电影体系的一个梳理。所以第一个我想提的是“电影工业美学”这个提法从中国电影发展阶段来说,到底是在描述电影升级还是在描述电影的一个“固本”。我看陈老师或其他作者引了一些观点,其中有一句说:不管电影是什么品,电影一定是工业品。这一点很具象。所谓的工业品,就是他在逻辑的技术保证上来生产。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把它上升到作为电影升级,还是电影的一个新的时代的范式,我们对中国电影来说,从固本来说,说的好听一点先是补课,回到常识,回到电影的基本生产手段去看电影的工业美学。当我们提电影工业美学,一定要看它的一种专业分工思想,一种专业和专业之间的互补,包括我们说的行业契约尊重,以及上面有供应链的层次关系。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说回到常识,回到建立电影的一个分工体系。
第二个是从电影的本体定位,就电影文本来看到底是电影艺术还是电影其他?“电影是一个工业品”这是一个前提。工业品我不是说它很垃圾很low,很流水化,不是,它是靠一系列技术保障生产出来的。如果从我们文产的角度来思考,电影不管是宣传品、艺术品、工业品,它最后落脚是文创品。如果说是文创品的话,肯定是以IP 为核心的,这个IP 就是我们所说的智慧知识产权,在一个标准的商业环境下,电影的内容就是IP 生成的一个非常前期的开端。像刚才天铎老师说的,有的电影生产,它所有宣发的手段都是来源于他把他的商业押宝押在电影院线的票房上,因为他没有把电影作为文创产品。我们以前说的是1/3 法则,就是电影票房的收入是占它整个电影IP 的1/3,现在有人说27%,另外一个说现在是1/5 了,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属于文创意义上的,属于电影的文创产业,也就是说电影的票房收入只占总收入的20%。
我们刚才提到的互联网平台、猫眼,大家刚才说了抖音成为电影宣发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因为它有关注度,要把这些抖音的粉丝吸引到票房呈现他的关注,因为主要的宝都押在这个地方,如果他不是押在这个地方,可能他整个宣发也不会那么去做,包括炒作,它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吸引。所以我们要从文创产品角度来看,看典型的一个产品的内容形式、材料和场景,再来看我们整个工业的关系。这是第二个。
第三,我们说从电影的生产体系来说,到底是电影工业还是电影产业?虽然在英文里面是一个词——film industry,但是我们现在翻译成中文是两个词,翻译成是电影工业或者是电影产业。我们提电影工业,在我理解它要跟整个工业发展的使命环环相扣的话,其实就是怀德博士在他论文当中的一个发现,就是指的是在经典好莱坞时期,也就是1948、1950年代以前,好莱坞的电影制片体系,包括大家提到的以制片人为中心、以制片厂为中心,也就是说电影工业的时候,跟电影有关的生产要素全部是企业可以控制的,这是作为工业化的标准化生产的一个前提,包括演员、编剧、导演。显然我们现在是做不到的,这些他们现在都有自己的公司,都有自己的行业协会,他给你形成另外一个权利攫夺的关系。所以从电影制片的公司,作为电影工业的主体,你没有办法像当年1930年代到1948年代经典好莱坞时期,他们能够组织电影工业的所有要素。以制片厂为中心制的生产模式有一些保留下来了,组织生产为了方便控制成本,也为了节约化生产。但是也有一些刚才提到的跟导演签长达8年10年以上的合约是不可能的,都是临时雇佣制,都是项目制。所以我说这个是电影工业还是电影产业,或者是电影生态呢?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从电影的发展动能来说,这种增长动能到底是电影供给还是电影消费?显然,虽然现在我们是供给侧改革,消费在电影生产过程当中是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怎么进一步的释放消费,更好地消费呢?前面提到了,我们不能只看票房,虽然可能电影票房以后的收入很少,但是现在后面毕竟还有版权收入,比如说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甚至在传统电视平台上也都在播。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整个电影产业的统计数据是不完善的,因为我们现在只是报票房数据,没有基于IP 的。
陈宇:现在票房收益大概是10%。
向勇:后面的收入,如果电影产品是一个文创IP 的话,商标、专利、版权,授权就多了。
陈宇:现在是都收不上。
向勇:对,我们都是琳琅满目,顾及不上。
陈宇:现在除了票房,就是卖给网络赚钱。
向勇:我们说提重工业美学、工业美学是偏重的生产端、供给端,偏重的是我们生产者素质和他的机制,反过来,重工业美学,当然这里面我也看到您提的四个维度,四个维度里面有关于受众的维度。当然这个还有其他消费者的问题,现在我认为有这个消费能力,要么是消费渠道,我说除了线上可以看以外,去电影院算是看电影的话,还有是我们的供给产品,这里面供给产品开放就起来了吗?我们关于用电影工业解决它的增长功能的时候,就要看怎么去平衡这个供给端和消费端。
第五,中国电影的模式选择,或者是中国电影工业美学的未来。如何回到狭义的电影工业美学?这个我们要大大地回到常识去补课去固本。如果从电影本身发展来说,确实刚才前面提到了,还有很多当年可以从轻度、中度、重度去解释,也有我们在电影工业美学视野范围之外的。
陈旭光:主旋律?
向勇:对,就是那种故事,其实也不是主旋律。
陈宇:一些艺术电影,一些非常窄小的艺术电影?
向勇:对。但是这种窄小的艺术电影从狭义的电影工业美学来说,它也要回到常识,也需要工业化的生产。那么从广义的,或者是从泛义上的中国电影工业美学发展有一个适用的范围。我看见陈老师的一篇文章,把“开心麻花”的整个制作模式也看成工业美学。
陈宇:“开心麻花”也很工业。
向勇:我觉得这里面就有好多阐释和讨论的空间,到底“开心麻花”的模式是不是工业美学?我把它叫做一种美学创业管理。它的跨界、IP,它的标准化不是我们一般理解意义上的标准化了,它是把它舞台戏剧的IP 搬到荧幕上。
陈旭光:这就是一种中国的特色,跟我们说的美国好莱坞黄金时代的电影工业不一样,我们现在说建构中国的电影工业美学,应该与时俱进,应该在本土的意义上来建构。“开心麻花”从戏剧IP转化,自己又做戏剧,又做电影,成为了一个跨界的产业链运作,这也是中国特色。
向勇:我们看到旭光老师的电影工业美学的强大的阐释力和指导力,我们也期待。
陈旭光:感谢向勇教授,刚才他对我的电影工业美学理论提出了非常有意义的商榷,有的地方让我豁然开朗,比如说电影工业美学不一定要以古典好莱坞时期的工业化为准绳,为唯一的标准,因为现在很多语境都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电影传播的媒介文化语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互联网正在而且已经改变一切。大文化产业观念会对电影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
电影工业美学肯定是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但是从我分析的新一代导演,不同于第六代导演的一代人,的确可能好莱坞电影生产制作模式和供给化的管理生产方式更适合于他们,他们是比较务实的,比较商业化,对观众和制片人、投资人都是非常尊重的,他们是这样的一代人。
肖怀德:我讲几点感受:
第一,李老师这一次的分享有两个最核心的内容:一是对于全球不同地区电影工业生态的一个观察。包括对美国的,包括对中国台湾、香港产业的变迁,包括日本、韩国经济结构影响产品结构的产业生态,不同的这种产业生态的比较,呈现出全球的一种新的产业的结构。
第二,他对于中国电影生态的结构性的缺陷做了非常生动的、内在的一些问题的揭示。在这样一种特别的产业结构和模式化生产的结构当中,他大概说了7 个问题:一是消费通过和终端的问题;二是中国电影内向行动问题;三是行政规制行销金融,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市场干扰因素和要素配给带来的市场不稳定性问题;四是我理解是一个产业链环节的、主题的内嵌式的联动问题;五是阿里巴巴,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商业诚信的问题;六是关于《地球最后的夜晚》是一个商业伦理问题;七是谈到市场秩序问题。
这七个问题有双重价值。一是用产业经济学的语境,把电影作为一种产业的商业结构,把这样一种共性的问题揭示出来,如果我们沉浸在电影产业内部,你不跳出来,把它放到整个用产业经济学的方式去理解,在一个工业的语境里很难看到这样的一些共性的产业经济学的问题;二是他在这种行为背后,我们电影从业者日常的很多越轨行为的背后,对于整个市场伦理秩序的破坏,甚至于对整个电影工业生态的健康良性生态的破坏,他揭示出来了。
关于陈老师的电影工业美学,我理解成一种商业电影的美感生产的过程。如果把工业美学理解成商业电影生产过程的话,商业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娱乐的产品,它的美感生成具有它内在的逻辑,这种逻辑是大众的审美情趣的生成,或者这种美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会发生变化和时尚风格的变化。这样的一种工业,或者是商业电影美感生成,它带有很强的时代的集体无意识的属性。它不是个人化的,不是隐蔽性的,它是一种显露性的、浅层化的、情欲化的,商业电影美学不同于艺术电影美学。
我认为中国的电影生态的变化有几个特点:
一是互联网平台的进入对于中国电影产业格局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已经发生,或者是正在发生。互联网平台不熟悉电影制作和生产的体系,所以他们的介入很可能并不能真正地动摇电影工业的内在结构。但是它们有强大的IP 互生能力、生态的整合能力和国际的并购和投资能力,可能已经在改变我们的电影生产结构。
二是我们中国电影工业的生产或者是结构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过程,匆匆进入到工业和后工业的混杂阶段。这个会带来什么问题?第一个,我们电影从业人员的专业性和职业精神缺失。我们在工业化的体系里面经过洗涤,所以我们每一个个体都不具有足够的专业精神;第二个是我们的整个工业化秩序和商业伦理并没有真正的建立。我们现在是这种工业化到后工业化混杂的一个阶段,我们今天电影生产创意生产单元和工作室跟互联网平台的一种结合,这种结合使得我们的电影生产,因为能和互联生态平台直接结合,从而激发了很多创作活力。
第三,电影是一种工业的生产的产品。但是它最特殊的或者是与其他工业产品最大的特殊点在于它是一种精神产品。精神产品的生产,最核心的是在于如何就导演或者是编剧生命的投射和人性激发,对于人性洞察的能力,或者是说共情的一种能力,或者是能够激起观众情感共鸣的能力,无论是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工业化生产流程,那个东西是最核心的。
第四个关于制片人制度。manager 其实是一个执行,但是producer 其实是一个创意、艺术、领导的一个战略家。producer 需要一种系统的架构能力,需要对于文化和经济的平衡能力,需要对艺术和科学、感性与理性的一种平衡能力,是一个建筑师,他是在架构这样一个电影工业的既有商业又有艺术、既有情感又有工业化的一个综合性的产品的架构师,所以他需要综合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