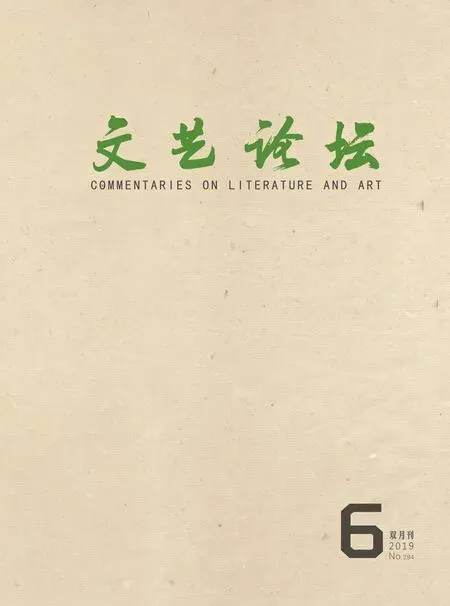诗意的探寻与先锋的追问
——论木叶文学批评的审美品格
2019-11-12◎赵牧
◎ 赵 牧
一
最先读到木叶的文字,应该是在他的博客上。他当时大概还在一家以电视为名的媒体上工作,而所写的文章,印象中有几篇是关于京津曲艺界知名人物的专访,这对于我来说原本是陌生的,但我却因此而喜欢上了木叶的文字,于是隔三差五地在网上找一些他的文章来拜读,并从中发现有关曲艺访谈,或不过是工作需要,他更多的兴趣,大体还是集中于所谓“纯文学”尤其是先锋文学的品评及鉴赏上的。因为惊叹于木叶的语言功夫,我记得自己那时就曾猜测他一定有过长久的写诗经历,而后来在他的《先锋之刃》中,果然就读到了他所写的令人沉迷而又富有哲思的题诗。但又不仅于此,他的批评文字中,竟在诗意的隽永与深邃之外,还表现出强大的叙事能力。或正是诗意与叙事的叠加,文学批评这一志在以理服人却常拒人千里的文体,在他那里竟实现言辞、诗意和事理的高度契合,成了婉转多姿和韵味无穷的美文。将批评文章写得漂亮,木叶当然并非特例。记得有一次与项静闲聊,她言及文学批评并非为作家打工,而是写自己的文章,经营一片属于自己的园地。“自己的园地”,这说法很容易让人想起周作人。事实上,他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美文的第一个倡导者,而恰在他发出这倡导的时候,现代白话的美文尽管还不成气候,却已有不少人将评论文章写得漂亮了。就周作人本人而言,他就不仅是一个美文大家,而且将美文观念贯彻在评论文章中。木叶曾在一篇有关废名谈读书的编者序言中,引述了周作人给《莫须有先生传》所作的序:“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他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汊港弯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这里周作人的“流水”之喻,显然是指废名文体上的散淡从容和文笔上的涉笔成趣,但他并不急着用这四字俗语来做生硬的概括,而是在修辞上复现了废名在叙事或抒情上水流婉转的神韵。这样一来,读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所能得到的审美愉悦,在他的序言中也一样领略得到,两者相得益彰,就不再是谁为谁服务的问题,而是各自在文本的世界中获得了审美的生命。
追求独立的审美生命,或是木叶引述周作人的原因,但在文体风格和审美意蕴上,他却与周作人有着很大的不同。即以对废名的评述而论,木叶首先肯定了周作人所论的“形象”,但他更为在意的,显然是“在这率意、诗意、诗化叙事之外,还可珍重的是废名对诗与思的卓越的连接”。木叶的诗歌创作便是在丰富的意象中蕴含了深邃的对于诸多人生境遇的思考,而他的诗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偏重于以诗的语言,以期在美的震惊中,进入诗人以及诗歌内部“无法解释的东西”。在论及多多的诗歌时,木叶竟然一连选取了十多个意象,“以雕刻的方式写诗,以迷离的丰饶的减法,以田野中的犁铧和风中突然晃动的橘子,以在夜晚涌动于异域的河流,有时还以否定,以局限,以离散和沉默,以无,以审视作为邀请,以省略的方式获取加速度,力量乃至聚合幻变”,揭示它们何以能够“进入你深层的困境”。在这些充满矛盾却又内涵丰富的意象中,我们可能不仅联想到多多诗歌的复杂与含混,而与此同时,也为这丰饶与诡谲的修辞感染,情不自禁地沉浸于诗与思的辩证关系之中。如果说诗人多多在20 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离散漂泊中仍在记忆和现实的交错里思考知识分子与祖国息息相关的命运(“秋雨过后,那爬满蜗牛的屋顶/我的祖国,从阿姆斯特丹的河上,缓缓驶过”),那么,木叶就是借助深刻的感悟、丰饶的修辞、多维的思考,将对于诗歌的品评灌注为自成一格的美文,既“在足够的语言里交换着我们的沉默”,又用“深渊里的语词向外照亮”,给“我们的沉默”探寻到一个诗意的出口。
“我把一些石头搬出了诗歌”,这是臧棣在一首诗中表达的意愿,而木叶的诗论,大抵可与这一意愿做一番类比。按照木叶的解读,臧棣所谓的“石头”应该从多个角度理解。首先从诗歌的内涵角度,“石头”显然是与苦难和沉重之类的主题相关联的。比如,20 世纪80年代末被木叶视为臧棣诗歌之路的重要转折点,而“石头”,则成了他理解这一转折的入口。臧棣的长诗《在埃德加·斯诺墓前》中,“石头”显然指向了墓碑,但它作为“一块石头”,被臧棣看作是“一个世界上最强硬的句号/准确地点在我们的大地上”,所以,在隐喻层面上,它不仅仅意味着一个终结,而且承载了历史和现实的重量,与苦难、悲剧、崇高以及对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把一些石头搬出了诗歌”,就是将这些具有“重量感、历史感、硬度和凸显性”的意象和内涵祛除,摆脱那种“你身上有世界上最重的石头”的压迫,终结“给石头做记号”的诗歌行为,甚至一并忘却“在石头里醒来”时的恍惚,而更愿意与生活妥协,伪装出轻松和惬意的姿态。正是基于这一前提,臧棣提出“希望诗学”,主张“通过诗歌的创造,来肯定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诗意”。这般夫子自道,应该是遭遇到了一些误解,而臧棣针对“某些现代派诗人或先锋派诗人假装与社会对立,然后批判社会现实的做派”所表达的诸多不满,也或者如暗箭一般射向他自身,以至于不得不“以诗论诗”的方式来给自己辩护。
这一辩护的有效性当然有赖于臧棣的创作实践,但是,他的诸多诗歌能不能获得理解,却还需要一番“把一些石头搬出了诗歌”的阐释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石头”在木叶那里,可能不仅包含了阐释的难度,而且意味着深入到词语的背面,于轻逸中发现沉重,于笑噱中体会悲哀,于虚无中探究实在,搜寻那些被假装搬出的“石头”在诗歌中的位置。所以,木叶在阐释臧棣诗歌时遭遇的“石头”与臧棣诗歌中的“石头”同中有异,他不但要从臧棣创作的历史中阐明“石头”的存在,而且在横向的比较中鉴定它的类型,发现它的退隐、揭示它的潜伏及其在被搬离时发生在文本内外的“争吵”。正是通过对“在搬运过程中,几乎每个词都冲我嚷嚷过:‘见鬼’或是‘放下我’”等等诗句的深刻阐释,木叶进入了诗歌内部“无法解释的东西”,发现了臧棣的创作心理中“深层的困境”,并由此认定“他不是不能写沉重的、抵抗性的、与现实高度紧张的诗歌”,而是“试着把一些石头般的存在移出自己的诗歌”。因为在富于思辨的阐释中还原了“石头”被“移出”的过程,木叶才让我们得以在臧棣的诗歌中发现“旁逸斜出”的背后,其实藏着与现实不能和解的东西。
二
“石头”不仅藏在诗歌中,在有关小说的阐释中,木叶也常做着“石头”的搬运工作。在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中, 《红楼梦》 一度以“石头记”为名,而就因为这块无力补天而被遗弃在大荒山青埂峰下的“石头”,“太多的人有了太多的故事”,所以,在中国叙事传统里,“石头”或可理解为小说的精神内核,它关联着作家与社会遭遇的方式,以及应对这遭遇时所选择的表现形式。在叙事的褶皱和语言的缝隙里发现“石头”并阐释其意义,在木叶看来,应该成为批评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余华的小说《第七天》出版后,广受诟病的是他引入了大量的新闻报道,而在这个过程中,“把一个新闻事件作为灵感源头”,似已成为作家脱离生活的原罪。木叶对此不以为然。为此,木叶就杜鲁门·卡波特《冷血》作了一个类比,认为《冷血》这一部在美国开创了“非虚构写作”先河的作品,其在严密调查一件谋杀案的过程中,对于新闻手法的借重,“仿佛安格尔画《泉》是静穆丰腴一笔一画的写实之美”,而《第七天》,则“更接近于杜尚的《泉》所开启的以‘现成品’进行艺术创作的风尚”。木叶说,在杜尚那里,“现成品”是小便池,在余华那里,“现成品”是新闻事件,他们都深得欧仁·尤奈斯库所谓的“先锋派就是自由”的真谛,但相比杜尚所针对的西方审美传统,只将买来的小便池翻转过来就拿去参加展览,余华挑战的对象,却还包含了他自己于20 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参与构建的先锋文学成规,它们横亘在那里,很大程度上就像是一块块亟待超越的“石头”。
“石头”之喻,当然不止于此。通过与杜尚的类比,木叶发现,“余华从不曾简单地拼贴,其先锋性是以文学洞察和个人经验为依傍”。作为例子,木叶提及一个细节,就是死后的李青遇见前夫杨飞,她把他遇难后掉在外面的眼珠放回眼眶,把他横在旁边的鼻子和挂在下面的下巴一一归位,然后说“你现在像杨飞了”。像这样一种在荒诞中尽显真情的对话,以及相互悼念的眼神,就“超越了新闻,让死者在另一世界里,拥有了一个生命本应得到的关照与温暖”。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这一对前世的怨偶,在死后的相遇,是在一处破旧的长椅上,“像是要塌了”是李青一再的担忧,而杨飞,却说“像是坐在一块石头上”。这迥然不同的感觉,根源于杨飞的记忆,在他4 岁的时候,曾经被养父杨金彪试图遗弃在一处幼儿园旁边的石头上,而这石头的故事,虽然是养父许久之后才告诉他的,但让“死无葬身之地”的他,靠着惊人的意志力游走迷雾重重和雨雪交替的阳间,并借此引领我们见证了诸多枉死者在他们生前所遭遇的不公。木叶说,这些“生前渺小、凄惨”的死者,“死后却未对强权和不公进行反抗和声讨,连倾诉与省思也是平缓的”。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他们都是社会秩序的接受者,而“他们带着这样的思维,走向死无葬身之地。在那里,石头会向你微笑,人人死而平等”。然而这样的“死托邦”却“并非是一个彻底解决了问题的所在,在抵达之前,没有经过任何意义上的末日审判”。像余华这样“把源自社会的一系列事件集束性地回敬给了这个社会”,如同臧棣将“石头搬出了诗歌”一样,试图将“石头搬出小说”,然而通过对这一搬出过程的复现,木叶却又在余华的文本世界里发现为粗疏的历史叙述所有意忽略的“小数”拥有了死后的“生活”。这种“为死去的见证者作见证”,也是一种犹如“石头”一样沉重的、尖锐的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木叶宣称“那些无能的力量,那些文学意义上的见证,是渺小的,也可能是浩大的;是柔弱的,也可能是尖锐的;是无用的,也可能是意味深长的”。
相比于触碰文本内坚硬的“石头”,作为批评家的木叶也敢于检视砂砾。如果说“石头”对应了小说的内核,那么抵达这内核的路途上,我们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无数的砂砾,但唯有目光锐利的批评家,才能精确地指出它们如何影响了我们的阅读,限制了主题的实现,以及何以让一个雄心勃勃的作家折戟沉沙的。在一次访谈中,木叶向苏童提及葛红兵对《碧奴》的批评,认为写作这类作品是在浪费生命,他应该把功夫用在针对现实发言的长篇小说上,而后苏童果然推出了《黄雀记》,并强调真正的“黄雀”,“其实就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现实”,然而在木叶看来,“文本中的时代和社会现实,却不那么精准宏阔”。如作为重要场景的井亭医院“成了作者的实验基地”,内中集结的代表人物种种荒唐的行径,虽以精神病为掩护,却“无不屈从与作者的意图,少有鲜活的内心流转”。苏童用以赞叹福楼拜的话,“他不光是在一个单纯的平面上写人性,另外一个方面,他兼顾到了社会对一个人心灵的影响”,于是被木叶用作靶子,以为“对经典的研习或感佩,与自身实践还是有些距离的”。这般不留情面的批评,虽然并不能阻止它此后获得茅盾文学奖,却从根本上揭示了苏童的写作在处理“时代意义”上的局限,而这局限,借用木叶所引述的葛红兵的话来说,就是“苏童常常不能为自己笔下的人物提供一个社会性的解释,苏童笔下的人物常常是宿命的”。宿命的解释,或给种种俗世的失败找到了根由,但它反过来也变身为一根绳索,在其牵引和束缚下,不但祖父的挖魂找魂变得徒劳无功,而且造就了“期许和文本、虚构和现实之间的缝隙”。
因为对这缝隙的重视,完成度成为木叶文学批评中的关键词。我们知道,任何一部作品,都包含了作者的野心,但作者的野心和文本的现实之间,却常常存在巨大的差异。冯唐曾自信满满地宣称他的“北京三部曲”树在那儿,够后两百年的同道们攀登一阵子的了,但木叶说,关于青春小说、成长主题,“冯唐并未有多少新发现,或给出什么绝妙揭示”。关于《王城如海》,徐则臣曾对于“主题先行”的批评不以为然,声称“最牛的和最烂的作家差不多都是主题先行,有能力主题先行起码他是有想法的”,但在木叶看来,他在“具体叙事时又未能巧妙地让人物和故事在现实中自在生长”。曾以《最后一个渔佬儿》进入文学史的李杭育携《公猪案》卷土重来,该小说借助公猪旺财的三世轮回,叙写了太平天国、土改和当下三个时空的故事,因为每个故事均触及法律并有楼法官这一视角的存在,“小说是存在深度自洽之可能的”,然而木叶经过一番探究发现,“《公猪案》由一个案件引出一个又一个案件,初始设计很魅惑,但是,到了具体叙述之时,缺乏内容上的纵横和法理上的辩证”。在木叶那里,无论冯唐的“北京三部曲”,还是徐则臣的《王城如海》,抑或李杭育的《公猪案》,都与作家的野心不相称,“野心勃勃,境界与实绩并没有预想中那么高”。
这样的判断,隐含了一个“完成度”的概念,而木叶用以度量的,就是作者的野心与文本的现实之间的落差。这一落差原本就是普遍的存在,而今众多批评家未必不明于此,但很不幸,他们却在批评实践中,总倾向于出于种种现实的考量而曲意迎合,以至文学批评一方面沦为了朋友圈里廉价的点赞,另一方面则成了别有用心的广告。尽管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世俗的环境中,对于这样一种批评家与作家的互动,比较能够宽容以待,毕竟乡愿就是谁也难以逃脱的悲哀,但像这样拉低文学批评的信用,木叶无论如何都是心存不满的。在《水底的火焰》一书的后记中,他就一再强调“谈论一个作家实际上‘并不具有的美德’,这是一种虚妄的不负责任的批评”,所以,他既不溢美也不隐恶,以“完成度”作为度量衡,不仅执着于在文本中发现“石头”般沉重和尖锐的内核,而且不遗余力地在作家的野心和文本的实际之间的缝隙中挑拣着冗余的砂砾,从而让人对于文学批评重新充满了敬意。
三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屈原《九歌》中的诗句,或者是木叶笔名的由来,而他在文学上的师承,却可能除了中国古典的滋养之外,更多地受惠于20 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现代派”“后朦胧诗”“先锋小说”等文学创作潮流以及与之相关的“审美自律”“回到文学自身”“纯文学”等文学观念。20 世纪80年代不仅意味着一个开始,而且被视为一种终结,它的这种相对独立性,在新世纪以来的诸多历史回望中被赋予了重大意义,所谓“文学的黄金时代”的说法于是不胫而走,而此间种种的文学思潮,在“重返八十年代”的号召下,也一再成为当代文学史家谈论的对象。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是,80年代的文学思潮似乎是此起彼伏的,而作为它们的遗产,却在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和新媒体的冲击下变换了名目,各自带领不同的受众群体,占领不同的文学阵地并各领风骚。作为“七零后”的木叶,显然是“先锋文学”观念的继承者,他的对于语言和修辞及其诗性的苛求,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孙甘露的影响。若以年龄计算,80年代对于他,显然应当归入“文学史的时间”,他开始接触“先锋文学”的时候,“先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风潮已经“终结”,但作为文学上的探索精神,却仍在不同代际的作家那儿生生不息。而昔日“先锋”的遗产,比如形式的实验,语言的探索,叙事的裂变,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文学观念,则已转化为文学的基本教养。大概就是在这“后先锋”的语境中,木叶借助“迟到”的阅读累积起对于先锋文学的敬意。
因为这敬意,木叶在批评中对于先锋文学颇为用心。在木叶的评论集《水底的火焰》中,“辑一”部分就主要讨论了先锋作家“后先锋”时期的创作。而“辑二”部分,虽然评述的都是“新世纪”以来文坛上崭露头角的“七零后”“八零后”的作品,但基本上以“先锋精神”作为了评价尺度,至于最后一辑,虽则是两个年度的文坛回眸,其中重点论述的作品,也在很大程度上以肯定其先锋探索为旨归。从相关篇目的安排以及论述中,发现他有着坚定的先锋立场。他对于先锋的理解,既是把先锋文学放置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首先把它作为“特定称谓每每指向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人物,在此意义上,马原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以及莫言残雪等被称为先锋作家”,对于他们当初的创作不断有人贬低,比如“没有来得及认真消化,很多作品的借鉴痕迹过分浓重”,“而且多数注重一些表面性与技术性的东西”,但木叶坚持认为,“那段实验功不可没,是一种传承,也是中国文学一种必要的自我检视、更新与丰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木叶宣称,“难以想象没有1980年代先锋探索的中国当代文学”。从这里,我们不难判断,木叶对先锋文学的认识是具有强烈的历史感的,他觉得,先锋文学运动中种种的语言和形式的实验、文学思维的革新,不但造就了文学史上的辉煌,提供了一系列站得住脚的作品,而且影响已经超越特定的“1980年代”,这既丰富了我们对此前文学的理解,又改变了此后的文学路径,尤其是其试图颠覆相对单一的文学主流而追求异质的精神品格,为文学地“表达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在认知方面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


注释:
①周作人:《莫须有先生传·序》,选自鲁迅博物馆编:《苦雨斋文丛》,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②木叶:《向空中画一枝花》,《文汇报》2018年 6 月 27日。
③木叶:《多多:诗人的原义是保持整理老虎背上斑纹的疯狂》,《上海文化》2018年 9 月号。
④臧棣:《搬运过程》,摘自《宇宙是扁的》,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
⑤木叶:《臧棣:我把一些石头搬出了诗歌》,《上海文化》2018年 5 月号。
⑥木叶:《“越尖锐……越具体……”》,摘自《一星如月看多时》,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
⑦⑨木叶:《谁为死去的见证者作见证》,摘自《水底的火焰》,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2页、第16页。
⑧余华:《第七天》,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
⑩木叶:《苏童:一个漫长而简洁的仪式》,摘自《先锋之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4页。
⑪⑫木叶:《被缚的宿命》,摘自《水底的火焰》,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年版,第6页、第6页。
⑬木叶:《冯唐论》,摘自《水底的火焰》,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96页。
⑭木叶:《过于正确与急切的叙事》,摘自《水底的火焰》,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98页。
⑮木叶:《另一种独立特行的猪,及其死亡》,摘自《水底的火焰》,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页。
⑯木叶:《水底的火焰·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52页。
⑰⑳木叶:《作者与总叙事者的较量》,摘自《水底的火焰》,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10页。
⑱木叶:《一个作家的叙事之夜》,摘自《水底的火焰》,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3—24页。
⑲木叶:《一个人的小说史?》,摘自《一星如月看多时》,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