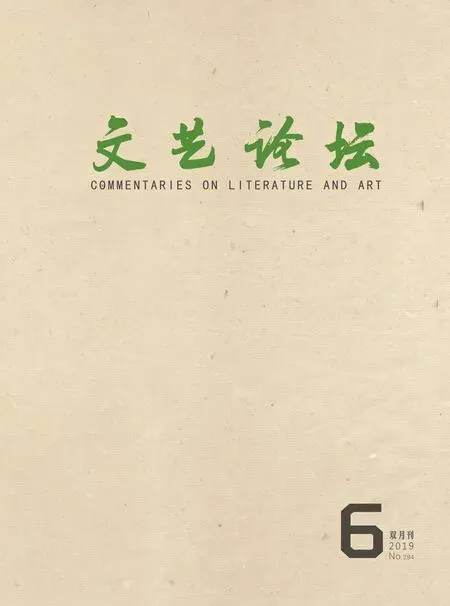新中国文学与海外文学叙事断裂的修复
——论海外华文文学对新中国文学的贡献
2019-11-12古远清
◎ 古远清
在探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明确新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定义。新中国文学是指1949年后的文学,又称共和国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大陆文学。为庆祝建国七十周年,不少评论刊物均推出“新中国文学七十年”专辑。“中国文学”之前加上“新”的定语,主要是为了说明新中国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或民国文学的不同性质。通常认为,“新中国文学”的“新”是指它的社会主义性质;而海外华文文学,是指中国陆台港澳以外的文学。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新文学的延伸,可称其为“华侨文学”或“侨民文学”,可当这些侨民落地生根加入了该国国籍时,他们写的已不是“华侨文学”,如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写的是马华文学,新加坡华文作家写的是新华文学,泰国华文作家写的是泰华文学,印度尼西亚华文作家写的是印华文学,越南华文作家写的是越华文学,因而不能再将这些华文文学看作是中国新文学尤其是“新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如把这些“华人”再看作是“华侨”,把其写的作品当成中国大陆文学的一个支流,这对他们不尊重,也不符合他们的写作实际。
但海外华文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界线并不是如楚河汉界分明。远的不说,像北美的严歌苓、加拿大的张翎写的作品,究竟是海外华文文学,还是中国当代文学或新中国文学?过去以护照作为辨别作家身份的标准,是不够的,还应该看他们是不是用母语还是用外语书写,其作品内容是否与中国有关,其发表处主要是海外还是海内,其读者是外国人还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受众?如果从严歌苓们出身于中国大陆,作品常在中国发表或改编成影视的作品在祖国上映,其本人参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还以中国作家的身份参加评奖——某些不出身于中国大陆的台湾作家同样加入过中国作家协会,或没有加入但向往社会主义甚至认同新中国,故把他们看作是“双栖”(而不是“双重国籍作家”) 作家,即既是海外华文作家,又是广义的新中国作家,也是可以的。
至于东南亚华文作家,他们绝大部分在赤道线上出生,其身份是“华人”而非“中国人”,其作品当然不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或属新中国文学的支流。2000年,重庆师范大学召开新加坡作家尤今作品研讨会,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邓友梅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钱谷融,都异口同声地说尤今是中国作家。在分组讨论时,我当面向尤今验明正身:“你真的是中国作家吗?”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是新加坡公民,是华人作家而决不是中国作家。”
这里要分清海外与海内、境内与境外的关系。台港澳是中国领土,其文学属中国文学。为了和大陆文学区分开来,我们称其为“境外文学”。大陆有些知名度很高的文学评论刊物,把台湾陈映真的作品称为“海外华文文学”,这是用词不规范不科学的表现。因为陈映真这类作家是地道的台湾作家,从未移民到国外,故可以称其为境外作家,但绝对不能称其为海外华文作家,因为海外华文文学除上述严歌苓和下面要谈到的陈若曦、刘大任等人作品与新中国文学时有交叉乃至关系如胶似漆外,一般属外国文学。还因为海外华文文学不存在有社会主义性质,他们也没有按照新中国文学的主旋律去写作。下面着重讲讲海外华文文学对新中国文学的贡献。
一是某些海外华文作家成为新中国文学与台港文学交流的先行者。
由于政治、历史的原因,海外华文作家对中国文学分流成陆台港澳四大板块,均有一种焦虑感。他们希望这四大板块从分流到整合,让这些文学分而不离,合而不并。须知,在政治上统一中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这本是政治家考虑的问题,文学家的能量毕竟有限,一时无法改变这种局面,他们能做到的是建立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让“文化统一中国”成为不同立场的中国作家的认同对象。如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美国的聂华苓等海外作家,就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
1979年9 月由安格尔和聂华苓共同主持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又称“国际作家工作坊”),邀请了世界各地华文作家,举行“中国文学创作前途座谈会”。在这个“中国周末”上,最值得重视的是海外作家的发言。叶维廉说:“今次中国作家能够从世界各地聚合在这里(爱荷华城),对中国文学的前途作开放的讨论,无疑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这次聚会也许可以成为我们已经期待很久太久的文化统一的开端。我们——住在中国两个区域的同胞——虽然被分隔和沉默了三十年,我们的交往交谈虽然被一些我们的意志无法掌握的事件所切断,虽然我们这次只是初会,可是,我们并非陌路人,我们不仅血缘相亲,而且心的底层有着相同的忧虑和瞻望,忧虑中国在十九世纪以来在外族的强权侵击下溃灭,瞻望我们共同的努力可以复活一个新的文化中国,尤其是可以和唐宋相提并论的强大的文艺新中国。”这里说的“文艺新中国”虽然不等于新中国文学,但其精神确有相通之处。叶维廉这段发言,毕竟说出了东道主不便点明的话。
这次座谈会结束后未发宣言,也没有做出结论。作为世界华文文化史上的标志性的会议,这个“中国周末”不仅有政治意义,而且有重要的文化史、文学史意义。首先,“中国周末”让两岸及香港文学重新秩序化,推进了中华文化的接续与整合的双向过程。在确定两岸及香港文化同属中华文化的前提下,通过打破政治的封锁寻求历史转折的契机,以海外会议的形式,创造两岸及香港作家交流的机会。其次,对“中国文学周”会议的定位,不能局限于美国,而必须放在更开阔的视野中:一方面考察它与早期寻求两岸文学整合的关联性,另一方面衡量它时,充分肯定政治统一文化先行的开拓之功与历史影响。
聂华苓另一贡献是和其夫君共同创办“国际写作计划”项目。截至2018年,已有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 多名作家和诗人受邀参与,其中改革开放后来自中国大陆的有艾青、徐迟、王蒙、张贤亮、冯骥才等50 多人。
二是海外华文作家松动了新中国作家队伍的板块式结构。
新中国文学队伍的结构一直呈现板块状态,这在五六十年代是不可动摇的。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国门大开后,“板块”开始松动,大陆作家的成分有了很大的变化。“文革”前,它清一色由工农兵外加为工农兵服务的知识分子所构成。后来一些大陆作家趁改革开放的东风,自我流放到境外乃至海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尤其是中国经济实力一天天强大,海外华文作家也有“二次移民”或“回流”现象的出现。海外华文作家这种跨区域、跨族裔乃至跨语言的写作状况,对原有的新中国作家的写作方式及其结构破天荒地重新作了洗牌,促使这一“板块”不再成为凝固和单一的状态,并将其置入现代性的框架内。虽然这支出走的队伍绝大部分是在新中国文学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仍植根于中华文化传统,早年又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和影响,但这不等于他们的创作是新中国文学的简单复制。他们的作品既具有国际性,同时又有本土性,这本土性的“本土”不是新中国,而是加入了异国元素。也就是说原先未出过国门的作家留洋后经过现代化、国际化的洗礼,把新中国文学的传统在海外加以发扬光大。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在写其留学经历及其挣扎的苦痛过程时,常用中外对照或中外互证的方法,以求其多元立体:不是新其内容,就是新其技巧;不是异其语言,就是异其观念。总之,他们不甘于平庸守旧,不甘于原地踏步只写中国的人和事,而对新中国文学常写的题材加以改造,其策略是:把东方题材加入“离散”的因素,写移民创业过程时与中国原有的生活作对比,在行文上突出异国情调,在语言上不纯用中文而夹杂一些洋文。显然,海外华文作家的跨区域写作及其对新中国作家队伍所做出的重构,其精神离不开中西文化的碰撞,离不开现实主体与新中国文学传统之间所做出的自主性选择。
海外华文作家对新中国作家所写作品内容所做出的重组,体现在加入移民史书写、宗教史书写,甚至以“零度叙述”的写作策略介入历史现场,加入多元共存、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内容。这些新移民作家多半从中国大陆出去,有不同于白先勇、刘大任的人生经验,乃至不同的创作方法。
还应指出的是,在海外华文作家跨区域、跨族裔、跨语言的创作中,并没有抛弃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他们只不过是用开放性、包容性进行虚构或非虚构的写作。原有的语言表层,均会有选择地保留。在这个基础上,海外华文作家为中国大陆文学的系统结构和语言增添了来自异国的现代化因子,从而使新中国文艺的“新”更加绚丽夺目。卢新华的《伤痕》,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张翎的《唐山大地震》,就是具有中国风味然而又有新质的佳作。
三是海外华文作家参与了新中国文学的经典建构。
通常说来,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典范,就在于它不受时空限制,其丰富的内涵像金矿那样不断被人开采,不断有人做出新的阐释。被命名为经典的作品,不是一般的优秀之作,而是能传世的杰出作品,在中外文坛上发生过广泛影响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文学经典的生成及其诠释,是一个不断开放和选择的过程。
也许有人会认为,新中国文学经典的建构主要靠大陆作家去完成,其实某些海外华文作家也就是广义的新中国作家,也出过力。像“伤痕文学”,人们认为开创者是时在复旦大学读书的学生卢新华在墙报上发表的《伤痕》。其实,早在卢新华之前,当时在海外的陈若曦就在香港发表了《尹县长》。这篇小说来源于生活,具体来说故事发生的地点在陕南某县。作品有悲痛,有愤慨,有嘲讽,其中一腔忧国忧民的热忱更使人感动,以至成为“伤痕文学”的先驱,陈若曦本人也成为文学界的一颗明星。
大陆的“伤痕文学”所呈现的启蒙并没有超越政治启蒙的层次,尤其在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观念及主题先行方面,均显得老套。而陈若曦的《尹县长》,与大陆“十七年”的文学没有关联,与“帮派文艺”更是不沾边。她这种海外视角,是大陆的伤痕文学所没有的。在审美的选择上,它没有采取忆苦思甜的基调,更不是刘心武那种“服务型”的文艺。陈若曦对自已所经历的大陆经验,采用热题冷写的方式,是先旁观后转述的手法,显得客观冷静,而不似《班主任》那样主观激昂,因而使人读来耳目一新。
内地反映上世纪七十年代生活的文学创作之所以成为弱项,是因为人们对常态性的文学较重视,而对非常态的文学不够关注,而陈若曦不但对内地而且对海外的文学创作现状十分了解,能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上升到新的层次。尤其是她能比较海内与海外之间的异同,使其把“伤痕文学”创作带进一个新境界。
某些海外华文作家也就是广义的新中国作家参与新中国文学的经典建构,还表现在留学生文学的创作上。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台湾掀起出国留学的狂潮,不少滞留不归的海外作家以留学生生活为素材,谱出了一曲曲海外游子在异邦留学、成家立业的悲喜剧。代表作有於梨华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张系国的《香蕉船》。这类作品属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怀乡文学的延伸和深化,同时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现代文学的一支劲旅。它拓宽了怀乡文学的天地,增添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品种。在沟通两岸和海外华人的感情上,起到了桥梁作用。
四是海外华文作家丰富了新中国文学的爱国主义内涵。
海外华文作家富有革命情操,多写表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题材,以用来激励民心士气。就主题而言,凡拥抱人民、歌咏山河、担当历史,都离不开爱国范畴。这里说的是高标准,再退一步从低标准看,爱国主义作家也可以抒发个人的性情和一己的隐衷。如果只许“车辚辚马啸啸”,不许“香雾云鬟湿”,那就是把艺术局限在政治的范围,否定它探讨心理学、哲学,甚至宗教各方面的力量。余光中说得好:“一位中国作家只要真能把中文写好,写美,就已经尽了他爱国之责了,因为历史和文化就在那语文之中。英国人宁失印度而不愿失去莎士比亚,倒不是因为他写了英国史剧,而是因为他把英文写成了艺术。时到今天,印度果然已失去,但莎士比亚依然长存。”
刘大任的保钓小说,既有“大江东去”的豪放,也有“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柔情,从多角度体现了爱国情怀。比起陈若曦来,刘大任属“迟到的归来者”。他已年过八十,可始终抱有对新中国强烈的爱。他分析自己身上的两种情绪:对国家近代以来命运的屈辱感,对中华伟大文化的自豪感。其身分尽管多变:在台湾他被当成“外省人”或另一类人。在海外,他又被当作华侨。“可在我的心目中,就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这位中国人于2017年9 月10 日,在新中国的山东书城举行《刘大任集》新书发布会。他用自己的系列作品,为新中国文坛“树立一个新的标杆,新的镜子,新的视野,新的高度。”
在海外华文作家中将家国情怀发扬光大的人,自然不止刘大任一例,但刘大任的保钓小说,对新中国文学发扬爱国主义的价值与贡献,毕竟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事实也正是如此,刘大任还有张系国等人的政治小说,充实了新中国文学爱国主义的内涵。一方面,它否定了文学可以不食人间烟火的说法;另一方面,它以开放的视野修复了新中国文学与海外叙事的断裂,更重要的贡献在于它改变了由于封闭的环境所造成中国当代文学过于单一化的线性格局。
总之,海外华文作家从异国他乡给新中国文学带来革新的火种。它点燃了新中国文学从一体化走出的创造热情。海外华文文学像一把劈刀,无畏地在坚冰之上打开一条裂缝,让新中国文学劲吹现代化之风。这是思想的解放,也是艺术的跃进。
注释:
①也斯:《爱荷华的中国文学座谈会》,《诗潮》1980年12 月。
②《明报月刊》(香港)1974年 11 月号。
③余光中:《紫荆与红梅如何接枝?》,载《香港文学节研讨会讲稿汇编》,香港市政局公共图书馆1997年版。
④⑤佚名:《刘大任:迟到的归来者》,《齐鲁周刊》2017年9月2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