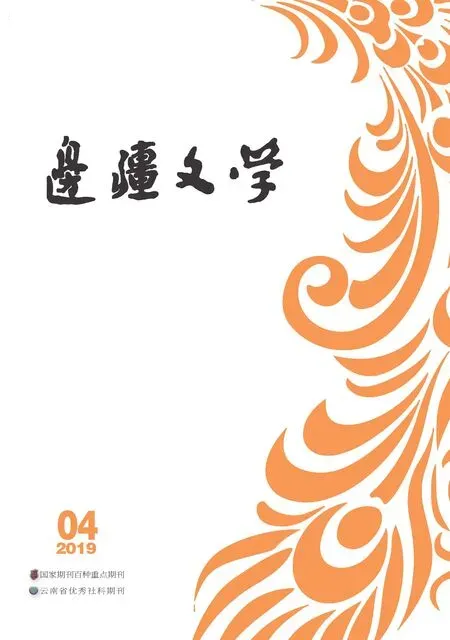支教者的片段记忆[散文]
2019-11-12陈洪金
陈洪金
一、山路抽打着人生最初的脚步
太阳升起来,照着一条长长的峡谷和五六个高高的山峰。远远地看见一条路,伸向一座庞大的山。那黝黑色的山,半山腰上的森林就像一个老人身上的斑痕,浓浓地蔓延,在太阳的照耀下,遮住了鸟羽的飞翔也遮住了行人的脚印。一场跋涉在不动声色地展开,即将迈开脚步的人,他怎么也不清楚,当太阳升起来,他将会面临着什么样的人生。但是序幕已经渐渐揭开,当无数的山群以高、远、深、幽、冷的面孔来面对一个年轻的灵魂和面孔,滇西北在人们的忽视与冷漠中,用曲折的山路和漫长的时间来磨练一片水一样柔软的目光。
在最初的山路上,还没有接近自己的讲台的老师,向着自己的讲台走去。那是一个远方的山村,一次次在梦里,始终没有看清楚那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于是,当峡谷里的村庄渐渐降低,以全部的面貌呈现,让人坐在半山腰上,可以看到那一片被淡淡的炊烟笼罩着的村庄和缓慢地从村里走出来向着山坡上走来的水牛。这时候,一个梦想着开始独立生活的人,背靠着未知的前途和未知的天空,坐在尽揽了那峡谷里自己的村庄的半山腰上。在注视中,一片稻田在阳光里波浪一样晃动着,思念如同一个崭新的线团,被揣在怀里,线头却拴在峡谷里的村庄中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以后的路越走越远,那思念的线也就越拉越长,只是在半山腰上独坐的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一种生活方式已经展开,许多梦想即将次第破灭,生命即将显示出它的真实面孔。
汗水开始在额头上出现。山路升上一个小小的山头,侧身进入了另一个被斜斜的山坡夹裹着的峡谷,所有与村庄相关的事物被身后的山峦遮住了。进入从来没有走过的山路上,两边的山坡,就像是走进了一个魔术里,森林消失了,满山遍野的被阳光晒成黑色的石头,把仅剩的灌木和野草逼得走投无路。阳光的照耀,让无边的山坡再也没有水分可供蒸发,索性敞开了惨黄的胸膛,显示出所有的裂缝与砂粒。这样的行程上,嘴唇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干渴了,在他的眼睛里,脚下的山坡向着前方延伸着,那血红色的山路在凝视中成了细细的一条线,伸到了很远很远的天边那没有云朵飘荡的山顶上。这时候,身边的汉子用那不是那么利索的汉语告诉他,走过那道山梁,再过一座山就到学校了。年轻的眼睛顿时失去了稚嫩的坚持,书本里成长起来的一片绿色的信念,被遥远的山路鞭子一样抽打着,尽显痛楚。
一套简单的行李在肩膀上越来越沉重。在那双崭新的球鞋里,汗水从脚底流出来,和着不停地飞进鞋子里去的红土和尘埃,让滚烫的脚板粘乎粘乎的。汗水从头顶上淌下来,顺着额头,流过被阳光晒得烫乎乎的眉心,流进眼里,让所有的山峦、野草、土坡、灌木、云朵、石头、蛇蜕、枯叶、悬崖,都变得模糊起来。汗水顺着脊背淌下去,湿透了的薄薄的衬衫,让山路上的空气充满了渴意。寂静的山路上,没有鸟飞过的影子,也没有溪泉流动的声音,连知了的噪音都消失了。世界忘记了一条山路的存在,时间失去了它原本应该具备的形象,没有可以作为参照的痕迹。
前面不紧不慢地走着的一匹矮小的毛驴,白亮白亮的蹄掌轻轻地碰撞着路上散乱的石块。那连摇晃一下尾巴都嫌累的驴子,在漫长的山路上,再也忍不住它那被视为水分的尿液,终于微微地叉开双腿,不知羞耻地对着两个不声不响地行走着的人撒了一泡尿。那驴尿浓烈的腥臭味在空气里发散开来,窜进他们的鼻子里。还没走上讲台的老师,艰难地加快了脚步,绕过了那一滩黄色的泛着泡沫的驴尿。身边的汉子,闻到驴尿里的骚腥味,用一种古老的语言,绕过了汉语的之乎者也,歌唱着一个遥远的爱情悲剧的源远流长。歌声远远地传出去,渗进无边的峡谷里的空旷,还没有抵达那些陡峭的山崖就消失了,没有人们所希望着的悠悠的回声。
太阳已经偏向西方,路还在脚下延伸着,似乎没有停止的意思。山路紧紧地缠绕着层出不穷的山峰,铁青着脸,让两个行走着的人,以最原始的方式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背在背上的那个从都市里学校中带回来的很时尚的书包里,作为零食的种种营养已经只剩下一些碎屑了。身边的汉子从他装马料的帆布袋里拿出杂志大小一块苦荞饼,用污浊的手撕下一块递过来。接过一块苦荞饼,咬了一口,还有一种特别的苦味和饥渴之中的香味,于是他一边吃,一边悲哀着,把脚下的路走得如泣如诉。山路上只有无动于衷地暴晒着的阳光,没有水。此刻,他不止一次地想起了故乡和亲人。
终于翻过一座让人们一次次感觉到自己渺小的大山。山路却还在向着更高的山峰更远的天空延伸。再也忍不住向着来时的地方回望,所有的视野,只看见一些山脊和另外一些山脊,不动声色的把圆圆的天空托举着,刚刚走过的山路,命运一样时有时无,时隐时现。在春花秋月里梦想了好几个年岁的讲台,始终没有呈现在精疲力竭的寻望中。此刻的行走,即使是在手里拄上一根支撑疲倦的树枝,都会深深地感觉到一种沉重从指间传来,足以磨灭诗歌的光芒、潜行的血液和曾经的誓言。
太阳继续偏向西方,山路继续延伸。鞭子一样在时间的平台上挥舞着的山路,一边是未知的讲台,一边是遥远的故乡和那些稻田里静默着的村庄。
二、孩子们瘦小的身影
太阳缓慢地爬到了极目之涯处的山顶上,巨大的山影渐渐地向着幽深的峡谷退却。
没有风。阳光明亮地照在屋后的岩石上,凝结了一夜的露水,在晨曦淡淡的橘红色里升起若有若无的水气,给寂静的山峰、山崖、山谷抹上了薄薄一层湿意。醒来的山鸟,从遥远的一处突兀的峭崖上陡然起飞,它在宽大的峡谷里平平地张开翅膀,在斜斜的飞行中滑翔一段距离,再扇动几下翅膀,飞行的高度随即向上升起几米,然后又平平地张开了翅膀在斜斜的飞行中滑翔一段距离。如此的几起几落,那鸟儿在阳光中越飞越远,渐渐地在窄窄的天空中缩小成为一个黑点,在蓝色的天边消失了。一只鸟的影子在峡谷里的出现与消失,没有逃脱山坡上一个简陋的土屋前面的泥院里的人不动声色的注视。
一天的开始,在脱离了喧哗与骚动的深山里,总是静悄悄的,连山风都还没有来得及敞开那撕心裂肺的呼叫。所谓山坡是与土屋为参照系的,那个淡黄色泥土垒成的土屋,在左右无限延伸的山坡上,下面直对着望下去让人眩晕的深深的峡谷,上面耸立着看上去后颈都抬得酸痛的山峰。一望无际的山坡上,那个土屋就像不经意点在一个巨人身上的一颗淡黄色的痣,可以被岁月湮没,也可以被风霜吹散。泥院里站着一个人,那微微地眯起的眼睛里那一丝淡淡的目光,在四面山野里搜寻着。
太阳渐渐升向天空,四顾的目光看到远远的野地里那些叶脉一样细小的山路上,在世事一样纷乱的石丛里、崖缝中、山褶里不经意之间闪现一两个黑点,向着土屋,就像沙尘一样飘过来。土屋前站着的人,在阳光下望着那些黑点在他的注视中渐渐变大,成为一个个鸟儿一样跳跃着的孩子,目光也随着那些身影的临近而变得温热起来。他在一个孤独的院子里,望着那些孩子从四面八方向着土屋跑来,那破旧的鞋子踩得枯草之间的山路尘土飞扬。
孩子们在山路上奔跑着,在他们瘦弱的肩膀上,斜斜地挎着一个破旧的书包。那些单薄的身影,一次次在泥院里的注视中,就像田野里的小狗一样灵活地在沟壑之间时隐时现,被巨大的岩石遮掩,让茂密的野芦苇隐藏,只有那只被他们在手里挥舞着的书包,一次次在他们头顶上空出现,让站在土屋前泥院里的人,用目光追随着,目睹他们一步步靠近。
孩子们绕过山坡上的土屋两旁让这里的地形呈“W”字形的山谷,从山谷里跑出来,喘着粗气跳进破旧的土门站到院子里,男的穿着小小的草绿色的军装,鼻子下面白而且清澈地流淌着的鼻涕,在阳光下闪着光;女的头上拢着一块深红色的头巾,红通通的脸庞明显地留下了山风吹过的痕迹,胶鞋里微黑的脚上没有穿袜子。孩子们还没有全部到齐,先来的孩子便在院子里的石头丛里、断墙两头追打嬉闹着,嘴里用那种让新来的老师听不懂的语言呼喊着。大一些的孩子就像森林里的猴王,老是把瘦小的孩子捉弄得左躲右藏,那瘦小一些的孩子实在受不住欺侮,就用他们民族语言里仅有的几句脏话,尖声地咒骂大孩子。旁边的女孩子听了,红着脸,向着土屋靠近山坡的老师居住的房间里告状:老……师……某某某骂……人……了……男孩子马上用自己的民族话对着女孩子放炮一样急红了脖子解释自己骂人的种种原因及其合理性,女孩子又用同样的方法回敬他,大一些的男孩子得意地站在一旁嘶嘶地笑着。院子里顿时乱开了,泥院里的一天从这时候真正开始。
老师从房间里拿了沾着油污的课本出来,用南方的没有撮口音和卷舌音的普通话对孩子们凶恶地说:笔(别)烙(闹)了,资(值)日森(生)去敲宗(钟),我们桑(上)课了。一个头发枯黄的孩子向着屋檐下跑去,从走廊边的柱子上取下一根大拇指粗细的铁棒,对着一块在树枝上吊着的巴掌大小的钢板怯生生地胡乱敲了四五下,就随着蜂拥而入的孩子们进了有些阴暗的教室。老师站在一块开着无数纵横交错的裂缝的黑板前面,嘴唇轻轻地蠕动着,无声地数了数今天到校的学生人数,说:今天一二节课,一年级桑语文,二三年级做作业;三四节课,三年级桑数学,一二年级做作业;五六节课,二年级桑数学,一三年级做作业。
一个声音在土屋里响起来,十几个声音从土屋里前前后后地窜出来,阳光穿过屋顶上陈旧的瓦片,变成了一根根明亮的光柱子照射到破旧的桌子上、落了几片枯叶的地面上、孩子们乱蓬蓬的头发上、老师用来装粉笔的玻璃罐上、手里握着的短短的铅笔头上。光柱子不断地移动,从学生们背后的墙上,渐渐地移到老师的额头上。孩子们开始在座位上不停地扭动身子,回答问题的声音也变得零零星星、稀稀拉拉的。于是,老师说:今天就桑到这里……他的话还没说完,教室里马上响起了收拾书本文具的声音。那声音放肆地响着,把老师说话的声音淹没了。
孩子们在渐渐下坠的夕阳中离开土屋,向着四面八方飞奔而去,留给山坡一间孤零零的土屋和一个孤零零的老师。
峡谷随着孩子们的离开而显得越来越空旷,被太阳照射了一天的山坡,散发完昨夜里凝结着的水分,干枯得连半坡上的草丛都在发着躁涩的光。暮色像河水一样带着凉风从深深的峡谷里缓缓地溢上来,经过土屋,向着高高的山顶继续溢上去。风声经过屋檐,吹落了细细的尘埃,飘散在空气里,悄悄地落到老师居住的那个房间里散放着的杂粮口袋上、课本上、吉他弦上、日历画上、盐巴瓶口上。一缕炊烟从土屋里冒出来,铁勺碰着锅边的声音,在风声里单调地响着,一声、两声、三声、五声、六声、七声、九声……土屋旁边,没有别的生灵,连一只鸡或者一只狗也没有。
夜色终于淹没了所有的山群和山坡上的土屋,世界正在退却。夜里,只有高远的星空和一盏摇曳的灯光。
三、第二天清晨
今天是第二天。今天早上是第二天的早上。
她走的时候,太阳刚刚从山顶上升起来。清晨的山风吹着她染黄了的一缕头发,就在那一缕黄发被风吹起的一瞬间,他看到了她的脸上露出了一层微笑。他发现,那微笑的出现的确有些艰难。他跟在她的身后,把她送出那矮小的土门。从土门出来,她很小心地走下门外向西那十三级陡陡的简易石台阶,站在通往山外的土路上。土路稍微一弯转,延伸进幽深的还没有被阳光照着的山影里,陡峭的石壁上,偶尔有一滴昨夜的露水,从突出的石棱上滴下来,落到覆盖满了尘埃和碎石的土路上。
她慢慢地在山影里走着,他跟在她的身后。在即将走出山影的时候,她转过身来,无声地抱住他,神色凝重。他发现,她的唇吻还是有一股清香的气息吐出来,真实地印证着曾经有过的许多梦想。他的手,悄悄地伸开,环在她的腰间。她的唇凑上来,碰着他的唇,那是两片微微张开的粉红色的湿润的唇。他有些激动起来,想要轻声地说一句话,她挣脱了他抱得越来越紧的手,一转身,低着头,走出了巨大的山影。前面是一片刺眼的晨光。
他站在路边,望着那个身影渐渐走远。在她的脚下,她白色的休闲鞋一次次绕过昨天暮归的牛羊留下的粪便,却踩得路上厚厚的粉末状的灰尘飞扬起来,让那个曾经熟悉的身影在尘埃中时隐时现。绝望的尘埃让温暖的阳光失去了歌唱的意义,他静静地望着那渐行渐远的身影,如同注视着一场迟迟不肯醒来的梦和梦中翻飞的誓言。她在他的注视中走得尘土飞扬的时候,他不得不想起一座图书馆。那里的每一个宁静的夜晚,灯光也像今天的阳光一样明亮。当校园里人影绰绰的时候,她挽着他的手走进图书馆,她跳动的长发时常拂过他的肩膀。坐在那个角落里,冬天悄悄临近,她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悄悄地向他伸过来,抓住他的手,让他伸进她温暖的袖口里,十个指头絮絮而谈,他对她手指的每一个骨节和涂了指甲油的指甲的了解,胜于对自己的了解。
山路随着地势伸进一个浅浅的山洼里,斜斜的山梁上一片空白。在他的视野里,山洼对面站着一只黑色的山羊。它顶着两只瘦长的羊角,一边发出沙哑的叫声,一边四处眺望。山羊孤独地站在一块巨大的岩石旁边,对着幽深而空旷的峡谷,不停地叫着。在高高的天空中,眩目的湛蓝色里,一只鹰张开了它那宽大的翅膀,在无边的空中缓慢地飞翔着,就像一片被峡谷里的山风吹起来的叶子,起起落落,又像一段悠扬抒情的萨克斯乐曲,断断续续。他知道,她还需要在山洼里走几分钟才会在山羊站着的那一头出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燃了,轻轻地抽了一口,那蓝色的烟雾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的蓝。他想起两年前的初秋,班里组织去看英文版电影《人鬼情未了》:在那个不停地旋转着的陶盘前,一段歌曲怆然响起:
Oh, my love, my darling
I’ve hunger for your touch
A long lonely time and time goes by slowly
Yet time can do so much are you still mine
I need you love, I need you love
God speed your love to me……
歌声断魂,他俩坐在一个窄小的包厢里,她坐在他的身边。四周随着电影镜头时明时暗,她突然转过身紧紧地抱住了他的头,疯狂地吻着,她汹涌的泪水,打湿了他的脸。他记得,他把她拥在怀里,吻着她小巧的耳垂,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悄悄地说着不离不弃的誓言。
山野一片寂静,她在他的注视下走得越来越远,最后在他的视线里成为在山路上不停地晃动着的小白点。峡谷里开始吹起了山风,风从土路上跑过,再次扬起了弥望的灰尘,一个世界开始对另一个世界说再见。
山谷里无边无际的夜色中,他的笔触不止一次提起城北客运站高高的钟楼和无声地走着的指针。坐在钟楼的对面一家火锅店里,她和他坐在她姐姐姐夫的对面。她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幸福而坦然地直面桌子对面望过来的目光。在火锅刚端上来的时候,在那热气腾腾的水气中,她总是把自己最喜欢吃的菜抢先夹到自己碗里,然后再分一些到他的碗里,弄得他害羞得额头直冒汗。好在他能够准确地回答出她姐夫提出的种种关于社会和哲学方面的询问,并且能够恰当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当钟声传来整整十响,火锅店外面人来人往,挥手告别的时刻开始到来。姐姐把他叫到一边,用低沉而凝重的语气,对他说了许多话,让他顿时感觉到人生的责任和作为男人的义不容辞。她焦急地在一旁,不停地用脚踢着路边的一棵行道树。她知道,电影即将开演了。
空荡荡的泥院里没有蚂蚁爬过去的痕迹。山风吹着屋檐下那一串通红的辣椒,阳光刺眼地从红辣椒上返回来,记忆,让昨天无比地临近,却又让更多的昨天恍若隔世。昨天的山风吹得昨晚的时间就像身边的峡谷一样空旷而幽深。当火塘里的柴火渐渐燃尽,红红的火炭模糊地映照着她的脸庞。那让人心醉的眉宇和唇吻,在荒无人烟的野地里,让土屋的存在仿佛是一个魔幻。谁也没有说一句话,静静地坐在火塘边,望着柴火渐渐燃尽,火焰渐渐熄灭,只剩下几块通红的火炭把整个屋子淡淡地照亮。
无声的枯坐中,他几次听到她的眼泪悄悄地滴落在地上,隐隐约约中可以听见那些液体与地面碰撞发出的可有可无的声音。只有一张床,他们谁也没有到床上去,哪怕只是躺一会儿。旁边的柴堆里始终有一只老鼠在里面窜来窜去,有时从米袋子上面跑过,有时把学生们交来的作业本啃得哧拉直响。最后的一枚火炭也熄灭了之后,她在黑暗里窸窸窣窣地摸索了一阵,最后递过来一样东西,放在他的手里,他隐隐地感觉到,那是她的一缕带着她的淡淡的香气的头发。然后,他们一直在黑暗中坐到天亮。
这些都是昨天的事了。
四、隐藏的面孔
出发的时候,天晴得很好。可是他刚走出去没有多远,天就被一块山里女人的头巾一样灰白灰白的云朵给慢慢地遮住了。峡谷开始吹起清冷的风来,风声在岩石与岩石之间撕扯着,像是谁躲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吹起了口哨。那旋律忽起忽落,几次让他想起曾经一片漆黑的夜里一个山里的女人突如其来的号哭。于是,走在山路上的他,心情像在峡谷里跌坠的石头,不断地向下沉。山里草丛和灌木林在阴云的笼罩下开始显得湿润起来,潮湿的颜色让楼房一样站立着的山崖显得更加坚硬和粗糙,让脚下的路被走出了一种无言的拒绝和无动于衷。
刚翻过一道山梁,雨终于下起来了。碎碎的雨珠在高高的山顶那边随着风的吹扬略带着飞舞的姿势,雪粒一样纷纷扬扬地充满了整个峡谷,使那些长年累月地在山坡上散乱地分布着的黑色的石头,呈现出一层油亮,在雨雾中隐隐可见。雨还顺着眉毛淌下来,流过眉心进入眼睛里,流过颧骨顺着腮帮沿颈而下。红土路在脚下变得越来越潮湿,最后积起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水洼,走在那些窄窄的山路上,红泥在鞋底上越裹越厚,让行走成了一件很艰难的事。
远远地看见那个山梁之上的山崖下面不起眼地有一间小小的草屋。沉重的云朵从峡谷里吃力地升起来,不断地遮住了黑色的山崖以及点缀在山崖脚下的草屋。望着那草屋,他的脚下拖着不断地粘在鞋底上的红泥,在细雨里走了将近两个小时,才听见有狗叫声从头顶上传来。狗站在篮球场大小的一块巨石上,巨石与山崖构成了一把椅子的形状,那一间草屋就像放在椅子上的一个火柴盒。狗站在巨石的边沿上不停地叫着,望着在绕过巨石从它的侧面向上攀援的路上走着的人。
气喘吁吁地踏上一段陡峭的土坡,一棵高大的橘子树遮住了草屋前面的院子。叫了几声一个学生的名字,回应他的却只有那只不停地围着粘了厚厚的红泥的鞋子狂叫着的狗。草屋的门是开着的,一眼望进去,低矮的草屋里,因为没有几件家具而显得异常地空旷。屋子中间是三块石头支起来的火塘,一个铁三角支架上面的一只漆黑的铝壶里,烧沸了的开水正冒着蒸汽。他站在院子里叫着一个女孩子的名字,除了山崖以外,没有谁应答。他沿着一条隐隐约约约的被草丛和树叶掩蔽了的小径,绕到草屋背后,只看见离屋檐大约有两米宽的空间里,山崖向里面凹进去了的部分,形成了一个与草屋同样大小的空间,一头牛站在里面,低头吃着几根干枯的玉米秸。
在牛背后面,他看见半个面孔,被牛背遮住了一半、只露出鼻子以上部分的半个面孔。从牛背上面露出来的那一双黑色的眼睛里,他看到了一种强烈的胆怯,没有眨动,也没有转动,一直在注视着他在小径上越走越近。牛悠闲地甩动着尾巴,尾梢不停地拍打在那张面孔上戴着的一顶破旧的青灰色帽子上,帽子上面的灰尘早已被牛尾巴拍干净了,与那半张很久没有洗过的脸形成了一种反差。
他对牛背后的人大声说:“你是索拉加米的父亲吗?”
站在牛背后的人没有说话,向着外边望过来的眼睛没有眨动,没有转动,只是轻微地点了点头。
他说:“我是索拉加米的老师,她三天没有去上学了,我来看看。”
那人还是站在牛背后,没有说话。
他说:“你出来,我有话要对你说。”
那人慢慢地从牛身后走出来,还没有迈出两步,一脚踩在一堆牛屎上,脚下一滑,差点跌倒在地。等那个人站稳了,他才发现那个始终没有说一句话的人是一个矮小的男人。他在前面走着,身后跟着那个男人。来到草屋门前,他带着男人像走进自己的家一样在火塘前面坐下来,铁三角支架上的铝壶里依然在冒着蒸汽。他从脚边找了一块石头当作凳子坐下来,男人在他面前孩子一样站着。
他刚坐下来,火光照耀着他的脸,顿时有一种山里人特有的烟火味道温暖地窜到鼻子里来。在这些大山深处的草屋中,从来都不兴有烟囱的,炊烟总是在屋子里缭绕着,天长日久,屋顶、屋梁、柱子、床铺等凡是在屋里的东西,全部都被烟尘染成了漆黑的一片。男人在那里站了大约五六分钟,猛然醒悟似的从床边一个失去了原色的麻布口袋里拿出一把旱烟叶来,递给他,让他抽。他摇头说不会抽烟。男人羞怯地把手里的烟叶放了回去,仿佛做错了事情,眼睛洋溢着不自然的神色。
他在山路上被雨淋湿的疲惫渐渐地融化在火光带来的温暖里,于是,他对男人说:“索拉加米已经三天没有去上学了,你为什么不让她去?再拖下去,她的课程可就赶不上了。”
男人站在他面前,用手背使劲地揩了揩正在从上嘴唇淌下来的清亮的鼻涕,用带着浓厚的民族味道的汉话磕磕绊绊地说:“粮食一个没有了,劳动力家里也缺着,病了她妈在床上。前些天,看病的钱一个没有了,哪里还能抚她上学呢,读书一个她是去不成了。”
他知道山里人家不让自己的孩子去上学一般都是这几个原因。于是开始对男人说了很多不能误了孩子的话。
男人又不说话。等两人都安静了很久,他等不及了,催问男人的意见。男人说:“粮食一个没有了,劳动力家里也缺着,病了她妈在床上前些天,看病的钱一个没有了,哪里还能抚她上学呢,读书一个她是去不成了。”
天气开始慢慢地转晴,太阳从云层里渐渐显露出来,终于有一缕阳光透过门前的橘子树梢,照到草屋里来。借着阳光的照射,他终于发现,在屋里左侧靠墙的地方,有一笼斜斜地挂着的早已被烟火熏黑了的蚊帐,蚊帐一阵晃动之后露出一个女人苍老而惨白的面孔来,那双灰白色眼睛一直在注视着他的脸,准确地说是注视着他的眼睛。她无力地在他的目光上胆怯地碰了碰,说:“老师,都已经让你垫付了两年的学费了,我也想让娃儿去读书……”她的话还没有说完,男人又在他耳边说:“粮食一个没有了,劳动力家里也缺着,病了她妈在床上前些天,看病的钱一个没有了,哪里还能抚她上学呢,读书一个她是去不成了。”
他不时望着屋外渐渐下落的太阳,开始在大脑搜寻曾经看过的《演讲与口才》杂志中说过的许多成功的事例,对站在面前的男人和躺在床上的女人说话,劝导他们让索拉加米去学校上课。男人说:“粮食一个没有了,劳动力家里也缺着,病了她妈在床上前些天,看病的钱一个没有了,哪里还能抚她上学呢,读书一个她是去不成了。”
太阳就要落山了,从草屋到学校要走四个多小时的山路。他在火塘面前站起来,走了出去。在橘子树后面,他看见索拉加米隐藏在那些茂密的树叶与枝柯之间。一个还没有成熟的橘子,被她撕成了一瓣一瓣的,落在地上,那橘子皮里散发出来的味道,很浓烈。当他一步一步离开那间巨石与山崖之间的草屋,隐隐约约地听见有哭泣声传来。
五、镜子中的自己
学生们背起书包,在叶脉一样的山路上飞快地向着他们在山褶里的那些树林间山谷中的草屋里跑去,归巢的鸟一样。西边的太阳照着峡谷里安详地飞动着的蚊蚋,草丛里屎壳郎推着一粒圆圆的牛屎,缓慢地向着越来越长的石隙里爬去。一个时刻渐渐临近了,一群人即将踏着夕阳向着土屋骡子一样踩得长长的土路烟尘飞扬而来。
在乡政府旁边那间瓦房里的乡教委办公室里,一群脚踏被红土染红了的白球鞋的老师,被分布在群山里的某一个小山坳里,各自守着一片天空和十几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彼此在山与山之间默默无闻地成为山里的景物。早在一个星期前,五六个老师约定了要到土屋里来聚集。于是,细碎的山路在他们的脚下展开,向着山坡上的土屋里跋涉而来。守着一间土屋,阳光里的尘埃欢快地游动着,让居住在土屋里的人为了一个时刻的到来,心情如潮。他在一群被山里的阳光晒黑了的孩子离开他的视野之后,一个人守着他的土屋,等待着一群人从乡政府的诺言里走出来,在太阳即将落到山谷里之前的某个时辰,出现在他的眼前。那时候,整个峡谷将被山歌和酒歌灌溉着,所有的尘埃和虫鸣都将沉醉,所有的鸟影和山脊都将舞蹈。他在幽深的峡谷里,不需要把自己的狂喜掩藏起来。
峡谷在阳光里静静地守着土屋和他的脚步,他在屋里简陋的火塘上烧开了一壶水,水蒸汽从壶嘴里冒出来的声音,让他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很特别的愉快。于是他哼着那首已经不再流行了的《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踱着不紧不慢的步子来到土屋背后,在屋后墙脚下不足一米高的鸡圈里捉出那只从三十里外乡政府小街上买回来的老母鸡,用母亲从老家给他带上的那把菜刀,把鸡杀了,回到屋里,把鸡放到脸盆里,早已烧开了正在火塘上面唱着歌的开水,缓缓地浇下去。在院子里,他蹲在石头之间,拎起用开水浇透的鸡,把鸡毛拔干净了,唱着歌,回到屋里,翻出他所有的作料,仔细地放进去,唱着歌,在火塘里再放进去一根栗柴。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了,他拍拍手,来到院子里。站了一会儿,他一步一步慢慢地踱到路边,对着深深的峡谷和没有一个人的山路,舒畅地撒了一泡尿。然后,他在路边的山石上坐下来,望着远处的山路尽头,等待着人影在那里由一个黑点渐渐地变大,最后成为一个个具体的朋友。
金黄色的太阳在峡谷上空渐渐地向着山顶偏移,那传说里居住着神仙的地方,有一只鹰在飞翔着,那庞大的翅膀,把一个影子不经意地投在山坡上,掠过岩石、掠过衰草、掠过那一条曾经被孩子们走得尘土飞扬的山路。他坐在山石上,目光一直随着那只鹰在天空中的飞翔而移动着。每一次看到鹰在峡谷上空飞了一圈,复又回到它出发时的山峰,他就会向着那山路的尽头望一眼,盼望着那里出现一个小小的黑点。那只鹰一直在峡谷的上空飞翔着,一次次回到它出发的山峰,他一次次向着山路的尽头望去,那山脊上的路口,始终没有他所希望的黑点出现。鹰,也许在天空中感觉到了飞翔的孤独,突然间,像是在某一件事情中醒悟过来一样,庞大的翅膀一挥,那棕黑色的身体猛然间向着峡谷底下那长了一棵苍老的松树的悬崖飞奔而去,它还未到达那青黑色的悬崖,就被悬崖庞大的阴影掩没了。整个峡谷上空一片空白。
他慢慢地从山石上站起来,随手一挥,把手里那一支点燃后但一直没有吸上一口的香烟熄灭了,慢慢地走到路边的斜坡,在门口停下来,坐在门槛上,对着山路的尽头失神地望着。太阳已经被山峰遮住了它最后的一缕光芒,峡谷开始渐渐地暗淡下来。暮色带来了风的声音,它在耳畔轻轻地走过,拂落了门沿上的砂粒。砂粒落到肩膀上,发出细小但很清脆的声响。山风渐渐地让脸庞感觉到了夜晚的凉意,山路的尽头处,还是没有人在他的注视里呈现,只有风却吹得越来越响,到最后就成了一片止不住的呜咽。
当暮色海水一样渐渐澎湃起来,峡谷被黑暗染得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却愈加空旷,仿佛是一段漫长而空洞的人生。暮色在峡谷里不动声色地向着山头上攀援,星星在天空中出现的时候,山路的尽头处慢慢地被暮色融化了,注视的目光再也看不见那山脊上的一个小小的缺口。峡谷里一片黑暗。
他慢慢地从门槛上站起来,经过泥院,他在窄窄的房间里靠着门坐下来,把头微斜地靠在门框上,目光跨过土门的顶上,依旧可以看见那山路的尽头。夜晚来临,路在夜色里,似乎已经失去了注视与观察的意义。但是,他还是坚守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心里一直在热切地想象着就在某一刻,一连串打着火把的影子会跳进他的视野,让他惊喜地跑到门外的土路上,隔着一条宽大的峡谷向着那些火把狂呼。然而,火把始终没有在他的视野里出现,门外总是一片被夜色淹没了的漆黑的世界。山风开始在峡谷里疯狂地奔跑起来,到处激荡着呼啸的声响。一颗明亮的星星在山顶上升起来,说明夜已经很深了。
他慢慢地站起来,最后看了一眼山路尽头处的那一片黑暗,泪水无声地从脸庞滑落。他的手轻轻地推动简陋的门扉,把整整一个下午的等待,艰难地关在门外。一个世界在门外被山风无情地吹着,一个世界在屋内充满了失望的泪意。
一锅鸡肉被炖得骨肉分离了,满屋子的香气,围绕着一个失望的人和一张小小的桌子。一只鸡盛在一只脸盆里,放在桌子上,一双筷子,一只碗,一个酒杯,一张床,一只收音机,一把吉他,一个火塘,一个屋檐,一方泥院,一洞土门,一条土路,一条峡谷,一段山路——门关上以后,只有一杯酒,连呼吸都是一下一下的,泪水也一滴一滴地顺着脸庞和鼻翼往下流到下巴上。所有的孤独与寂寞,被酒意浇灌得膨胀起来。
当酒遇上了孤独与寂寞,生命开始了一种近似于癫狂的状态,他在窗口发现了一面镜子,便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把镜子放到桌子中央,在微微的火光下,镜子里便出现了一个人影,此刻的他,还没有真醉,当他发现镜子中自己苍老的面容,禁不住痛哭失声。泪水落到酒杯里,他举起了手中的酒杯,对着镜子中的影子,喊着自己的名字,向着镜子把手中的酒杯伸过去。镜子里也有一个痛哭失声的人,手里举着酒杯向着自己伸过来。当世界空旷得只剩下了自己,他的痛哭失声,没有谁听见。
整个宽广的峡谷只有一个痛哭着的生命。一群人在半夜里抵达土屋的时候,他们发现屋子里的人,
酩酊大醉地痛哭着,不停地向着镜子里的自己敬酒。
N、一1封家书
爸爸、妈妈:你们好!这是我到这里支教两年以来第六次给你们写信。这里已经下了半个月的雨了,到山里来的路也已经全部坍塌,没有车子进来。我这封信被送到您们手里的时候,也许要等到冬天了。说不定,等您们收信的时候,我已经站在您们面前了,就像前年的那一封信那样。只是现在山里依然在下雨,不知到哪天老天才会把雨下完。
在这里,我每天看着高高的天空,想家。我很想奶奶,每一次当我回到家里,看到奶奶,都会发现苍老了许多。我很害怕,不知哪一天,就像现在一样断了出山的路,她就不在了。她最喜欢我,我肯定,在奶奶临终前,她最想见到的,一定是我。奶奶的风湿病在这样雨季节里,肯定是很疼了。我在这里找了一条蛇,用酒泡着,她擦了,可能会不疼一些。只是等了两个月都没有人出山去,后来雨季就来了。那条蛇在我的酒瓶里泡着,一直。听说蛇酒治风湿病很有效的。
我在这里,还要支教一年。很快,我就要回到您们身边来了。在这一段日子里,您们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我再给您们唠叨一句,不要在家里给我相什么亲了。凭我现在的情况,我不可能结婚的,人家也不可能跟着我到这山里来。等我回来的时候,我自己的婚事,我自己会考虑的。你们如果再在家里给我到处相什么亲,我可真的生气了。
好了,就写到这里,一定要照顾好奶奶,您也要注意身体!
儿子 于 月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