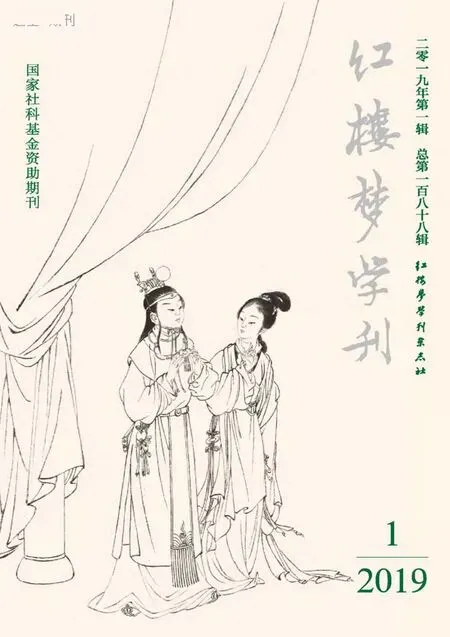回目聚焦 真情揆理
——《红楼梦》第五十八回散论
2019-11-12
内容提要:《红楼梦》第五十八回的叙事转向和回目聚焦同性恋爱,是实现“大旨谈情”总体构思的重要布局。贾宝玉由此完成了对“情”的超越性精神本体的认识。程本对脂本的删改,导致写实表意功能的弱化。
一、叙事转向
《红楼梦》第五十八回的情节转向,创造了小说新的广阔艺术空间。
《红楼梦》继承章回小说传统,各回情节之间大多紧相衔接。第五十八回却比较特别,开头接过上回,三言两语收束,随即以一大段概述文字,为转向作铺垫。主要内容,一是老太妃去世(第五十六回开头有老太妃病的预叙),贾母等命妇皆须入朝随祭,只得留下尤氏李纨管理家务;二是因国丧禁筵宴音乐,贾府家庭戏班解散。这两件事又内在关联。前者暗示国事与家事的牵联,实际上是后来元妃病逝与贾府衰败关联的预伏;后者则是家事与情事的内在关联,管理松弛、家政混乱、女伶为婢,众多小人物走到前台,大观园里种种矛盾错综交织。由此,小说叙事方向发生了重要转变,从上层贵族转到下层奴仆,特别是进入大观园的童奴女伶,成为叙事焦点。从五十八回到六十一回,是《红楼梦》写小人物最多最出色的篇章。而芳官藕官等主要女伶命运描写,一直延续到前八十回的七十七回。把上层叙事和下层叙事连接起来的贯串性人物,则是身处上层却对下层深怀同情的贵族公子贾宝玉。
女伶是《红楼梦》中一个特殊奴婢群体。她们年龄幼小,进入贾府前,生活于比较开放自由的平民社会,在昆曲戏班里,长期接触和表演流行的才子佳人戏剧。耳濡目染,使得她们中一些人更容易早熟,萌发情愫。来到贾府后,她们以技艺为家主提供特殊服务。虽然身份卑微,然而特殊技艺尚能使其养尊处优,有的还发展出独立人格个性(如龄官)。戏班解散成为女伶命运的转折点。微弱的优势完全丧失,能走的走了,多数不能走的分到各处成为丫鬟,“也有说父母虽有,他只以卖我们为事,这一去还被他卖了;也有父母已亡,或被叔伯兄弟所卖的;也有说无人可投的;也有说恋恩不舍的”。外面的世界更加悲惨,但留下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一方面,她们处于比一般小丫头更受人歧视的地位。连赵姨娘都如此辱骂:“你是我银子钱买来学戏的,不过娼妇粉头之流,我家里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的!”这不能不激起她们的本能反抗。在失去家庭温暖和外在关爱的情况下,更加珍惜情谊,抱团取暖。另一方面,她们来自市井,生性活泼好动,擅长唱曲表演,却缺少贵族家庭需要的家务技能和习惯教养,而多一些散漫野性。特点和弱点都很突出。从保守观念看来,“大概不安分守理者多。”引起其他奴仆,尤其是园内承包利益守护者婆子们不满。可以说,她们进入大观园,成为丫鬟群体中的另类,冲击原来的规矩秩序,激荡出新的生活浪花。这样一个身份至卑、年龄至幼、个性突出的弱势群体受欺压的现实,更加激起了主张“世法平等”的贾宝玉“物不平则鸣”的仁爱情怀,由此演出了一系列有声有色意蕴无穷的动人故事。
就具体情节而言,五十八回主要写了几件事:宝玉病后出门;藕官烧纸风波;芳官洗头风波;宝玉向芳官询问藕官故事。这里两条线索:一条是女伶与婆子的关系;一条是女伶之间及其与贾宝玉的关系,都向后延伸出一系列事件。
前一条线揭露底层的噬利与欺压。欺负藕官芳官的婆子竟然都是自己的干妈。藕官烧纸痛哭,要把她拉去见“奶奶”的是夏婆子,克扣芳官的是春燕的母亲何妈。其实,姐妹俩都是贾府的世代家奴,但她们对无家可归的女伶没有丝毫同情怜悯,反而借干妈的身份肆行欺辱。遇到反抗,又动用伦理权威压迫。这就难怪尽力保护她们的宝玉会恨恨地说:“这些老婆子都是些铁心石头肠子!”春燕说:“只说我妈和姨妈,他老姊妹两个,如今越老了越把钱看的真了。”作者在家族盛衰即家事主题的描写中,在批判上层“安富尊荣”的同时,对下层边缘群体以利相噬导致良知沦丧极其痛心,以此为起点在以下几回中给以深刻的暴露,这是一种包含人性关怀的艺术匠心安排。
但本回的故事主体是后一条线,是紧承五十七回“木石情缘”并与其相互辉映的女伶间的“假凤虚凰”故事。主旨是对同性情爱的肯定和理解。从“假凤泣虚凰”到“真情揆痴理”,贾宝玉完成了对“情”的精神本体的认识。这是作者“大旨谈情”整体构思的又一重要布局。关于这一点,还很少有人关注。本文拟重点论述。
二、回目聚焦
第五十八回的情节转向,在“情事”主题上呈现与五十七回藕断丝连的特点。
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忙玉慈姨妈爱语慰痴颦”以极为动人的笔墨描写了宝黛的生死之恋,第五十八回却峰回路转,别开天地。这回叙事内容比较繁杂,但回目“杏子阴假凤泣虚凰茜纱窗真情揆痴理”却只聚焦一件事,即以藕官烧钱纸为线索和悬念引出的女伶童奴的同性之恋,以及此事在宝玉心中的回响。这是与宝黛异性恋相对应的另类恋爱。“假凤泣虚凰”是因,“真情揆痴理”是果。“假凤虚凰”是故事主体,“真情痴理”为内在思理。由因及果,一脉相连。一般回目皆以对句写两事,概括本回内容。全书中唯独此回目以对句总一事,这种着意聚焦显示了作者的高度重视和精心布局。
查各版本此回回目,大同小异。庚辰本、己卯本、蒙府本(补配)、俄藏本、梦稿本均作“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甲辰本作“杏子阴假凤泣虚鵉茜纱窗真情揆痴理”;戚序本作“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红纱真情揆痴理”。这说明在作者修改和作品传抄过程中,这种剪除枝蔓突出主体的回目艺术构思是稳定未变并得到认同的。
“真假”二字,是《红楼梦》的基本语词符号。“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贾真甄,内涵异常丰富。但在回目中,用“真假”二字,全书仅第五十八回一次,且含义独特。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这一回目揭示了一种为世俗否定的感情形态与作者肯定的价值内容之间的深刻联系。
红研所校注本释“假凤虚凰”云:“——因藕官和菂官在戏中扮演夫妻,在生活中也俨若夫妻,但她们都是女孩子,故称‘假凤虚凰’。”
正确无误。但可以看出对实质性概念“同性恋爱”的有意回避。这是一个敏感话题。
本来,同性恋和异性恋都是出自人性本能的感情形态。古代虽无同性恋概念,但性取向不同是人性的客观存在。只是由于同性恋取向另类和性观念混乱,长期被歧视误解甚至污名化色情化,所谓“龙阳之兴”就是污名化色情化的典型例子。
曹雪芹是人类精神命运的关怀者和思考者。他以同样的仁爱情怀关注异性和同性的各种情感关系。《红楼梦》的第一个爱情婚姻悲剧的男主角,就是具有明显同性恋倾向的冯渊(谐音“逢冤”)。他“酷爱男风,最厌女子”,却对被拐卖的英莲一见钟情,并发誓再不交接男子,也不再娶。然而,这样一位能“定情于一人”的好男人却被既霸占女性,又玩弄男性的豪富纨绔薛蟠打死。很明显,“薄命女偏逢薄命郎”的故事,不只是为了写英莲(香菱)的不幸,也包含着对同性恋者命运的关怀。
曹雪芹在第五回借警幻仙姑之口阐述“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划分“意淫”(痴情)与“皮肤滥淫”的界限,作为其“情观”的基本纲领。
以此统领,他描写了宝玉与秦钟、蒋玉菡、柳湘莲、北静王等的同性情谊,如与秦钟“恋风流情友入家塾”,秦钟病重时置元春封妃于不顾,前往临终诀别;与蒋玉菡初见便交换汗巾,挨打不悔等;也写到这些俊俏男子之间“惺惺惜惺惺”的相互爱慕(如北静王与蒋玉菡、柳湘莲与秦钟之交)等等。同时,他也描写了薛蟠借上书塾玩弄金荣香怜玉爱等男童的“龙阳之兴”;描写了贾珍,琏,蓉等包括同性在内的淫乱不堪;甚至描写了两类人的冲突,如薛蟠调情遭柳湘莲痛打,形成美丑鲜明映照。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划清“意淫”(痴情、真情)与“皮肤滥淫”的界限。其实质,乃是为同性情谊和同性恋正名。
应该说,这才是曹雪芹“假凤虚凰”意象和故事的心理动因,并成为作者“大旨谈情”总体构思的重要组件。凤凰是古代传说中象征祥瑞的神鸟,从《诗经·卷阿》“凤凰于飞,翙翙其羽”,《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以及《楚辞》《庄子》的高贵意象,到《左传》以“凤凰于飞,和鸣锵锵”喻美好婚姻,再到传说司马相如借弹琴曲《凤求凰》表达热烈爱情,凤凰意象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曹雪芹继承这份珍贵遗产,创造“假凤虚凰”为同性恋张目,并把这一优美深闳而又带有悲剧性的意象献给身份卑贱的童伶女奴。这是一种诗意化的构想。
“假凤虚凰”的同性恋爱故事,是本回的故事主体,但在小说中并未有正面描写。它是通过清明节藕官烧纸祭奠引出悬念,直到回末芳官叙说侧面介绍完成的:
这里宝玉和他只二人,宝玉便将方才从火光发起,如何见了藕官,又如何谎言庇护,又如何藕官叫我问你,从头至尾,细细的告诉他一遍,又问他祭的果系何人。芳官听了,满面含笑,又叹一口气,说道:“这事说来可笑又可叹。”宝玉听了,忙问如何。芳官笑道:“你说他祭的是谁?祭的是死了的菂官。”宝玉说道:“这是友谊,也应当的。”
芳官笑道“那里是友谊?他竟是疯傻的想头。说他自己是小生,菂官是小旦,常作夫妻。每日里那些曲文排场,皆是真正温存体贴之事,故此二人就疯了。虽不做戏,寻常饮食起坐,两个人竟是你恩我爱。菂官一死,她哭的死去活来。至今不忘,所以每节烧纸。后来补了蕊官,我们见他一般的温柔体贴,也曾问他得新弃旧的。他说,这又有个大道理。比如男子丧了妻,或有必当续弦者,也必要续弦为是。便只要不把死的丢过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只是因死的不续,固守一世,妨了大节,也不是理,死者反不安了。你说可是又疯又呆?说来可是可笑?”
芳官没有想到,这番“可笑又可叹”的话,却引起宝玉的强烈共鸣和极大震撼:
宝玉听说了这篇呆话,独合了他的呆意,不觉又是欢喜,又是悲叹,又称奇道绝,说:“天既生这样人,又何用我这须眉浊物玷辱世界。”
接着,他嘱咐芳官转告藕官:“以后断不可烧纸钱。”
芳官是藕官的朋友,也是唯一了解藕官故事的局外人,却讥笑她们“又疯又呆”,“可笑”。因为她无法理解,同性之间有超越友谊的“你恩我爱”,而且所爱者故去后,有新欢而又不忘旧情。这反映世俗眼光对“假凤虚凰”的否定和“真情”追求者的孤立。
然而宝玉不但在不知内情时出自本能地保护藕官,而且在知情后,对芳官对藕官的非议,他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这表明宝玉与世俗观念的对立,对“假凤虚凰”的完全理解和接受。藕官的“呆话”,合了宝玉的“呆意”,意味着“木石情缘”和“假凤虚凰”的不同情感形态实现了“真情痴理”的完全沟通。
没有俗笔和秽笔,同“木石情缘”一样,“假凤虚凰”也是一种纯真圣洁的感情,“你恩我爱”,“温柔体贴”。然而,它们都为世俗所不解、不容,同样孤独无助。
比较起贵族子女的“木石情缘”,“假凤虚凰”因为是卑贱者的“无果之花”,要承受外在奴役和世俗观念双重恶的压迫,更有绝望之痛。
在这个冰冷无情的世界里,理解就是最大的温暖和支持。这就是贾宝玉与藕官隔空对话的意义。
这是贾宝玉的声音,也是曹雪芹对同性恋者发出的声音,也就是本回回目嵌入“真假”二字的意义。
当然,宝玉的同情和作者的诗性用笔,并不能改变“假凤虚凰”的命运。和“木石情缘”的主角贾宝玉一样,藕官和蕊官最终也都遁入空门。
只是,人们在思考《红楼梦》“情”的悲剧意义时,总是有意无意地放过了“假凤虚凰”这个闪光点。
三、内省自否
贾宝玉对“假凤虚凰”的反应方式和强度耐人寻味。
贾宝玉对他所倾慕的美,对他所服膺的真理的崇拜是极为强烈而无条件的。这突出表现在具有其情感和思维特质的内省自否态度上。在小说中,我们多次听到这种声音,那是女性美(包括具有女性气质的男性)使他倾倒的强烈反应:
第七回第一次见到秦钟“粉面朱唇,身材俊俏,怯怯羞羞,有女儿之态”时:
(宝玉)心中似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呆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这等人物,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
第十九回第一次到袭人家,看到她的姨妹,不由赞叹,回家后向袭人说道:
我不过是赞他好,正配生在这深堂大院里,没的我们这种浊物倒生在这里。
第四十九回宝琴等来到贾府,一批新人进入大观园,宝玉不胜赞叹:
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可知我井底之蛙……
鲜明的平等观念和人本位意识,必然导致对贵族等级制度和贵族身份的自我否定。
这次听了芳官所述藕官故事,宝玉竟“又是欢喜,又是悲叹,又是称奇道绝”,反应更为强烈。又说此话:
天既生这样人,又何用我这须眉浊物玷辱世界。
但仔细读来,这些描写并非简单的重复。如果说,前面几次自否,是一种对美的偶像崇拜,那么,这次反应却表现为对真理(“真情痴理”)的崇拜,令他折服的,是“这样人”的所作所为所言语的真理性认识的力量。
贾宝玉话语中的“这样人”是指什么人?
是敢于冲破世俗偏见追求爱和深悟爱的真谛的人,是“假凤虚凰”故事主角的童伶女奴。
在这一点上,“这样人”的所作所为所言语为“木石情缘”所远不及。宝黛敢爱却不敢追求爱的实现,黛玉甚至害怕爱的表白,忍受着爱的痛苦折磨,更不用说去享受爱的幸福,领悟爱的真谛。
王夫人说她们“装丑弄鬼”,是“狐狸精”,赵姨娘骂她们“不过娼妇粉头之流”,连同样来自苏州的林黛玉,都为把她“比戏子”而大动肝火——然而,她们却是封闭的大观园里真正的春的使者。
这些贫寒之家的孩子,呼吸了晚明以来商品经济市民文化的新鲜空气,特别接受着优秀爱情戏曲及其表演实践的滋养,成为人性觉醒和个性觉醒的先行者。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贵族子女宝黛人性觉醒和个性觉醒的引路人。
茗烟弄来的传奇脚本《西厢记》催开了宝黛内心潜伏待萌的爱情之花;梨香院传出的《牡丹亭》艳曲唤醒了林黛玉的青春芳心;“龄官画蔷”让贾宝玉感受了异性痴恋,也是龄蔷之恋让贾宝玉懂得了“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坚定了在“木石”与“金玉”间的选择态度。
现在,又是“假凤泣虚凰”让贾宝玉“真情揆痴理”,完成了情观的认识。
所以,贾宝玉为之倾倒:“天既生这样人,又何用我这须眉浊物玷辱世界。”这已不是幼稚单纯的女性美崇拜,而是带着成长轨迹的贵族公子自我批判的时代先声了。
四、真情痴理
现在,我们进一步研讨本回的主旨“真情揆痴理”。
细读文本,可以体会到,所谓“真情痴理”,就是贾宝玉获得的“情观”认识,“揆”就是他获得认识的思考过程。
这种“情观”认识包含以下内容:
“情”的所有形态:友谊、恋爱(包括同性恋爱)、恩爱婚姻(包括再婚),都是值得肯定和应该被接受的; “情”的本质内涵,是“诚心”即自我的真情和对所爱者的感情奉献,是“敬”即对对方感情和人格的尊重; 反对“情”的物质化等级化形式化,回归和实现“情”的平等精神本体。
这是贾宝玉的情观,也是曹雪芹借以表达的自己的情观。其核心,是“情”的精神本体。这种精神本体,就是超越性别、婚姻,超越现实物质和等级制度等一切形式的洁净“诚心”,但它为当时社会所难以接收,反被看作“呆”“傻”,因而是“痴理”。
就贾宝玉而言,他的“情”观,从警幻仙姑梦中“意淫”之教和性的启蒙,直到“真情揆痴理”对“情”精神本体认识的完成,经历了从朦胧到成熟的过程。作者对此做了清晰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比较警幻仙姑“好色即淫,知情更淫”的“情”“淫”难分,它更强调“情”的精神层面和精神本质(“你恩我爱”“情深意重”“诚心”“敬”),显然是一种超越和进步。
由此,我们看到作者的精心布局:第五十七回写宝黛的生死之恋和第五十八回写藕官等的同性之恋,是在一个“情”的太阳下的相互辉映,或者说,后者是对前者的重要补充。完整的体现“情”的丰富形态和作者的博大情怀。
同时,“真情揆痴理”中以“情”揆“理”的观念,又是对至真纯情的一种补充。藕官在菂官死去后,与蕊官的“一般温柔体贴”,和她对男子续弦仍可“情深义重”的议论,实际上是对“从一而终”的情感偏执和礼教节烈观的否定。宝玉的赞许,显示出作者开明理性的情感态度。
后文将会论述,藕官和宝玉的议论,则体现了“揆痴理”的“揆”即理性思考的过程。
可以说,“理”即理性的介入和补充,才最后完成了贾宝玉对“情”的认识和态度,也才完成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情观的表述。
这种认识和表述,是对晚明以来主“情”思潮的继承和发展。汤显祖倡“情至”论,《牡丹亭题记》云:“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贾宝玉认可的情观,反对“分出等例,各式各例”的等级制度,强调“世法平等”“情深意重”的“真情痴理”,以“情”揆“理”,以“理”融“情”,体现主“情”思潮已经从浪漫走向成熟,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开拓。
曹雪芹刻意把贾宝玉塑造成“情不情”的“今古未见之人”(己卯本第十九回批语),一个重要意图,就是把“情”从单纯狭隘的两性之爱拓展到人类情感世界(包括异性和同性)的方方面面,进行更深层次的社会反映和哲理思考。贾宝玉的情感历程和情感世界极为丰富,他有刻骨铭心的恋爱,也有举案齐眉而不忘旧情的婚姻,有相互倾慕的同性交契,也有疑似“涉性”“涉同”的少时美妇腻友,更有一片痴心体贴的种种情感放射和延伸。但不管是哪种情,也不管其对象存逝,他都能做到“诚心”二字。在同藕官的隔空对话里,他特别提到自己:
你瞧瞧我那案上,只设一炉,日夜焚香。他们皆不知缘故,我心里却各有所因。
“他们”(按:指怡红院诸人)不知宝玉心中秘密,从文本内容中,我们却可以知晓,他“日夜焚香”“各有所因”者,是在此前死去的秦钟、金钏等人,也许包括秦可卿。总之,他们在宝玉心中,都是不能舍弃不能忘怀之人。
毋须去一一做伦理评判,不是纯而又纯,但却真而又真。宝玉确是一位有着佛性善根的“情之圣者”。宝玉的“情”史,就是一位少年的青春史,人性美善的成长史。同时,也是作者的自我心灵史。
这段“真情揆痴理”不只是从“假凤泣虚凰”就事论事,而且还是“木石情缘”的“草蛇灰线”,具有暗示宝黛钗爱情婚姻结局处理的意义。根据《红楼梦》“怀金悼玉”的意旨,和《红楼梦曲》“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等曲词,以及脂砚斋批语提供的线索,我们大底可知作者未完成作“黛死钗嫁”的构思,绝不同于今本一百二十回“钗嫁黛死”的描写。它呈现出另外一种悲剧性,可惜人们已无法看到其完成文本了。
需要补充的是,这既是为“木石情缘”伏笔,也是作者自吐衷曲。脂批早就指出二者的内在联系:“以顽石草木为偶,实历尽风月波澜,尝遍情缘滋味,至无可如何,始结此木石因果,以泄胸中悒郁。”(甲戌本第一回眉批)作者不但有苦痛的恋爱史,也有难忘旧情的再婚史。敦诚《挽曹雪芹》诗句“新妇飘零目岂瞑”,就透露了其间信息。
可见,曹雪芹不但是“情”的伟大描写者和思考者,也是“情”的追求者和实践者。也正因为曹雪芹有勇敢的追求和实践,他才能成为伟大的描写者和思考者。
五、“事体情理”:版本评析之一
在《红楼梦》的流传过程中,第五十八回不同版本出现了一些异文。其中最重要的是脂本与程本的异文。由于以庚辰本为前八十回主要底本的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是当前的普及本,而程高本是过去近二百年的《红楼梦》流行本。两峰并峙,二水分流。而版本选择事关阅读研究,学界又尚存不同意见,因此,比较这两个版本是很有意义的。
本回文字,程甲本与程乙本完全一致。脂评本(己卯、庚辰、戚序等)基本一致,略有差异。如果我们把庚辰本(己卯同)作为端点,程乙本(程甲同)作为终点,审视这一演变过程,大体是:
首先,戚序本(简称“戚本”)将“菂官”改名为“药官”。胡文彬先生指出:“菂官与藕官二人的名字均与荷花有关。荷根曰藕,荷花结实为莲房(又作莲蓬),其子学名为菂或称莲菂。”这种同根同命的关系,用于二人同性相恋的比喻是极为贴切的。改为“药官”则意境全无了。但这种改易却为甲辰本及程本所继承。
甲辰本开始出现明显删改异文。主要是删改了回末宝玉关于勿烧纸钱的议论,为梦稿本和程本继承(见后文)。
梦稿本改文与程本完全一致。“梦稿本的形成,最早出于程伟元之手”,从稿本可以看得出,这一部分的抄本底本属己卯庚辰本系统。
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就第五十八回而言,异文主要出于程本对脂本(庚辰本)的修改。
本文不拟全面评价程本对脂本修改的是非功过。仅从第五十八回故事主体看,这种修改明显是不妥当的。发生错误的原因:一是由于不明事体情理;二是由于不解作者用意。兹分论之。
“取其事体情理”是曹雪芹《红楼梦》的创作原则。所谓“事体情理”,应指人物性格、情节和细节情境等叙事内容的内在逻辑的合理性。
且看宝玉护庇藕官烧纸摆脱婆子纠缠,婆子离开后的叙事。庚辰本的文字是:
这里宝玉问他:“到底是为谁烧纸?我想来若是为父母兄弟,你们皆烦人外头烧过了。这里烧这几张,必有私自的情理。”藕官因方才护庇之情感激于衷,便知他是自己一流(戚本作“派”)的人物,便含泪说道:“我这事,除了你屋里的芳官并宝姑娘的蕊官,并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今日被你遇见,又有这段意思,少不得也告诉了你,只不许再对人言讲。”又哭(戚本作“笑”)道:“我也不便和你面说,你只回去背人悄问芳官就知道了。”说毕,佯常而去。宝玉听了,心下纳闷……
在这段文字中,宝玉询问藕官,有关切的口吻,有自己的分析推断,完全合乎贾宝玉惯于关心体贴女孩的性格。但程本改作“为谁烧纸?恐非父母兄弟,定有私自的情理”,就变成了咄咄逼人的责问语气和武断的主观推论,那里还有“情不情”的意味?明显不妥。
难点在“佯常而去”四字。藕官哭着说完话,怎么会“佯常而去”呢?《汉语大词典》释:佯常,又作“扬长”,“大模大样地离开的样子”。也许因为费解,红学所校注本在此未作注释。而程本改为“怏怏而去”,合适吗?
笔者尝试就其“事体情理”做出解释。
从前文描写中可以看出,藕官是一个用心缜密而情绪变化很快的女孩子。在烧纸事件中,她从受婆子纠缠,紧张啼哭,得到宝玉庇护后,“转忧成喜”到反过来“益发得了主意,反倒拉了婆子要走”,致婆子求饶。这就是藕官性格的“事体情理”。细读她与宝玉的这段对话,也可以感觉藕官的心理情绪变化,刚才“含泪”说要告诉宝玉,忽然又“哭”着说不便当面告诉,作者没有直接描写她的心理状态即所思所想,而是间接的通过两次话语内容的变化传达出来。其原因,究竟是因为情感另类难以启齿,还是恐怕宝玉难以接受(连芳官都觉得可笑可叹),作者也没有明说,留下了叙述空白。可以想象,从准备说到不愿说,当藕官对宝玉表明态度后,此时她既摆脱了婆子的纠缠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又下决心回避了当面自我陈述的难以为情,心情已经完全放松,“佯常而去”就是很自然的了。相反,如果改成“怏怏而去”,那才说不过去。《汉语大词典》释“怏怏”为“不服气或闷闷不乐的神情”,藕官有什么不服气或闷闷不乐的事情呢?而宝玉从期待听到藕官自述,到突然被拒绝,又眼见藕官“佯常而去”,自然不免“心下纳闷”了。这样,才合乎“事体情理”。
在“真情揆痴理”部分,程本还有两处错改。
宝玉向芳官询问时,庚辰本写芳官“满面含笑,又叹一口气,道:‘这事说来可笑又可叹。’”程本改为“眼圈儿一红,又叹一口气,道:‘这事说来,藕官儿也是胡闹。’”。“满面含笑,又叹一口气”的表情与芳官对此事“可笑又可叹”的看法完全对应。芳官年纪最小,对这种超乎友谊的情感不理解,是合乎其性格情理的。相反“眼圈儿一红”倒不可解了。因为“假凤虚凰”故事主体是真情而不是悲哀。况且依其改文,芳官既认为藕官“胡闹”,又怎么会“眼圈儿一红”呢?
更大的错误是对宝玉强烈反应的描写的修改。庚辰本写道:“宝玉听说了这篇呆话,独合了他的呆意,不觉又是欢喜,又是悲叹,又称奇道绝,道:‘天既生这样人,又何用我这须眉浊物玷辱世界。’”而程本改为:“宝玉听了这篇呆话,独合了他的呆性。不觉又喜又悲,又称奇道绝。”不但把生动描写宝玉心态的连续三个排比短语缩成两个,大大降低了表达的强度,而且把宝玉后面两句很重要的话语删去。这真是点金成铁了。须知,原文此处的内省自否式话语正是最典型的贾宝玉思想性格表现。贾宝玉在受到强烈心灵震撼时,产生内省自否,表现出一种十分可贵的平等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而这次,身份卑贱的女伶童奴的“假凤虚凰”故事所表现的“真情痴理”对怡红公子心灵的征服,更具有深刻性和震撼力。然而,程本却对此完全不理解,断然删去,曹公九天有灵,当作何感想?
六、“谁解其味”:版本评析之二
程本对脂本第五十八回改易不当的另一原因是不理解作者的写作用意,用曹公自己的话,就是不“解其中味”。
这在“真情揆痴理”部分表现得十分突出。
客观地说,就文字而言,程本比较简洁顺畅,便于大众阅读。但程本删去了脂本中的许多重要内容,除了把宝玉话中带有时代色彩的“友谊”一词改为传统词语“朋友”,以及宝玉的内省自否之语外,特别大量删削了藕官和宝玉话语里的议论成分。现录有关原文如下,以资比较。
其一,删去芳官转述藕官话语里的议论成分。庚辰本见前引,程本文字是:
后来补了蕊官,我们见他也是那样,就问他:“为什么得了新的就把旧的忘了?”他说:“不是忘了,比如人家男人死了女人,也有再娶的,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就是有情分了。”你说他是傻不是呢?
其二,删去宝玉话语中的发挥议论,这一段删削最多。现分别引出。脂本(庚辰本)文字是:
以后断不可烧纸钱。这纸钱原是后人异端,不是孔子的遗训。以后逢时按节,只备一个炉,到日随便焚香,一心诚虔,便可感格了。愚人原不知,无论神佛死人,必要分出等例,各式各例的。殊不知只一“诚心”二字为主。即值仓皇流离之日,虽连香亦无,随便有土有草,只以洁净,便可为祭,不独死者享祭,便是神鬼也来享的。你瞧瞧我那案上,只设一炉,不论日期,时常焚香。他们皆不知原故,我心里却各有所因。随便有清茶便供一钟茶,有新水就供一盏水,或有鲜花,或有鲜果,甚至荤羹腥菜,只要心诚意洁,便是佛也都可来享,所以说,只在敬不在虚名。以后快命他不可再烧纸。
程本文字是:
以后断不可烧纸。逢时按节,只备一炉香,一心虔诚,就能感应了。我那案上也只设着一个炉,我有心事,不论日期,随便新茶新水(程乙本作“新水新茶”),就供一盏。或有鲜花鲜果,甚至荤腥素菜都可。只在敬心,不在虚名。以后快命他不可再烧纸。
从纯粹叙事角度看,这种删节似乎并没有影响故事进程。但它却是对《红楼梦》话语体系特别是第五十八回话语系统完整性的破坏,因为它造成了“真情揆痴理”意义的悬空。
按照程本的删改,只剩下“假凤虚凰”故事叙述和宝玉勿烧纸钱的劝告,读者能了解所谓“真情揆痴理”的“痴理”是什么吗?能说出是怎样“揆痴理”的吗?
而依据庚辰本所写,人们就能体会到,“真情揆痴理”乃是贾宝玉在“假凤虚凰”故事及藕官议论的启发下,对“情”完成的理性思考,是贾宝玉“情观”的一次认识飞跃。被程本删除的议论文字,正是实现“揆痴理”的手段。
曹雪芹在这里借藕官的话说“这又有个大道理”,就表明了要从更高的精神层面“揆痴理”的意图。而藕官与宝玉隔空对话(通过芳官传言实现),包括令他“称奇道绝”的藕官的议论,和他自己的思考议论,则是完成“揆痴理”的理性过程。
可见议论成分,乃为实现主旨所必需。然而,删改者不懂作者深意,“买椟还珠”,令人不胜嘘唏。
在议论部分中,作者的两种手法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对各种思想资源的融合吸收,为我所用;二是通过“溢出”的议论直接表意。
程本的失误正是由于“不解其味”。
一是不理解作者对思想资料融合吸收为我所用的艺术手段,任意删削,导致思想意蕴的丧失。庚辰本文字所包含的思想信息是非常丰富的,从原始儒家、神佛宗教观到晚明王学左派。如“友谊”一词,从现知资料看,是晚明开始流行的。其中异端思想家李贽的《焚书》中《朋友篇》尤其著名。李贽称道:“去华(潘去华)友朋之义最笃,故是《纂》(指潘著《訚然堂类纂》)首纂笃友谊。”用“友谊”代替朋友之义,有突出朋友在“五伦”中地位的时代新意。“杂学旁搜”的贾宝玉接受了李贽影响,所以在议论藕官时说“这是友谊,也应当的。”然而程本反而改回“朋友”一词。
宝玉厌恶八股科举,但并不反对儒家学说,特别是原始儒家,他用“孔子的遗训”为依据批评烧纸钱陋习,这与他一贯尊孔的态度是一致的,也加强了批判世俗陋习的力量。议论中还借用了“诚”“敬”等儒学伦理修身基本概念,为“情”所用,阐述“心诚意洁”的情观,其中王阳明的“诚是心之本体”(《传习录》上)尤其有直接影响。在婚姻问题上,作者虽用了包含传统传宗接代观念的“大节”概念。但反对“孤守一世”,实际包含男女两性,男子再婚与女子再嫁实为同理,其批判礼教节操观的用意就很清楚了。所有这些思想资料,除个别词语外,几乎被删削殆尽。
二是不理解作者写实与表意相结合的艺术手段,片面删削,导致表意功能的弱化。可以说,“真情揆痴理”一段,既描写出贾宝玉对“情”的认识的飞跃,同时也寄托着作者自我情观表达的意图。前者是艺术写实,后者是主观表意。总的来说,主观表意是通过艺术写实实现的,但也有“溢出”的内容。其具体表现,就是人物语言中超出其性格情理逻辑的部分。这些“溢出”部分尤其成为作者直接表意的手段。被删去的藕官议论和宝玉议论都有这种内容。表面看,它们与人物年龄、教养、经历等并不完全吻合,而这正说明是作者在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藕官说“这又有个大道理”,特别是男子“孤守一世,妨了大节”的话,似非童伶口吻。前文已论,此处有暗示黛玉死后,宝玉与宝钗成婚甚至宝玉再娶之伏笔,且因曹雪芹逝世前有“新妇”,其借以自陈情怀的意思就更易体会了。至于宝玉关于祭奠形式的议论,其中“即值仓皇流离之日”几句,绝非宝玉人生经历所能道及,更是作者有所寄托无疑了。宝玉批评烧纸钱是“后人异端”,“无论神佛死人,必要分出等例,各式各例的”,就是因为这种物质化、形式化、等级化的仪式严重背离了“情”的精神本体,也背离了佛家“世(是)法平等”的要义。要求实现“情”的心灵化、洁净化,正是作者回归“情”的精神本体这一重要思考之本义所在。引孔子神佛,说“仓皇流离”,不但融合了各种思想资源,也融入了作者本人的家庭人生经历。虽为当时宝玉所无,却为作者所有。可以想象,“历尽风月波澜”“仓皇流离”之苦的作者一瓣心香所祭奠,该有多少我们至今还不了解的浃髓沦肤之痛。而且宝玉对祭奠物质化、形式化、等级化的批评,对心香的倡导,还与前面大肆铺张描写的秦氏之丧、元春省亲、除夕祭祖等遥相对应,暗含“情”对“礼”的批判,包括对家族衰败历史的反思,是一种大的思想布局。然而,所有这些深刻的表意内容,在程本不复可见,只剩下宝玉勿烧纸钱的劝告了。
有必要指出,在叙事中掺入议论,是曹雪芹实现写实与表意相结合的常用手法,且惯用“溢出”的议论直接表意。从纯叙事学,或者说故事的角度,它们容易被视为赘笔,而被忽视,甚至遭到处理。庚辰本被删削的例子不只第五十八回一个,另一个著名例证是第六十三回贾宝玉为芳官改名及由此所发议论,一千余字被统统删去,在庚辰本发现以前,堙没二百余年。对此,笔者已另有论述。
笔者不否定程本的优点和历史功绩。从程高刻印本取代脂批手抄本,再到今天出现以庚辰本为前八十回底本配以后四十回程本“脂程合一”的完整普及本,以及各种版本影印出版研究的百家争鸣,是红学版本史进步的轨迹,“也是新时期红学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在无法得到曹雪芹手稿本的情况下,比较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且保存又较完整的庚辰本文本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而囿于某种阅读和思维定式,这种低估确实还严重存在。笔者相信,必要的版本辨析比较,将有助于我们走近曹雪芹,走进《红楼梦》。
注释
① 本文所引《红楼梦》内容和原文,除特别注明版本外,均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 晚明以来,家班女伶一般由12 岁左右的角色齐全的12 个女孩组成,参见董昕《明清家班的兴盛和昆曲的传承》(《名作欣赏》2014年第14期)。
③ 参见《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④ 参见《玉台新咏》卷九《司马相如琴曲二首》,王实甫《西厢记》中“琴挑”折等。
⑤⑥⑦ 陈庆浩《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7年版,第349、18、18页。
⑦ 敦诚《四松堂集付刻底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⑧ 参见《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前言《大观红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⑨ 《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影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⑩ 胡文彬《感悟红楼》,白山出版社2010年版。
⑪ 《甲辰本红楼梦》第五十八回,沈阳出版社2006年版。
⑫ 《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杜春耕《梦稿本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⑬ 本文所引庚辰本原文,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程乙本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红楼梦》(程乙本);程甲本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红楼梦》(程甲本)。
⑭ 《汉语大词典》第1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5页。
⑮ 《汉语大词典》第7卷,第475页。
⑯ 李贽《焚书》卷5《读史·朋友篇》,岳麓书社 1990年版。
⑱ 参见刘上生《贾府早期家奴和包衣曹家之痛》(《曹雪芹研究》2017年4期)。
⑲ 张庆善《读红楼,你选哪个本子》,《光明日报》2018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