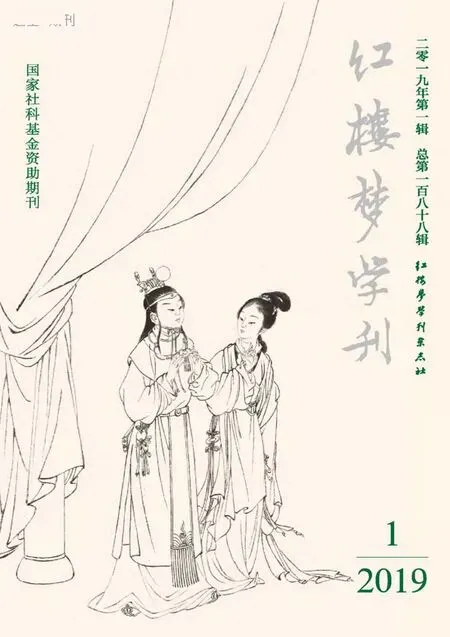“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
——林黛玉与《西厢记》《牡丹亭》
2019-11-12
内容提要:《红楼梦》第二十三回所描写的林黛玉读《西厢记》、听《牡丹亭》曲的情节,对揭示林黛玉的心理、性格与她身世处境的关系至为重要。林黛玉说《西厢记》“果然有趣”,之后又斥之为“淫词艳曲”,显示了林黛玉在内心情感、审美感受和道德观念之间的矛盾,也与明清两代对《西厢记》普遍的社会评价相关。明清许多文人认为,王实甫《西厢记》至第四本而止是至妙之文,显然,《红楼梦》著者亦持此观点。听《牡丹亭》曲,林黛玉先是由衷赞赏,随后“心痛神痴,眼中落泪”,其原因是《牡丹亭》曲触及了她如影随形的“身世之伤”。薛宝钗、史湘云、薛姨妈与林黛玉围绕其身世处境的对话,凸显了林黛玉对世情人生“通达”、透彻的认知。
《红楼梦》的描述中多次说到林黛玉不喜欢热闹,“天性喜散不喜聚”,“素习不喜看戏文”。但是实际上,多数重要的演戏场合林黛玉都在场。不过尽管林黛玉演戏活动参加得不少,却少有她点戏的描写。林黛玉点过戏没有呢?点过,只是在第二十二回薛宝钗过生日演戏时。那次是荣国府家宴,饭后演戏,点戏者的次序由贾母指定。首先由宝钗点了《西游记》,接着凤姐点了《刘二当衣》,之后便轮到林黛玉。林黛玉点了戏,但所点戏目没有说明。之后贾宝玉、史湘云、探春、迎春、惜春、李纨依次点了戏,均未说明戏名。想必大家都关注林黛玉究竟点了哪出戏,这很能显示她的情趣性格以及应对能力,偏偏阙如。
其实,著作者把关于戏曲之于林黛玉的影响的描写,留给了更为醒目的情节和更为深细的点染。人的心态一般不会在众人面前表现,而会显露在个人生活里不经意出现的插曲中。《红楼梦》正面描写了林黛玉私下里读《西厢记》、听《牡丹亭》曲,并由衷赞赏,这在当时可谓出人意表的一笔。《西厢记》《牡丹亭》两部戏在明清两代固然盛行,但文人士大夫对它们的态度却很微妙。例如对《西厢记》,虽然不乏赞美之辞,但其中不少笔墨是极力说明《西厢记》中描写的崔张相悦之情犹如《国风》中的“郑卫之音”,属“思无邪”之列,不应以淫邪视之。总之,让林黛玉这位深闺少女正面接触这两个戏,并令其由衷赞赏,是创作者剑走偏锋的笔墨。本文旨在透过林黛玉读《西厢记》、听《牡丹亭》曲情节,并且通过对相关情节的剖析,探讨这两部戏曲名著的加入,对小说里举足重轻的人物林黛玉形象的刻画,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同时,也对学界以往的相关研究及观点做出相应的辩证。
一、林黛玉与“十六出”本《西厢记》
林黛玉读《西厢记》,是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仲春时节,一个春光烂漫、诗意盎然的日子,桃花飘落,“落红成阵”,林黛玉来到花园葬花,恰与贾宝玉相遇,于是有了读《西厢记》的机会。且看以下描写:
那一日正当三月中浣,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走到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一块石头上坐着,展开《会真记》,从头细玩。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的满身满书满地皆是。……
宝玉正踟蹰间,只听背后有人说道:‘你在这里作什么?’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帚。……
宝玉听了喜不自禁,笑道:‘待我放下书,帮你来收拾。’黛玉道:‘什么书?’宝玉见问,慌的藏之不迭,……宝玉道:‘好妹妹,若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别人去。真真这是好书!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一面说,一面递了过去。林黛玉把花具且都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
显然,林黛玉是第一次读《西厢记》,而且是第一次接触《西厢记》这类通俗文学读物。她“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十六出一气读完,“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只管出神”“默默记诵”。头一次就遇到一部杰作,以林黛玉的文学品鉴力,心生赞叹实属必然。林黛玉读的是哪种《西厢记》呢?小说写贾宝玉拿的是《会真记》,《会真记》多指唐元稹的小说《莺莺传》。但是从林黛玉一口气读完十六出的描写,以及后文写林黛玉听《牡丹亭》曲文时联想到的《西厢记》曲文看,她读的是戏曲剧本《西厢记》。
戏曲剧作《西厢记》在明代之后有南北之分。清代舞台上所演多是明代李日华编撰的《西厢记》(在崔时佩《西厢记》基础上改编),即南《西厢记》,以昆曲演唱。李日华《西厢记》有三十六出;另有陆采所作南《西厢记》三十七出,均远超十六出。且李、陆的南《西厢》,文采意蕴远不及王实甫的北《西厢》,作为文学读物,无法替代王实甫《西厢记》。
尽管从明代始,北曲杂剧的演唱在戏曲舞台上渐成绝响,但是王实甫《西厢记》的刊刻却是从明代嘉靖之后到清代一直盛行。文人加入“笺注”“解证”“题评”抑或“白文”的北《西厢记》刊本蔚为大观。就今天能看到的版本,明代有近六十种,清代则有九十余种。尽管清代的近百种《西厢记》刊本大多是金圣叹和毛奇龄批本的不同刻本,但仍可见北《西厢记》作为读本盛行的程度。
小说中有贾宝玉正读到“落红成阵”的描写,“落红成阵”出自北《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第二首曲词【混江龙】“落红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贾宝玉说出的让林黛玉恼怒的两句词出自北《西厢记》第一本第四出第四首曲词【雁儿落】“我则道这玉天仙离了碧霄,元来是可意种来清醮。小子多愁多病身,怎当他倾国倾城貌”,都说明林黛玉读的是北杂剧《西厢记》。
随之问题出现了:王实甫《西厢记》分明是五本,每本四折一楔子,共二十折戏,为何林黛玉读的是“十六出”?众多北《西厢记》版本中有十六折的吗?蒋星煜先生对此问题的解答是:明代崇祯年刊刻的闵遇五《六幻西厢》中第三种《剧幻·王实甫西厢记》是十六出,林黛玉读的是闵遇五《六幻西厢》中的《剧幻·王实甫西厢记》。先了解一下闵本王实甫《西厢记》的具体情形。《六幻西厢》中《王实甫西厢记》之所以十六出,是因为它不包括第五本,到第四本止。在《六幻西厢》这套书中,《西厢记》第五本作为《六幻西厢》之第四种《赓幻·关汉卿续西厢记》独立存在。《六幻西厢》所录书目为:《幻因·元才子会真记》《搊幻·董解元西厢记》《剧幻·王实甫西厢记》《赓幻·关汉卿西厢记》《更幻·李日华西厢记》《幻住·陆天池西厢记》。可知《六幻西厢》实际收录的是写崔张故事的五部作品,北《西厢》一分为二,才成为六种。问题在于,无论第五本是否为关汉卿续,《西厢记》五本都是一个整体,《六幻西厢》将其作为两部作品收录,终属勉强,也属反常。况且,闵遇五还刊刻有一种《西厢记》,五本二十折俱全。笔者以为,决意弄清楚宝、黛所读《西厢记》版本的做法,与文学研究的要义偏离。那么是否还要去讨论闵本《六幻西厢》在清初是否容易看到,茗烟在一般的“书铺子里”(庚辰本为“书铺子里”,戚序本为“书坊内”)是否能够随意买到等问题呢?小说情节有无必要证之以实,属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答案应是不言而喻。《西厢记》的王作关续问题是个由来已久的公案,此处也不讨论。总之,说林黛玉恰恰读的是闵刻《六幻西厢》中《王实甫西厢记》,有过于拘泥实证之嫌。为什么程伟元本将“不到一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改为“不顿饭时,已看了好几出了”?蒋星煜先生认为,首要原因“可能是觉得看得太快了”,一顿饭的工夫看不了十六出。原因之二可能是“对十六出本的《西厢记》的出数发生怀疑”。笔者以为,改动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十六出”与《西厢记》出数不符。
值得注意的是,说《西厢记》为“十六出”,抑或说《西厢记》应该为“十六出”的,并非只是《红楼梦》的著者。此观点在明清文人及曲家对《西厢记》的评论中不时可见。明人徐复祚说:“《西厢》之妙,正在于《草桥》一梦,似假疑真,乍离乍合,情尽而意无穷,何必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而后乃愉快也。”金圣叹批本《西厢记》表达此观点更加鲜明。在第四本第四折《惊梦》(常见的四字出目为《草桥惊梦》)开篇,金圣叹批曰:“旧时人读《西厢记》,至前十五章既尽,忽见其第十六章乃作《惊梦》之文,便拍案叫绝,以为一篇大文,如此收束,正使烟波渺然无尽。”又在此折结尾处批曰:“为一部十六章之结,不只结《惊梦》一章也。于是《西厢记》已毕。何用续?何可续?何能续?今偏要续,我便看你续!”再于第五本第一折开篇批曰:“此续《西厢记》四篇,不知出何人之手,圣叹本不欲更录,特恐海边逐臭之夫,不忘膻芗,犹混弦管,因与明白指出之,且使天下后世学者睹之,而益悟前十六篇之为天仙化人。”如此等等,其意一言以蔽之:《西厢记》到第十六出就应该结束了,之后无可续。金圣叹说,他之所以将《西厢记》第五本纳入,是想让后人通过对比,看到至十六出而止的《西厢记》如“天仙化人”般美妙。尽管对金圣叹评点《西厢记》,尤其是他改动《西厢记》,清人颇有微辞,梁廷枬说他“强作解事”,但他关于《西厢记》前十六出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再如,俞樾《九九销夏录》记:“国朝沈起评点《西厢记》言:‘十六阕立名,上下相对。’”类似的观点不一而足。
回到《红楼梦》,重点要关注的问题在于,《红楼梦》中写《西厢记》为“十六出”有何用意?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相对忽略。若将林黛玉所读“十六出”《西厢记》理解为王实甫《西厢记》的前四本,倒是让人感到其中有深意。从《西厢记》本身说,抛开第五本,前四本写崔张二人越过重重障碍、终成连理。短暂的欣喜过后,不得不分离。全剧至此一气呵成。第四本的第三和第四两折,是抒写崔张离别悲情的重要场次。第三折写崔莺莺与张生离别在即,不仅崔莺莺心痛神伤,“阁不住泪眼愁眉”,“遍人间烦恼填胸臆”,“哭啼啼独自归”,张生同样感伤难抑,“阁泪汪汪不敢垂”。这出戏常见的题目为《长亭送别》,其中对离情别意的抒发可谓倾尽心力,妙笔生花。唱词说白中写离情的词句频频出现,如“离人伤感”“离人泪”“别离”“此恨谁知”“合欢未已,离愁相继”“别离情”等,尤其开场那首著名的【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对离愁别恨的文学表现,堪称经典。第四本第四折《草桥惊梦》,则写张生离别后第一晚,草桥夜宿,寂寞凄凉,梦魂萦绕。离恨难消,思念绵长。大家知道,唐小说元稹《莺莺传》(亦名《会真记》)中,崔张此别即恩情永诀。《西厢记》里,对崔莺莺和张生离别伤情的描写之所以动人心弦,成为经典篇章,除了二人情真意切外,更在于二人前途未卜。在崔张的时代,以崔张的境况,一旦分离,则重聚渺茫。“我则怕你停妻再娶妻”,是别离之际崔莺莺心中所想,也是她“眼中流血,心里成灰”的根源所在,这在当时绝非无谓的恐惧。而接下来的第五本,写半年之后,张生一举及第,立即给莺莺写信通报。赴任之际带着凤冠霞帔,准备迎娶崔莺莺。欢喜团圆。无论从艺术性还是现实性看,实为平庸之笔。所以,明清有曲评家讥其为“狗尾续貂”者。
对于《红楼梦》中描写林黛玉一口气读完的是“十六出”《西厢记》,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西厢记》前四本吸引打动林黛玉的,有美文,更有超越时空的悲情——离别之悲。从小说人物看,“别离”之于林黛玉,是终其一生无法躲避的遭际。她自幼到长,每一次离别都无比惨痛。幼小之时,经父母离丧,别母离父,音容永隔。青春妙龄,魂断贾府,死别贾宝玉。以林黛玉的审美情趣和欣赏格调,只有到《长亭送别》《草桥惊梦》而止的《西厢记》,才当得起林黛玉的由衷赞赏。作为小说的描写手法,只有《西厢记》第四本渲染的崔张别离之悲情,才暗合林黛玉的身世和命运。再从小说著者说,曹雪芹当与清代诸多文人的看法相近:《西厢记》只有前十六出为美妙之文,到第十六出戛然而止才是这部戏的理想之境。
二、读《西厢记》——“果然有趣”与“淫词艳曲”
当贾宝玉问林黛玉,这《西厢记》“你说好不好”?林黛玉毫不掩饰地笑道:“果然有趣。”林黛玉是对文艺作品有自己判断的人,对诗文有敏锐的鉴赏力,所以看似随意的一句“果然有趣”,绝非虚言。可是紧接着,“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城倾国貌’”,林黛玉听后,立刻心生怒气,顷刻翻脸,指斥宝玉说:“你这该死的胡说。”又斥《西厢记》为“淫词艳曲”,说贾宝玉学说里面的“混账话”“欺负”人。宝玉说的两句词出自《西厢记》第一本第四出《斋坛闹会》的【雁儿落】曲,是张生的唱词,表达内心对崔莺莺的爱慕,并非对崔莺莺当面表白。贾宝玉向林黛玉说出这两句曲词,应是因见林黛玉与他一样喜爱《西厢记》,情绪大好而有的忘情之举。可是,林黛玉的好心情霎时被破坏了。这是她“行动爱恼”“最是多心”的性格造成的吗?当然没有这么简单。虽说林黛玉的敏感性格也是她突然翻脸的一个因由,但更内在的原因,是《西厢记》这类通俗文学作品彼时在受众心目中所处的位置以及普遍的道德观念所决定。
自尊和敏感常常让林黛玉遇到一些事情时反应“激烈”,但这一次她的恼怒应该不算过激。林黛玉初次出场就表现出极度的自尊和敏感。“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原因是“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关键就在这里:怕“被人耻笑了他去”。即使处处小心,她还是格外容易感到被冒犯、被“耻笑”。如第二十二回看戏时湘云说出一个小戏子和她相像,她便大为生气。实际史湘云没有轻看她的用意,但以她的感觉,戏子地位那么卑微,当众拿她相比,就是对她的羞辱。当然,贾宝玉此番对她说出《西厢记》曲词引起的恼怒,情况不同,内涵更复杂。
可以肯定,贾宝玉并非拿她打趣,是当时的愉悦心情和素日的亲密情谊一并流露。庚辰本侧批曰:“看官说宝玉忘情有之,若认作有心取笑,则看不得《石头记》。”可谓道出了要领。可是林黛玉的感受不同,她感到的是不被尊重,受到“欺负”。问题还是出在贾宝玉身上。突然以戏里的情人相比,这对林黛玉来说,太随便了,是一种轻慢之举。实际上无论什么地位、什么年龄的人,都不能忍受轻慢的言语,也反感打趣的口吻。此时此刻,即使平日性情相投,有朦胧的恋情牵系,在关于男女婚嫁大事上的信口而言,对林黛玉来说仍是一种触犯。可作为比较的是,当贾宝玉认真地、发自肺腑地向林黛玉吐露感情,说出“你放心”时,林黛玉非但没有生气,而是感动得泪流满面。当贾宝玉让晴雯给林黛玉送去两条旧手绢,她虽然想到“令人私相传递与我,又可惧”,但体会到贾宝玉的心意,“不觉神魂驰荡”。并不像送手帕前晴雯所担心的,黛玉看到旧手绢“又要恼了”,会觉得是“打趣他”。
说到底还是道德观念问题。遵父母之命,依媒妁之言,守男女之防,这些道德规范的遵守与否,是在周围人群里显示人品高低的基本标准之一,涉及一个人的名声,尤其对女孩子,与维护自尊紧密联系。《西厢记》里崔张私下定情,无媒而娶,按传统社会的普遍观念,是有伤风化的事。所以后来文人和民间创作中,都有替崔莺莺述冤的作品。例如明代嘉靖年刊刻的曲集《风月(全家)锦囊》收有无名氏《打破西厢·莺莺述冤》,以崔莺莺的口吻说:“父亲兴时,母亲官诰重重赐,俺肯失落了人伦礼?……冤枉诉与谁?”并诅咒作者关汉卿:“逞你能,卖你会,数(教)你一家儿世世为娼,称不了崔莺莺心儿意”。明李开先《园林午梦》里通过戏曲人物李亚仙之口唾骂崔莺莺行为不端,“先奸后娶”。明代曲论家王骥德对《西厢记》赞誉有加,但也称《西厢记》为“淫词”,其曰:“《西厢》,韵士而为淫词,第可供骚人侠客赏心快目,扺掌娱耳之资耳。彼端人不道,腐儒不能道,假道学心赏慕之,而禁其口不敢道。”这段话含讥讽“假道学”之意,但也可见给《西厢记》戴顶“淫词”的帽子,当时较普遍。明清的杂史笔记中,为崔莺莺洗刷“羞辱”以及相关传闻,不时可见。例如,清代经学家焦循《剧说》记:“辉县褚邱,去百泉四十里,有白马将军祠,土人多崔姓,而近又有郑村。有演崔郑传奇者,土人以石击之。(见《书影》)《旷园杂志》云:‘唐郑太常恒暨夫人莺莺合袝墓,在淇水之西北五十里……,明成化间,淇水横溢,土崩石出,秦给事贯所撰志铭在焉。……志中盛传崔夫人四德咸备,乃一辱于元微之《会真记》,再辱于关汉卿、王实甫之《西厢记》。历久而志铭显出,为崔氏洗冰玉之耻,亦奇矣。’”关于褚丘演《西厢》艺人被驱赶一事,俞樾所记更详细,更丰富:“国朝周亮工《书影》云:辉县褚丘去百泉四十里,有白马将军祠,土人多崔姓者。而近又有郑村,有于褚丘演崔郑传奇者,土人以石击优人,讼之官。张菉居有《过褚丘》诗:‘玉勒追风下古乡,鸳鸯队里阵云黄。怪底褚丘看社上,无人敢去演《西厢》。’”竟至为演《西厢记》打官司,可知那时褚丘一地崔姓郑姓的人,认为《西厢记》对他们的侮辱之重。关于“郑恒崔莺莺合袝墓碑”及拓本的记载见于多种清人笔记,也有认为其为“赝物”者。另有家庭禁演《西厢记》的记载:“自元人王实甫、关汉卿作俑为《西厢》,其字句音节,足以动人,而后世淫词纷纷继作。然闻万历中年,家庭之间犹相戒演此。”这些记载反映了《西厢记》流传中的舆论生态和微妙状况。也正因为如此,宝黛只敢私下偷偷地读《西厢记》,不能让人知道。被长辈知道要遭责罚,让同辈姐妹知道便是自贬品格。林黛玉固然有些观念不从众随俗,例如对于关乎贾宝玉前程的“仕途经济学问”,大家都看重,她却视之若无。但对男女感情、男女交往以至男婚女嫁之事,她是顺从社会道德规范的。茨威格有句话说得很对:“儿童和年轻人都愿意让自己先体面地适应自己生活环境中的各种规范。”“适应”与否关系到“体面”,非同小可。这也是后来在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中,林黛玉在席间行令时,情急之中说出“良辰美景奈何天”(《牡丹亭·惊梦》)、“纱窗也没有红娘报”(《西厢记》第一本第四折)等曲词后,对薛宝钗的“审问”和教导,她心悦诚服、感激不已的原因。小说的描写是,经薛宝钗提醒,林黛玉“方想起来昨儿失于检点,那《牡丹亭》《西厢记》说了两句,不觉红了脸”。自己认为是“失于检点”,“羞得满脸飞红,满口央告”。
第五十一回也写到薛宝钗、林黛玉等关于《西厢记》《牡丹亭》的讨论。起因是薛宝琴作了怀古绝句十首,第九首《蒲东寺怀古》、第十首《梅花观怀古》分别咏《西厢记》《牡丹亭》故事,众人“称奇道妙”,独薛宝钗拿出姐姐的身份,批评道:“前八首都是史鉴上有据的,后二首却无考,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另作两首为是。”林黛玉、贾探春、李纨都不同意宝钗之言,林黛玉说:“这宝姐姐也忒‘胶柱鼓瑟’,矫揉造作了。这两首虽于史鉴上无考,咱们虽不曾看过这些外传,不知底里,难道咱们连两本戏也没有见过不成?那三岁的孩子都知道,何况咱们?” 李纨说:“如今这两首虽无考,凡说书唱戏,甚至求的签上皆有批注,老小男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况且又并不是看了《西厢》《牡丹》的词曲,怕看了邪书,这竟无妨,只管留着。”关于两首诗的去留,分歧的焦点在于,薛宝钗认为,《西厢记》《牡丹亭》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传说故事,即使随意写写的小诗,吟咏了也不雅。林黛玉、李纨等则为薛宝琴说话:闺阁小姐们并非是读了《西厢记》《牡丹亭》等书而熟悉这些故事,平日生活中看戏、听书、求签等活动常涉及戏词,躲不掉避不开,使得人人皆知,所以写写无妨。其实从对话看,他们基本看法是一致的:《西厢记》《牡丹亭》等“邪书”不看为好。
数百年间,戏曲小说所热衷描写的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是适应观众欣赏趣味构想出来的故事模式。尤其关于官宦贵族小姐的才艺容貌和情感经历,大同小异,几乎千篇一律,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崔莺莺这个戏曲人物正对应了贾母所指斥的当时戏曲小说里描写的“佳人”形象:“把人家女儿说的那样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是佳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这是基于实际生活的“掰谎”,反映了当时普遍的道德观念。此处无意贬低《西厢记》的思想艺术价值,只是阐述一种历史状况。
贾母对孙子孙女们宠爱有加,但不能容忍女孩子私下的恋情。当林黛玉得知贾宝玉成婚而病重时,贾母说:“若他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若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若林黛玉真恋着贾宝玉,即使是从小看大的外孙女,贾母也可以置之于不顾。
对《西厢记》,欣喜与怨怒,夸赞与指斥,在林黛玉来说,是审美共鸣和道德尊严相互矛盾的表现。心存朦胧的恋情,属意于贾宝玉是一回事,以私定终身相暗示是另一回事。说到底,《西厢记》在林黛玉心目中还是属于“淫词艳曲”,属读之有害的“杂书”。
三、听《牡丹亭》曲——“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与“心痛神痴”
还是第二十三回,读《西厢记》后,宝玉被袭人叫走,黛玉独自回屋,小说里的描写如下:
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上,只听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呢。只是林黛玉素习不大喜看戏文,便不留心,只管往前走。偶尔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道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又听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想毕,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又侧耳时,只听唱道:“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亦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又有词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
林黛玉无意间听到汤显祖《牡丹亭》曲的演唱,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反应。她先听到的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是《牡丹亭》第十出《惊梦》第四首曲【皂罗袍】的前四句。清代舞台演出本将汤显祖原作《惊梦》分为《游园》《惊梦》两出,此【皂罗袍】在舞台本《游园》中。听到此林黛玉感叹:“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前面说林黛玉“素习不大喜看戏文,不大留心”,一经留意,即领略到妙处,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于此可见。庚辰本《石头记》在“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句旁的批语曰:“将进门便是知音。”确乎如此。又,庚辰本在“自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句旁批曰:“非不及钗,你不曾于杂学上用意也。”的确,林黛玉前此对戏曲作品的了解品鉴似乎没有薛宝钗多,并非林黛玉见识不及薛宝钗,而是她从小没读过这类“杂书”,一向对戏曲不太留心的缘故。对《牡丹亭》曲的赞叹,见出林黛玉对戏曲作品的欣赏水平绝不弱于薛宝钗。
为什么林黛玉认为《牡丹亭·惊梦》好、感到深有“趣味”?《惊梦》写杜丽娘在自家花园游春后,春困小睡,梦里与柳梦梅缠绵。这出戏主要写杜丽娘伤“春”,既伤自然春光易逝,又伤青春年华易老,还伤男女春情难遇。杜丽娘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被母亲严加管束,春光大好时,即使自家花园也不让随意去游玩。林黛玉的处境不同,她住在如画似图的大观园里,可随时到花园游玩,没有春到园林而不知的苦恼。但她的感伤却有比杜丽娘更沉痛之处。接下来她听到的是:“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此为《牡丹亭·惊梦》的第八支曲子【山桃红】之首句。【山桃红】系杜丽娘梦中柳梦梅向她表达关切的唱词,情意绵绵。爱慕她青春正茂,又怜惜风华易逝,可谓知心知意。林黛玉听了便“心动神摇”。又听到“你在幽闺自怜”,这仍是【山桃红】的词句,林黛玉听了竟“如醉如痴,站立不住”。记忆里的诗句和刚听过的曲文,凡与伤时伤春相关联的,一时都涌上心头:“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水流花谢两无情”;“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综合看,都是感叹流年似水、青春易逝、岁月无情的名句。
看到此,明白《牡丹亭》曲何以令林黛玉情动神伤了吗?是伤春伤时令林黛玉心痛流泪吗?并不完全是。与杜丽娘相同的惜春伤时之感,只是引起林黛玉伤感的表层因素,且并非关键所在。“你在幽闺自怜”一句才是关键,是这句曲词引得林黛玉“如醉如痴”,浮想联翩。前文没有说明,读《西厢记》,感动林黛玉的究竟是什么?小说在描写林黛玉听《牡丹亭》曲时一并给予了说明。不能否认,除伤春伤时外,少女春情也是令林黛玉心动的内容之一。深闺静寂无人时,林黛玉曾将崔莺莺思念张生的曲词念出了声:“每日家情思睡昏昏”,恰巧被贾宝玉撞到听见,林黛玉顿觉忘情,弄了个大红脸。(第二十六回《蜂腰桥设言传心事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不过此处要强调,这不是主要的,真正刺痛林黛玉的,是【山桃红】曲中“在闺中自怜”一句。那么多寂寞白日和不眠长夜,她大都在“自怜”中度过。“自怜”的根源,是她的身世之伤。“不觉心痛神痴”一句上有眉批说得好:“上云‘不觉心动神摇’,此云‘不觉心痛神驰’,是身世之感,非春感也。”显然,令林黛玉“仔细忖度,心痛神痴,眼中落泪”更内在的根源,是她那排遣不掉的身世之伤。“你在幽闺自怜”一句后有王伯沆批语曰:“此五字括尽黛玉身世,作者选语岂非仙才。”所言极是,著者一定是费心挑选的曲词,恰到好处地概括了林黛玉的处境和心境。
可是,“你在幽闺自怜”分明是六个字,为什么说五个字呢?的确,汤显祖《牡丹亭》的原文只有五个字。此处插入一个小问题,在将《红楼梦》里的戏曲曲文与戏曲原本比对时,笔者时常看到《红楼梦》里所引曲文有所不同。而且,这些不同点显然多不是随意而为,耐人寻味。汤显祖《牡丹亭·惊梦》【山桃红】原文为“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清代的舞台演出本里这一句也都是“在幽闺自怜”。以折子戏选集《缀白裘》所选《惊梦》和另一种清代中叶的昆曲折子戏舞台本选集《审音鉴古录》所录《游园》为例,其中【山桃红】曲此句均是“在幽闺自怜”五个字,均没有“你”字。《红楼梦》里加了“你”字,变为“你在幽闺自怜”,则这句柳梦梅向杜丽娘倾吐真情的词句,显得更加温情脉脉,更加知心知意。对听众(观众)而言,则更容易令人产生代入感,更能直击人心。
林黛玉内心无时不在的伤痛,源自她孤独无依、寄人篱下的境遇。她那流不尽的眼泪,都是为此。《葬花吟》里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塚飞燕泣残红》),若看作是对林黛玉所受煎熬的比喻,这“严相逼”的“风刀霜剑”,其实就是她那无时不在、如影随形的身世之伤。有谁真正关心她、能给予她安慰吗?毋庸置疑,贾宝玉对她是关心的。但与贾宝玉的感情,对她是慰藉,也伴随着担心、猜疑和烦恼,这些烦恼又大多与无父母做主、孤独无靠的身世相联系。如小说里描写的她的心思:“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刻骨铭心之言,无人为我主张。”
薛姨妈、薛宝钗和史湘云都劝慰过她,每次劝慰无不围绕“身世”的话题。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薛宝钗让林黛玉吃燕窝粥保养身体,林黛玉说:“我又不是他们这里正经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多嫌着我了。如今我还不知进退,何苦叫他们咒我?宝钗道:‘这样说,我也是和你一样。’”说到要燕窝,林黛玉马上想到自己“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薛宝钗的安慰言辞恳切,“我也是和你一样”,言下之意自己也没有了父亲,也系借住贾府。林黛玉感到安慰了吗?她回答说:“你如何比我?你又有母亲,又有哥哥,这里又有买卖地土,家里又仍旧有房有地。你不过是亲戚的情分,白住了这里,一应大小事情,又不沾他们一文半个,要走就走了。我是一无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纸,皆是和他们家的姑娘一样,那起小人岂有不多嫌的。”与薛宝钗的差异,她心里一清二楚。有母亲、哥哥和家业在,就有依靠,就有人做主。即使没有了父亲,有母亲在,无条件的关爱、情感上的慰藉就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依靠就在。这些,再好的亲戚也做不到,人性使然。林黛玉的一番话,说得薛宝钗无话可说。不论林黛玉是否真的是“一无所有”,按理她是继承了林家遗产的。她说的这番话的关键,也是她凡事忧心的要害,还是无父无母,无依无靠的身世处境。
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联诗悲寂寞》,贾府中秋赏月,林黛玉见贾府老少齐聚,贾母犹叹人少,勾起心病,“不觉对景感怀,自去俯栏垂泪”。史湘云劝慰她说:“你是个明白人,何必作此形景自苦。我也和你一样,我就不似你这样心窄。何况你又多病,还不自己保养。”不需询问,史湘云便清楚林黛玉伤感的因由。史湘云的劝慰,确乎发自肺腑。自己现身说法,同样是自幼无父无母,依傍亲戚生活,心里的苦楚相通。与薛宝钗不同,小说描写史湘云的处境十分令人同情。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含耻辱情烈死金钏》,薛宝钗和袭人说到史湘云在家里的苦处:“问他两句家常过日子的话,他就连眼圈都红了,口里含含糊糊待说不说的。想其形景来,自然从小没爹娘的苦。我看着他,也不觉的伤起心来。”可知史湘云只是比林黛玉更善于自我排遣,不经常去咀嚼心底的苦痛,才能少流眼泪。真要说起来日常遇到的事,还是想哭,连薛宝钗看着也“伤起心来”。史湘云心里的苦楚并不比林黛玉少。
史湘云的劝解起了什么作用吗?就像史湘云说的,林黛玉是个明白人。她深知史湘云的好心和诚意,“见他这般劝慰,不肯负他豪兴”,便笑着把话题转到了联诗上。其实,林黛玉对人生、对事理的理解很透彻,她知道没有无忧无虑的人生。不仅如此,她还明了,凡事若真达到完美就无趣了。她说的那句“事若求全何所乐”概括了她看待事物通达的一面。当看到月光下的水面波光粼粼,史湘云说能坐船就好了,林黛玉说:“正是古人常说的好‘事若求全何所乐’。据我说,这也罢了,偏要坐船起来。”史湘云说起心里的苦恼:“就如咱们两个,虽父母不在,然却也忝在富贵之乡,只你我竟也有许多不遂心的事。”林黛玉回答:“不但你我不能称心,就连老太太、太太以至宝玉、探丫头等人,无论事大事小,有理无理,其不能各遂其心者,同一理也,何况你我旅居客寄之人哉!”她心里再清楚不过,不同处境的人有不同的苦恼,谁也不会例外。这是林黛玉对人生、对事理总的认识。任何一个文学经典人物都有多个性格侧面,林黛玉当然不会例外。林黛玉的聪慧过人体现在多个方面,对人生世情的透彻理解是其中之一。也许因为她“最是多心”“行动爱恼”“小性儿”的性情表现得太突出,人们不禁对她的“通达”感到惊讶,“事若求全何所乐”句上有眉批曰:“黛玉竟尔作此达语”,即为一例。
有谁真正关心林黛玉呢?抛开贾宝玉且不说,她的丫头紫鹃算一个。紫鹃为她试探贾宝玉,闹出一场风波。紫鹃还趁薛姨妈说起宝黛相配合适的话题,向薛姨妈说:“姨太太既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薛姨妈也曾安慰林黛玉说:“‘也怨不得他伤心,可怜没父母,到底没个亲人’又摩挲黛玉笑道:‘好孩子别哭。你见我疼你姐姐你伤心了,你不知我心里更疼你呢。你姐姐虽没了父亲,到底有我,有亲哥哥,这就比你强了。我每每和你姐姐说,心里很疼你,只是外头不好带出来。你这里人多口杂,说好话的人少,说歹话的人多,不说你无依无靠,为人作人配人疼,只说我们看老太太疼你了,我们也洑上水去了。’”薛姨妈这番话言及林黛玉的处境心情,俱是实情,言语不乏关切,只是太实了,句句触及林黛玉的痛处。说到对林黛玉的怜爱关怀,就像薛姨妈所言,外人看到的不太多。其原因除了她不能十分地表现出来,实际上她也不可能在林黛玉身上多花心力。尽管有段时间她住在潇湘馆照顾林黛玉——因一位老太妃过世,按制贾母等需“入朝随班按爵守制”。于是,贾母、王夫人等“每日入朝随祭”,“有一月光景”。因而贾母“托了薛姨妈在园内照管他姐妹丫鬟”。尤其“贾母又千叮咛万嘱咐托他照管林黛玉”。薛姨妈欣然应允,小说描述:“薛姨妈素习也最怜爱他的,今既巧遇这事,便挪至潇湘馆来和黛玉同房,一应药饵饮食十分经心。”林黛玉对此“感戴不尽”,干脆称薛姨妈为妈,叫宝钗姐姐,叫宝琴妹妹,“俨似同胞共出,较诸人更似亲切。”——林黛玉也曾说起要“认姨妈做娘”。总之,从对林黛玉的关照而言,薛姨妈确实给予了长辈的慈爱。但是,各家有各家的事,谁又能真正关心一个外人。加上薛姨妈当然知道贾宝玉的婚姻在贾府是举足轻重的大事,她怎么会轻易置喙。即便是贾母,对林黛玉来说是最亲的人,也是唯一有可能为林黛玉做主的人。自从林黛玉进到贾府,贾母对她“万般怜爱,寝食起居,一如宝玉,迎春、探春、惜春三个亲孙女倒且靠后”。给予了林黛玉生活上的呵护,但是她又何尝关心林黛玉的心思心情。如果涉及贾宝玉,贾母无疑首先从贾宝玉的利益前程考虑,林黛玉是可以舍弃的。确实像紫鹃所说:“替你愁了这几年了,无父母无兄弟,谁是知疼着热的人?”
另有一次,林黛玉谈到她十分重视的一件事——薛宝钗给予她的关心。那是在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风雨夕闷制风雨词》,林黛玉对薛宝钗说:“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姊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像你前日的话教导我。”这是林黛玉少有的发自肺腑地吐露心思。因林黛玉行令时说了《西厢记》《牡丹亭》的曲词,薛宝钗提醒、“教导”了她,在林黛玉心里,这次薛宝钗是真心关心她。关于看“杂书”问题,她甚至觉得是弥补了她幼年丧母的教育缺失。也因为那次“教导”,她对薛宝钗的看法彻底改变。她说:“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怨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昨儿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一向“孤高自许”的林黛玉,连自己的弱点——“最是个多心的人”和以往对薛宝钗的嫉妒和戒心都说出来检讨,可知她受感动的程度。
看看林黛玉大受感动的原因,还是“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姊妹兄弟”的不幸身世。母亲不在,谁会给予她关乎品格尊严的教导呢?她认为,薛宝钗给予了。以前有评论说薛宝钗善于笼络人心,自己看过“杂书”,却用一番一本正经的说教把单纯的林黛玉哄住了,让林黛玉感激她到如此地步,对她解除了戒心。其实,薛宝钗不会有意以读杂书不好这样的说辞去博得林黛玉的好感,林黛玉也不是那么好哄的人。以薛宝钗的精明聪颖,人情练达,她自然知道林黛玉不是容易被操控的人,不会轻易妥协和服人。薛宝钗是真心认为读“淫词艳曲”对女孩子不好,林黛玉也是打心底认为薛宝钗的提醒很重要。对薛宝钗的感激只能说明,林黛玉知道,读“淫词艳曲”若让众人知道,对自己极为不利,联系她曾吟出“质本洁来还洁去”的诗句,林黛玉对自身品格的“洁”的重视,不言而喻。而薛宝钗从小读过《西厢》《琵琶》“元人百种”等“杂书”,有过被家长“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的受教育经历,私下告诫林黛玉,是她的一片真心。今天的读者,也许对《牡丹亭》里杜丽娘连自家的花园都不能随意去游玩,裙衫上“花鸟绣双双”也要被家长责怪等情形感到不解,但是对于读淫秽读物不要张扬还是容易理解的。
林黛玉深知,她的身世变不了,性格改不了,心病去不掉,身上的病也好不了。第四十五回,薛宝钗说应该请个高明的医生来治病,林黛玉说:“不中用,我知道我这样病是不能好的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强的。”明白了这些,林黛玉应对寂寞困苦之境的方式,就是独自忍受,自我消解。于是,“在闺中自怜”,成了她的日常写照。自尊的品性,敏感的性情,使得身边的一景一物、他人的只言片语都可能引发感伤甚至气恼,她从来都是独自应对,不会去找别人述说。她明白,从他人那里,她得不到真正的安慰。所以,宁可让人说她“行动爱恼”,“小性儿”,也不找人诉苦,不向人解释。这中间,她自尊敏感的性格可见,洞明事理的心境可见。
曾读到北岛《记忆中的冯亦代》一文,其中说当代翻译家冯亦代是“一个绝望的浪漫主义者”,因冯亦代襁褓中丧母,命定一生内心苦楚。读到此颇被触动。“绝望”“浪漫”很接近笔者对林黛玉的感受,只是对林黛玉,实在不愿用“绝望”一词。但是,若不绝望,她何以吟出“冷月葬花魂”这样让史湘云、妙玉连称“太颓丧”“太悲凉”“太颓败凄楚”的诗句,何以写出让贾宝玉称为“哀音” 的《桃花行》。而另一方面,如果不是天赐任情浪漫的秉性,她又怎能生发出“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的诗意遐想。
一切看得透彻,明知难以到达心安之处,林黛玉心如止水了吗?没有。与贾宝玉的感情,是她内心深处潜在的希望,给予了她生活的力量,这是林黛玉始终葆有清纯浪漫气质和任情随性状态的源泉。唯其如此,她读《西厢记》、听《牡丹亭》才会产生那么强烈的情感反应。直至她心中的爱情离她而去,她情感的波澜才止息,她生命之花才凋落。
注释
① 《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词警芳心》,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版,第325、326页。按:本文凡引《红楼梦》第二十三回及其他原文,均依据此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校注本,下文不逐一出注。
② 王实甫《西厢记》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第一折,崔莺莺唱。付晓航编辑校点《西厢记集解》(此书所用底本为凌濛初《西厢记五本解证》本),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5页。
③ 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第一折,张生唱。(付晓航编辑校点《西厢记集解》,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
④ 此处不讨论“出”和“折”的区别,权且等而视之。
⑤⑥ 蒋星煜《关于宝玉、黛玉所读的十六出本〈西厢记〉》,《明刊本〈西厢记〉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第210—214、212、213页。
⑦ 徐复祚《曲论》,《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年版,第241、242页。
⑧⑨⑩ 张国光校注《金圣叹批本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56、268、274页。
⑪ 梁廷枬《曲话》卷五,《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中国戏剧出版社1960年版,第288页。
⑫ 俞樾《九九销夏录》卷十二“因琵琶记而知学问”条,中华书局 1995年版,第140页。
⑬ 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付晓航编辑校点《西厢记集解》,第246页。
⑭㉒㉓ 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24、526页。
⑮ 徐文昭编辑《风月(全家)锦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9页。
⑯ 李开先《园林午梦院本》,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398页。
⑰ 王骥德校本《西厢记》“新校注古本西厢记附评语十六则”,引自付晓航《西厢记集解》,第351页。
⑱⑳ 清焦循《剧说》卷二,《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中国戏剧出版社 1960年版,第104、160页。
⑲ 俞樾《茶香室四钞》卷二十“白马将军”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03、1804页。笔者按:俞樾《茶香室续钞》卷十九“白马将军祠”条记载了同一件事。
㉑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76页。
㉔ 出自《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崔莺莺所唱【油葫芦】曲的最后一句“每日价情思睡昏昏”。
㉕㉙ 冯其庸辑校《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青岛出版社2015年版,第644、1877页。
㉖ 引自成爱君校辑《红楼梦八十七回汇校汇评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页。
㉗ 汤显祖《牡丹亭》第十出《惊梦》,钱南扬校点《汤显祖戏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70页。
㉘ 笔者按:《缀白裘》和《审音鉴古录》这两部清代刊刻的戏曲折子戏舞台本选集,均录有《牡丹亭》折子戏《游园》和《惊梦》,系由原作《惊梦》分剖而成,但二者差别较大。原作《惊梦》共12 首曲词,《缀白裘》所选系从第六首【隔尾】截断,成《游园》一出,余下六首组成《惊梦》,故【山桃红】曲在《惊梦》里;《审音鉴古录》所选是从原作第八首【山桃红】截断成《游园》,余下的四首曲加【出队子】【寿眉序】【滴溜子】【五般宜】四曲组成《惊梦》,故【山桃红】曲在《游园》中。于是,“在幽闺自怜”一句,《缀白裘》在《惊梦》里,《审音鉴古录》则在《游园》中。(《缀白裘》第四集《惊梦》,中华书局1940年版,第111页;《审音鉴古录》录《游园》,《善本戏曲丛刊》第五辑,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554页。)
㉚ 汤显祖《牡丹亭》第十一出《慈戒》中,杜丽娘的母亲说:“少年女子,最不宜艳妆,戏游空冷无人之处。”钱南扬校点《汤显祖戏曲集》,第274页。
㉛ 汤显祖《牡丹亭》第十出《惊梦》,杜丽娘的母亲见她游园穿戴漂亮,说:“怪他裙袂上,花鸟绣双双”。钱南扬校点《汤显祖戏曲集》,第271页。
㉜ 北岛《记忆中的冯亦代》,《语之可》12“流水别意谁短长”,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