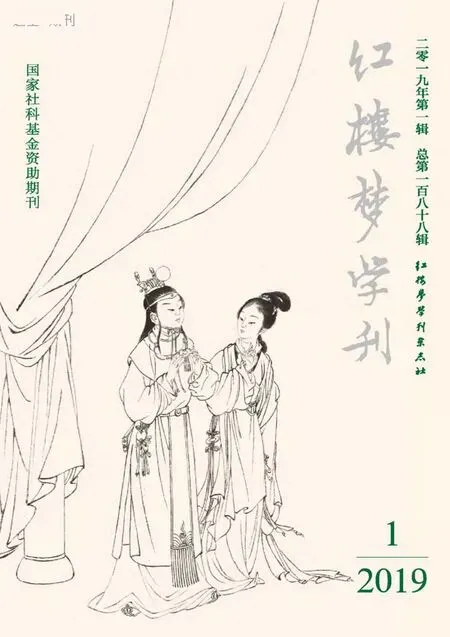文化理论视域下的美国《红楼梦》研究
2019-11-12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介绍近年来文化理论影响下的美国《红楼梦》研究。在梳理其产生的学术脉络和理论语境的基础上,对其思路方法和研究特点加以评析。近年来美国的《红楼梦》研究试图超越结构主义的二元概念,倡导一种更具开放性和多元性的新红学研究范式。文化理论的视野为其拓宽了研究对象和史料的使用范围,发掘出如园林、图像、医药、阅读出版等新的议题,并使之趋向于历史-文化的转向、对身份和主体的关注及意识形态批评。本文也试图探讨文化理论和美国汉学在解决《红楼梦》研究的困境方面带给我们的启示,以及在借鉴这些理论方法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在美国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一直是最为丰富,也最能代表该领域研究水平和关注趋向的。近年来,文化理论风行于欧美学界,它对美国汉学界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也自然体现在《红楼梦》研究中。从20世纪60年代文化研究的兴起,到90年代以来流布甚广的新文化史和新历史主义,这些新鲜的文化理论为近年来的《红楼梦》研究提供了诸多新的研究课题和批评方法。本文将对近二十年来文化理论视域下的美国《红楼梦》研究进行一番梳理和分析,探寻这些研究在学术史意义上的内在理路——其学术源流和理论语境,它与前代研究的承继关系以及与整个西方文艺思潮的互动,从中察知美国汉学界在研究中国小说问题时,是如何参与到这一“文化转向”的新范式之中的。通过检视其学术脉络,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美国红楼梦研究的洞见与缺失,并在研究思路和方法方面获得一些启示。
一、多维的阐释空间:《红楼梦》研究新范式的探求
美国的《红楼梦》研究可以说经历了两次重要的方法论上的转变,进而影响到对于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第一个转变出现在20 世纪70年代中期。1974年,余英时借用库恩的“范式”概念,呼吁红学研究亟需一种范式的转变,要把研究重心从《红楼梦》的外围问题转到中心问题,即小说的“创作意图和内在结构的有机关系上”。余英时所倡导的新范式旨在从新红学自传说的束缚中跳脱出来,强调《红楼梦》的理想性和虚构性,从一种史学的研究转向文学本位的研究。同时,他提出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说,以探讨小说中的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为中心,显示出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随后在米乐山和浦安迪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与余英时相似的理论姿态与批评实践,即要将红学研究从传统的历史研究中分离出来,赋予《红楼梦》的文学性以严肃的意义,而他们所依赖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都是结构主义式的,都以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模式为其研究的范型。
如果说由余英时、浦安迪等学者在20 世纪70年代中期所倡导和实践的这次范式转型是一场“由外至内”的(从外围的历史研究向文学本位研究的转变)、体现结构主义理论影响的重大突破,那么在新世纪之初,美国的《红楼梦》研究再一次提出的研究方法和范式转型问题则是“由内至外”的,并且是在后结构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进行的。苏源熙、顾明栋、鲁晓鹏等对此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理论探讨。苏源熙于2003年发表的《赋予作者的时代:〈红楼梦〉是如何最终获得一位作者的》一文对新红学“作者论”提出质疑,重新回到“评点”这一中国小说阅读的传统中,强调清代以来的评点者并不太在意《红楼梦》的作者为谁,而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这部作品的美学形式和哲学追求,他们“明了阅读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过程,成功的阅读不是获取一个确切的答案,而是不断地积累有益的洞见。”苏源熙把重点放在“由读者所发现和创造的那一面”,强调诠释者不断发掘的新视界,“我不是说我们应该忘掉所有关于曹雪芹的一切,只是说不应该忽视在曹雪芹被发现以前批评者所获得的关于小说文本的完全不同的视界”。苏源熙此处极力阐明的乃是阅读和阐释过程的开放性和动态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对待文本的基本方式,即将之理解为一种开放性的对话,这场对话发生在文本与读者之间,在文本的历史与未来之间。
顾明栋对“红学”新范式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探讨。他提出的新的“阅读范式”旨在超越色空、真假、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这些两极化概念,而强调两级的过程。他在《〈红楼梦〉是一部开放性小说》一文中着重论述了有关大观园和太虚幻境的隐喻具有多向度的特征,激起读者各自不同的解读和诠释方式,它们不仅具有理想世界和女性福地的乌托邦性质,同时也是象征皇宫、青楼、监狱、地狱等的反乌托邦意象。顾明栋的这篇文章明显地呈现出一种解构的倾向,认为《红楼梦》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来源于小说中符号间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网络,最显著的例子是读者熟知的“真”与“假”这对悖论性概念被重复地运用在小说中的各个层面,指向不同的人、事和场合。“这些文字游戏被安置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性交汇处,使得作者有关小说创作的开放性观念得以具体化。”因此,他呼吁一个新的“红学”范式,一个“开放式阐释空间”、“包纳各种不同的理解和阐释的阅读范式”。顾明栋对于《红楼梦》文本开放性的讨论固然是建立在解构主义关于符号的流动性以及语言、表意的多样性基础上,但同时他也像苏源熙一样,试图回到中国自己的叙事传统中,从中国的美学和形而上传统来探究中国小说具开放性和多元性的原因,如“意在言外”的抒情思想,以及阴阳有无相生、万物齐一等道家思想。
苏源熙和顾明栋都对文本的符号性以及读者在文本诠释中所具有的意义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由此阐述《红楼梦》意义的多重性和开放性,表明一种超越美国七十年代《红楼梦》研究“结构主义范式”的企图。正如罗兰·巴特所说,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是“从作品到文本”的转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解构主义者在颠覆结构主义关于文本的整体性、形式统一等概念的同时,也像结构主义一样屈从于对文本单纯的形式主义研究,而脱离了文本与阅读的历史维度。
近年来,西方人文社科领域对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进行各种反思和批评,越来越把注意力从抽象的语言系统转向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开始向历史倾向转变。鲁晓鹏正是从这个角度来反省《红楼梦》研究的结构主义范式的。他在《从史实性到虚构性:中国叙事诗学》一书中检视了余英时等学者的研究方法,指出“用文学研究来代替历史研究必然会带来某种损失,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对意识形态的忽略和将文学与历史的分离。”这一观点显示了新历史主义的痕迹。20 世纪80年代诞生于美国的新历史主义基于对后结构主义非历史倾向的反省,开启了各种对新的历史方法的探索,并渗透到所有文学研究的领域,凸显了历史与文学的互动关系,“同时关注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但是,新历史主义者虽然呼吁在文学研究中恢复历史维度,却努力避免陷入实证主义历史研究的旧路中,即讨论作品如何体现作者的原意,如何反映当时的历史现实和文化背景。这一点显示出新历史主义从它的批评对象后结构主义那里所承继的东西,即对文本开放性和阐释多元性的认同。正如鲁晓鹏指出的,“新的历史阐释学是一种开放的、未完成的、各种视角的集合”。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文学文本不只是对历史的模仿或者反映,它本身参与到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构成中,参与到与其他文化文本的对话中。因此,他们将文学文本看成是文化实践的一部分,试图解释文本与历史语境在具体文化实践中的相互作用。斯蒂芬·葛林伯雷甚至将新历史主义称为“文化诗学”(the poetics of culture),以此表明新历史主义者致力于从文学批评的视角进行文化研究的抱负。在很大程度上,新历史主义是与文化研究和新文化史运动相呼应的,它们普遍关注意识形态和文化特性等问题。因为将整个文化作为研究的对象,新历史主义和广义的文化研究具有强烈的跨学科性质,跨越了历史学、文学、艺术、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各学科的界线。
鲁晓鹏在对旧的《红楼梦》研究范式的批评中,强调了这种历史——文化的转型,并试图证明中国传统小说充满了文类的混杂、文本的不确定性、相互矛盾竞争的意识形态声音,它们是由历史、社会和文学多元决定的文本,这些特征正适合一种注重历史和文化多元性的新的研究范式。而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看到,新的历史意识和文化理论影响下的美国《红楼梦》研究正朝着阐释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的方向发展,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实践等角度对文本进行综合性和跨学科研究。在此意义上,新世纪的《红楼梦》研究经历着“从里到外”——从文学本位到历史文化的转型,它反映了一种新的历史意识,而在批评实践方面则大量运用了文化理论。
二、新视角的发掘:内容与范围的拓展
近二十年来美国学界的《红楼梦》研究与其理论思考相呼应,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这首先体现在其研究内容和范围的广泛性上,从宗教、性别、情感和心态等有关意识形态的内容,到园林、饮食、图像等物质文化方面,再到阅读出版、宫廷文化等社会层面。它所关注的议题则涉及社会政治、商品生产、意识形态、文人身份心态等各个方面。这些研究往往体现了新历史主义的倾向和文化研究的理论视野。
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成为史学研究的一种主流发展,物质文化的研究如食物、器物、书籍等成为文学、文化研究的重要主题和研究对象。《红楼梦》的百科全书性质使之特别适合这类日常生活和物质文化的研究。萧驰的著作《作为抒情之域的中国庭园:〈石头记〉通论》专门探讨明清园林文化对“大观园”的构造及小说整体结构的深刻影响。通过对晚明清初相关笔记文献的广泛考察,萧驰论述了晚明文人的园林文化旨在将文人行为抒情化,小说所描绘的大观园的诗意生活正是明清园林文化的生动再现,而这种园林化、抒情式的生活方式是明清文人文化标志性的构成因素。
宋安德的文章《〈红楼梦〉中的医案》则从日常医药文化入手,处理明清医案与小说叙事的关系,说明二者如何回应着相似的社会文化语境。文章细述了医案与小说的相互影响,试图说明《红楼梦》借鉴了医案的形式和修辞,并借助病症来界定人物性格和类型。该文对医案叙事性的强调,体现了新历史主义的研究视角,同时表明《红楼梦》囊括了当代的各类文本、民间信仰和日常知识,并使之作用于小说叙事。
在文化史和各类文化研究中,图像证据日益成为文献和统计证据的补充,最终图像本身成为物质文化的一个部分,也成了研究对象。文化理论倾向于采用细读的方法研究非文学类的文本,诸如图像、档案等。商伟的《假作真时真亦假:〈石头记〉和满族宫廷的视觉文化》就是用图像史的研究方法,通过细读清代满族宫廷档案和视觉、装饰艺术,还原《红楼梦》创作的历史语境。该文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论述自雍正朝开始,满族宫廷和庭园的装饰中流行用通草制作假花草、假宝石等。这使得“造假”的概念成为满族贵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文章指出,大观园的各种构造样式和视觉效果,与“造假”的宫廷艺术之间具有微妙联系,如台阶的西番莲花样式、假花盆景、假山石等,还有摆钟、壁画和西洋镜都是当时宫廷通景画和室内装饰中常用的艺术元素。由此可见雍乾时期宫廷文化对西洋文化的借鉴和想象,以及宫廷文化对《红楼梦》创作产生的影响。该文章体现了《红楼梦》研究中新的历史化的倾向,从视觉文化和宫廷文化的视角追索该小说的历史印记、以及它所具有的当代艺术的感性特征,使小说研究重回历史情境中。
书籍史和阅读史是文化研究者关注的另一大主题。文本不只是被看作一个静态的物质对象,更是一个流通和传播的媒介,“要建设一个研究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让与文本的形式相关的历史和阅读史读者史以一种辩证关系结合起来。”林凌翰《老祖宗的私下倾听:〈石头记〉中的表演、阅读、文禁和内在性的建构》就是从文本传播和印刷文化的角度来讨论清代文禁的历史现象和其间的权力运作。文章讨论《西厢记》《牡丹亭》等剧作在贾府的接受情况,并将这个问题与明清戏剧作品的印刷出版以及案头剧和舞台演出距离愈渐增大的情况联系起来讨论。林凌翰的研究提示我们在研究文本的阅读和接受时,不只要关注文本的内容,更要关注其媒介性和物质性。
文化研究既关注物质文化因素也包含对精神和意识结构的探索。事实上,自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欧美史学界日益关注价值与心态在人类行为中的角色,注意研究家庭史、性意识史以及情史。文化研究也进一步发展关于自我认知和情绪探索的讨论,把精神分析引入这一领域,以弥补文化研究在情感驱动和自我意识方面的不足。对情感和情绪问题的探索有利于了解社会价值观念以及日常思想的历史。这一观点和研究视野对美国汉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少探讨明清小说中欲望与情感问题的著作涌现出来。
黄卫总的专著《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将《红楼梦》置于明清世情小说的欲望主题下加以讨论,强调《红楼梦》在成书过程中如何“去性欲化(desexualization)”,从而重新塑造“情”的主题。该书把明清小说的兴起与市民社会和城市化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探讨市民文化的繁荣下,人们的情感生活和情感结构的特征。
吴逸仙《作为前提的情欲:〈石头记〉中的情色问题》一文则讨论《红楼梦》与情色文学和文化的关系,将《红楼梦》放在色情小说传统中进行考察,即所谓的“淫书”传统,如《隋炀帝艳史》《如意君传》《浓情快史》等“野史”类小说。文章梳理了巫山神女所代表的情色文化的传统,指出警幻仙姑本身也带有巫山神女的情色意味,并将之与“玄女”“素女”“玉女”等道教传统和房中术联系在一起。文章在讨论情色文化时也运用了精神分析的方法,把宝玉的梦游太虚幻境看作是传统心理学意义上的成人礼的象征,用弗洛伊德理论解释这一梦境中的情色因素。在海内外的《红楼梦》研究中,大多比较强调小说诗意(雅)的一面,而对其中色情文学和文化的因素关注不多。该文则比较深入地解析了《红楼梦》是如何在色情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改写和超越的。
马克·费拉拉的论文《宝玉和第二自我:〈红楼梦〉中的配对、镜像和乌托邦》是从内在的乌托邦冲动这一角度来探讨《红楼梦》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和在道家文化中寻求救赎的努力。文章指出《红楼梦》在人物、情节、场景等方面使用配对、镜像等叙述方式,凸显了阴阳五行和道家的文化观念。该文借用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将第二自我解读为被压抑的或者崇高化的欲望,也就是说,甄宝玉作为贾宝玉的第二自我是贾宝玉身份危机的心理投射,反映了贾宝玉获取理想自我的心理冲动。
文化在表述时还具有整合的特点,宗教观念、审美表达、对于身体的描述,甚至是书籍阅读等都往往与性别表述叠加在一起。文化理论受到后结构主义的深刻影响,在性别方面采取反本质主义立场,认为女性和男性的区别不是本质的差异,只是不同的话语结构。艾梅兰在《竞争的话语:明清小说中的正统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义》一书中引入性别视角来讨论“阴阳五行”之说。她极为关注小说中含有“六”和“九”的章节,认为“六”代表阴的一面,“九”代表阳的一面,诸如妒妇、死亡、不道德的欲望等负面意象都出现在带“六”的章节。艾梅兰认为阴阳之数与性别观念结合,表明正统性的话语潜藏于小说的叙事之中。另一方面,艾梅兰指出宝玉将大观园中的女性理想化,是对“女子气”的尊崇。“女子气”既可以是女性的属性也可以是男性的,它标志着自晚明发展起来的与儒家正统性抗衡的“本真性”,是一种美学和文化的策略。“本真性”代表的非正统价值观与“正统性”在小说中形成了一种竞争的关系。
黄卫总的著作《晚期中华帝国男子气概的建构》呼应了艾梅兰关于女子气的研究,认为明清小说中普遍存在的阴阳象征主义在表现性别结构时超越了简单的男女二元对立,而呈现一种微妙的动态性,“男子气”和“女子气”一样,“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在《红楼梦》里,“男子气”并不与“女子气”相对立,而是包含了某种女性特质,男女主人公都具备“才美兼而有之”的特征,从而模糊了性别界限。周祖炎的《晚明清初文学中的男女双性现象》论述贾宝玉和林黛玉所代表的男女双性的理想如何在父权社会性别秩序和文化的碾压下而破灭。周祖炎所谓“男女双性(androgyny)”的概念不止关乎性别,更象征着阴与阳、主流与边缘、臣服与颠覆等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问题。双性理想意味着边缘对主流文化的质疑和背叛,表达了边缘文人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挫折感。
性别研究与文化理论可以说是相伴而生。近年来的社会性别研究不再局限于女性形象或妇女史的研究,而是将男性纳入研究视野中,注重两性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关“男子气概”和“女性特质”如何被建构的讨论,强调的是性别的社会和文化构成。中国的文化传统对于性别的界定,与19 世纪以来西方关于性别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界定不同,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以男女生理特征来区分的固定或静态的概念,而是一种社会、政治、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建构。明清小说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对“女性特质”和“男子气概”的建构都有力地表现了性别的流动性,并有助于我们深入中国文化的特定历史情境和文化变迁来讨论性别建构和性别关系背后的种种动因。
三、方法论意义:特点与趋势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在文化理论的视野下,美国的《红楼梦》研究试图重新梳理作者、读者、文本与历史的复杂关系,回到历史的情境中解读作品,日常生活和日常文化成为研究的核心。文化理论中后结构主义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它的反本质主义。它启示我们意义并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总是在运动并不断得到补充。《红楼梦》研究范式的不断更新也是从固定的意义框架中不断跳脱出来,发展出新的阐释空间。这种反本质主义倾向也不断打破中心与边缘的分界,使《红楼梦》研究越来越关注边缘的领域和材料,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同时,文化理论对后结构主义的超越在于它的人文性,即对文本的诠释从抽象的语言系统转向社会文化语境,重视文化和社会的建构性力量、文本与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具体实践和作用。《红楼梦》的百科全书性质及其丰富深刻的意涵充分体现了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多元性。以下是文化理论视域下美国《红楼梦》研究所呈现出来的一些特点和研究场域:
首先,新的理论视野发掘出新的学术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比如新文化史也常被称为“表象史”,它既注重可见的文学形象,亦关注头脑中的意象,可归纳为“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本来处于边缘的研究领域——如器物、食物、日常生活、阅读、感官、情绪、知识等——近年来成为关注的焦点。史料的范围也被空前扩展,不仅是戏剧、小说、诗歌等文学文本,诸如图像、档案、仪式等非文学类文本也都可成为史料。对新的研究对象、新史料的挖掘必然要求新方法的开发。《红楼梦》研究的跨学科命题——文本与演出、艺术与小说、心理与仪式、小说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表明其研究方法也必然是跨学科的,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与文学的方法彼此参照并用。事实上,文化理论较少涉及方法的技术细节,而多涉及支撑它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即方法论。美国学者在研究《红楼梦》的文化问题时,并非停留在文化现象的描述层面,而是深入其产生的历史情境,对其文化逻辑进行思考。他们并不满足于描述作者赋予小说文本的思想含义,而试图说明意义如何产生,文化体系是如何塑造身份认同、情感表现和日常生活的。因此,文化理论对美国“红学”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文化视野的开拓上,更体现在方法论层面上。
比如萧驰对园林文化的研究,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美国学者有关大观园及园林空间的讨论由来已久,对此一问题做全面讨论的首推浦安迪。他发明出“二元补衬”“多项周旋”两个概念,用阴阳五行的哲学和美学观念来诠释大观园的构造以及小说的叙事结构。萧驰则进一步深化了有关《红楼梦》空间化叙事原则的讨论,将建筑模式与人物关系、空间意象与文人生活方式联系起来,探索这些空间特征背后的文化逻辑,特定的抒情美学和文人文化塑造了明清文人抒情化的生活方式,因而赋予大观园和小说叙事以抒情特征。与浦安迪结构主义研究范式下对中国文化总体特征的归纳不同,萧驰对《红楼梦》空间化的形式特征加以文化史的关照,具体落实到明清文人文化的特定语境中,并将文化语境和形式研究有机结合,体现了新的史学观念和文化理论对传统叙事学研究的影响与推动。
商伟的研究同样体现了历史化和情境化的倾向。他发掘出《红楼梦》中蕴含的清代宫廷视觉文化的因素,通过融汇艺术、历史和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揭示出作品中特定的文化语境,进而探讨其与文学审美和创作的互动关系。这种文化语境不是大而化之的,而是一种非常具体、细节化的历史解读。新历史主义或新文化史理论往往将格尔茨所谓的“厚描(thick description)”方法运用到自己的批评实践中。“厚描”被称为一种“微观的描述”,即“从以极其扩展的方式摸透极端细小的事情这样一种角度出发,最后达到那种更为广泛的解释和更为抽象的分析”。于是,文学批评可以进入那些边缘的、陌生的文化文本,“以颇有趣味的方式与人们熟知的文学经典进行互动”。商伟从小说中不为人注意的细节入手,将之与满族宫廷室内装饰中新兴的“造假”技术这一文化文本相结合,对《红楼梦》中广泛存在的“真假”主题重新进行历史化的诠释。这样的研究既重新诠释了文学经典,又为传统的文献和考证方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和可能性。这种“厚描”的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与美国学界自新批评以来的“细读”传统相呼应,可以说形成了一种更广范的“文本细读”方法,包括文学文本和非文学类文本的细读。上述的研究示例都很好地呈现了这种文本细读的方式。
其次,对于自我、身份和主体性的讨论,是文化理论关注的中心领域,也是美国明清小说研究探索的一个核心议题。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的流行使文化身份的问题越来越被强调。“身份”问题体现了权力制约和社会关系中的自我界定和自我表达。在明清时期的社会环境中,文人群体所面临的身份危机与科举制的关系最为密切。当科举制越来越无法保障文人们进入仕途,获取相应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他们就需要重新定义文人角色和重建文化认同来加以应对。“情”是自晚明以来重建文人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显示了文人主体在面对社会变化时所面临的身份危机,重新寻求和获取文化身份,以平衡科举制所带来的弊端。
在文化理论视域中,情感是一种文化性的界定,它会随着文化和历史的改变而改变。正是在情感的表达和讲述中,形成了一种身份的认同。从宋代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正统话语,到晚明将情欲自然化的“异端”之说,再到清代对情、欲重新加以规范的修正策略,“情”是明清小说寻求另类的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的方式之一,而关于性的话语也是定义主体性的方式之一。黄卫总的研究表明,“情”和“欲”之间或相融或相斥的关系表现出自我的复杂性。虽然《红楼梦》不同版本的删改表明其成书经历了一个不断地从“欲”到“情”的“净化”过程,但“欲”总会悄然突破各种界限,最终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形的越界作用,构建一种异于传统的新的自我观。吴逸仙的文章指出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一节不仅表现了宝玉的潜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有意识的修辞策略,戏剧性地再现了身份认同形成的过程。这个梦对理解宝玉完整的现世存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些研究在文化理论强调社会、文化等外部话语的同时,也关注内在情感,完善一个关于自我、主观性和身份的叙述。
文化理论也特别关注性别是如何被建构的。性别身份是身份认同的一种重要构成。文化研究对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不同模式的探讨,关注的是主体本身的文化结构。正如后结构女性主义反复论述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不是普遍和永恒的,而是描述和训练人类主体的方式和话语结构。近年来关于《红楼梦》的性别研究多从这一文化立场出发。宋安德研究医案在性别概念上对小说的影响,医案如何通过疾病和身体的知识进行性别构建,而小说将这种性别区分加以强化。艾梅兰对“女子气”文化意涵的辨析和黄卫总讨论“男子气”时对男子气概与女性特质互动关系的强调,都表明《红楼梦》中的性别身份是主体性构成和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女子气”对传统自我观进行反思,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
再者,文化研究强调文化和社会的建构性力量,最终回到意识形态议题、权力与文化关系的探讨。正如林·亨特所指出的,“如果说新文化史有什么一以贯之的目标的话,那就是通过对各种文化体系的调查去研究话语、仪式、再现中权力运作的机制、所使用的技术手段,揭示权力是如何通过控制知识的生产来展开博弈的。”权力概念居于文化理论的中心地位,它探讨的是弥漫在社会关系、文化体系各个层面的权力是如何运作,并使社会和文化的各方面联结在一起的,意义是如何通过社会权力的运作来完成的。
林凌翰的文章通过对《红楼梦》中阅读“禁令”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小说中规训和压迫等权力运作的问题。他认为这些“禁令”主要指向小说阅读,而并非戏曲表演。贾母对才子佳人故事的“禁令”则更明确地指向弹词这种低俗的表演形式,而对《牡丹亭·惊梦》的昆曲演唱却采取了默认的态度。昆曲和弹词的区别在于标识着不同阶层的趣味,贾母对昆曲的偏爱显示了贾府的贵族趣味和特权。不过,正如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宝玉和黛玉违背禁令,私自阅读这些故事反而成为小说中最为动人的场景之一。由此,文章试图以一种更微妙的视角来重构文禁这个历史现象及其背后的权力运作模式。该研究显然受惠于布尔迪厄和福柯的理论。文章运用布尔迪厄有关“文化资本”的理论分析不同的文学传播方式以及不同的戏曲表演形式代表不同阶层的趣味,是维持阶级身份的重要标识。同时,福柯关于规训、惩戒等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批评也为该文讨论权力-文本-媒介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
此外,对性别问题的研究也倾向于关注边缘群体或文化如何挑战主流的儒家文化秩序和价值观。比如周祖炎有关“双性”理想的论述则表达了对父权社会性别秩序和主流文化的质疑。宋安德的医案研究表明知识与性别话语、意识形态密不可分。明清医案和小说叙事中,女性疾病与“血”有关,男性疾病与“精”相关。女性的疾病往往是其情感压抑的表征,而男性则由于过度的欲望导致疾病。在这里我们看到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知识的生产来展开的。
结 语
美国的《红楼梦》研究经历了两次范式更新,从早期实证主义的社会、历史研究转向以“创作意图和内在结构”为中心的文本研究,再到近来广义的文化研究,从对小说虚构性和艺术性的强调到一种历史主义的重现,从结构主义的二元构架到后结构主义多元阐释空间的发展,体现了近年来美国学界的研究趋势和潮流。不过,我们应当辩证地、反思地看待这种发展,它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进程,而应该是不断地对原有问题的反思、拓展和深化,是更新而非替代。朝向历史-文化新范式的转型,首先是对结构主义有关文本自足性的反思,因而以恢复历史意识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原则,但它又并非回到作品反映历史现实和文化背景的旧思维中,而是探索文化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要素如何发挥其作用,强调文学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文学与权力政治的复杂关系,文学参与意识形态构造的方式。更深刻地挖掘《红楼梦》的历史文化语境,并不能否认它的虚构特性;对文化现象和文化逻辑的重视也不应否定文学自身的价值,因为文学本身就植根于历史文化话语,并参与其中;对社会和文化进程的强调也不能忽视对个人和主体的人文主义关注。总体而言,对《红楼梦》研究方法和范式转型问题的呼吁应朝向一种更具开放性和动态性的模式,从政治权力、身份认同、文化实践等角度对文本进行综合性研究,最终进入文本、主体和文化多重对话的层面,而《红楼梦》的卓越之处正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多向度的阐释空间和可能性。
受到后结构主义影响的文化研究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不断对自身方法进行反思。对新材料和新视角的发掘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研究的边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是对新议题永无休止的追逐,而应探讨文学和历史研究更普遍的方法和目标。文本阐释的深度和可靠性仍然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原则。文化理论也还要回归文本本身,达到文本分析和语境研究(历史的、文化的和理论的)的平衡。不论是从文本基础出发,对文化现象进行分析和归纳,探寻其规律得出宏观的结论,进而获得理论价值,还是以一种理论眼光审视文本,发掘新的研究视角从而寻求理论意义,最后检验二者的价值都是看它解读作品、解释文学、文化现象的有效性。
同时,多元共存的理念和多种研究方法的交叉使用,其目的是构成一种综合性的、更具开拓性的研究视野,而非某一种单纯理论或文学批评方法的生搬硬套。美国的《红楼梦》研究虽然深受后现代主义观念和文化理论的影响,以之作为学术思考的平台,但其最终目的是试图借助这些理论和方法,深入探究《红楼梦》的原始文化语境及其背后的中国文学、文化自身的问题与特征,由此对西方的文化传统、社会伦理与现代性等问题进行反思。重视文化差异的同时也强调文化沟通的可能性,是文化研究的愿景所在。对美国汉学家而言,《红楼梦》显示了一种持久而活跃的独特性,可以藉此参与到整个西方思想文化潮流和议题讨论中,同时他们也致力于在全球理论视野中展现中国文学文化的独特经验,由此为西方的文学概念和文化观提供反思。
可以说,文化史家是在一个去经典化的时代里从事他们的工作,对边缘的知识和材料的强调,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一部分,但并不能因此而忽视对精英文化和经典著作的研究。就《红楼梦》研究而言,美国学者也面临着与我们相似的困境,如何为经典文本寻找新的释义空间,如何与当下的文化思潮和社会关注相联系。美国学者对中国及中国文学问题的关注自然取决于其自身的知识视野和问题意识,但也为我们本土的研究提供了反观自身的媒介。在方法论上,将文本阐释、历史还原、理论探索结合,去思考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在这样的方法论基础上写作的文化史不应当从某一种特定视角来写,而应当是一种“众声喧哗”的历史。新世纪以来美国学者对红学研究范式之开放性的探索,既凸显了对小说本身在结构和意义上的开放性的认识,也指向研究视野的多元性。只有将文学诠释与历史意识、文化视野相结合,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互为补益,才能构成对《红楼梦》的完整认识,形成各种研究方法和角度的深度对话。
注释
① [美]理查德·比尔纳其《超越文化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② [美]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2卷第期,1974年6月。
③ [美]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2期,1974年6月。
④ Lucien Miller,Masks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Tuscon: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75;Andrew H Plaks,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
⑤⑥ Haun Saussy,“The Age of Attribution:Or,How the “Hongloumeng”Finally Acquired an Author,” 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 (CLEAR),Vol.25 (Dec.,2003)。
⑦⑪ Ming Dong Gu,“Theory of Fiction:A Non-Western Narrative Tradition,” Narrative,Vol.14,No.3,October 2006;[美]顾明栋《小说理论:一个非西方的叙事传统》,《原创的焦虑——语言、文学、文化研究的多元途径》,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158、159页。
⑧⑨⑩ Ming Dong Gu,“The Hongloumeng as an Open Novel Towards a New Paradigm of Redology,” Monumenta Serica,Vol.51 (2003);[美]顾明栋《〈红楼梦〉是一部开放性小说》,《原创的焦虑——语言、文学、文化研究的多元途径》,第308、309、328、307页。
⑫ [法]罗兰·巴特《从作品到文本》,《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5期。
⑬⑮ Lu,Sheldon Hsiao-peng.From Historicity to Fictionality:The Chinese Poetics of Narrativ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美]鲁晓鹏《从史实性到虚构性:中国叙事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第145、149页。
⑭ Louis Montrose,“Professing the Renaissanc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ulture,”in The New Historicism,ed.H.Aram Veeser (New York:Routledge,1989),第20页。
⑯ [美]斯蒂芬·葛林伯雷《通向一种文化诗学》,张京媛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⑰ Xiao Chi,The Chinese Garden as Lyric Enclave:A Generic Study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1.
⑱ Andrew Schonebaum,“The Medical Casebook of Hong Lou Meng,” Tamkang Review,Vol.XXXVI,Nos.1-2,2005。
⑲ Shang Wei,“Truth Becomes Fiction When Fiction Is True:The Story of the Stoneand the Visual Culture of the Manchu Court,”The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Vol.2,Issue 1,April 2015,第207-248页。
⑳ [法]罗杰·夏蒂埃《过去的表象——罗杰·夏蒂埃访谈录》,李宏图选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4页。
㉑ Ling Hon Lam,“The Matriarch’s Private Ear:Performance,Reading,Censorship,and the Fabrication of Interiority in‘The Story of the Stone ’,” HJAS,Vol.65,No.2,Dec.,2006.
㉒ [英]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 1929-2014》,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114页。
㉓ [英]克里斯·巴克《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第127—132页。
㉔ Martin W.Huang,Desire and Fictional Narrative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n Center,2001)。
㉕㉞ I-Hsien Wu,“Lust as Prerequisite:Eroticism in The Story of the Stone,”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Vol.4,Issue 1,Apr.2017.
㉖ Mark S.Ferrara,“Bao-Yu and the Second Self:Pairing,Mirroring,and Utopia in HonglouMeng,”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ies,Vol.17,No.3,2015.
㉗ Maram Epstein,Competing Discourses:Orthodoxy,Authenticity,and Engendered Meanings in Late Imperial Chinses Fiction,(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n Center,2001),第150-198页。
㉘ Martin W.Huang,Negotiating Masculin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6),第8页。
㉙ Zuyan Zhou,Androgyny in Late Ming and Easrly Qing Literature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第155-198页。
㉚ [美]伊佩霞《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第23页。
㉛ [英]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
㉜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㉝ Gallagher C.& Stephen Greenblatt eds.,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2000,第30页。
㉟ Linda J.Nicholson,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第1-18页。
㊱ [美]林·亨特《新文化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7页。
㊲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㊳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