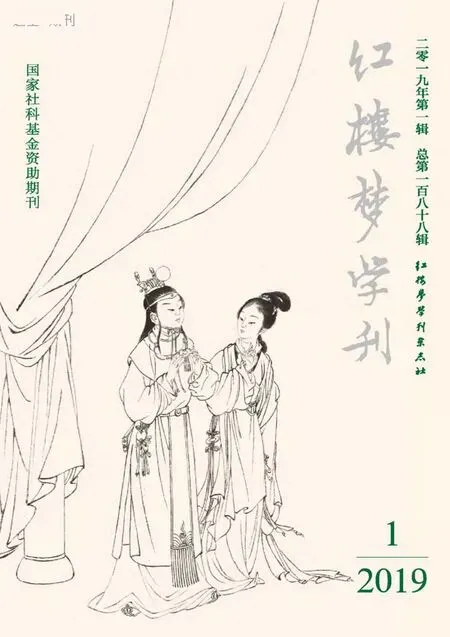薛宝钗与“冲喜”
——明清小说中女性的日常生活
2019-11-12
内容提要:“冲喜”虽为中国古代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婚姻形式,但在婚姻家庭史、丧葬制度等社会学、民俗学研究中都难以查到对它的详细介绍、分析和研究。本文通过对“冲喜”和“荒亲”的婚姻行为的研究(包括在冲喜婚姻中,冲喜女性要面临的五大问题、男性的自喻和自我激励、女性的参政意识等),对宝钗的信件和伴随着一系列人物死亡的整个议婚、结亲、成婚过程的分析,论证了“冲喜”婚姻使得人物性格前后一致、丰满完整,更好地诠释了黛死钗嫁的悲剧结局。
一、缘 起
民间所谓“冲喜”有多种形式和内容,其中之一就是以婚姻为将死之人冲喜。《红楼梦》中唯一、也是最重要的“冲喜”就体现于宝钗与宝玉的婚姻中。可是到目前为止,对此问题的研究却几乎没有。无他,皆因宝钗为宝玉的“冲喜”发生在后四十回中。殊不知,《红楼梦》对这次“冲喜”的描写之详细清晰完整,实为明清诸小说乃至诸文献中此问题叙写与记载之首,极具文学、史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研究价值。
另有一奇处,即“冲喜”虽为中国古代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婚姻形式,但在婚姻家庭史、丧葬制度等社会学、民俗学研究中都难以查到对它的详细介绍、分析和研究。相关论文或专著中最多是没有抛弃这一形式,偶有提及“冲喜”这一词语并捎带几句解释而已。至于对这种婚姻形式的具体性质、方式、影响等,更无一星半点主动研究或论述。事实上,就其在民间的使用率和对女性生活的巨大影响来看,这种研究上的疏漏,实为憾事。
鉴于此,本文将对《红楼梦》中宝钗和宝玉的婚姻所涉及的“冲喜”在小说创作中的价值和意义加以研究,兼谈明清小说、文献中提到的“冲喜”与两性对冲喜的态度及冲喜给女性生活造成的影响等。
二、《红楼梦》中一个独立存在的主题:宝钗的婚姻
《红楼梦》的主题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几十种说法,其中,宝黛爱情当然众口一词,是不可否认的主题之一。但作者专注于宝黛爱情描写的同时,还对另外一个问题给予了同等关注,我们也不应该忽略,即宝钗和宝玉的婚姻。《红楼梦》诸多主题中,虽说已有金玉姻缘和木石姻缘冲突悲剧说,但这与在小说中早已是自成体系的钗玉完整婚姻关系的叙述有质的不同。《红楼梦》是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完美结合的文学作品,如果说宝黛爱情是浪漫主义的代表,黛玉是爱情悲剧的象征,那么,钗玉婚姻便是写实主义的代表,宝钗是婚姻悲剧的象征。
《红楼梦》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向世人展现了清代贵族的生活全景。这种所谓生活全景所呈现的不仅仅是桌椅古董、饮馔服饰、医药建筑、礼仪典制等可查考之物,更重要的是一种在任何古籍文献中也找不到的、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现实生活过程与经历。宝钗和宝玉的婚姻便是一例。
先查中国婚姻史,所涉及婚姻形式包括掠夺婚、交换婚、服役婚、买卖婚、赠婚、赐婚、赘婿与养媳、虚合与姘度等。因宝钗与宝玉是以“冲喜”为目的而结婚,则应属其中的“虚合”。但大多数婚姻史要么根本不提这种婚姻形式,要么至多说上一句:“其中亦有于未婚夫病危时而即过门者,往往由未婚夫之姊妹代行其婚礼,是又可称曰代婚,俗则以冲喜名此过门之事云。”从历代婚姻史的记录中,我们无从了解这种以“冲喜”为目的的婚姻形式其过程到底是怎样的。次查各种古籍文献,虽然有几十条关于“冲喜”的记载,却多存于明清时期对为夫守节女子的旌表文字中。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材料,对冲喜对女性今后生活所造成后果与影响略知一二,但因以旌表节妇为目的,整个叙述着重展现节妇的自我牺牲精神,至于婚姻中所涉人物的态度、心理,以及整个议婚和娶亲过程皆无详细描述。再查中国古代小说,不乏“冲喜”事件,但大都略一提及,即便少数有相对详细描述者,亦无法与《红楼梦》钗玉婚姻之描写相抗衡。钗玉婚姻,从女性研究角度看,更确切说是宝钗的婚姻,它在《红楼梦》中不依附宝黛爱情而存在,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题,而以“冲喜”形式来完成这一主题叙述,更使人物性格前后一致、丰满完整,表现了作者对故事结局和人物命运掌控的非凡能力,绝属奇思妙想。
三、“冲喜”,冲而得喜?冲而得忧?
读《红楼梦》,大家都认为“黛死钗嫁”即为一种悲剧结局,但唯有穷其因,方能得其果。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黛怎么死?钗怎么嫁?”作者要写的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女孩子们的悲剧命运。如果单看字面,“黛死钗嫁”,似乎只有黛玉的命运是悲惨的,宝钗能够走入婚姻,也算成就了一个女人完整的一生。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宝钗的婚姻形式,就知道她的命运才是更悲惨、更值得为之痛哭的。可以说,从小说创作角度看,“冲喜”最终完成了宝钗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最终完成了“黛死钗嫁”的悲剧。但从女性视角看,冲喜本身就是以悲剧开始、以悲剧结局的婚姻形式。作者把这种婚姻形式给了宝钗,大有深意。“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现实生活,这都是一个无法逃遁的事实——对于女性而言,成年意味着结婚嫁人,意味着故事的结束。”在这一点上,中西方有共通之处。从《绿山墙的安妮》中安妮的嫁人,到《小妇人》中乔·马奇与老教授步入婚姻等等,“莎士比亚的喜剧多以结婚为结局,悲剧则以死亡为结局。莎翁赋予了婚姻和死亡同样的许是效果,……两者都有让故事结束的作用。”巧合的是,《红楼梦》所谓的“黛死钗嫁”主题,也正是体现了作者把婚姻和死亡放在同等地位来看待的叙事特点。对于中国古代的女性来说,结婚就意味着一种死亡,一种结束。为了能更好地理解宝钗婚姻的性质,我们先来看一下历史上参与“冲喜”的女性都有着怎样的生活。
在“冲喜”的问题上,人们所关注之事,古今不同。古时男女双方亲属态度亦有不同。古代婚姻中的男方所关注者莫过于男子或男子父母能否因得“冲喜”而康复;女方亲属所关注者,则是如何能尽量躲过这一不幸。而我们今人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更多关注的还是用来“冲喜”的女子今后的生存和命运。
1、“冲喜”并不违法
婚姻乃吉祥之事,将婚姻作为“冲喜”的对象有两个,一是为男方父母,《国史唯疑》卷九:“……民间压灾冲喜之说,早婚弱冠不以为嫌。往往借子孙之吉祥,禳父母之凶咎……”二是为男子本人冲喜。《二知轩文存》“吏部侍郎胡公家传”:“张太夫人病笃,从里俗,为长男娶妇,云以‘冲喜’。”也可见,“冲喜”之俗连贵族官僚之家亦不能免。《古今谈概》杂志部卷三十六“嫁娶奇合”中讲述了一个故事,“嘉靖间,崑山民为男聘妇,而男得痼疾,民信俗有冲喜之说,遣媒议娶。女家度婿且死,不从。强之,乃饰其少子为女归焉。”让女子的弟弟装扮成新娘去冲喜,男方家因新郎病中,不许其与新娘同寝,让小姑与新娘同寝,结果成就了女方弟弟与男方妹妹的好事。后小姑怀孕,男家告到官府,却是“连年不解”。后“有叶御史者判牒云:‘嫁女得媳,娶妇得婿。颠之倒之,左右一义。遂听为夫妇。’”看官府的态度可知,冲喜并不触犯法律,且因此而引发的争端如若不涉及图财害命类刑事案件,亦可听之任之,同样的案件还记载于《坚瓠集》“姑嫂成婚”中。但也有不同情况,这种男扮女装顶替冲喜之事在传奇中亦有表现,清初张大复《快活三》第八出:“……新官人不过有病冲喜,料勿同床个。我就假扮子妹子应过子……”后来公爹企图调戏儿媳,才发现系男子假扮,加之新郎病势沉重,遂告至官府。官员心想:“我想有病冲喜,世情有之……”但他最后判假扮者“打二十”,因其“男作女”,判女方父亲“打二十”,因其“不正闺门”,判男方父亲“打二十”,因其“人面狐淫”。可见,冲喜期间,如若出现伤风败俗之事,也只是稍加惩戒。“冲喜”本身并不违法。
2、“冲喜”女性要面临的五大问题
面对将死之夫,女方的家人自然都是不情愿的。但在文献中,这些女性最终都还是能够令男方家长遂愿。但用来“冲喜”的女性,有五大问题要面对,这些问题并不是肩负着“冲喜”使命的女性结婚以后才会知道的事。前朝往事、亲友教训,以及自己周围生活中看到的事实都能使这些女性很早就明白“冲喜”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五大问题分别是:(1)与丈夫基本素未谋面,明知丈夫将死(2)面临一进门便要夫死守节的选择(3)面临没有子嗣,得不到财产继承权、无法生存的问题(4)面临婆家是否准许其在婆家守节的问题(因为普通人家的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的,很多婆家不希望儿媳妇在家守节)(5)面临寡妇的艰难生活。针对宝钗的情况,我们主要了解一下第五个问题。
《司业文集》卷四“金壇蔡氏女传”:“妇不幸早寡,非见凌犯,无死法狥夫者,特以情死非中道,乃有求死而不得死,不死而又迫之不得不死者,金壇蔡氏女是也。女许嫁于氏,行有期,夫病革。于氏信世俗冲喜之说,请先期。母难之。女曰:‘儿身已许之矣,愿往。’往则居别室。数日,夫死。视含殓,脱一钏带夫臂,抽一如意簪夫首,而藏其半。求死,百方俱救免。舅姑苦新妇之甘死,无已也,立嗣子以慰之。女之诸父往告以大义。女曰:‘昔夕,梦亡父语我:汝盍两全。意节与孝之谓欤’,自此,不复求死。一以事舅姑抚嗣子为己任。然阅七年而卒。以死死之故冤抑沉痛号无告其至亲熟悉。厥隐者为余言:于氏饶于财而丧子,近属生心雅,不喜妇守节立后,以故怨丛于妇。而舅姑年未艾,尚冀自能生子,实无意于嗣。孙,聊以饵其妇,使勿死耳。女逆知其旨,数乘闲为姑道:古贤妇逮下多男之美。姑始听夫买妾,已又祷祀祈子女虔助之,祈姑心喜,曰,新妇爱我家务一以委之,外内怨者日益甚曰,是将专有于氏之产。妾既生男,幼子不敌长孙。谗口百端,舅姑不能无动。蔡女无以自明,不得已,举来时奁具尽纳诸姑谗者,又曰,彼将有他志,示不持一物去也。女闻之大恚,顿足曰,人头畜鸣敢加于我,我不可以须臾活。潜取平日所阅书及手迹焚之。夜,沐浴,更新衣,加常服其上。出一钏一如意簪带之缠结,牢甚。厥明,待姑早饭,如平时食讫入房,雉经床后,死年二十五。适于氏凡七年未尝归宁。母遣婢邀之,谢曰,儿以寡妇事翁姑,日甚一日,犹恐不终。敢无故归家,滋外人口舌乎?其秉礼如此。是女也,不得于七年前以殉夫死,乃于七年后于谗口死。身死而致死之故,上关舅姑,旁阆族党,吞声饮恨,难于诵言。此死之犹痛,而宜为表白者也。既嫁,应称妇,然犹女也! 故署为蔡氏女云。”这则故事讲述了一位替夫冲喜的女子的悲惨遭际。尤其最末一句寄托了作者无限悲悯与同情,可见作者记录此事的缘由正是因为他认为为将死之人冲喜,使其面临“既嫁,应称妇,然犹女也!”的命运,面临“乃有求死而不得死,不死而又迫之不得不死者”的无奈。
《钝斋诗选》“节女行”:“吴兴有节女,陆汇赵氏儿。少字周宗制,嫁当夫死时。夫病急婚礼,冲喜习俗卑。……公姥贪且愚。百计摇其持,甚且捶楚下,女志终不隳。缝纫累锱铢,葬夫颇威仪。穿穴虚其右,将以死追随。公姥亦继殒,哭声邻为悲。来时年十八,膏沐即不施。终身茹蔬食,头裹疏布缁。女红乃受值,外此丝粒辞。乙酉遘国难,村媪挽同驰。女泣且谢曰,未亡人安之。绝粒未即殊,白刃入茅茨。兵欲挟之往,嫚骂无衰词。身死交刃下,数日如生姿。嗟乎节女节,岂独妻道维。”以上两则文献中的记载,皆是丈夫死后,冲喜女性守节的悲惨生活。
四、“冲喜”:女性的个人牺牲?抑或政治行为?
我们现在谈的是一种婚姻形式,但实质上,这种婚姻却也涉及两性的政治理想。因为绝大部分“冲喜”都是以丈夫死亡,妻子守节而告终。要求女性守节,虽然是有违人道和人性的,但是先抛开这一层面不提,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如此没有人道的事,很多女性还会趋之若鹜。
1、男性的态度:以女性的“贞”自喻和自我激励
封建王权对男性的要求是“忠”,对女性的要求是“贞”,这是有其政治目的的。男性读书考科举,为的就是有政治话语权。东汉末年,宦官、外戚干政,李固、杜乔等宿学名儒明知“善政少而乱俗多”,仍要与阉党之流对抗,不避山林,誓忠于大一统政权。李固、杜乔死后,郭亮、董班等又继而临尸痛哭,亦不顾个人安危而尽君臣之义。同样的,女性的本分就是节操。男性一方面给女性制定了行为规范,另一方面也将能够践行这些行为规范的女性当作自身的榜样,进行自喻和自我激励。“在精英家庭中,政治斗争既涉及男子,也涉及女子。当一个直臣英勇赴难,他的母亲、妻子和其他女性亲属,被期待以同样的勇气和力量来行动。儒家士人促成了家庭中儒家妇女的产生,而儒家妇女又感召了儒家士人。”明末遗民李世雄在《黄氏官节妇七十岁寿序》中说:“……试贞病且笃,俗以毕姻为‘冲喜’,……合卺三十日而试贞竟夭。黄悲痛屡绝。既毕丧,阿奶微讽曰:‘儿名为官氏妇,实黄氏室子耳。盍归黄乎?’黄厉声曰:‘必出官门,便归地下。’家人竦然,若含阙在口,莫敢出声者。自此,悯默掩抑,趾无翔,目无游,容无矧者,十年如一日。翁姑哀其诚悫,为试贞立嗣以事之,今年七十有一矣。严冷如寒崖枯木也。……难矣哉! 岂非屹然大丈夫哉! …妇道臣道一也。……”《清史列传》载:“(李世雄)住泉上四十余年,足迹不入州府。居恒常戚戚。其母谓之曰:‘汝官耶?’对曰:‘然。儿弱冠食忾,岁靡朝廷十余金而无所用,能无愧乎?’因号愧庵。……”宋明士人所恪守的人伦道德规范主要是通过忠臣、孝子、节妇这三者体现出来的。李世雄作为无官之人且能亡国之后僧隐山林,正如同冲喜女性和丈夫没有真正的夫妻生活却要为其守节一样。他将忠臣与节妇相比,对那些亡国之臣嗤之以鼻,大加鞭挞。甚至认为,阿奶因黄氏与丈夫未成夫妻之礼而加以讥讽,是灭女人从一而终之真性的错误言行。他又举春秋卫女的例子说:“春秋卫女嫁太子,中道,太子卒,女特往当丧。丧毕,不复归,终之以殉。高子问孟子曰:‘婚嫁者,非人所自亲也。卫女何以得编于诗也?’孟子曰:‘有卫女之志则可,无卫女之志,则怠也。’”作为女子,无论是否有名无实,皆应从一而终。如李世雄所说:“圣人表其诗,以风万世。”是世风世德之规箴,士大夫亦以此自拟,甚至成为自我激励的工具。女人的贞洁和政治联系起来以后,已非简单的情感守候或者个人行为,“贞女一直是儒家道德话语的重要内容。……在贞女形象中,他们找到了自身情感的表达;通过描述和赞美贞女,他们重新确认自己的道德信念和政治选择。贞女的象征意义从未像这一时期(明清)那样深切地为儒家精英所利用,贞女行为也从未得到如此热情的膜拜礼赞。儒家精英大力宣扬和美华贞女,为贞女们在这个政治巨变的时代的辉煌展示创造了关键条件。”所以,明清时期,女性守节,尤其是“冲喜”的女性守节的最大推动力来自于男性。
2、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女性的参政心理
女人为夫守节与士人为朝廷守节尽忠同理。和男性一样,女性守节最重要的动力还是政治,女性以这种形式参政,表现自我价值。“她们的行为显然围绕这一套核心价值而开展,而这些价值定义了光荣与耻辱、高贵与卑贱。她们通过自己的行为,又使这套价值观得到了再生产和传播。……儒家士人促成了家庭中儒家妇女的产生,而儒家妇女又感召了儒家士人。在这样的境况下,‘贞’不仅仅是作为妻子的美德,也可以是女性的一种政治美德。”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历来有用立牌坊、赐匾额等方式来表彰贞洁烈女。受到政府旌表对于自尊心强、好胜心强的女性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诱惑。和当寡妇受到的歧视相比,还不如当节妇,既能免受侮辱,又能光宗耀祖,何乐不为?再说,女性从来不仅没有社会地位,在家族中也是一样,女性甚至都不允许进入祠堂。但是当了节妇、贞女就不同了。“雍正元年(1723)清朝曾规定各地要修建节孝祠,在祠门外建大的牌坊一座,上面刻上贞孝妇女的名字,死亡的节妇要在祠中设牌位。每年春秋时节,地方官来节孝祠祭祀节妇。……当时能够获得旌表被视为家族的荣誉,牌坊或在住所或在墓地建立。被旌表者一般可得到受表扬的匾额,上面题字有‘清标彤管’‘巾帼完人’等等。”
“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士。”(《黄石公三略》)“冲喜”女性为了守节之名,所做之事,令现代人匪夷所思。(雍正)《浙江通志》载:“(明·镇海县)王贞女……舅姑有病,迎妇于门,谓之‘冲喜’。吴母适病,欲迎妇,约晨往夕归。女适病疽,以次女代往。吴竟留婚。父母曰:当为汝再择佳婿。女坚,矢不复嫁,遂以处子终其身。”(道光)《肇庆府志》载:“源贮晃妻温氏。初,贮晃病,俗有‘冲喜’之说,迎妇归,实未成夫妇礼也。甫五日,晃病革,谓妇曰:我死,汝早适人,毋自苦。妇曰:妾归时,已甘作源氏鬼矣。贮晃曰:若是,吾目且不瞑。妇退,取薙发刀自刎,死。贮晃闻之,亦一恸而绝。”《光绪重修天津府志》:“王绍维妹玉女,年十九字尚立身子蟒,归有日矣。而蟒猝病濒死。家狃俗‘冲喜’谬说。诹吉迎女。及期,女甫入门,而蟒死矣。女兄弟遂诫诸从者逼女返。女父母皆喜,女羞涩不敢言。遽毁妆,素衣以表其志。寻有来议婚者,母告女,女拒以死。居无何,蟒母病革,讣音达女家,女请母为姑奔丧。母不答,女愤甚,不食。母惧,谋于邻。邻人义之,劝令奔赴。女驰至,大恸而绝。救之复苏,顾母曰:‘儿不返矣。’屏处一室,足不出户,一老婢朝夕侍侧。”《见闻随笔》“褚贞女”载:“……因沿俗例,娶以冲喜,乃成婚。……嗣讣至梦之日,即吴逝之日。贞女遂茹苦抚孤,清操自励,……患病时,邻里见旌旗幡盖围绕宅中。不数日,一笑而逝。合葬于武林之原,请旌建坊,以表扬之。”《三借芦赘谭》卷二十“过贞女”:“……令女先婚期过门,俗名‘冲喜’,可以起病,亦不经语也。采舆僱未发,忽有急足来报,仲寅死。女闻讣,气绝。母惊呼且泣,良人渐甦,泪盈盈如贯珠焉。泣请母曰:‘儿命薄,不幸失所,天愿全儿志。盖恐母怜女寡,或别有他意。’是晚,果有人以私议进其母者。女闻之,乘间自缢,以救得免。知志不可夺,因共议送女宏农,抱木主成亲。女婉转哀啼,旁观者皆掩面泣。丧事告终,送木主入祠。归经江溪,女跃入水。众晔救起,而女终不乐。比返戚族,咸集以祭,母抚弟责女,女本欲绝食戕生,至是始进饮食。然气噎声嘶,食下辄吐。人皆谓其气隔矣。”
男性不允许女性参政,甚至不能参与宗族中的事物,但却大力支持女性守节。作为男性为女性划定的少数几种值得官方奖掖的行为之一,守节就成了女性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思想,是女性实现人生道德、政治理想的途径和方式。《红楼梦》作者要为宝钗建构完整的人格特征和思想内涵,“冲喜”这种在诸多女性身上都产生过严重影响的婚姻形式,对宝钗命运的操控当然也不会有例外。
五、宝钗“冲喜”:奇思妙想的命运与结局
“悲金悼玉”,前半部“悼玉”,后半部“悲金”,“悼玉”悼的是二玉的悲剧,“悲金”悲的是二宝的婚姻。这个主题最发人深省、触目惊心的就是,对于女性来说,嫁人和死亡一样,是一件值得哀悼的事。《红楼梦》中的各种出嫁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不幸,尤其是以“冲喜”的方式嫁人,就是不幸中之大不幸。恰恰宝钗就是这种包含了儒家道德、政治、文化、宗族等诸多因素的礼俗的牺牲品。
翻开各种地方志,我们能看到的最多的就是:冠、婚、丧、祭。这是清代礼俗中最重要的内容。但是无论多少地方志和文献,也没有一部作品能像《红楼梦》这样,把整个“冲喜”事件写得如此真实、深入和淋漓尽致。从小说中,我们看到的不再只是地方志表彰贞女时的那几个没有名字的姓氏,和她们因何而被嘉奖的短短几行字迹。小说从参与策划的人物言行到当事人的情感体验等,将“冲喜”这一婚姻形式在当时的家庭生活中给人们带来的变化写得如此清晰完满。这是一种对历史、风俗和情感的再现,加深了人们对“冲喜”这一礼俗的了解和认知。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不能把宝钗“冲喜”婚礼的全过程一一介绍一遍,但小说中很详细地讲述了包括提亲之前贾府各路人等的态度、议婚、提亲的经过和婚礼在内的一些具体内容,都是在任何关于冲喜的文献记载中无法找到的。我们这里要特别关注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1、宝钗给黛玉的信:宝钗之“永伤”
宝钗自己的婚事,本人的态度就更为重要。第八十五回,知道薛蟠打死人的消息后,薛家乱成一团,贾府遣人探问,作者说:“宝钗虽心知自己是贾府的人了,一则尚未提明,二则事急之时……”从宝钗的心理活动和贾府态度可知,钗玉婚姻此时已成定局,在两府里也不是什么秘密。
第八十七回,宝钗忽然寄给黛玉一封书信,信中写道:
妹生辰不偶,家运多艰,姊妹伶仃,萱亲衰迈。兼之猇声狺语,旦暮无休。更遭惨祸飞灾,不啻惊风密雨。夜深辗侧,愁绪何堪。属在同心,能不为之愍恻乎?回忆海棠结社,序属清秋,对菊持螯,同盟欢洽。犹记‘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开花为底迟’之句,未尝不叹冷节遗芳,如吾两人也!感怀触绪,聊赋四章,匪曰无故呻吟,亦长歌当哭之意耳。悲时序之递嬗兮,又属清秋。感遭家之不造兮,独处离愁。北堂有萱兮,何以忘优?无以解忧兮,我心咻咻。云凭凭兮秋风酸,步中庭兮霜叶干。何去何从兮,失我故欢。静言思之兮恻肺肝。惟鲔有潭兮,惟鹤有梁。鳞甲潜伏兮,羽毛何长!搔首问兮茫茫,高天厚地兮,谁知余之永伤。银河耿耿兮寒气侵,月色横斜兮玉漏沉。忧心炳炳兮我哀吟,吟复吟兮寄我知音。”黛玉看了,不胜伤感。又想:“宝姐姐不寄与别人,单寄与我,也是‘惺惺惜惺惺’的意思。
有人对宝钗的这封信中的诚意表示怀疑,认为她明知黛玉身体不好,故意写这种伤感之文令黛玉悲伤,欲损伤黛玉的健康云云。还有学者对宝钗这封书信不以为然,认为“薛蟠行凶打死张三,受官场庇护的情节,是第四回打死冯渊的模仿。所不同的是曹雪芹的同情显然在受害者一边,而续书者则让宝钗在信中大肆歪曲事实,混淆视听。明明是张三家被弄得家破人亡……宝钗在信中却偏说自己‘更遭惨祸飞灾’。……宝钗就危言耸听地说是‘不啻惊风密雨’,还‘长歌当哭’,‘寄我知音’,完全颠倒了黑白! 续作者居然以同情的笔调,把这些当作宝钗抒情咏怀的内容。还让黛玉‘同心’相感,与之唱和,其立场爱憎,不问可知。”这种解释有失偏颇。
我们不能抛弃人性来考虑问题。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她再成熟稳重、识大局,也无法跨越年龄和经验带来的缺憾。她生长在封建家族,在生活一团糟,出现变故的时候,还能不为自己的亲哥哥担心(虽然哥哥行凶),而只去为对方考虑?这就是人性,是立场问题,不是什么恶毒的、明知故犯的行为。如果非要强调所谓“续书者”,非要强调他所谓的‘颠倒黑白’,那我们也可以说,恰恰是这一立场,更加证明了后四十回作者的阶级属性。而且笔者认为,给出这种解释,说明研究者并未将宝钗当时所处环境进行全盘考察。因为除了哥哥出事外,对于一个女孩子,更不能释怀的应该是婚姻大事。在小说中,宝钗不是常常喜欢把自己的真实情感泄露出来的人。恰在她马上嫁为人妇之时,致信黛玉,且之后不久便是她二人生离死别之时,读之令人感到作者在预设一种氛围,又不能不令人对宝钗的婚姻幸福产生疑问。
其实黛玉看后的感受即作者的意图,“宝姐姐不寄与别人,单寄与我,也是‘惺惺惜惺惺’的意思。……叹道:‘境遇不同,伤心则一。不免也赋四章,翻入琴谱,可弹可歌,明日写出来寄去,以当和作。’”便叫雪雁将外边桌上笔砚拿来,濡墨挥毫,赋成四叠。又将琴谱翻出,借他《猗兰》《思贤》两操,合成音韵,与自己做的配齐了,然后写出,以备送与宝钗。”很明显,黛玉是领会了宝钗的意思,也并没有认为她有冒犯自己之意,而且认为宝钗和自己虽境遇不同,但伤心的感觉却是一样的。聪明敏感若黛玉,宝钗如若信中有歹意,她怎么会完全看不出来?关键是,这时候不仅是宝钗家中出现变故,还是宝钗知道自己和宝玉的婚姻之后的行为。我们必须把面临结婚这件事作为更大的因素考虑进来。如果是一个心中充满待嫁喜悦的少女,此时即使家中有事,文字中也不该完全充满着悲伤和凄怆,没有一星半点的快乐可言。只有一种解释,即她并不喜欢这桩婚事,而且还觉得这是“失我故欢”“无以解忧”,不知“何去何从”,感到与孤苦无依的黛玉一样要“长歌当哭”了。到此,宝钗启问天地,“谁知余之永伤”?这不是普通的现代人所说的“婚前恐惧症”,这是实实在在地对于未来婚姻生活的不自信、恐惧、悲哀和无奈。很多人说宝钗是喜欢宝玉的,还巴不得当上宝二奶奶,我们只能说这种分析是完全忽略了人性中的变化因素。宝钗从小就听说自己的婚姻是要和“有玉的”人相关,换任何人可能都会感到好奇,会留心于此。及至见面相处之后,随着宝钗对宝玉的了解的加深,再加上他二人的性格迥异,思想不能契合之处甚多,宝钗这么冷静理智地人怎么就不能认为宝玉并不是自己最好的婚姻对象呢?怎么就不能不喜欢这个婚姻呢?“黛死钗嫁”的悲剧,到了宝钗的婚事开始启动时,也就缓缓拉开了它的大幕。宝钗的婚姻在提亲之前就笼罩上了一层浓密的乌云。宝钗心中也一开始就是凄惨悲伤的。小说第三回结尾写因薛蟠打死人命,薛姨妈和宝钗才因此进入贾府,初见宝玉。第八十五回,薛蟠又打死人命,这次又正恰逢宝钗要嫁入贾府之时。宝钗的婚姻竟脱不了人命官司,这是否作者有意而为,我们不得而知。但宝钗的婚姻开始之前,两府便蒙上一层愁云惨雾,也的确是客观事实。
2、“冲喜”的提出与“荒亲”的违礼违法行为
钗玉婚事的始作俑者是贾母,“冲喜”的说法当然也是贾母首先提起的。第九十六回贾政被放江西粮道,马上就要离家去外省赴任,临行前贾母和他商议宝玉的婚事说:“我今年八十一岁的人了,你又要做外任去。偏有你大哥在家,你又不能告亲老。你这一去了,我所疼的只有宝玉,偏偏的又病得糊涂,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我昨日叫赖升媳妇出去叫人给宝玉算算命,这先生算得好灵,说:‘要娶了金命的人帮扶他,必要冲冲喜才好,不然只怕保不住。’我知道你不信那些话,所以教你来商量。”这是“冲喜”的首次提出。但贾母自己也承认这是违礼违法的行为,贾政的内心更是极其不情愿的:
(贾政说)“他哥哥在监里,妹子怎么出嫁?况且贵妃的事虽不禁婚嫁,宝玉应照已出嫁的姐姐,有九个月的功服,此时也难娶亲。……贾母想了一想:“说的果然不错。若是等这几件事过去,他父亲又走了,倘或这病一天重似一天,怎么好?只可越些礼办了才好。”……若说服里娶亲,当真使不得;况且宝玉病着,也不可叫他成亲,不过是冲冲喜。……趁着挑个娶亲日子,一概鼓乐不用,……一概亲友不请,也不排筵席。”贾政听了,原不愿意,只是贾母做主,不敢违命,勉强陪笑……贾政答应出来,心中好不自在。
宝钗的“冲喜”几乎是所有“冲喜”的婚姻中最令人不能容忍和不耻的一种,即“荒亲”。何谓“荒亲”?就是在家中有长辈或者重要成员去世期间举行“冲喜”婚礼,这种行为被世人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荒谬的。《诗铎》卷二十三吴世涵“荒亲”极力批判所谓冲喜以至荒亲的陋俗:“古圣制典礼,凶嘉不相假。……期服而成婚,识者犹惊讶。嗟哉吾越俗,荒亲事可吒。厥亲遘危疾,厥子迎妇奼。名之曰冲喜,饰语一何诈。更有亲初没,秘丧事迎迓。堂上肉未寒,堂下舆已驾。哭者方在寝,贺者旋盈舍。岂意衰絰中,吉服晤姻娅。岂意泣血辰,花烛问良夜。厥风沿自宋,遗俗久未化。至今人士家,纷纷相蹈藉,惜才费有几,蔑礼罪难贳。……”
《红楼梦》作者先安排了元妃的薨逝,造成了必须有九个月功服的局面,同时又安排宝玉失玉得病,贾母又认为必须用婚姻冲喜的状况。我们不能不说,作者这种情节设置是精心设计的,充满戏剧性和矛盾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贾母要救宝玉,就一定得要违礼违法举行婚礼,贾政的不情愿就很说明问题,而这也正是我们早已对古代婚丧嫁娶的很多风俗礼仪了解甚少现代人所不容易注意到和完全理解的地方。不能理解这是一桩处于怎样的复杂窘境下的婚姻,也就无法明白“钗嫁”的真正悲剧性所在。
贾母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她知道在元妃功服期间行婚礼是“越礼”的,但是她打算和王夫人一起去求薛姨妈这就和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普通人家为给生病男性冲喜而去请求女方家长的行为完全一样。贾母的意思只是为了给宝玉“冲喜”,并不在意婚姻本身,所以她一再强调虽然婚礼违法但却是为就人命的理由:“说是要救宝玉的命,诸事将就……若说服里娶亲,当真使不得;况且宝玉病着,也不可叫他成亲,不过是冲冲喜。”因为是违礼违法的,所以婚礼连鼓乐都不能用,贾母只要宝玉能好,并不管别人。虽然也想到宝钗,但一大堆理由也搪塞过去了,并不在乎宝钗的感受。这还不算完,正在宝玉亲姐姐元妃丧事中,宝钗和宝玉的亲舅舅王子腾又突然病故。冲喜,偏又要在两家都有近亲之丧期间举行婚礼,这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遭人唾骂之事!
像宝钗这样的人品才干、相貌性情、家世门第,本是准备入宫的人选,结果却要给一个病人“冲喜”,还是在违背礼制风俗的情形下,没有风光仪式,委委屈屈地过门。肯定也躲不开诸多亲友、族人对于丧礼中娶亲的“荒亲”行为的诟病和指责。对比前面提到过的“冲喜”中的女性,我们就可以知道这对于任何一个女性来说都是极大的不幸和压力,而对于心性高强、自重自爱的宝钗来说,无疑更是人生之大不幸! 何况宝钗未知冲喜之前就给黛玉写过信,那时已是万般悲哀。可想而知,当她知道要当“冲喜”新娘时,又会是产生怎样哀痛欲绝的心理呢?
更悲哀的事还在继续发生。宝玉虽然疯疯傻傻,但是袭人认为宝玉心里只有黛玉,并不想和宝钗结婚。她担心贾母想要冲喜,让宝玉的病情好转,但很可能适得其反。站在宝钗的立场上看,这就是另一件最可悲的事了,即她嫁的男人并不想娶她,而是早已心有所属。到此,我们看宝钗真是要什么没什么,整个一桩婚姻都是虚假的、冰冷无情的、支离破碎的,生存在疾病和死亡的背景下。
3、阴谋和欺骗中的婚姻
古代用婚姻“冲喜”,大都是不被女方家庭接受的。一般会经历很多阻碍,我们上文也都谈到过,比如女方父母的阻拦,甚至还有人家把女子的弟弟扮成新娘嫁到夫家冒充。很多不情不愿的行为就有可能随之发生。那么“冲喜”的婚姻里就必然充斥着阴谋和算计、诡谲和陷阱。《红楼梦》中钗玉的“冲喜”婚姻也不能例外。
“冲喜”的方针即定,接下来就是袭人捅破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她担心被宝玉知道娶的不是黛玉而引起麻烦,就去找了王夫人,说出了宝黛二人的心事。由此引发了所谓的“掉包计”。贾母的一句“只忒苦了宝丫头了”,我们就能明白掉包计伤害的不仅是宝黛二人,宝钗这个用来“冲喜”的“工具”所受伤害也是相当大的。前面我们提到的冲喜的女性和丈夫之间的关系时,只要丈夫还是清醒状态,二人的感情还都是不错的,尤其作为丈夫的男性,因是为自己生病而娶妻,大多数都会对女性有一些歉疚感和感激,因此,男性基本都是没有不满和不情愿的情绪的。如果一个女子,一辈子的婚姻大事被用作治病的方法,结婚还得要装神弄鬼,让自己做丈夫心仪女子的替身,才能完成婚礼,不啻为奇耻大辱!
宝玉一听要给他娶林黛玉,果然高兴非常,所说话“一丝不乱”。宝钗之悲至此愈显浓重。接下来,就是贾薛两家长辈在一起议亲,小说中不断提及“薛姨妈恐宝钗委屈”之类的话,提请读者的注意:
凤姐便道:“……二则也给宝兄弟冲冲喜,借大妹妹的金锁压压邪气,只怕就好了。”薛姨妈心里也愿意,只虑着宝钗委屈,说道:“也使得,只是大家还要从长计较计较才好。”王夫人便按着凤姐的话和薛姨妈说,只说:“姨太太这会子家里没人,不如把妆奁一概蠲免,明日就打发蝌儿告诉蟠儿,一面这里过门,一面给他变法儿撕掳官事。”并不提宝玉的心事。又说:“姨太太既作了亲,娶过来,早好一天,大家早放一天心。”正说着,只见贾母差鸳鸯过来候信。薛姨妈虽恐宝钗委屈,然也没法儿,又见这般光景,只得满口应承。鸳鸯回去回了贾母,贾母也甚喜欢,又叫鸳鸯过来求薛姨妈和宝钗说明原故,不叫他受委屈。
至此,又和宝玉病前说亲时不同,薛姨妈也开始对这桩婚事有想法,碍于面子,已经答应了的事不好再反悔。但心理活动已经很明显,觉得自己的女儿受了委屈。而贾家长辈们的态度却更为含糊,王夫人和贾母都不仅不提宝玉真实的内心想法,对宝玉的病情也遮遮掩掩,只瞒着薛姨妈一个人。更卑鄙无耻的是,贾府利用帮助撕掳薛蟠杀人案而利诱薛姨妈上钩,让她为了救儿子,进一步心甘情愿牺牲宝钗的婚姻。王夫人对薛姨妈说的那句话便揭露了一切:两家母亲,都要救自己的儿子,宝钗便是她们达成心愿的阶梯。这里面有谁曾经把宝钗的利益放在心上过?有谁为她考虑过呢?
“薛姨妈回家,将这边的话细细的告诉了宝钗,还说:‘我已经应承了。’宝钗始则低头不语,后来便自垂泪。薛姨妈用好言劝慰,解释了好些话。宝钗自回房内,宝琴随去解闷。”贾府逼薛姨妈,薛姨妈又逼宝钗。此时此刻,她一个满心要当淑女、尊妇道、守女教的女性,又能说些什么呢?更令人可悲的是,她的亲哥哥知道了这件事后,说出来的话一样令人寒心:“……叫咱们预备赎罪的银子。妹妹的事,说:‘妈妈做主很好的。赶着办又省了好些银子。叫妈妈不用等我。该怎么着就怎么办罢。’”薛蟠不仅不管妹子,还一味地只管为自己的事向家里要钱。薛姨妈满心里想的也不是宝钗:“薛姨妈听了,一则薛蟠可以回家,二则完了宝钗的事,心里安顿了好些。便是看着宝钗心里好象不愿意似的,‘虽是这样,他是女儿家,素来也孝顺守礼的人,知我应了,他也没得说的。’”完全不是做母亲疼惜女儿该有的心情,一味老奸巨猾,自私自利。
4、宝钗的婚礼
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钗玉大婚当天,即是黛玉死亡之日,宝钗的婚姻注定了与死亡脱不了干系。欺骗仍在进行中,黛玉的丫鬟雪雁替代贾府长辈们所希望的紫鹃,到宝玉和宝钗的婚礼现场,作为骗局中的一枚棋子,安插在宝钗的身边,假装所娶者为黛玉。宝钗作为黛玉的替身,参加了自己不幸的婚礼。作者又借用雪雁的眼睛对宝玉认为自己娶了黛玉时的外貌进行了一番细致地描绘:“宝玉虽因失玉昏愦,但只听见娶了黛玉为妻,真乃是从古至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畅心满意的事了,那身子顿觉健旺起来,只不过不似从前那般灵透,所以凤姐的妙计,百发百中。巴不得就见黛玉,盼到今日完姻,真乐的手舞足蹈,虽有几句傻话,却与病时光景大相悬绝了。”这种喜剧场面更增加了这场婚礼的悲剧色彩,正是作者一贯的写作手法,“冷热悲喜”交相隐喻,让读者欲哭无泪。接下来的婚礼经过就更令人啼笑皆非,全部都是欺骗和诡计,颠倒是非,混乱伦常,违制冲喜的侮辱,毫无情意的婚姻对于宝钗来说也只能用无言来回应。这场可笑的婚礼,以宝玉病势沉重结尾,正像袭人所担忧的那样,不是冲喜,倒是催命符了,作者此时才补充了一句:
幸亏宝钗是新媳妇,宝玉是个疯傻的,由人掇弄过去了,宝钗也明知其事,心里只怨母亲办得糊涂,事已至此,不肯多言。独有薛姨妈看见宝玉这般光景,心里懊悔,只得草草完事。
薛姨妈的懊悔说明了一切。
5、守寡的结局
虽然宝玉在为他冲喜而办的婚礼之后没有像大多数文献记载中的冲喜故事中的男主人公那样很快死去,但我们都知道,他最终还是抛弃了宝钗和她腹中的孩子,和一僧一道飘然离去,不知所踪。第一百二十回这样归结宝钗的行为和思想状态:
王夫人哭着和薛姨妈道:“我叹的是媳妇的命苦,才成了一二年的亲,怎么他就硬着肠子,都撂下了走了呢!”……宝钗哭得人事不知。所有爷们都在外头。王夫人便说道:“我为他担了一辈子的惊,刚刚儿的娶了亲,中了举人,又知道媳妇作了胎,我才喜欢些,不想弄到这样结局!早知这样,就不该娶亲,害了人家的姑娘。”薛姨妈道:“……幸喜有了胎,将来生个外孙子,必定是有成立的,后来就有了结果了。你看大奶奶,如今兰哥儿中了举人,明年成了进士,可不是就做了官了么?他头里的苦也算吃尽的了,如今的甜来,也是他为人的好处。我们姑娘的心肠儿姐姐是知道的,并不是刻薄轻佻的人,姐姐倒不必耽忧。”王夫人被薛姨妈一番言语说得极有理,心想:“宝钗小时候便是廉静寡欲极爱素淡的,他所以才有这个事。想人生在世,真有个定数的。看着宝钗虽是痛哭,他那端庄样儿一点不走,却倒来劝我,这是真真难得。不想宝玉这样一个人,红尘中福分竟没有一点儿!”想了一回,也觉解了好些。……那日薛姨妈并未回家,因恐宝钗痛哭,住在宝钗房中解劝。那宝钗却是极明理,思前想后:“宝玉原是一种奇异的人,夙世前因,自有一定,原无可怨天尤人。”更将大道理的话告诉他母亲了。薛姨妈心里反倒安慰,便到王夫人那里,先把宝钗的话说了。王夫人点头叹道:“若说我无德,不该有这样好媳妇了。”说着更又伤心起来。
在万般不情愿下出嫁和去给人家冲喜,又在被丈夫抛弃后依然安分守节,抚养遗腹子,这就是宝钗这种性格的淑女必然会有的行为和思想认识。宝钗的性格和思想,可以说,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中并无二致,也没有很明显地相互矛盾之处。钗玉从一见面,便伴随着一场人命官司,等到议婚之时又发生一场人命官司,紧接着元妃之死、王子腾之死、黛玉之死,钗玉在一连串的死亡中成婚,在孝服未满期间“荒亲”冲喜,冒天下之大不韪,违礼违法,一场对于女性来说非常重要的婚礼也被变成一出闹剧,宝钗充当了自己丈夫心爱之人的替身,屈辱成婚,最后成为寡妇。一路走下来,宝钗始终得在命运的摆布中低头,演好众人心中的贤德温良的淑女。一生只有一次真正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情感,就是在给黛玉的那封信里,却也被黛玉带进了坟墓。没有人真的心疼她,很多人赞美她,她和那些在文献中被旌表的节妇一样,乖乖地用自己的婚姻去给别人治病,然后再忍气吞声地守寡活完自己的余生。所以我们说“黛死钗嫁”这个悲剧主题,真正的意义就在于,“黛怎么死,钗怎么嫁”。把这个内涵弄明白了,才能真正知道《红楼梦》作者要说什么。
注释
① 陈顾远《中国婚姻史》(《民国从书》选印),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12—113页。
② [美]丽贝卡·特雷斯特著,贺梦菲、薛轲译《我的孤单,我的自我:单身女性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5页。
③ 黄景昉《国史唯疑》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④ 方濬颐《二知轩文存》卷二十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⑤ 冯梦龙著、栾保群点校《古今谭概》“杂志部”卷三十六,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80页。
⑥ 张大复《快活三》,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版。
⑦ 陈祖范《司业文集》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74页。
⑧ 方孝标著,唐根生、李永生点校《钝斋诗选》卷二“五言古体二”第十八首“节女行”,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32页。
⑨⑫⑬ [美]卢苇菁《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第46—47、44、46页。
⑩ 李世雄《黄氏官节妇七十岁寿序》,《寒支初集》,清初檀河精舍刻本卷五,第74页。
⑪ 《清史列传》卷七十,文苑传一,中华书局 1987年版,第5695页。
⑭ 常建华《婚姻内外的古代女性》,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1页。
⑮ 《浙江通志》卷二百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4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26页。
⑯ 《肇庆府志》卷二十“人物五(烈女三)”中“右开平县”,《续修四库全书》第71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24页。
⑰ 《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四十八传十列女三,《续修四库全书》第69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75页。
⑱ 齐学裘《见闻随笔》卷二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18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页。
⑲ 邹弢《三借庐赘谭》卷十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26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758页。
⑳ 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98页。
㉑ 张应昌编《诗铎》卷二十三“婚嫁·荒亲”,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