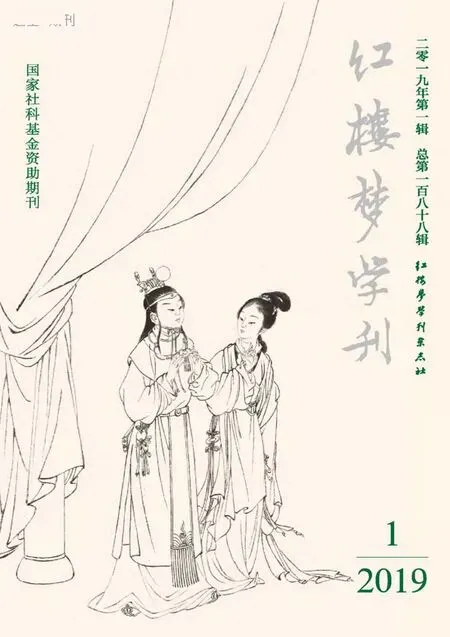论当代影视剧创作中的“《红楼梦》因子”
——以《琅琊榜》为例
2019-11-12
内容提要:本文以《琅琊榜》为例,分析当代影视剧创作中的“《红楼梦》因子”。通过考察《琅琊榜》对《红楼梦》的“化用”,人物命名原则的借鉴,以及对二者“女性意识”的互文性解读,指出《琅琊榜》一方面承袭了《红楼梦》,另一方面,它又表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和时代特点。
在当代热播的、反响强烈的影视剧里,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红楼梦》的影子。这些“影子”似有若无,或隐或现,有时我们能清晰地捕捉到它,有时却又只是似曾相识的神韵。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把这些“影子”称作影视剧里的“《红楼梦》因子”。这些“因子”于浅层次上说,可以直观地表现在人物的声口语言、性格特征和情节设置上;于深层次上说,这些“因子”还表现为作品的悲剧意蕴、叙事策略、结构安排等方面。这个现象已经引起学者的关注。有关于此,学者们讨论比较多的,如前些年的《大宅门》《金粉世家》与《红楼梦》之间的关系,近年来的《甄嬛传》与《红楼梦》的关系等。但是就笔者所见,学界尚未有学者把《琅琊榜》与《红楼梦》联系起来分析讨论。事实上,在《琅琊榜》中,“《红楼梦》因子”不仅存在,而且以一种脱胎换骨的方式完成了化用与借鉴,细细体会和分析,我们能够发现其中的脉络和纹理,顺着这些脉络和纹理,我们看到经典在当代影视剧中依然发挥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一、《琅琊榜》对《红楼梦》的“化用”
《琅琊榜》对《红楼梦》的化用是普遍存在的,但这种化用不僵化、不板滞,不比附。有自己的独特的艺术生命,充满动感和灵气,细细体会,能体味作者信手拈来背后深厚的红楼素养,兹举例如下:
(一)地名、府邸、姓氏的化用——金陵、宁国候府、林家
《琅琊榜》中,梅长苏回到金陵住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宁国侯府。宁国侯府的大公子萧景睿邀请他前来金陵休养身体,就住在宁国侯府的雪庐里。这里的“宁国候府”与《红楼梦》里的“宁国府”只有一字之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红楼梦》里的宁国府。且《红楼梦》虽然“无朝代年纪可考”,但主要故事的发生地、故事的展开都是以“金陵”作为背景的,“金陵”无疑是《红楼梦》里的一个高频词。《琅琊榜》作为一部架空历史的剧本,故事的发生地在金陵,故事里出现了宁国候府,已经让人觉得有《红楼梦》的影子了。而《琅琊榜》主人公梅长苏本名是“林殊”,故事里对“林家”的叙事与回忆,又让人隐隐想到《红楼梦》里的林家……上述各个方面,如果孤立地看,可能只是跟《红楼梦》的一个巧合,但结合起来看,《琅琊榜》里《红楼梦》的影子已经越来越清晰。
细细考察下去,笔者发现,《琅琊榜》里的林家和谢家的“联络有亲”与“利益冲突”,与《红楼梦》里宁荣两府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颇有一些对应,但小说毕竟是虚构的艺术,为避免穿凿,本文不对上述问题再进行具体深究。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琅琊榜》里对金陵、宁国候府、林家等地名、府邸、姓氏的设置,明显化用了《红楼梦》里的相关构思。
(二)人物、情节、语言的化用
《琅琊榜》里病弱的麒麟才子林殊身上,有着《红楼梦》里病弱的才女林黛玉的影子。二者都被冠以“林”姓,都身形羸弱,才思敏捷过人,不同流俗。前人评《红楼梦》,说林黛玉骨子里是不得志有风骨的文人,从这一点上看,林黛玉与林殊,除去作者的性别设置以外,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此外,《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母亲的名字叫“贾敏”,为了避母亲的讳,她每写到“敏”字就要添一笔或者减一笔;这一点在《琅琊榜》里,被化用为林殊避母亲的讳,在给《翔地记》作注时,遇到母亲的闺名,便减去最后一笔(第三十九章)。
《琅琊榜》里的言国舅,“两耳不闻红尘事,只想着求仙问道炼丹”(第二十二章),从未把管儿子言豫津放在心上。小说借言豫津的口抱怨:“除了前一阵子我爹突发奇想要把我塞进龙禁尉里当差以外,平时倒也没怎么操心我的前程。”这段描写,颇似《红楼梦》里两个情节的“合体”:一是贾敬只知道求仙炼丹,一心不管红尘事,不管贾珍这个儿子。二是贾珍在秦可卿死后为了葬礼上风光给贾蓉捐了一个“龙禁尉”的官。
语言的化用就更普遍了。《琅琊榜》第十七章写到一场大雪“扯絮撕棉似的下了三天”,与《红楼梦》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中借宝玉的眼睛看到的“一夜大雪,下将有一尺多厚,天上扔是搓棉扯絮一般”如出一辙。《琅琊榜》第二十一章,梅长苏赞霓凰郡主“豪阔宏量,霁月风光”,则是化用了《红楼梦》中史湘云与晴雯的判词。《琅琊榜》里蔺晨称梅长苏是“水晶玲珑心肝人”(最终章),跟《红楼梦》四十五回李纨称王熙凤是“水晶心肝玻璃人”一脉相承。此外,纪王爷口中“红袖招的解语花”、卓鼎风手中的“飞鸟投林”剑法……从中都看得到“《红楼梦》因子”。而《琅琊榜》电视剧静妃口中“真是奇了”,豫津赏灯时说的“是真名士始风流”……更让人听到《红楼梦》里人物对话的声口语言。更值得注意的是,《琅琊榜》电视剧主题歌中的“关山横槊,谁可补天”,跟《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无才可去补苍天”暗合,这样看来,梅长苏的身上不仅结合了林黛玉的病弱,还结合了有如贾宝玉身上“补天”一样的期许。
此外,在《琅琊榜》有关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等的描写中,也常常能感到《红楼梦》的影子,让人觉得似曾相识,却又在似与不似之间,构筑起自己独特的艺术生命。总之,《琅琊榜》对《红楼梦》的化用是自由而灵活的,并非简单的仿写和比附,而是在“吃透”了《红楼梦》的文字以后,在熟悉《红楼梦》相关描写的基础上,信手拈来,涉笔成趣。
二、人物命名原则的借鉴——既符合性格又暗合情节
《红楼梦》里的人名不只是一个代号,其意义超越了文字符号层面,与小说人物性格的塑造、故事情节的走向融为一体,在赋予人物一个指称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作家的艺术用心。《琅琊榜》在人物命名艺术上,充分借鉴了《红楼梦》的命名原则。
《红楼梦》里人物姓名与人物性格之间的关系,要么通过谐音双关,要么通过名字的字面意义反映出来。
谐音双关如贾雨村名化,化谐话,姓名合在一起则是“假话”,与甄士隐(真事隐)对照着看,能体会本书的大旨和作者的艺术用心。绛珠仙子中的“绛珠”谐音“降珠”,暗示了黛玉每日以泪洗面。甄士隐家的仆人霍启抱了英莲看灯而丢失英莲,正是甄家祸事的源头,这个仆人名叫“霍启”,谐音“祸起”。贾政门下的几个清客相公的名字分别叫“詹光”(沾光)、“卜固修”(不顾羞),“单聘仁”(善骗人),刻画出这些清客相公的真实嘴脸;贾芸的舅舅名叫“卜世仁”(不是人),暗喻了他的势利;甄英莲谐音“真应怜”,暗示了她“平生遭际实勘伤”;此外,裘世安谐“求世安”、吴新登谐“无星戥”、冯渊谐“逢冤”、娇杏谐“侥幸”、秦钟谐“情种”、秦可卿谐“情可轻”,等等。这些名字的谐音,均成为这些人物性格特征或情节命运的内在规范。
通过名字的字面意义揭示的,如黑山村的庄头乌进孝年终向贾府交租,呈上实物单子以及租银2500 两(第五十二回),他就是来向贾府“进孝”的,他的名字就是对他身份的概括。此外,“女中之凤”王熙凤、老实倔强的石呆子、滥用虎狼剂的胡庸医、都察院的钱大爷、吃酒混日的多混虫、薛蟠的帮闲胡斯来、宫里的太监夏守忠……都是通过名字的字面意义揭示人物的身份性格。
《琅琊榜》中,人物姓名与人物性格之间的关系,同样要么通过谐音双关,要么通过名字的字面意义反映出来。
谐音双关如秦般弱。秦般弱的名字中,“般弱”谐音“般若”,在佛经中,这两个字读作“bō rě”,意为“终极智慧”“辨识智慧”,即如实认知一切事物和万物本源的智慧。在《琅琊榜》中秦般弱是誉王萧景桓的谋士,从作者赋予人物的这个命名来看,这个谋士智计不同凡响。
本文在环境话语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从生态语言学、环境传播学、环境社会学、环境政治学、环境地理学、环境史学等多种学科视角回顾了环境话语的研究成果,重点阐述了环境话语分析的多种研究路径和基本观点。研究发现:基于环境话语跨学科研究的内在需求,环境话语研究具有超越传统学科框架的视野和开放性,需要研究者突破单一学科视角的固有认知与思维模式的局限。随着现代环境学科群的枝繁叶茂以及环境话语概念在不同学科的动态建构,环境话语将迎来更为广阔的研究前景。环境话语研究势必将语言学和环境科学的诸多分支学科聚合起来形成多学科交融、合作共赢的发展趋势,并最终构建出一个以研究系统化、多种学科结合为特色的环境话语研究框架。
《琅琊榜》惯于通过名字的字面意义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情节寓意。如出类拔萃的林殊(殊,殊胜也)、重情重义的蒙挚(挚,诚恳也)、拨乱反正的靖王(靖,使秩序安定也)……其他如沽名钓誉的誉王、息事宁人的宁王、平和娴静的静妃、轻功高绝的飞流、深谙处世之道的高湛……莫不是如此。此外,宫羽的名字来自“宫、商、角、徵、羽”,是我国五声音阶中五个不同音的名称,亦称作五音。作者把这“五音”中的头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结合起来用作名字,含有“精通五音”的意思。所以宫羽就是一个精通音律的姑娘,她是妙音坊的头牌姑娘。霓凰郡主姓穆,在她的身上,既体现了穆桂英挂帅的气魄,又体现了女中“凤凰”的过人才干胆识。越贵妃姓“越”,僭越的“越”。僭越,指超越本分,古时指地位低下的冒用在上的名义或器物等等,尤指用皇家专用的。所以《琅琊榜》中越贵妃专宠多年,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处处压着皇后,是为“僭越”,故姓“越”。言国舅(言阙)姓“言”,在《琅琊榜》中,言国舅能言善辩,曾经“舌战群臣”,以一己之力震慑住前来进犯的邻国使臣,故姓“言”。还有,靖王手下的战将“列战英”“戚猛”;梅长苏(赤焰军少将林殊)手下的“聂锋”“卫铮”等,他们的名字都凸显了他们本人作为武将的骁勇善战。
需要指出的是,《红楼梦》的命名是一门艺术,有关于此,学者多有论述。胡文彬先生在其《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中,对《红楼梦》人物的命名艺术作过系统分析和总结,指出《红楼梦》里的人物命名总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人物命名与姓的谐音关系;2、人物命名取自诗词名句;3、人物命名与人事有关;4、“范字”取名;5、随文而出,按文命名;6、《红楼梦》中取姓命名,乃至字号安排,曹雪芹还利用了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从中可见《红楼梦》的人物命名是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充分融入了作家的艺术创作。某种程度上,《红楼梦》的人物命名自成体系,博大精深。而《琅琊榜》作为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在借鉴《红楼梦》命名艺术的基础上,其人物命名则更注重通俗性、娱乐性,但这种通俗性和娱乐性中又不乏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内涵,表现为一种融合了武侠小说与历史演义的传奇色彩。如江左梅郎、璇玑公主、霓凰郡主、穆小王爷、十三先生、南楚的宇文暄、药王谷的素谷主、红袖招的秦般弱、妙音坊的宫羽、琅琊阁的蔺晨、天泉山庄的卓鼎风……这些名字颇具武侠韵味。其中,蔺姓、蒙姓、穆姓都是历史上有名的爱国功臣之姓,烘托了《琅琊榜》所要突出的家国情怀;而梅姓、林姓则让人感觉到一种飘渺玄远的士大夫遗风。
三、二者“女性意识”的互文性解读
“互文性”理论认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转化(法·克里斯蒂娃《符号学》)。其含义有两层:一是指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二是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用“互文性”来描述文本互涉的问题,显示了写作活动内部多元文化和多元话语相互交织的事实;同时展示了写作的深广性及其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内蕴和社会历史内涵。《琅琊榜》对《红楼梦》的化用与借鉴是普遍存在的,这是我们能够将这二者进行“互文性”解读的基础。从互文性角度探讨二者的关系会发现,二者体现出共同的“女性意识”;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一方面,《琅琊榜》承袭了《红楼梦》对女性力量的赞美,另一方面,它又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红楼梦》是一曲大规模的女性的颂歌。在《红楼梦》第一回,从《石头记》抄本开始,一直有一段非正式的文字,虽然抄写的款式不尽相同,文字也稍有出入,却始终保存在各种版本里。这段文字意义重大,它具有作者自叙的性质,作者是这样写的:
……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我虽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
正是因为作者要“使闺阁昭传”,所以《红楼梦》集中描写了这样一群天真、自然、本性的女性形象,她们的才华与美丽、她们的爱与恨、她们的苦与乐……她们张扬的个性与棱角、她们身上洋溢着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千红一窟,万艳同杯”——以“金陵十二钗”为代表,女性悲剧构成了《红楼梦》悲剧故事的基本内容。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不仅以女性本位的叙事构筑了男权时代女性的生存悲剧,而且还开掘了女性身上蕴含着的,创造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小说开篇就被作者鲜明地表现于女娲补天神话中。补天神话的象征意义,学者多有论及,但从神话学层面上关注,却鲜有学者注意。据《淮南子·天文训》记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这才导致了天崩地裂,女娲才炼石补天。也就是说,两个男人争斗引出了一场浩劫,而一个女人来收拾残局,挽救了世界。笔者认为,开篇补天神话的寓意正在于此,《红楼梦》中关于“颂红”“怡红”和对男性社会的极度失望,也根植于此。
《红楼梦》广泛地反映了身处末世中的女性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世界。如果说宝钗之“停机德”和黛玉之“咏絮才”更多地是体现为一种自我修持的话,秦可卿的深谋远虑、王熙凤的杀伐决断、贾探春的精明改革……则是力图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手段来阻止这个大家族走向衰落。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作者对女性力量的深层次开掘。其中,王熙凤的判词是“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探春的判词是“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判词都突出了她们身上的“才”。这种“才”,立足于女性,却又不输男子,超越了封建社会对女性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评判,体现出一种全新的女性理想,是那个时代所少有的,作者赋予女性的人文新素质。
《琅琊榜》沿袭了《红楼梦》对女性力量的赞美。这部剧表面上看起来,是以男性为主角,讲述男人复仇的故事。其中充斥着权利的制衡,力量的消长,阴谋的诡谲,政坛的风云变幻和尔虞我诈。盘点其中近40 名主要演员,女性角色只占9 个,尽管数量上不占优势,但其中的每个女性在剧中却都起着至关重要、甚至影响着剧情走势的关键作用。《琅琊榜》中的正面女性形象如霓凰郡主、夏冬、静妃、莅阳长公主,宫羽、靖王妃等;反面女性形象如秦般弱、越贵妃和言皇后等。她们一个个形象饱满生动,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夺嫡之战中有各自的位置,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在一部以男性为主角的电视剧中,女性力量得到了充分的挖掘和完整的释放,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以女性力量的深层次挖掘而言,《琅琊榜》中霓凰郡主、夏冬、秦般弱最为典型。
霓凰郡主无疑是巾帼英雄的代表。郡主父亲云南王穆深战死沙场,霓凰临危受命,血战楚骑于青冥关,歼敌三万。从此,代幼弟镇守南境,她指天盟誓,幼弟一日不能承担云南王重责,她便一日以一介女流之身保家卫国,直到幼弟能当重任为止。作者让她姓“穆”,穆桂英的“穆”,显然是借北宋著名的巾帼英雄穆桂英来烘托她“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她英气勃勃,神采精华,豪阔宏量,霁月光风,是琅琊高手榜上唯一的女子,是威名赫赫的女中英豪。
夏冬是悬镜司掌镜使,悬镜司首尊夏江的徒弟,赤焰军前锋大将聂锋的遗孀。“悬镜司”的命名,应有封建时代官府衙门里“明镜高悬”的用意。在《琅琊榜》中,悬镜司专门替皇帝督办大案要案。夏冬作为悬镜司里最勘重用的女掌镜使,她的个性与她的名字一样,体现出“夏”与“冬”的对立统一。一方面,她对逝去的丈夫,对朋友始终保持着炙热赤诚的感情,另一方面,她又如冰雪一般凛冽,她武艺精湛,执法公正,毫不偏私。
秦般弱作为誉王的第一谋士,美貌与智慧并存。她身为一介女流,角色跟梅长苏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为助帝王成就帝业的谋士。谋士的远祖是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战国策》一书中记录了他们穿梭于各国之间,纵横捭阖,把自己辅佐的一方,推上帝王的宝座。他们辅佐明君圣主,成就王霸之业,如刘邦之张良、刘备之诸葛亮、朱元璋之刘伯温、李自成之宋献策。野史小说中这样的人物就更多了,如东汉的邓禹、北宋的苗广义、瓦岗寨中的徐茂公、水浒里的吴用。但这些人无一例外是男性。《琅琊榜》里塑造这样的一个女谋士秦般弱,虽然在智计方面她最终敌不过梅长苏,但她美艳动人且精明干练,她借助红袖招搜集信息,为誉王献计献策,逐渐壮大誉王的势力,扳倒了太子。在这个过程中,她还有一个矢志不渝的复国理想。这样看来,秦般弱又何尝不是一个女中豪杰呢?
《琅琊榜》在塑造这些女性的时候,并不是孤立地写这些女性,这些女性背后,往往是一个女性群体。以秦般弱为首的红袖招,以滑族女子组成,主要任务就是复国,类似于现代的特务机构。以宫羽为首的妙音坊,表面上是一个乐坊,但实际上听命于江左盟,主要任务就是为江左盟收集情报。以心杨和心柳为首的“杨柳心”,实为青楼,但这些姑娘从小被权贵压榨迫害,她们和“妙音坊”的姑娘一起,为江左盟出力。甚至在强调手腕和强权的悬镜司里,夏冬也不是唯一的女掌镜使,她是“高阶”掌镜使,在她手下还有一些不同阶位的女掌镜使,她们的存在和个人能力已经突破了传统女性身份和角色定位。
可见,在《琅琊榜》作者的心中,跟《红楼梦》作者心中一样,有一个深深地,对女性的期许。这种期许超越了传统男女两性的性别限制,渴望女性能够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和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是在男性形象弱化和被动化的背景下凸显女性才干的,如贾政之庸、贾赦之色、贾珍之奢、贾琏之浪、贾芸之乖、薛蟠之霸、焦大之醉、茗烟之滑、李十儿之奸、柳湘莲之冷、孙绍祖之狂……在《红楼梦》所创造的艺术世界里,曹雪芹通过社会生活的真实的描述、揭发和批判,显示了对男性为中心的贵族社会的强力否定,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那些坐吃山空、尸位素餐、以至荒淫无耻的男性贵族。可他却把全部同情和爱,给予了清净洁白的女儿们,明确宣布要“为闺阁昭传”,热烈地赞颂了那些行止见识“高于堂堂须眉”的裙钗,尽管在他的思想观念里也还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时代的鸿沟,我们却难以否认,《红楼梦》所显示的审美理想,在他那个时代,又是提供了人性觉醒的新的视角。
《琅琊榜》中,则是真正的“男女平等”,男女“平分秋色”。如果说,对于女性力量和女性才干的赞美,《红楼梦》时代还只能通过对男性形象的弱化和被动化来实现,还只能通过贾宝玉孩子气的“女儿论”来发表,还只能通过探春的“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有我说的”来抗议的话,在《琅琊榜》中,作者显然没有“男尊女卑”这个“预设”,在一个架空了时间地点定位的历史故事里,作者尽情地释放她的“女性理想”,不受限制。
注释
①② 胡文彬《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中国书店2005年版,第400、400—403页。
③ 李可《甄嬛传与红楼梦的互文性解读》,《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3月。
④ 李希凡《论贾府诸爷们的末世形象》,李希凡、李萌《传神文笔足干秋——〈红楼梦〉人物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