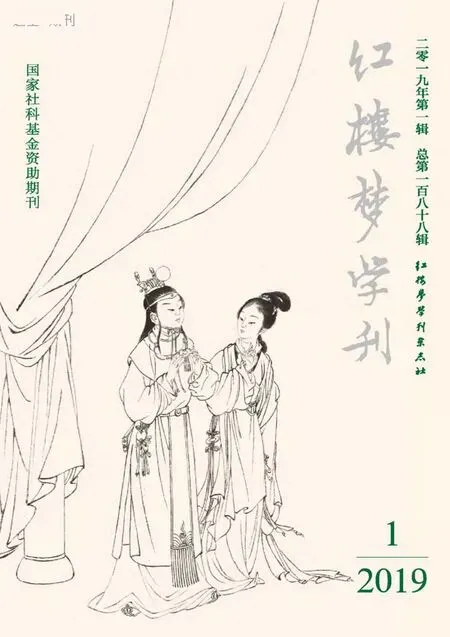论《红楼梦》中“歌行体”对人物塑造的作用
2019-11-12
内容提要:《红楼梦》中歌行体诗作近二十首,代表作如《葬花吟》《桃花行》《姽婳词》,及《芙蓉女儿诔》中骚体部分。在红楼诗词诸多体裁中,数量不算最多,成就却最高。曹雪芹选择特定诗歌体式完成人物塑造的做法,在歌行一体上也体现得最为典型充分。本文拟从诗体学的角度,分析歌行篇制结构、艺术传统、抒情手法对《红楼梦》人物塑造的独特作用,并试图以管窥豹,探究特定诗歌体式对小说人物塑造的不同影响。
《红楼梦》中共有诗词八十余首,体式包括绝句、律体、乐府、歌行、词、曲、酒令等,可谓“诗备众体”。其中歌行的数量,按照不同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若采用“广义歌行”概念统计,共有近二十首。在红楼诸多诗体中,数量不算最多,成就却无疑是最高的。歌行一体篇幅宏大,辞藻华美,最为耗费作者心血,因而几乎全部用于关键角色。《葬花吟》《姽婳词》等作纵情长歌,斐然成章,凸显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内心,预示人物结局,起到了画龙点睛、锦上添花的效果,成为《红楼梦》诗词艺术冠冕上的明珠正是曹雪芹巧妙选择,有意安排的结果。
歌行体长于藻采,可充分彰显人物才华;歌行体婉转回环、寄托深遥,故能触及人物最深层的内心;歌行体声情激越,故能宣泄人物最强烈的情绪。这些特点,都被曹雪芹巧妙的运用到人物塑造中,丰富了人物形象,提升了人物的品格。
对于红楼诗词本身艺术价值的探讨,前人成果颇丰。专著有《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红楼梦诗词鉴赏辞典》《红楼梦诗词解析》等。关于红楼诗词与人物塑造关系的研究,也已有大量论文。但对于曹雪芹通过不同的诗歌体式,推进小说元素的论著还较为少见。仅《〈红楼梦〉的人物塑造和文体选择》《〈红楼梦〉诗歌体式的人格化设计》《代拟的超越与疏离:〈红楼梦〉中女性人物诗词作品探析》等篇有所涉及。又多为通论全部诗体,对于歌行这样一种特殊体裁还未见深入的专论。本文拟从诗体学的角度,分析歌行篇制结构、艺术传统、抒情手法对《红楼梦》人物塑造的独特作用,并试图以管窥豹,探究特定诗歌体式运用对小说人物塑造的独特影响。
一、歌行体富于藻采的特点,可充分彰显人物才华
歌行一体篇制自由,故能驰才骋气,尽情彰显作者的个性才华。正如胡应麟所论:“古诗窘于格调,近体束于声律,唯歌行大小短长,错综阖辟,素无定体,故极能发人才思。李、杜之才,不尽于古诗,而尽于歌行。”曹雪芹对歌行体裁优势有着清醒的认识,有意识运用歌行长篇凸显人物才性。以七十八回《姽婳词》的创作为例。
贾政以姽婳将军林四娘的传奇事迹为题,命贾环、贾兰、宝玉三人在清客面前各赋一诗,以试高下。贾兰成七绝一首、贾环成五律一首,皆四平八稳之作,然而就连“老学士”贾政也感到似有不足:“还不甚大错,终不恳切。”这个恳切,指的并非立意用词,而是“合体”。贾宝玉最晚动笔,完成了歌行长篇,引得“众人都大赞不止,又都从头看了一遍”,连一贯严苛的贾政,也一直面带笑容。宝玉得以胜出,不仅因其辞藻飞扬,更因其选择了与题材最适合的体式——歌行。
“姽婳将军”这个题材具有浓厚的猎奇色彩。听闻姽婳将军之名时,“众清客都称妙极神奇”,贾政则云“更有可奇可叹之事”。林四娘的事迹,也的确称得上可奇可叹。她是王侯宠姬,又是殉主女将。其战死沙场的忠烈、睥睨须眉的豪情,应当也只应当由歌行体来抒写,才能极尽转折腾挪、跌宕起伏之致。从汉乐府《铙歌》起,歌行呈现出辞彩丰华的“尚奇”色彩。其篇制自由,句式错落,故长于书写具有传奇色彩的题材。岑参《走马川行》、李白《蜀道难》、杜甫《大食刀歌》、李贺《李凭箜篌引》无不如此。奇人、奇事、奇物、奇景,皆以歌行长篇铺叙而出,令人目眩神摇。这便是宝玉认为此题“不称近体”“须得古体,或歌或行长篇一首方能恳切”的原因。
除尚奇外,歌行体从定型之初就有任气逞才,铺张扬厉的艺术特点。“初唐四杰”歌行《长安古意》《帝京篇》等,被称为“词极藻艳”。宝玉创作《姽婳词》过程中:“长歌也须得要些词藻点缀点缀,不然便觉萧索”的言论,也显示出他对歌行体艺术特征的准确把握。
高明的诗人会根据创作对象,“度其体格宜与不宜”,选择最恰当的诗体。方东树言“一诗必兼才、学、识三者”,而刘熙载则言:“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对诗歌体裁的选择属于“识”的部分,高于技艺与学问储备,是主人公才华更高层次的体现。
当然,七律联章(《菊花诗》)、七绝联章(宝琴《怀古十绝句》)、联句(凹晶馆联句)也能显示诗才。角色间立意高下、诗技长短的差别,还能彰显人物性格,形成对比。但此类创作毕竟有韵脚、题目的限制,功能也以交际应酬为主,更多是诗歌技艺的较量,不能算完全个体情绪抒发。比如大观园题咏中,“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想贾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违谕多作,只胡乱作一首五言律应景罢了。”黛玉之才,即便分韵限题,也并非不能写出佳作,而是嫌这种体裁束手束脚,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奇才”,不屑为之。唯有不受限制,气象淋漓的歌行体,能匹配宝黛走笔成章、倚马可待的才性。
主人公的歌行体创作,不仅见才中之“技”,更见才中之“气”,才中之“识”。这正是歌行体在塑造人物时不可取代的作用。
二、歌行体婉转回环、寄托隐喻的特点,适于深入刻画人物内心
与五七律常用于应制、唱和不同,歌行是一种更私人化的体裁。抒情更为自由,因而能更真切地抒发个人化情感,深刻展现人物的心理。黛玉所作《代别离》《桃花行》《葬花吟》这三首歌行,不是一时一地的感慨,也非文字游戏,而是黛玉高洁人格的象征,悲剧命运的预示。
《代别离》出现在第四十五回,黛玉病卧潇湘馆,“觉心有所感,亦不禁发于章句,遂成《代别离》一首,拟《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词曰《秋窗风雨夕》。”
《春江花月夜》《代悲白头翁》属于歌行体中深情周致一派。特点是以清词丽句,抒写悲伤之情,最适于展现黛玉此刻心理,故曹雪芹有意让其模拟此体。《代别离》连用十五个秋字,回环往复,表达缠绵悱恻之情。同样,《桃花行》以“桃花”作为一个贯穿意象,用帘外“花”与帘中“人”反复对比,大量运用顶针、重复、罗列等歌行手法,使诗意层层勾连,情感逐步推进,最终达到“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的抒情高点。最恰当地描绘出黛玉纤细精微的内心,预示其“花落春尽”的悲剧命运。《葬花吟》则以花、我(闺中女儿)、春、鸟等意象环环相扣,彼此呼应,构成了一个悲怆而美丽的外部世界及内心世界。这三首作品中,歌行体富于层次、婉转缠绵的体裁特征,与人物内心达到了完美匹配。
此外歌行体巨大的时空容量,也扩展了人物内心的书写维度。《葬花吟》抒情维度极为丰富,就时间而言,既有当下:“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也有想象中的未来:“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也有昨夜回忆:“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就空间而言,有现实中的“绣闺”“阶前”,也有想象中的“天尽头”。就表达而言,有叙述、描写、抒情、议论,融汇交织,层层推进,共同描绘出主人公层次丰富的内心世界。这是“窘于格调”“束于声律”的其他体式无法做到的。
总之,曹雪芹选择歌行体为黛玉的特长,成功地彰显了她不同凡俗的才华;呈现了她纤细精致的内心;突出了她于大观园群芳中的地位。这正是以特定诗歌体裁完成特定人物塑造的成功尝试。
此外,歌行体还有层次丰富、宛曲周折的特点,故能容纳主人公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这一点也被曹雪芹所吸取,用以呈现人物内心中最深层曲折、不为人知之处。
贾政“命题考试”时,正是宝玉悼祭晴雯不得,又未寻见钗黛,万分伤感之时。按照常理,本该无心参与这种文字游戏。即便有贾政之命,也可如贾兰、贾环那样,以五七言近体敷衍交差,而不是写下倾注了心血与情感的长歌行。这段看似“不合情理”的安排,引发后人纷纷猜测。周汝昌称之为“用意安在,费人思索”。脂砚斋提出,《姽婳词》与《芙蓉诔》“互为宾主”。关于宾主说,赞同者认为是有意安排的妙笔,反对者则认为“是曹雪芹在结构和剪裁上的败笔”。
本文认为,《姽婳词》的创作意图,是曹雪芹受歌行一体创作传统的影响,以隐喻寄托的手法,展示出宝玉心中的哀悼之情。讽喻寄托是乐府歌行的传统手法,而其中又有一类以女性为主人公,述其悲剧命运,以小见大,触类旁通,悲悼整个时代。崔颢《邯郸宫人怨》、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韦庄《秦妇吟》、吴伟业《圆圆曲》《萧史青门曲》、樊增祥前后《彩云曲》皆属此类,形成了一个完整而独立的体裁传统。贾宝玉《姽婳词》的创作正是对这一传统的接续。认清这一点,或许能为“姽婳词创作意图”之争提供新的角度。
欲言“寄托”,必须先找到所言之物与所托之物的共性。前人多认为晴雯与林四娘“两个阵营里的人根本无法衬托,无法进行类比”“把一个以生命去酬答平日恩宠的贵族姬妾,与一个遭遇封建势力迫害而死的女奴放在一起写,以便作某种类比的意图,实在也不妥当。”然而,两人的共性不在于身份、立场,而在于“报恩还情”的决绝。宝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触类旁通、以小见大,使《姽婳词》成为一腔悲情的寄托。
林四娘因为姿色、武艺出众而被提拔,并非 “王妃”(何士明)、“贵族姬妾”(蔡义江),而只是侍妾仆婢一类。美人习武,也非备战,而是宴席中的余兴节目,和歌舞丝竹并无本质差别。恒王兵败被杀后,“林四娘得闻凶报,遂集聚众女将,发令说道:‘你我皆向蒙王恩,戴天履地,不能报其万一。今王既殒身于国,我意亦当殒身于王。’”在林四娘眼中,恒王是她的主人与恩人。她以性命回报的,与其说是夫妻之间的爱,不如说是主对仆、上对下的恩。这和专诸、豫让、聂政等人,得到到高位者的接济优待,决意舍身报答“知遇之恩”是一样的。所谓“胜负自难先预定,誓盟生死报前王”正是“国士遇我,国士报之”精神的体现,也是贾宝玉被深深触动的原因。
晴雯出生低贱,无亲可倚,却心比天高,不以奴婢自命,是众人的眼中钉。唯宝玉对她另眼相待,使她感到了难得的温暖以及为人的尊严。因此,她目中无人,唯有宝玉。第五十二回里,为宝玉病补雀金裘的炽烈之情,并非全是男女之爱,也包含了对“恩遇”的感激。她深知离开怡红院后,便再无人将她以“人”对待,所以剪下指甲,又将贴身穿着一件旧红绫袄脱下,赠与宝玉。她交付的,不仅是让宝玉睹物思人的旧物,还是全部的生命与爱。她愿将自己一切的青春美好留在怡红院,留在宝玉心中,做好了“以死还情”的决绝准备。
当豫让第一次说出“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豪言壮语时,就将烈士酬知己、女子报深情联系在一起。林四娘不负君王恩深,血染沙场;晴雯报答公子多情,埋骨荒垅,正是“报恩还情”的一体两面。
宝玉对晴雯的感情也颇为复杂。悯其孤苦飘零,爱其风流灵巧,赏其骄傲任性。晴雯蒙冤,他亲眼目睹却无力救援,又多了一份愧疚。哀悼晴雯不得时,听闻了林四娘的故事,正好借题发挥,利用歌行寄托讽喻的特点,将满腔“不可说”的悲痛融入字里行间。“马践胭脂骨髓香,魂依城郭家乡隔”悲叹,也可理解为对晴雯尸骨未寒就被烧化的痛惋。“此时文武皆垂首”的讽刺里,或许也暗含他对无力打破罗网、救晴雯于绝境的愧疚。“我为四娘长太息,歌成馀意尚徬徨”的彷徨非为林四娘一人而发,而是将晴雯逝去、司棋等人被逐、宝钗迁出、迎春将嫁的悲痛融化在内。既与前文宝玉感叹“天地间竟有这样无情的事”“大约园中之人不久都要散的了”的情绪一脉相承,也是后来《芙蓉女儿诔》的前导。脂批云:“姽婳词一段,前后似断似连,如罗孚二山,烟雨为连合,时有精气往来。”所谓精气往来,或许正是从《邯郸宫人怨》《长恨歌》到《圆圆曲》等长篇歌行一脉相承的艺术源流及情感内核。
贾宝玉天生情种,真诚欣赏女性身上的未受世俗沾染的天真,赞美有情有义的品格,悲悯其身不由己的悲剧命运。这种情感不仅限于怡红院,也不仅限于大观园,而是寄托于天地间一切美丽纯净的灵魂。第五十二回中,宝玉听宝琴偶然说起真真国有少女能诗,立即心生向往,缠着宝琴将诗作拿给他看,可见其怜香之心不因女子身份、种族、地域改变。同样,听到姽婳将军故事时,宝玉感慨万千,故借歌行之体,走笔成章,咏林四娘同时兼挽晴雯,预感大观园诸女必将飘零四散的未来,推之及天下一切美好女性之命运。这正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主题的体现。曹雪芹让宝玉于此刻写下的姽婳词,不是闲笔,也非炫技逞才,而是借歌行体长于隐喻、寄托深遥的特点,展示出人物的隐微曲折又广阔悲怆的内心世界。
三、歌行体声情激越的特点,适于宣泄人物的强烈情绪
由于歌行体没有对偶声律的拘束,也不刻意要求典雅温厚,不宜在更为正式的体式(如五七律)中表现的情绪,皆可在歌行中得到宣泄。如《红楼梦》开篇第一回,跛足道人所唱《好了歌》及甄士隐《好了歌解》。跛足道人“疯狂落拓,麻屣鹑衣”的人物形象,口中所念固然不该是雍容华贵的七律、淡泊高古的五律,而是楚狂人一类“狂歌”。两歌内容也愤世嫉俗,离经叛道:“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皆如当头棒喝、振聋发聩。只有不拘声律、句式的狂歌之体,才能承载这样激越的情感。
红楼诗词中几篇最著名的歌行,如《葬花吟》《好了歌》《姽婳词》等,都写于主人公心怀郁结时,长歌当哭,歌以抒愤。而骚体又是歌行中抒情烈度最强者,可谓“呼告”式抒情。《红楼梦》作者(及续作者)都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将之用于人物内心描写、情绪抒发中。以宝钗《致黛玉诗四首》为例。
薛宝钗一向沉稳持重,其创作也多以近体为主。全文中唯有一处写过古体。宝钗在等待薛蟠伤人案结案期间,感慨身世,作四首骚体歌行,内容则多悲怆惨恸之语。如“无以解忧伤兮,我心咻咻!”(其一)、“何去何从兮,失我故欢! 静言思之兮恻肺肝!”(其二)、“鳞甲潜伏兮,羽毛何长! 搔首问兮茫茫,高天厚地兮,谁知余之永伤?”(其三)、“忧心炳炳兮,发我哀吟。吟复吟兮,寄我知音。”(其四)
这组诗与宝钗平日温柔敦厚的诗风颇为不同,有人认为是续作者为美化宝钗,勉强造情。蔡义江批之为“不伦不类”。续作者固然艺术水平不高,立场不正,把薛蟠罪有应得说成是“惨祸飞灾”,但不妨碍“续作者”以歌行体抒发人物强烈情感的良苦用心。因领会到诗歌体式与人物塑造的关系,以四首骚体歌行,作为宝钗少见的真情流露。正如宝钗信中所言,“匪曰无故呻吟,亦长歌当哭之意耳”。重重困境中,宝钗难得地揭下温柔端厚的面具,对黛玉坦布内心。而黛玉见信后,也“不胜伤感”,认为“宝姐姐不寄与别人单寄与我,也是惺惺惜惺惺的意思”,稍后作《琴曲四章》和之。其一:
风萧萧兮秋气深,美人千里兮独沉吟。望故乡兮何处?倚栏杆兮涕沾襟。
时逢深秋,人遭离散,黛玉回想起故乡远在千里,不得不涕泪沾巾。这种悲伤由宝钗原作引发,而进一步积蓄深化。黛玉将身世飘零之悲,寄人篱下之痛一并融入诗中,配乐歌咏。宝玉和妙玉在潇湘馆外听到,皆深感悲凉。听到第四首“人生斯世兮如轻尘,天上人间兮感夙因。感夙因兮不可惙,素心如何天上月”时,妙玉呀然失色,认为其悲伤太过,恐不能持久。正在此刻,“听得君弦磞的一声断了”。可见骚体与乐配合,能将悲怆之情推到极致,以至于令弦断绝,预示出黛玉走向毁灭的命运。续作者的手法或许不够巧妙圆融,但以骚体写至悲至痛之情的意图是毫无疑问的。
骚体是汉代以后仿效楚地民歌和楚辞而产生的一种诗体,其特点就在于极致抒情。短篇如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刘细君《乌孙公主歌》、刘辩《弘农王悲歌》、蔡琰《悲愤诗》等。除蔡琰外,诸作者都非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之所以能创作出传颂千古的名篇,是因为他们皆置身于兵败被围、去国离乡、被囚将死、母子永别等极端环境。抒情主人公情绪剧烈动荡,需要痛快淋漓的宣泄,所谓言之不足,故咏歌之。他们以歌体的形式,将激烈的情绪以最不遮掩地方式抒发,取得了直击人心的艺术效果。随着诗歌艺术的发展,声律、对偶、辞藻之风渐盛,骚体渐渐淡出主流,而其传统并未断绝,当面临绝境、或遭受重大创痛时,诗人们就会再度选择骚体,借其“呼告”式抒情特质,宣泄最激烈的情绪。杜甫于全家饥寒时写《同谷七歌》,文天祥当国破家亡之时写《离乱歌六首》(原题《六歌》),皆呼天告地,悲愤激烈。宝钗《与黛玉诗》、黛玉的《琴曲》亦为此类,是对骚体抒情传统的继承。
此外,《红楼梦》中还有一篇骚体长歌,即《芙蓉女儿诔》中“歌曰”的部分。宝玉悼祭晴雯不得,听小丫鬟称其已成为芙蓉花神,于是写下了《芙蓉女儿诔》,月下设祭祷祝。这篇诔文是红楼诗词中的杰作,与《葬花吟》前后辉映,代表了红楼诗词的最高水平。关于此诔创作意图,曹雪芹借宝玉之口已有阐述:
诔文挽词,也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袭前人的套头,填几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使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切。……
宝玉摒弃时人彼此因袭、套语搪塞的作法,在诔文中加以骚体歌行,体现“尚古之风”。既因为他要“远师楚人之《大言》《招魂》《离骚》《九辩》”接续《楚辞》传统,也因为他要选择一种最不受拘束的体裁,表达无可排解的悲怆。在这一点上,骚体有其他诗体难以企及的优势。面临挚友离世、骨肉永诀等重大创痛时,声律对仗皆成桎梏,只能长歌当哭、呼天告地才能表达真情。这篇骚体歌行作于《芙蓉女儿诔》中段,经过序文的层层铺垫,主人公情绪已经到了汹涌澎拜、呼之欲出的地步,唯有骚体可以抒发。“天何如是之苍苍兮”“地何如是之茫茫兮”“余中心为之慨然兮,徒噭噭而何为耶?”等一连串的问句,对象包括天地诸神、时空宇宙,情绪激烈动荡,以至于进入恍惚迷离的想象世界,见晴雯魂魄化为神仙,驾鸾凤、纫兰草、配明月而来。这一刻宝玉已起了离尘之意,愿与晴雯魂魄“冀联辔而携归”,真切刻画出一个情痴的形象。然而神仙鬼怪,本属虚妄,只不过是情到极致的幻象而已。宝玉不得不回到现实“君偃然而长寝兮,岂天运之变于斯耶?既窀穸且安稳兮,反其真而复奚化耶?”,最后又兴起渺茫的希望,希望魂魄因自己还在尘世桎梏之中,而暂驻人间:“余犹桎梏而悬附兮,灵格余以嗟来耶?来兮止兮,君其来耶?” 情绪从信——不信——信的复杂过程、幻——真——幻的多重层次,也唯有骚体长篇可以容纳。可见,就人物情感抒发的烈度、深度、广度而言,歌行体都其他诸体难以企及之处。
此篇骚体歌行与黛玉的《葬花吟》前后辉映,是红楼诗词中最具悲剧性、最为动人的篇章,也是男女主人公心性最极致的体现。真正实现了诗歌与人物的相辅相成。若将两作换为五七言律、五七言绝,哪怕是组诗联章的形式,也万难达到这样的效果。这正是曹雪芹善于选择特定诗体,塑造人物性格、刻画人物内心的表现。
四、余论:小说要素对歌行艺术的反作用
一方面,歌行一体的巧妙运用,促进了人物塑造等小说要素的完善。而另一方面,小说要素也能增加歌行体的艺术魅力。《红楼梦》中的几篇歌行家喻户晓,其流传性超过了同时代歌行名篇。这固然是由于诗歌本身艺术达到了一定高度,更因为这些作品置于小说背景中。试想将《葬花吟》等作品从小说背景中抽离,艺术价值无疑会受折损。可以说,小说人物、情节、环境等要素弥补了诗歌本身的不足,为之增光添彩。
歌行一体篇制虽然较近体更为自由,但毕竟有声韵、审美上的限制。为弥补这一点,诗人往往选择“长序”交代背景。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序近二百字,有描写、有对话、有议论,首尾完整,堪比一篇笔记小说。元、明歌行作者多袭其体,甚至有长达千字者。但无论如何,诗序的篇幅终究有限,只能略陈梗概,难以全面展开。《红楼梦》中的歌行作品则不同。作为长篇小说的一部分,抒情主人公的情绪可事先积蓄,形象可充分描绘,因此到抒情言志时,便更能放开手脚、无所拘束。这是歌行本身(哪怕加上长诗序)无法完整实现的。
以《葬花吟》为例。第二十六回,黛玉被拒之门外后感慨身世,立于花阴下悲泣。次日逢芒种节祭饯花神,黛玉独自去花冢葬花。这些都仿佛诗歌的一篇漫长的序章,经过积蓄酝酿,悲喜反衬,使主人公的情绪喷薄欲出。直到第二十七回,方才以长歌行的方式宣泄出来,比起一篇单独的歌行,自然别具魅力。
诗歌以抒情言志为主,塑造人物不是主要目的。即便有诗序作补充,抒情主人公形象在诗歌中往往也并不鲜明。小说则不同,人物塑造为其核心要素,正可补充诗歌的短板。第二十三回,黛玉第一次葬花,解释了葬花缘由,展示了她孤傲高洁、不肯同流合污的心志。这是对《葬花吟》的一次铺垫。而第二十六回的泣花阴则是第二次铺垫。“原来这林黛玉秉绝代姿容,具希世俊美,不期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一闻此声,俱忒楞楞飞起远避,不忍再听。”这一段其实是次日黛玉作《葬花吟》时外貌神态的预写。真正到了《葬花吟》创作的时候,作者有意将黛玉隐藏起来,使宝玉只闻其“呜咽之声”,闻其诗而不见其人。外貌神态有意隐去,突出歌行的内容。创作缘由、人物情态的交代已在之前完成,到此便可隐退,将全部舞台让给这一篇悲怆浓丽的长篇歌行,使之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人物的内心,故取得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葬花吟》是黛玉生命的歌唱。它倾注了作者的心血,彰显人物形象,也预示了人物悲剧的命运,被誉为红楼诗词中的第一杰作。它的诞生,正来源于歌行体裁优势与小说要素的完美结合。
总之,是黛玉成就了《葬花吟》,《葬花吟》也成就了黛玉。脱离了小说,《葬花吟》便无复原有的神采;若摒弃歌行体,人物魅力也很可能受到贬损。《葬花吟》既是红楼诗歌艺术的巅峰,也是诗歌体裁优势与小说要素互相促进、彼此成就的硕果。
五、结论
总而言之,曹雪芹对歌行一体的特性有着清楚的认识,并主动加以利用。在《红楼梦》中,歌体体裁优势与小说要素实现了完美的融合。歌行体尚气逞才、辞藻斐然的特点,被用于彰显人物的才华;歌行体宛曲达意的特点,被用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歌行体直抒胸臆、纵情长歌的优势,被用于抒发人物的激烈情感。诗歌体裁优势与小说要素紧密结合,诗歌与小说之美相生相济。曹雪芹在掌握不同文体的基础上,又打通其界限,使之融会贯通。这个先立后破、由法度而入自然的过程,也正是《红楼梦》艺术世界创生的过程。
注释
① 关于“歌行”体界定,历来众说纷纭。胡震亨《唐音癸签》云:“或名歌,亦或名行,或兼名歌行。歌,曲之总名,衍其事而歌之曰行。歌最古,行与歌行皆始于汉,唐人因之。”提出了一种较为广泛的定义——乐府即为歌行。钱良择《唐音审体》则有意区分两者,认为只有不含乐府古题的那部分可归属于歌行。其实,歌行与乐府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概念,互有交叉。乐府归根到底是一个音乐概念,包括最早入乐的乐府诗及后世文人不入乐的拟作,大体应与“徒诗”相对;而歌行则是一个诗体概念,应与“律体”对立。一些带着乐府题目的七言长篇,如李白《将进酒》既是七言乐府,也是七言歌行。关于歌行与七古,则又是另一个纠缠不清的复杂问题。总之,无论从古人当初的创作状况、还是今天我们面对的文本实际考虑,都无法、也不宜作整齐划分。近年来王志民、薛天纬等学者主张回归于广义歌行概念,将歌行放到乐府、七古的大范围内做整体性考察,即胡应麟所谓“七言古诗,概曰歌行”,并指出只有回归“广义歌行”视野,才能揭示歌行最本质的诗体特征,可谓溯本清源,一语中的。本文即采用“广义歌行”的概念——题名中有含“歌”“行”“引”等标志性语汇的七言、及含七言的杂言诗歌,都归于歌行(明显为词、曲者除外)。
② 王双腾:“反观《红楼梦》中的几位主要人物,热衷于古体诗写作的实际只有林黛玉与贾宝玉二人。”其实,《红楼梦》中有歌行创作的除了宝黛之外,疯道人、甄士隐各有一篇《好了歌》,后四十回中宝钗也有四首骚体歌行。但无论如何,歌行体被用于重要人物、表达其关键情感转折是无可争议的。参见《〈红楼梦〉诗歌体式的人格化设计》,《济宁学院学报》2018年1期。
③ 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中华书局2001年版。
④⑯ 何士明《红楼梦诗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291页。
⑤ 刘耕路《〈红楼梦〉诗词解析》,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5年版。
⑥ 张新艳《〈红楼梦〉的人物塑造和文体选择——以林黛玉、薛宝钗诗词为例》,《中州大学学报》2012年4期。
⑦ 王双腾《〈红楼梦〉诗歌体式的人格化设计》,《济宁学院学报》2018年1期。
⑧ 詹颂《代拟的超越与疏离:〈红楼梦〉中女性人物诗词作品探析》,《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1辑。
⑨⑩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第52、47页。
⑪ 方东树《昭昧詹言》,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年版,第225页。
⑫ 刘熙载著、王气中笺注《艺概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页。
⑬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228页。
⑭ 郭永强《姽婳词新论》,《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4辑。
⑮ 梁竞西《论〈葬花吟〉、〈姽婳词〉〈芙蓉女儿诔〉的意蕴和作用》,《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3辑。
⑰ 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60页。
⑱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华书局 1959年版,第2519页。
⑲ 这四首诗作出现于八十七回,一般认为非曹雪芹亲笔。其作者归属,学界争议颇多。未避免枝蔓,只称续作者。
⑳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693页。
㉑ 文天祥著、刘文源校笺《文天祥诗集校笺》,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028—1042页。
㉒ 作者自言此诔“前序后歌”,则“乃歌而招之曰”之后的部分,可看做骚体歌行。文的部分则可看做骚体歌行之序。
㉓ 诗歌中,鲜明性格的抒情主人公,要么是一组诗歌共同呈现的,要么则是与诗人化为一体。古典诗歌中,抒情主人公多数时候就是诗人本身,故难以分辨。也有不同者,如男性文人所作闺怨诗,即代拟体,大部分女性抒情主人公都较为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