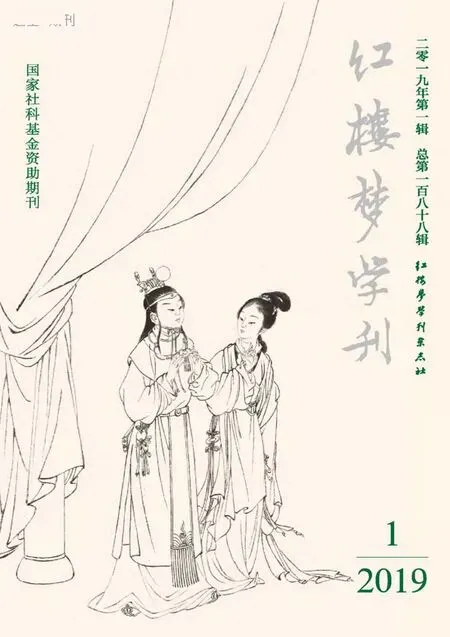真理的追求
——李希凡同志追思会综述
2019-11-12子卉
李希凡先生,祖籍浙江绍兴,著名文艺理论家,红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终身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红楼梦学刊》名誉主编。1927年12月11日生于北京通州,1953年8月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54年12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1955年1月调入《人民日报》文艺部,历任《人民日报》社文艺部编辑、评论组长、副主任、常务副主任等。1986 至1996年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2018年10月29日在北京家中安详离世。2018年12月13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的“真理的追求——李希凡同志追思会”,在院第五会议室举行。
追思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吕品田主持,前来参加的专家学者有:文化部原部长王蒙;中宣部原副部长翟泰丰;文化部原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原院长王文章;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副司长周汉萍;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党委书记、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祝东力;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国家清史办原主任、国家清史编纂文员会原常务副主任卜键;中国艺术研究院马文所原所长涂途;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所原所长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文彬;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吕启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原书记、副院长李心峰;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丁亚平;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文所副所长鲁太光;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所副所长喻静;中国艺术研究院马文所研究员李荣启;中国红楼梦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丁维忠;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处原处长林秀娣;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当代文艺研究室主任郑恩波;《人民日报》蒋元明;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副所长孙伟科;中华英才副总编辑范丽庆;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学刊》编审张云;北京东方彦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马丽;中华服饰文化研究会会长张雪扬;参加追思会的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何卫国、李虹、卜喜逢、胡晴、王慧以及红楼梦研究所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等。李希凡先生的女儿李芹以及外孙女李慧可也参加了追思会。
吕品田先生首先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对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感谢,并提议大家起立,为李希凡先生默哀一分钟,表达深深的缅怀。
吕先生讲述了李希凡先生在管理岗位与学术成就上的巨大成绩。他说,李希凡先生坚持办院宗旨,采取多种措施,促进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新时期开局时期的重大发展。同时,李希凡先生也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出版有《红楼梦评论集》《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题材·思想·艺术》《〈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红楼梦艺术世界》《李希凡文学评论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贡献》等二十多部著作,并于2014年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李希凡文集》(七卷),还与冯其庸先生共同主编了《红楼梦大辞典》等。
吕先生特意提出了在年逾古稀之时,李希凡同志促成并担任了艺术科学类国家九五规划重大课题《中华艺术通史》总主编,带领国内三十余位各艺术门类的专家学者历时十年完成了这项填补我国艺术科学研究空白的编纂,这部十四卷的艺术史2007年面世后荣获多项国家级大奖。他说,李希凡先生历经风雨,而不忘初心,以坚定的信念、求真的精神、高远的视野、严谨的治学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成为一代令人敬仰的文学批评大家和成就卓著的学者。
追思会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祝东力副院长代表韩子勇院长致辞,表达了对老领导的缅怀与悼念之情,他深情地回忆了李先生的学术之路,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李希凡先生便从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分析研究《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在此后近七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作品以及电影创作等。尤其是对《红楼梦》的艺术成就做了博大精深的研究,成为当代红学最具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
祝先生特别指出李希凡先生文艺批评的鲜明特色,那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在文艺的多个领域展开研究,历经几十年风风雨雨而从不动摇,这样一种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正是党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也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相吻合。李希凡先生作为文艺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面旗帜,获得了广泛赞誉,他的学术成就及其重要意义必将随着时间推移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得到彰显。他还指出,李希凡先生有着光明磊落、不计荣辱的胸怀和淡薄名利的人生境界,他既有共产党人的坚定政治立场,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又有着深厚的文史修养和极为广泛的研究和著述。通观《李希凡文集》,可以看到他留下的辛勤耕耘的足迹。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华艺术通史》是迄今为止资料最翔实、内容最丰富的中国艺术史著作。他的文艺评论既有思想内容的深入分析,又有艺术形式上的独到见解,能使二者水乳交融,浑然天成。祝先生还表示,得知先生去世的消息后,中国艺术研究院第一时间和家属进行了联系和沟通,表达了深切的慰问;还将以实际行动来纪念李希凡先生,将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严谨治学的方法,向更广范围进行宣传和推广,也希望大家可以认真梳理更多细节,以更多的方式怀念李希凡先生。
王蒙先生回忆起李希凡先生几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深情地表达了对李希凡先生的怀念、惜别与尊敬。一次是李先生的自我介绍。那是在山东大学原址中国海洋大学的一次活动中,王蒙先生主持会议,李希凡先生回忆他在山东大学的种种经历。“他上台自我介绍说我是李希凡,中国共产党党员。”虽然没有什么新鲜的信息,但李希凡先生对成为一名党员的严肃认真的态度令人肃然起敬。王蒙先生还提到李希凡先生性情坦率,有责任感,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写过不少批评性的文艺评论,比如对被赞扬的新编历史京剧《曹操与杨修》明确地提出不同的看法,李先生没有私心,也没有圈子观念,也不是为了迎合什么,他就是很坦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王先生说,尽管与李希凡先生没有任何个人的交往,但二人有着互相赠书的情谊,而且很感谢李希凡先生在一些比较特殊的场合中都对他采取了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李希凡先生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学者,是一个好党员,真正是一个讲政治、讲党性的书生。”
翟泰丰先生则表示尽管与李希凡先生来往不多,但他特别欣赏李先生坦诚的性格,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李先生一生追求真理,该批评的批评,该赞扬的赞扬,从来不追风,对待学术问题严肃认真,不计较个人得失荣辱,令人敬佩。翟先生对李先生的学术成就高度赞扬,他曾就李先生的文集写过《精道文心 渊博论说——读〈李希凡文集〉有感》发在《光明日报》上,认为李希凡先生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史,以文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的辩证研究方法,挖掘中国古典小说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典型形象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力量,弘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李希凡先生敢于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精神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并发扬光大。
在王文章先生看来,李希凡先生不仅仅是老领导,还是自己的学长、老师。李希凡先生坚定的学术理念、刻苦的学术追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李希凡先生初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时候,国家正处在一个经济体制转型的时期,研究院也处在发展转型的艰难时期,但李希凡先生非常坚定地领导中国艺术研究院坚持学术追求,这也是立院之本。在李先生个人的学术生涯中,他同样坚持自己的学术追求,比如他主持的《中华艺术通史》,他后来跟冯先生共同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这些都是新时期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建设的重大成果,都是对国家艺术学发展的贡献。我们任何时候做研究,都需要这种学术理想和这种刻苦的精神。李希凡先生的不计荣辱、澄怀淡然,也令王文章先生印象深刻。尽管一生起起伏伏,但李先生内心的那种学术理想的追求是非常强韧的。他也提到了李先生对《曹操与杨修》发表的批评意见,是发自自己真诚的认知与信念,有益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这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京剧。这是一位真诚的学者认真的学术坚持。王先生还对李希凡先生的红学研究进行了高度赞扬。李希凡先生开拓了自成一家的红学研究的道路。今天,我们的学术研究仍然需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坚持自己创新性的意见,学习他的精神,学习他的为人,这样才能不断地对我们艺术学的研究有所贡献。
周汉萍副司长受部领导的委托,也表达了对李希凡先生的缅怀之情。她认为,李希凡先生有几点精神特别值得我们晚辈学习:一是在治学上坚持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的精神,这也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加强文艺评论是要把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一致。二是李希凡先生沉心静气,学术无止境,秉着艺术良知治学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尤其在这个浮躁的现实社会里,我们的青年学者一定要有这种不怕坐冷板凳的精神,要淡薄名利,才有可能取得成就。三是我们不仅要怀念李先生的治学精神,还要大力宣传,弘扬《红楼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李希凡先生相识四十年的张庆善先生饱含深情地回顾了多年的老领导、也是十分敬仰的师长的学术之路与巨大成就。他认为,李希凡先生是被毛主席表扬的“小人物”,也毫无疑问是红学界的大人物,是影响一个时代的大学者,在红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恰如冯其庸先生所说,新中国红学是李希凡、蓝翎开创的,他们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标志着红学研究从旧红学走出来,走进了一个新的天地、新的方法、新的理论,也因此找到了新的研究前途,这是红学史不可回避的事实。张先生还就李希凡先生的主要红学观点做了论述:作为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在六十余年《红楼梦》研究的学术生涯中,李希凡先生始终不渝地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文艺观研究《红楼梦》,坚持着他自己的基本观点。他坚持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是清朝封建贵族阶级、也是整个封建贵族阶级制度必然灭亡的宣判书,而绝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他坚持认为“色空”不是《红楼梦》的基本观念,《红楼梦》不是“自然主义”的作品,不是曹雪芹的自传。他坚持认为《红楼梦》具有“新生的资产阶级萌芽”,《红楼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不仅仅具有叛逆性,更具有人性的觉醒,这些基本观点对红学的当代发展产生了长远而广泛的影响。尤其是李先生的《红楼梦艺术世界》《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用现实主义美学理论对《红楼梦》的艺术世界和人物形象做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展现了李希凡先生最新的学术成就。张先生认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是新时期红学的重镇,不仅因为有冯其庸、李希凡等人,也因为新时期红学一系列奠基性的研究成果都离不开中国艺术研究院。比如一直以来发行量最大的、影响最大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校注本,比如《红楼梦大辞典》《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以及《红楼梦学刊》的创刊,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成立等。张先生还提到了李希凡先生令人感受颇多的两部著作。一部是《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一部是李先生与大女儿李萌一起完成的《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修订版)。前者是张先生在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时候曾提出的建议,尽管当时并没有被李先生接受。“自述中充满了坦诚、真挚和自省。你从自述中会感到他为人的正直、真诚、坦荡、宽厚、善良,他是一个充满了真情的大写的人。”后者是李希凡先生在九十岁高龄的时候,与女儿李萌共同完成的巨著。此书修订出版,李萌功不可没,但斯人已去,只留下悲伤的老父四年后才知道女儿离世的消息。张先生说,这既是李老最后一部学术著作,也是对他一生研究《红楼梦》的总结,这部专著的出版无论对李希凡先生,还是对新时期红学,都是非常重要的收获。
张先生说李希凡先生晚年最关心的两件事:一是修订《红楼梦大辞典》;二是修订《红楼梦》新校本。“在他逝世的前十几天还两次给我打电话,说起这两件事,要我负起责任。”他认为,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研究开创了一个时代,他们毫无疑问是新中国红学第一人。而几十年来,李希凡先生不忘初心、不改初衷,始终不渝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典型论,这种坚持,这种高尚的学术品德是令人敬佩的,更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邱华栋先生说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读过李希凡先生的《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等,并从文学创作以及个人角度谈起了李希凡先生的人生经验与所取得的成就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李先生少年时代生活艰难的磨砺是其人生中特别重要的阶段。因为童年经验对一个人的人生影响巨大。李希凡先生从十三岁一直到1949年之后、进入华东大学之前这一段时间,可以说经历了很多的磨砺,但艰难的成长过程中仍不忘阅读各种各样的古代典籍,我们对他的这一时期应该做更细致的研究。而后来李先生在山东大学读书期间,认真努力,奋发图强,为今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个阶段则是李希凡先生中年时期的苦苦求索与老年时的壮心不已。李希凡先生1986年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常务副院长,已经是五十九岁了,但他在繁重的管理工作之余还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比如《红楼梦大辞典》《中华艺术通史》等等。“我觉得李希凡先生为我们做了特别好的表率,他在文艺理论、红学研究、文学写作各个方面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为人谦和、善良、幽默,这些品性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邱先生表示,我们一方面要深切地缅怀李希凡先生,另一方面要把李希凡先生开创的红学事业、文艺理论研究的事业、文学事业和文化事业,更加发扬光大。
卜键先生则从自己与李希凡先生的日常交往中深情回顾了李老,并提到了自己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的纪念文章《清寂中的持守——我所了解的晚年的李希凡先生》。他认为,清寂是李希凡先生晚年的生活状态,尽管没那么热闹,但持守是他个人意志、个人学养的一种坚持。卜先生认为,李希凡先生是一个非常认真、磊落的人,有什么说什么,他对现实很关注,而且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他很宽容,即使是对观点不一致的人,也能理解他们不同的学术思考。“我想希凡先生他其实还是幸福的,李芹当时告诉说他最后是躺在床上,说我困了,拉着李芹的手然后就没有呼吸了。很少有人会这样幸福地离开人间,我觉得也是一种美好的结局。”
刘梦溪先生说:“王国维说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同样,人物也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物。能称得上人物的,常常留下时代的记忆。希凡的不同之处,在于二十几岁就烙印上了人物的标记,不管是大是小,他都作为一个时代的人物进入人们的记忆。人物是时代所成就,也受时代的限制。并不是所有人物都值得怀念。如果一个人物不幸中断了生命的旅程,很多人都表示怀念,那他一定有超越时代的品质被人们记住。我和希凡有五十四年的交谊,以我对他的了解,我想他是一个值得怀念的人。特别是我个人,我青年时期的努力问学,中年之后的学术追寻与建构,我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所和创办《中国文化》杂志,希凡是有力的支持者,他是我想忘也忘不了的人物。有时他入我梦中,第二天打电话给他,告知梦中情景,我说真是挥之不去啊! 所以然者,主要在于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肯助人的人,一个好人。”“李泽厚也是我多年的朋友,他的学术立场与希凡不一定相同,但他在美国看到我写的《忆希凡》,打电话表示赞许,说希凡人很好,诚恳谦和。”
刘先生谈到,评价人物,有三点最要紧:首先是分正邪,其次是辨是非,最后是定功过。分正邪是第一位的,因为好人也会犯错误,不好的人也会做出正确的事。好与不好、正与邪的分野,在于善与不善,在于廓然大公还是私心私见。也就是孔子说的“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无非公也,小人无非私也。是非易辨,正邪难分。至于给人物定功过,生前固然难于定论,死后也不见得定得明白,而是需要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学术是公器,可以有宗主,但不能有宗派。《易经》的“同人”卦,警示人们不可“同人于宗”,“同人于宗”的结果必然“吝”,即狭隘而不能容纳异己之见,这是学问的大忌。真正的大学者,在德范方面常常可圈可点。没有风骨,没有气节,没有一种志不可夺的精神力量,无法写出能够传之久远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刘先生说:“希凡为人诚恳,心地宽厚,帮助过很多人,从不嫉妒人。他的这些品质是可以超越时代的。作为一个时代的人物,希凡是值得我们怀念的一个人物,尤其是值得我个人怀念的人物,我不会忘记他。他耳朵软,心也软,我无法不念他的好。”
涂途先生从三个方面追忆了李希凡先生。他说,李希凡先生虽是一位“小人物”,却有着巨大的意义。他代表一种新生力量,有着蓬勃的朝气,他是不断向前的,有闯劲、有创造精神。同样他也关怀、支持年轻人,一贯鼓励他们奋发向上。涂先生还提到了李先生在艺术研究院任职期间对马文所的支持,“他坚持马文所要办下去,有的人提出要把马文所撤销合并,他几次顶住,认为马文所和《文艺理论与批评》都应该坚持下去,是文化部建立的一个很重点的所。”涂先生说,李希凡先生给了他很多帮助,不仅有工作上的支持,还给他的文集写了总序。尤其序中所说的“作者的无怨无悔是因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从事美学与文艺理论的研究,虽不时髦,却是对真理的追求”,这恰好符合今天追思会的主题。
吕启祥先生则认为李希凡先生是一位真正的仁厚长者。自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知道了李希凡先生,但真正认识是在七八十年代,接触比较多则是在李先生退休之后的晚年时期。吕先生认为,李希凡先生的仁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他对于艺术研究的那种眷眷之情,这是一种怀念,包含着欣慰和感激。1986年,李希凡先生由《人民日报》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角色转换。在吕先生看来,李先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任职期间,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前海学派,一是艺术通史。从前者来说,他尊敬前辈,爱惜人才,虽然他本人没有大量时间搞研究,但是他在背后做了很多默默的支持和策划工作。另外一个关键词是艺术通史,在退休之际领了这么一个项目,确实是吃苦受累做了这么一件有风险和挑战的事情。如果没有坚韧的意志,没有认真学习的精神,没有他的凝聚力,这个项目也不可能完成。另一方面就是李先生对红学事业的拳拳之心,这是一种挚爱,包含着关怀和期望。吕先生认为,在新时期的红学里,李希凡先生很少用红学家的身份出面,也从来不用“小人物”来炫耀。她重申了曾经在李希凡与当代红学座谈会上的看法,1954年不是什么个人的侥幸一夜成名,更不是刻意地迎合,李希凡有学术准备和理论准备,而且有足够的学术担当和勇气,因此历史选择了李希凡,而且历史检验了李希凡。吕先生提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李先生曾拒绝江青找他写批判文章,这是极不容易的,令人钦佩。吕先生指出李希凡先生是新时期红学航船的“压舱石”。首先,李希凡促成了红学界的大团结。红学是一个体量很大、渊源很深、路径纷繁,而且参与者众多、牵动很广的一门学问。从红楼梦研究所的成立、《红楼梦学刊》的创刊以及中国红学会的成立,都离不开李希凡先生的全力支持与配合。其次,作为“小人物”,李希凡自己不提起、不矜持。对于社会上的诸多议论与质疑,他的基本态度是“坚守史实,任由评说”,显示出“压舱石”的定力。吕先生说,“对于一个历史事件,评说可以见仁见智,然而历史事实只有一个。在维护历史真实这一基本点上,希凡从不含糊、旗帜鲜明,显示政治的定力和学术上的独立精神,从不随风摇摆,随人俯仰。”第三,作为红学界的“压舱石”,李希凡维护正常的红学生态,抵制各种歪风邪气。他对新时期很多戏说、揭秘持不同意见,坚持曹雪芹的著作权。吕先生认为,李希凡先生是一个很磊落的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即使是与一些名家的争论,如果有不同意见也会直言,非常令人敬佩。而且,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曾经的掌门人、艺术通史的学术带头人、新时期红学的“压舱石”,李希凡先生除了那些摆在桌面的著述以外,更有其背后的默默付出和鼎力支持,他仁厚的风范和磊落的胸怀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李心峰先生则从李希凡先生对新时期中国艺术学建设的非凡贡献方面表达了自己的缅怀之情。他说,李希凡先生从1986 到1996年整整十年间担任的是唯一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即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掌门人,这也正是新时期艺术学比较早的时期,一些史论方面所诞生的经典之作以及培养的一批人才都与他有直接的关系。第二,李希凡先生也是新时期艺术学学科建设方面的组织者、领导者,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设计者。我们国家的艺术科学的规划、评审、组织、领导,他花费了巨大的心血。而且如果没有李先生牵头来做《中华艺术通史》,到现在可能也还没有人敢承担这样一个课题,还是做不出来。今天艺术学已经成为一个门类学科,而且这里面有一个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其主要学科方向就是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从这点看李希凡先生提出并主持这个课题,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为我们的艺术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好好总结他的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包括整个研究过程。
丁亚平先生表示,李希凡先生是一位坚持求索、学无止境的大家,具有可贵的学者素养和学术精神。他是无所不能的大家,涉猎广博,红学、当代文学、文艺理论、马列文论等等,有很多写作、批评、研究的成果。“记得他晚年时不只一次和我谈他对国产电影的看法,他晚年眼睛不太好,他说有时候还看电影听电影,也评论国产电影,我觉得很有意思。评论里贯穿了他直率的批评精神与褒贬,某种意义上也包含体现着他自己对真理追求的精神。”丁先生还提到李希凡先生作为出色的学术机构的领导者、组织者,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他懂得科研是重中之重,不流于形式。在他的领导下,可以说形成了很好的新的传统,特别是注重科研,注重史论、学科建设,注重集体项目。他在尊老的同时,也为青年人提供平台,为青年人的成长鼓掌。他是一个宽厚、有真情、有包容心的好人,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更是一个本色的大学者。
郑恩波先生则饱含激情地提到了李希凡先生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他说,从1956年自己初中毕业时就立志要做刘绍棠式的创作者,或者是李希凡式的文学评论家。尽管大学学了外文,但对李希凡先生念念不忘,尤其是对中国文学史非常感兴趣,经常在图书馆看李希凡先生对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形象的分析,特别注重他在各家报纸上一些有争论的小说讨论。郑先生说,从《人民日报》社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李希凡先生不仅有对我工作上的支持,也有生活上的关心。我们的许多活动他都参加并做书面发言;他在百忙之中给我的小书作序,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还把孩子从美国寄回来的治疗糖尿病的药品送给我。同时,李希凡先生也爱帮助提拔年轻人,与时俱进,重视他们的看法与想法。“我感觉李希凡先生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多情仗义的汉子。”
《人民日报》的蒋元明先生回忆了自己当年和李希凡先生在同一间办公室相处了大约十年,提到了自己写的悼念文章《我所知道的李希凡与江青、蓝翎的那点事》,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尽管希凡离开报社很长时间了,但好多人记得他。他宽厚、和善,帮助了好多人,他是一个好人。”
李荣启先生则认真总结了李希凡先生的两个治学特点: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具有求真思辨的学术勇气;二是坦然面对人生的磨难,执着不懈地进行理论探索。林秀娣先生详细论述了《中华艺术通史》立项,完成过程中的种种艰难,李希凡先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对中国艺术科学的基础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希凡先生的外孙女李慧可代表家属发言,她“代表全家感谢各位学术界前辈、姥爷的同僚、故交、旧知齐聚一堂,在此聊聊姥爷年轻的过往,寥寄哀思”。李慧可从“桌子”的独特角度将大家带入满含真挚深情的回忆。随着她对姥姥、姥爷、爸爸、妈妈、自己的桌子的描述,我们似乎都看见了李希凡先生的那张大桌子,“偌大的写字台被他齐齐摞上了四五叠书,平时写作的那一方寸天地也仅仅能铺下他的稿纸、笔筒、烟灰缸和正在看的一两本书,而且也只能摞着放。搬到了罗马家园以后,新家的写字台各设了三层搁架,供他放书,不知是不是站起身取书不方便,他依然是严严实实地给我们砌起了书墙,还给我们立下规矩,写字台是私人领地,不得侵犯,任何人都不得给他收拾桌子。”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总是留给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感动。那与家人围坐吃烤鸭、打麻将的李老,与外孙女畅谈文学与人生的姥爷,似乎令人愈加怀念。
吕品田先生最后做了总结发言。他说,大家都满含情意对李希凡先生的学术成就、人格魅力以及时代意义等畅所欲言。李老是满怀理想的,也是一位充满责任担当的人。他坦诚认真、光明磊落、为人谦和、仁厚,正像王蒙部长说的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好学者,一个好党员。希凡先生不仅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而且具有时代意义。他用历史唯物史观开创了中国红学研究的新境界,是红学这艘航船的“压舱石”;希凡先生也在艺术评论、艺术学科建设方面作出了非凡的贡献。而他的追求真理,坚持原则,不计荣辱,不忘初心,具有强烈的关注现实的意识,以及旗帜鲜明的对不良现象的批评精神,都是推动我们这个时代进步所需要的。
李希凡先生是一位会被这个时代记住的人物,也是值得我们怀念的人物。今天我们在这里追思缅怀希凡先生,也衷心祝愿希凡先生的在天之灵能够长眠、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