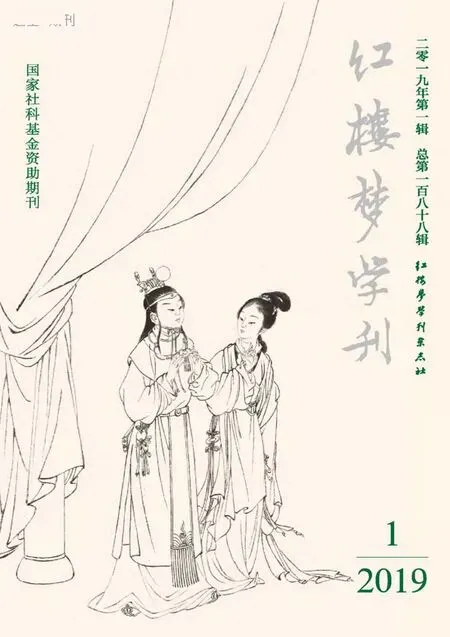仁厚长者李希凡
2019-11-12
希凡先生是在我们没有任何精神准备的情况下,遽然离去的。前天还在电话里听到他的声音,今忽杳然。一种巨大的空白和失落袭来,生前种种,宛在眼前。这里只能就我的直感,追忆片断,难窥全豹。
希凡从《人民日报》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在1986年,那时已五十九岁,进入人生的中老年。也就是说,他的后半生是在研究院度过、在这里离退的。我认识他虽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但较为熟悉还是在他来院之后,真正接触较多是近十几年的事,在这期间,每年有少则三两次多则十来次的见面,电话则不曾间断。在他晚年相对寂寞的岁月中,我是一个能够倾听、易于沟通的晚辈友人,在我心目中,希凡的形象也较前更为亲和真切,他是一位仁厚长者。
他的仁厚,以我观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艺术研究的眷眷之情,是一种怀念,包含着欣慰和感激。
一是对红学事业的拳拳之心,是一种挚爱,包含着关切和期望。
先说第一方面。他曾多次说过,“不后悔来艺术研究院”,虽则调令逋出,告状不少,阻力不小,但他决心已下,且得到时任文化部长王蒙的支持。来院后,他在任内做了实事,并未虚度。
说实在的,李希凡从《人民日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很大程度上是角色的转换。从一线新闻单位到研究单位,性质不同;从直面现实发言写文章到沉淀积累静心搞研究,特别是从自己上阵到领导众人,位置不同。希凡从来未做亦不擅行政工作,尤其不擅理财开发,曾因当法人代表而被债主包围,十分狼狈。但他懂得研究院的主业是搞研究出成果。他尊重前辈,爱惜人材,在政治风波中竭力保护了一批人,使研究院不伤元气,我曾在过往为文中提及。这里只想说,希凡在回首这一段经历时有两个关键词“前海学派”“艺术通史”,令我印象深刻。
所谓“前海学派”并非实体,我理解是对基础研究、对各学科奠基工程的重视,是对群策群力朴实学风的肯定。近年他还充分评价我所参与的红学基础工作为“前海红学”。希凡在职期间,规划和支持了此类项目,自身虽无暇写作,而研究院早期各种成果的背后有他的辛劳,为此付出他是心甘情愿的。
另一个不断提到的关键词是“艺术通史”,即《中华艺术通史》,这是他退休之际所领的一个项目。在国家艺术科学规划会上,他提出了两个项目,艺术概论和艺术通史,前者被北大领走,后者无人问津。他掂量再三,终于鼓足勇气认领了下来。
此举还真有点“犯傻”。退休了,本可放松下来,写自己的东西,驾轻就熟,照样著书立说;而他却选择了吃苦受累,去挑担子,进入那并不熟悉充满挑战和风险的领域。当年院内外不乏质疑甚至轻蔑之声,他要承受多方面的压力。外部的经济压力,没有钱,钱不够;更吃重的是人才压力、知识积累和理论提升的压力。对他个人而言,须重新学习、拓荒开疆。他给我的电话很多是有关通史的,比方说坦陈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而“恶补”,比方说感念北师大出版社的投入,比方说如何请专家讲课,比方说经历十三次编委会每次讲话都自己写稿,更多的是提到编写人员特别是分卷主编,钦佩他们的学识、感谢他们的坚守。他怀念已故的、牵记健在的,总说稿酬很少,并无名利。每有通史消息,如评论、获奖、译成外文版等,他都会很快告知,欣慰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十分可贵的是他的凝聚力。希凡不仅是学者,更是学术带头人。长时段集结一批优秀学者共同完成一项学术工程,谈何容易,没有坚韧意志和学术民主是做不到的。几年前,《李希凡文集》出版座谈会上有一位艺术通史骨干也是我北师大校友说,原先以为李希凡锋芒尖锐,存有戒心,多年相处,“他真是一位忠厚长者!”诚哉斯言。
我曾说,希凡为官一任,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留下了一张学术名片。当然,他很清醒,不足未善多有,但无论如何,填补空白的首倡之功不可没。他有理由欣慰。不讨巧,不避难,唯醇正仁厚者方能为之。
以下再说他对红学事业的拳拳之心。
人们看到,来院之后的几十年间,李希凡大大淡化了他“红学家”的角色。客观上职责所在任务压身,他没有时间专事红学写作和活动,主观上他从不以红学家自诩,更不以“小人物”光环炫人。但他热爱《红楼梦》,心系红学,竭尽全力支持和推动以冯其庸为代表的红学同道,开辟了红学新时期。
顺便说一下,李希凡和冯其庸二位,个性不同、学养不同,冯较多艺术气质,李更具理性风范;坚强的事业心和报国的大情怀使他们友谊深固,互相支撑、互为补充。新时期的红学活动,冯其庸在前台,李希凡似只在幕后。
然而李希凡是不可或缺的。当历史进入2016年,也就是希凡九十岁的时候,才有了“李希凡与当代红学”的学术座谈会,这是第一次,如今也是最后一次了。在这个会上,我郑重提出:历史选择了李希凡,历史检验了李希凡,他是新时期红学航船的“压舱石”。
红学是显学,体量巨大,影响广泛,众声嘈杂,牵动多方。这艘航船唯有行稳,才能致远。“压舱石”对稳定船体、把握航向,关系至大。兹举大端:
首先,促成了红学界的大团结。1980年开了首届全国红学研讨会,成立了中国红楼梦学会,之前创办了《红楼梦学刊》和红楼梦研究所,在红学历史上都属于首次。须知红学界的大团结来之不易,红学渊源深长、路径繁复,老中青、东西南北、高等学校和研究单位、资深和新锐、考据和评论……各路神仙、各有诉求。其间李希凡和蓝翎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们顺应潮流、不负时代、协调各方、瞻顾大局,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实现了红学空前的大团结。中国红楼梦学会的第一任会长是吴组缃,第二任是冯其庸,李希凡始终是副会长。
与此同时,他协助和支持冯其庸为新时期红学搭建了一个起点很高的平台。时当改革开放之初,学术开始复苏,红学犹如一枝报春花,她的绽放得到了格外的关注和多方的浇灌,只要列举当年参加红学会议和活动的人物就可见盛况。不必说原本就是治红学和文史的俞平伯、顾颉刚、吴世昌、吴恩裕、周汝昌和本院的王朝闻、郭汉城等,更有文化教育界的重量级人物沈雁冰、王昆仑、叶圣陶(沈老为题刊名,叶老为看校本,王昆老宁可人大常委会请假也要来开红学的会)。特别是文艺界的资深领导人周扬、林默涵、贺敬之和本院的苏一平都给予热情支持以至亲自与会。至于为刊物题词、赋诗、赐稿的就更多了,有吴组缃、启功、夏承焘、端木蕻良、霍松林,丰子恺、聂绀弩、陈从周、姚雪垠、舒芜等,从大学教授到著名作家,济济萃萃。当然,还有一大批与李希凡冯其庸年辈相仿的学人:蓝翎、蒋和森、陈毓罴、魏绍昌、魏同贤、蔡义江、吴新雷……名家之多、层级之高,均属空前。应当说,此乃拜时代所赐、改革开放的风气所赐,今天想来不禁神往。李希凡促成和亲历了这一盛况,深刻地意识到红学的兴旺和延续乃是一种历史的责任。
其次,作为“小人物”,希凡自己不提起、不矜持(他的七卷本《文集》连1954年的文章也没有收)。然而社会上多议论、多质疑,真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对此,李希凡的基本态度是“坚守史实,任由评说”,显示出“压舱石”的定力。
在红学界以至学术界,可以说很少有人像李希凡那样,受到如此之多的误解、曲解、猜测、质疑以至污蔑谩骂,甚至海外的谣言,十分离奇,居然也有人为之传播。笔者闭塞所知甚少,只是听他说起,那些海外奇谈,匪夷所思,不胜其烦,只能不予理睬。然而,面对国内许多对此抱有兴趣的学人和传媒,不论是想重新评价或探索研究,都不能置之不理,于是就有了几十年来不断的访谈。希凡出于历史当事人的责任,以极大的耐心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的采访,向采访者提供史实,回答各种问题。希凡本人只写过有限的回忆文章,而对外界以至身边的各种看法和著述,从不干预。
对于一个历史事件,评说可以见仁见智,然而历史事实只有一个。在维护历史真实这一基本点上,希凡从不含糊、旗帜鲜明,显示政治的定力和学术上的独立精神,从不随风摇摆,随人俯仰。
远的不说,只说两件近事。一是2011年我在海外探亲,偶尔从网络上看到一篇“揭秘”1954年的长文,回来后询及希凡,其时他老伴病危、心力交瘁,然因事关重大,必须澄清,他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自己口述由大女儿李萌笔录,予以全面回应。事实俱在,本无秘可揭,他以当事人的责任,维护历史现场,斩钉截铁地说:“谁都休想让我把‘有’说成‘无’!”
另一件时间更近,已到2016年,外地的一位红学研究者张胜利正撰写一本关于王佩璋女士(俞平伯先生助手)的专著,有一个重要史实要向李希凡先生求证,即所谓1954年由王佩璋之文引发了李希凡蓝翎与俞平伯先生的商榷(即“第一枪”) 是否属实,此说的来源是《红学:1954》,流传甚广。李希凡虽早有此著,但与其文艺观、世界观歧异,不想与相差四五十岁的青年争论,亦料想不到此说影响之广。如今有研究者来认真求证,希凡先生以十分鲜明的态度郑重地做了书面答复。老实说,希凡要求书面作答大出我的意料,我自愧缺乏他那永不褪色的革命激情和坚韧意志。他在答复中严正陈明:以事实论,当年他根本不认识王佩璋,从未谋面,亦未读过她的文章。以逻辑论,一场触发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大讨论竟由俞先生门下的一篇版本文章引起?无此可能。以情论理,说李、蓝本无学术勇气,是从王文那里借了胆,这未免太看轻了当年“小人物”的气概了。在这一字一句答复的最后,不禁感概万端地说:“我虽已几近九旬,却还是为六十多年前的战斗豪情(一生只有这一次)被漫画化,感到屈辱,不得不出面一辩。”这是李希凡生前的最后一文,十分沉痛。
由此,可以感受到李希凡的刚正之气和坦荡之心,见出其经历风雨摧折而始终屹立的坚韧品性。
复次,“压舱石”的作用,还在于维护正常的红学生态、抵制各种歪风邪气。
作为一个经历风雨的长者,李希凡有足够的度量容纳不同的学术意见,爱护青年,平等待人;但他决非无原则的好好先生,不是庸俗的和事佬。
比如,他对一切戏说、揭秘、解构及新老索隐说“不”,那火爆一时的“秦学”他是不赞成的。他认为《红楼梦》不需揭秘,并非皇权争夺和宫廷内幕的演绎。无论是接受采访或发言为文,他都重申《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审美品性和不朽价值。
又比如,他对小说作者的种种新说也不以为然,始终维护曹雪芹的著作权。在曹雪芹逝世250 周年之际,还发文见于报端(《中国文化报》2013年6月26日),并参加各种纪念活动。他在文中列举了大量内证、外证后指出曹雪芹是《红楼梦》、即八十回《石头记》的真正的作者“无可置疑”。“至于非给《红楼梦》另外找出一个作者,不管那些遐想出来的论证说得多么天花乱坠,都不如曹雪芹亲友们的这些文字确证更有力,更有信任度。”
再比如,也是更为切近之例,当2015年初,邪风起于萧墙,是他以高度的敏感识破了所谓致主编信(兼致我)的用心,第一时间电话告知了我,“你对辞典质量的善意被诬为‘破坏’,信里充斥着攻击,你要通过组织、据理申诉,维护学者的尊严。”他建议申诉并与其庸共同为我作证。在此后的几年间,尤其在另一主编冯其庸病危和逝世后。李希凡萦绕于心念念不忘的是《红楼梦大辞典》的重新修订,不遗余力地推动、促进。他曾提出自己出资几万元作为启动之用,不断提出要请客慰劳大家编写工作的辛劳。其庸逝后重发他的《相知五十年》,他特别提出,倡扬冯氏的研红之路,“不只是寄托自己的哀思,而且有益于纠正当前红学的乱象。”最近几个月他一再说要写一封信递上去,为辞典、为刊物、为红学,孰料信未成而人已去……对红学事业可谓鞠躬尽瘁,至死不忘。
希凡仁厚,不是无底线的忍让,而是有刚正之气为依凭的大仁。他喜论辩,是为真理而辩,光明磊落,可以说,他一生没有什么私敌,“仁者无敌”。我从这位仁厚长者那里感受到的是正气和温暖。
希凡仁厚,不是无是非的苟且,而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定力。他不像某些知识分子那样怨天尤人,满腹牢骚。当我时常因社会的负面现象而丧气时,电话那头会传来他的声音:“你放心,这个世道自有担当的人。”每有令人振奋的国内外大事发生,他会立即打个电话过来,直抒观感。
希凡仁厚,爱才举才,更能洞见人的深层品性,察知正邪、真假、偏私。他帮助和提携过许多人,得失长短,心明如镜。他从不强加于人、强人所难,比如他受老贺(敬之)所托为其友写序欲委我,我不应终于作罢。他看似大大咧咧,其实善解人意,举最近之例,他给大辞典修订负责人专致一信,陈明修订目的在学术,特别提出“启祥同志就不要担任什么名义了,她还是编委”。这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辞所长至今,并未汲汲名利,希凡知我心迹。
回顾这段时期,他虽离退居家,却关心世界大势、国家前途尤其是文艺现状。我常惊叹八九十岁视力有限的老人还能看几十集的电视连续剧,从《北平无战事》到《传奇大掌柜》都是他推荐给我的。他能记住许多剧情的桥段,叫出许多演员的名字。有一次(2017年10月21日)电话打了个把钟头,详细复述故事情节,点评表演得失,竟然是地方台节目。他常说,还是有肯吃苦的导演,会表演的新人,有生活气息的作品。然而当文化部文联偶尔请他开会或征询时,他会对当下文艺界的歪风乱象痛加指斥、直言不讳。我感叹老李是个天生的文艺批评家,他对文艺事业如同对红学事业一样,关切牵记,期盼风清气正,达到真正的创作和批评的繁荣。
最后我想说,作为曾经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掌门人的李希凡、作为《中华艺术通史》学术带头人的李希凡、作为新时期红学“压舱石”的李希凡,当然,还有文艺批评家的李希凡,单是那多卷文集显性著作是不足以概括其贡献的,他在背后的默默付出和倾力支持、他的仁厚风范和磊落胸怀,是留给我们的可贵精神遗产。
生活就是这样,当你失去了什么就会加倍地珍惜。希凡先生离去带来的失落在此,今天追思的意义也在于此。
本文收束之际将发之前距希凡离世已近一月,回想10月29日晨接她女儿李芹电话如惊雷震心,茫无所措、思绪纷然,曾草一联今稍修葺,以寄哀思:
大音希声 不同凡响 文坛惊艳小人物
风雨历炼 初心不改 红学痛失压舱石
(注:首句为九十寿辰祝词,末句为多篇悼文题目)
2018年11月15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