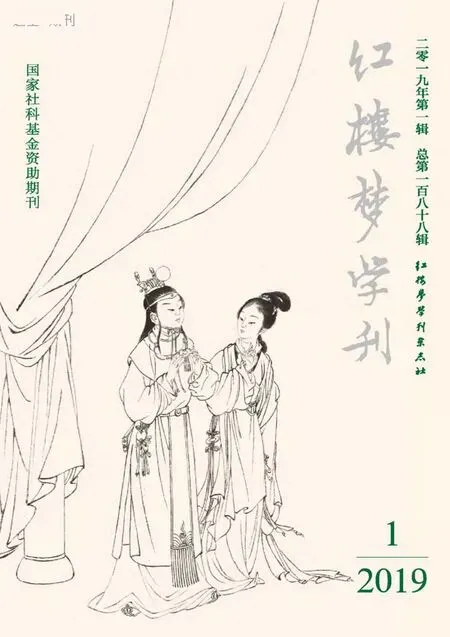平生德义人间诵身后何劳更立碑
——深切悼念李希凡先生
2019-11-12
李希凡先生逝世已一个多月了,我还是无法接受这残酷的事实。在他离去前的十多天,我们俩还通电话,说《红楼梦大辞典》修订事、说《红楼梦》新校本修订事,他还问我10月16日去不去西山参加北京曹雪芹学会举办的重阳节雅集,老先生兴致很高,要我一定去。在他离去前的三天,即10月25日早上,他还给我打电话,说早晨起来检查血糖低,不能去参加《田青文集》的出版发布会了,他感到很遗憾。李老和田青先生是老朋友,他们共同参与了《中国艺术通史》的编撰,李老是总主编,田青先生是分卷主编。在《田青文集》的附卷《田青印象》中,就收有李老给田青的书写的序。李老听说《田青文集》出版,非常高兴,表示一定去。可到了10月25 号早上起来感觉不舒服,血糖低等,我对他说那就不要勉强了。他非常遗憾,要我一定转告田青先生,不仅他本人表示祝贺,还特别强调一定要转达《中华艺术通史》总编委会的衷心祝贺。在这一次的通话中,虽然李老说血糖低,但他的说话声音还是那么清楚有力。第二天在接待韩国红楼梦研究会代表团的朋友们时,我还对吕启祥先生说,李老血糖有点低,但感觉问题不大,电话里说话声音很有底气。后来听说当天他就去医院做了检查,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李老虽然年事已高,大家一直感觉他的身体没有大问题,他的心态好、生活有规律、家人又照顾得好,所以大家对他的健康和长寿是很乐观的,真是没想到他这么突然离开了我们。
李老去世以后,“李希凡”这个名字引起媒体的关注,但在接受媒体的采访和与年轻朋友的交流中,似乎感到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李希凡先生,并不真正认识李希凡先生在学术界、文学艺术界的地位和成就。许多人只知道他是毛主席表扬的“小人物”,如今是学术界的大学者、大人物,除此之外,所知不多。甚至还有人总是把“大批判”“庸俗社会学”等等与李希凡先生联系起来。当你问他,你认识李希凡先生吗?你读过他几本书、几篇文章?他们往往是一脸茫然,竟然根本就没有读过李希凡先生的著述。
在李希凡先生逝世以后,我深切地感到要向人们说说李希凡,要让人们知道李希凡,要让人们知道李希凡是多么了不起,要让人们知道李希凡在中国文化艺术和学术发展的进程中占据多么重要的地位,更要人们知道李希凡是仁慈宽厚的好人。
凡是熟悉李希凡先生的人无不对他的为人极为敬佩,都会说“李希凡是好人!”作为一位有很高知名度的大学者,李希凡先生一点架子都没有,对人非常友善,始终保持着淳朴的品格,他宽以待人、严以律己,我们曾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无不受到他人格魅力的影响,无不受到他的关爱,直到他的晚年、直到他人生最后的路程中,他还是关注着红学的发展、关注着朋友的进步、关注着《红楼梦大辞典》的修订……王蒙先生得知李希凡先生去世的消息,第一时间给中国艺术研究院发来唁函:“沉痛悼念李希凡同志去世,他的为人为友为文,永志不忘。”这是真正认识李希凡先生,这是对李希凡先生的定评。李希凡先生为人为友为文都是值得敬佩的。
我认识李希凡先生四十年了,他是我多年的老领导,也是我十分敬仰的师长。认识李希凡先生,当然是缘于《红楼梦》。记得第一次见到李希凡先生,是1978年,几月份记不清楚了。那是在虎坊桥北京工人俱乐部看电影越剧《红楼梦》,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第一次解禁放映,是轰动一时的大事。那时弄一张这样的电影票很难,因为我的老师林冠夫、应必诚等正在做《红楼梦》新校本的校注工作,他们比较容易搞到票,也使我有机会弄到电影票,最重要的是这一次看电影见到了李希凡先生。那时我们都是以一种崇拜的眼光看着他,不想李先生竟是那么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在剧场里一位崇拜者(一位女士)见到李先生,希望李先生给签个名,可她既没有带笔也没有带本,签哪儿呢?不想这位崇拜者伸出手,李先生一看就笑了,就在这位女士的手上签了名。多年后我和李先生开玩笑,又提起这件事,李先生大乐,却故意说我怎么想不起来有这样的事。自那次见到李希凡先生后,第二年我就从文化部办公厅秘书处调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工作,还有幸参加了中国红楼梦学会筹备的具体工作,使我有了更多的机会见李希凡先生了。再后来他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那时的常务副院长就是实际上的一把手,院长都是文化部部长兼任的,这样他就成了我的领导,见面就更多了,也就更熟悉了。
记得多年前,一位朋友问我:“你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认识李希凡吗?”我说当然认识。他又问:“那你怎样评价李希凡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地位?”我回答说:“今天,人们尽可以对李希凡先生的红学观点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但都不能否定李希凡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上的贡献,都无法抹杀他在《红楼梦》研究上的影响与历史地位。在红学史上,李希凡就是一个时代。”
2013年新年刚过不久,我收到了李希凡先生赠送的新作《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这部“盼望已久”的书。说“盼望已久”,决不是奉承李先生的话,而是发自内心。因为几年前,在我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时候,曾有几年分管文化艺术出版社工作。一次,我对李希凡先生说,能否写一部自传交给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记得当时李希凡先生断然回答:“我是不会写自传的,功过是非让历史去评价。”我表示不同意,我说:“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你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人物。你有责任把你自己经历的事情说清楚,这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你自己负责。你不写自传,别人也会说三道四,与其别人这样说那样说,不如你自己说一说。”当时李先生并没有接受我的建议。2010年或2011年某一个时候,李希凡先生让人带给我一封信,信里说:“庆善,送一瓶野葡萄酒,换一点稿纸如何?”这当然是李希凡先生的幽默,这时我才确切地知道李希凡先生正在写自传。由于老先生不会用电脑打字,还是用稿纸一字一字地写,而且是喜欢竖着写,他特别喜欢当年的那种五百字的大稿纸。李希凡先生小小的玩笑,可让我作了难,我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劲,在院行政处朋友们的帮助下,总算是搞到一点稿纸送给了李希凡先生。所以,我对李希凡先生的自传是盼望已久,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是“事出有因的”。说到这瓶野葡萄酒,李先生还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这酒可不是受贿得来的,是我给朋友的书写序,人家要付稿费,我是坚决不要的。人家为了感谢我,就送了一瓶野葡萄酒。我的葡萄酒可是用序言换来的。”大家都知道,李先生一辈子待人宽厚,是少有的仁慈长者。同时又是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他从不收礼。比如这两年我们修订《红楼梦大辞典》,开完会大家吃一顿饭,都是李先生掏钱。作为学生,我们哪能要老师请客呀,他总是说我工资比你们高。他甚至要拿出5 万元钱交给我,供修订《红楼梦大辞典》使用,我当然不能接受他的钱,但李老对修订《红楼梦大辞典》的期待以及他的宽厚仁慈都让我们深深感动。李先生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出了名的好人,这是认识李希凡先生的人一致的看法。需要指出的是,多少人看过了《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都有这样的感受,自述中充满了坦诚、真挚和自省。你从自述中会感到他为人的正直、真诚、坦荡、宽厚、善良,他是一个充满了真情的大写的人。
写李希凡先生,绕不过1954年那场运动,绕不过如何评价李希凡的学术成就和历史地位。2016年12月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红楼梦学会举办了“李希凡与当代红学学术座谈会”。在开会之前,我向冯其庸先生汇报了要开“李希凡与当代红学学术座谈会”的事情,冯老非常高兴。他与李希凡先生有几十年友情,两位老朋友几十年为红学事业并肩奋斗,曾共同主持了《红楼梦》新校注本的工作,共同主编了《红楼梦大辞典》,还曾长时间共同担任《红楼梦学刊》的主编,他们为新时期红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按照以往,冯老一定会为这个座谈会作诗题字的,但当时冯老年纪太大了,再过两个月就九十四岁了,身体状况也不太好,写字已经有些困难了。冯老虽然没有为这次座谈会作诗题字,但他对座谈会非常关心,冯老对我说:“开这个会非常必要,新中国红学是李希凡、蓝翎开创的。”
确如冯其庸先生所说,新中国红学是李希凡、蓝翎开创的。冯其庸先生曾指出:“李希凡与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标志着红学研究从旧红学走出来,走进了一个新的天地、新的方法、新的理论。也因此找到了新的研究前途。这是红学史不可回避的事实。”的确是这样,李希凡先生研究《红楼梦》始于1954年,他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学典型论评论《红楼梦》中的人物,他说:“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用脱离社会、脱离时代的人性善恶、生命意志,是不能对《红楼梦》中如此众多的典型性格的个性形象,进行准确而透彻的分析的。”“我历来认为,曹雪芹对中国文学史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笔下的‘真的人物’,都是典型环境中的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我还认为《红楼梦》中人物的个性化的艺术创造,堪称世界小说之最。”王蒙先生曾为2013年举办的“纪念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250 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题词:“中国小说第一人。”李希凡先生对王蒙先生的题词极为赞赏,他多次对我说,曹雪芹就是中国小说第一人,王蒙说得好。
不管今天人们对1954年那场批判胡适俞平伯红学观点的运动如何评价,李希凡和蓝翎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开辟了红学发展新里程的历史贡献则是不争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作为自觉地努力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红楼梦》第一人,在六十余年《红楼梦》研究的学术生涯中,李希凡先生始终不渝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和文艺观研究《红楼梦》,始终不渝坚持着自己的一系列基本观点,他坚持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是清朝封建贵族阶级、也是整个封建贵族阶级制度必然灭亡的宣判书,而绝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他坚持认为“色空”不是《红楼梦》的基本观念,《红楼梦》不是“自然主义”的作品,不是曹雪芹的自传。他坚持认为《红楼梦》具有“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红楼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不仅具有着叛逆性,更有着人性的觉醒。这些基本观点,对红学的当代发展产生了长远而广泛的影响。
作为1954年那场运动的当事人,如何评价那场运动,李希凡先生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反对全盘否定的观点,也不否认那场运动存在的问题。他曾说:“对这场运动作历史的结论,是党中央有关部门的事。1980年在济南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谈到1954年问题时,我曾引林则徐赠邓廷桢的两句诗‘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我说:我没有林则徐这样悲观,我要改他这两句诗的两个字,叫作‘青史终能定是非’,我相信这是真理。”多少年来,“青史终能定是非”这句诗常常挂在他的嘴边。他完全赞成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对这场批判运动的评断:“1954年,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又发动了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胡适是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位,这次批判提出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党发动这两次批判(另一次指批判《武训传》),提出的问题是重大的,进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结合实际事例,开展批评和讨论,来学习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种方法。这两次批判,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这两次批判已经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李希凡先生认为这样从正反两个方面来总结这场批判运动,才是有说服力的。
李希凡先生并不否认胡适新红学的历史性贡献,认为:“胡适批评索隐派红学切中要害,但新红学完全不把《红楼梦》看成一部真实、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伟大文学作品,而一口咬定,曹雪芹写的自己的家事——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是‘写闺友闺情的’。他们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考证,虽作出了一定贡献,却大大曲解了《红楼梦》的历史内涵、时代意义和文学价值。1954年对新红学的批评虽有过火之处,却引领红学研究走上了回归文学之路。”他还指出:“‘五四’以前的旧红学,以‘索隐派’最盛行,他们的所谓‘阐证本事’,无非是从历史事实寻找小说中人和事的‘关合’之处,加以附会;至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则完全把小说的内容变成康熙朝政事的隐托,借以抒发他自己的反满思想;胡适虽斥旧红学为‘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但他标榜的‘新红学’,又把小说《红楼梦》完全看成作者曹雪芹的‘自叙’,断定‘贾政即曹頫’,‘贾宝玉即是曹雪芹’;到了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中,则做了更细致的发挥,把小说看成是作者‘感叹身世’和‘情场忏悔’的自传,是一部‘怨而不怒’的书,甚至认为,小说的‘基本观念’是表现‘色空’等等。这些看法我至今仍然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把小说所描写的内容看成是隐托的家事也好,真实的家事也好,都抹煞了艺术的典型概括、典型塑造,贬低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的伟大社会意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阐释的唯物史观的这些基本观点,应该成为我们研究文学现象的科学理论依据。”他认为:“从红学本身的发展来看,从1954年有了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新的开端。……1954年提出的主要观点基本上已被大家接受。……拓宽了《红楼梦》研究的视野,推动了红学在新的历史阶段下的发展。”
关于《红楼梦》的性质,李希凡先生并不否定《红楼梦》中关于爱情的描写,他甚至用十分热烈的语言赞美宝黛爱情,他说:“《红楼梦》究竟是一本什么性质的小说,……《红楼梦》当然是无可否认地写了爱情,而且是用最优美的文字、最炽热的感情、最浓郁的诗意,描写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叛逆性的爱情。《红楼梦》所展现的爱情境界,是中国文学史上其他作品中还没有出现过的,也可以说它透露了新的青春的信息。……但是,用‘爱情小说’这样的名目能概括《红楼梦》的创作意旨吗?《红楼梦》的爱情描写,能囊括它所反映的广阔的社会生活风貌吗?《红楼梦》的思想价值与社会意义,难道仅仅因为它写了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吗?毛泽东同志曾诚誉《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虽然引起当今一些红学家的非议,我却以为,这也不妨作为一家之言。……我总觉得,毛泽东同志给《红楼梦》以政治历史小说的称谓,要比那爱情小说的冠冕更切合它的实际。”
李希凡先生在九十岁高龄的时候与大女儿李萌合著的《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洋洋洒洒五十余万字,堪称巨著。全书分四组,三十三篇文章和一篇很有分量的“修订版后记”。全书“论”了《红楼梦》中几十个人物,有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这样的主要人物,也有晴雯、香菱、平儿等次要人物,还有“大观园丫头群掠影”“十二小优伶的悲剧命运与龄官、芳官、藕官的悲剧性格”以及“漫话茗烟和兴儿的个性化的创造”等等,真可谓琳琅满目、蔚为大观。李老在给我的信中说:“送上《人物论》修订版,标题依旧,有半数以上却是重写,李萌有大功……出版社愿出修订版,以纪念作者之一的离去。痛哉,女儿离去四年,我才知道她早已不在人世。”看到这封信,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2012年10月7日李希凡先生的老伴徐潮老师去世,三个月后,大女儿李萌去世。记得2013年2月1日,丁亚平夫妇请李老吃饭,田青、卜键和我参加,吃饭时李老说大萌病了,情况不太好,其实当时李萌已经去世了,我们都瞒着李老,怕他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他的老伴徐潮老师去世不久,大女儿李萌也去了,这是怎样的人生磨难,我们为李老担心,毕竟他那时快九十岁了,所以要瞒着他。今天想起当时的情景,我的心里难过极了。看着这样的信,看着这样厚重的学术著作,一位九十岁的老人,有如此执着的学术精神,令人敬佩。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认真拜读了这部凝聚着李老父女心血的巨著,深深为李老的学术坚守、学术奋进的不屈精神所感动。这既是李希凡先生最后的一部学术著作,也是对他一生研究《红楼梦》的总结,这部专著的出版无论是对李希凡先生,还是对新时期红学,都是非常重要的收获。
贾宝玉无疑是《红楼梦》中最主要的人物,是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人物形象,凝聚着作者曹雪芹全部心血,因此如何认识贾宝玉也成了认识《红楼梦》的关键。李希凡先生在《“行为偏僻性乖张”——贾宝玉论》中,明确指出:“贾宝玉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主体’人物,是作者许多重要思想理念的主要承载者,是小说中最具时代意义的文学典型。”正因为贾宝玉这个形象在《红楼梦》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而形象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对贾宝玉的认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李希凡先生对贾宝玉的认识和评价无疑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贾宝玉是曹雪芹所创造的在‘天崩地解’的封建社会末世出现的、富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贵族青年叛逆者的形象,而绝不是时代的‘怪胎’,也绝不可能是作者曹雪芹。他具有初步民主主义精神,他关心尊重、真诚地爱戴周围的人们,不论身份的高低贵贱,没有贵族纨绔子弟的玩世不恭、蛮横霸道的恶习,尤其是他懂得尊重女性。在他的心目中妇女不是被压迫、被玩弄的对象,而是世界上最纯洁的人,这在‘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中自然是离经叛道了。”他认为:“‘行为偏僻性乖张’的贾宝玉,一生都在用自己的行动向封建贵族的宗法观念和礼教规范勇敢地挑战,最后用他自己的人生悲剧为我们吹响了向往自由、追求爱情和人性觉醒的反封建的号角。”这些见解都是很深刻的,体现出当今《红楼梦》人物论的最高水平。
读《“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林黛玉论》,我们时时被作者优美的语言、深切的情感所感染。贾宝玉、林黛玉毫无疑问是曹雪芹最为钟情的人物,如果说贾宝玉的形象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是人生体验的感受和人生感悟,那么林黛玉的形象则更多的是情感心弦的拨动。“当远离世间的纷扰,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捧读《红楼梦》之时,小说中的‘精灵’——美丽的女主人公林黛玉,便仿佛踏着缤纷落英,吟着她的《葬花词》寻寻觅觅地向我们走来。那充满诗情画意、竹影婆娑的潇湘馆也随之呈现,我们耳畔也似依稀听到了那孤傲、敏感、纯真的少女在暗夜中低低的饮泣和哀怨的叹息……永远的林黛玉就如此真切地站在面前,引领我们走入她的世界。”李希凡先生对林黛玉的钟情溢于言表。他认为曹雪芹对林黛玉典型性格的创造,达到了形神兼备极其完美的结合。的确,如同李希凡先生所描绘的那样,这个以眼泪、诗词和灵巧雕塑而成的“精灵”——一个美丽、真挚、为爱情理想而生而死的典型形象,必将永生在中国和世界文学艺术史的宏伟殿堂里,也必将在无数热爱《红楼梦》的千秋万代的读者的心中走向永恒……
在《红楼梦》人物论中,如何评价薛宝钗,是一个难题。一是薛宝钗形象的复杂性超过所有《红楼梦》人物;二是在薛宝钗的认识上自《红楼梦》产生以来,就有着很大的争议。李希凡先生认为林黛玉、薛宝钗是《红楼梦》中两个最为成功的艺术典型,认为薛宝钗是一个复杂性格的封建淑女的典型,丝毫不逊色于林黛玉,“薛林双绝”凝聚着作者精湛的审美理想的概括,但他不同意“钗黛合一”的观点,认为二人性格、情志迥异,各具不同的人生底蕴和精神内涵,反映着各不相同的社会人生意义和美学价值。他还进一步指出,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绝非是一个概念化的、功于心计的“冷美人”,她的冷是冷在内心深处的伦理观念和生活哲学上,这是很深刻的见解。
读李希凡先生的《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如饮美酒,时而感到痛快淋漓,时而感到美妙无比。他论《红楼梦》决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活脱脱的形象和细节出发,他为了论好一个人物,在每篇文章中都对所论的人物建立一个档案,论得细腻深刻,又观点鲜明。他十分注意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层次发展及其复杂丰富的心理世界。《〈红楼梦〉人物论》,体现了李希凡先生最新的研究成果,展现了新时期红学《红楼梦》人物研究的高度和深度。这实际上也是李希凡先生对《红楼梦》解读的心血结晶。他说:“我们深知,《红楼梦》的感人肺腑,魅力无限,在每个读者心中都装有一部令自己感动的《红楼梦》。《红楼梦》的博大精深,早已凝聚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情结’,深深植根于你我的心灵之中。……这本《〈红楼梦〉人物论》,虽然只是写出了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出了我们的感动和爱憎,但终极目的还是试图解读这部伟大杰作的真、善、美。”
李希凡先生有着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理论修养,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文学典型论深有研究,对俄罗斯“别车杜”的文艺思想也非常熟悉,尤其对鲁迅的文艺思想认识很深刻,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运用自如,时有创意,多有新见。今天李希凡先生论《红楼梦》人物,既有不改初衷的学术坚守,又有新的发展和丰富。他的学术见解更显厚重、全面、细腻、深刻,确实开拓了《红楼梦》人物研究的新境界。在当今的学术界,像他这样论述《红楼梦》人物之多、之细、之深,是很少见的。
李希凡先生晚年最关心的两件事:一是修订《红楼梦大辞典》;二是修订《红楼梦》新校本。在他逝世的前十几天还两次给我打电话说起这两件事,要我负起责任。他说吕启祥先生、胡文彬先生年龄都大了,他们会帮助你,但具体工作还得你来做。我说《红楼梦大辞典》的修订,我一定努力完成。至于《红楼梦》新校本的修订,我怕是干不动了,但我会记住你的嘱托,与孙伟科、与红楼梦研究所的同志好好研究修订事宜,在吕启祥、胡文彬两位先生的指导下,争取完成你的心愿。没想到半个月以后,李老竟仙逝西去,每每想起就格外难过,心里非常沉重。
几十年来李希凡先生不忘初心,不改初衷,始终不渝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典型论,这种坚持、这种高尚的学术品格是令人敬佩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毫无疑问,李希凡先生是新中国以来最负盛名的红学大家之一,是开创一代风气的学术巨擘,李希凡先生的红学观点,影响了一个时代,至今仍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和地位。我们可以说,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研究开创了一个时代,他们毫无疑问是新中国红学第一人。
今天是李希凡先生九十二岁生日,谨以此文深切缅怀敬爱的李希凡先生。
2018年12月11日于北京惠新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