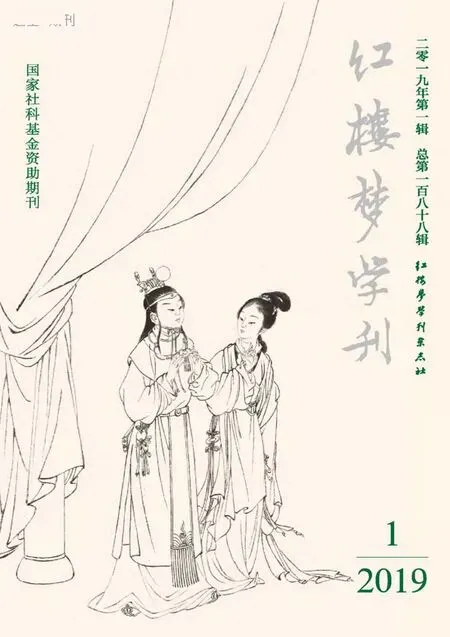从“西昆体”到“长吉体”①
——由诗风的转变看贾宝玉的成长
2019-11-12
内容提要:在《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成长是曹雪芹创作的着力点,为了塑造他的成长,曹雪芹是通过多个侧面的描写来进行的,其中诗风的转变是重要的一环。从最初的“西昆体”至后期的“长吉体”,无不是曹雪芹体现贾宝玉性格及思想在成长中不断变化的重要依托。对人物诗风与性格及思想的关系,可以深入分析曹雪芹借诗词来体现人物成长与变化的意图,并通过人物成长来揭示人在成长中思想会不断转变的必然性。
《红楼梦》是一部成长型小说,主人公贾宝玉以及主要人物,都会随着情节的展开而有所变化,由此可见曹雪芹写人写事的匠心独运。其中贾宝玉这个主人公如何随着时间、情节的推进与发展,不断的成长或变化,更是全书人物刻画的重中之重。而如何来体现贾宝玉的成长,曹雪芹不仅仅以人物外貌、形体的变化为基点,而是通过更为隐秘的变化来体现,如世事磨砺、思想变化、诗词风格的转变等。本文拟从诗风的变化入手,来展现贾宝玉在小说中的成长历程。
一
《红楼梦》第十五回,北静王与贾宝玉初次相见,即赞宝玉道:“将来‘雏凤清于老凤声’,未可量也。”这句赞誉,脂批作者点明:“雏凤清于老凤声”是西昆体! 而贾宝玉闻听北静王引用西昆体,便对其刮目相看,这就说明贾宝玉对于“西昆体”是极其推崇和认可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书中的诗词与人物性格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那么,什么是“西昆体”呢?田况在《儒林公议》中评曰:“杨亿在两禁,变文章之体,刘筠、钱惟演辈皆从而效之,时号杨刘。三公以新诗更相属和,极一时之丽。亿乃编而叙之,题曰《西昆剧唱集》,当时佻薄者谓之西昆体。”后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深入地分析了西昆体与李义山的关系:“咸平、景德中,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而杨文公与之鼎立,绰号江东三虎。诗格与钱、刘亦绝相类,谓之西昆体。大率效李义山之为,丰富藻丽,不作枯瘠语。”总之,“西昆体是以李商隐为主要师法对象,用词廉丽、文辞典雅的一种诗歌创作风格。”这一诗歌流派,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首的十七位宋初馆阁文臣互相唱和、点缀升平的诗歌汇集而成。在延续晚唐五代的诗风的同时,艺术上大多师法晚唐诗人李商隐,但更多的是片面承继了李商隐追求形式美的倾向,其诗风格雕润缜密、声律和谐、对仗工稳、辞藻虚浮、华赡富美。总体而言,西昆体诗歌思想内容贫乏空虚,缺乏真情实感,脱离了社会现实,给人一种似是而非,言此意彼,迷离恍惚的感觉。
西昆体孕育于宋初馆阁唱和之风,追求辞藻,堆砌典故,文字绮丽,大多内容空洞,备受北宋诗文革新人物批评,但这一流派“创造了以典雅为美的诗歌范式,这种典雅美对宋诗的发展具有引导作用,以后的诗歌大家都从此得到涵养”。因此,欧阳修在他的《六一诗话》中写道:“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金代元好问也曾赞曰:“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总之,西昆体对宋诗的发展流变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其文学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且它在唐宋诗之间不仅起到了承前启后的特殊作用,对后世诗词的影响也是颇为深远的。
《红楼梦》第一回有脂批明言“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为传诗之意。”且用茅盾先生比喻的“按头制帽”来说,书中穿插的诗词曲赋都具有人物的鲜明个性,如风流别致是黛玉的风格、含蓄浑厚是宝钗的风格等等,这些对于塑造人物形象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第一主人公贾宝玉,他的诗词什么风格,应是曹雪芹着重关注的。据脂批所示,贾宝玉是极其推崇和认可“西昆体”的,因此,也可以说贾宝玉这个人物成长过程中的诗词风格必然在某一阶段会有“西昆体”的影子。如第二十三回宝玉所写的四首即事诗,就有着声律和谐、对仗工整的共同特点,且用词靡丽,华美妖艳,虽多用典故,却语意轻浅,内容空洞,正是典型的西昆体。这四首是分春夏秋冬四季而写的即事诗,真实地记录了宝玉初入园时与众女儿相亲相近的生活情景,不仅从侧面烘托了人物的性格,还恰当地体现了此阶段宝玉的心境情性。
《春夜即事》运用了移步换景的手法,从“霞绡云幄”“枕上轻寒”的室内,到“隔巷蟆更”“眼前春色”的室外,都是对于春日的描写,而“盈盈烛泪”的“泣”,“默默花愁”的“嗔”,以及后两句的“小鬟娇懒”“拥衾笑言”,都是非常形象的描写了宝玉眼中的女儿情态。此诗用词绮丽,然而思想空洞,仅是宝玉对春天及身边人事最直接的感触。《夏夜即事》中涉及六个丫鬟,“袭人(“佳人”的隐指)、鹦鹉、麝月、檀云、琥珀、玻璃”,或是贾母身边的,或是宝玉身边的,她们日常伴随宝玉较多,因而被信手拈来嵌入诗中,可说是最乏味的诗材,难免有借以填补长夏之寂寥的嫌疑。而“唤茶汤”“开宫镜”“品御香”“纳风凉”等,都是宝玉着力渲染大观园生活奢华闲适的一种措辞。《秋夜即事》中所运用的“桂魄流光”“桐露栖鸦”则是描写秋日风光最滥用的典,虽是借景抒情,却景浓而情淡。“抱衾婢”和“倚槛人”也是泛用之辞。全诗写秋,而并无秋意,满篇堆砌之感。
《冬夜即事》较之前三首,略有深意。全诗用岁寒三友之“梅、竹、松”来烘托渲染冬日雪景,在体现了三者傲雪迎风的风骨之时,也与“鹤”“莺”之动形成动静结合之感。但颔联的由景及人,由物及人转换过急,似有意断之嫌。且尾联的“新雪烹茗”与《秋夜即事》中的“沉烟烹茶”有重叠之意。因而也可看出宝玉对于作诗素材的驾驭,以及对于诗词的用语、修辞、意境等方面的把握都是非常稚嫩的。
但也正因上述这些个性特征,才更符合宝玉这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公子形象,不仅能够恰当地反映出这个“富贵闲人”悠闲自在、吟风弄月的日常生活,也能表现他在这个特定阶段的思想状态。事实上这也是曹雪芹的高明之处,正所谓“诗如其人”。对于这四首风格显著,颇具代表性的即事诗,脂批评曰:“四诗作尽安福尊荣之贵介公子也”,所以“当时有一等势利人……抄录出来各处称颂,再有一等轻浮子弟,爱上那风骚妖艳之句,也写在扇头壁上,不时吟哦赏赞。因此竟有人来寻诗觅字,倩画求题的。宝玉亦发得了意,镇日家作这些外务。”由此可见,这些轻浮子弟、势利人等的追捧,让宝玉对自身这种西昆诗风颇为得意,而这正是曹雪芹用诗词塑造人物的点睛之笔。
其实,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节中宝玉所做的四幅对联,“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新涨绿添浣葛处,好云香护采芹人”“吟成荳蔻才犹艳,睡足酴醿梦也香”,就已初步显现了他的这种风格。这四联无论对仗声调,还是节奏词藻,都严格遵循了对联的“形稳、音稳、义稳”,构思方面也称得上新奇别致,这无疑说明宝玉在诗词方面的极高天赋,并且突出了宝玉性格中的敏与慧。敏,是指他对万物、景观、人事的敏锐和敏感;慧,是指他在诗词方面的灵慧、聪慧、颖慧。但内涵才是联语真正的灵魂,诗言志,词缘情,对联亦然,优秀的联作能够充分地表现出作者的思想、胸襟、情操和感触。但细品之后会发现,宝玉的这些对联显然还未达到如此高的境界,所以脂批评其虽是“恰极,工极”,但用词“绮靡秀媚,香奁正体”,总难失“香奁格调”。端方严肃的贾政也认为宝玉是管窥蠡测,“专在这些浓词艳赋上作工夫”。所以,此阶段宝玉对对联的拟作充分说明了他正处于诗词学习的初级阶段。
同一时期内,在元妃省亲时宝玉还作了三首应制诗,分别题写的是潇湘馆、蘅芜苑、怡红院三处。虽然这三首诗一洗前文多首应制诗的颂圣之风,但终究难脱西昆之韵。如“迸砌防阶水,穿帘碍鼎香”“软衬三春草,柔拖一缕香”“绿蜡春犹卷,红妆夜未眠”等,不仅对仗工稳,而且辞藻华美,都可隐约看到西昆体的影子。这些特点不仅体现了宝玉性格中着意闺阁、不通世务的一面,也体现了宝玉作诗设色浓丽而富有感性,颇具李商隐的“沉博绝丽”之风。尤其最末一首《怡红快绿》更是深得西昆体之精要,不仅雕润缜密、声律和谐,且对仗工稳、深情绵邈。也难怪脂批赞曰:“双起双敲”又“双收”,既解“海棠之情”,又察“芭蕉之神”,不仅“极工极切”,且“极流离妩媚”。
总之,此阶段的宝玉是个标准的“富贵闲人”,在祖母的溺爱和母亲的宠惯下,无忧无虑地徜徉在与世隔绝的大观园中,每日关心的不是这些姐妹在想什么,就是那些丫头在做什么,对人生、对世界,基本都还处于浮浅的混沌中,并未形成一定的认知体系。所以,此一时期他的诗词风格更趋近西昆体,无论是对联、应制诗,还是即事诗,都是内容相对空虚浅显,缺乏真情实感的同一类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孩提式的懵懂终将远去,宝玉的诗词风格也必将随着阅历的增长而不断转变。
二
贾宝玉是具正邪两赋于一体的“情痴情种”,在红尘中造幻历劫是他一生的追求与磨难。至于如何造幻、历劫、曹雪芹都是以他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为基础而展开的。通过他自身对“情”与“世事”的认知的不断改变,来充分体现他如何悟情、悟世。
书中有关的情节以第二十一回和第二十二回中的续庄、禅悟最为醒目。这两回主要描写了宝玉与袭人、黛玉、湘云等在日常的耳鬓厮磨中所不断发生的摩擦与纠葛。这些小摩擦都给予宝玉细微的感触,使他对于世俗的抵触,对于情的执着更加强烈。而在这种种纠葛中,宝钗与黛玉给予他的点醒,则让他对“情”和“世事”也有了一些深入地思索。他虽然一心受享着花柳繁华、温柔富贵的惬意生活,但也在努力的辨识、蜕变。宝玉是聪慧的,也是敏感的,这一切外物带来的烦恼和搅扰,让他对“人生而为人”有了更多的迷茫和疑惑。因而对身边的人或事,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但以他此时的经历和认知远远不能了悟此中蕴含的玄机,所以使他一度陷入自我认知的困境,从而产生了无限惆怅。究其缘由,还是为情所累,为世俗的牵绊而苦恼,他的《续〈庄子·胠箧〉文》和《参禅偈》《寄生草·解偈》,也是反复强调这一点。因此,他和众人的纠葛,都是作者为了呈现宝玉如何成长而刻意所做的铺设。
对于袭人以柔情警之的劝诫,宝玉的“恶劝”癖性更进一步,不但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结,反而更加弄性尚气,感慨自我之心无人理解,无人可诉,甚至续作一篇《庄子·胠箧》,狠下心来,“权当他们死了,毫无牵挂,反能怡然自悦”。对于宝玉种种不为世人所解的乖僻行为,脂批作者深有感触的评曰:“宝玉悟禅亦由情,读书亦由情,读庄亦由情。可笑!”并进一步指出宝玉此等行为,正是“暗露玉兄闲窗净几,不寂不离之工业。”他每日尽心尽力为众姐妹丫头善意斡旋,不想调和未成,反落了多处贬谤。细想自己劳心劳力,“目下不过这两个人,尚未应酬妥协,将来犹欲为何”,情绪低落的宝玉,观眼前思前日,多情反被情困,那种“知音不易得”的难言之苦,再次涌上心头。此情此景,正与他所读《南华经》上的“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相契合,于是内心更增添了一份惆怅,所以又感而占偈:
你证我证,心证意证。
是无有证,斯可云证。
无可云证,是立足境。
写毕,又恐人还是不解,更填一支《寄生草》,以表其心。脂批作者对宝玉是颇为理解的,所以评曰:“前文无心云看《南华经》,不过袭人等恼时,无聊之甚,偶以释闷耳。殊不知用于今日,大解悟大觉迷之功甚矣。”前续《庄子》,后占一偈,更填一曲,皆因闺阁闲情而起,剪不断理还乱。说到底,这些都是宝玉一种寻求知音的追问,庄子提倡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崇尚自然之精神,则成为他借以宣泄的一个媒介,是为“打破胭脂阵,坐透红粉关”。因一出《寄生草》而偶然参禅,在外人眼中是宝玉的“疯癫”之症在作怪。但这也充分说明,宝玉天性中那一种追求精神自由的意念在不断复苏。
宝玉被姊妹们戏称为“无事忙”,事实上他是“事事忙”,只是他所忙之事,不是八股学问,不是仕途经济,而是闺中情事。正如脂批所说的“宝玉是多事者,情之事也,非世事也”。较之宝玉先知先觉的钗黛二人,对于宝玉的这些文字是可笑又可叹。而钗黛二人的点醒,让他做到了发乎情止于情,不再纠结其中。这段宝玉因感情纠葛而引起的困扰和苦恼,仅仅是宝玉在茫茫红尘中造幻历劫的第一步,这颗根植于思想深处的种子,并未停止萌发,随着宝玉精神世界的不断丰富,终将继续成长、慢慢成熟。
至黛玉伤春葬花之时,那声声诉愁、字字泣血的《葬花吟》,更是给了他强烈而深刻的启发,使他对人、对外物、对茫茫尘世的感触步步加深。那种欲罢不能,欲说还休的难言之痛,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深入地折磨着宝玉。其实,这也是宝玉成长中又一次重要的思想蜕变。他对黛玉的体贴,对诸钗的体贴,对人间万物的体贴,已经达到无我的境地。因为体贴,所以懂得。因为懂得,所以他更加深陷于对情、对世事的参悟之中,并且以花推人,由景及人,以黛玉推及诸钗,以花冢推及整个大观园,来体悟整个尘世中的繁华与消亡,青春与衰败。只是宝玉这个体悟的过程是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的。因此,宝玉的诗词也随着他日趋成熟的思想发生了质的转变。第三十八回的《螃蟹咏》和第五十回的《访妙玉乞红梅》正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但较之他前期用词绮丽的西昆诗风,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
其一,第三十八回的《螃蟹咏》:
螃蟹咏·其一
持螯更喜桂阴凉,泼醋擂姜兴欲狂。
饕餮王孙应有酒,横行公子却无肠。
脐间积冷馋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
原为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
对于书中三首螃蟹诗,前人大多着眼于三首之冠宝钗的那首,对于宝黛二人的两首却多认为是第三首的陪衬,是为末首作引,所以多不曾细究。但以曹雪芹惜墨如金的行文风格,前两首也绝不仅仅是陪衬那么简单,尤其开启螃蟹之咏的宝玉一首,出现在此处也应有很重要的作用。这首诗写的感情充沛,酣畅淋漓,醋用“泼”,姜要“擂”,因馋而忘忌,视腥而为香的“王孙”“公子”,品蟹之时简直就如“饕餮横行”一般贪婪。全诗借咏蟹来直抒胸臆,豪放明快,真挚而生动,说明此时的宝玉,作诗已不再局限于追求辞藻华美,而更注重情感抒发。总之,此时的宝玉心甜意洽,对于黛玉的讥笑和宝钗的讽刺,都不以为意,一心沉浸在快乐中。
其二,第五十回的《访妙玉乞红梅》:
第五十回“芦雪广即景联诗”宝玉再次落第,但却被罚的雅致有趣,不仅要折枝红梅,还要作诗一首。但曹雪芹笔有曲意,并未直接写宝玉如何“访”,如何“乞”,而是把宝玉此次的踏雪寻梅隐匿在一首诗之中,真可谓别出机杼,一击两鸣,不仅给人以美轮美奂的意境美,更是在完成情节延续的同时,深入地刻画了人物性格。
酒未开樽句未裁,寻春问腊到蓬莱。
不求大士瓶中露,为乞嫦娥槛外梅。
入世冷挑红雪去,离尘香割紫云来。
槎枒谁惜诗肩瘦,衣上犹沾佛院苔。
这是一首典型的叙事诗,韵属上平十灰,仄起入韵。整首诗章法布局清晰可见,遣词造句清新雅致,语言直白易懂,诗词风格倒略有几分“元白体”的“浅切平易之风”。全诗以宝玉的踏雪寻梅而起,乞得红梅而归,处处流露出宝玉的真情实感。且情节完整而集中,人物性格突出而典型,有浓厚的诗意,又有简炼的叙事,做到了情因景生、以景衬情、借景抒情的完美交融,可谓浑然天成。此时的宝玉不再像前番一样借故参禅,凭空而思,而是脚踏实地地享受着身边最真实的快乐,并把这种快乐在以诗的形式尽情的挥洒,他的诗风也明显走向平叙抒情两者兼顾的更高境界。同时,这也说明宝玉的精神境界已提高到一个追求朴实真诚的层次。那枝杈纵横颇具凌厉之姿的红梅,是妙玉“天生成孤僻人皆罕”的性情写照,更是对“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的宝玉的性情反衬。只是此时此刻的宝玉,浑然不知有朝一日,他也会被世俗逼迫到无立足境,从而摆脱“入世”与“离尘”的矛盾折磨,成为一名绝尘而去的“槛外人”。
三
在书中贾宝玉“禀性乖张,生情怪谲”,既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对于曲意逢迎贾府众人的贾雨村,他充满抱怨和不耐烦。所以,他作诗最不喜备感束缚的拟题限韵。但在作《姽婳词》时,却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构思,且立意新奇,寄托深远,用辞也多有意外之笔。可以说宝玉作《姽婳词》这一情节非常重要,不仅体现了宝玉的诗词功底已经今非昔比,而他对于世俗应酬之事也不似先前那样抵触,而是能够隐忍的应对。贾政对宝玉作诗态度在此回有明显转变,一是他认为,宝玉天性聪敏,诗风空灵娟逸,杂学远超环、兰叔侄;二是宝玉在官宦宴饮中和众幕友前的表现应对自如,且表现不俗。所以,当宝玉说《姽婳词》拟题“须得古体,或歌或行,长篇一首,方能恳切”时,贾政是赞同的。而且宝玉用意拟古,也确实做到了半叙半咏,流利飘逸,言有尽而意无穷。《姽婳词》全诗共四十六句,转韵八次,大致分为四个层次,从起承转合,到辞典运用,夹叙夹议,层层深入,直至抒怀,都具备歌行体的风神气骨。第一层从“恒王好武兼好色”至“脂痕粉渍污鲛鮹”,写恒王和林四娘与众不同的闺阁情趣;第二层从“明年流寇走山东”至“月冷黄沙鬼守尸”,写流寇之窜与恒王之死;第三层从“纷纷将士只保身”至“马践胭脂骨髓香”,写林四娘如何战死沙场;从“星驰时报入京师”至结句为第四层,写世人对林四娘忠义报君的赞美,以及宝玉无法抒写的无限惆怅。宝玉所感从晴雯之死而起,以林四娘之死为喻,以赞颂忠义为明,以体贴女性为暗,做到了情境交融,人诗合一,一洗他旧日“西昆”之艳丽轻浮。但表面上,宝玉不仅做到了贾政以“忠义”赞颂林四娘的目的,也为贾政面上更增添了光彩。所以,众清客相公交口称赞“妙极,妙极! 布置,叙事,词藻,无不尽美”的时候,刻板的贾政也一改往日的严厉,亲自执笔为宝玉抄录誊写。但宝玉终究是宝玉,他内心深处依然是不愿与仕途之人结交的,也不愿真正的踏上追求仕途经济的道路,他骨子里那种与世俗难以妥协的乖谬之气终究存在,只是他在经历了诸多历炼之后,有了些许缓和的表现。但这些绝不能代表他已经对世俗真正妥协。那种被世俗沾染之后,失去人性本真的“鱼眼睛”“禄蠹”之流,在他看来,依然是难以接受的。而不曾被世俗所沾染的女儿们,依然是他要体贴和守护的对象,就便为这些人、这些事死了,他也是情愿的,并且这种“痴”会随着他对世俗认知的深入而更加坚定。虽说林四娘之忠勇,正如宝玉心中的晴雯之忠勇,但终究是依命而作,且作于宝玉刚刚获知晴雯新逝之时,那种因被父母约束而不得送别晴雯的满心凄楚和无以名状的哀思,并不能尽情的表达。所以,他只是借题发挥,以表达对晴雯新逝的冥冥愁绪,这种表达,有痛心,有不舍,有隐忍,也有无奈。也正因这种郁抑不申的悲痛,让宝玉把难以明言的情感融于诗中,用古喻今,以抒发宝玉对生命短暂美好易逝的深深感触。虽然此间有清客赞宝玉“当日敢是宝公也在座,见其娇且闻其香否?不然,何体贴至此”是歪打正着,但也确实写出了宝玉平日对闺阁女子的体贴,诸如对平儿理妆时的体贴、对鸳鸯抗婚的体贴、对龄官画蔷的体贴、对香菱弄污石榴裙的体贴,等等,无不体现了他对拥有高贵品格的女性的同情、爱怜,只是这种同情爱怜,是世人所不能理解的,所以一直被误认是乖僻之举。
透过林四娘,宝玉仿佛看到了晴雯,也仿佛看到了与林四娘具有同类品格的大观园众女儿的身影。对于花鸟鱼虫,尚且怜惜哀叹,更何况对于这些高贵品格的女儿,所以诗中或明或暗都显露出的宝玉对女性的体贴之情,也是他性格中“情不情”的一笔重要描写。全诗诗眼“丁香结子芙蓉绦”句,更是直指晴雯的“芙蓉花神”之说,而诗末的“我为四娘长太息”句,不仅写明了宝玉对林四娘之死的一声长叹,更是暗寓了宝玉对晴雯、司棋、芳官命运多舛的一声长叹,甚至也是对林黛玉等一众女儿未知命运的一声长叹。所以,这首诗不仅仅是赞颂林四娘,而应是饱含了宝玉对女性的终极体贴之情。结句的“歌成馀意尚傍徨”,更是把那种诗罢情未了的悲痛,化为一抹醒目的留白。
晴雯之死,让宝玉大受震动,也让宝玉意识到他生命中最不能承受的苦痛在源源不断地逼近。从金钏之死到晴雯之死,再到遗失后文中的黛玉之死,层层递进,不断苦苦相逼贾宝玉脆弱的心灵,而他的苦痛不能为人所理解,只能默默承受。而这不能承受之痛,压得他无处可藏,进而迸发出对人性、人生、现实的震天诘问。所以,《姽婳词》是《芙蓉女儿诔》(后文简称《女儿诔》)之前作者的重要顿笔,藏锋于无形之中,但又笔断意连,终是为《女儿诔》做以铺垫。与作《姽婳词》时被世俗之人群相环绕的情景相比,写《女儿诔》时的宝玉才是最真实的他,因为他已经摆脱了众人的束缚和世俗的羁绊。此时此刻,宝玉对于晴雯之死的悲戚,在隐忍、拖延、憋屈、无奈中的不断膨胀,已经达到了爆发的边缘,他终于可以把那伤感到极限,哽咽到无声的情感百无禁忌的悲鸣为一首当哭长歌,洋洋洒洒抛向天地之间。这首饱含深情的《女儿诔》,充分说明了世俗的压力也罢,世人的侧目也罢,宝玉都绝不会为此而改变自己的本心,即使有再多再大的压力,他也终究不会妥协。
《姽婳词》的出现,是命题成诗,是遵命而为,是世俗的逼迫,所以是被动的。而《女儿诔》则是有感而发,是痛心而作,是情感的倾诉,是主动的,也是势在必然。因此,在宝玉的生命中,世俗与情感的相搏自始至终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在宝玉的思想上,情与理的冲突也是不曾间断的,而宝玉的选择显而易见,终是以情起,以情悟,以情而做结来完成这一世的造幻历劫。
《红楼梦》中宝玉的祭奠观是别具一格的,他认为“……逢时按节,只备一个炉,到日随便焚香,一心诚虔,就可感格了……他们皆不知原故,我心里却各有所因。随便有清茶便供一钟茶,有新水就供一盏水,或有鲜花,或有鲜果,甚至于荤羹腥菜,只要心诚意洁,便是佛也都可来享,所以说,只在敬不在虚名。”所以他躲开凤姐生日的热闹,跑至那人烟稀少的水仙庵,用贴身的散香以表对金钏的哀思。但与晴雯相较,金钏和宝玉的关系,要疏远得多。所以,宝玉祭奠晴雯的方式,虽相类,却更严肃、庄重。此一祭目的全在心之诚敬,“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且诔词须得“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使文不足悲有馀,万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因而任意纂著出这如泣如诉的《女儿诔》。
这篇诔文共一千三百七十六字,字字珠玑,声声泣血。前叙后歌,叙语凄凄,歌言潇潇;前骈后骚复转骈收,骈文对仗工整而声律铿锵,骚赋情深意切而浪漫洒脱。这篇诔文,无论在构思、意象方面,还是在遣辞、设色方面都表现出“长吉体”新奇独创的特色。其间嵌入多个神话传说和名人轶事,运用怪诞华美的语汇,表现独特的艺术想象,营造出虚荒诞幻思想境界,使全篇充满伤感冷艳的格调,从而抒发心中复杂的情感。较之宝玉前期的虚浮艳丽,这首诔文达到了宝玉诗词创作的巅峰,字字句句无不凸显出宝玉破茧成蝶后空灵娟逸的诗词风格。无法排遣的悲痛充满宝玉的精神世界,从群花之蕊、冰鲛之縠、沁芳之泉、枫露之茗的四者微物,到质如金玉、性如冰雪、神如星日、貌如花月的终极盛赞……宝玉让天地间所有神灵贤士为女儿所驱,集一切美好事物为女儿所饰。在宝玉眼中心里,集天地精华之灵秀的唯有这些青春女儿,即使倾尽世间所有都不足以形容他心目中的女儿之美。面对池上芙蓉,宝玉任由自己思绪翻飞,彻底放纵自我,此时的他才是最真实的他。《女儿诔》道出了他对世俗、对人性的最深理解,也道出了他对青春女儿的无限爱怜。
他痛斥那令人憎恶的“鸠鸩”“薋葹”,叱责那令人痛恨的“诐奴”“悍妇”,但无论他怎样悲愤,终究无法改变现实,只能把对女儿的无限爱怜化作一种恍惚游离的情绪,借叶法善之笔、李长吉之墨、素女之瑟、弄玉之箫、宓妃之曲、寒簧之敔……融合于梦中乾坤,来赞颂那“闺帏恨比长沙”“巾帼惨于羽野”的女儿精魂。他成长了,也醒悟了,他明白人生在世,缘聚缘散不过瞬间,只是他不愿面对,不愿正视这种人生的本质。晴雯已死,司棋、芳官、四儿等已去,宝钗为避嫌匆匆搬离,温柔可亲的二姐姐也即将出嫁。宝玉眼见热闹要走向孤独,青春要走向衰亡,繁华要走向破败。而他却无能为力,任由那“寥落凄惨之景”噬咬他的心灵。晴雯因谤而夭,是宝玉最大的哀痛,也是宝玉珍爱的纯真在世俗面前的夭亡,因此他满腔的激愤无法释然。所以,他要诔祭芙蓉花神,诔祭风流灵巧的晴雯。事实上,这也代表着他诔祭即将泪尽而逝的黛玉,诔祭那终将风云流散的大观园众女儿。
宝玉成长的心路历程是漫长的,也是曲折的,流过诸多眼泪,遭遇诸多挫折,他排斥,他拒绝,他曾努力尝试着摆脱这个现实,但现实终究是无法摆脱的。也正因这些挫折与折磨,才能使他更深的感受生命的本质,感受人生的不易,感受到那由盛及衰的趋势,却又一筹莫展的看着它走向灭亡而无可奈何。现实依然如故,生命依势运行,宝玉终究要长大。他的成长,除了对“情”的体悟,还有对世事的感触,但他对于“真善美”的本真之追求,是坚执不变的。而宝玉诗风的转变正体现了他对世事的感触和思想的转变,作《四时即事》是他在体味生活与现世的美好,作《访妙玉乞红梅》是他在了解入世与离尘的不同,作《姽婳词》是他在反思历史与现实的严酷,作《芙蓉女儿诔》则是他已经下定决心,决不与世俗妥协。或者可以说,宝玉学习诗词的过程,等同于他思想成长的一个过程。
追忆往昔,谁曾料那为解新愁强参禅的偈语,会成为宝玉一生的谶词。从最初的追求华丽,到领会流逝,到想要留住一切,再到难以哽咽面对,一步步走向无以立足的境地,最后不得不摒弃一切,毅然决然的悬崖撒手而去。此时的宝玉对于真与幻、盛与衰、好与了、生与死的感悟,已经深刻的生成为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孤独。说他情极之毒也罢,说他为世人所不忍为也好,他都已不在意。这种遗世独立的孤独,更加促使他没有任何顾虑的走向那一片白茫茫的广袤大地。
结 语
宝玉在成长,思想也在转变,从最初的西昆体,到前八十回中最终的长吉体,他的诗风在转变中趋于平稳。诗风的平稳,也说明宝玉思想的成熟,他倾尽全力而作的《女儿诔》,可以说是他的巅峰之作,也可以说是曹雪芹的心血之作。通过对《女儿诔》的深析,我们或可从中窥见曹雪芹的诗风。雪芹生前好友敦氏兄弟,就常在他们的诗词中把曹雪芹比作李昌谷,称其“诗笔有奇气”“诗胆昔如铁”,其中“牛鬼遗文悲李贺”句被敦诚运用过两次,可见曹雪芹与李贺在诗才方面确实是极其相像的。另外,除了《红楼梦》,曹雪芹仅存于世的两句题敦诚《琵琶行传奇》诗:“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其中的“诗灵”和“鬼排场”的用词,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想象力丰富,诗才诡谲的李昌谷,这种极度的相似绝非巧合,应是曹雪芹本人诗风更贴近长吉体的明证。而贾宝玉是曹雪芹倾心而塑的人物形象,他应是曹雪芹思想与灵魂的最大寄托。所以,他把自己最为推崇,也最为得意的长吉体,赋予宝玉,让他化身为《红楼梦》中的自己,从而借宝玉之笔,悼晴雯,悼黛玉,悼一众闺中女儿,也是悼念那逝去的一切。
如果说贾宝玉百分百等于曹雪芹,那是不恰当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贾宝玉这个人物确是曹雪芹思想的最大承载者。曹雪芹丰富的人生经历,激发了他对人、对事、对现实产生诸多的人生思考,当这些思考不断凝炼成型的时候,也就促进了《红楼梦》的问世。所有这些思考引起的感悟,一定也是经历了从浅显到明晰,再到深入骨髓的一个漫长过程。而如何体现这个过程,曹雪芹最终选择以人物成长的形式来体现。因此,从贾宝玉的身上,我们或多或少可以看到现实中曹雪芹的一些影子。贾宝玉不断成长的人生历程,其实也是曹雪芹不断思考人生的思想历程,而他所经历的那些磨难和挫折,或者就是曹雪芹亲身经历过,或者至少是引起他深入思考的人生疑问。所以通过贾宝玉的个人成长历程,我们可以了解曹雪芹的思想转变,也可以了解他想要表达什么。而研究曹雪芹的思想,也就是研究《红楼梦》的意义所在,同时也是研究他们带给世人的启示中蕴含着怎样的人生哲理和智慧。虽然世人都认为,所谓的成长就是因世俗的消磨而慢慢变得悲观、冷漠、现实,但《红楼梦》不同。在曹雪芹的眼中,那些在经历岁月风蚀之后,依然坚强不退缩,依然保持人性本真的人才是最值得赞颂的。贾宝玉便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成长了,也成熟了,但不论是在锦衣玉食、珠环翠绕的曾经,还是在“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的未来,他都依然是那个永葆初心的少年,这也是他能够成为《红楼梦》第一主人公的重要因素。
注释
① 本文出现“西昆体”和“长吉体”的提法,仅是为了概括贾宝玉成长过程中初期的诗词风格和后期的诗词风格是与“西昆体”和“长吉体”有一定的近似性。
②⑫⑮⑰⑳㉑㉒㉕㉖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吴铭恩汇校《红楼梦脂评汇校本》,万卷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78、295、293、267、281、280、282、473、601、74、76、71、955、957、956、701、958、958、966页。
③ 田况《儒林公议》,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
④ 阮阅《诗话总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⑤ 白贵、高献红《西昆体诗之传播与接受》,《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⑥ 梁永青《西昆体再认识》,学位论文,2006年。
⑦ 欧阳修《六一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⑧ 施国祁注《远遗山诗集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27页。
⑨⑪⑬⑭⑯⑱⑲㉓㉔朱一玄《红楼梦脂评校录》,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8、343、235、235、261、332、314、329、330页。
⑩ 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全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0页。
㉗ 王晓萍《元白体的艺术特色》,《边疆经济与文化》2014年第2期。
㊳ 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卷一,敦诚《挽曹雪芹》《挽曹雪芹甲申》,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页。
㊴ 敦诚撰《四松堂集》,中国环境出版社2005年版,刻本卷五,第十四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