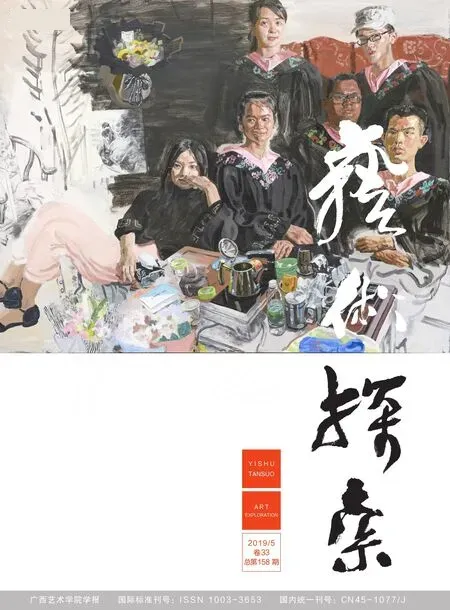牛弘雅乐歌辞创作及其艺术特征
2019-10-22李波
李 波
(渭南师范学院 高教研究室,陕西 渭南 714099)
牛弘(公元544—610年),字里仁,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牛弘在隋朝历任秘书监、礼部尚书、太常卿、吏部尚书等职,是杨隋时期朝廷重臣。作为“好学博闻”[1]1310的隋朝大儒,牛弘的历史功绩主要体现在文化建设方面。除了在秘书监任上请开献书之路、整理文化典籍、弘扬文教之外,牛弘在隋朝一代“制礼作乐”方面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创制隋朝雅乐歌辞正是其“制礼作乐”方面的重要内容。牛弘不但参与了隋朝全部雅乐歌辞的创作,还单独撰定其中三分之一的作品,为隋朝雅乐歌辞的最终确定立下汗马功劳。
可惜目前学界对牛弘在隋朝“开皇乐议”中的作用认识不足,因此牛氏在隋朝正乐活动中的贡献也没有得到充分揭示和公允评价,其在雅乐歌辞创作方面的贡献也同样被人忽视。有鉴于此,本文拟对牛弘雅乐歌辞创作及其作品的艺术特征进行初步阐释和分析,从而为揭示牛弘在隋朝雅乐制作方面的贡献提供依据。
一、牛弘雅乐歌辞创作
中国传统雅乐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祖先及朝贺、宴享时所用的舞乐”[2]828。雅乐的文本形式是雅乐歌辞,这是雅乐实现其文化功能的重要依托,因为它更直观地传达着“制礼作乐”者的治国思想与政治伦常观念。加之古代中国音乐的记谱方式并不发达,音乐的传播与传承更多依赖于口口相传的模式,雅乐歌辞的流传和留存相较于音乐音声而言便具有更大的优势。故此,历代统治者也特别注重对雅乐歌辞的改作。牛弘作为掌管“礼乐祭祀”[3]138的太常卿,正值隋朝“礼乐可兴之日”[4]卷46,他对隋朝雅乐的制作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实际上,牛弘不但主持持续十二年之久的“开皇乐议”,还亲自创作雅乐歌辞。隋朝雅乐歌辞的创作均有牛弘的参与,可以说牛氏正是隋朝制作雅乐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因此,考察牛弘雅乐歌辞的创作,实际上也是揭示隋朝雅乐歌辞制作的关键环节。
(一)牛弘创制雅乐歌辞的背景及过程
根据史书记载,隋朝一代雅乐歌辞的制作与完善经历了四次创作历程。这四次雅乐歌辞创作,第一次为牛弘等人创作《清庙》歌辞的前提背景,后三次为牛弘创作雅乐歌辞的基本过程。本文试将隋朝雅乐歌辞创作基本脉络按照时间顺序梳理如下。
1.第一次(开皇初年,约公元582年):李元操、卢思道创作《清庙》歌辞
《隋书·音乐志下》记载:“高祖遣内史侍郎李元操、直内史省卢思道等,列《清庙》歌辞十二曲。令齐乐人曹妙达于太乐教习,以代周歌。”[1]359这是隋朝第一次创作雅乐歌辞的记载。我们可以根据当时两位作者的官职来判断其创作时间。卢思道任内史侍郎之事,《隋书·卢思道传》有明文记载:“岁余,被征,奉诏郊劳陈使。顷之,遭母忧,未几,起为散骑侍郎,奏内史侍郎事。”[1]1403这段文字是《隋书》续接开皇初卢思道创作《劳生论》而来。而根据研究者考证,卢氏创作《劳生论》的时间,“当在隋开皇元年岁末入高颖幕府之前”[5]31。以此时间为基点,再考虑“岁余”的时间距离,卢思道“直内史省”也就应该在开皇二年岁末至开皇三年之间(公元582—583年)。这个时间粗概来看也应该属于开皇初年的时间范畴。卢思道和李元操在当时便颇有文名,被隋文帝杨坚看重,令其创作宗庙歌辞。李、卢二人创作的《清庙》歌辞沿用了近十七年之久,直到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初为太子的杨广认为其“文多浮丽,不足以述宣功德”[1]360而建议改作,这十二首《清庙》歌辞才被牛弘等人重新创作的歌辞所替代。考察李元操和卢思道留存于今的文学作品,也没发现相关记载,辞作亡轶的可能性较大。
2.第二次(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文帝诏令牛弘创作《圜丘》《五帝》《凯乐》歌辞
隋朝第二次创制雅乐歌辞,是由主持“开皇乐议”之事的牛弘在开皇九年单独完成的。《隋书·牛弘传》记载:“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诏改定雅乐,又作乐府歌词,撰定圜丘、五帝、凯乐,并议乐事。”[1]1305隋文帝诏令太常卿牛弘创作雅乐歌辞,而牛弘独自撰定了《圜丘》(8首)、《五帝》(即《五郊》,5首)、《凯乐》(3首)三种类型的雅乐歌辞。这次创作雅乐歌辞的作者和作品类型、时间都十分明确。开皇九年恰恰是隋朝统一天下之时。由于国家统一,祭祀活动的开展与隋朝立国之初相比显然更为完善、完备。圜丘祭天,五郊迎气,凯乐庆祝战争的胜利,这些祭祀活动的开展以隋朝统一南北的局面为前提背景,也间接说明了隋朝雅乐制作的必要性。而歌辞的创作当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此,牛弘应诏创作雅乐歌辞也是隋朝“制礼作乐”的现实需要。
3.第三次(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牛弘、姚察、许善心、虞世基、刘臻创撰歌辞
牛弘主持“开皇乐议”,除了讨论音律问题,他还将相当多的精力用在王朝音乐制度的建设方面。譬如,确定宫悬制度、乐员编制、文武舞蹈、皇后用乐等,而雅乐歌辞的创作也是其制乐的重要方面。牛弘等人在议定音律问题、确定礼乐制度的同时,要保证雅乐(歌曲)付诸实践也离不开雅乐歌辞的创作。因此,为配合“开皇乐议”时期的制乐活动,创制雅乐歌辞的问题便无法回避。对于此次雅乐歌辞的创作,《隋书·音乐志下》也有记载:“十四年三月,乐定。秘书监、奇章县公牛弘,秘书丞、北绛郡公姚察,通直散骑常侍、虞部侍郎许善心,兼内史舍人虞世基,仪同三司、东宫学士饶阳伯刘臻等奏曰……于是并撰歌辞三十首,诏并令施用,见行者皆停之。其人间音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者,并加禁约,务存其本。”[1]359创撰歌辞30首,这是隋朝制定雅乐歌辞规模最大的一次。与牛弘一起参与歌辞创作的作者也都参与了议乐。虽然此次雅乐歌辞创作之内容不得而知,但是根据史书记载议乐之内容,可以大略明确其范围。其内容涉及食举乐、文武之舞、享神宴饮、射礼等方面。另外,根据现存隋朝雅乐的数量(57首),排除牛弘于开皇九年创作的《圜丘》《五郊》《凯乐》歌辞和稍后创作的皇后房内乐歌辞(合计17首),以及仁寿元年牛弘等人创作的《清庙》歌辞(9首),其数量是31首。而若将《朝日》《夕月》视为同一首歌辞来看,则隋朝雅乐歌辞的总体数量应是56首,而此期创作的歌辞数量则恰好是30首。由此推测,此期牛弘领导议乐诸人创作的雅乐歌辞应该包括《感帝》1首、《雩祭》1首、《腊祭》1首、《朝日》和《夕月》1首 、《方丘》4首、《神州》1首、《社稷》4首、《先农》1首、《先圣先师》1首、《元会》2首、《食举》8首、《上寿》1首、《宴群臣》1首、《文舞》1首、《武舞》1首、《大射》1首。
4.第四次(仁寿元年,公元601年):牛弘、柳顾言、许善心、虞世基、蔡徵重新创作《清庙》歌辞
牛弘等人在“开皇乐议”期间对雅乐歌辞的修撰应该是比较全面的,但是也有遗漏,那就是《清庙》歌辞,他们只是修改了音乐(音声)而没有改动歌辞。其原因是“辞经敕定,不敢易之”[1]360。也就是说当初李元操和卢思道撰定的《清庙》歌辞是由隋文帝亲自审定的,牛弘等人自然不敢改动。直到仁寿元年,时为皇太子的杨广提出“清庙歌辞,文多浮丽,不足以述宣功德,请更议定”[1]360,牛弘等人才能奉诏“更详故实,创制雅乐歌辞”[1]360。因此第四次创作雅乐歌辞的内容较为明确,那就是用以取代开皇初年创作的《清庙》歌辞。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牛弘等人撰写的《清庙》歌辞只有9首,而不是当初李元操和卢思道创作的12首。
可将后三次雅乐歌辞创作情况列表如下(表1)。
纵观隋朝雅乐歌辞创作历程,第二次由牛弘独立完成,第三次和第四次由牛弘领导完成。而《隋书》所录则是后三次撰写歌辞内容。由此更能凸显牛弘在隋朝雅乐歌辞创作中至关重要的作用。

表1 隋朝雅乐歌辞创作情况统计
(二)后世对牛弘创作歌辞的认定
上文揭示隋朝雅乐歌辞创作的历程其实也是对牛弘雅乐歌辞创作的说明。而从歌辞创作者的角度来看,现存隋朝雅乐歌辞的创作,牛弘全部参与。除了独撰17首歌辞之外,其余39首雅乐歌辞牛弘都享有部分著作权(表2)。

表2 《隋书》所载隋朝雅乐歌辞作者统计
除了《隋书》记载,后世收录隋朝雅乐歌辞较为全备的是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明代冯惟讷的《古诗纪》、明代梅鼎祚的《古乐苑》、明代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和清代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隋朝乐府歌辞较为全备,但并未标明作者,仅在《圜丘》和《太庙》的解题部分以《隋书·音乐志》为凭,以其为牛弘等人集体创作。
冯惟讷《古诗纪》收录隋朝雅乐歌辞也较为完备(表3),冯氏结合《隋书·音乐志》和《隋书·牛弘传》的相关记载,判断歌辞作者:“按此则诸歌辞当为牛弘所作也”[6]卷139。也就是说,冯惟讷也将隋朝雅乐歌辞的作者认定为牛弘。梅鼎祚《古乐苑》虽然是“因郭茂倩《乐府诗集》而增辑之”[7]提要,但他在收录隋朝雅乐歌辞时也注意结合《隋书·音乐志》和《隋书·牛弘传》来阐明作品创作背景,实际上也就承认了牛弘绝对主创者的身份。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牛弘集》将《隋书》所载雅乐歌辞全部系于牛弘名下。其收录情况与冯惟讷《古诗纪》完全相同。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卷九》收录隋诗作品与冯惟讷、张溥所录作品完全一致,编者同样以《隋书·音乐志》和牛弘本传为据,指出“诸歌辞当为牛弘所作”[8]2755。另外,还有个别作品在收录中被归到牛弘名下。如南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王志庆《古俪府》都将隋朝社稷歌的作者直接认定为牛弘。

表3 冯惟讷《古诗纪》收录隋朝雅乐歌辞情况统计
由此看来,隋朝一代雅乐歌辞之创作,主要由牛弘领导完成。后世编者将隋朝雅乐歌辞创作全部归属于牛弘一人名下,虽然不一定正确,但是也客观地说明牛弘之于隋朝雅乐歌辞创作的绝对重要性。作为主持隋朝制乐活动的太常卿,牛弘不但独自创作近三分之一的作品,他对每一首雅乐歌辞的最终定型应该都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将隋朝雅乐歌辞的创作归在牛弘名下也并无不妥。
二、牛弘雅乐歌辞的艺术特征
明确了牛弘创作雅乐歌辞的基本情况,下面我们尝试对其歌辞艺术特征作简要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基于上文对牛弘雅乐歌辞创作情况的分析,我们尽量以牛弘独撰作品为例来分析其艺术特色,同时也注意兼顾其与人合撰之作品。
(一)文辞质实而严整
从文辞上来看,牛弘创作的雅乐歌辞文辞质朴而句式严整。仁寿元年隋朝第四次改作雅乐歌辞,是因为太子杨广认为卢思道和李元操创作的《清庙》歌辞“文多浮丽”而达不到“述宣功德”的用乐目的。因此,牛弘等人重新创作的歌辞应该在文辞方面避免了“浮丽”的风格。实际上,早在开皇九年牛弘创作《圜丘》《五郊》《凯乐》歌辞之时,其文辞就具有质朴严整的风格特点。如《圜丘》第一首:
肃祭典,协良辰。具嘉荐,俟皇臻。礼方成,乐已变。感灵心,回天眷。辟华阙,下乾宫。乘精气,御祥风。望爟火,通田烛。膺介圭,受瑄玉。神之临,庆阴阳。烟衢洞,宸路深。善既福,德斯辅。流鸿祚,遍区宇。[1]360这是一首降神歌辞,三言句式,配《昭夏》乐。首句是对祭祀之事及其氛围和环境的描写,采用白描的写作手法。第二句是对祭祀目的的交待,文辞同样简明直接。第三句是对祭祀所用礼乐情况的说明,直陈其事。第四、五句是对祭祀效果的交待,直接叙述,文辞简朴,几无修饰。第七、八、九句是对神灵感动降临过程的描写,同样采用简单扼要的白描写法。第十、十一句是对神灵降世场面的描写,后两句是对神灵施福的描写。同样是对场景的简单描述和交待说明,文辞简洁,没有过多修饰,因此现场感较强,仪式感也较为突出。由此可见,牛弘歌辞并不追求文辞的华丽而重点在于直接描述祭祀的过程和场景,以及祭祀的效果。整首歌辞叙事清晰,场景的描写也侧重于白描,因而文辞层面质朴无华,概无浮丽之嫌。特别是与北周、北齐、南朝雅乐歌辞对比,牛弘雅乐歌辞的这一艺术特征尤为鲜明。
试看北周庾信所作《圜丘》歌辞(降神):
重阳禋祀,大报天。丙午封坛,肃且圜。孤竹之管,云和弦。神光未下,风肃然。王城七里,通天台。紫微斜照,影徘徊。连珠合璧,重光来。天策暂转,钩陈开。[1]333
此诗虽然同样重在描述祭祀的场景,但是其歌辞显然更具想象力和文采。姑且不论其采用四三结合的句式更有表现力,仅其歌辞意象的丰富性和唯美特征亦足以说明文采斐然的特质。“孤竹之管”、“云和弦”、降临的神光、王城之外的通天台,斜照的紫微星辰及徘徊的身影,一个个唯美的意象接踵而至,意境顿生。而意象的唯美正是通过文采的优美呈现的,故此整首诗歌以优美的文辞呈现唯美的意象,意境悠远,祭祀的庄严凝重之感似被悄然化解。牛弘的圜丘祭祀降神之辞与庾信作品相比,前者的文辞显然要质朴许多。其文辞三言成句,动宾结构为主,缺少变化,当然也明显要严整一些。所以相较而言,牛弘歌辞文辞质实、严整,缺少像庾信诗作那样的灵动与变化。但是它的长处也是明显的,即传达了一种祭祀的庄严情绪,与祭祀场合的严肃性是较为匹配的。
如果说北周《圜丘》歌辞是出自文学大家庾信之手而文采斐然,那么,北齐《大禘圜丘》歌辞在文辞上的面貌又如何呢?我们同样可以加以分析比较。其诗如下:
肇应灵序,奄字黎人。乃朝万国,爰徵百神。祗展方望,幽显咸臻。礼崇声协,贽列珪陈。翼差鳞次,端笏垂绅。来趋动色,式赞天人。[1]314
此诗在文采方面当然要稍逊于庾信所作《圜丘》,应该说也是质朴之作,但是对祭祀场景的描写也有一定的想象,体现在文辞方面则是采用一定的修饰和加工。尤其是第五句,采用比喻手法,文辞精美。这种情况在牛弘的诗作中也是比较少见的。当然,文辞质朴,可能还与歌辞作者的身份也有一定关系,儒官学者之诗与文学家之诗自然有所不同,创作思想上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别。
文辞质实的风格在牛弘等人创作的《清庙》歌辞上亦有鲜明的体现。我们以其第一首(迎神)为例:
务本兴教,尊神体国。霜露感心,享祀陈则。官联式序,奔走在庭。几筵结慕,裸献惟诚。嘉乐载合,神其降止。永言保之,锡以繁祉。[1]367
整首作品文辞质实,要么是对祭祀目的的直接交待,要么是对祭祀场景的直接描述,要么是对祭祀祈福内容的直接表达。文辞意义明了,质朴无华,的确是克服了卢思道和李元操“浮丽”的缺点。当然如从诗歌的角度来看也就显得有些平淡乏味了。
(二)工对偶,擅白描,多用典
从修辞和表现手法来看,牛弘创作的雅乐歌辞工于对偶,因此显得特别规整严谨。同时,在描述祭祀场面时又较少修饰,而擅长使用白描的表现手法,使其诗作具有真实的现场感和强烈的仪式感。关于牛弘诗作的工整,上文在阐释其文辞特点时已有交待,在此特从修辞角度阐释其对偶工整的特点。仍以其独撰的《圜丘》(第四首)为例:
肇禋崇祀,大报尊灵。因高尽敬,扫地推诚。六宗随兆,五纬陪营。云和发韵,孤竹扬清。我粢既洁,我酌惟明。元神是鉴,百禄来成。[1]361
特别是诗中第三、四两句,对偶精妙。数字对、动作对、器物对、声音对,对仗工整巧妙,这也是牛弘辞作中较有文采的一篇。整篇歌辞虽不是全部对偶,但是其中不乏相当工整的句子,诗作整体规整严谨。歌辞用典也较为频繁,“六宗”“五纬”“云和”“孤竹”都有典故。其他歌辞也是如此,每首都有至少三四处用典。在表现手法上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擅用白描:直接描述祭祀的场景和环境,而较少进行艺术加工。如上引园丘第四首开头即描写祭祀的情状——禋祀典开始,平安报神灵而没有曲笔。然后辞作分别描写祭祀者的诚敬、祭祀的活动以及祭祀用乐的美妙和贡品的清洁,整首歌辞像是对祭祀现场的文字“还原”,现场感和仪式感特别突出。
这个特点在牛弘等人创作的其他辞作中亦有体现。如其奉诏所作的《感帝》歌辞:
禘祖垂典,郊天有章。以春之孟,于国之阳。茧栗惟诚,陶匏斯尚。人神接礼,明幽交畅。火灵降祚,火历载隆。蒸哉帝道,赫矣皇风。[1]363
开篇就交代了祭祀目的,接着是祭祀地点、祭祀贡品和音乐、祭祀的场景和效果。突出白描直叙的写作手法,其效果就是将祭祀时强烈的现场感和庄严性凸显出来。这也是官方祭祀需要的气氛和效果。所以这首歌辞同样是在修辞方面着力不多,偶有对偶和用典,而平铺直叙的描写是其显著特点。因此整首诗抽象性的概念偏多,而诗歌形象较少,意象数量的有限和场景转换的过密,致使整首作品难以构成完整的意境。这也是牛弘雅乐歌辞作为诗歌来看,一个较为突出的缺点。当然这些诗作还是作为祭祀雅乐歌辞,其应用属性是首先要考虑的方面。
(三)歌辞具有音乐性,押韵形式多样化
歌辞是“歌曲的唱词”[2]1466,所以用于祭祀的雅乐歌辞实际上还具有歌唱性,因此考察这些歌辞的特点还应考虑其音乐层面的特征。就牛弘创作的雅乐歌辞而言,其音乐性应该是作者在创作时纳入考虑的重要因素。牛弘作为隋朝主持制乐的太常卿,他对音律是颇有研究的,而且他对创作的歌辞用以祭祀歌唱的目的也是非常明确的,因此,牛弘创作的歌辞在音乐上也应该具有与其歌唱要求相一致的特点。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无法知晓牛弘雅乐歌辞的旋律调式,但是通过考察这些文辞在不同乐曲中的韵律特点也能对其音乐特质有所了解。牛弘雅乐歌辞在使用同样乐曲的作品中,其句式长短、用韵规律较为相似。如表4所示,使用《昭夏》乐的作品,均为三言,且前六句的押韵方式完全相同。《皇夏》《登歌》亦是如此。这应该和歌辞的音乐属性密切相关。当然,也并不是乐曲相同的歌辞在句式和韵律上必须完全一致,如《诚夏》曲,就存在很多变化。

表4 牛弘雅乐歌辞用乐情况统计
另外还有《五郊》歌辞分别采用宫、商、角、徵、羽作为主音来演奏,均是四言六句,两句押一韵,是比较固定的用法。其余作品《隋书·音乐志》没有注明用乐情况,但是也基本以押韵为主,且其中也有部分变化。通过对牛弘雅乐歌辞用乐情况及其诗作押韵情况的列表分析,至少说明牛弘在雅乐歌辞的创作上注意到其用于歌唱的特点,但是同样的乐曲也注意歌辞内容(如字数和韵律方面)不同的处理,这是其变化的地方。总之,牛弘雅乐歌辞的音乐性是其值得关注的地方,也是其艺术特征之重要方面。此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但是有一点明确的是,牛弘雅乐歌辞在音乐方面也是有要求的,这是其作为入乐歌辞的一个基本特征。
(四)歌功颂德凸显政治功能
从歌辞的思想内容来看,牛弘雅乐歌辞歌功颂德,凸显政治功能的特点尤为突出。中国古代王朝向来重视祭祀活动,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9]974。祭祀与战争一样是国家大事,是因为祭祀是国家仪式的重要形式,它是一项体现君国意志的重要活动。因此祭祀歌辞内容自然要反映君王的统治意志,宣扬王道而有助教化。牛弘雅乐歌辞作为祭祀所用文辞,其思想内容同样也有这样的特点,而且尤为突出。
牛弘独创的《凯乐》歌辞,其歌功颂德的创作意旨特别明显。不用细看其文辞之内容,仅看三首歌辞作品的题目就能一目了然:“述帝德”“述诸军用命”“述天下太平”。这些歌辞作于开皇九年,牛弘把隋文帝以武功统一天下的伟大历史功绩付诸诗文,其思想层面的政治意识和目的也就不可避免。不仅如此,就是在祭祀神祇的《五郊》歌辞中,也能凸显出牛弘创作歌辞的宣扬王教、服务政治的基本功能。如《青帝》中“牺牲丰洁,金石和声。怀柔备礼,明德惟馨”[1]362是对王朝礼乐兴盛的颂扬;《赤帝》中“庆赏既行,高明可处。顺时立祭,事昭福举”[1]362是对王朝顺势而为、兴旺昌盛的称颂。总之,牛弘作为代表封建王朝掌管祭祀等事务的太常卿,他更应该明白祭祀对于国家政治的重要意义,这种认识对他的雅乐歌辞创作显然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体现在歌辞思想内容层面就是其政治伦常意识的凸显和宣扬王道、有助教化主旨的明确。
三、牛弘雅乐歌辞的影响及意义
阐明了牛弘创作雅乐歌辞的基本历程及其艺术特征,我们再来讨论其影响和价值意义,特别是它在当时的影响及价值应该是巨大的。
牛弘创作雅乐歌辞与其主持制定隋朝正乐的活动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创作雅乐歌辞本身就是牛弘“制礼作乐”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这一角度来审视其雅乐歌辞创作在当时的影响和价值则较为客观。从牛弘创作雅乐歌辞的时间上来看,分别是在开皇九年、开皇十四年和仁寿元年。其中开皇九年恰逢天下一统,其时雅乐的制定是对一统政治的呼应。《圜丘》《五郊》和《凯乐》歌辞正是对王道的宣扬和歌颂,其政治意义是尤为突出的。仁寿元年改作《太庙》歌辞,只是一个完善的过程而已,它的影响和价值要相对有限一些。开皇十四年的雅乐歌辞创作,则是牛弘主持“开皇乐议”的总结,也是长达十二年朝廷正乐制定活动结束的标志。《隋书·音乐志》记载牛弘于此年三月向隋文帝上奏《乐定奏》,并称“臣等伏奉明诏,详定雅乐,博访知音,旁求儒彦,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为一代正乐,具在本司”[1]359,实际上宣告了正乐活动的结束。“于是并撰歌辞三十首,诏并令施用,见行者皆停之。其人间音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者,并加禁约,务存其本。”[1]359《隋书》其后的描述则说明牛弘等人创作雅乐歌辞是在他们确定了雅乐(音律、规格、乐仪等方面)之后进行的。只有雅乐的音律、使用规格等问题确立之后,雅乐歌辞的创作才能有效开展。如此看来,雅乐歌辞在开皇十四年的大量创作其实恰恰标志着隋朝一代正乐的定型和完工,因此它的意义不可谓不大。隋文帝很满意,诏令施行。而其在当时的影响,正如《隋书》所述,之前的、民间的音乐要么被废弃,要么被禁止,而主要由牛弘创作的雅乐歌辞成为隋朝一代正乐的成果而广为流传。
牛弘雅乐歌辞对唐代音乐文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在相当长时间内甚至作为唐代雅乐而继续使用:“时军国多务,未遑改创 ,乐府尚用隋氏旧文”[10]1041。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才由曾经参与牛弘制乐的祖孝孙主持修定唐朝雅乐。因此,牛弘等修定的雅乐歌辞作品在唐朝雅乐制作中的影响也一定是存在的。
今天,我们了解和掌握隋朝正乐活动的资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相当有限,其中我们能掌握的重要信息就是牛弘议乐的理论文字和这些歌辞。就这些雅乐歌辞而言,无论是将其作为封建王朝祭祀文化之文本样态,还是作为古代音乐文化之历史遗存,抑或是作为古人表达观念信仰之诗文创作,它们都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值得我们珍惜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