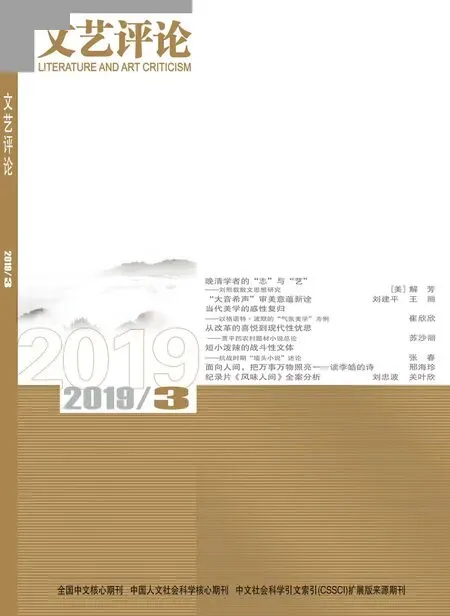叔本华审美理论中的意志与根据律
2019-09-28○张迪
○张 迪
审美在叔本华哲学体系中是被当作特定的认识形式来看待的,它与其他认识形式的不同在于,其他认识形式的目的在于探寻关系和作用,而审美的目的在于认识理念。在叔本华哲学中意志与根据律是我们意识中明确的认识,也可以说是全部认识内容的质料。因而,当叔本华要求审美主体应该无意志与摆脱根据律时,我们就不能将审美视作对意志与根据律的否定。而以往,人们在理解无意志与摆脱根据律时,恰恰都是强调意志与根据律是审美的障碍,并进而以为审美实现的途径就在于“自我否定”。①进一步而言,即便我们不将审美视作对意志与根据律的根本否定,而仅仅将审美实现的途径视作根绝个体的欲望以及放弃在根据律中认取事物的方式。这种设想依然会带来不可避免的矛盾。②同时这种“自我否定”也没有回答下面这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处于“自我否定”状态下的审美主体如何构成理念以及构成理念的材料是什么?另外,当我们强调审美过程中主体的自我否定时,审美不可避免地带有被动与消极的意味,似乎只要经由自我否定,理念就会自动呈现于眼前。但这种被动与消极的意味恰与叔本华将审美视为智力的异常活跃是矛盾的。③
而且,随着人们对叔本华审美理论研究的深入,我们也逐渐感到审美与意志及其根据律的关系仍需进一步思考。④本文写作的目的即是对上述疑窦进行尝试性解答。而本文认为解答上述疑窦的关键在于——思考意志与根据律在审美过程中的积极意义。
一、对意志的直接认识是认识理念的前提
在叔本华看来,世界一面是意志,一面是表象,因而,理念或者归于意志或者归于表象。审美既然是认识形式的一种,理念自然要以认识主体的存在为前提,这决定了理念属于表象的范畴。
如果我们笼统地谈论审美中的自我否定并将意志错会成作为世界本质的意志,那么审美就失去了合理的基础。因此,叔本华要求审美“无意志”时提及的意志必然不是意指作为世界本质的意志,而只能是作为表象的人的意志。我们也可以将叔本华论述审美时提及的“意志”视作自我。而自我大致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作为认识主体的自我;一是作为意志主体的自我。⑤因为我们通常是在意志活动中意识着自身,所以自我主要是由意志活动来形塑的。认识主体的自我在一般情形下只是意志主体自我的奴仆,它的作用在于运用认识能力形成表象世界,并确定表象与意志、表象与表象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作为认识主体的自我是被意志主体的自我遮蔽的。因此,虽然表象有赖于认识主体,自我却认表象世界为他物。这是因为自我与他物的确认是基于意志主体而言的。因此,物我之分确证的只是作为客体的自我与客体的他物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自我还是他物都是受制于根据律的表象,即在关系和作用中才有的存在。因此,我们似乎有足够的理由经由弃绝自我(意志)和根据律来认取理念。但这样做时我们往往遗忘掉自我不仅包含意志主体的自我还包含认识主体的自我这个事实。再加上叔本华将审美认识形式与根据律的认识形式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于是,人们就误将认识主体与意志主体都视为审美的大敌。但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叔本华在论述审美时一再强调的只是割断或者说隔离个体意志与表象世界之间的关联,而并不是割断认识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关联。再进一步而言,割断个体意志与表象世界的关联,其目的是为了纯化认识主体,纯化我们的认识能力,使认识主体转变成叔本华所说的纯粹而无意志的主体。另外,根据律中的认识虽然完全不同于审美认识,但根据律并不是审美的大敌。
既然作为认识主体的自我对审美而言并不是威胁,那么想要从积极的方面或者说从正面来论述审美的根本面目就意味着探寻认识主体的自我独自面对世界时,主体会看到什么。因为根据律是主体认识世界的形式,所以即便隔绝了个人意志与其他表象之间的关联,在根据律的认识形式下,我们依然只能看到表象以及表象与表象之间的关系。假若我们认识时仅仅拥有根据律这个工具,那么在上述情形下我们依赖根据律得到的认识相比个人意志参与其中时依靠根据律得到的认识,只是相对更加独立与完整罢了。⑥而就认识的性质而言,两者并没有质的不同。
主客体分立是叔本华哲学的根基,所以主体认识世界就意味着在世界上打上主体的烙印。反过来说,每一客体必然在主体方面有其对应物。理念既然是不同于根据律中一般表象的特殊表象,那么,相应地主体中必然存在着一种不同于根据律而又不弱于根据律的特殊认识。唯有如此,人们才能认识理念。而这正是叔本华下面这段话想要表达的意思。“因此,正如我说过的,理念并没有揭示事物的自在本身,而仅仅是自在本身的客观特性,因而,理念仍然是表象。而且,假如事物的内在本质不为我们所知,或者至少模糊地被我们感到,那么即便这些客观特性,我们也将不能理解。”⑦
叔本华认为:“除了意志和表象之外,根本没有什么我们能知道,能思议的东西了。”⑧我们知道表象有赖于根据律,那么对意志的认识如何呢?叔本华认为我们对意志的认识不同于对表象的认识。它是我们对自身才有的特殊认识,是不经由根据律得到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与根据律一样可以视为先验的认识。⑨叔本华将其称之为对意志的直接认识。
因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那就是理念作为审美认识的结果在主体方面的对应物必然是主体对意志的直接认识。而审美过程大致应该是这样的,审美的必要条件是智力或者说认识能力挣脱其为个体意志服务的处境,而后当认识主体抛开根据律直观这个世界时,自然而然地会将我们对自身内在本质的感受一并赋予直观中的世界。这样一来,世界在纯粹认识主体的眼中除了是意志的客体化之外,就不再是别的什么(意志的直接客体就是理念)。叔本华认为假若我们不能将我们对自身内在本质的认识赋予其他客体就意味着否认外在世界的真实性。⑩另外,纯粹认识主体在直观这个世界时,还会发现意志的客体化存在着不同的级别。纯粹认识主体只是意志世界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只知晓意志而不知其他,或者说其他的一切在这面镜子里最终都转化为意志。但这镜子中的意志并不是作为世界的本质的意志,而是已经能被主体所见的客体化的意志。这时的主体之所以为纯粹主体,其原因在于世界的本质既然是意志,那么理所当然的只有能恰如其分地反映意志客体化的主体才是纯粹主体。纯粹主体这时候既然只知晓意志客体化,只知晓意志客体化的不同级别,所以根据律对理念而言并没有意义。理念只是常驻的形式,它不知变化。需要提醒的是,人们切莫将理念与艺术形象等同。因为,某一特定艺术形象可能是多种理念的载体。⑪我们发现假若我们不拥有对意志的直接认识,那么世界要么是根据律中的表象,要么就是一团漆黑。因此,对意志的直接认识就是审美的前提。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正如根据律是先验的,而表象不是先验的一样,理念也不是先验的。人只有睁开眼观审世界才有认识理念的可能性。因此,理念是先验与后验的统一。
“柏拉图的理念,被认为是纯粹的客观表象,是纯粹的形式,因此理念能够从时间和各种关系中超脱出来。这一理念从经验上而言,就是种与类,而种与类就是理念与经验相关的部分。”⑫这就意味着虽然理念超越于根据律,但是人对理念的认识却不得不与根据律发生关联。
二、根据律是认取理念的路径
对于理念的疑问在于,既然认识理念的过程以及理念显现的过程都在根据律之中,为何理念不在根据律之中,或者说,理念与一般表象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如黄文前认为“理念是可以直观的客观存在,却又在时空之外……理念是表象,又在根据律之外。”是叔本华美学理论的自相矛盾之处。⑬又由于认识个体以及认识个体向纯粹认识主体变化的过程都在时间之中,就使得上述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由此引发的疑窦导致人们错误地以为审美与根据律是根本对立的关系,认为两者不根本对立叔本华的审美认识论就无法自圆其说。
因此,要弄清楚根据律在审美过程中的作用,就需要理清理念与一般表象、认识个体与纯粹认识主体的关系。
首先,理念与一般表象之间并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或并存的关系。因为,先后与并存都是对处于时间之中的一般表象而言的,而理念不在时间之中——在时间中的是理念的表出,是对理念的认识——所以,理念就不能与一般表象做先后与并存的比较。作为表象的世界,一方面可以是无时间性的理念,一方面可以是有时间性的一般表象。总之,凡是时间的概念统统不能用于理念与表象的比较。时间性的概念只能用于理念的表出,而理念的表出就意味着进入根据律的形式。
其次,虽然理念不具有时间性,但并不意味着理念是自在的。在叔本华哲学中,自在的只有作为世界本质的意志。作为世界本质的意志无需以任何事物的存在为前提,而理念却以主体的存在为前提。同时,无论是认识个体还是纯粹认识主体,就他们正在认识时而言,他们必然要有具体的承载物,而这个承载物就是我们的肉身,即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的存在方式,只能是一般表象,也就是说,虽然纯粹认识主体不受制于根据律,但承载这一主体的身体却受制于根据律。
再次,人们能够认识理念的前提,是人对意志的直接认识。而人对意志的体认是通过身体的意志活动进行的,即是说,虽然人对自己意志的认识是直接的,但这一认识过程却是在时间之内完成的。
综合以上的说明,我们可知,一方面理念、纯粹认识主体以及人对意志的直接认识都不受制于根据律,而另一方面,认识理念的过程,从认识个体向纯粹认识主体的转化,特别是人对意志的认识过程都要受制于根据律。
因此,如果仅仅就审美认识的完成形态而言,作为审美认识客体的理念与作为审美认识主体的纯粹认识主体都是摆脱根据律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审美认识(艺术的创造与艺术的鉴赏)是一个过程,那么审美必然与根据律发生关系。
因为,在叔本华看来,主客体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审美认识与根据律的关联可以从主客体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先就客体而言,因为,理念的载体总是一个具体物,或者说总是个体,所以,无论是认识理念的过程还是表现理念的过程,都要在根据律之内进行。因此,叔本华在论述具体艺术形式时,每每会提及关系、作用以及动机等等这些表征根据律的词汇。实际上,随着呈现理念的不同,审美与根据律的关系的密切程度会相应地不同。叔本华认为要表现植物只需要考虑空间因素即可,要表现动物与人,就需要动作。如果就认识的过程而言,叔本华认为即便是认识植物这一理念,也要经由时间的形式才能完成。⑭
再就主体而言,主体在审美认识过程中需借助个体的生活经验与后天习得的艺术技巧来传达理念。叔本华指出“个人自己的经验是理解文艺和历史不可缺少的条件”;⑮天才“能够把这种天禀借给我们一用,把他的眼睛套在我们头上,这却是后天获得的,是艺术中的技巧方面”⑯。在《论美》这篇论文中,叔本华表达了与上述内容大致相同的观点:“在着手制作艺术品时——在此,目的就是传达所认识之物——意欲就可以、并且必须重新恢复活跃,因为此时已经有了目的。这样,充足理性原则再次恢复了统治;我们就根据这些原则,恰如其分地运用艺术的手段以达到艺术的目的。”⑰也可以说,审美主体只有借助根据律才能创造与理解。审美达成的关键并不是摒弃根据律而是穿透根据律发见或者展现意志的客体化。因此,一切艺术都要借助根据律进行创造,而我们也要借助根据律来进行欣赏。
由此可知,叔本华审美理论的难题并不在审美与根据律之间的对立,而是我们怎样才能发现或者确定我们创造的或者看到的就是意志在它各个级别上恰如其分地表出。即是说,经由上文的论述,我们虽知晓理念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需要通过什么手段来构造理念,却不知道理念的面貌是什么,这就类似于手工课上,我们每人都拿着所需的材料,使用着正确的手段,却不知道要将材料做成什么一样。
叔本华通过天才论解决上述难题。叔本华认为天才之所以为天才的禀赋在于他们能够先验地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并以此“补充大自然后验地提供出来的东西”⑱。然后,天才通过艺术技巧,将已被提升为理念的个别完整地传达出来。在此之后,普通人就能够借助天才的眼睛,更加容易地认识理念。
而天才之所以能够先验地把握到理念,首先是因为我们人类自身就是意志的客体化;其次,是因为我们能够直觉到世界的本质是意志;最后,天才的纯粹认识能力相比普通人在程度与持续的时间上都更胜一筹。由于上述原因,天才能够认识并传达理念,而普通人也能够借助天才的成果相对容易地看到根据律之外的理念。⑲
在确立了意志与根据律在审美中的功用时,我们也为审美中的悲剧性与喜剧性预留了存在的空间。
三、审美认识中的悲剧性与喜剧性
叔本华提出“关于美的形而上学,其真正的难题可以以这样的发问相当简单地表示出来:在某一事物与我们的意欲没有任何关联的情况下,这一事物为什么会引起我们的某种愉悦之情?”⑳当然,我们也可以再加上这个疑问,那就是这一事物又何以引起我们的悲伤之情。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既然已经知晓对意志的直接认识是审美得以实现的条件,那么此时我们便不会困惑于审美中依然存在着愉悦或悲伤之情。正如叔本华所言,虽然“审美的个人变成了一个纯粹认知着的、不带意欲活动的主体,但他仍然意识到自身和自己的活动”㉑。我们也可以说审美中悲剧性与喜剧性的根源就主体而言,是因为我们是意志主体和认识主体的同一。
但是要说清楚审美认识中悲剧性与喜剧性的正确含义,我们要完成以下两个任务。第一是论证悲剧性与喜剧性在审美中得以存在的基础;第二是在此基础上演绎出悲剧性与喜剧性的正确含义。
悲剧性与喜剧性作为审美理论的重要范畴,其根基自然是审美中的愉悦与悲痛之情。因为,前文已经说明了审美中愉悦与悲痛之情发生的可能性,那么我们这里的目标就是说明审美主体能感受到怎样的愉悦与悲痛。我们知道,在一般情形下个体依靠根据律确定他物与个体意志之间的关系,因此,对于个体而言的悲喜必然是具体的他物引发的。与之不同的是,审美主体只保有对于意志的意识,而个体意志是处于沉寂状态的,这就决定了审美中的悲与喜不能由特定时空中的特定对象引发,而只能由意志客体化的本质特征所引发。
审美主体虽然为悲剧性和喜剧性的存在提供了可能,但是,如果审美的客体不具备使悲与喜这两种情绪发生的条件,那么悲剧性和喜剧性就仍然没有真实的基础。同时,客体所激发的悲与喜这两种情绪的特征必须同主体可接受的特征吻合。
审美的客体是理念,而理念是意志的直接客体化,这是我们上文已经说明了的。但只就理念来看,它并不能引发悲与喜这两种情绪。理念是处于非活动状态的,或者说,理念是作为意志客体化的理想状态呈现给我们的。在审美认识形式中,只有理念的表出,即意志客体化的实现过程,是意志的活动状态。由此可知,悲剧感和喜剧感只能由理念的表出方式引发,而不是由理念引起的。又因为,理念不在具体的时空之内,所以理念的表出方式也超出了具体的时空。即是说,虽然理念的表出每次都要在具体的时空之内发生,但是具体的时空不能决定理念以及它的总的表出形式。在审美中人们之所以会对理念的表出方式感兴趣,是因为对于意志的直接认识是审美认识方式实现的条件之一。同时,理念表出方式引发的悲喜情绪不针对特定时空中的特定对象,它就不会促发人的意志活动。
因为整个世界在本质上只是同一个意志,所以在意志客体化为理念时,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自我分裂。这种自我分裂对于理念而言,就意味着理念的表出必然采取矛盾和冲突的形式。理念为求得自己的实现好像要争先恐后地劫夺物质。这使得时间和空间中的个体必然经受痛苦和毁灭的命运。但是,所有的存在物不会因为必然毁灭的命运而欣然放弃自身占据的物质。这同样不符合意志的本性。因为存在即意味着意志的客体化,而意志的客体化所稳有的只是现在。至于过去和将来,也只存在于现在之中。如果稳有现在的主体不复存在了,那么过去和将来也会一并消失。因而当理念以无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来显现自己时,那认识理念的主体,因为仍然保有对意志的意识,就会产生悲剧感。
当理念以它的表出方式使审美主体感受悲剧感的同时,也使喜剧感的发生成为可能。审美中虽然不存在迎合意志实现的活动,但是审美是将主体从为意志服务的劳苦中解脱出来的活动,这种活动能够赋予人们更为强烈的愉悦。
因为在审美认识形式中,对意志的直接认识是审美认识形式实现的条件之一,所以,意志能够带来的痛苦对于主体而言依然记忆犹新。一旦认识不再为意志的实现服务,主体就会如释重负,审美主体此时就感受到无比巨大的愉悦。这种巨大的愉悦自然是寻常的幸福不能比拟的。寻常的幸福是以某种具体匮乏的限度为限度的,所以它是有限的可量度的;而审美中的愉悦是以整个意志的痛苦为限度的,所以它是无限的不可量度的。其次,喜剧感的发生来自于人们对存在自由的认识。人们在将自身视作意志的同时,是将意志的自由特征也认作个体特征的。但是,这种幻觉很快就被现实所打破。正如叔本华所言:“在行为中不可能看到的自由,必须寓于存在之中。把必然性加于存在和把自由加于行为,在任何时代都是根本错误的,都是把根据和结果加以颠倒。相反的,自由只寓于存在之中,但是从存在和动物中必然会产生行为,从我们的所作所为中,我们认识我们是什么人。”㉒当我们认取理念时,我们就是发现理念作为存在的自由。
综上所述,悲剧性与喜剧性是由理念的表出方式引发的。而理念又是分为不同级别的。当我们认识这些不同级别的理念时,我们对它们表出方式的注意程度是不同的。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形式都会引发明显的悲剧感与喜剧感。实际上,在认识某些理念时,我们并不需要注意它们的表出方式,它们的表出方式在体现理念表出方式总的特征方面也并不明显。而且,同一理念在不同的情形下,体现理念表出方式总特征的程度也不相同。
结语
理念的每次实现都受着根据律的支配,都是有所待的,但是理念却超越于根据律。根据律只能决定理念的表出,但决定不了理念本身。与之相应,审美过程中,审美主体无时不借助个体的生活经验,但审美主体最终却能够超越个体处处受制于根据律的存在方式。而审美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审美主体在审美过程中重获自由意识。但审美过程中悲剧性与喜剧性的时隐时现,告诫我们审美只是“生命中一时的安慰”,它不是“意志的清净剂”,无法将我们永远解脱。㉓
①金惠敏《意志与超越——叔本华美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②参见王妍《超脱与复归——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说的现象学解读》[J],《文艺评论》,2017年第10期。
③⑤⑭⑰⑳㉑[德]叔本华《叔本华思想随笔》[M],韦启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第176页,第38页,第37页,第33页,第34页。
④参见王荣祥《走出失乐园——叔本华的意志哲学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44页。
⑥⑦⑫[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英文版)第二卷[M],E.F.J.Payne译,纽约:Dover Publication Inc,1966年版,第363页,第364页,第364-365页。
⑧⑨⑩⑪⑮⑯⑱⑲㉓[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8页,第152页,第157页,第297-300页,第339页,第272页,第309页,第271-272页,第370页。
⑬黄文前《意志与解脱之路——叔本华哲学思想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页。
㉒[德]叔本华《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M],任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