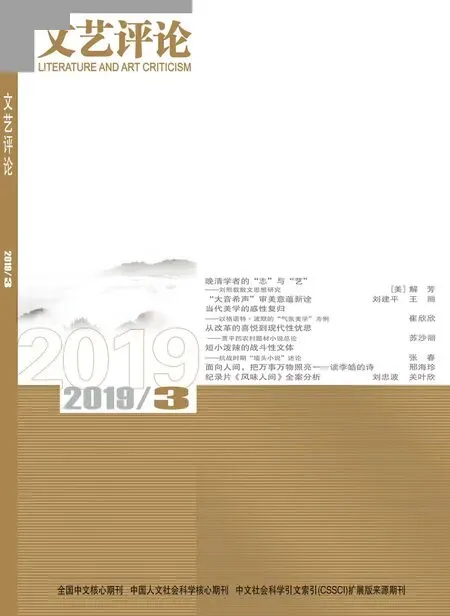吹响新世纪军旅文学的集结号
——评傅逸尘《“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
2019-09-28贺小凡张丽军
○贺小凡 张丽军
在《“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这套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下军旅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基本面貌,这不仅是对于当下军旅文学创作主力和代表作品的一次深度梳理,也是对目前军旅文学批评成果的一次展现。
“新生代”军旅作家,被傅逸尘定义为进入21世纪之后的一批进入读者视野的军旅作家。他们大都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以后,是一个日渐活跃,并且具有相当创作实力的作家群体。他们大都有过军旅生涯,且恰逢新军事革命浪潮涌动的时期,加上市场经济时代来临,军旅题材影视作品的瞩目,都为这批新生代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基础和极佳的机遇。他们从各个角度挖掘军旅文学的创作资源,从战场到军营,从历史到当下,题材不拘,形制不拘,描摹出军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面貌,无论在艺术形式、题材内容,还是伦理意识上,都为军旅文学开拓出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创作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态势,令当代文坛瞩目,与之相比,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却远远不够。在军旅文学批评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现状下,正如朱向前教授所言,傅逸尘“不卑不亢地脱缰而出”,在长期的批评实践中,作为一名“80 后”的批评家,他的追求无疑是相当宏大的——我们看到,他着眼于建构“新世纪军旅文学”的版图,持续性地描绘出新世纪军旅文学的发展面貌和整体景观,做研究的思路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问题意识,做研究的态度更是深具使命感,以一己之力奋力填补军旅文学批评研究的空白。
傅逸尘对“新生代军旅作家”进行命名和积极推介,而他也在文学批评的道路上逐渐走出了自己的姿态:“新潮军旅批评家”。两“新”合力,无疑仍会继续为当代军旅文坛作出极大的贡献,为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新老换防的历史变革留下鲜活见证,写下深刻注脚。纵观傅逸尘的批评研究,在内容主题方面,傅逸尘注意到“历史伦理”由“宏大史诗”到“个人私语”的诗学转化,作家们开始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个人的、小写的历史,聚焦“小人物”和日常生活经验;在艺术技巧方面,傅逸尘看到了新生代军旅文学向文学本源性的回归,并运用极具现代性和学术性的视野来进行批评实践。从“写什么”,到“怎样写”,他坚持站在军旅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最前沿,全面而执著地探析当下军旅文学的新样貌。傅逸尘——新世纪军旅文学的守望者。
一、写什么:更“真”的写作
从“学院派”出身的学养积淀,再到随着军旅文学新军一路走来,傅逸尘能够极为准确地把握军旅文学发展的脉络——由对宏大史诗的追求,到题材叙事越来越走向“个人化”,越来越多的作品开始书写“个人”的历史和“小写”的历史,书写日常生活经验。傅逸尘提出,这样的叙事理念一方面根植于作家“当下”的生存体验,一方面来源于创作主体对历史多元性、复杂性和虚构性的个人化理解。
首先,我们能够看到一大批根植于当下生存体验的作品。正如傅逸尘所言:“小说的终极关怀当是关乎生活和生命,是对人的心灵世界和生命情状的描摹与考量,它依赖着作家丰沛的生活经验与积淀,以及对生活本身的真切体察与精深研究。”①这样的创作观念与许多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创作不谋而合。这些作家大都有着军校背景和部队生活经历,军营承载了他们太多的成长与青春记忆,于是,他们对当下的军队、军营、军人,有着极为丰富的生命体验和不可磨灭的深厚感情,表现更为真实,认识更为切近。王甜的《笑脸兵》塑造了一个因为笑脸灿烂的天赋具有极好的宣传作用而在部队“走红”,甚至因此得到了“优秀士兵”荣誉的普通士兵任小凡的故事,展现青年军人在军队中成长的迷茫与彷徨,用幽默的语言表现小人物的心路历程,挖掘日常生活表层之下的意义。王甜认为,自己的创作“是从切近的地方捕捉题材”,小说创作是一个“寻找自我、获得救赎”的过程。同样,王凯的《魏登科同志先进事迹》从被安排去资料室整理材料的“我”的视角入手,魏登科始终没有出现在正面描写当中,甚至连叙述者也同样好奇,在陈年的资料中,渐渐拼凑出了从前那位有口皆碑、勤勤恳恳的魏登科的形象。在小说的结尾,我们知道魏登科并没有如曾经熟悉他的战友们所愿,被定义为“先进事迹”而受到表彰,这次事故的后果仅仅是这位小人物军队生涯的结束。在这样的作品中,我们能够读到作者对普通个体命运的同情与关怀,读到一种深挚的悲悯之心。书写何以真切?情真,所以意切。军旅生活的影响已经汇入了作家们的创作血脉,理解了新生代军旅作家对那身军装的感情,对昔日战友的感情,也就不难理解他们在展现军营,展现人物的时候,是如何做到叙事的真实了。
其次,在书写军人战场和职场生涯的作品中,体现出强烈的个体关照。军人,是一个特殊的职业,他们注定要用生命承担着自己的职业使命,承担起国家兴亡和民族命运。新生代军旅作家脱离了打造英雄集体的创作程式,人物塑造不再程式化、脸谱化,而是深入开掘每一个普通士兵的生命历程与内心世界,在他们笔下,每个兵都不再相同,他们才是构成军队不可替代的主角。从“人”的角度出发,展现个体生命在生死考验面前的颤栗与英勇,才能找到一条接近真实的路径。例如,以讲故事的方式呈现的《士兵与蚯蚓》《炸药婴儿》《麻雀》,从谍战到战场,重塑逼真的历史情境,更关注个人,是饱含人情和体贴的书写。
“在21世纪的今天,生活现实远比小说还要陆离、生活荒诞远远超出小说荒诞的时代,作家为何创作、如何创作?这是作家必须追问和思索的当代性课题。”②和平年代,职场成了军人们的战场,以此为题材的作品大量出现,作家们更多地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小说的土壤。没有了战争年代生与死的考验,军人们依然面临着别样的困境:军队里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暗涌着的各种潜规则,给每个人带来难言的焦虑和压抑。这些作品真实敢言地揭露了军队内部的暗面,反映出和平年代部队的重重积弊,英雄主义和理想世界在现实的逼仄下走向湮灭,青年的奋斗者们却要面临着不公和苦涩。王凯的《终将远去》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写作为连长的“我”面对一次老兵转退,内心的波澜与挣扎,其间穿插有“我”对曾经的指导员张安定的回忆,于是,一种平凡而伟岸的军人精神在小说中渐渐树立起来了,那种胸怀如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一般,荫蔽着“我”,也警醒着“我”。小说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极为细腻,对部队生活诸多细节的表现也颇费笔墨,尤其是以一位连长的视角,去审视、关怀他最最熟悉的每一个兵,是对基层部队生活真实的、有温度的书写。在他的笔下,每一个士兵都是有血有肉的,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军队就像一部冰冷的机器,永远那样高效、精准、甚至冷酷,王凯将视野投向军队日常生活里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命运遭际,这里面就有了对现实的怀疑和思考的意味。其中寄寓了作者的无奈与抗争,我们可以从中读出灰色的痛感。但在这疼痛的军旅青春中,一种更耀眼的东西也随之浮出水面——那是经历了生存困境、自我省察,经历了灵魂的拷问和欲望的考验之后,军人灵魂越发明晰的那种担当和不朽。李骏的《费尽心机》和《待风吹》,将官场生态描摹得入木三分,体现了军旅文学“强健而充分”的现实主义。作家们展现着和平军营下涌动的暗流,这其中的反思是值得注意的: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下,军人该如何葆有自己的精神和信仰。再如董夏青青的《科恰里特山下》和《垄堆与长夜》,专注于塑造戍边军人的生活常态,她的叙事就是为了真实地去还原基层官兵粗粝困厄的生活,为他们留下生命的轨迹。这种记录式的书写方式,执着地将自己耳闻目睹的经历展现出来的创作态度,展现出当和平年代的军人已经不等同于英雄,而渐渐变得职业化,他们依然面对的生之艰难的现实。作家们反复书写着平凡军人日常生活的生命情态,书写着年轻的军人成长的故事,书写着戈壁上的青春,荒原上的青春,真实的青春。
再次,是一批体现出创作主体对历史的个人化理解的创作。这些作品往往有一个独特的背景创设,发生于陌生化的地理空间,而散发着遥远的想象意味。读卢一萍的《索狼荒原》,一种野性而生猛的气息扑面而来,英雄营长与两位女性的命运交集同时展开,故事情节紧张激烈,但因为作者对帕米尔高原的了解,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表达,人物形象塑造的立体化,残酷现实席卷而来的命运感,涌动其中的人性的挣扎与勃勃生机,那些在西部边塞发生的故事具有了真实可感的血肉。真实的写作是有难度的,因为其中必须融入作者切身的生命体验,卢一萍在新疆生活了二十年,他说:“我熟悉那里尘土和植物的味道,熟悉好多新疆人的皱纹、微笑和叹息。”③他“赖于此并扎根于此”,笔下的人物生长于此,在他的新疆,与土地发生着血肉的联系。真实是建立在细节上的,这是文学于虚构之中唤醒真实的力量。王龙的创作反身向古,强调重大题材、重大历史事件对文学的重要意义。他的《刺刀书写的谎言》耗时两年创作完成,意图以文学的方式使湮灭70年的日本侵华的历史事实大白于天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创作者的历史担当。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一味地谴责或者妖魔化那些侵华作家,而是更多地从人性的角度,去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抱着悲悯之心,与人物悲欢与共,去还原他们在历史夹缝中同样痛苦的灵魂。严复、荆轲、康熙大帝,慈禧太后,甚至维多利亚女王都出现在王龙创设的历史情境之中,充实的知识储备,审视分析的创作态度,令人仿佛被他带入过去的岁月之中,这样书写出的一个个历史事件,真切可感,历历在目,让人有一种置身历史的实感。
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期的到来,国防和军队建设也面临着新的考验与变化,在编制的调整、装备的更新、战斗力的提升之外,更有着军人内在情感和精神世界的变化,而这一转化无疑同样重要。展现转变过程中生命个体的生命情状,是军旅文学全新且有价值的话题。军旅文学更关注个人的、小写的历史,日常经验崛起,作家们尽可能真实地记录、塑造军人和英雄形象,这种个人化写作也为军旅文学拓展了题材空间,由理想主义转向了更“真”的写作。
二、怎样写:对文学本源性的回归
近年来,由于其生动鲜活、紧张曲折的故事情节,军旅题材的作品在图书市场和电视剧市场都具有相当的认可度,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多元化、宽松化的文化环境,也给了军旅文学更大的生长空间,得以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更加回归到文学自身。不仅在内容题材上得到了拓展,艺术技巧方面更是做出了异彩纷呈的全新尝试。傅逸尘有着丰厚的学术功底,他以“学院派”的眼光来打量今天的军旅文坛,见证着军旅文学一点一滴的突破与成长。
首先,艺术技巧的尝试表现在作家们的叙述方式上。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创作摆脱了英雄叙事的藩篱,相反,非英雄叙事佳作迭出,军旅文学也因此实现了真实性的复归。我们已经很难找到完美无瑕的理想主义英雄,取而代之的是有血有肉、性格各异的真实军人。叙述不再局限于宏大的历史视角,而是可以从更加个人化的角度切入,从而赋予历史与生活更为具体感性、生动真实的面貌。在此基础上,叙述方式朝着各个方向开拓出去。举例来说,董夏青青的叙述是“记录式”的,她的小说几乎完全是生活的片断。她更相信自己的眼睛与耳朵,而不是理想与想象,于是,她不再煞费苦心地编织故事情节,而是转为诚实的记录,这种片断式的写作,不再关注线索与情节,时常旁逸斜出,于是,作品中甚至没有了完整的人物,这在某种程度上切合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论。许多作品都采用微观性、个体性的叙述视角来展开叙事,勾勒出具体可感的历史时空和个体的心灵体验。于是,历史背景的展示不再是首位的,战争描写时常是片断性的,叙事变得极富主观性,也因此更能体察普通的灵魂的真实样貌。整体上,叙事方式变得越来越“非传统”、“非意识形态性”,如傅逸尘所言:“作家在个人化、边缘性和日常经验性的叙事伦理理念之下建构起消弭历史所指深度和崇高审美风格的‘个人化历史’,彰显了迥异于传统的‘个人私语’式的叙事风格。”④历史在作家们的想象中得以再生,不再执着于对历史再现,而是在历史中注入自己的思考和情感价值,这与海登·怀特的观点相契合。这种“个人私语”式的叙事策略,取代了“史诗性”的宏大叙事模式,从个人化的视角切入历史,将历史变成了具体的生命历程和人生经历的一部分,变得更加日常化,也更具体验性与生命力。例如《亮剑》中,历史作为一种时空参照,映衬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作者通过对历史的主观想象,将人物放置于历史进程当中,塑造出具有鲜明个性的圆熟的人物形象。另外,许多作品选取第一人称叙事,强调“我”的在场,置身于历史语境之中,增强了叙述的可靠性。在《坝上行》《穿军装的牧马人》《沙漠之羊》等小说中,作者都采用了“第一人称记忆”叙事,增强了历史的心灵体验效果。“零度叙事”,是法国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提出的,指的是一种不介入、中性的写作立场,在董夏青青的小说中,叙述者虽然在场,但却接近于“零度叙事”,这一点可以作为创作的风格所在,而前路仍值得继续探索。更有作家采用了互涉文本的叙事策略,例如李亚的《将军》,在对老将军一生的采访记录的叙述中,又通过老将军的梦境和幻觉,插入了一个并行的过去时的叙事线索,形成了一种过去与现在并行的复调式叙事结构。历史叙事与现实叙事各自独立又相互补充,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演变更加真实,更有力度。
其次,在小说的结构上,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创作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质。许多作家不再以故事来结构小说,而是更加关注人的心灵世界和生活本身。这是对以往小说过度依赖故事性的一种反拨。傅逸尘在他的评论文章《怀想寓言时代起》中写到,近一二十年来,写一个“好看”的故事已经成为很多中国作家的创作旨归,这使他不能不怀念先锋文学曾经呕心沥血建构的寓言时代。他用大量的中西方文论来打量今天的中国军旅文坛,如马尔库塞的作品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观点,去分析新世纪军旅小说形式和技巧的突破与创新。西元的小说尤其值得注意,《死亡重奏》堪称佳作,借用西方音乐形式的结构,交织成一曲悲壮而写意的“死亡重奏”,他的小说兼有文学的美、音乐的美、绘画的美,没有中心情节和中心人物,而是聚焦于时空碎片,却紧张激烈、寒暖交织,使人仿佛亲临战场。结构方式颇似中国画里“散点透视”的技法,而故事似乎是可以被消解的。项小米的《英雄无语》更是三条线索穿插并行来建构故事,结构极具形式的美感。在李亚的《将军》中,人物和事件的呈现是作者经验和见闻的拼贴,整部作品打破了现实与梦境的界限,令人难分虚实,通过回忆与当下的完美对接,带给人一种丰沛的现实主义的力量。
再次,就是作家们艺术技巧的突破与创新,这是一种多向度、多元化的提升。2016年,海飞的《麻雀》改变的同名电视剧热播,它的原著小说就足够精彩,小说围绕日常经验和人物铺展,叙述重点落脚到人物上。小说本身已经充分具备了影视作品的特质,海飞大量极具视觉化的语言,将故事编织得极具画面感,同时对小说和剧本的区别有着深刻的认识,注意小说语言结构上的张弛有度,注意小说的留白,从而使他的创作保持了一种特有的美感。话语狂欢对语言的讲究到了字雕句琢的程度,语言的狂欢消解了人物、事件、情节,连死亡都被沉浸在急促、跳跃、激烈、疯狂的语言之中,成为一种特殊的诗学诉求,如张卫明的《城门》。小说速度减缓,通过大量的心理描写、穿插其中的评论、人称的交替和回忆性文字的出现,在历史和现实之间交替转换,从而区别于传统的“线性叙事”。此外,还有戏仿和反讽手法的运用,反意识形态,反英雄叙事,以幽默滑稽的笔法揭露生活荒诞的本质,如朱鸢的《坝上行》。
可见,新生代军旅作家有意识地以更贴近文学本质的方式去书写军旅文学,努力去实现对文学本源性的回归。
三、写得怎么样:新世纪军旅文学世界的建构与超越
新世纪以降,走在强军路上的中华民族为军旅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土壤,军旅文学迎来了发展的“第四次浪潮”。新生代军旅作家,以不懈的创作实践,为军旅文坛注入了一脉新鲜而强劲的血液,实现了对前代军旅创作的超越,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品格。总体而言,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创作有着蓬勃发展的态势,题材和艺术均处在生长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不得不引起重视的是,这些创作的文学风格有待成形,尚存未来生长的瓶颈,这是对新生代军旅作家们的考验,更是对他们未来创作的期待。
新世纪军旅文学对前代创作的突破以及数年来着力开拓出的新质,无疑是卓有成效的。在新写实小说的影响下,写日常生活的军旅文学找到了新的叙事方向。他们开始从新的角度观察、认识生活,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情感体验和精神资源,写细腻的心灵体验和人性内面,从个人化视角切入,以小写大,写个体人物的生命与存在。战争历史题材的创作,则受新历史主义影响较深。在历史的建构中融入作者的感性思考,以情写史,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有的作家的作品有着深刻的思想力度,涉及到对战争、死亡等大命题的审视与认识。在新写实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下,新世纪军旅文学对日常生活和战争历史的表现都具有了可喜的新质。正如朱向前教授所言:“生活首先不是大时代、大转捩、大跌宕、大事件,它首先是个人的际遇和命运,而个人感受又总是由绵密、细致、柔婉、丰满的生命和生活之流所组成。有了这个,时代、事件才是立体真实的和鲜活可感的。”⑤作家们有意识地从日常生活中寻找新鲜的感觉与素材,细细描摹着生活经验的丰饶与精细,欣喜与苦难,从中极为珍贵的一点是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作家的悲悯情怀。王凯的创作颠覆了宏大的军旅叙事,为小说注入了关乎生活和生命的形而上的哲思,里面有对现实本质的怀疑与思考,有对多种对立事件的把握与表现,有时隐时现而又真真切切的生命的痛感。对世俗和官场的潜规则,敢于质疑,敢于反拨,具有理性的思辨力量和当下的现实意义。西元在创作中关注到“无名英雄”的群体,通过成长模式的运用,加入对话、回忆等方式的表现,为每个人物写一段“小历史”,使得情节发展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成长同步展开,加之对人物内心世界和灵魂挣扎的细致刻画,塑造了一个个血肉饱满的平凡英雄,为和平时代的英雄书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其次,新世纪军旅作家的文学语言较之以往,更具有了轻盈和诗化的质地。例如,王甜的小说语言幽默、细腻,语汇时尚化,充满着清丽自然的美感和富有智性的文化价值。卢一萍的语言带有“兵味”,具有军旅文学的色泽与品质。他的《帕米尔情歌》语言从容、舒缓,将自己为寻找“真实”的生活面目流下的时间和汗水化为文字,贴切得像一曲西部边塞的牧歌:“从射击孔望出去,夕阳像一坨即将燃尽的牛粪,在我们身后缓缓下沉。”⑥好一幅令人神往的异域景象。同时,他能够捕捉到生命禁区中的喜剧色彩,运用恰到好处的夸张和戏谑,丰富了小说的喜剧内涵,流露出生命的无意义与生存的荒诞。
新生代军旅作家以自身的经历和创作,使当代文学的地理空间逐步完整,这是他们创作实绩的第三个方面。卢一萍的帕米尔高原叙事是其典型代表。书写巨大社会变迁下的酸甜苦辣、挖掘塔吉克民族精神领域的“异质”性存在、守护笔下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他创作上三个维度的突围。人性的挣扎与复苏在荒原上生生灭灭,悲喜交织,对于生命的无意义、生存的荒诞、生之孤独与痛苦的表达,超越了军旅文学的局限,向更加广阔的维度飞升出去。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到帕米尔高原,流沙和荒漠,绿洲和雪山,在极边之地的万事万物、芸芸众生之间,卢一萍说:“人类之所以能适应一切,因为其本身自带天堂。”⑦
论及新世纪军旅小说的不足之处,傅逸尘表现出了更多的关注和忧虑。正如卢一萍所说:“80年代军旅文坛曾占据中国半壁江山,即使90年代,这个‘坛’还在。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已构不成一个坛了。”这样的忧思很大程度上是对新世纪军旅文学创作新的寄望。
忧虑首先来源于真正的了解。总体来说,傅逸尘对当下的军旅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的文学应该从狭窄的个人视域和封闭的内心世界走出来,以更加客观的创作态度和更加强健的写作伦理、更加开阔的美学精神,去追求创作的深度和高度。相对于前代作家,“70后”军旅作家特别执着于日常生活的写作,该现象不仅局限在新世纪的军旅文坛,而是在经济因素的撬动下这个时代文学的总体趋向。“应该看到,这种‘非虚构写作’在给作者带来叙述的客观性、真实性、民间性等品质的同时,不可避免容易削弱作家审美虚构想象的自由空间,而且往往难以避免文学性品质弱化的倾向。”⑧贾平凹就曾表达过自己的忧虑:“这种文学现实无形中改写了中国社会的现实,给人一种误导,以为现在的中国人都是这么活着的。”⑨纵观世界级的经典文学名著,无论是托尔斯泰、雨果还是肖洛霍夫,他们展现的都是大的历史题材、重大的历史事件,其作品充斥着作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极具恒久品格的现实意义,而仅仅有日常生活和个人经验是无法做到的。许多军旅作家的艺术技巧已经相当纯熟,然而,题材的开拓和思想的深度甚至已经成了困扰这个群体的创作瓶颈。加之兴起于21世纪初的“底层叙事”思潮的影响,许多青年作家走入了“形而下叙事”的圈子,造成了作品气象格局的狭小,与新军事变革中波澜壮阔的军旅现实拉开了距离。对于21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呈现今日之中国,如何阐释今日之中国,这是我们亟需面对的”⑩。“新生代军旅作家”在整体上还没有形成具有辐射影响的集群,太多的军旅文学作品一旦将作者的名字隐去,读者将很难辨别这篇小说究竟出自哪位作家之手。傅逸尘强调主流社会生活、重大题材、重要历史、重要事件之于文学的重要意义,呼吁“70 后”的军旅作家由“怎么写”再回到作“写什么”的问题上去。王凯小说中的“疼痛”书写,写世俗、欲望、成长过程中的痛感,最终指向的却是更为坚韧、宽广、豁达的人生态度,更为崇高的理想和信仰,在故事层面进行批判和思辨,是表现军旅气象的优秀范例。不仅仅局限于表现个人的精神世界,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些内心的挣扎与困顿的探索,将小说的气象格局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学高度,从而获得一种诗性的升华和精神气度的开阔。
傅逸尘认为,“新生代军旅作家”未来生长的瓶颈,首先在于把握现代军旅生活的能力较弱。我军新军革命浪潮、信息化建设的图景、战略战术、武器装备、训练方式等都出现了新的调整和变化,基于这些变化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没能充分地予以把握,缺乏对于当下军队发展主流的表现,所塑造的人物更是缺乏典型性和代表性。1990年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来,英雄形象在文学中渐行渐远。回望《安娜·卡列尼娜》《欧也妮·葛朗台》《约翰·克里斯朵夫》等文学巨著,我们当下的作家很少再去用人物的名字直接命名一部作品。“英雄叙事应该是军旅文学的精神风骨”,傅逸尘提倡“新型高素质军人”的写作,以文学的方式建构新的军人伦理,写出和平年代新英雄的人性光彩,塑造不朽的人物形象。
第二,由于市场经济和信息化时代的影响,市场机制、大众文化下的军旅文学的确获得了一个更为多元化、宽松化的创作环境,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我们不缺少‘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物质发展主义,却还没有形成心灵可以依附的文化伦理和道德规范。”⑪在这样的情况下,新世纪的中国作家集体陷入了极力编织一个好看的故事的创作模式中,这样的结果就是小说的类型化。然而,好的文学不仅仅只有故事,在追求世俗化、戏剧化、大众化的路上,作家们不能忘记还应有对思想性、哲学性的追求。唯有具备了这样的特质,文学才有可能成为时代之文学,甚至具有永恒精神意义的文学。应当努力穿透时代的考验,以思辨性的创作立场,创作出具有超越性的文学作品。
第三个方面的缺陷,是创作中精确和真实的缺失,写实能力日趋下降。当创作中的主观性倾向压倒了对真实和细节的执着,小说的客观性效果就大大削减了。文学必须迈过虚妄的大门,才能获得永恒的审美品格。军旅文学,应当是最靠近对于战争、死亡等重大问题的文学类型,新生代军旅作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应当强化生命意识,注重死亡哲学,回归文学自身,回归对军人真实的个体生存状态的反映,将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融入新时期军旅文学精神之中。
总而言之,新世纪军旅文学亟待精神上和技术上实现双重突破,创建一片完整而成熟的思想艺术场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面旗帜。
结语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认为:“当下,军队建设走进强军新时代,军旅文学乃至军旅作家的职业道路面临新的前景,迫切需要思考军旅文学在新时代应该如何发展。”⑫军旅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曾取得过极为辉煌的成就。步入新世纪,作为率先命名并跟踪研究“新生代军旅作家”的批评家,傅逸尘秉持着客观的评论态度,既看到了这个作家群体蒸蒸日上的创作势头和可贵之处,也看到了他们存在着气象格局狭小和未来生长瓶颈的问题。这首先表现在,作品的气象、格局和境界上仍然存在的缺陷,作家不应该仅仅满足于表达个体的精神世界,还应该深入挖掘内心世界的精神挣扎,来表现人性的复杂、追求人性的崇高,从而使作品获得饱满的精神气质和更为强大的生命力,这一点是“新生代军旅作家”在整体上还未达到的。此外,“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创作还存在着过度沉溺于“底层叙事”,缺乏大视野、大气象;过分抽离了军旅文学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核,缺乏对于当代英雄的塑造;现实性的缺失和想象力匮乏,沉溺于“形而下叙事”的泥淖等问题,傅逸尘认为,文学若要与时代同步,甚至走在时代前面,就要“先立其大”,“以一种大方大正的理想、情怀、精神、气魄,把文学从低迷、小我的趣味里解放出来”⑬,作为批评家,他坚持真正的文学批评“从来都不应该成为作家作品的附庸”,“不应该伴随着文学的堕落而沉沦”⑭,而应该“引领者着文学的发展、预示着未来的方向”⑮从而建构起一个“属于文学与批评自身的温暖、自由、高贵、和谐的公共场域和精神家园”⑯,意图建构并超越“新世纪军旅文学”,体现出一位“80 后”评论家的文学责任意识和文学担当。总体而言,《“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既为我们展示了21世纪军旅文学主力较高水准的创作,创作实力不容小觑;也以负责任的文学批评的形式介绍了“新生代”军旅文学的整体风貌、艺术水平、理论批评和发展前景,全方位地展现了新世纪军旅文坛各方面的成果,并为其未来发展提供了诸多经验和参考,吹响了新时代军旅文学的集结号。
①傅逸尘《灰暗中闪耀着金属的光泽》[A],《“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②⑧⑩⑪张丽军《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性蜕变的痛苦灵魂——论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J],《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③李墨泉、卢一萍《孤寂之中的灿烂与繁华》[A],傅逸尘《“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235页。
④傅逸尘《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的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A],《“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478页。
⑤朱向前、徐艺嘉、西元《军旅文坛“拳击手”》[A],傅逸尘《“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409页。
⑥吴平安《拓展的文学地理空间——以〈帕米尔情歌——卢一萍中短篇小说选〉为例》[A],傅逸尘《“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224页。
⑦卢一萍《高海拔场域的写作》[A],傅逸尘《“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233页。
⑨傅逸尘《从“怎么写”再回到“写什么”》,《“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251页。
⑫李菁《不断吹响中国军旅文学的“集结号”——傅逸尘编著〈“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研讨会在京举行》[OL],http://www.chinawriter.com.cn/n/n1/2018/1013/c403994-30338582.teml.
⑬傅逸尘《21世纪初年军旅非虚构叙事一瞥》[N],《中国艺术报》,2017年7月。
⑭⑮⑯周明全《傅逸尘:“新潮军旅批评家”的建构与超越》[A],《“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5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