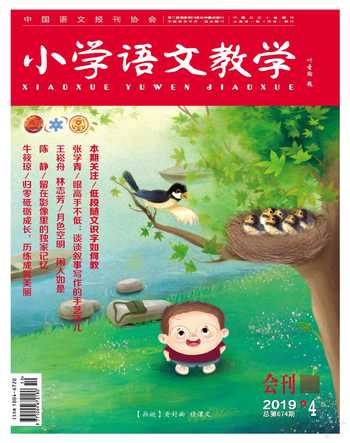汉字三对偏旁解析
2019-09-10金文伟
金文伟
汉字里有三对偏旁值得注意,它们或因形义同源而容易混淆,或因表义特殊而望文生义。理解和掌握它们,不仅错别字减少,识字效率提高,还能学到相关的汉字文化知识。这三对偏旁是“皿”与“血”、“纟”与“幺”、“弓”与“矢”。
一、“皿”与“血”
“皿”与“血”形近,“血”多一个短撇,两偏旁的字义和构字作用由此不同。
1.皿
甲骨文写作“■”,象形字,像一个带底座的大口容器。小篆写作“■”,隶书写作“■”。本义是器皿。“皿”在构字中主要作意符,表示器皿的意思。试举数例。
盂,从皿,于声,是一种盛液体的敞口器皿,如“痰盂”。引申指盛饭的食器,如“钵盂”(古代和尚用的饭碗)。
盆,从皿,分声,本义是一种口大底小、比盘深的圆形盛器,如“脸盆”“花盆”。比喻引申指盆状物,如“盆地”。音符“分”是前鼻音,盆也因此是前鼻音。
益,从皿,上部是横放的“水”字,会意水从皿上漫出。本义是溢出。水溢出多因加水过多,由此引申为增加,增长,如“延年益寿”“益智玩具”。由“增长”引申为利益,好处(跟“害”相对),如“公益”“受益匪浅”。进一步引申为有利的,如“益鸟”“良师益友”。后来,引申义成为“益”的常用词了,人们就再为“益”加意符“氵”造“溢”字表示。这种现象叫字的分化,“溢”是“益”的分化字。
蛊,繁体写作“蠱”,会意字,从蟲(用三个虫表示很多虫)从皿。古代传说取百余毒虫放于器皿中,使其互相咬食,最后剩下不死的叫作“蛊”,最毒,可以用来毒害人。“蟲”规范简化为“虫”,“蠱”也类推简化作“蛊”。本义是害人的毒虫。引申为毒害,使人迷乱,如“蛊惑人心”。又引申指害人的邪术,如“蛊道”。
2.血
比“皿”多的这一撇表示什么呢?看甲骨文,“血”写作“■”,皿中有一个小圆圈,这是血液。原来商朝人举行祭祀活动或会盟时有一种仪式,把动物或人的血液滴入盛着酒的器皿中,或供奉神祖,或直接饮用。“血”字由此产生。演变到小篆写作“■”,“血液”写成了短横;古隶写作“■”,短横(血液)在“皿”上面;楷书写作“血”,“血液”写成了撇。撇运向“皿”的左边短竖——这样能使前后笔衔接,加快写字的速度。本义是血液,特指祭祀用的鲜血。由于人们把保家卫国而流血牺牲看作勇敢、忠诚的体现,血就被用来比喻刚强和热诚的精神,如“血性男儿”“血气方刚”。也引申指像血一样的红色,如“血色”。流血会使很多人流泪,于是本义又引申为泪水。如“泣血涟如”(《周易·屯》),是说泪流不止。
“血”在构字中作意符时表示血液,如“衅”;作音符有“恤”。
衅,音xìn,会意字,从血从半(表示缝隙),会意为古代杀牲取血涂于器物的缝隙,是祭祀的方式之一,如“衅鼓”,“(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孟子·梁惠王上》)由涂抹缝隙引申为缝隙,嫌隙,如“寻衅”“衅端”。进而引申為争端,如“挑衅”。
二、“纟”与“幺”
这两个偏旁形近且同源,须认真辨析。
1.纟
“纟”的甲骨文写作“■”,像一把细丝绞在一起的形状。小篆写作“■”,下部“■”是束丝的头儿。隶书写作“■”,楷书写作“糸”,读音mì。“糸”现在只作偏旁,在字左时繁体写作“糹”,简化为“纟”;在字下部时仍写作“糸”。我们知道,“糸(纟)”在构字中表示蚕丝、线绳、纺织、颜色等义,如“纤、绸、织、素、紧、绿、紫”。这里解析几个字以增强理解。
级,形声字,“纟”表示蚕丝,及声。本义指丝的优劣等级。后引申泛指等级,如“级别”。进而引申指学校里学生的学年分段,如“年级”“班级”。引申为量词,如“五级台阶”。
综,形声字,“纟”表示纺织,宗声。本义是织布机上使经线和纬线能交织的装置,引申为总合,聚合,如“综合实践”“综合分析”。
绍,形声字,“纟”表示丝线,召声。本义指一根丝线断了或不够长,用另一根丝线接上。由此有了继承、接续的意思,引申为介绍,两个不相识的人,经过别人介绍或自我介绍而互相认识了,犹如用丝线联系在一起。
索,会意字,甲骨文写作“■”,从宀从糸从双手,表示房屋内有人用双手搓线绳。小篆写作“■”,楷书简化写作“索”,“糸”(mì),丝线。这是会意字。本义是搓绳索。古人把小的称为“绳”,把大绳称为“索”,引申泛指各种绳索或链条,如“索道”“铁索桥”。搓绳时需要把绳扭合在一起,又引申为寻找,探求,如“搜索”“探索”“索引”。
2.幺
幺的甲骨文也是“■”,本义也是一把细丝。引申为细、小。由小又引申为排行最末的,如方言中的“幺妹”“幺儿”。又引申用作数词一(最小的整数)的俗称,如“呼幺喝六”。
“幺”在构字中作意符,表示微小、细小等义,如“幽、幼”;也作声符,如“吆”。
幼,会意字,从幺从力(力气),合起来就是“小力”。本义是力气小。力气小多因年幼,引申出“幼儿”之义。也引申指小孩儿,如“幼不学,老何为”(《三字经》)。
三、“弓”与“矢”
这二字并不形近,却同属弓箭系统,词义关系密切,作偏旁表意有特色。
1.弓
甲骨文写作“■”,象形字,像一张弓的形状,弓背、弓弦、弓梢皆备。小篆写作“■”,省去弓弦而扩大了弓梢部分;汉隶写作“■”。本义是射箭或发射弹丸的器具。引申指弓状物,如“琴弓”。因弓形弯曲,又引申为弯曲,如“弓身”“弓步”。
“弓”在构字中主要作意符,表示弓箭、弓形、弯曲等义,如“弦、弹(dàn,弹弓)、弯”;也作意符兼音符,如“躬、穹(qiónɡ)”。弓箭是古代人民同外界作斗争的重要武器,因此蕴涵着人类丰厚的传统文化。
引,是一个从构字到引申义都很有意思的字,从弓从丨(ɡǔn,指箭),表示箭在弦上即将射发。本义是开弓。“开弓”要拉弦,因此引申为牵,拉,如“牵引”“引车卖浆”。“开弓”使弦伸长,引申为伸长,延长,如“引申”“引领相望”。“开弓”时箭指前方,又引申为引导,带领,如“引领”“引路”。“开弓”时弓弦往自身方向拉,引申为引来,招引,如“引火烧身”“抛砖引玉”。进而引申为引起。“开弓”时弦往后拉,引申为引退,引避。
张,形声字,从弓,长声。古人用弓时安上弓弦,叫“张”,不用弓时放松弓弦,叫“弛”。安上弓弦,引申为拉开弓,张开,打开,扩张。进而引申为放纵,如“张狂妄行”。“张弓”欲发射,又引申为主张。“张弓”则弦紧,引申为紧张,进而引申为慌张,张皇。由“张弓”欲射又引申为举目而望,如“东张西望”。又引申为排开,陈设,如“张灯结彩”。用作量词,如“一张弓”“两张纸”。
2.矢
甲骨文写作“■”,象箭的形状。金文写作“■”,小篆写作“■”,汉隶写作“■”。演变得不象形了。本义是木制的箭。先秦称木制的为矢,竹制的为箭,秦汉后逐渐混同。假借为“誓”,表示发誓,如“矢志不渝”“矢口否认”。又为求词雅,书面语常以“矢”代“屎”,如“千村薜荔人遗矢”(毛泽东《送瘟神》其一)。
矢作偏旁,在有的字中作音符,如“雉、疑”;在有的字中作意符兼音符,如“知”;更多的是作意符,表示箭、直等义,如“医、族、矫”。
不过,弓和矢作意符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表意功能:作度量物体长短的器具。因弓长矢短,弓用于度量長的物体,矢用于表示短的物体。如“疆”字,本义是田界,从弓从土从畺(jiānɡ,用两田三横线表示田间界线),弓在“疆”中表示丈量田界、以弓记步的意思。矢则在“短”中表示空间或时间的距离小,如“短途”“短期”;在“矮”“矬”字中表示人的身子短,如“矮个儿”“矬子”。
由于很多人不知道“弓”“矢”的这个特别的表意功能,因此有人认为“矮”“射”两个字的意思弄混了。“矮”从“矢”,应该是射箭的意思;“射”从身从寸,会意身子一寸长,应该是矮的意思。“矢”旁已解析,现在谈谈“射”的“寸”偏旁。
“寸”字产生于“又”字。“又”的甲骨文写作“■”,像右手形,三指代表五指,伸向下方的一笔是手臂。金文“寸”字写作“■”,在“又”(手)下加指示符号(点),指手腕下的一寸处,隶书写作“■”。本义是寸口,中医把脉的地方,引申指比较短的长度单位:寸。但是作偏旁时,“寸”却主要是作意符,表示手臂。比如,付,从人从寸,是手持物给他人;守,从宀从寸,是用手护卫;尊,从酋(久酿之酒)从寸,是手持好酒敬人。所以“射”字,从身从寸,表示的是从身边引弓发射之意。■
(作者单位:福建省集美大学)
责任编辑 郭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