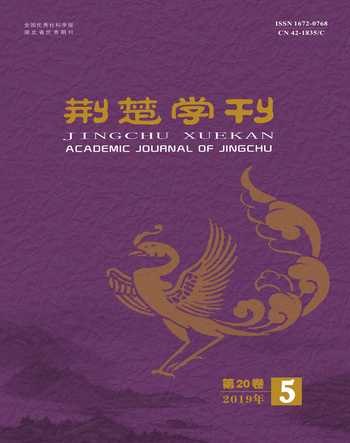美国出口管制法的域外管辖
2019-09-10卢菊
卢菊
摘要:美国域外管辖与长臂管辖是不同的概念,两者在定义、依据和主体上均存在区别。在出口管制法方面,美国借助立法确立的产品或技术国籍、控制关系以及国际法上的保护原则不断扩张其域外管辖。这一做法不符合国际法的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原则,且违反《关贸总协定》项下的出口义务。为应对美国域外管辖的过度扩张,一方面,中国企业应当充分运用司法规则合理规避或主动挑战其管辖并加强自身的合规建设;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双边协商或诉诸WTO来解决争端。
关键词:域外管辖;出口管制;WTO;安全例外
中图分类号:D9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19)05-0054-07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美国利用其反腐败、反垄断、出口管制等方面的法律对中国企业发起调查或诉讼,并以此削弱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推行贸易保护。从中兴到华为,美国将针对中国企业的域外管辖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聚焦于出口管制的趋势愈发明显。域外管辖是指一国在其境外行使主权权力或权威[1],有别于长臂管辖。事实上,国际法并不绝对禁止域外管辖,但国家行使域外管辖是有限度的。美国频繁针对中国企业的域外行为适用其国内法的做法亟须受到限制。
一、美国域外管辖不是长臂管辖
“域外管辖不是长臂管辖(long-arm jurisdiction),因為长臂管辖只是对人管辖权 (personal jurisdiction)中的一种特别管辖权。”[2]4《布莱克法律词典》将长臂管辖定义为,在起诉时,对与管辖区域(法院地)有联系的非居民被告的管辖权。长臂管辖起源于1945年的国际鞋业公司诉华盛顿州案。美国联邦法院在该案中确立了“最低联系”(minimum contacts)原则,即非居民被告只要与法院地存在最低限度的联系,美国法院即可对其进行管辖。按照国际法理论,管辖一般包括属地管辖、属人管辖、保护管辖和普遍管辖。但是长臂管辖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
事实上,长臂管辖属于对人管辖权。美国法院若要管辖一桩以外国人为被告的民事案件,必须同时满足对人管辖权、事项管辖权和审判地三个要求[3]。有学者认为,美国法上的长臂管辖仅限于民事诉讼中的对人管辖权[2]6。而美国在对外国企业进行域外管辖时,往往还会涉及刑事指控,如依据《反海外腐败法》(FCPA)对外国企业提起诉讼。“从其对违法行为定罪处罚角度出发,《反海外腐败法》属于刑事法律制度。”[4]再如依据出口管制法等经济法对域外行为进行管辖。也就是说,域外管辖和长臂管辖的依据不同。一方面,两者依据的法律所涵盖的范围不相同;另一方面,域外管辖的依据为联邦法律,而长臂管辖的主要依据为长臂法规,其由各州制定。联邦法院虽然可以借用其所在州制定的长臂法规确立对于外国企业的对人管辖权,但国会并未在联邦层面上制定长臂法规。此外,域外管辖往往由行政机关行使执法管辖权(执行管辖权)启动,随后也可能会引发法院行使司法管辖权[5]172。而长臂管辖的行使主体主要是法院。综上,域外管辖与长臂管辖的不同集中表现在两者的定义、依据和主体上。
然而在政治、外交领域,存在将两者混用的趋势。2018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中就写道,“长臂管辖”是指依托国内法规的触角延伸到境外,管辖境外实体的做法。并以出口管制为例,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要求其他国家的实体或个人必须服从其出口管制法,否则会进行民事、刑事、贸易等制裁的情况进行阐释。2019年6月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中再次提到,美国政府连续对华为等多家中国企业实施“长臂管辖”制裁。事实上,美国商务部等政府机构依据出口管制法对华为等中国企业进行制裁是行使域外管辖的表现。此外,很少有学者对两者进行明确区分,存在以长臂管辖概指美国管辖中国企业域外行为的情况。简言之,域外管辖是一个更大的概念,两者有交叉但又相区别。
二、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管辖的依据
美国出口管制法律体系由一系列法律、法规及规则构成,包括《出口管理法》等基础法律,《出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及《商业管制清单》等规则。出口管制法律法规众多,不同部门联合进行管理,虽各司其职但也不免存在交叉。其中商务部在出口管制法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出口管制实践的增加,其域外管辖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属人原则,仅以自然人的国籍为依据推行出口管制法的域外效力,而是基于产品国籍或技术国籍、控制关系与保护原则不断扩张。
(一)基于产品或技术国籍确立管辖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通过《出口管理条例》实施出口管制政策。与美国其他规定域外效力的法律不同,《出口管理条例》通过产品或技术与美国的联系来判断外国企业是否受约束,即基于所谓的产品国籍或技术国籍。该条例以肯定式列举和否定式列举的方式规定了适用的主体。以受到《出口管理条例》规制的产品为例,其包括:(1)美国境内的产品(包括美国原产产品和外国产品);(2)原产于美国的产品(不论其位于何处);(3)使用美国产品作为零部件或原材料的外国产品(有不同的比例要求);(4)采用了美国技术或软件的外国产品;(5)由美国境外工厂生产的产品,但该工厂使用美国的技术或软件建成[6]。
对于外国企业而言,其主要在以下两种情况中受到美国出口管制法的限制。首先是基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等考虑,美国政府对源自美国的产品和技术实施出口管制。这里的“出口”包括出口、再出口和(国内)转卖。工业与安全局所认定的“出口”概念针对原产于美国的产品或技术的所有流转,采取的做法是考察产品的终端用户或终端用途(end-user and end-use),即美国原产产品或技术不可以通过任何流转被禁运对象所用[7]。也就是说,若外国企业进口了美国原产产品或技术,不得将其再出口至禁运国家。
其次是对非原产于美国的产品或技术即外国产品或技术进行限制。《出口管理条例》在以下几种情况中管制外国产品:(1)美国境内的外国产品,包括运输途经美国的外国产品;(2)外国产品中的美国成分(美国产品作为零部件或原材料)达到一定比例;(3)使用美国技术或软件生产的“直接产品”。只要外国产品落入美国出口管制法的范围,那么该产品也将适用终端用户或终端用途原则受到考察。2016年,中兴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就因将含有原产于美国的零部件的产品再出口至伊朗等受制裁国家而违反美国的出口管制制度。
(二)基于企业控制关系确立管辖
美国《对外关系法(第三次)重述》中讨论了基于公司从属关系行使的管辖权。其中指出(国内)母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在其与外国分支机构和子公司之间建立了类似国籍的联系[8],从而确立美国法律的域外管辖。出口管制方面的法律亦是如此。在1977年的《出口管理法修正案》中,国会引入了“美国人”(United States Persons)概念,并将其界定为“任何美国居民或国民,任何国内的相关人(包括一个外国实体在美国国内的子公司)”以及“任何在事实上受控于国内相关人的国外子公司或分支机构”[9]。 2018年8月13日正式签署生效的《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对此作出保留[10]。也就是说,中国企业设立的美国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将被视为“美国人”而直接受到规制;而美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基于母公司对其的控制属于“美国人”,也受到美国出口管制法规制。
关于公司国籍的判断标准,主要有多数英美法系国家主张的设立地主义以及一些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住所地主义。而基于控制关系确立国籍的做法并不是主流,这主要是由于控制权的认定存在困难等缘由,因此其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在以控制关系为依据确立美国国籍进行域外管辖的过程中,对于那些不是按照美国法律设立,也没有位于美国境内的子公司而言,该做法并不合理也不能使域外管辖正当化。
除了以立法模式规定出口管制法的域外效力,美国还通过法院的司法程序推进其适用。当法律缺乏对其域外效力的明确规定时,法院往往会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确立域外效力,而此时的法律解释大多是以立法目的为基础的。美国经济法的域外适用问题从20世纪初的不承认本国经济法的域外效力,发展到防御性地域外适用美国经济法,直至富有侵略性地主动域外适用美国经济法,对立法目的的司法解释方法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11]。出口管制法属于经济法,也符合这一发展趋势。
(三)借助保护原则确立管辖
美国《对外关系法(第四次)重述》指出,美国行使管辖权应当符合五项原则之一,即属地原则、效果原则、属人原则、保护原则及普遍原则[12]402。在出口管制法方面,除了传统的属人原则,保护原则也被用来说明域外管辖的正当性。保护原则是指,国际法承认一国具有管辖权,就非本国国民在其领土外针对国家安全或针对有限类别的其他基本国家利益的某些行为制定法律[12]412。
美国充分运用该原则推行出口管制法的域外管辖。1988年,美国国会针对东芝事件通过《多边出口管制增补修正法案》规定,如果“一个外国人违反了一个国家(美国)以安全为目的而颁布的对出口实行管制的规定”,就可依美国的出口管制法对其进行制裁[13]271。以国家安全和基本国家利益为切口,美国借由保护原则为其规范外国企业的出口行为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实践中美国往往通过宽泛理解该原则来扩张其域外管辖,比如对于上述国家安全的扩大解释,以此推行贸易保护,最终引发贸易摩擦等问题。对于美国依据保护原则管制外国企业出口的行为,有学者指出保护原则适用的对象为针对国家的犯罪时,仅限于弑君、伪造国玺和货币、偷渡、走私等特定的罪行,而不是侵犯本身就“捉摸不透的”(amorphous perceptions)所谓“国家安全”的行为[13]272。美国依据国内法适用保护原则的做法被质疑不具有国际合法性。
三、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管辖的违法性
事实上,在几乎所有与美国政府就出口管制案件达成的和解协议中,美国政府从未解释其为什么对外国企业享有管辖权。但是这些协议的首要条款均要求相关当事人承认美国法律及其执法机构的管辖权[14]。美国遵循出口管制法进行域外管辖有其国内法依据,而国际法层面虽有属人原则、保护原则作为支撑却仍具有违法性。
(一)未遵守国际法基本原则
国家依据属人原则对其域外的国民进行管辖时应当受领土主权原则的限制。“即使一个国家对它的国外国民有属人管辖权,只要他们是在另一个国家的领土内的,该国行使属人管辖权的能力就受到了限制。”[15]国家的管辖权源自主权,国际法禁止一国在他国领土内任意行使管辖权也是主权平等的要求。
遵守主权原则意味着属人原则受到属地原则的限制。对于属地原则和属人原则的关系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其一认为两者是平行的,均为独立的管辖基础;其二认为属人原则是属地原则的例外[16]。但实践中一般以属地管辖为优先。以刑事管辖为例,甲国对其境内的乙国国民行使属地管辖优先于乙国的属人管辖,因为乙国不能去到甲国境内行使主权权力,只能等到其国民返回本国或被引渡回国后才能进行管辖。“国际法虽不禁止国家对其在国外的国民行使管辖权,但是却限制其行使权利的方式,即国家只能在自己的領土范围内,而不能到他国领土上去行使其属人管辖权,否则就是对他国领土主权的侵犯。”[17]美国依据出口管制法行使域外管辖,要求外国企业在境外也要遵守美国的法律,涉嫌侵犯他国领土主权。
此外,美国出口管制法的域外管辖还涉嫌违反不干涉原则。《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款规定,国家管辖范围内的事件属于内政。出口管制涉及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国家事务,属于一国内政。企业在出口管制领域的违法行为应当由行为地的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负责处理。美国以国内法干预外国企业的域外行为是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当然,不干涉原则也是从主权原则派生而来的。
(二)未履行条约义务
条约为缔约方创设权利和义务。国内法不能违反条约的规定,缔约国应当履行条约义务,包括双边条约义务和多边条约义务。目前中美尚未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因此这里仅讨论美国在《关贸总协定》(以下简称GATT)项下涉及出口管制的条约义务。在GATT涉及到的出口义务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中规定的最惠国待遇义务;第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数量限制义务;再就是第八条和第十条关于出口关税和程序事项;第九条关于原产国标记的规定;最后,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对总协定义务的重要例外[18]。
GATT第十三条对出口管制提出了非歧视的要求。美国《出口管理条例》第738部分中列明了对不同国家的管制原因,此种国别差异涉嫌违反GATT第十三条第一款与最惠国待遇原则。GATT第八条规定,有必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出口手续的影响范围和复杂程序。而且该条明确指出其适用于许可证事项。许可证制度作为美国出口管制的重要手段因而受到该条限制。第十一条第一款中涉及出口管制的内容规定,各缔约国除征收关税、国内税或其他费用以外, 不得设立或维持出口许可证等措施。但是第二款的例外则大大削弱了第一款的效力,缔约国仍可依据必需品严重短缺等理由禁止或限制出口。
GATT就缔约国出口管制设定的义务,对于消除非关税壁垒、推进自由贸易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其第二十条与第二十一条的例外规定却为缔约国提供了规避义务的路径。如果说第二十条还有“不得利用限制对国内工业提供保护,也不得背离本协定的有关非歧视的规定”之类的限制,第二十一条被滥用的风险则更大。“由于安全例外是可以证明歧视性出口管制合理的唯一真实的途径,因此《关贸总协定》要求成员国根据保护原则确立规制管辖权的域外性。因为只有保护原则才能同时满足《关贸总协定》的要求,并为域外管辖提供基础。”[19]美国在出口管制实践中随意援用GATT第二十一条,通过对安全例外的扩张解释延伸出口管制法的域外效力。该行为的实质是利用WTO规则为其行使域外管辖提供“合法的外衣”。
“乌克兰诉俄罗斯与转运有关的措施”(DS512)案专家组报告为限制对安全例外的援引提供了途径。该案第一次就GATT第二十一条的安全例外作出解释。专家组首先明确WTO争端解决机构对国家安全事项具有管辖权,其次阐明就被告方俄罗斯依据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援引安全例外是否满足该款列明的三种情形应由专家组进行客观判断。专家组指出,WTO成员有权对其所保护的基本安全利益与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之间的必要性进行主观判断,但应当遵守“善意”(good faith)原则[20]132。如何判断成员方是否为善意?对此,专家组要求成员方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与所保护的基本安全利益存在最低限度的合理性(a minimum requirement of plausibility)[20]138。此外专家组还强调,成员方不得将贸易利益视为安全利益,从而规避在GATT下本应承担的义务。根据DS512案的专家组报告,成员方对于安全例外的解释受到了较大的限制。由于报告在事实上具有先例的效果,因而可以限制成员方任意解释国家安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然而,专家组对基本安全利益并未作出完整的解释,比如经济安全是否属于基本安全利益尚未有定论。传统安全框架能否应对新的发展环境还未可知。
四、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域外管辖过度扩张
近些年,美国将域外管辖频繁用于对外国企业的调查或诉讼。以出口管制法为例,仅工业与安全局2018年的执法案件就涉及中国、俄罗斯、波兰等国的企业,处罚措施主要为罚款及纳入实体清单。其中对于中国企业的指控占多数,而中兴事件则成为罚款金额最高的出口管制案件,对此应当引起重视。中兴最终以“罚款+合规官”的司法和解模式结束案件,而华为的未来尚不明确。借助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等工具,美国的司法扩张可见一斑。为应对美国的过度域外管辖,中国可以在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制定相应的对策。
(一)企业的应对措施
首先,企业可以合理运用司法规则对美国域外管辖提出质疑。美国的域外管辖扩大了法院的司法管辖范围,将原本不具有或不完全具有管辖权的案子纳入其中[21]。中国企业应当在了解美国司法过程的基础上,运用相关判例合理规避其不合理的管辖权。一方面可以就美国的对人管辖权提出抗辩。对人管辖权包括一般管辖权和特别管辖权。201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戴姆勒公司诉鲍曼案中裁定,外国企业在美国设有子公司这一事实不足以确立对外国企业的一般管辖权。一般管辖权是指法院对与本地有密切和持久联系(國籍和住所等)的被告行使的管辖权。根据一般管辖权,法院可以审理针对该被告的任何诉讼请求,包括与法院地完全无关的行为所引起的诉讼请求[22]。中国企业可以援引这一判例就美国法院对相关案件的管辖权提出抗辩。但是,在出口管制案件中,美国法院仍可基于外国企业与美国之间关于管制物品的交易活动确立特别管辖权。
另一方面可以对事项管辖权提出抗辩。确切地说,是质疑出口管制法的域外效力及其合理性。2010年的莫里森诉澳大利亚国民银行案(以下简称莫里森案)中,斯卡利亚法官在判决书中再次强调了反域外适用推定原则(presumption against extraterritoriality)。根据该原则,“除非国会清楚地表明它意图赋予某一规则域外适用效力,否则只能推定该规则主要与国内事项有关”(1)。该原则最早于美国香蕉公司诉联合水果公司案中提出,此次重申是否表明了在域外适用问题上回归对美国法律进行限制的趋势?至少企业可以援引莫里森案对未明确规定域外效力的美国法律提出质疑。以出口管制法为例,其中虽然考虑了对在美国之外的源于美国的产品和技术的管制,但并未对司法管辖区域进行明确说明[23]。尽管中国企业主张不受美国出口管制法规制存在较大的困难,但作为应对的一个方向仍值得一试。
其次,诉诸美国司法挑战其域外立法和执法管辖权。在难以避免美国法院管辖的情况下,中国企业甚至可以主动诉诸美国法律体系,寻求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虽然美国出口管制法律体系庞杂不利于理解运用,但处于这样一个法治国家,利用规则应对规则或许是最合理的方式。三一重工案中,三一集团利用三权分立的制度维护自身权益的做法值得其他中国企业借鉴。在出口管制领域,被工业与安全局等机构列入黑名单的个人和实体除可以申请将其移出黑名单,还可以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审查政府的相关决定,借此企业可以将行政决定诉诸司法。然而,由于近来美国法院对于政府有关国家安全事项的决定往往采取较为宽松的审查态度,这大大增加了通过其国内法成功寻求救济的困难。
最后,為应对美国的域外管辖更重要的是企业本身做好合规建设。“合规”源自英文compliance[24]61,原意为“服从、遵守”。从中文字面上看似乎更容易理解,也就是“合乎规定”。如何符合美国出口管制法以应对其域外管辖是中国企业合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合规建设应当兼顾事前预防与事后应对。在事前预防上,中国企业可以借鉴外国企业的经验,如设立权威的合规管理组织架构;加强对第三方、供应商和客户的合规管理,实现企业价值链各环节的合规经营等[25]。在事后应对上,如调查过程中,中国企业应当积极配合、正确陈述而不是采取逃避甚至掩饰行为;即使进入诉讼程序,中国企业仍可主动援引相关的美国法律进行合理抗辩。这就要求企业必须熟悉美国法律的内容并且密切关注其动向,如最新的《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法案》正式签署生效,其虽未对现行出口管制体系和管制措施做出实质性改变,但在管制范围、审查的严格程度等方面作出较大调整。这意味着新的合规要求。因而企业应当及时了解最新规定以对自身的合规管理进行相应调整。
当然,合规建设的事前和事后并不是绝对分离的。因为合规不只是公司治理方式之一,还作为刑法上的一种激励机制。美国检察机关会根据涉嫌犯罪的企业建立合规计划的情况,来决定是否对其提起公诉;在法庭审理中,法院会据此来决定是否对企业加以定罪,或者在完成定罪程序之后,决定是否对其减轻刑事处罚[24]66。可见合规建设对于企业而言大有裨益,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有学者指出,面对美国的全球法律殖民及其霸权利益的非理性扩张,仅仅依靠“合规”避险式的法律顺服主义远远不足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及国际法秩序,唯有通过国内对等反制性立法及国际层面的制度性合作,才可能构筑一个适当而有力的法律制度基础[26]。这就要求国家层面的参与来协助企业应对美国的域外管辖。
(二)政府的应对措施
域外管辖引起的纠纷同时存在于公法和私法层面,但两者并非完全独立,管辖权冲突往往会影响政府间的关系。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对于美国以其国内法随意制裁中国企业持反对态度。在国际法上,国家的管辖权是平等的。一国不能单方面以立法、行政或司法的形式对他国行使管辖权,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不能只强调本国的利益。
首先,政府间应当基于国家平等进行协商寻求争端的解决。针对美国国内法域外效力的扩张,有学者提出中国应利用本国法进行反制[5]175。制定反制立法或者完善本国法的域外适用看似直指美国的域外管辖,却也不过是以新的管辖冲突回应已经存在的冲突。国家间的对抗性立法不仅使管辖冲突“具象化”,也会使这一法律问题蔓延至政治、外交等领域引发新的问题。国家间的对抗至多只能成为推动谈判的一个因素,以此为契机在谈判中实现对本国利益的保护才是应有之义。域外管辖的实质是利益冲突,在出口管制方面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通过协调利益解决冲突优于以对抗加剧冲突。“通过外交协商解决域外管辖冲突,应将重点放在协调各方的竞争利益上,而不是放在推行本国法域外效力的单边司法决定上,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管辖权限制的国际对话,将有助于国际一致的达成和进一步便利跨国经营的发展。”[27]
也有学者提出了制定阻却立法(blocking statutes)的设想[28]。阻却立法的目的在于禁止当事人为诉讼目的将相关信息提交美国。事实上,阻却立法在美国法院吃了闭门羹。美国法官照旧要求当事人进行证据开示而不顾其本国的阻却立法。此时阻却立法反而将本国当事人置于一个两难的境地,是违反美国法院命令受到制裁还是违反本国法律面临民事和刑事处罚[29]?当然,美国法院在特定的情况下承认外国阻却立法的效力,即外国存在执行阻却立法的实践。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切实际的。首先,中国目前尚未制定阻却立法。其次,即便中国制定了阻却立法,能否保证严格执行而不流于纸面?最后,若中国确立了执行阻却立法的实践,是否就能够得到美国的承认?因此,制定阻却立法的设想还有待进一步的斟酌。由此可见,单方面的立法并不能应对美国的域外管辖,双边协商才是更合理的方式。当然,协商方法并非十全十美。谈判往往出于双方自愿,并且平等的谈判需要双方拥有相当的筹码,而很多时候国家之间并不具备这一条件。因此在政府间协商之外,寻求替代性解决方法如在WTO框架下处理争端也是必要的。
其次,将出口管制争端诉诸WTO是最为符合多边贸易体制的方式。美国依据出口管制法采取的措施应当符合GATT项下的非歧视、透明等要求。在WTO体制下,美国任意解释国家安全扩大出口管制法域外管辖的做法应当受到限制。根据DS512案的专家组报告,成员方虽有权对其所保护的基本安全利益与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之间的必要性作出主观判断,但两者应当存在最低限度的合理性。而出口管制导致的技术交流与研发受阻、贸易失衡加剧等后果对美国产生的影响冲击着其所谓的合理性。
然而,诉诸WTO解决关于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管辖的纠纷存在其固有的缺陷与不足。虽然DS512案突破性地对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作出解释和说明,但由于该条款的政治性,其与作为经济组织的WTO之间存在天然的隔阂。事实上,即使是在DS512案中,专家组仍然对适用安全例外持谨慎态度。此外,争端解决机构可能停摆的困境也增加了纠纷解决的不确定性。由此,中国在WTO寻求救济的前景并不十分明朗。在DS512案之前,关涉安全例外的捷克斯洛伐克诉美国限制出口措施案、尼加拉瓜诉美国案、欧盟诉美国赫尔姆斯-伯顿法案等案件,最终多以协商方式结束。这可能加剧对WTO争端解决机制有效性的质疑,但同时应当看到其能够为纠纷的解决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若中国将与美国的出口管制纠纷诉至WTO,通过审查美国国内出口管制立法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能够促使双方进行协商。即使WTO未能作出有效裁决,也能够对纠纷的解决起到推动作用。
注释:
(1) Morrison v.National Australia Bank Ltd, 561 U.S.247, 280(2010).
参考文献:
[1]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正式记录(A/61/10)[C].纽约,2006:390.
[2]李庆明.论美国域外管辖:概念、实践及中国因应[J].国际法研究,2019(3):4-6.
[3]理查德·D.弗里尔,罗伯特·豪厄尔.美国民事诉讼法[M].张利民,孙国平,赵艳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40-47,181-183,280-283.
[4]袁杜娟.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对我国域外管辖的冲突及启示[J].理论前沿,2009(4):30.
[5]廖诗评.国内法域外适用及其应对——以美国法域外适用措施为例[J].环球法律评论,2019(3):172-175.
[6]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15 C.F.R.§734.3[EB/OL].[2019-09-11].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0b596fbee38c936af88bbb80e193a840&mc=true&node=se15.2.734_13&rgn=div8.
[7]方建伟,乔亦眉.美国出口管制制度与企业合规建设[EB/OL].(2017-03-16) [2019-09-11].http://www.zhonglun.com/Content/2017/03-16/1109532901.html.
[8]American Law Institute.Restatement (Third)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414, comment b (1987)[DB/OL].[2019-09-13].https://1.next.westlaw.com/Document/Ic9b567f5da6411e2b3fd0000837bc6dd/View/FullText.html?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oc&transitionType=CategoryPageItem&contextData=%28sc.Search%29.
[9]张利民.经济行政法的域外效力[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16-117.
[10]Office of the Law Revision Counsel.50 USC§4801 (13)[EB/OL].[2019-09-13].https://uscode.house.gov/browse/prelim@title50/chapter58&edition=prelim.
[11]刘艳娜.经济法的域外效力辨析[J].理论界,2016(6):75.
[12]American Law Institute.Restatement (Fourth)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402, 412(2018)[DB/OL].[2019-09-13].https://1.next.westlaw.com/Browse/Home/SecondarySources/RestatementsPrinciplesoftheLaw/RestatementoftheLawTheForeignRelationsLawoftheUnitedStates?transitionType=SearchItem&contextData=%28sc.Default%29.
[13]徐崇利.美國及其他西方国家经济立法域外适用的理论与实践评判[J].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01(1):271-272.
[14]王婧,邹明春.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风险之出口管制——解析美国出口管制制[EB/OL].(2017-03-23) [2019-10-14].http://www.zhonglun.com/content/2017/03-23/1853365111.html.
[15]詹宁斯,瓦茨.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M].王铁崖,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329.
[16]路易斯·亨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M].张乃根,等,译.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41.
[17]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91.
[18]杨帆.关贸总协定与出口管制[J].国际贸易问题,1991(3):33.
[19]A.L.C.De Mestral and T.Gruchalla-Wesierski,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Export Control Legislation: Canada and the USA[M].Dordrecht/Boston/London: Nijhoff/Canadian Counci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0:49.
[20]The Panel.Russia-Measures Concerning Traffic in Transit[R].WTO, 5 April 2019: para.7.132, 7.138.
[21]钟燕慧,王一栋.美国“长臂管辖”制度下中国企业面临的新型法律风险与应对措施[J].国际贸易,2019(3):93.
[22]杜涛.美国联邦法院司法管辖权的收缩及其启示[J].国际法研究,2014(2):82-95.
[23]潘永建,孔焕志,黄凯.警惕美国出口管制的域外适用——“中兴事件”事实与法律三问[EB/OL].(2018-05-10) [2019-09-11].http://lawv3.wkinfo.com.cn/topic/61000000472/index.HTML.
[24]陈瑞华.企业合规制度的三个维度——比较法视野下的分析[J].比较法研究,2019(3):61-77.
[25]张曙光.积极应对“一带一路”合规风险带头建设完善合规管理体系[J].国际工程与劳务,2018(2):26-28.
[26]田飞龙.长臂管辖与美国的全球法律殖民——评《美国陷阱》[EB/OL].(2019-09-19).http://www.civillaw.com.cn/bo/t/?id=35990.
[27]纪文华.内国经济法域外管辖的冲突解决浅析[DB/OL].[2019-09-11].http://www.pkulaw.cn/fulltext_form.aspx?Gid=335566110&keyword=&Search_Mode=.
[28]张劲松.论欧盟对美国经济法域外效力的法律阻却[J].欧洲,2001(2):54-57.
[29]M.J.Hodaa, The Aérospatiale Dilemma: Why U.S.Courts Ignore Blocking Statutes and What Foreign States Can Do about It[J].California Law Review, 2018(106): 231-232.
[责任编辑:卢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