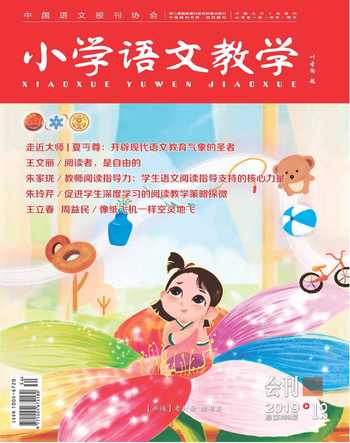“不教”之难,该如何破解
2019-09-10孙小冬
孙小冬
潘新和教授认为,习作难教,其根本之难不在“教”,而在“不教”,难在“发现、顺应、养护他们(学生)的言语天性与个性、潜能与才情,让他们的言语生命得到最大发展”。在我看来,潘教授的这段话至少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习作教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可教的,如文辞规范、谋篇布局等。一部分是“不教”的,即涵养、发展儿童言语生命的根基。“可教”的加上“不教”的才是完整的习作教学。第二,“可教”的部分不难,目前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难的是“不教”的部分,亟待我们的关注和研究。那么,如何破解“不教”之难呢?也许从我所接受的习作启蒙教育中能够得到一些启发。
1970年,我出生在江苏南通一个非常偏僻的乡村。我的父亲沉默寡言,但母亲简直就是《月光启蒙》中孙友田母亲的翻版,她能说会道,是个唱民歌民谣、讲故事的高手。一点都不夸张地说,我是在母亲的歌声和故事中长大的。母亲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习作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在我们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家庭,是没有机会接触到古典诗词以及各种读物的,但我并不遗憾,因为母亲的《孟姜女哭长城》《九斤姑娘》等一点儿也不比那些经典逊色。而且我觉得,跟古典诗词、经典读物相比,这些民谣和故事似乎跟儿童的世界更加接近,更容易被儿童所接受。当然,母亲从来没有、也不会像现在的一些父母那样要求我在规定的时间内背出一首民谣、学会一个故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只是唱(讲)给我听,同时也唱(讲)给她自己听;我也只是听,有时候也跟着哼唱、跟着讲。——我与民间文学的初遇没有感受到任何压力,所以,我自然地接受了它、爱上了它,并因此一步步走进了阅读和写作的大门。古代罗马教育家昆体良强调:“应当特别注意的是,不可使还不喜欢读书学习的学生对读书发生厌恶的心情,不可使他尝到学习的苦味,以免他过了青年时期还觉得读书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阅读对习作的意义重大,但我发现,现在有很多孩子并不喜欢读书,这是不是跟老师、家长的要求过高、过多有关呢?如果是,就请向我的母亲学习吧!
我们小时候,规模稍微大一些的村子都有文艺宣传队,而我们村的宣传队是最出色的。我是宣传队的“铁粉”,进入冬天,宣传队就开始排练了,于是围观他们排戏就成了我每天放学后的头等大事。我能从傍晚看到深夜,几乎见证了每个节目从雏形经过反复打磨到成熟的全部过程——多年后我发现,完成一篇习作的过程其实也是这样的。正月里,宣传队会在各村“巡演”,我就追着他们到处跑,坐在地上看,站在凳子上看,爬到矮墙上甚至树上看,不知道看了多少场,但总是乐此不疲。当然,他们的每一出戏我都了然于胸,他们的唱腔、对白、动作我都模仿得惟妙惟肖。我二姐是宣传队的“主力”,她经常给我“说戏”。有一次,她教我《天仙配·路遇》中七仙女的一段唱:“我本住在蓬莱村,千里迢迢来投亲。有谁知亲朋故旧无踪影,天涯沦落叹飘零。”她问我:“这段唱词很凄惨,严凤英(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却唱得轻松欢快,知道为什么吗?”我当然不知道,她说:“当董永问七仙女,家住哪里,去往何处时,七仙女无法回答,所以‘我本住在’这开头的四个字她就唱得特别慢,以此表现七仙女在苦思冥想。情急之中,七仙女突然想到了‘蓬莱村’这个答案,她很得意,于是,接下来的部分就像泼水一样倾泻而出了。”姐姐还说:“严凤英为什么能成为名角呢?就是因为她的每一个表演都跟人物的心情严丝合缝。”姐姐的话如醍醐灌顶,从那以后,我这个粗枝大叶的男孩似乎变得细致了很多,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体会,而这些都在我的作文中体现了出来。
“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习作教学也是这样,它不仅在课堂上,也在生活里,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这个意义上说,宣传队算得上是我的第二个习作“启蒙老师”。我在这里的学习可以是有意或无意的倾听,可以是对话、交流,可以是一遍遍地觀看、模仿宣传队演出的节目,可以是对剧情和演员的评头论足……这种学习跟生活是融为一体的,或者说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它没有强迫性,没有隔离感,一切都那么真实、自然。所以,我完全是敞开的、投入的,当然也得到了很多收获。
我的第三个“启蒙老师”是自由的童年生活。小时候,除了吃饭、上学和睡觉,我几乎整天都在外面疯,而田野则是最好的游乐场,所以对庄稼、对农活、对田野里的一切我熟悉得不得了:只看颜色,我就知道玉米秆甜不甜;山芋还在土里,我就能判断它的大小。我知道哪里有鸟窝,我知道花生地里的老鼠洞有多深,我知道猪喜欢吃什么草,我知道黄鼠狼藏在什么地方……一年冬天,我突发奇想,要像狗一样睡在打谷场的草堆里。父亲居然同意了,他帮我在棉花秆堆成的草垛中心掏了一个洞,铺上稻草,还用芦苇编了一扇门挡在洞口,于是,这个冬天我和一个小伙伴就天天睡在这个洞里。一个深夜,我们出来小便,发现下雪了,我们两个就在外面跳啊,喊啊,闹了好一阵子才进去睡觉。
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给了我无比丰富的体验,也让我对世界始终充满了好奇。中学语文老师经常表扬我有一颗细腻柔软的心,我想跟我童年生活的经历有很大关系。相比之下,我不知道如何形容当下孩子的生活。许多孩子每天被家长送到学校,再从学校接到家里,直来直去,几乎没有任何“旁逸斜出”。学校有图书馆,有操场,有体育馆,但他们能待在这些地方的时间少之又少,真正属于他们的也许只有教室里两张桌子之间几十厘米的空间和那张仅能容纳他们屁股的椅子。学校也会举办活动,家长也会带着孩子们去旅行,但功利的目的,让这些活动改变了味道。而在学校,伴随孩子们的往往是军营般的严肃、紧张,工厂般的机械、重复,还有随时都可能降临的“自带”巨大压力的各种测试——是的,这样“打磨”几年,我们的确可以打造出一部高度精密的、人工智能的考试机器,这部机器的确可以按程序“制造”出一篇篇文章,但它却很难滋养习作最需要的情感、审美、个性、想象……我以为,这是当下教育教学包括习作教学最大的危机。钱学森先生说:“我们生活在苦难的时代,但有一个幸福的童年;现在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但却是个苦难的童年。”过去虽然只能成为回忆,但尽可能地多给孩子们一些空间和闲暇,以此来放松他们紧绷的大脑和心灵——我以为,这还是可以做到的。
该说说真正的学校启蒙教育了。我没有上过幼儿园,1977年直接读小学。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乡村小学几乎全是“魏敏芝”式的代课老师,他们的专业素养和能力自然无法跟现在的老师相比。坦率地说,我真记不得老师在作文方面教过我什么,我只记得从三年级起步到五年级毕业,作文写来写去总是《新学期的打算》《一件小事》等几个题目。《新学期的打算》无非是表表决心,《一件小事》不是捡到东西在原地苦等失主就是帮“年过半百的老爷爷”推车——这些难不倒我们,更重要的是老师对我们似乎也没有什么要求,写了就过了,质量如何,无所谓。
但我并不认为我的小学习作启蒙教育是完全失败的。第一,我的老师没有进行令人厌烦的、反复的训练,所以,我头脑里没有什么固定的程式,也从来没有对习作产生过厌烦或反感的情绪。第二,我的老师因为不会教习作,所以她干脆什么都不教,这不仅让我拥有了自己学习的巨大空间,也省去了二次启蒙的麻烦和痛苦。确实,那时候的作文基本上都是胡编乱造,但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我受到的“伤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何况那时候,我们自愈力极强,一有阳光雨露,就会蓬勃生长。
如果把习作教学比作一棵大树的话,那么它的枝叶就是习作“可教”的部分,而“不教”的部分则是深藏在土壤里的根系——它对习作教学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应该说,我所接受的启蒙教育较好地突破了“不教”之难,虽然因为时代的原因,这种破解方式再也无法复制,但比复制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老师要认识到其中蕴含的规律,并自觉地、智慧地运用这些规律,也许只有这样,习作教学才能“根深叶茂”,充满生机和活力。
(作者单位:江苏昆山市花桥中心小学校)
责任编辑 郭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