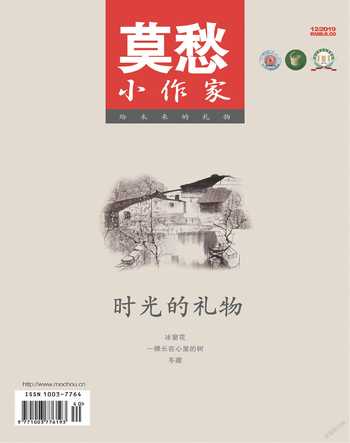冬藏
2019-09-10胡亦敏
今冬大雪时节,忽然想寻一只瓦缸,那种最粗鄙的陶土烧制出来的,不需釉彩,不需图绘,最本色的瓦缸。脸盆般大,到小腿肚高,就够了。
起因是我在菜场上看到了满目的香肠腊串,红彤彤、油光光,饱满结实,一挂一挂如张灯结彩,用喜庆的形式炫耀着一种满足。吸引我的不是它们的味道,而是它们勾起了我对那些深藏家族印记的年味儿的追忆。
瓦缸用来腌鱼。这是门手艺,虽然并没有尝试过,但我想试试。
江南人家都有腌货的传统。小时候,每进腊月,就看到四邻右舍开始行动了。以年长的女人为首,中青年女性打下手,先是洗瓦缸陶瓮、洗竹匾木桶,洗瓶瓶罐罐,然后烫好了陈列在院子里晾晒,要狠狠地经过一两个大太阳后才可以进入下一步程序。
早晨上学时,还看到成捆的雪里蕻堆在脚下,几个女人坐在小圆凳上,细细地挑拣,有些女人蹲在井台上或河埠边,弯腰躬身清洗一篮篮萝卜或雪里蕻。萝卜珠圆玉润,泡在水里,倔强地浮起,徒勞地挣扎,白得像瓷器。雪里蕻青翠欲滴,茎叶蓬松,精神抖擞,给冬天添了一道生机。
洗干净的雪里蕻很快就被挂上竹竿。下午放学回来,它们已经在太阳下蔫头蔫脑、萎靡不振了。萝卜不是切成条就是切成片,白花花地摊在三五只竹匾里,经过时还可以闻到生辛的气味。小巷悠长,日影流动,一会就拐到了房梁后面,门口的竹匾追着太阳的光和热,被不断变换着位置。
记忆中,我家做过一次腌雪里蕻。那个年代,幽深的老宅里只剩下两个孤独的老人和一个被寄养的孩子。没有劳力,老人也没有太多的物质欲望,可孩子对邻居们晒在门口的腌菜充满了羡慕。正好那年表姐回来过年,家里多了些生气,也有了帮手,祖母就和表姐洗刷了瓦缸、木盆,买回了成捆的雪里蕻。祖母用长着冻疮、已经皴裂了的手,抓了粗粝的盐在木盆里揉搓,反反复复,直到揉出墨绿的汁水,一双手却因为冰冷咸水的浸泡,变得特别的红亮。揉一会,她就抬起手背吹吹那些裂口,然后继续把那些已经变得软塌塌的茎叶像拧毛巾一样拧干,一层层码好放进大瓦缸,再撒盐,再码,直到压上一块石墩。
那缸不含任何色素、添加剂的雪里蕻,是我记忆里吃到的最鲜美的腌菜,一次便已永恒。
母亲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大学生,毕业后就去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她在遥远的三湘之地,练就了一手腌鱼、灌香肠、炒肉松、做团子、包饺子、腌咸蛋的好手艺。家里也因此多了一批瓷的、瓦的、陶的,不同质地、不同大小、不同用处的容器,那都是母亲的爱物。哪怕平时积了厚厚的油垢灰土,到了时节,它们一定会被翻寻出来,洗得干干净净,里外烫过,如圣器般收藏经过时间转化的荤腥。
即便后来全家迁回故乡,那些瓮罐坛子,也被装进木箱,关山千重,一路追随到了江南。此后,母亲继续用这些家什坚守着一份传统和心意。二十年前,还在读书的我,没来得及继承她的手艺,母亲就意外去世。那些家什被堆到了阳台的旮旯里,从此再无天日。它们沉默地隐忍着,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因为长年的遗忘,风化的裂纹爬上了它们老朽的身体,残存几只,粗笨暗哑在现代的厨房里那么格格不入。
老宅早已被拆,亲人也一个个离我而去,可以承载故乡记忆的东西越来越少。我又想起了祖母的雪里蕻,想起了母亲的腌鱼干,越近年关,它们越是强烈地提醒着我。于是每年大年夜前夕,不管多忙,我一定要动手做几盘金黄的蛋饺,那是苏州人口中的“金元宝”,一定要皮厚馅小,才合我们全家的口味;做一锅苏式熏鱼,大青鱼宰杀干净后,沿着脊梁骨片成两半,剁了头尾,再摸着骨缝切成约一公分长的小段,撒点盐揉揉,熬一锅用姜末、老抽、砂糖、白酒、葱花等合成的卤汁,旺火大油锅,把炸得金黄的鱼块沁到卤汁中,吱吱作响。吸饱了卤汁的熏鱼里混合了苏州人最爱的鲜甜,可以吃上一个春节;做一碗油炸肉丸子,斩得细细的肉馅里还要掺些蛋清、面包粉才会酥嫩,和蛋饺一起,用鸡汤煨了,再加上冬笋、火腿、菠菜之类,哦,千万不能少了“银链条”——粉丝。这样一锅寄予了种种美好的“合家欢”就做好了。鲜香、清淡却热烈、醇厚,一碗下肚,热乎乎地熨帖着五脏六腑。
这些腊味,如今随时可以在菜场、超市里找到,不需再亲力亲为,耗时费力。可今年除此之外,我还腌了鱼。但现在已经很难买到适意的瓦缸,遍寻不得只能以一只搪瓷脸盆替代。比母亲幸运的是,遇到困难我可以上网找答案。第一次试手的鱼干已经在阳台上风干,在阳光下有着半透明的玫瑰色。味道并不重要,而是通过它们,寻找久远的回忆,重建与故乡、故人的联系。
胡亦敏:作家,文宣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