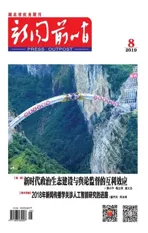故宫夜场“灯会”的媒介仪式叙事与文化记忆建构
2019-09-06◎郑晨
◎郑 晨
博物馆是承载文化记忆的场所,故宫以其独特的文化品格在国内众多博物馆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近几年,故宫“热”的现象层出不穷,从文创产品譬如故宫“彩妆”等饱受观众亲睐,到 《国家宝藏》、《我在故宫修文物》、《上新了故宫》等系列节目的高收视率,再到“紫禁城上元之夜”的一票难求,故宫正在尝试以多样化的媒介方式宣扬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本文以故宫首次夜场“灯会”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故宫是如何通过媒介仪式叙事,唤醒观众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从而实现观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一、故宫作为文化记忆的时空媒介
博物馆作为存储、收藏和展示人类文化遗留物的空间场所,其文字、图像、古物、建筑等都是对于各历史时代风貌与思想的记载、呈现和反映,因而博物馆可看作是存储文化记忆的场所。而故宫作为国内最大的古遗址博物馆,以其明清两代独特的宫廷建筑群、国宝级的艺术文物品以及丰富的文化艺术史迹,在国内众多博物馆的地位中非比寻常,其所承载的保留历史文化记忆功能更加凸显。可以说,故宫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记忆力。
一方面,故宫作为空间媒介的维度构建了 “记忆的场域”。地点是记忆的源泉,其本身可以成为记忆的载体,虽然故宫并不拥有内在的记忆,但是它能够把对于明清皇家的历史回忆固定在故宫之内,从而起到建构文化记忆空间的作用。古罗马记忆术理论家西塞罗认为,在历史场所感受到的印象,比通过听说和阅读得来的印象要更加深刻和生动。故宫作为一个典型的历史纪念地,它不仅体现了作为旧时皇宫神圣与威严并存的特征,而且也展示了它是如何由天子的宫殿成为游客游览之地的历史记忆。
另一方面,记忆赋予场所情感和意义,人们可以对其进行诠释、赋予其意义。观众把记忆和意义融入感知体验,将单纯的物质空间转变为令人愉悦和深刻的记忆场所。走进紫禁城内,行走于宫墙之内,体验只有皇帝才有资格行走的御道,近距离触碰与感受只有皇室家族才能居住的宫殿楼宇,观众置身其中,仿佛跨越了时空,被唤起了对历史与过去的记忆。同时故宫所收藏的数以万件的国宝珍品,其中的绘画、书法、器物等都是历史的见证,是历史文化记忆的载体,它传达出久远时代的信息重新激活了对于过去的回忆。
文化记忆离不开媒介与传播。俄国塔尔图学派的文化符号学家尤利·洛特曼和鲍里斯·乌斯宾斯基强调了文化记忆对某些实践和媒介的依赖性。文化记忆不会自动地进行下去,它需要一再地重新商定、确立、传介和习得,同时需要借助外部的存储媒介和文化实践来进行建构。由于科技的进步,过去通过口述和手写文字保存的内在记忆方式已逐步转变为依靠印刷、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外在化的记忆载体。故宫作为博物馆本身是一种媒介,其文字、档案和地点形成的时空媒介,连同物质空间和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共同构筑了故宫文化的回忆空间。故宫文化的传播意义不仅在于展示和宣扬中华传统的历史文化知识,还包括文化精神的营造、仪式感的实现、社会关系的建构。总之,故宫是文化记忆的场所。故宫的文化记忆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是过去的,也是当下的;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

二、故宫夜场“灯会”:媒介仪式叙事与表征
美国学者詹姆斯·W·凯瑞的 “传播仪式观”中提到,传播本身作为一种仪式媒介,可以唤醒并吸引受众参与建构共同的文化记忆与民族情感,以实现文化的集体认同感。传统的媒介仪式是强调实体性的仪式空间,正如故宫选择在院内和传统的元宵节举办隆重盛大的活动,也是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通过灯光秀、戏剧的表演、书画古诗词的展示等媒介形式,将弘扬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隐喻精神以移情的方式呈现给仪式参与者;而现代大众媒介在虚拟世界中的运用突破了传统意义上仪式的时空阈限,使得局限于实体空间的仪式可通过新媒介传达给受众。故宫的夜场活动仅对普通民众发放门票500张,这对于众多的受众需求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无缘于现场的观众可通过电视、手机、网络等平台来了解和感受活动现场的氛围。
当然,无论活动的形式如何丰富和多样化,最终都是媒介仪式的具体呈现和表达。媒介通过仪式化的传播方式和现代媒介技术,不仅给观众带来仪式化的体验,更重要的是它为传统文化的仪式化传播提供了现代框架,并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其宗旨就是要通过“媒介仪式”建构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下面将从仪式的内容、方式和活动本身的形式来讨论故宫夜场“灯会”的“媒介仪式”建构。
一是故宫夜场“灯会”的仪式性内容。在本次夜场“灯会”中,故宫选取了体量最大、等级最高并寓意着时下中国江山稳固、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的建筑物太和殿进行灯光投射;与此同时,分别对中国文化艺术历史的巅峰之作—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卷》、《清明上河图》,明代诗人唐伯虎的《元宵》等古诗词采取了灯光映照的方式进行展示。故宫将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作品作为活动元素,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审美价值,建构共同的集体记忆,加强了观众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二是故宫夜场“灯会”的仪式化传播。故宫的夜场“灯会”,首次采用了ALPD激光显示技术,对太和殿进行了为幕的近3000m2的巨大灯光投影,呈现出“2019紫禁城过大年贺岁迎祥”、龙凤呈祥以及各种福字组成的字样和图案,太和殿在巨幕灯光的映照下俨然换了一身新装,更加壮美雄姿,同时故宫将画作、古诗词文字以灯光画轴、红墙投射的形式进行展现,更加衬托出故宫的别样风韵。通过这一系列盛大而恢弘并具有视觉美感的仪式活动,使观众在不知不觉中体验和感受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并且随着新媒介技术手段的提高,大大提高了活动的观赏性和仪式感,同时也升华和增强了民众对于故宫的情感。
三是活动本身成为一种“集体庆典”。在特定时空环境中的仪式活动,媒介本身成为了一种仪式,其主要作用不仅是为了传达信息,而且也起到了沟通交流、渲染气氛、表达意义的作用。故宫的夜场活动借助于灯光、戏曲、音乐等交流媒介的形式,使观众参与其中,将故宫的传统民族文化与观众建立了一种交流沟通渠道,并且通过受邀参加的各行各业的3500名代表的亲身参与和行为示范,扩大和倍增记忆的人群数量,唤醒更多民众的文化记忆,从而形成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
三、故宫夜场“灯会”:媒介仪式传播与文化记忆
故宫夜场 “灯会”的仪式化传播实际上是以媒介为依托,以仪式活动为对象,在仪式空间内构筑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进而建构观众乃至整个社会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感。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论述故宫是如何通过媒介的仪式传播建构了观众的对于传统文化的集体记忆。
一是媒介仪式的“观众参与”。在阿斯曼看来,为了通过仪式化传播来激发唤醒共同体的文化记忆,就必须要有共同体成员的亲身到场以形成群体仪式场域,来实现对共同体文化记忆的追忆。任何仪式活动都需要参与者,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中,戴扬和卡茨讨论了观众参与重大媒介事件的模式:“观众受邀请来并提前好几天就做好准备。事件进行了很好的宣传和排练,观众知道那一天会发生什么并寄予期待。”在故宫灯会举办的前夕,各大主流媒体纷纷报道,为灯会的开幕宣传造势,同时通过网上开放免费预约门票的方式吸引观众参与抢票,这实际上是故宫主办方与观众建立了一种召唤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也可以看作是主客体之间相互召唤,主办方以期待的心情迎接观众的到来,观众以积极的姿态参与观赏。
二是是情感的共享和精神的凝聚。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的仪式观是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是共享信仰的表征。故宫“灯会”通过仪式的展演,起到了沟通人与历史、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作用。譬如一系列的文化表演:观赏午门城楼及东、西雁翅楼的灯光展、布满红灯笼的故宫东城墙,聆听畅音阁戏楼的戏曲表演,观赏艺术灯光投影于建筑屋顶上的绘画作品等,观者“身临其境”,感受与体验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也是加强和凝聚观众对于故宫文化精神的认知和理解的一种方式。
三是集体认同感的建构。“通过借助集体记忆、共享的传统和对共同历史和遗产的认识,才能保持集体认同的凝聚性。”无论是传统的仪式化表演,还是现代的仪式化媒介,都应当承载与传播中华民族的集体文化记忆,借以形成对于传统文化的群体认同。故宫的夜场“灯会”通过媒介的仪式传播,一方面沟通了人们与故宫文化的交流,另一方面升华和强化了人们对于故宫的情感,建构了人们对于故宫的文化记忆。因此,故宫的仪式化传播的重要作用即在唤起和重申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记忆与关注,增强人们的集体认同感。
四、结语
故宫作为中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象征物,在媒介仪式构建的过程中,将建筑、书画、古诗词等传统文化元素进行仪式表演,成为传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切入点,媒介本身也就成为了一种仪式,观众参与到仪式空间内相互交流,增强对于故宫文化精神的情感认知,对于传统文化对的集体记忆被唤醒,从而形成集体认同感。故宫的夜场灯会的成功举办,对于今后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场所更好地传播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