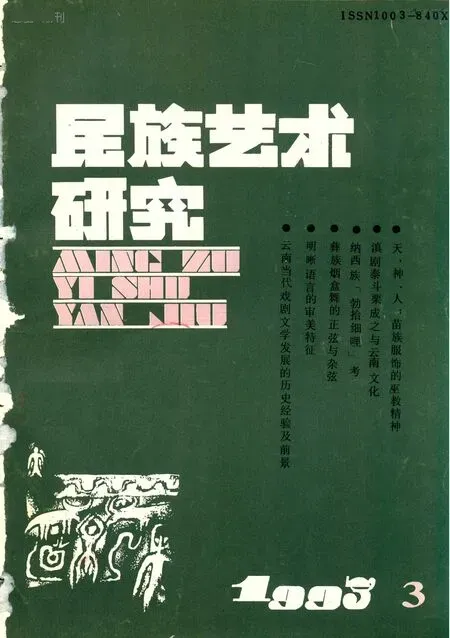类型拓展、“工业美学”分层与“想象力消费”的广阔空间
——论《流浪地球》的“电影工业美学”兼与《疯狂外星人》比较
2019-07-17陈旭光
陈旭光
2019年春节档,科幻大片《流浪地球》成为现象级电影,颇有“孤片盖全唐”之势,并再次打破中国电影口碑、票房不一致的魔咒,收获票房/口碑的双赢。
毫无疑问,春节档一部科幻电影的一枝独大,不仅夺走了原来这一档期惯习的偏喜剧、“轻奇幻”风格的“贺岁片”或“合家欢电影”的风头,实际上已经且还将深刻影响中国电影生产的格局,甚至可能就此开启一个我称之为中国电影的“想象力消费”或“虚拟消费”的新时代。
《流浪地球》几乎引发全民性的强烈关注(以及一定程度的海外关注),从沸腾喧闹的大众网络舆评到知识分子精英的几乎一致地交口称赞,从中宣部的种种宣传表扬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报——而这种强烈关注的背后,也使得中国科幻电影、想象力、虚拟美学、游戏美学、想象力消费、虚拟消费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美学等话题进入学界业界、民间官方关注研究的视域。关于“想象力”,《流浪地球》的原著作者,被称为一个人把中国科幻文学的水平提升到世界级水平,以获得“雨果奖”(被称科幻文艺领域的诺贝尔奖)而独步世界科幻文艺前台的刘慈欣(他几乎已经成为某种“中国骄傲”“民族英雄”,大家喜欢叫他“大刘”),在“2018克拉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获奖词中说,“想象力是人类所拥有的一种似乎只应属于神的能力,它存在的意义也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未来,当人工智能拥有超过人的智力时,想象力也许是我们对于它们所拥有的唯一优势。”
笔者曾痛感中国科幻电影不发达,进而反思中国电影“想象力缺失”的问题:中国电影缺乏想象力。而想象力丰富奇诡则是美国电影的重要制胜之道。从想象力的角度着眼,有外向型想象和内向型想象之别。美国电影中既有向未知领域攻城略地的超级科幻大片,也有迈入人的最深层最未知的意识与潜意识领域的心理片、惊悚片、悬念片、梦幻片、游戏电影等。前者以视听想象、形象造型想象以及对宇宙毁灭、人类生存等终极问题的宏大想象制胜,后者往往在原有心理惊悚类型的基础上复合进科幻、幻觉、潜意识想象、电子游戏等要素,属于一种“高智商电影”。美国电影想象力的丰富发达与西方文化世纪末情结、娱乐游戏观念和假定性美学观念有关系。而这些观念恰是中国电影所缺失的。”[注]陈旭光:《关于中国电影想象力缺失问题的思考》,《当代电影》2012年第11期。
而今天,以《流浪地球》为标志,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时间,开始了”(胡风诗句)。
一、科幻大片还是新主流大片:类型创生与升级加强
今年春节档,《流浪地球》作为带动春节档票房佳绩的“头部”[注]“头部”理论源于互联网行业,相对于“长尾理论”的“尾部”而言,“头部”现象即是指产业营利重要依靠的最前端,占主要流量、销量的内容和产品——即头部内容或产品。引申到电影界,可以用来描述如下现象:每年生产将近1000部作品,但主要票房由其中不到5部作品贡献。且第一名与第二名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倍数差。如2017年,《战狼2》一部电影获得56.83亿,占全年国产电影总票房18.88%,是票房排行榜第二名《羞羞的铁拳》的2.58倍;2015年的《捉妖记》是《港囧》的1.51倍;2016年《美人鱼》是第二名《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2.82倍。参见陈旭光、赵立诺《2018中国电影产业与艺术年度报告》,《文艺论坛》2019年第1期。当之无愧:自大年初一首映,首日排片并不高,票房也仅为1.87亿,但凭借高口碑逆袭,小春节档7天,票房累计超过21亿元,称为票房冠军,排片占比上升到37%,排名第一。大春节档(到正月十五)《流浪地球》继续攀升到39.7亿,最终以46.56亿元人民币稳居《战狼2》之后第二位。而且在海外市场和舆情上,《流浪地球》比票房冠军《战狼2》,比去年春节档冠军《红海行动》有更佳表现:在美国上映11天即得到382万美元的票房,登顶华语电影美国票房排行榜。其可谓“孤片(篇)盖全唐”,尽显“王者”风范。
《流浪地球》是业界公认的一种“硬科幻”新类型的创生,且出手不凡,一开篇就把水准标得很高,按饶曙光的说法是“凭借一己之力提升了中国电影工业化的水平。”这为后来的类型制造者悬拟了仰之弥高的高标准——这个类型就是科幻电影。
不能不说,科幻电影类型一直是中国电影的“软肋”和“稀缺物种”,世界上在很长时间之内都只能据“美国标准”:“‘科学幻想(Science Fiction)’一词是美国人雨果·根斯巴克(Huge Gernsback)于1926年提出的,而‘科幻电影’则被科幻文艺家赫伯特·W·弗兰克(HubertW Frank)定义为‘科幻电影所描写的是,发生在一个虚构的但原则上是可能产生的模式世界中的戏剧性故事’。”[注]转引自蔡卫、游飞:《美国电影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页。美国科幻片包括太空旅行片、外星入侵片、机器人片、灾难片等。
在此标准下,笔者认为:
第一,《流浪地球》是美式科幻大片的加强版,新主流电影大片的升级扩大版。
此前,中国也不能说没有科幻电影,但零零星星,不成规模、气候,更无科幻类型电影或大片的气度、格局,不足以以类型冠之。如《珊瑚岛上的死光》《大气层消失》《长江七号》《美人鱼》《超时空同居》等,科幻的世界观设定比较幼稚,科幻性不强,在画面、声效等工业水准上更是不值一提。而《流浪地球》与美国科幻电影密切相关,没有对美国科幻类型电影大片的学习借鉴是不可能拍出这样的电影的,虽然我们对里面的一些标签性的“中国意象”、中国情感引以自豪、津津乐道。
《流浪地球》中,冰天雪地、沦陷崩塌的地表灾难之于《后天》《2012》等灾难电影,太空场景之于《2001太空漫游》《星际穿越》《火星营救》等太空片,我们能看到其和这些美国科幻大片的“似曾相识”和高度融合,至少从类型的角度看,《流浪地球》是一部美国式的科幻大片,或者说是灾难片与科幻电影的类型叠合。
在我看来,《流浪地球》以其全民热议的现象电影性,又跨越了类型电影的格局,为新主流大片增加新元素、新内涵,其跻身于新主流电影大片之列,甚至是之首。
近年来,新主流电影大片占据文化主导性地位,无论是票房硬指标还是文化影响力。这一类电影体现了香港电影人与内地电影人的产业协作与美学、文化融合,也表征了好莱坞电影工业与本土气息、“中国梦”等的融合,各个受众阶层的融合等,体现出类型加强、视听工业化、“产业升级”、“接地气”、强化国族情结和群体文化认同等,表达“大国崛起”的意识形态,满足国家和普通人的强国梦、强军梦、中国梦的特点。
笔者曾经研究过以《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等为代表的新主流电影大片的一个亚类型,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当下性、跨国性、奇观性上的‘异域奇观性’,往往讲述我国特警、维和人员等在异国他乡执行国家任务的故事,现代枪战与军事动作兼有,节奏明快紧张激烈,主题则是维护国家尊严、弘扬国家形象”[注]陈旭光:《中国新主流电影大片:阐释与建构》,《艺术百家》2017年第5期。。
毫无疑问,就像美国太空科幻片是西部片的延伸,《流浪地球》也在这一亚类型序列中继续“高歌猛进”。其时间上延伸到未来世界,空间上扩展到外星宇宙,当然价值观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更进一步强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再像《战狼2》那样强化中西对立,渲染中国受列强欺负的“苦难历史”和悲壮情怀。
所以就此而言,与其说《流浪地球》是新电影形态或类型的诞生,毋宁说其是原有电影形态的加强版或升级版,是“新主流电影大片”阵容的扩大和品格的再一次升级。
第二,《流浪地球》是近几年中国电影界呼唤和期待已久的体现电影工业化程度的一个高峰,也为“电影工业美学”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案例。
当然,我们说的电影工业化也是其体系化。一种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并非仅指巨额的资金投入、高新的工业技术,更指电影生产过程中高度的标准化、流程化、规范化。一部电影需要经由无数工序共同来完成最终的制作。真正的电影工业化必须是逻辑化的,分工精细的,协同性良好的。电影作为一种“核心性创意文化产业”,更需要各个电影生产环节的协同工作。
因此,《流浪地球》的高度的工业化主要体现在:
其一,投入资金的保障。虽然因为商业机密,中影股份董事长剌培康在回答记者电影投资时始终不肯透露,但小作坊式的小打小闹显然无法支撑《流浪地球》工业化的要求。不菲的资金投入与配置,当然是工业化的一个条件,一种基础。
其二,制作的难度和质量,技术的高新、尖端、前沿。据相关统计,《流浪地球》使用了8座摄影棚,置景车间加工制作了1万多件道具,置景延展面积近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足球场,包括运载车、地下城、空间站等都是实景搭建的。摄制组历经15个月的设计、绘制、规划和搭建工作,置景延展面积接近10万平方米。
其三,投入人数之多,整个制作时间之长,这个庞大复杂工程的协调、统筹需要一种高度工业化的管理,也即郭帆说的“一整套分工明确的专业化流程”。也就是说,“工业化”意味着项目与人力的组织过程规范化、制度化、合理化和最优化。据称,《流浪地球》的制作团队多达 7000 多位来自不同国家、从事不同职业的员工。如何让这些人在两年时间内通力协作、完成制作,其工业化管理组织难度可想而知。
导演郭帆对《流浪地球》的“工业化”制作和管理体味颇深并身体力行。郭帆曾说:“钱并不是工业化的标准,一整套分工明确的专业流程才是。”在第二十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郭帆曾说电影的工业化就是对电影创作的管理。“我经常和组里人说现场不要创意,现场就要施工队。在这个就像是施工队的团队里,整个过程中最核心的是计划、时间、管理,怎么样安排、统筹这么多的项目。”因此, 电影工业化就是把杂乱的东西标准化,从而对内容进行量化和拆分,之后再进行分工。简而言之,就是标准、组织与分工。
此外,《流浪地球》的演员没有使用流量明星(吴京甚至不要报酬还贴钱出演),这就大大降低了按原来中国电影制作“惯例”在演员上花很多钱的做法,高额的片酬使得电影的实际制作成本遭到不断挤压,甚至影响到电影创作本身。《流浪地球》把资金用在刀刃上,这也是符合“电影工业美学”原则的。
第三,作为一种现象级电影,《流浪地球》具有超出电影之外的重要文化意义。
不难发现,《流浪地球》不仅引发了关于中国硬科幻电影元年的说法,在中国电影类型建设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更在作为新民俗的春节档,掀起了一个全民观看、热议的热潮。克拉考尔认为,电影比其他艺术更能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 “电影,人民深层倾向的反映”——而这基于两个最基本的理由——第一,电影不是个人的产品;第二,电影必须适应大量观众的愿望。[注][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从卡里加里到希特勒》,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因此,与前年《战狼2》相似,也与在此之前以刘慈欣为代表的中国科幻文艺的崛起一样,它实际上有着更为微妙的文化症候和更为复杂的文化“多元决定”性。正如论者指出的,“从2008年《流浪地球》小说出版,到2019年电影版问世,正是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崛起的时代,也成为理解中国科幻文学兴起和科幻电影起步的时代背景”[注]张慧瑜:《〈流浪地球〉:开启中国电影的全球叙事》,《当代电影》2019年第3期。。
科幻电影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我们“千呼万唤不出来”的某种“他者”,如果说这种文化缺失源于中国电影的“想象力”缺失的话,那么今天科幻大片终于不期而至,则亦非侥幸偶然,而是时代、文化、科学精神、中国梦、青年文化等多元因素综合而成的,是因一种阿尔都塞所说的“历史的多元决定”形成的:“是文明转型、科幻想象力、电影工业体系及其技术水平、能力、综合实力、国力合力形成的一个结果”[注]饶曙光:《〈流浪地球〉与“共同体美学”》,《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2月20日。。《流浪地球》在春节期间的热映,不仅再次强有力证明了春节档爆款电影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已经介入国人的精神生活,而且该片以及围绕电影引发的几乎全民性的热议、各种观点交锋、豆瓣打分,更成为绕不过去的文化现象。从某种角度说,《流浪地球》也成为当下国人无意识梦幻的表达。因为,“幻想片又是对我们潜意识的表达,并且正是这类影片特别易于表现我们所压抑或压制的东西,也即我们的无意识领域和梦的世界。与此同时,幻想片亦如其他类型片一样,转喻性地承担着主导意识形态和社会神话表述者的功能。”[注][英]苏珊·海沃德:《电影研究关键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6页。
《流浪地球》的爆款,全民热追热议,除了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因素外,从国民性格的角度看,也表征了中国人尤其是年轻观众在性格、思维、科学理性精神等方面的新变,笔者曾论及中国人的思维、人生态度等国民性的超验与经验的问题。“从人的知识世界的来源看,有两种,即经验和超验。经验含有个体理性经验、个体感性经验与社会道德经验;经验离不开主体人的经历感知和体验,经验的世界是务实的、现世现时的。超验则是指超越经验、超越人自身的东西,它关乎人的存在的终级归旨,又是一个存在论的问题。从西方思想史意义上说,超验有两种形态,即哲学上的超验和宗教上的超验。超验关注的是彼岸的世界、想象的世界、理想的世界。”[注]陈旭光:《“超验”、“经验”、制片机制与类型化——从〈画皮2〉〈搜索〉等对当下中国电影突围的几点思考》,《当代电影》2012年第9期。
从这个角度看,不妨说,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思维、想象已经走出了一般我们认为的中国人的性格和思维模式,走出了奠定国人文化性格的先师孔夫子式的坚执于现世、世俗、感性、经验的一面,青年人有了更多超验性的情怀,有了更大的想象力空间。换一句话说,时至今日,“忧天”的“杞人”,“逐日”的“夸父”,向往、玄思“彼岸世界”“超验世界”的人多起来了,中国人在其国民性中不再持“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式的经验主义人生态度。这些新人,无疑是《流浪地球》以及未来科幻电影的主力受众。
不用说,一部《流浪地球》汇聚了具有表征时代热点的话题,是中国梦的隐喻性、转喻性表达。特别是,电影体现的那种把地球推离太阳系,带着地球流浪,以及电影中堪比“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等文化原型呈现的民族精神,以及某种隐约可见的家庭伦理叙事构架(外公-父亲-儿子-养女),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暗合了全球化时代和谐共处互惠互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智慧,西方媒体在评论时,最看重的也是这一最基本创意的“非好莱坞化”,他们都感觉到中国要开始在科幻电影领域加入全球竞争了,而这一竞争的背后是中国早已在其他领域介入全球竞争了。
德国有谚语说,“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这对于《流浪地球》同样适用——略改一下,不妨说——“不是刘慈欣和郭帆创造了《流浪地球》,而是当下中国观众、中国情怀、中国梦想创造了《流浪地球》”。
无疑,《流浪地球》并非完美无缺,甚至存在剧作、细节的不周全和人物性格的单薄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其现象级成功与观众对中国第一部硬科幻大片的新鲜、好奇、宽容,对电影中充满的中国元素、中国人救地球等主题激发的民族热情、中国梦、民族主义情绪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另外,这部电影除了基本结构、创意理念与中国符号之外,在父亲牺牲、儿子成长的终极拯救的情节模式、父子情深型人物关系,尤其是灾难画面等方面,实际上还是非常“好莱坞化”的。
也同样不妨说,是好莱坞科幻大片、灾难大片培养了今天以中青年为主体的观众,正是这些观众创造了《流浪地球》。
二、另类的《疯狂外星人》:中国式本土科幻电影的探索
在我看来,票房成绩似乎不佳、颇有争议的《疯狂外星人》才是真正的“中式科幻”片,它不仅远离好莱坞科幻片的剧情模式和宏大场面,更对美式科幻的种种经典桥段极尽嘲讽、解构之能事。
《疯狂外星人》肯定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幻电影,至少不是美式科幻电影(但《流浪地球》是),宁浩自己对《疯狂的外星人》“当时提出的目标就是‘这电影拍出来,美国人无法翻拍’,也就是说,美学上,你得保持自己的个性”“一直以来,大家脑子里的科幻电影只有好莱坞,容易被好莱坞的套路套住。好莱坞电影中充斥着概念,你就容易用概念套概念。最开始编剧写出来的版本,有点儿好莱坞,但我就是不想‘像好莱坞’。”因此,《疯狂外星人》更是非常中国非常现实的黑色幽默喜剧,也可以说是宁浩以自己的作者电影风格,以对中国现实的体认为准绳,对美式科幻大片的搞笑之作。“电影虽说是改编自《乡村教师》,但实际上留原著之神而尽弃原著的人物、情节。留下的最重要的‘神’在于人类与外星人的沟通对话问题以及用乡土文化可以对抗宇宙先进文明这一合相创意。”正如记者采访宁浩时,他如是说。
《疯狂外星人》具有类型叠合或曰类型创新的意义,尤其在中国。科幻电影作为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幻想类电影,也常常与动作片、喜剧片、恐怖片、灾难电影等类型叠合。也可以说,科幻片都有着其他类型电影为依托或互相依托,《疯狂外星人》正是一种与黑色幽默喜剧亚类型杂糅的科幻电影。
该片充满了解构与反讽的气质。“在反讽的叙事上可谓做足了文章。该片建构了外星空间、C国和世界公园这样三个等级森严的空间;但是,在宁浩充满反讽的镜头语言中,这三者的等级关系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构与嘲弄。”[注]范志忠、蔡骏:《〈疯狂的外星人〉:后全球化时代的拟像话语》,《当代电影》2019年第3期。反讽的力量源于“反差”、滑稽拼贴、情境错位等,于是,美式科幻大片的浩瀚宇宙场景碰上乡镇游乐园,美国特工遭遇中国耍猴人的戏耍,外星高智商人被当猴子调教,猴子具有了外星人的超能量和智商,又保留了猴子的某些特性——令人忍俊不禁的喜感油然而生。而这些天然具有喜感的动作情节桥段,在宁浩的“作者性”思维之下,更是包孕了对人与人、国与国、人类与外星人、人类与动物等之间如何相处沟通等的思考。国与国、人与动物、人与人关系和谐了,才能处理好人与外星人的关系,这里也有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意向。“最卑贱者最聪明”,宁浩以其特有的,从《疯狂的石头》开始一直秉有的底层精神昭示一种中国智慧或中国梦想——一个身处底层,但正直、真诚、敬业的耍猴人(也可以理解为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和守护人),以其四两拨千斤的平民智慧化解美国人“始作俑”却解决不了的与外星人的冲突危机,也以中国哲学特有的世俗化、经验论思维将外星人“去魅化”——当外星人被擅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中国人用酒文化搞得神魂颠倒,与我们友好相处时。
当然,在处理中国底层耍猴艺人与美国特工的关系时,宁浩又似乎显得过于轻松了,以至于有网友戏称该片为科幻版的“手撕鬼子”。宁浩表现的民族情结还是颇为明显的,民粹主义还真是有的。实际上,对美国人的嘲弄过度,过于夸大其自大、自负和愚蠢,岂不是又导致另一种人与人的不平等?
三、电影工业美学的分层
从电影工业美学的视野来看,《流浪地球》与《疯狂外星人》各自从不同的层面丰富了“电影工业美学”体系。
近年来,电影学界、业界关于电影工业体系与“电影工业美学”建构的探讨较集中。
广义地围绕电影工业、重工业电影、电影工业升级等话题的文章不计其数,如饶曙光、李国聪的《“重工业电影”及其美学:理论与实践》(《当代电影》2018年第4期), 饶曙光、李国聪的《创意无限与工匠精神:中国电影产业转型升级新动能》(《电影艺术》2017年第4期),张卫的《新时代中国电影工业升级的细密分工与整体布局》(《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第1期),赵卫防的《中国电影美学升级的路径分析》(《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刘汉文的《中国走向世界电影制作中心》(《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等。
专门围绕“电影工业美学”议题的争鸣探讨,从笔者2017年金鸡百花电影节提交的论文《中国导演新力量与电影工业美学原则的崛起》开始,相关争鸣探讨文章多达20余篇,如:张卫、陈旭光、赵卫防的《以质量为本 促产业升级》[注]张卫、陈旭光、赵卫防:《以质量为本 促产业升级》,《当代电影》2017年第12期。、陈旭光的《当下“新力量”导演群体及其“工业美学”建构》[注]陈旭光:《当下“新力量”导演群体及其“工业美学”建构》,《当代电影》2018年第1期。、陈旭光、张立娜的《电影工业美学原则与创作实现》[注]陈旭光、张立娜:《电影工业美学原则与创作实现》,《电影艺术》2018年第1期。、陈旭光的《新时代中国电影的“工业美学”:阐释与建构》[注]陈旭光:《新时代中国电影的“工业美学”:阐释与建构》,《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陈旭光的《论“电影工业美学”的现实由来、理论资源与体系建构》[注]陈旭光:《论“电影工业美学”的现实由来、理论资源与体系建构》,《上海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徐洲赤的《电影工业美学的诗性内核与建构》[注]徐洲赤:《电影工业美学的诗性内核与建构》,《当代电影》2018年第6期。、李立的《电影工业美学:批评与超越——与陈旭光先生商榷》[注]李立:《电影工业美学:批评与超越——与陈旭光先生商榷》,《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2018年第4期。、陈旭光、李卉的《电影工业美学再阐释:现实、学理与可能拓展的空间——兼与李立先生商榷》[注]陈旭光、李卉:《电影工业美学再阐释:现实、学理与可能拓展的空间——兼与李立先生商榷》,《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2018年第4期。、陈旭光、李卉的《争鸣与发言:当下电影研究场域里的“电影工业美学”》[注]陈旭光、李卉:《争鸣与发言:当下电影研究场域里的“电影工业美学”》,《电影新作》2018年第4期。、郭涛的《技术美学视域中的电影工业美学》[注]郭涛:《技术美学视域中的电影工业美学》,《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等。
概括而言,电影工业美学是工业和美学的折中和妥协。它秉承电影产业观念与类型生产原则,以理性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工作方式,游走于电影工业生产的体制之内,服膺于“制片人中心制”,但又兼顾电影创作的艺术追求,最大程度地平衡电影艺术性/商业性,体制性/作者性的关系,做“体制内的作者”,追求电影美学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电影工业美学的体系建设则“涉及电影观念、电影文本、电影技术和电影运作机制、电影接受消费传播等多个层面,要求把电影看作一种核心性的文化创意产业,在电影工业流程的每个环节都发挥创意和审美的功能,在文化定位上则将其定位为大众文化(而非精英、小众的文化),既尊重电影的艺术性要求、文化品格基准,也尊重电影技术水准和运作上的‘工业性’要求,彰显‘理性至上原则’,在电影生产过程中弱化‘作者风格’和感性、自我的体验,代之以理性的、协同性、规范化的工作方式,力图达成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之间的统筹协调、张力平衡和美学的统一。”[注]陈旭光:《论“电影工业美学”的现实由来、理论资源与体系建构》,《上海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按照李立在《再历史:对电影工业美学的知识考古及其理论反思》[注]李立:《再历史:对电影工业美学的知识考古及其理论反思》,《上海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中对“电影工业美学”形态作的“重工业美学”“中度工业美学”“轻度工业美学”的区分,《流浪地球》毫无疑问属于一种“重工业美学”电影,“它有巨大的投资、超强的匹配、完整的工业流程、宏大的场面、惊人的票房,甚至还代表国家主流一致的表达”。
不用说,《流浪地球》正以其工业化成绩掀起新一轮对于电影工业体系建构和电影工业美学建构的热潮。“新时代中国特色电影工业体系的建构”也成为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
而《疯狂外星人》则与《我不是药神》等相似,属于“中度工业美学”电影:“它主要以典型化的故事为核心,以类型化工业流程为美学配方,以人物命运为动力要素,陡转、延展、聚焦或裂变社会现实和个人遭遇,实现电影与社会的双向互动”。
实际上,宁浩对于自己做何等规模的资本投资和工业化程度的电影有相当清醒的自我认知。而且他从小成本电影《疯狂的石头》一举成名到后来的《无人区》《心花路放》等,驾轻就熟的就是走中小成本电影制作的道路。他在2009年就曾经表示,“从战略上讲,我是希望做中型成本的电影。”“中型成本是最能满足投资老板的,钱花得掉,赚得回来。小型的,我有两千万的钱要投资,我只能投 200 万,剩下 1800 万投到哪儿去,满足不了投资欲望,然后也赚不了什么钱。但大片子又进不去,也不敢投,这样问题就产生了,如果把中间成本弄开了,大量投资可以进入这个成本,也解决了大量演员的就业问题,也会创造出明星。”[注]宁浩、吴冠平、吴孟璋:《讲故事是一门技术活儿——宁浩访谈》,《电影艺术》2009年2期。
宁浩的这种清醒自觉的“中等工业美学原则”意识,使他自觉地不是从画面造型、场面规模、视听效果等方面求胜,而是尽量接上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的“地气”,并在故事叙述、技巧打磨、现实思考与人性考量等方面下功夫,这也使得《疯狂外星人》这部号称科幻、改编自刘慈欣的电影显得颇为“土气”,无论是人物、故事,还是装扮、造型、场面设计等。
宁浩对《疯狂外星人》的某种超越于商业电影之上的作者性、思想性、接地气性的追求颇为自觉。在回答记者的采访时,宁浩明确表达了对商业电影的反感和对“作者电影”的推崇,明确宣称“我从来都不是商业电影导演”,同意把《疯狂外星人》归入“作者电影”之列,强调“所谓‘作者电影’,就是有自己独立的态度”[注]杜思梦、李霆钧:《专访宁浩:我从来都不是商业导演》,《中国电影报》2019年2月21日。。因此,从表面上看,宁浩似乎是反“工业”“商业”的,但在我看来,他之所思所想所实践恰恰是符合电影工业美学原则的。他要做的是“体制内的作者”,他的电影的戏剧性、强情节性、类型特色以及接地气的世俗性,都证明宁浩绝对不是只顾自己思想表达的艺术电影作者,我们肯定不能说《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无人区》都是艺术电影,相反,《心花路放》就更接近商业化的公路类型片。因此我认为宁浩是在商业性于艺术性、体制化于作者性之间保持了比较好的张力的导演,他是一种“体制内的作者”。无疑,正是宁浩在商业追求的“众人皆醉”中保持作者性和艺术电影品格的“独醒”,成就了他的电影商业与艺术的某种折中和“双赢”。
当然,在商业/艺术、体制/作者的矛盾关系未能获得双赢的最佳张力时,也有可能互相牵制掣肘。在笔者看来,《疯狂外星人》的“作者性”还是被强化了一些,与贺岁档电影“合家欢”式的轻喜剧风格稍有“违和感”,可能中国部分观众也还不太适应那种具有后现代反讽恶搞风格又蕴含深刻的思想性的宁浩风格。
四、在虚拟消费或想象力消费的格局中
在好莱坞类型电影谱系中,科幻电影并非一种独立的、比较大的电影类型,而是一种常常被归属于“幻想片”的“亚类型”。科幻片是大约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的战后科技发展、冷战、太空竞争的产物,美国学者约翰·贝尔顿甚至把科幻片看作是西部片的延续和“变种”:“西部片以科幻片的形式生存下来”“ 西部片和科幻片在赞美拓荒经验上显然很相似”“的确,西部片的力量在退却,科幻片夺取了其主题、情境、符号和主旨。《星球大战》从《搜索者》中进行大量的借用,重新搬用其基础的情节设置”[注][美]约翰·贝尔顿:《美国电影美国文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0页。。同样,英国电影学者苏珊·海沃德在《电影研究关键词》中就没有科幻电影这样的词条,而是将它归属于“幻想/幻想片”词条:“一般而言,幻想片包含四种基本类型:恐怖片(horror)、科幻片(science fiction)、童话片(神话片)和某种冒险片(对不明之地的旅行和难以置信之‘生物’的遭遇,例如《人猿星球》)。 幻想片是关于我们未知之领域的,因而我们也未视其为真实。”[注][英]苏珊·海沃德:《电影研究关键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6页。。
当然,科幻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个极大的发展,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尤其是《太空2001》,这与美苏冷战、太空竞争和科技迅猛发展的背景是有密切关系的。
综上种种关于科幻片的划分方法,无疑说明了幻想电影的多样性,也可将其归结为“想象力”的多样性。笔者曾经在《关于中国电影想象力缺失问题的反思》[注]陈旭光:《关于中国电影想象力缺失问题的反思》,《当代电影》2012年第11期。中归纳过美国幻想类电影的四种“想象力”模式,认为《2012》《阿凡达》《盗梦空间》《黑天鹅》分别代表了好莱坞电影的几种重要的想象力模式。
笔者的具体阐释是,《2012》是对人类、地球的未来的想象,关注本身(地球),表达对自身未来的焦虑症,也反映出宗教色彩上的难以遏制的人类悲剧意识,这是一种“中观”层面的想象。
《阿凡达》关注地球与外星球的关系,视野是向外的。影片背后还有科幻想象力和电影技术的支撑,以及考古学、生物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知识依据。对所谓“纳美人”语言煞有介事的想象性再造,与对潘多拉星球上的物种的想象性再现,都充满了想象力,这是一种向外的、奇观性的宏观性想象(虽然主体故事情节很一般)。
《盗梦空间》与《黑天鹅》都是向内的,是人对于本我、自我、超我关系的想象,对梦境与现实关系的想象。其背后的依据是心理学和多元时空观等,是一种微观层面的想象。这一类电影有更多的心理学知识的依托,其想象力则还体现在情节设置的复杂精巧方面。
因此,笔者认为,从科幻电影是幻想电影的一个组成的归属和想象力多元化的角度看,《流浪地球》开启的想象力模式只是诸种想象力模式之一。除了硬科幻大片,还有灾难大片、软科幻电影,还有心理惊悚、悬念丛生的“高智商”电影,影游融合的与游戏相关的电影,中国特色的玄幻、奇幻电影等,这些都是“虚拟消费”或“想象力消费”的几种电影模式,也是中国电影可以大力开掘的文化空间。
结合中国电影发展现状和实际并立足于前瞻,笔者在这里还拟特别探讨两种潜力巨大的“想象力电影”。
其一,影游融合的游戏类电影。美国电影如《生化危机》系列、《寂静岭》系列、《古墓丽影》系列,还有一类直接以游戏冠名的电影如《杀人游戏》《饥饿游戏》,以及新近的斯皮尔伯格的《头号玩家》,这些电影或以有着巨大的玩家市场的游戏为IP,或者整个情节情境的设置就具有游戏性,或者直接以游戏情节建构电影情节,玩游戏或游戏作为一个重要的人机一体的道具成为推动情节的缺之不可的驱动力。如《头号玩家》把故事设定在2045年,几乎每个人都有现实世界和虚拟的游戏世界即“绿洲”两个世界。现实世界令人失望。主人公韦德·沃兹只有在“绿洲”世界中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在“绿洲”中,你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成为任何人——唯一的限制是你自己的想象力。《头号玩家》探讨了虚拟游戏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在观影的过程中,观众如同做了一场由VR与电子游戏制造出来的“白日梦”。
近年来中国电影《微微一笑很倾城》《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等也是改编自游戏的,电影中也出现了玩游戏的情节,主人公在现实世界和游戏世界两个世界中来回穿梭。但总体而言,中国电影中影游融合的电影还比较少,评价不高,仍处于初级阶段。但2018年的中国电影,以《幕后玩家》《中邪》《动物世界》《无问西东》等为代表,一种我称之为“媒介美学”的电影,颇为引人注目,“《幕后玩家》的电影名称本身已‘网感’十足,‘玩家’两字瞬间带领观众走进一个游戏世界。后者导演通过一个封闭空间、密室逃脱的故事,不同程度破坏、毁灭、重置各种电子设备或更新、互换其中的机械零件,这些过程本身构成了故事/游戏的主体。”[注]陈旭光、赵立诺:《2018:中国电影文化地形图》,《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2期。这一类电影与电子游戏密切相关,虚拟性很强,需要架空现实的世界观以及超现实的想象力。
其二,在中国的语境中,还有一类中国玄幻、魔幻类电影,也是幻想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也成为当下虚拟消费或想象力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如《倩女幽魂》、《画皮》系列、《狄仁杰》系列、《捉妖记》以及大量以西游记为IP的电影改编等,它们源自民间文化、民间鬼怪的传说,缺乏科学精神但仍然具有充沛的想象力,颇有玄秘神奇的色彩。“这些妖鬼仙魔题材电影借助高科技手段,在视觉奇观表达、特效等方面强化玄幻色彩,以奇观化的场景、服饰道具人物造型等营造出一种有别于好莱坞魔幻、科幻大片的东方式的幻想和奇诡,把人性、爱情、人与动物、人与妖、人与自然等的原始情感推向幻想世界进行某种‘询唤’,完成大众对魔幻和超验想象世界的超验想象和奇观消费。”[注]陈旭光:《试论中国艺术精神的现代影像转化》,《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笔者认为科幻电影在中国诞生遥遥无期的时候,曾经特别寄希望于中国的玄幻、魔幻类电影。
总之,《流浪地球》以及其引发的全民关注热议的文化现象,不仅使2019年成为“中国硬科幻电影元年”,更重要的是电影中那种具有中国特色又不输好莱坞式幻想的大胆的想象力呈现,预示了一个新力量导演更加如鱼得水的“想象力消费”“虚拟消费”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里,想象力将成为电影产业重要的推动力和创意力,而“想象力消费”或“虚拟消费”将成为一种重要的国民消费经济。
结 语
当下,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在当今世界中的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养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在一定程度上,“幻想类电影”是衡量一个民族想象力、创意力、创造力之程度的尺度。这类电影不仅因其故事的假定性和虚构性充分迎合了当下年轻一代观众对于拟像环境的依赖感与“想象力消费”,而且在类型融合的基础上加入中式幻想再造的创作模式,这也有助于在电影中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而从工业的角度看,幻想类电影,尤其是硬科幻电影因其想象力的大胆丰富、场面的宏大壮阔、工业化的程度高、技术的先进、人员的众多,更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准。
而中级工业水平的科幻电影或玄幻、魔幻等幻想类电影,因为其“接地气”的本土性,因为其与传统文化的关联,因为其体量的适中,比之于投资巨大的硬科幻大片,风险系数又相对较小,更有着广阔的前景。
当然,“今年春节档是硬科幻走红,并不代表每年春节档都是硬科幻电影大片一枝独秀。只有更多的类型,更多的大鱼和中鱼,更合理、更多样的类型格局,才能推助中国电影常态化的继续发展,也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人民群众(当然包括作为主力军的青年群众)日益增长、日益多元,日益与时俱进的审美消费需求。”[注]陈旭光:《感知2019春节档电影:表征与启示》,《电影评介》2019年第2期。
无疑,当下电影观众的内涵、构成和文化程度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主流观众的年轻化是一个不可逆的重要趋向。就此而言,电影获得青少年就获得了制胜权。对于在一个互联网多媒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网生代”一代来说,他们与架空历史、超越现实、放飞想象力的互联网新媒体时代,与一个拟像化或“类像化”的新世界是同体共生的。这个世界归根到底是他们的。媒介现实的变革势必影响到艺术思维与艺术生产也即电影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故事形态方式等的变化,那种互联网思维也会体现在他们的电影思维中,例如玄幻类、科幻类电影、“烧脑电影”、“高智商电影”、脑神经电影、“数据库电影”等等不同称谓的电影形态,实际上都是他们作为“网生代”的电影思维的折中表现。
一言以蔽之,中国观众对中国电影的“想象力消费”的需求空间是非常巨大的;中国幻想类电影的发展前景,也是非常远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