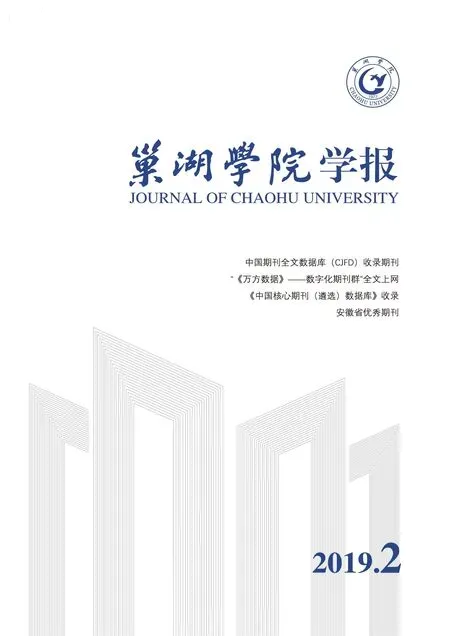周昉《簪花仕女图》之形象审美分析
2019-07-15时茹婷
时茹婷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0)
《簪花仕女图》被传为属唐代周昉所绘,画面描绘了贵族女性真实生活中的情景。辽宁省博物馆对其介绍称:“1972年重新装裱时发现此图系后拼接而成,较明显者为左数第二人比例较小的仕女为后嵌入,又白鹤与画左小狗亦为剪裁而来,有研究者据此认为其原为屏风画。”如果此画为屏风画,唐代的屏风画常被放置于“胡床”的榻上,其功用在于装饰空间和遮掩“胡床”上的坐者,那么据此而推画家创作《簪花仕女图》时更多的意图是为了表现女性之美,以此达到和其他元素共同美化空间布局的效果。如若以审美的视角分析《簪花仕女图》,女性形象必然是研究的重点。所以文章试图从形象与审美的关系为切入点,依次展开对形象审美的演变、审美文化以及社会文化的探析。
关于这幅名画的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以谢稚柳为代表,他在1958年发表的《唐周昉簪花仕女图的商榷》一文,是首篇探讨《簪花仕女图》的文章,文中提及“假使以赵佶摹张萱的‘捣练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与周昉的‘调琴啜茗图’‘戏婴图’和‘簪花仕女图’来比较”[1],文中根据张彦远的记录,把赵佶与周昉的其他画作对比,从风格、笔触、神态等方面猜测《簪花仕女图》为南唐时期的作品。继谢稚柳先生之后,学术界分别从年代、人物、作者、主题等层面展开对《簪花仕女图》的探析。如刘伟冬在《图象的意义——对〈簪花仕女图〉的“另类”欣赏》一文中,以画面呈现的形象为解密线索,分别以荷花、拂林狗、蝴蝶、花为四条线索,力图追寻图像背后的象征意义,指出“这幅具有装饰功能的绘画作品用一种委婉、含蓄而又优雅的表现方式使观赏者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会产生一些 ‘性趣’来,或许这也是作品的实用功能之一”[2]。这种以图像元素为切入点对图像进行阐释的方式,会丰富某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但过于聚焦局部则难免忽视图像的整体情境。因此,文章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不以追求图像的象征意义为最终目的,而是注重分析《簪花仕女图》中女性形象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簪花仕女图》 唐代 绢本 纵46厘米,横180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
一、《簪花仕女图》之审美形象演变
仕女画风格的转变体现了时代审美风貌的变迁,仕女画形态经历了由“德”至“美”的审美形象演变,其间体现出时代审美文化由宣扬政教作用回归至审美需求的趋向。《簪花仕女图》中描绘的女性形象丰肥腴丽,具有唐代仕女画的典型特征,较之两晋六朝时期“道德说教”的女性形象更具时代审美趣味。
(一)美的时代性
美的时代性反映出个体对审美形式的需求逐渐发展成群体的审美需要。审美需要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所以不同社会背景下产生出不同的审美趣味。初唐时期,仕女图中的女性形象还未形成唐代的主流风格,尚处于转型阶段。阎立本的艺术成就代表了初唐艺术家的最高水平,其笔下的《步辇图》尚存有六朝“秀骨清像”的遗风。唐张怀瓘的《画断》一书最早记载了“秀骨清像”一词,“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3]这里张怀瓘所说的“秀骨清像”,指人物清秀孱弱的外形特点。如《步辇图》中凸显了人物孱弱的外形特征,画面中描绘了唐太宗以威严的姿态端坐在步辇上,身旁有六名宫女抬着他威座的步辇,其他女性则在他身旁为他手持华盖或持扇,这些侍女形象多被描绘为清瘦的形态。至盛唐时期出现了绮罗人物画,国力的强盛与社会风气的自由使曲眉丰颊、雍容华贵的女性形象成为这时期的审美标准,直至中晚唐时期发展成熟。唐代仕女形象之所以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属性,其原因在于唐朝独特的审美观。女性形象以“丰肥腴丽”的特点成为大唐审美的标准,这种审美风尚在张萱的《捣练图》中鲜明可见。《捣练图》描绘的是宫中妇女捣练的场景,她们穿着艳丽的齐胸长裙,身材丰满,妆容艳丽,神情姿态各异,整个画面都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继张萱之后,画家周昉对中晚唐时期的仕女画有重要的影响。周昉所描绘的贵族妇女,其形态以丰肥腴丽为主,且女性神情中伴有一丝宫怨、哀愁之情。如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其画不设背景,以工笔重彩绘仕女五人,女侍一人,另有“拂林狗”、鹤以及鲜花点缀其间。画面右起第一人头插牡丹花,曼妙的身姿以侧面右倾的方式,用左手执拂尘引逗小狗;第二位女性穿着靓丽的服饰,并用右手轻提薄衫裙领子,仿佛缓解炎热之感;第三位是手纨扇的侍女,相比之下,她衣着朴素,发饰普通,与其他游玩的贵妇形成鲜明对比;第四位贵族女性髻上佩戴一朵荷花,右手捻一朵红色的花;第五位贵妇髻上佩戴海棠花,其身形相对其他贵妇较小;最后一位贵妇髻上佩戴芍药花,右手捻一只蝴蝶,且身形以弧线的形状与左起第一位女性身姿遥相呼应。《簪花仕女图》中的女性在着装上可谓衣裳简劲,彩色柔丽;在形体上可归纳为丰肥、曼妙;在神态上则流露出百无聊赖、悠闲寂寞之感。宋代董逌《广川画跋》中载“唐人所尚,以丰肌为美”[4]。董逌概括了唐人的审美风尚,“丰肥体”的女性形象自初唐就已现端倪,后经盛唐的发展至中晚唐时期,“丰肥体”的人物形象更为完善。“昉于此时知所好而图之矣”[4]。周昉因知其时代审美风尚,故其画《簪花仕女图》也体现出女性丰肥腴丽、曲眉丰颊的时代审美形象。
(二)美的普遍性
美的时代性与美的普遍性有关,正因为美的普遍性,才凸显其鲜明的时代性。“敦煌莫高窟壁画是唐绘画风格最真实而可靠的来源……,选择唐敦煌壁画中女性形象研究这个命题,就是为了还原唐代仕女画的真实风貌”[5],由此从唐代其他艺术类型中的女性形象出发,以此更好的还原那个时代的审美观。
唐初对女性形象之美的追求,使女性形象更贴近现实生活。如吐鲁番阿斯塔那230号墓,墓中发现的《舞乐屏风图》被界定为初唐时期的作品。屏风画中呈现出舞伎二人、乐伎四人。画中的舞伎被描绘为乌黑的长发挽成高髻置于头顶,舞伎的面容上描花钿用以修饰,面目清秀,身形曼妙纤细。这些女性的形象特征代表了初唐时期女性的主流形象,但这时已经出现了丰腴之美的形象。如敦煌莫高窟第 71窟的壁画《菩萨像》,此外初唐壁画中的菩萨形象已表现出世俗化的形态。与以往菩萨造型不同,初唐菩萨造型逐渐由传统的清瘦窈窕型过渡到丰腴华美型。
初唐的仕女画风格深受张僧繇所创“张家样”的影响,出现了体态丰满、白肌阔面、高髻浓眉的仕女形象。这种审美风貌发展至张萱时期已趋向成熟,周昉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衣裳劲简、丰肥腴丽的女性形象特征。仕女画如此,壁画同样表现为这种时代性的特征。此外还有阿斯塔那古墓187号墓出土的绢画《围棋仕女图》,与周昉所画的“绮罗人物”近乎一致,都是浓丽丰肥的体征、流畅的线条、神情的质感,具有中原画风。可见周昉的画风与同时期其他艺术的形式特征相吻合,他“以体丰为美”的画风彰显了时代趣味。初唐的仕女画偏“秀骨清像”的风格,至盛唐、中晚唐发展成以“丰肥健硕”为主流风格。唐朝的墓室壁画、新疆的阿斯塔那古墓也都呈现出同样的时代特征。人物画如此,其他类型的艺术领域也与其有共性。韩幹笔下的马膘满臀圆、唐代的女佣在民间被称为“胖娃娃”、书法风格也呈大气之感。总之唐代丰肥健硕的女性形象不为人物画所独有,还反映在整个艺术领域中,体现了美的时代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审美的时代性与普遍性的统一究其本质是时代审美文化作用于艺术并产生了审美趣味。审美趣味既有历史的传承又具有发展性,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相应的发生变化,但始终离不开审美文化的制约。
二、《簪花仕女图》之审美文化
(一)关陇文化
“丰肥体”的审美形象体现出美的普遍性与时代性统一的审美趣味,是关陇精神在审美文化中的体现。“隋到唐初所逐渐建构并不断延伸的‘关陇文化精神’,却成为盛唐帝国不曾泯灭的文化惊魂”[6]。唐王李渊建立王朝的政治基础是以关中陇上的豪强为主体的关陇军事贵族,李渊祖上三代都是西魏、周、隋朝的贵族,唐朝继承了北朝以勇为美的审美观念并继续发展,可以说“关陇精神”贯穿了整个唐朝的审美文化。这些关中陇上骁兵悍将带来了战场的英雄风范,为社会注入令人振奋的崇尚阳刚之美的风气。唐朝统治阶级的属性注定了其审美文化偏向刚健、勇猛的倾向,这是关陇贵族久经沙场具有的野性美的外溢渗透于艺术审美实践的各个层面所形成的强劲的时代氛围。根植于人自身上行下效的本能,唐朝艺术风格迎合了勇猛的审美趣味,表现在绘画领域,艺术家创作了表现贵族英勇气概的绘画作品。“又鄠、杜间有苍虎为患,天皇引骁雄千骑取之。虢王元凤太宗之第也、弯弓三十钧,一失毙之,召立本写貌以旌雄勇。”[7]阎立本绘画表现太宗御容、虢王射虎的主旨是歌颂其崇尚阳刚之气的审美文化,表明了审美主体不满足于对审美对象的艺术观照,审美客体不仅仅是审美主体理念的物化,而开始作为美学整体树立贵族集团的形象。所以在初唐时期的女性形象虽然有“秀骨清像”的遗存,但是“丰肥体”已现端倪,这种根植于贵族阶级的审美价值在盛唐、中晚唐尤甚。到了周昉所处的中晚唐时期,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佛禅与道家思想的融合在唐后期尤为突出,并渗透于士人的审美意识,使艺术转向对创作客体心性的关怀,表现在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中,其女性形象给人以孤寂的“画外之音”的情感。
(二)多元文化的融合
《簪花仕女图》中女性忧愁的神态是多元文化融合后在审美文化中的体现。周昉在《簪花仕女图》中表现了贵族女性闲逸生活中的烦思苦闷之情,是愁又不是愁,是哀怨又不是哀怨的神情,在古代“传神”思想的背景下生动地表现出来。周昉是贵族子弟,《宣和画谱》载:“昉贵游子弟,多见贵而美者”[8]。“多见贵”是周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环境所提供的;“美者”是周昉在社会审美文化背景下把体会到的贵族女性的思想感情寄托于作品中,他所处的中晚唐时期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审美文化也同期发生转变。中晚唐时期形成的审美文化既传承前期的文化形态,同时也吸收同期其他的文明成果,用以发展出新的具有生命力的审美文化,从而形成文化精神与文化形态相一致的范式。
从地理位置的层面讲文化融合现象,唐朝统治阶级所处的关陇地带,它处于华夏西北,既有儒家为主流的中原文化,又有五胡之乱后融入的异质文化,尤其在中唐,儒、道、佛思想的互相交融,形成了新的文化范式,影响了这一时期的艺术特性。从文化史的领域来讲,汉代建构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使儒家思想处于三教并用、特用儒学的政治局面。儒家学说具有的政治、伦理功能一直被统治阶级所重用,如唐太宗即位后尊孔子为“先圣”。《旧唐书》载:“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6]。在唐太宗的政治视野中,儒学才是平天下的主导思想,儒学由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兴盛于初唐,其虽一直贯穿于唐朝的思想,但前后呈现不同的儒学特征。《旧唐书·儒学传》载:“薄于儒术,尤重文吏”[6],表明儒学在唐朝开始出现衰败的迹象,加之魏晋时期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论辩,儒学被认为禁锢思想而逐渐被冷落。刘禹锡的《袁州广禅师碑》载:“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以世衰而寖息;佛以大悲救诸苦,广起因业,故劫浊而益尊。”[6]表明此时佛教被当作救世主,以其佛教哲学建立的心性论弥补儒学对本体的观照中所缺失的心灵感悟。在佛教追求心性论的影响下,道教也致力于对心性的阐发以此发展道教。《道门经发相承次序》载:“夫道者圆通之妙称,圣者玄觉之至名,一切有形,皆含道性。”[6]唐代道士潘师正根据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以“自然”为道与人的本质、本性,以不受增损的自然本性为真道性,由此认为道性即人性,进而认为人人都有道性,道教从佛学中汲取思想,提升了对心灵的关照度。至此文化的发展使儒、道、佛以互补的文化形态渗透于唐人的审美文化,表现在绘画领域,唐初期的艺术有别于两晋时期的女性形象特征,边塞文化对古代传统儒学的冲击,使唐代女性真正趋向“美”。唐中期艺术特性有别于初、盛唐的风貌,人物画虽仍据绘画类型中心,但是水墨画开始逐渐发展,最为显著的是由初唐的青绿山水转向设色淡雅的形式,直至晚唐出现完全的水墨山水画。这种审美思想的转变得益于庄子玄学和佛教禅宗思想的融合,这时的绘画风格趋向于以心境作为艺术创作的标准,把对主体心性的关怀、对心灵的追求以及对自然的崇尚融入艺术创作中。在晚唐社会衰落的社会背景中,艺术家笔下的艺术形象多表现为孤冷、伤感的情感基调,如中晚唐时期的周昉,其笔下的女性形象较之张萱,缺少一种欢快活泼的生活气息,与之替代的是忧伤寂苦的情感宣泄。
《簪花仕女图》所属的中晚唐时期,在历经初唐、盛唐的孕育之后,不仅在审美文化的传承、转换、以及发展中展现出与社会文化相适的雄厚浑劲、色彩绚丽等审美气象,而且在美学思想上也指向其特有的审美文化气质。其中既有对前朝历史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地域文化如关陇地区与江南文化的融合,既有自身华夏文明儒、道的传承,又注入外来佛教、胡风、西方的文化,各种文化建构了兼容并蓄的美学精神。唐代美学思想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文化中,所以美学思想在多元并存的文化形态下也具有统一性。初唐在新旧历史转换的文化语境中,一方面恢复了儒学的政教地位,使艺术审美倾向政治教化性;另一方面在开放的时代语境的影响下重新发展审美文化,在超越国家统治的政治局面突破狭隘的复儒思潮的局限,继承魏晋南北朝的审美文化的同时试图融汇多种审美文化,以此倾向于雄厚苍劲的美学精神,奠定了盛唐时期“风骨”和“兴寄”的审美文化。而中晚唐时期的审美文化更多的偏向对艺术本体规律的探索,即对主客体审美意象的内在意蕴的追寻。中唐以后儒、道、佛三家思想的融汇,尤其道家玄学和佛禅思想不断深入唐人的审美意识,中晚唐便注重气韵生动蕴含的深邃的美,艺术创作重在“意境”则成为中晚唐绘画的重要内容,在唐代后期的诗论上也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美学文化。唐代诗人皎然《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山寺宿敡上人房论涅槃经》中写:“诗情缘境发,法性寄筌空。”皎然把佛禅思想与诗境结合,他认为诗的境界就是诗人创造的境界,它犹如佛教中的“独影境”,诗人借诗境中描绘的景物阐发诗人的想象。本诗句阐释了情、境、象的关系,情产生于境,境从象外生。“境生于象外”是刘禹锡对意境的审美特征的概括,他在《董氏武陵集纪》中写:“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投万景,工于诗者能之;……诗者其文章之蕴邪?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6]。他认为从“缘境不尽”显现为“境生象外”,指艺术意境区别于艺术意象,虽然它生于意象但超越于之上指向无限的境。“意象”只能表现艺术创作的普遍原理,但不能表达心灵的感悟、表情的含蓄等一切艺术情感的范畴。由此艺术创作中主客体的关系由创作主体把对自然的感悟、想象融入客体对象,塑造象外之象的艺术境界,此时的象外之象并非单个具体的事物形象,而是指一个广阔的精神世界,“意境”在唐代文化合流的社会中成为一个具体的审美文化,周昉《簪花仕女图》中体现的“以形写神”的美学就是这种审美文化,形不单单是创作客体,同时它也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周昉把对生活的感知、对自然的崇尚等不能言说的理念物化为具体可感的女性形象,故此,我们可以在中晚唐时期看到女性在宫闱生活中的寂寥。虽然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同样具有盛唐女性的娇艳,但是这时期追求“象外之境”的审美文化使《簪花仕女图》比前期仕女画作品多了“意境”。“意境”美既是艺术家基于自身的审美需要,也是审美文化渗透士人后形成的审美观念。
艺术的时代性审美是人基于审美需要对社会文化的反映,所以《簪花仕女图》中女性形象的时代性表明了唐人对“审美需要”的要求,也表明了社会文化对审美需要的建构。
三、《簪花仕女图》之社会文化
(一)女性形象与社会思潮
以仕女图的呈现方式为例,六朝唐初至晚唐出现仕女画风格由秀骨转向隋唐的丰肥腴丽,仕女画形象由“道德劝解”转向“唯美是从”的审美倾向。这种审美风格的演变反映在身体美学中,表现出女性对个体主导地位认知的觉醒。从六朝到唐朝时期的女性形象,明显看出女性对自我主体性认知的觉醒,由最初形而上的道德律令转向个体本身的自由。《簪花仕女图》中女性形象通过身体意识诠释了社会文化对女性思想的影响。《簪花仕女图》画卷最左端的女性,她站在辛夷花旁边,手持蝴蝶作回首顾盼“拂林狗”之态。辛夷花在二月底和三月初之间盛开,盛开时美而不妖,更不失素雅之态,同样作为观赏之物的蝴蝶,被这位女性捉住,却丝毫提不起她的兴致。辛夷花在文学作品中常被赋予孤寂之情,如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诗中以涧口寂静、杳无人迹为过渡,转向描写辛夷花独自开花花又落的情景,既写出辛夷花盛开的魅力形象,又渲染一种环境的孤寂。唐朝文化是华夏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合流,社会的开放使唐朝女性的束缚相对减少,女性的思想也逐渐从原始儒学的禁锢中解脱。女性身体的形象不再作为道德宣传的工具,而是表达自身情感的载体。无论是在生活中消遣还是在生活中孤寂,女性始终都是处于个体思想的中心,其一颦一动都具有生命意识,而非六朝时期机械僵硬的躯壳。
(二)女性形象与社会制度
古代是礼制社会,绘画领域表现的社会等级是艺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政治化体现。唐朝的仕女画多表现贵族妇女,周昉《簪花仕女图》中对女性身体形象的差异性描绘,正是社会等级分明的体现,这种表现形式是唐朝儒家思想在社会文化中的体现。《簪花仕女图》描绘了五位衣着华丽的女性,唯有手执长柄团扇的侍女衣着单调且身形微微向前躬,身体呈现随时待命侍奉的“意识”,画卷中突出的主仆关系,体现了权利话语在社会等级中的表现。
权利话语在绘画中的体现尤其表现在男性对女性审美标准的要求上。唐朝时期的仕女画,其丰肥腴丽的绘画风格,正是大众审美趋向类型化的模式。仕女画由宫廷画家为贵族女性作画,属于宫廷绘画,也代表了阶级社会的艺术表现形式。“阶级艺术所表现的是那创造它的阶级认为好的和重要的东西。这种意识在这里并不是宗教意识。它不是直接由经济决定的,而是由那些在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社会关系决定的。这些关系决定着心理。”[7]可以说社会意识形态存在于阶级艺术中,阶级社会的所好决定着艺术的表现形式。以《簪花仕女图》来讲,它属于宫廷画家创作的宫廷绘画,其绘画作品中的女性作为宫廷妇女或贵族女性,则承担了男性的审美标准。刘向的《说苑》记录了宫廷绘画的创作来源,“齐,敬君者,善画。齐王起九重台,召敬君画之,敬君久不得归,思其妻,乃画妻对之。齐王知其妻美,与钱百万,纳其妻。”起初敬君为妻子画画像以解相思之苦,后来这种用画像表现女子美貌的绘画功能被广泛用于宫廷,用于皇帝筛选后宫佳人的方式,女性形象从此被打上满足男性审美的烙印。唐代社会风气虽然赋予女性极大的自由,但是还是以男性统治为阶级社会的中心。《簪花仕女图》则是社会环境下男性的权利话语体现,此时的女性绘画仍是男性的艺术。
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审美要求不仅体现在女性的形象方面,在绘画中描绘的内容也是按照男性对女性生活的规范所设计的。唐代描写女性生活的画卷,基本都被规范于以宫廷场景为中心狭隘、封闭的地域范围,绘画中的贵族女性生活是一部永远走不出的后花园传记。女性居住的场所一般用闺、阁、闱、阃代称,与之对应的是闭、闷、闲的心境,由此可知女性被“门”牢牢锁住,是社会文化赋予男性锁住“门”的权力。极端的幽闭使贵族女性以自我消遣为主要生活内容,周昉和张萱作为宫廷的世俗画家,用画笔记录了这时期的女性生活,如《捣练图》《挥扇仕女图》《簪花仕女图》等,这些绘画作品描绘的女性活动有纺织、刺绣、游戏甚至发呆等,这些画家描绘的女性生活方式几乎是上层女性现实生活的全部内容。周昉的社会地位使得他看透宫廷女性生活的百态,这种特别的生活经验奠定他表现闲寂的细腻感受。《簪花仕女图》所描绘的画卷便是男性规范下的女性生活形态,画卷便是锁住贵族女性的那道门,走不出后花园的贵族女性以戏狗、赏花、拈蝴蝶等自我消遣活动抒发孤寂闲适的内心情感。
社会等级文化决定了男权社会对女性审美形象和生活内容的规范作用,艺术与社会的磨合中,艺术显然受制于社会文化。
四、结束语
形象是文化的载体,对《簪花仕女图》描绘的女性形象的溯源中,探索其形象背后蕴含的时代审美文化和社会文化。其中“丰肥体”的审美形象体现出美的普遍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关陇精神在审美文化中的体现;“象外之境”的美学思想是由于唐后期佛禅与玄学思想居于唐人审美文化的中心地位,艺术家不仅仅把创作客体当做审美对象,还把对自然的感发、宇宙的感悟和个人心性的观照寄托于客体,表现在《簪花仕女图》中,女性神情中透漏出哀伤、孤寂之感。关陇精神和多元文化共同构建的审美文化同时也表明了社会文化对审美需要的建构,其中女性审美形象与当时的社会等级制度、社会思潮相统一。总之,《簪花仕女图》作为宫廷绘画,绘画意图更多地趋向审美性,通过分析《簪花仕女图》中出现的形象,由点及面扩展到审美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层面,而非从《簪花仕女图》中的形象猜测图像虚幻的象征含义,一方面扩宽了对图像研究的方向,打破了分析图像象征含义的固定“套路”;另一方面建立了艺术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在艺术学理论视域下与社会学、美学、历史学等学科相结合,更真实地还原艺术家在社会生活视域下对艺术品的创作,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大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