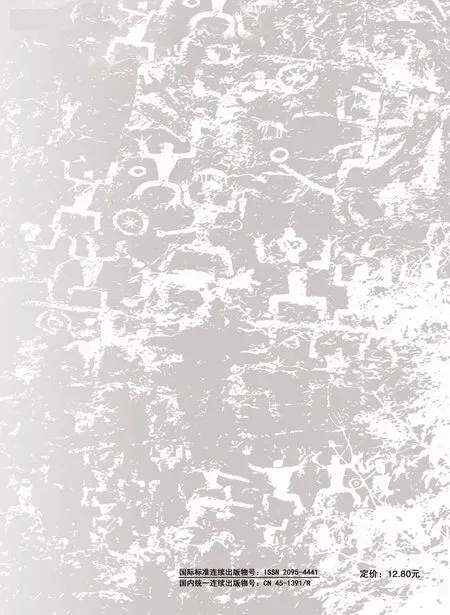概念辨类与译法择取
——中医术语“气”的英译再思考
2019-07-06郑鸿桥
郑鸿桥
(莆田学院,福建 莆田 351100)
《黄帝内经》为中医典籍始祖,号称“医家之宗”。它的翻译对于传播中华医学具有重大意义。中医理论以“气”概念为核心,以阴阳学说为基础。所以,“气”概念和“阴阳学说”翻译的规范性对《黄帝内经》的翻译有着根本性的意义。通过对《黄帝内经》各英译本的对照梳理,可以发现,作为中医理论的核心概念,“气”一词的翻译经历了21世纪前的意译为主到进入21世纪后的音译为先这一转变。
由于中医理论的哲学渊源,中医“气”概念集哲学意义和具体所指于一体,产生了与科技语言特征相悖离的模糊性(ambiguity)与多义性(polysemy)。姚振军[1]指出,中医用语标准化程度不高,名词术语的翻译是中医翻译最为混乱的一个方面。笔者选取《黄帝内经》英译本中影响较大、流传较广的李照国译本(下称“李译本”)和吴连胜、吴奇父子译本(下称“吴译本”)(两版皆为全译本),并参考倪毛信(Maoshing Ni)《内经·素问》译本(下称“倪译本”)、文树德(Paul Unschuld)译本以及艾尔萨·威斯(Ilza-Veith)《内经·素问》(前三十四章)译本进行比对研究,发现各译本对“气”一词的概念识解(concept construal)与翻译方法异态纷呈。以“诊法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故乃可诊有过之脉”(《黄帝内经·素问》之脉要精微论篇)一句当中的“阴气”一词为例,李照国译为Yinqi,倪毛信译为yin qi,吴氏父子译为Yin-energy,IlzaVeith译为the breath of Yin(the female principle in nature),难以统一。再比如,“因于寒,欲如运枢,起居如惊,神气乃浮”(《黄帝内经·素问》之生气通天论篇)一句当中的“神气”一词指道家所谓存养于人体内的精纯元气,李照国译为Shen-qi(Spirit-Qi),吴氏父子译为spirit and energy,倪毛信译为the spirit and the yang qi,IlzaVeith 译为 spirit and breath of life,不一而足。而核心概念译文混乱对于中医在国际的推广是相当不利的。
1 中医语言与科技语言的特征差异
科技语言是科学技术工作者用以表达探索自然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应用于社会生产事件的一种语言手段[2]。就词汇层面而言,科技语言客观而理性,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明晰的所指性,在同一门学科中,极少出现一词多义的现象。就文体层面而言,科技语言重推理论证和逻辑思维。而概念准确则是推理论证和逻辑思维以及正确判断的基础。
文学语言作为符号,具有具象性,和客体对象密切相关,但它又是经过作者主观审美情感改变过了的客体对象,诱发了客体对象的审美意蕴,扩大了它的能指,从而引起读者联想出更多的所指[3]。所以,文学语言往往包含着多种阐释的可能性。
就性质而言,中医翻译应属于科技翻译;其目的在于向目标读者传递医学知识。然而,就语言特征而言,中医典籍行文高度文学化,概念感性而模糊,与科学用语力求客观、严密、准确、简洁格格不入[4]。这其间所形成的张力(tension)正是中医翻译最令人头疼的问题。
2 概念辨类与译法择取
“气”理论作为中医学的核心,其翻译能否缓解上述张力,是中医典籍英译能否尽可能符合英语科技语言特征的一个关键。而要缓解这种张力,概念的准确性和明晰性则是关键。《韩非子·扬权》曰:“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辨类。”对于中医“气”这一宽泛而又复杂的概念,欲达准确与明晰,辨类不可或缺,这也是译法选取的关键一步。换言之,就是要先做好语内识解(intra-lingual construal),再进行语际翻译(inter-linguistic translation)。
王彬等[5]将中医典籍的“气”概念划分为哲学意义上的“气”、药性之“气”、症象之“气”、气候之“气”以及器官功能之“气”,并提出相应的翻译方法,比如对哲学意义上的“气”采用音译法;对药性之“气”、症象之“气”和气候之“气”采用意译法;对器官功能之“气”应用意译法,若用音译法,则应加注,在译为“…qi”的基础上,加上“the functional activity of…”予以注释。但对何为“具有哲学意义的‘气’”这一最为重要的“气”概念类别语焉不详。实际上,中医理论中的“气”概念是一个所指非常广泛,类型十分复杂的概念,在辨类上远不止上述五种。崔维强[6]将中医的“气”分为精微物质、生理功能、兼含物质和功能双重涵义、病邪、脉象、气血、气分、气候、节气、矢气、药性以及针感等十二类别。笔者认为,从翻译的角度来看,作为中医术语的“气”概念可从哲学概念和具体概念两类进行分辨,对哲学概念,音译为主;对具体概念,意译为先。
2.1 作为哲学概念的“气”
2.1.1 类别界定 作为中医核心的“气”理论,发端于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庄子》。其中所涉及的“气”在很多情况下抽象于其自然概念,属于哲学的范畴。《伤寒论》载:“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此句中的“气”是病者所能感受到的一种物质状态,属自然概念,所以,罗希文[7]依实将其译为 air。然而,与自然概念的“气”相比,哲学概念的“气”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被视为世间万物的本原或基本元素,而不再是一种可以直接感觉到的气体状态的物质[8]。王充《论衡》云:“天地气合,万物自生。”其中之“气”已非英文单词air或atmosphere所能对应。
作为构成万物的本原,气本为一,分为阴阳,称“阴气”与“阳气”;天气是自然界的清阳之气,地气是自然界的浊阴之气,人气是人体之气,具有本原意义。人气又称“正气”(Healthy Qi),《内经》称“真气”,《难经》称“元气”,由真气(先天之精所化生,故为先天之气)以及宗气(后天之气)构成,宗气又由水谷之精和自然清气化生。人气行于脉中而具有营养作用,称“营气”;行于脉外而具有保卫作用,称“卫气”;行于胸中,称“胸气”;行于脏腑中,称“脏腑之气”,如肺气(Lung-Qi)、胃气(Stomach-Qi)、肝气(Liver-Qi)和脾气(Spleen-Qi)等;行于经络中,称“经络之气”。上述各种称谓的“气”或为气的构成来源,或为气的体现形式,或为气的运行部位,归统于“气一元论”,是构成人体的最基本物质,维持人体的生理活动,故都应纳入哲学概念的范畴。
较早的《内经》译本都曾试图通过意译传达“气”概念(如the energy,the vital force等)。然而,意译虽提升了文本易读性,对于具有哲学意义的“气”概念而言,却往往未能尽释其义,或片面,或偏差,导致文本核心概念混乱,也导致文化异质性的消失。
2.1.2 音译理据 音译(transliteration)属于用译语符号转写原文之音以指称源语特有事物或术语的翻译表达手段,一般发生在源语文化有而译语文化无的情况下[9]。
拉温杜斯基(Lawendoski)[10]基于社会符号学和交际学将翻译定义为“从一套语言符号到另一套语言符号的‘意义’转移”。那么,中医当中作为哲学概念的“气”意义为何?万物之本原也。西医却认为“万物之本原”乃是原子(atom),然而我们总不能把“气”译为“atom”。这个差异源于文化,体现在概念,既然不可通约,那只能通过音译显化这个差异。李照国[11]就曾指出:“《内经》中的核心概念均含有浓厚的中国国情,且在英语当中没有完全对应之语。对于这样的概念和用语,音译加注恐怕是唯一可行之法。”
美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克里普克(Saul A Kripke)[12]提出了“因果链”(causal chain)这一概念。克氏认为,无论是通名还是专名都是固定的指示记号,都是由一条历史的、因果的传递链条决定的。这一链条就是“因果链”,也称“历史链”(historical chain)或“交际链”(chain of communication)。他还指出:一般来讲,当一个通名逐环传递下去的时候,其指称关系的确立方式已无足轻重,不同的讲话者可能会以不同方式来理解其指称关系的确立,但只要“所指”已确定清楚,这些差别也就无关紧要了。对于专名,情况也大抵如此。
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普特南(Hilary Putnam)支持克氏的“历史的、因果的指称论”,认为通名,比如水、电等的指称并不像弗雷格认为的是通过与这些名称相联系的概念而被确定下来的,而是取决于人们已经掌握的范例或规范。他进而提出了“引进事件”这一概念,认为当人们首次使用某个科学名词来指称某个事物时,这个首次使用就称为“引进事件”[13]。一个名称以“引进事件”为发端依次地发展为后来的使用,这就构成了这个名称通过历史和社会渠道传递下去的因果链。
我们可以用图示表达如下:

事实证明,在“针灸热”“功夫热”以及“汉语热”等“历史的因果链”的作用下,中医术语“气”的音译似乎已为英语语言文化所接受。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国际标准化传统医学词汇(2007)》将“气”译为Qi。《黄帝内经》在时间上较后的译本对具有哲学意义的中医“气”概念基本都采用音译(加注)法,比如以下2例:
例1: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黄帝内经·灵枢》之营卫生会篇)对于“营气、卫气、精气、神气”李译本译为“Yingqi(Nutrient-Qi)、Weiqi(Defensive-Qi)、Jingqi(Essence-Qi)、Shenqi(Spirit-Qi)”,译本译为“camp qi、guard qi、essence qi、spirit qi”。
例2:帝曰:“络气不足,经气有余,何如?”(《黄帝内经·素问》之通评虚实论篇)对于“络气”“经气”李译本译为“Luoqi(Collateral-Qi)”“Jingqi(Channel-Qi)”,倪译本译为“qi in the luo collaterals”“qi in the main channels”。
2.1.3 “气”概念音译存在的问题 对具有哲学意义的“气”概念进行音译有着语言哲学上的理据性和现实考量的必然性。但是,赵彦春等[14]指出,从符号学角度来看,音译只是源语言的语音转写,割断了符形、符指、符释之间的关系,导致文化信息丧失。笔者认为,音译固然已约定俗成,终究割断了语言符号与涵义之间的惯式关联,导致未能见词明义,且若不辨或误辨概念类别而一律音译,则有损文本语言科学性的构建,导致中医语言与英文科技语言特征差异张力依然存在,影响了译本的传播效果。如“春,气在毛;夏,气在皮肤;秋,气在分肉;冬,气在筋骨。”(《黄帝内经·灵枢》之终始篇)中“春,气在毛”,李译本译为“In spring,pathogenic factors tend to attack hairs”,吴译本译为“In spring,the evil energy is in the fine hair”,文树德译本译为“The qi of spring are in the fine body hairs”。可以看到,李译本和吴译本都将此句中的“气”识解为具体所指(致病因素)而采用意译;而文树德教授采用音译,造成主语所指模糊,句意不明。
2.2 作为具体概念的“气”
2.2.1 生成缘起 古汉语崇尚微言大义,讲究对仗(如“脉弱气微”)和韵律(如“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具有强烈的“美学意识”,但恐“字不工而害其句,句不工而害其篇”。所以,在中医典籍当中,“气”一词,除了上述的物构本原和病机病理等具哲学意义概念之外,另有诸多具体所指,如呼吸、脉象、气候、季节变迁、节气、病邪、药材属性等,或简略,或指代,而成“气”一词。
2.2.2 概念所指与译法 与古汉语相比,英语语言崇尚理性与自然。然而,正如刘宓庆等[15]所言,英文科技文献也具有审美客体的属性,也受美学意识支配,只是这种美识基于其语言的“理性素质”(rationality)之上。对于中医典籍文本而言,句子层和语篇层契合英文对应层级相对容易,所以,只要有意识、有选择地克服其部分抽象概念的模糊性,便可优化译本从词语到句子再到语篇三个层次与英文科技文本“理性之美”这一期待视野的契合度。表1归纳了《黄帝内经》文本中常见具体概念之“气”和不同译本译法。

表1 《黄帝内经》文本中“气”的不同译法
我们看到,除了例1和例2,对于另外7个例子当中的“气”概念,不同译者的译文较为一致,方法上基本都以意译为主,即使音译,也会另加注释(文内加注和/或文后加注)以明其所指。例9“芳草之气美,石药之气悍,二者其气急疾坚劲”一句当中,“气”泛指药材属性[16]。故直接译出“芳草”与“石药”属性特征即可,不同译者择词各异,方法却是一致。
例1“脉乱气微”一词,李译本译为irregular pulse and weakness of Qi,似有过度使用音译之嫌。此处,“脉乱”出自中医“切”之诊法,故译为irregular pulse;而“气微”出自中医“闻听”诊法,不同于“气虚(deficiency of Qi)当中的“气”,故笔者不揣冒昧,认为此处使用音译无此必要,可依实译为weak breath。实际上,在“肺气虚,则鼻塞不利,少气”(《黄帝内经·灵枢》之本神)一句当中,李照国教授就将“少气”译为shortness of breath。在“夫心胀者,烦心短气,卧不安”(《黄帝内经·灵枢》之胀论)一句当中,李照国教授也将“短气”译为shortness of breath。倪译本将“脉”和“气”合译为pulse似有不妥,乃属误译。
例2“因于气,为肿,四维相代,阳气乃竭”一句当中,李照国教授将“气”音译为Qi,但在文后注释中补充道:“Qi here refers to Fengxie(风邪)which means pathogenic wind.Gao Shizong(高 士 宗)said,‘Qi’means wind.‘Yinyang Yingxiang Dalun(阴阳应象大论)says,‘The Qi of Yang is named after the swift wind in nature.’That is why it mentions Qi instead of Feng in this sentence.”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在这里弃用意译而用音译原因所在。
然而,以上诸例还是表明李译本似有过度使用音译之嫌。作为大中华文库工程的一项内容,李译本负有保持与弘扬源语文化特色的责任,这一做法无可厚非。但笔者认为,从中医语言与英文科技语言特征差异的凸显与消弭之间的博弈而论,当以音译(加注)凸显具有哲学意义的“气”概念,以保留核心概念统一性,彰显文化异质性;以意译明指表具体所指的“气”概念,以削减其整体概念的模糊性与多义性,优化与科技语言特征的契合度,以利于文本内容的传播。
3 结 语
作为中医典籍始祖和中医理论集大成者,《黄帝内经》代表着古代中国劳动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与智慧结晶,对各类疾病的防治有着宝贵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但其语言的过度文学化以及核心概念的模糊性和多义性因悖于科技语言特征而一直为人所诟病,影响了中医理论在国际上的传播。纷杂的概念识解必然导致混乱的概念译本。笔者认为,为了缓解语言特征差异张力,有效传达中医典籍文本内容,对文本核心概念进行语内识解辨类而定语际译法乃是关键一步。这需要中医工作者和翻译研究与实践人员共同努力。